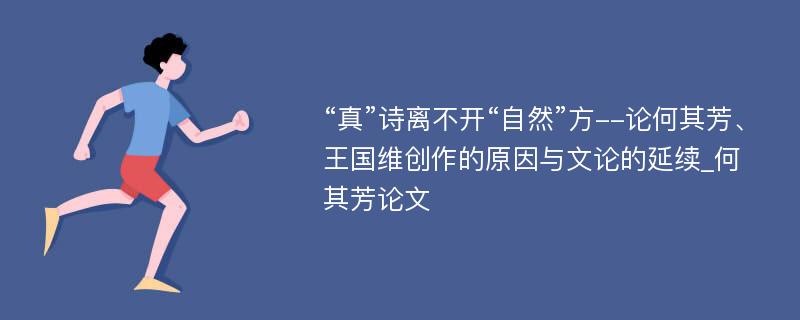
“真”诗“不隔”“自然”芳——论何其芳与王国维的创作因由与文论承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由论文,文论论文,王国维论文,自然论文,何其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何其芳与王国维放在一起比较,当然不只是“境界”①意义上的静态比照,而是基于以下四段论述。
一、语类意殊写佳篇:晚唐、五代诗词哺育了何其芳与王国维的创作
最能代表何其芳文学成就的是他的诗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其中所包蕴的晚唐五代气韵为人们所共识,他自己在散文《梦中道路》中也这样说:“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②有学者已论述过何其芳在选取“梦”的意象上与李商隐灵犀相通,和李商隐相仿,爱情是何其芳“梦”的主题,热恋带来欢乐,失恋伴着忧伤,还有韶华易逝的悲哀,但这些梦归根到底是美丽的、缠绵温柔而又有所向往、有所追求的,因而是年轻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③。何其芳从晚唐、五代诗词中所吸取的营养并不仅仅是“梦”和李商隐,晚唐、五代诗词所哺育的也不仅仅是何其芳,而是一个气韵生动、精致妩媚的文学传统,如王国维的《人间词》、《静安诗稿》也是这个传统链条上璀璨的一环。为了论述的集中与方便,下面我们先将《预言》与《人间词》的构成语言大体上按其确指意义分成若干类代表性的意象符号,然后再分析它们各自的独特意蕴。
何其芳《预言》:
(一)主体:我、你、年轻的神、少女、眉眉、小玲玲……
(二)状态:梦、睡、安睡、朝梦、梦话、酣熟、悄睡、睡眼、呓语、梦的边缘、辽远的梦、梦中、栖满、醉、微醺……笑(微笑、浅笑、欢笑)……哭(冷泪、哭泣、悲泣、流出眼泪、残泪)……
(三)空间:泰山、城阙、秋空、古城、古柏树下、屋顶下、巢、沙漠、田野间、都市……
(四)时间:冬天、秋天、夏天(长夏里)、黄昏(落日里)、夜、每夜、正午、日午……
(五)对象:爱情、树(柳树、垂杨、白杨树、菩提树、蓖麻树、松树、槐树、古柏树、森林)……花草(花、花瓣、花香、莲、槐花、石榴花、叶、梧桐叶、竹叶、草、衰草、麦冬草、新芽、绿荫、郁金香、含羞草、花朵、葡萄藤、二月兰、藤萝、芦苇)……动物(羊群、鹦鹉、蟋蟀、黄蜂、燕子、白鸽、鱼、骆驼、啄木鸟、乌鸦、蜗牛、狼、熊、蜂、鱼、鸟翅、蚕、蝶、鹿、鸟、流萤、巨蟒)……星星、月、风、日光、蓝天、太阳、天空、雷、云雾、冷露……金冠、蓝布衫、琴、幽光、明眸、积霜、朱唇、玲珑的冰、顺风的船、冻结的夜、砧声、寒塘、古波、金碧、罗衣、珍珠、露、手臂、危栏、阑干、土墙、瓦屋、锦匣、凉石板、重门、废宫、水车、镜子、宫扇、烟云、白帆、帘子、蜡烛……
(六)色彩:红色、虹色、粉红、朱、黄色、枯黄、金、亮亮、银色、素、绿、银、黑、油黑、纯洁、雪白、肥大而白、蓝色、幽暗、阴暗、灰色、青青、青色……
(七)感情:爱、伤感、悲伤、痛苦、恐慌、忧郁、郁郁、寂寞、静寂、枯寂、烦扰、忧愁、愁怨、残忍、怀念、挂念、忌妒、温柔、想念、喜欢、怀想、凄寂、叹息、朦胧、愉快、空虚、嘲笑……
王国维《人间词》④:
(一)主体:少年、思妇、婵娟、僧、他、侬、谁、自家、妾、君……
(二)状态:梦、醉、未醒、睡……朱颜红妆、年华、韶华……
(三)空间:天涯、严城、红楼、客中、故乡、高楼、高城、城郭、危楼、朱楼、层楼、寺、蓬莱、沧海、数峰、半山……
(四)时间:春、秋、今宵、良辰、一生、今夕、夜、长宵、明朝、暮、曛、昏、暝、阑、晚、曙、明、微茫、旧日、须臾、霎时、日日、平生、无限、年年、几度……
(五)形象:镜、月、影、泉、云、灯、光、星、水、波、溪、江、河、海、泪、露、雨、雾、云、霞、霜华、尘、蜡炬、蜡泪、烟、飞絮、纱、西风、轻雷、天、银河、斜阳、朝晖、夕阳……鹤、鸦、马、蝶、燕、雁、鹊、鸥、乌、鹃、鹂、鸢、鸡、鱼龙、萤、蝉、蜂……松、柳、萍、兰、杨、槐、桐、枫、竹、枝、草、叶、苔、花、落红、萸、菊、蕙、菰蒲……画船、绣衾、画屏、西窗、箫管、舟、孤帆、舸、画舫、棹、红袖、阑干、回廊、瑶阶、金波、银釭、朱阁、宫阙、路、桥、门、水晶帘、箫鼓、笙竽、高树、树杪、桐梢……
(六)色彩:白、翠、凉、黯、青、绿、朱、碧、紫、黛、冷、银、鹅黄、苍苍……
(七)感情:悲、愁、恨、伤、恐、怜、怨、悔、惊、愤、咽、苦、哀乐、旧欢、无聊……忆、相忆、思、相思、记、思量……斜、断、孤、顾、争、觅、回、落、离、闲、残、独、乱、细、栖、瘦、重、阔、空、低、疏、倚、傍、凭、别、回肠、峥嵘、寥落、狼藉、零星、迷离、突兀、窈窕、崎岖、厚薄、浅深……
即便这种分类比较粗略,但仍可清晰地看到何其芳的《预言》和王国维《人间词》的绝大多数语言都是这几类意象符号及其所衍生的同类符号的排列组合。
《预言》与《人间词》中的意象符号比较相似,而且有着相近的写作初衷与来源。只不过他们所吸取的西方营养,王国维更多地来自哲学,而何其芳更多地来自文学。晚唐五代则是两人共同的传统源头。这些意象符号也非何其芳和王国维新造,而是唐、五代、北宋以来中国词人所惯用的语言符号,似与某些“专作情语”的宫怨、闺怨、欢会、离别、相思、怀人等词甚至和“花间”题材都差别不大。在唐宋诗人与词人之中,王国维所激赏与何其芳所痴迷的对象也差不多,如冯延巳、温庭筠、李白、杜甫、苏轼、李商隐、李煜等。当然,因为时代和个人的阅历、思想境界不同,何其芳与王国维对这些类似于唐、五代、北宋诗词中的语言符号赋予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意义。何其芳的早期诗歌还体现出他对古代诗歌意象的现代点化。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诗歌的意象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什么样的意象就体现了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意象也就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倾向⑤。我们绝不能理解为有人所说的王国维“《人间词》的创作,走的是一条向唐、五代、北宋词的回归之道”⑥。
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这些类似的意象符号有着不同的指向与意蕴。倘若我们将所列的(一)类语言符号看作是《预言》与《人间词》之认识世界的“主体”,细究一下可发现,《预言》中的“我”就是抒情主体“我”,以及“我”与“你”(年轻的神、少女、眉眉、小玲玲)的对话。而《人间词》中的“少年”、“思妇”等并非作者主体之“我”,实际仍然是“客体”对象。虽然(二)类中最中心的状态都是“梦”或与“梦”相关的各种状态,但《预言》中赋予了“梦”或者“笑”(微笑、浅笑、欢笑)或者“哭”(冷泪、哭泣、悲泣、流出眼泪、残泪)等明确的表情。而《人间词》中的“梦”、“红颜”等却是(一)类“少年”、“思妇”等的主体,表现的是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形式中主体的感知。王国维是将梦作哲理的思索,何其芳是将梦作现实的隐喻。
《人间词》中的(三)类语言符号天涯、严城、红楼、沧海等空间意象与(四)类中春、秋、今宵、良辰、一生、无限等时间意象是主客体融合的意象,其感知的对象亦是主体“意志”的结果,空间比较朦胧而阔大,时间上着重无限与美好。《预言》中的(三)类秋空、沙漠等空间意象与(四)类中的冬天、秋天、夏天等虽然也是主客体融合的意象,但《预言》中的空间意象显得比较具体,而且空间比较狭小甚至局促,如古城、古柏树下、屋顶下等,而时间上除了象征勃勃生气的“春天”基本缺席之外,即使是冬天、秋天、夏天也往往是黄昏(落日里)、夜、每夜、正午、日午等,而缺失“朝阳”、“晨”等美好意蕴的语言符号。
《人间词》(五)类中的镜、月、影、水、云、纱等一系列相似的“象”,皆镜花水月,或似实而虚,或遥不可及,或易逝不定,或空无所依;鹤、鸦、马、蝶等“象”或高飞、或孤栖、或奔腾、或自由;松、柳、萍、兰等“象”,或高贞、或留别、或无依、或美洁;画船、绣衾、画屏、西窗、箫管等“象”则多是“宫怨”、“闺怨”之“象”。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表面上写的是“宫怨”、“闺怨”等内容,但基本不是抒写爱情。《预言》则主要通过一系列意象来抒写迷离的、隐约的、远去的爱情。《人间词》(六)类中的白、翠、凉、黯等“象”大多为冷色调,与前几类共同表现了(七)类中主体之悲、愁、思量、斜、断、孤、回、争、觅、峥嵘、寥落等要旨,即叔本华所谓意志的本质就是生命欲求“争斗”的痛苦、无聊、空虚。《预言》(六)类也多是素、绿、银、黑等冷色调,但也有少数的红色、虹色、粉红、朱、黄色等亮色,与前面的语言符号共同表现(七)类中寂寞少年的爱、伤感、悲伤、痛苦、恐慌、忧郁、愉快、空虚等青春主题。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王国维与何其芳都运用了晚唐、五代诗词的一些意象符号,却有明显不同。王国维主要用来表现哲思,是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观照下的文学;何其芳主要用来表现心理,是“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观照下的文学。王国维的《人间词》以儒道为“气”,以康德为“神”,以叔本华为“骨”,以传统语言符号为“象”,确实是“不屑于言语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的“天才之作”⑧。《预言》则近乎“青春的烦恼”,是从小孤独寂寞又远离现实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敏感年轻的读书人心路历程,是诗人画在“扇上的烟云”,独语青春的寂寞与感伤、苦吟渺茫的爱情与理想、咀嚼幼稚的欢欣与苦闷。何其芳的青春感伤在晚唐、五代的意象符号中不仅找到了心灵栖息之地,也找到了诗意的栖居。“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唐人的一些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⑨。
其实,何其芳与王国维还不仅仅是语言符号上的类似,而且还有其他有趣的类似之处。如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⑩王国维的《咏史》二十首便是无题诗,何其芳的杂诗十六首也是无题诗,只用前两字作题目。又如何其芳与王国维都好“戏效”,何其芳曾有标明“戏效玉溪生体”的七律《锦瑟》二首,王国维有“戏效花间体”《荷叶杯》六首,《人间词话》手稿扉页上还有“戏效季英作口号诗”六首。又比如,何其芳与王国维都好集句,王国维最著名的集句是“三境界”说,何其芳则在1964年11月作《有人索书,因戏集李商隐诗为七绝句》。何其芳与王国维都曾本李商隐的《嫦娥》而作诗,何其芳取自首二字的《青天》:“青天碧海太凄凉,不死嫦娥岁月长。何似人间儿女好,悲欢聚散俱如狂。”(11)王国维的《八月十五夜月》:“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12)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中说“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13)。这大概是他们灵犀相通的一个注脚吧。
为什么何其芳《预言》与王国维的《人间词》有着相似的语言符号却又不同的意蕴呢?这与他们的家庭环境、教育接受、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个性特点等关系密切,并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创作风貌与文艺观念。
二、表同里异言己志:何其芳与王国维的创作因由与文艺观念
何其芳和王国维小时候都孤独寂寞,一方面受着私塾教育,一方面养成自己读书的习惯,由爱好文学进而创作。他们的“独学”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创作的形式与主旨。虽然王国维酷爱哲学而何其芳讨厌哲学,王国维的《人间词》差不多就是形象的哲学,而何其芳的诗文里不可避免有哲思。何其芳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写道:“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小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一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和书本、和一些旧小说说起话来。”(14)虽然何其芳的私塾生活完全不适合儿童的智力与兴趣,但却因此开始接触到古代的诗歌,家庭生活的暗淡,被迫养成了他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唐宋诗醇》的阅读,不仅是何其芳第一次真正接触诗歌,而且真正被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所打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启蒙;上新式学堂之后开始接触冰心、泰戈尔等人的作品,是何其芳的“独学”时代。因一篇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作文,被乐育英才的国文老师将原名“何永芳”改名为“何其芳”,这是其文学创作的开始(15)。巧合的是,“王国维”也是由最初的“王国祯”改名而来。
王国维四岁的时候生母即去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七岁入私塾,“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16)。有意思的是,何其芳也认为他家占一个红色大书箱大部分位置的《十三经》不能作为儿童的课外读物。王国维二十二岁到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员,开始接触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尤其喜欢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在东文学社学习两年半之后到日本留学半年,又因脚气病归国,在日本教师藤田丰八等的指导下自己读社会学、心理学、名学、哲学等,这就是王国维的“独学之时代”。
何其芳的志愿是终生从事文学,他认为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了解人类思想的历史,所以在大学里上了哲学系。可是却事与愿违,“就西洋哲学来说,笛卡尔好像还可以念懂;康德就很吃力,念得似懂非懂;到了念黑格尔的哲学,就存心不好好念,干脆还它个不懂了”。所以一下课就“完全沉浸在文学书籍里”,“差不多把北京图书馆当时所有的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都读完了”(17)。无独有偶,王国维初读康德时也同样感到吃力,到二十九岁时“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到第四次研究康德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包括持处而已”(18)。
何其芳因为爱好文学而选择哲学,又因为哲学的枯燥而更加疏离了哲学而投身文学。王国维是因为热爱哲学而进入文学,又因为文学的成功而更加强调哲学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并用文学来表现哲学。王国维与何其芳都因为短小的诗词、诗歌散文的成功,而希望进行大部头的文学创作。何其芳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前期的《浮世绘》和后期的《董千里》都只写了十分之一左右就停笔了,而王国维的戏剧创作则还只是个构想而已。之后都进入到了文学评论当中,王国维有著名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何其芳有著名的《论现实主义》、《论〈红楼梦〉》等。王国维和何其芳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夹缝中坚韧地生长出来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的。
如果说家庭环境、教育接受、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等对何其芳和王国维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建构作用的话,那么个性人格与自我认同则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选择作用。王国维与何其芳都呈现着明显的紧张人格而对现实产生深深的焦虑感,这首先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得很明显,但有着不同的方式与内涵。究其他们各自在自己作品的形象,何其芳仿佛中国的“维特”,王国维好似清末的“名士”。儿时家教的严酷与私塾的无趣让何其芳的个性变得孤独与寂寞,基本上与人没有交往与对话,幸好后来找到了与文学的对话。如果说童年何其芳的孤独与寂寞来自于整日被“禁锢”在寨堡一样的家中,青年何其芳的孤独与寂寞则是自我意识凸显与实现自我评价之间的灵魂之战。他为之作出种种努力希望早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却总是不断地发现这之中的罅隙和差距。这是一种处于中心的边缘寂寞。生母早逝、严父期望、家道中落的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19),在时务报馆任书记员时曾有过一段非常寂寞苦恼的日子,主要是职业的繁杂与学业的不能精进之间的烦恼。研读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几年,正是王国维创作《人间词》的时段。因为填词的成功,王国维将对哲学的嗜好逐渐移向文学,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国维“疲于哲学有日矣”。其矛盾心理这时表现得极为明显:“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20)
毛泽东曾评价何其芳偏于“柳树性”,弱于“松树性”。何其芳自己认为是灵活性有余,而原则性不强。以此而论,那么王国维则属于偏于“松树性”,弱于“柳树性”。这种矛盾心理与个性人格也促使何其芳与王国维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生涯发生了几次转折。何其芳早期的《预言》、《画梦录》等是非常具有个人性与人类性的作品,由于他性格上的灵活性,使他在文学道路上发生了四次转折。第一次转折:《预言》、《画梦录》的“画梦”转向《还乡杂记》、《夜歌》等的“画人间”,在《夜歌》第三版时他说,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写的,有些是白天写的而外,还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第二次转折:由“画人间”转向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次转折:由完全的阐释与维护《讲话》转向建构“典型共名说”与“中间性作品”的文艺理论观,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讲话》框架内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大一统文艺思想。第四次转折:希望将自己的文艺思想与文艺理想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一部中国文学史,一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也想写点诗,甚至搞翻译。
虽然王国维同何其芳一样有着紧张人格和忧郁个性,但他在读书态度、学术转型甚至最后选择上都和何其芳不大一样。王国维最早的兴趣在哲学方面,然后因为填词成功而移向文学,最后在国学上蔚成大观。其《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等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文论方面的“境界说”最有影响,而美术应“表人类全体之性质”的理论则后继乏人,但何其芳是其中之一。
三、虚批实承创共名:何其芳对王国维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何其芳在文艺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典型“共名”说,这个观点在王国维的文艺理论中能找到确切的来源。何其芳早在1944年的重庆写作的《“自由太多”屋丛话》的第二篇《文学无用论》中就批评过王国维的“文学无用论”:“王国维先生一代名学者,早年所作文学论文,亦颇为世人所称道。但近读《静庵文集》,其文艺思想似并不高明,《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一文中,他开头即说:‘天下有最神圣最高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后面说中国的哲学家如孔、墨、孟、荀都想兼为政治家,诗人如杜甫、韩愈、陆游都有经世济民之抱负,而此为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哲学的事情我不大懂得,杜甫则是我佩服的大诗人,我要为他说几句话。”(21)
有用与无用,王国维与何其芳在字面上有着不同的内涵。在《讲话》“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理论指导下,表面上何其芳强调的正是“当世之用”,我们的文学有用论是主张文学为大多数被压迫者而用,为“唤起民众”而用。从主动要求到前线去,短时间内却黯然离开,自觉是个无用之人,何其芳的心里别提有多沮丧了。这件事后来成了他无法了却的一块心病,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忏悔:这是一个可羞的退却,这是畏难而退,“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何其芳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如梦初醒,尽管他早就写了很多优美的作品,但他却感到“我过去一直还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搞过文艺”,“我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都实在太狭隘了。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何其芳到延安之后,不仅觉得自身“无用”,而且觉得当初的文学也是“无用”的,因为何其芳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投入到政治革命中,由此获得了“用”的意义,他也能以此为资本,进而批判了王国维的“艺术无用论”(22)。所以他曾这样评价他的成名作《画梦录》:“那本小书,那本可怜的小书,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为他制造的一些玩具。”(23)
即使在这篇文章中,何其芳也部分地接受了王国维的观点。王国维所谓“无与于当世之用”(24)的意思并不是说哲学与美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美的艺术)无用,而是说不能成为当世工具之用,而应为无用之大用。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则表达得更为明显与痛切:“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25)何其芳在《文学无用论》这篇文章的最后说:“这就是越能说出历史与社会之真实者越有用;越能说得艺术手腕高,即越善于表达与感人者越有用。”(26)如果我们把几篇文章对照起来阅读,仿佛何其芳的“文学有用”正给王国维的文学“无用之用”做出了注脚。
何其芳对王国维文论观点的虚批实承最有说服力的是《论〈红楼梦〉》。他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关于这部巨著的第一篇正式的认真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推崇《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并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比。然而它对于这个大著述的内容的解释却是错误的。王国维不去肯定这部小说里的对于人生的执著和热爱以及对于不合理的事物的反对和憎恶,却把它和西欧资产阶级悲观主义哲学牵合起来,说它的思想价值在于鼓吹“解脱”和“出世”(27)。何其芳首先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这就是何其芳对王国维文论接受与发展的最好证明。何其芳认为王国维对内容的解释是错误的,这是其受到革命文论的熏陶尤其是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之后的产物。当然,王国维的解释主要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的角度入手,也有他个人与时代的片面性。
典型“共名说”最早就是在《论〈红楼梦〉》中提出来的,而不是在《论阿Q》中提出的。《论阿Q》文后注明是1956年9月24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而作,《论〈红楼梦〉》是1956年8月至9月初写成前八节,10月至11月20日续写完。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在同一时期。按照何其芳的自注,“共名”说应该是最先在《论〈红楼梦〉》中提出的:“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典型人物,它们那样容易为人们所记住,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正是由于它们不仅概括性很高,不仅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特征以至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而且这两者总是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中国的和世界的许多著名的典型一样,贾宝玉这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了一个共名。”(28)“共名”的雏形其实在1954年写作《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时谈到“马二先生”在现实中的两种称呼就已经有了。有学者对“共名”说做过比较精当的分析:“‘共名说’由此扩大了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内涵,在当时流行的对典型人物指认其阶级性之上,扩充和增添了指认其更丰富多彩、更有血有肉的人间性,并且把这种人间性作为‘名’之所‘共’的标志。也就是说,‘共名’是指遍及诸阶级、阶层的人类性或人间性性格特征的。这就不仅为解释文学名著中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有效的观察方式,还为分析文学作品中的那些并不十分典型、却有着比较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找到了一条可能性的途径。”(29)
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的基础在于真正的文学典型“不仅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特征以至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30)。这正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真正的美术应该“表人类全体之性质”的继承与创新:“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31)何其芳在文中多次强调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与典型行动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即使某个时代和阶级都已经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成为历史,但如贾宝玉、林黛玉、刘姥姥、阿Q这样的“共名”却仍然可以在生活中存在。而且还特别指出,世界上概括性很高的典型都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共名”就是对“人类全体之性质”的一个生动注脚与发展。“这些描写是这样重要,它们成为全书的突出的内容,并从而使全书闪耀着诗和理想的光辉”(32)。
何其芳还继承了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的悲剧理论。王国维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而何其芳说是双重的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曹雪芹把双重悲剧写在一起,它的意义就更为深广了……只有王国维那样一些自己原来有浓厚的悲观思想的人,才会把它局部的东西加以夸大,说它是旨在鼓吹‘解脱’和‘出世’。”(33)何其芳与王国维的分歧在于王国维鼓吹解脱与出世,而何其芳则认为是反封建。何其芳和王国维在对《红楼梦》主旨的问题上虽然看法不同,但艺术上的见解却罕有的一致。
何其芳提出“中间性作品”的理论是对典型“共名说”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整风”之后自己的文艺思想的一个修正。他认为:“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中间性的作品。”(34)简单地说,“中间性作品”暗合王国维提出的“不隔”、“通”等文艺观点,“不通”就“隔”,就“滞碍”。
然而,何其芳后来却忽视甚至否定了自己早期的那些“中间性作品”,到了延安之后,尤其是《讲话》之后,他提出“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35)。不过,何其芳永远都没能够成为一个他自己心目中和别人心目中的兵士,他陷在所谓的“思想上进步与艺术上退步”的“何其芳现象”中,自己跟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
四、用王国维的文艺理论重新阐释“何其芳现象”
如果说在地位与学术鼎盛之时的“王国维投湖”成其死后的不解之谜,那么“何其芳现象”不仅是别人而且是他自己大半辈子的难解之谜。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何其芳现象”的核心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笔者通过何其芳与王国维创作因由与文艺思想的比较,认为“何其芳现象”固然表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根本的疏离却是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全体”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与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小我”与“大我”问题。
为什么何其芳总在作检讨呢?为什么总是对自己作品的内容那么耿耿于怀,但又总忘不了那种精致的艺术的琢磨呢?何其芳的悲哀之处在于他不停地否定自己和肯定自己,这是一种难言的焦虑与撕裂。何其芳的这种矛盾终其一生,本来在到延安之前他的目标与思想都是很单一的,但后来一方面要做“革命”者,做“无产阶级”,做“人民群众”,另一方面灵魂深处却时时要做回“自己”,所以他总是矛盾的、冲突的、纠结的。毛泽东的《讲话》在何其芳的文学生活中的影响太大了,或者说这个影子太大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何其芳文论的航标,但往往却又在不经意间或本能地将艺术标准放到了第一位,所以难免产生裂缝。问题的关键在于,何其芳相信毛泽东的文艺标准是那样的虔诚,而他自己的文艺标准又是那样的顽强。何其芳于1976年9月21日下午写的《西湖》恐怕也是自己无法兼具内容与形式的两美而发出的无奈感慨:“应有高才兼两美,胸吞山态水容妍。”(36)何其芳在《回忆、探索和希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一文中写道:“只要他们的作品描写了人生的某些有意义的方面,而且写得很优美,我们今天也仍然由衷地喜爱,同样把它们作为遗产来接受。”(37)他最担心的是成为“口头上赞成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而行动上却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其中有些人甚至用作品来嘲笑和攻击劳动人民”(38)中的一个,所以他对自己多有苛求,即希望人民性和艺术性合二而一,但他又总不能真正地融入与融合,不能“不隔”就不能完全“真”与“自然”,因此这苦恼困扰了他一生。何其芳对人民性的认识还是很开阔的,但到了他自身的作品上就无法将内容与艺术协调一致了。
有人认为,何其芳《画梦录》时期的散文,如果我们超越时代,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思想情调大半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艺术上的精美动人,却也是今天的许多散文(包括某些被称为优秀之作的散文)所不可企及的(39)。这样的认识在我看来既是正确的无疑又是错误的,恰如王国维所言,真正的文学(美术)是应该表现“人类全体之性质”的,前期的何其芳无疑是以纯粹的“诗人之眼”观察与反映自然、社会与人,而后期的何其芳试图以“政治家之眼”来创作,但他终究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所以他的创作也便保持了一些诗人的真与自然。他的文学评论主要是特定阶级和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因为他有着长期而丰富的创作经历,因此也就能沙里淘金。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何其芳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何其芳后期有意地疏离了文学人情的、非功利的、审美的“真、自然、不隔、有境界”的文学本体,而刻意地开掘文学政治的、功利的、有用的文学。当然,尽管何其芳在许多文章中虔诚地检讨自己的文学与革命结合不紧密、自己的思想改造得不彻底,但因其最早的文学之路是自然萌发的,是擅长幻想的,是喜欢做梦的,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仍然保留了自然与真的因子。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理论一个最重要的立足点就是文学应该具有“人类全体之性质”,这也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之所以成为现代转型期文论经典的重要原因,或者可以说,王国维不多的几篇文学批评都在致力于将文学从政治的、功利的、有用的传统文学创作和批评观念的隶属之下解放出来,还原其人情的、非功利的、审美的“真”、“自然”、“不隔”、“有境界”的文学本体。何其芳在后期否定了前期《预言》、《画梦录》等,认为都是个人“小我”,进入延安之后希望表现“大我”。从王国维“美术”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恰恰是“小我”表现了人类全体之性质,而“大我”则局限于“工农阶级”,表面上是群体,但却只是人类的一部分。
王国维所强调的是诗人(美术家)、学者的独立与自由,而何其芳到了延安之后,则总是在不断改造之中,但是无论怎样改造都不能如意,要么是自己不如意,要么是不符合别人的(政治的)标准,两者都表现出了深深的焦虑与无奈,“松树性”居上的王国维最后选择了自沉昆明湖,“柳树性”居上的何其芳虽然表面上没有如王国维那般决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马上就写了很多应时的诗歌,并且热切地重新投入到管理与创作的工作之中,希望自己能够再次真正地回归到文学家的本位上来,但天不假年,1977年就因病不治,但就其深层原因来说,何其芳的“早逝”实际上是必然的,他拼尽全力憧憬希望地活着,一旦希望降临,他就耗尽活下去的力量了。
何其芳在逝世之前咏家乡重庆万州的太白岩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李杜操持事略同,天然毕竟胜人工。”(40)这或者可以看做是何其芳的自我追求与评价吧,“真”诗“不隔”“自然”芳!
注释:
①温兆海、张克军:《何其芳早期诗歌之“境界”论》,载《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②⑦(11)(14)《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215页,第215页,第356页,第2卷第214页。
③董乃斌:《超越时空的心灵契合——论何其芳与李商隐的创作因缘》,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④下面对王国维《人间词》的分类及部分分析摘引自拙作《人间总是勘疑处——现代转型期文论经典〈人间词话〉的写作》,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53页。
⑤高阿蕊:《从扇上的云到地上的歌——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载《渝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⑥吴蓓:《无可奈何花落去——以文本为基点论王国维〈人间词〉》,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
⑧拙作《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学熔铸而成的“天才之作”》,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⑨《何其芳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81页。
⑩(12)(13)(16)(18)(19)(20)(24)(25)(31)《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上部第83页,第150页,第87页,下部第282页,第282—284页,第283页,第282—284页,第3页,第95页,第12页。
(15)(17)(21)(23)(26)(27)(28)(32)(33)(34)(35)(36)(37)(38)(40)《何其芳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卷第316—319页,第320—321页,第2卷第111—113页,第72—83页,第113页,第3卷第294页,第306页,第287—299页,第294页,第5卷第216页,第1卷第418页,第6卷第160页,第4卷第179—201页,第179—201页,第6卷第163页。
(22)以上引文参见王雪伟《何其芳的文化心理》,载《名作欣赏》2008年第3期。
(29)杨义、郝庆军:《何其芳论》,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30)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39)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