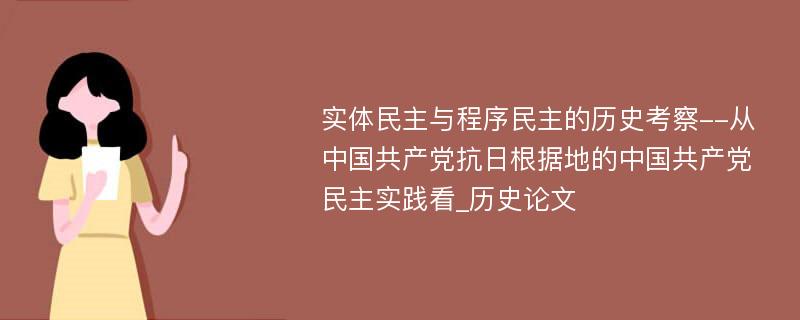
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透视论文,实体论文,中共论文,抗日根据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期间,只有3万余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从从陕北和江南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内中原因甚多。一些学者往往强调中共当时对外部条件的利用,如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冲击造成的地理和政治空隙,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等;其实,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努力是更为紧要的条件。其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所作所为,对老百姓在国共之间进行对比并作出选择,对中共整合根据地内部的抗日力量以维持长期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民主(注:在2000年9月于南京召开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先生曾就此处“民主”一词询问其内涵。笔者认为,民主,简言之,就是人民做主,人民介入政策的酝酿和形成过程。而“有无健康有力的反对党,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否公开、公平、公正,政权之转移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等西方政治学标准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尤其重要的是:讨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民主,必须考虑离当时并不遥远的封建时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新四军、八路军到达根据地前的社会政治现实。),是现代几乎所有志存高远的政府、政党的主要政治诉求之一,可分为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所谓实体民主,主要指民主在制度层面的规定,比如一般国家或政党都会规定要保护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权利;而程序民主,则是将这些制度性规定变成现实的结构和渠道。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尝试以选举、“三三制”、参议会等构建在战争环境中实行与推进民主的基本框架。应该说,他们在早期革命实践中缺乏类似的经验,因此,在把民主理念变成民主现实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出富有特色的程序,使民主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具体可观的实际存在。也就是说,在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之间开辟了一条影响深远的道路模式。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取得广泛支持、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一
现代政治运作离不开民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意是最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日伙伴,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具有逻辑上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但中国的政治现实并非全是按逻辑发展的,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承认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它们也经常尝试局部地取消中共领导的军队或根据地的合法性,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8年间经常地处于关于合法性的“焦虑”中。为解决合法性的问题,中共方面直接引进民意。各根据地实行的选举和“议会”或“准议会”制度,是民意运行的平台,也是将民主从规定转变成现实的管道。
早在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即获通过,《纲要》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员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得边区议会的同意。乡代表会及乡长每6个月改选1次,乡代表会每月召集1次;区议会及区长,每9个月改选1次,区议会每2月召集1次;县议会及县长,每年改选1次,县议会每6个月召集1次;边区议会主席、法院院长每2年改选1次,边区议会每年召集1次。各级议会除选举行政长官外,可批准预算、创制或批准各项建设计划、决定征收各项地方性的捐税及发行地方公债、议决边区内的单行法律(其中前两项权力专属边区议会)、召回所选出的行政长官等;边区议会内设少数民族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注:〔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5月12日,1941年5月1日。)。
根据以上规定,陕甘宁边区1937年组织了民主普选,参选率达70%。从选举结果看,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但地主、富农等过去被排斥在外的群体进入了参议会。在固林、延长、安定、曲子等4县的选举中,县级参议会里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分别占4%、65%、25%、1%、1%、2%、2%,区级分别占4%、67%、22%、2%、1%、2%、2%,乡级分别占5.6%、71.4%、17%、2%、2%、1%、1%。对此,李鼎铭曾盛赞说,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英美比较,“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延安〕《解放》周刊第68期。)。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选举林伯渠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共28条。陕甘宁此后在1941年、1945年先后组织过两次普选,完善了议会制度,成为其他各根据地的典范。
民意本身包含着对广泛性的要求,将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纳入民主体系之中,是中共方面的追求。“三三制”的实行体现出的这一追求,是各根据地选举和议会制度中的重要因素,是根据地进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开创性尝试。1940年3月,中共提出实行“三三制”的构想,随即在绥德、清涧、吴堡等地进行了实验。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了“三三制”的具体内容:“(共产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注:〔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5月12日,1941年5月1日。)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在选出18位边区政府委员时,共产党人数略超1/3,徐特立即主动退出,由无党派人士白文焕递补。这标志着“三三制”进入实施阶段。
各根据地在实施“三三制”的具体过程中,并非没有缺点。比如在苏北根据地,“参议会总的参议员成份还是可以满意的,只有个别的县,不大注意这个工作,随便找人凑数的现象也是有的。如像16个妇女参议员,大体上说来就没有工、青、农的参议员好,有的把县政府的女会计拉来凑数,而并未把那个县的妇女活动分子选出来。”(注:李一氓:《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总结》,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但是,上述缺陷是局部和个别的现象。通过“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表达了自己对民意的理解,显示了建设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诚意。《豫鄂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为保证共产党员参加各级竞选之候选人名单中及政府机关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起见,同意共产党员如超过三分之一时,其超过者自行退出,俾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之一切人民,只要不投敌者,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及民意之活动。”(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内部资料)第3辑,〔郑州〕《政权建设专辑》(一),第7-8页。)中共不仅这样规定,也是这样做的。很多地方,甚至突破了“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三分之一”的规定,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安塞、绥德、吴堡、米脂、合水、镇原、环县、新宁等8县中,共产党在乡(市)参议会中分别占18.4%、13.8%、29.1%、18.2%、29.3%、15.4%、27%、25.1%(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选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在晋察冀,国民党驻边区的联合办事处主任郭飞天被选进了参议会(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总结》(1943年1月24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由于有这样的诚意,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各阶层的热烈拥护,也给中国其他地区树立了建设民主政治的良好榜样。比如在晋冀鲁豫根据地临时参议会中,有国民党人士50余人,邢肇堂、宋维周为副议长,石磺为驻会参议员。其中邢肇堂曾任国民党新5军副军长,他曾说:“我是孙总理的信徒,那里有真的三民主义,我就到那里。”(注: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内部资料)下册,1980年,第295页。)由于“三三制”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高层领导曾设想建立“三三制”模式的民主共和国。林伯渠甚至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由这‘三三制’坦途走向民族解放以至于最终的人类解放。”(注:转引自陈志远、王永祥:《抗日根据地政权“三三制”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抗日战争后,由于种种原因,“三三制”未能继续普及实施,但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中,可以看到“三三制”的历史遗存。
二
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政正是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批评对象。所以,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明确表示:“我们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也不主张共产党一党专政。”(注: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节录),《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在不搞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既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要保障民主的实施,这对中共的党团运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国家议会中的党团操作。
美国议会中党团会议是政党的组织基础和政党领袖的权力来源,党团会议选举党的领袖,通过党的规则,确定党关于立法的立场(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页。)。党团之下,则有党的议场发言首领和督率员。众议院多数党议场发言首领“是关键性的战略家,是议长的主要助手……他与议长及众议院规程委员会共同安排辩论日程,并同各委员会主席及关于程序事项的本党成员商谈程序事项。他收发有关多数党议员的情报,如总统属于本党还要说服本党一般议员与议会党的首领和总统意图一致。……众议院少数党发言首领……领导反对党。他常要同多数党首领合作安排议事日程。当一场辩论将要进行时,常由两党首领一起会商分配双方发言的时间。”参议院中也有同样的安排。两党皆有督率员,“议场发言首领通过督率员在议场上经常与本党党员联络,了解其思想情况,并使之能采一致行动。督率员的任务很多,例如本党最近提出讨论的案件常由他事先通知,本党领导的意图常由他传达,本党的纪律常由他维持,遇有重大问题须付表决,也由他督促本党成员出席,按本党首领意图投票。”(注:曹绍濂:《美国政治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131页。)
美国议会中党团操作的程序说明,民主决非让每个人任意自由表达意见,而如因自己的个人意见未成为定论便说某种政治系统不民主,更属幼稚。中共在操作民主之时,即非常成熟,他们显然注意到了党团的作用和应有的规范。曾任苏北抗日根据地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的李一氓认为,在民主实践中,党团意见一致“特别重要”。他说:“这不是说对于某一决定之前在党团内的意见就要一致,而是说:(一)有一种是某项问题,事先毫无商量,而临时在会场上引起争论。在这种争论上,我们有一定的态度,因此首先要求党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二)另一种是某项问题,事先虽有决定,但没有通过大家,而且当时也认为小问题,就如此决定罢,临了在会场上引起争论,而党团又不依照最初决定,以致党团内的同志发言,亦是赞成与反对两方的意见,这就使其他党员无所适从”。他承认,“最好的党团也不能对于每一个争论,都有事先的预见,而就先讨论出一致的决定来的”,因此有两个办法:一是在会场中以党委书记或党团书记的意见为准;二是“对某项问题指定以某同志的意见为准,如讨论财政问题的,以某同志的意见为准,讨论军事问题又以另一同志的意见为准等。”(注:李一氓:《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总结》,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根据地不仅注意到了党团运作在民主运作中应有的地位,而且作了实际运用。在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党团进行了四方面的运作:一是提候选名单时为了达到名单平均分配于各阶层和各县的目的,党团决定在士绅提出候选名单后,再提出自己的名单,以便分配自己的票源;二是因为工、农、妇参议员文化程度较低,“不认识字怎么圈呢?”“因此在圈的时候,可以分为几组,某组以某人为准,大家依照他的圈法来圈。”第三是采取措施保证中共方面的选票达到多种目的,“假如我们希望选出某某等19人,我们的全部选举票都投这19人,就会有这样的毛病,支配的显然了……譬如某些士绅,估计到别人也会投他的票的,我们就少投些,而有些又是别人不会(或仅少数)投他的票的,我们就多投些。或者,我们只指定我们自己定要投那15个人(以19人为例)而其余4人就让他去自由选择。这就会把我们投的票变为无数形式,而不会完全清一色了。同时,也保证我们希望被选的人,定会选出了。同时,也保证我们自己的票会得最多数,而不会过甚的集中某某士绅的票,而使他胜过我们了。”(注:李一氓:《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总结》,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30页。)
根据地操作民主之时,正是“三三制”运行之际。在共产党员人数仅占1/3的情况下,党团运作成为展示力量的重要渠道。在淮北区的党政军民各届人士联席会议上,中共方面事先估计会议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多数地主士绅可能抱“听而不讲”与“讲亦无用”的态度,不肯说话;而右派可能会在会上发言,抨击抗日政府。于是党团决定对前者“随时启发,使他们由试言而至真讲”;对后者准备作为会议的高潮,并促成这种高潮的出现。会议开始后,“关照党员不得自行发言”,结果在右派发言后,这些党员群情激愤,党团又决定了发言反击的原则:“第一他们如果批评我们毛病确系事实,应坦白承认;第二如果他们夸大我们的毛病,应切合分量地予以解说;第三他们如胡言乱道,应根据事实给以对照,但并不责骂与打击;第四我们可以历史根源社会原因等与个别的现象,来泛论地主士绅方面的不对地方;第五我们从正面来检讨我们在抗战与民主建设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结果,在一些中共党员被气得脸色“转青翻白”的时候,右派估计中共方面可能会有人跳起来反驳,但实际情况是中共代表发言时表现温和,“没有带些意气”。这就使“有的人在私议中认为他们自己说话是多么‘乱嘈嘈’,而我们党员是多么守纪律,有规矩,要么是不说,说了又是多么近情近理。由于对我们恢复了信仰,特别觉得刘主任的发言非常明确清楚,反过来对国民党的幻想也就更打破了。”(注:冯定:《淮北边区党政军民各届人士联席会议总结》,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内部资料),第2辑第2册,1985年版,第221-222页,第215页。)
然而,根据地中党团运作毕竟经验缺乏,在成熟度上显然不能与英美议会中的党团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被动和民主启动时期常见的稚嫩。比如,在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1942年)上,据李一氓的总结,“党团在这次参议会上没有组织得很好”,首先是名单没有包括县和军区的同志;其次是党团与支部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特别在选举上,决定得过迟,使支部党员对于选举毫无主张,很难做会外活动、时时他问,而实际则党团自身也还没有定见。”党团组织不得力,直接导致会议的失控危险。在召开临时参议会的程序问题上,有人主张“参议会经1/3参议员请求时得召开临时会”,另有人主张“经1/3参议员请求、驻会委员会之同意者”召开,“结果,两方面都有我们的党员,互相对垒,最后表决时,也是各表决各的,后一主张仅以多一票通过。”(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非独淮海区如此,晋察冀根据地在运作民主时,“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某些同志还注意不够,以致发生某些不良影响,例如印发政府候选人名单时,我们计划的当选名单,恰恰在名单的前几名;某同志在台上向台下进行选举举例说明时,恰恰又是我们布置选举的人名来举例。台下有些非党人士反映,‘这大概是暗示我们选举这些人吧’。”(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总结》(1943年1月24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301页。)淮北区虽在事前有所准备,但“技术”性缺憾仍然不少:“对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右派分子的认识,个别的并非不知道,但作为整个党团来说,在开始时是不明确的……直至个别右派分子发言后才重新搞起来,这是党团领导上的最大缺憾。”其它如党团与一般党员脱节、会议中小组长活动突出、党员与干部暴露等均有存在(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三
民主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制度民主和现实民主之间,怎样调动人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投身民主实践,关系到民主是停留在纸面上作为政客欺骗民众的诱饵还是成为人民衷心拥护的目标和理想这一关键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已经用“中国民众文化教育程度低下,没有经过民主的基本训练”等类似的借口一再推迟“宪政”的施行,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扎实具体细致的工作,引导民众对于民主实践的兴趣,调动他们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入民主运作的热情,从而为根据地的民主打下深厚的基础。
中国基层民众曾被视为民主的荒漠,他们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下失去了对民主实践的兴趣。根据地运作民主,第一步工作即是唤起他们内心对民主的渴求。为了做到这一点,根据地艺术性地选择了小而具体的切口。比如,在淮南根据地的殿发乡,进行选举以前,用红白榜分别进行选民登记,不合格的登记在白榜上。其中有个“刚来此地不及两年的曹四,从贴出起就仰着头在看,后来人散得稀稀落落了,他还在看。最后天黑了,他又打着灯看,可是他失望了,原来榜上(指红榜——笔者)没有他的姓名。他气喘喘去找本村干部,说:‘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又大家都在农抗,你们有什么意见,尽说好了,何必叫我过不去呢?’干部摸不着头脑说:‘什么回事,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意见!’他继续城恳的征求意见,说‘不是公民就不是好人,你说了我好改。’怎样问下去,才知道榜上漏了他的姓名。干部答应他明早替他补上,他是半信半疑的转回去。第二天大清早曹四又至干部家要求添名字,因为没有毛笔就用钢笔替他添上了曹四两个字,可是他觉得和别人不同,不放心。终了由他自己去找了毛笔来,请干部描得大些,这才满足了他的要求。”(注:刘顺元、冯定:《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271页。)
选民意识的高涨构成中国民主史上的真正变化——曾经游离在民主之外,对民主毫无切身认同感的基层民众表现出积极介入民主运行过程的巨大热情。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经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有的则到处宣传某人的坏处等等。又如安塞四区一个乡长因工作消极,蟠龙区一、三、五乡乡长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等,均遭反对为候选人。至于那些平日对抗战工作努力的分子,在选举中都当选了。”(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延安〕《解放》周刊第68期。)
在唤起基层民众参与民主运作的问题上,除了国民政府方面前述悲观的论调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国民政府的批评者,但总是强调国民政府方面应作出“给予”人民民主的承诺和时间表,而没有认识到民主决非“施予”所能成为现实,更没有设计出可供基层民众操作的具体方案。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例如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韩兆鹗提出了他的“迎头赶上”民主潮流的办法;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身体等自由;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对一切文化经济事业,提高人民之自动性积极性;废除保甲长委任制,实行民选(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33-934页。)。上述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中国基层民众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根据地在唤起民众的过程中,显然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切合农民的生活实际,把民主变得通俗易懂,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前述的殿发乡选举,选举委员会将候选人名单贴在4家办喜事的人家门口,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选举时准备特备的红大芦林,被选举人后面放个碗,不许回头看,选举人中意谁,就将芦秫投入其后的碗中(注:刘顺元、冯定:《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73页。)。另据其他学者研究,根据地选举投票还有“画圈法”、“背箱法”等,以符合基层民众的需要,一位民主政团同盟人士对此评价道:“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注:转引自陈志远、王永祥:《抗日根据地政权“三三制”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250页。)
民众的唤起和对民主的介入,与他们对立面的态度在事实面前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农民曾长期处于“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东西不自主地往下落”的精神状态之中,而地主士绅开始也对民众介入民主操作冷嘲热讽,加以敌视。他们宣称基层民众“不识字,家里又没办法,过去又没干过事,这些人办不了事”,说什么“老粗也要上台了,赤足汉要当咱们的上司,得了嘛!”“选什么东西,还不是老一套!”但他们最终承认,“这回是民主。”(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选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137页;刘顺元、冯定:《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淮南抗日根据地》,第273页。)这些人态度的变化,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民主热情。像陕甘宁边区,“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平均是百分之八十,绥德、清涧、延川则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86-87页。)相比之下,1960年到1980年美国6任总统的选民投票率分别为62.8%、61.9%、60.9%、55.5%、54.3%、51.8%,近半个世纪中,中期选举的平均投票率低于42%(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1页。)。
当然,根据地的民主运作仍处于幼稚期,在设计有中国特色的唤起民众之路时,也免不了留下一些缺憾。比如当时流行的“投豆选举法”,虽方便了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但安娜·路易丝·斯特郎在目睹这种办法后提出疑问:“豆子人人可自带,因而从中作弊的可能性愈大,选举的真实程度愈低。”(注:李寿葆等主编:《斯特朗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90页。)而基层民众的民主热情被唤起以后,更有必要正确引导,以促进其政治成熟度。在苏北根据地,中共方面就承认“农民参议员发言太多、太猛,没有选择时机,过于尖锐……如在讨论公粮时,说地主‘少吃几顿猪肺汤就够缴公粮了’,是不好的。”(注:李一氓:《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总结》,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标签: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根据地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三三制原则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三三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