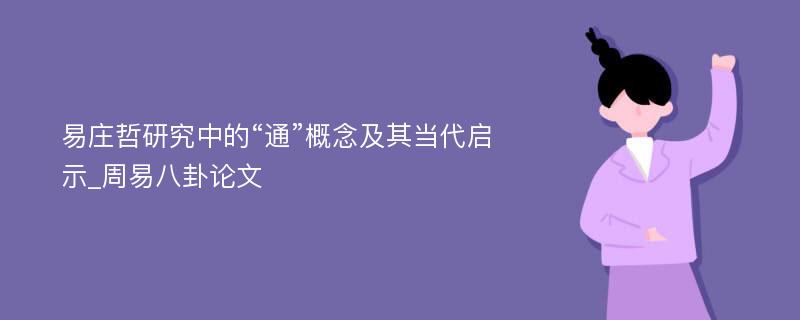
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学中论文,当代论文,观念论文,庄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2)03-0003-10
“通”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也是作为世界之问题,是中国自晚明以来与西方社会的接触,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世界打交道而逼出的新的哲学问题,也是近代世界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给全世界各民族带来的新的哲学问题。近代中国的变法烈士谭嗣同,以其敏锐的哲学灵感,提出了“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光辉哲学命题,努力依托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对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以后发展起来的新仁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通”的精神来诠释“仁学”的核心精神,从而第一次在哲学层面以清晰而又合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逻辑的方式,使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①的精神发生了内在的关联。
现代西方哲学史中,有众多哲学家思考了“世界哲学”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提出“通”的概念,但也具备“通”的观念。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所揭示的世界一体化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以及共产主义理想,雅斯贝尔斯的有关“世界哲学”的思考,无不包涵了“通”的观念。而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劳动斯强调“主体间性”,提出“沟通理性”,已经明确地触及了“通”的哲学观念了。要从人类精神文明史的角度考察“通”的观念演变史,然后建构出以“通”为核心观念的哲学形态,显然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工作,而且这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所能胜任的工作,因而也不是本文所要追求的理论目标。本文的主要理论目标在于:对于“通”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一般运用状态作一粗线条的勾勒,然后对《易》哲学传统中的“变通”,道家的“道通为一”的思想命题作一简明的论述,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学人关注中国哲学传统中“通”的观念,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同时也是世界哲学的“通”论。②
一、释通:“通”观念的思想史考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个普通的语词的“通”,其本意即到“达”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云:“通,达也。”《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具备”篇云:“故诚有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于有血气得乎?”③《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上述文献中所涉及的“通”字,均作动词,具有沟通、通达的意思。
依现代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通”在古代汉语中的训诂意思有一百多种,④择其要有如下十余种意思:(1)达、至;(2)行;(3)顺、畅;(4)共、同、举;(5)开;(6)连;(7)深;(8)知;(9)道;(10)卷;(11)辙(古代赋税单位),十井为“一通”。由此可见“通”字的意义十分丰富。
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观念而言,“通”的意思十分丰富而且复杂。特别是经过易哲学、庄子哲学,以及宋明儒学,直到近代谭嗣同的不断阐发,“通”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观念,其意义与内涵的丰富性,似乎还没有得到一次很自觉而且很系统的清理,因而对于“通”的观念史的清理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少数人在零星地从事研究,取得了部分少量的初步认识。⑤不过,中国古人对于“通”的思想观念是情有独钟的,司马迁在《太史公书》(即今俗称《史记》)一书中,将自己的历史写作任务就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而由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史家风”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不断地得到回应与发展。唐代史学家刘知已作《史通》一书、杜佑作《通典》;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郑樵作《通志》;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方以智作《通雅》,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作《文史通义》。以“通”命名的史学著作代不乏人,而以“通”命名的篇章就更多。王充在《论衡》一书高度赞扬“通儒”,“通人”。而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将自己的哲学著作命名为《通书》。直到现代汉语的“通论”、“通史”之类的著作,层出不穷。但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变通”、“通”进行系统论述的,似乎还只能从刘勰、刘知己、章学诚等人说起。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⑥
刘勰在讲“通变”的问题时,一方面讲“通变之数”,即对各种文学手段的融会贯通;另一方面讲“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依托创作者的感情来会通各种体裁及表现手法,以实现文学创作的创新。“通变”是古与今之间的整合与融通,然后实现创新。
刘知己在《史通》序文中说道:“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史通·原序》)刘知己的意思是说,历史研究或曰历史著作的任务就是追求古今的贯通,出于历史研究本性的理解,故尔将自己的史学著作称之为“史通”。
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看,章学诚对“通”的意义阐释最为丰富。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专门辟有《释通》一文。第一次从文化史的角度解释了“通”的观念及“通史”类著作的发展史,透过对“通史”不同类型的分析与批判,彰显了人们对“通史”的种种理解与误解,从而在文化史的论述中揭示了“通”的观念史的丰富性与歧义性。
首先,章学诚从“广同人之量”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易哲学“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一句中“通”的意思。他认为,易哲学这句话无非是说:“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236页)⑦“通天下之志”,也就是理解、了解、把握天下人的志向与想法,然后建立社会规范。
其次,他“从严畔援之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尚书》“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一句中意思。他认为,《尚书》中这句话无非是说:“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先王惧世有棼治,于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当然,章氏的这种说法是在尊重先王政治权威的前提下加以解释的。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绝地天通”即是运用政治权力垄断祭祀权,从而在宗教意识上垄断不同部族的人对天地鬼神等超越性力量的解释权。
通过对《易经》与《尚书》中“通”与“不通”——专司其职的两种相反意思的分析,章学诚将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件大事纳入“通”与“专”的两种观念之中。他说:“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于九,书要于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236页)这即是说,传统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分工可以溯源于“绝地天通”的各司其职的宗教祭祀活动,而后代政治文化中的九数、六经无非是《易经》时代圣人以卦爻词通达天下之志的一种扩展版。
再次,章学诚又从经学发展史和古代典籍发展的角度揭示了“离经而别自为书”的“通书”的历史起点及其演变过程。最先出现的“通书”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的汉代石渠《杂议》,后来“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236页)真正以“通”命名典籍的是班固的《白虎通义》和应劭的《风俗通义》。而在中国经学史上,有些著作虽然没有标出“通”字,然在实质上是“通书”之类的著作,如集解、集注、异同、然否、圣正、匡谬、兼明等类型的书,“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237页)。章学诚认为,这种“经部流别”的历史演变过程不能不加以辨别。这就表明,中国学术史上,“通”的观念并非就是直接以通的语词、概念来表达的,而是有其他的语词与概念来表达“通”的观念,从而显示了“通”的观念在学术史上具体表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就历史类的著作来看,梁武帝主持编纂的《通史》,是史学类的第一本“通书”。之后有郑樵的《通志》,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著作。在章学诚看来,“通史”类著作有六大方便之处:“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诠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说邻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39页)
章学诚特别表扬了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249页)。这其实是夫子自道,含蓄地表达了他自己追求“通史家风”的学术理想。
最后,章学诚还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将“通”解释成“通达”之意。他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第240页)此一层意义上的“通”,是理解与贯通,与专门性的知识与技术有关。“通”具有跨越理解与学问或曰知识的边界与障碍的意思。他本人在追求“通史家风”的过程中,对于世俗社会一些炫耀学问博通,其实并不博通之人,专门取了一个名字,称之为“横通”。“横通”之“横”当读作现代汉语heng的第四声,有蛮横不讲理,把本来不通的东西以主观的意志强横加以解释、融合的意思。这种“横通”与真正的“通”之意貌似而实不同:“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横通》,第262页)而章学诚理想中的“通”之意是:“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横通》,第262页)
章学诚在论学问的“博约”的关系时,也涉及通与专的问题,他说:“道欲通方而为学须专一”(《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博约下》,第119页),“学必求其心得,为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博约下》,第120页)
要而言之,章学诚对“通”有非常深刻而系统的思考,他认为“通”不仅是“扩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求通之方恰恰是因专而求其通,达于道。他说:“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之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无以致通之原;盖欲自得资深,然后学者取资左右而无骸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第495页)章学诚的意思是说,“通”可以由专家之学出发,然后“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最后达到“自得资深”,可以由专家之学而进入通人之学。
二、变通:《周易》哲学的智慧启迪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周易》是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一本经典著作了。稍微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应当听说过《周易》这本书,而且越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其神秘的光环也就越亮。而在历代的经学研究著作中,有关《周易》的研究著作也可以说是最多的一类。《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方面都有联系,尤其是《周易》与中医,《周易》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周易》中蕴涵的哲学精神,可谓是人言言殊。但在笔者看来,《周易》的根本精神还在于知变(或曰预变),从而达到御变,处变而不惊。在御变的过程中实现由穷而通,由通而久。变通而恒久,可以视为《周易》一书经、传两部分的基本精神。经部分卦爻辞的内容比较隐讳,需要通过经学史的解释加以理解。在经学的解释历史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意思,如乾卦“卦辞”中“元亨利贞”之亨,一般就解释成“通”的意思,以显示天道通达无碍之意。而《坤·文言》则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黄色为中和之色,故以此喻中和的美德。中和的美德在内,则能通达万理,从而成就人间的事业。在《周易》传的部分,论述“通”、“变通”的文字很多。可以这样说,《周易》一书的根本精神就是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⑧。《易》哲学在变化的世界面前绝不是毫无作为,恰恰是要通过对变化的把握,而尽得天下之利,故《易·系辞上》说:“变而通之以尽利”。“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哲学是如何规定“通”的呢?《系辞上》对“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所谓“往来不穷”既指时序方面的春夏秋冬、昼夜变化的无穷性,如《系辞上传》的作者说,“变通配四时”。又称“变通莫大乎四时”。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因而也是指人事世界趋时而更新,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生活世界,如《系辞下传》的作者说:“变通者,趣时者也。”甚至,《易传》的作者就将人类之事的性质界定为“通变”,说“通变之谓事”,从而与大业、盛德等并行在一起:“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由上简单地分析可以看出,《周易》一书就是阐述“变通”的道理,并要求人们在变化面前保持一种智的流动性,从而能实现知变、御变,以尽天下之利的现实目标。《周易》一书经与传两部分涉及“通”的观念,其根本意思就是行得通,无所滞碍。析而言之,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变通”。这一层意思应当说是最基本的意思。从自然的变化角度看:“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而易哲学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求人们知变、然后能正确地应变,从而让人能在天地宇宙、人类社会生活中正确地处理各种事情,实现人类“正德、利用、厚生”的大目的。《系辞传下》说:“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系辞上》说:“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而易哲学所讲的“通”,其最抽象的意思是“往来不穷谓之通”。即是实现人类的自由自在的意志。
就社会生活而言,“通变”的具体内容,其一是指通“天下之志”,如《系辞上》作者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而且还说:“夫《易》,圣人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因为“圣人通天下之志”,则可以“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
其二是指神明之德,《系辞下》讲:古者包牺作八卦,其目的是要“通神明之德”(两次出现),“类万物之情”。这与古代宗教精神有关。人类社会生活总是与某种神秘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故圣人之业要与神明之德相通,与万物之情相通。
如何实现“通变”呢?《系辞上传》作者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是运用“感通”的方式实现对天下人需求心理的了解与通达。而在具体的经济生活领域,“通”的方法是制造工具,如《系辞下》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从人事作为的角度看,“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而从时间变化角度看的“变通”,也涉及空间的变化。一个普遍性的原理落实到具体情境之中,一国、一地之风俗传到另一国或一地,也因变通而生存。佛教的中国化即是“变通”。而“变通”即是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通达、通行,这便是所谓的“推而行之”。故“变通”,是易哲学“通”的基本含义。
第二层意思是“会通”。《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将“卦爻”之“爻”的性质规定为对变化的符号化表达。换句话说,“爻”即是圣人考察天下万事万物的变化,观其会通,以语言的方式判断吉凶的符号及符号体系。《文言》中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处所说的“大人”,正是一个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通的人,是“会通”精神的人格化表现。
《系辞上》还说:“夫易广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这里所讲的“备”也即是“通”,可以称之为“通备”,具有遍覆包涵的意义。“通备”也即是“会通”的意思。而《系辞传下》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这乃是对天下“大通”的一种预言,也是“会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要而言之,“会通”有融会、贯通,而无所不能通达的意思。类似的说法还有:“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系辞上》)这里讲的“弥纶天地之道”即是“贯通”。
“贯通”另一层意思还可以表现在个人的德业一致方面。如《文言》又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是讲君子的美德畅于四肢而体现在自己的事业之中,也是“通”的表现。这是“德业”之通,后来儒家大讲“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篇)之道,主要讲的是君子一类人物的“德业之通”。
第三层意思即是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沟通与通达,让本来是隔离的两物、两事联系在一起。
《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从语言的发展史角度看,这一层意思上的“通”最具体,应当是最早出现的。其引申意当为人与神的沟通,如《系辞下》在解释《乾》《坤》两卦的卦德时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一层次上的“通”是更为抽象的哲学、宗教意义,是人类不断突破生存的局限,向着更加遥远的疆域迈进的一种理想性的要求。
第四层意思涉及“通”的方式与方法。下文所说的“感通”与“气通”当作如此理解。《系辞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里既讲到“会通”,又讲到“感通”的问题。“感通”只此出现一次。然结合《易经》下经《咸》卦(第三十一),则可以理解“感通”。“《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可见,天地万物之间的“感通”是通过“气”来实现的。圣人效法天地而感动人心,实现天下和平。圣人凭借什么来感动天下人之心的,当然是通过“正德、利用、厚生”的系统方法来实现的。从自然界来说,“感通”其实即是“气通”,是阴阳二气交相感应而实现沟通与理解的。如《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又说:“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大自然界的万物通过“气”作为媒介,实现相互之间的交通。
除上述四个层次的意思之外,《易经》“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亨”字,也即是“通”的意思。《文言》中还有“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的说法。旁通也即广泛地通达万物的意思。在解释具体卦德时,《系辞下》又说:“困,穷而通。”《杂卦》也说:“井通,而困相遇也。”⑨这意思是说:困穷之际,恰恰预示着通达机遇的到来。这是《易》哲学告诉人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泄气,而要看到问题解决的时机也就包含在困穷之中。所以《序卦》讲:“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通与不通,因为时间、地点、条件、环境的变化,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易哲学在追求通变的过程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
三、道通为一:庄子以通释道及其对道家思想的发展
众所周知,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概念与核心观念,没有涉及“通”字。但老子“道”的观念里其实就包含着“通达”,无所不包的意思在其中。第25章将“道”规定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混成之物,而第4章讲道“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很显然,道也是遍在于万物之中的。第34章讲:“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即是讲道包容万物而又不主宰万物。第62章甚至说,“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对于善人与不善人都是有价值的。可见“道”具有通用的价值。要而言之,老子之“道”虽未直接与“通”相关,但具有通达万物,包容万物的通性,而且道本身具有开放的、自在的通性,它无声、无形、无象而实有、可信,从而对万事万物都具有正面的价值。
(一)通在《庄子》著作中的一般意义考察
《天下》篇对于庄子哲学的精神概括非常精辟,体现了庄子哲学“以天地精神”为伍的开放性、生机性与无穷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哲学在道论方面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然在“道通为一”,与天地精神为伍等观念方面超越了老子。庄子以无限的、生动的、不可穷尽的宇宙本身作为其哲学思考的起点,在思想上不再有一神秘的、不可言说的观念的形而上预设,而是要人直接以全身心的领悟方式亲证无限的宇宙,并从无限的、动态的、生生不已的宇宙本身去亲证人生在世的意义。现存的《庄子》一书虽非庄子一人所作,其中在哲学的形上学方面表现出在道与天二者之间的徘徊。但这正恰好表明了庄子哲学意识到了老子哲学中“道论”的某种不足。天的无边无际的直观特征给予庄子哲学以更多的启示,也更能表现庄子哲学以无限性为思想起点的妙处。
“道通为一”的观念最先明确地出现于《齐物论》一文,该文在思辨地论述万物皆有其内在的价值问题时说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丁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道通为一”并不是说万物在形态上是一样的,价值上等量的,而只是从万物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角度看,都有其不可剥夺的价值,因而都有存在的理由。
该篇又论述了万物的分合成毁问题,说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这就表明,人世间的一切分、合、成、毁其实都是暂时现象,从动态的过程看,从不同的角度看,分、合、成、毁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与区别。这是“道通为一”的另一层意思。
“道通为一”与“劳神明为一”不同。狙公给猴子的茅粟,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类的“一样”,只是给予的次序有所变化,本质没有变。这种“一”不是“道通为一”之“一”。“道通为一”是从道的高度看,不同之物可以视为“大一”。此“大一”不是相同,而毋宁说各有其自身之所是,所可,也即是说各有其内在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这样的角度看,也即是从道的角度看,万物皆有价值,因而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因此,“道通为一”之“一”是肯定万有存在者自身的价值,因而无限的宇宙自身是极其丰富的、杂多的、在价值层面不相排斥的太和之一体,即宇宙本身的万有而和谐的状态。
除了“道通为一”的“通”之意以外,《庄子》一书“通”的意思还有其他两层意思:
其一,即是一般意义上的沟通与通达的意思,如《德充符》借孔子之口赞扬“才全”之人说道:“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又借哀公之口说道“至通”的观念:“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此两处的“通”字即是“通达”之意。《大宗师》篇“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一句中“通”字亦是此意。《大宗师》篇还有不用“通”字而其实表达了“通”的意思的文字,如该篇提到精神上通于道,朝徹而后见独的境界,即是通达的境界:“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至于《天地》、《天道》、《天下》三篇中所涉及的“通”字,亦是此意,引证如下,供贤者参考。
《天地》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又:“《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又说:“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广,其心之出,有物探之。”
《天道》篇:“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又说:“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又,“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此处“落”字通“络”,通之意也。又:“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另外,庄子一书中“达”字也即“通”字,《知北游》与《秋水》两篇所涉及的内容可以作为“通”的意思之补充。《知北游》又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此处“达”字即“通”之意,亦领悟之意。
《秋水》篇“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此处“达”字,亦即“通”之意,意谓知“道”之人,必通万物之理而最终不伤害自己的生命。又借孔子之口说:“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并认为:“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其二,是全部、整个、都的意思,作为副词来理解。《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此种用法,在《庄子》一书中比较少见。
另外,《应帝王》篇出现了“凿通”的观念,虽然没有用“凿通”一词。中央之帝“混沌”被“凿通”而死,则可见人为的、不合道之“通”并不是好事。故《庄子》一书中的“通”的观念必以合“道”为前提,即老子与庄子都主张的:因物之自然而“通”,正是从这一角度说,庄子对“通”的论述还是以道为前提的。
(二)“道通为一”与庄子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超越
“道通为一”是《庄子·齐物论》中重要的思想命题,历代注庄解庄者对此句的解释都不尽相同。近年来得知,友人商戈令兄已经先我而发明庄子“道通为一”的深刻含义,并由此提出了建构“通”论的哲学思想。⑩此处暂引他的两段文字如下:
其一,商兄认为:“庄子讲的通,就是道的基本状态和境界。通则一,一即通。是非彼此、生死等等,赅而存焉,通则无分无别,无分无别即是无成心,无耦,无待,丧我……故曰,‘圣人通于一,入于天’(天地)。通一为道,通外无道,通就是道,道就是通,道就是一,道通为一。也就是说,道在庄子并非什么外在的形上实体(真宰,真君),或宇宙始原,或普遍真理,而是人(实存)于生活世界里敞现自身自然,要逐步达到逍遥神游境界(一通)的修为实践而已。可见,道通为一,道通一三字义通,而义通的关键或枢纽(道枢)就在通字。故道通为一,重点是通。”(11)
其二,商兄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对庄子哲学中“通”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庄子的通,与其他的不同,是反基础主义,也是非实体主义的。通非本体,而是得的条件、状态和与此相适应的主体境界(通也者得也),它是通过环(始卒若环)、中(守中)、枢(道枢)、适、化、两行、天均、撄宁、滑移等等,来替代或消解传统的是、存在、实体、真理、变化等范畴而建立的论说或策略。也与佛教的觉、悟、明、圆通等境界相应。只是佛教不时还有佛性,真如之求,庄子只是一味通去。通即是道,道通为一。所以我说,庄子哲学的根本特征和全部秘密,正是这个通字。”(12)
我个人认为,商兄对庄子哲学的新解着实富有新义,而且可以视作庄子在道论层面对老子哲学的一种发展。不仅如此,商兄还进一步地说道,他记得金岳霖在《知识论》中说,科学是讲真,哲学则追求通,但很遗憾,以后就没有见他再说下去了。他似乎想就此问题要说下去。他这样说:“通的观念是中国特有的,西方也从未有过什么通的哲学。通既不代表实体、真理,也不代表虚无、错误;既不代表是、存在,也不代表现象、变异、过程、系统或结构,所以基本不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论域之中。通作为一种自然或天人和合的状态与境界,作为各种对立冲突以及成心偏执的积极克服和解除,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乃至科学主义在内的一切教条原则之超越。所以我还相信,若由庄子道通为一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或开创出一个相对全面的通的哲学论说,不仅能大大丰富发扬中国的传统道论,亦能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哲学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话语和方向。”(13)
对于商兄先我而发明的思想远见与哲学理想,深表赞许,并愿意与商兄一道建立现代中国哲学,同时也是世界哲学的“通”论派。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通”的观念仅中国哲学所有,西方哲学没有。现代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就非常重视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而其他哲学家,特别是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观念,都包含了“通”的观念,只是他们可能没有以“通”为核心概念而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而已。而依我之见,庄子对老子“道论”的发展,其最根本之处在于揭示了“道”之“通性”。道如果“不通”,则“道”就不具有周、遍、咸的特征。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可道之道,不是恒常不变的“道”?依“通”之道的哲学观念来看,所有可道之道都是已经被开辟的现成之道,至少是在语言领域被名言所规定了的道。而那让所有的已成之道、未成而将成之道成为道的“道性”,则不是任何现成的道。依此类推,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意思类似,即可名之名是已成之名,而那让名成为名的“名性”则总是隐藏在所有已成或未成将成的名之中。用现代逻辑学的话来说,即是“能指”(即名性)永远大于“所指”。“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即是公孙龙子所说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老子哲学中包含了“道性”的思想内涵,但没有从正面揭示出这一层意思。老子哲学也包含了道的“通性”,但也没有揭示“道通”的特征。第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一段中的“道”之“周行”,“可以为天下母”,即是描述“道”的通性。老子又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生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实也是在揭示道的“通性”。但王弼本《老子》和帛书《老子》,楚简本《老子》都没有出现“道通”连用的句子。只有《庄子》一书,多次而且明确地运用了“道通”的词语。甚且他努力从“通”的角度解释道的特性,有“同于大通”,“六通四辟”,“复通为一”等等说法,这些说法均表明,庄子已经开始从“通性”的角度来解释“道”的特征。他努力从通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消解老子“道论”之道所带有的实体性特征,而要求将道转换成一纯粹的非实体性之“状态”。《齐物论》篇开篇以“吾丧我”的寓言对话开头,其实就要彻底消解人的个体主体的实体性特征,从而使人在万物面前保持一种无是无非、无彼无此的“通性”。“吾丧我”之“我”,其实是一个封闭的、有执的我身与我心。丧失了这样之“我”后的“吾”将是一个与万物可以沟通、交流的开放的主体,因而也就是一个与万物具有“通性”的“吾之吾”。庄子意识到了道之为道的根本道理在于道之“通性”,然而庄子无法摆脱思想传统的束缚,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正是因为“通性”使道成为道。所以他的哲学还是以道为核心,并且有时将道与天混同起来,体现了庄子哲学试图突破老子道论又无法完全摆脱老子道论的思想企图。
庄子之后,道家思想在形上的理论方面几乎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更加有力的发展与推进,稷下黄老道家与汉代的《淮南子》一书,都开始将道家之“道”向实有的、经验的方向发展,试图将道解释成为万物规律。法家《韩非子》更是将“道”看作是“万理之所稽”的总根据。而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中,道家的道论思想则在禅宗与宋儒那里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禅宗“以明心见性”、“人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等命题,间接地解释了道家之道的周、遍、咸的通性。而宋儒则用儒家之仁来释释道之“通性”,提出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用身体的“麻痹不仁”的不通状态来形象地解释道德情感方面的不仁状态。对于“通性”的追求已经呼之欲出。但宋儒在道德境界方面强调“一体之仁”的通性,而在社会下、政治哲学层面又特别强调纲常伦理的固化秩序。程朱理学在理论上坚持“天理”的至高无上性,陆王心学则坚持良知中的“天理”的至高无上性。因此,宋明儒学中的仁学之“通性”最终被“天理”与本心、良知中的天理所“统”——统合、主宰而不能实现真正的“仁通”,而明清之际的儒者王夫之、清代儒者戴震都着重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倡“仁通”。谭嗣同能够在清末之际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实在是深刻地把握了宋明以降中国儒学与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主流脉络,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则着重从社会政治哲学层面把握了中国哲学追求“仁通”的社会政治理想。康有为之后,似乎再没有人接着中国传统哲学“通”的观念往下讲了。本篇小文仅以学术的方式梳理的”通”论的思想史轮廓,详细论述以俟来日。
“通”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相沟通的重要概念与观念,但在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下并没有引起中国现代哲人的重视。近些年来,有少数学者在不期而遇的情况下尝试从不同的方面阐释“通”的哲学思想,表现了某种可喜的新趋向,但还不是十分的充分。当代中国哲学要从哲学创作的实践上确立“中国哲学”身份的正当性,其途径可能是多元的,但努力从本民族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沟通中西古今的哲学观念与概念,并以这些观念与概念为核心建立新系统的理论体系,则应当是其中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本文在此也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学人对此问题给予关注。
收稿日期:2011-12-17
注释:
①在一次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以“全球哲学”来代替“世界哲学”概念,可能更好。姑备一说。
②本人对中国哲学史中“通”的概念与观念的关注,大约始于2005年带领学生读《仁学》一书之时。然将“通”上升为一哲学的观念,先受友商戈令兄的启发,后因2011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高等研究院与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合办的首届“哲学: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激发而在台北“中研院”写出了3万余字的初稿。本文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③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28页。
④参见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90-2291页。
⑤就笔者所知,商戈令较早从“通”的角度论述了“道通为一”命题的新意,并尝试对“通”作出更系统的论述。见其所撰《“道通为一”新解》,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近日看到乔清举兄在台湾大学举办的儒释道三教会通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论中国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该文主要是从中国自然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哲学史中出现的通的观念。
⑥刘勰著,周振甫校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0页。
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下凡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在正文中注明书名、篇名与页码。
⑧困卦就是“穷而通”。
⑨中国哲学中与“通”相反的词是“穷”。“穷”即是不通。儒家多讲“君子固穷”。这是对人格的坚持,对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反抗与批判。
⑩2008年夏,我在上海华东师大的逸夫楼里再次见到商兄,与他闲聊,他第一次向我透露了他的哲学新思,我非常高兴,说自己对谭嗣同《仁学》一书“以通释仁”的思想做过分析,并将论文的电子版发给他了。可惜我还没有读他的英文版“庄子研究”一书。
(11)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载俞宣孟、何锡蓉主编《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80-381页。原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
(12)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载俞宣孟、何锡蓉主编《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13)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载俞宣孟、何锡蓉主编《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