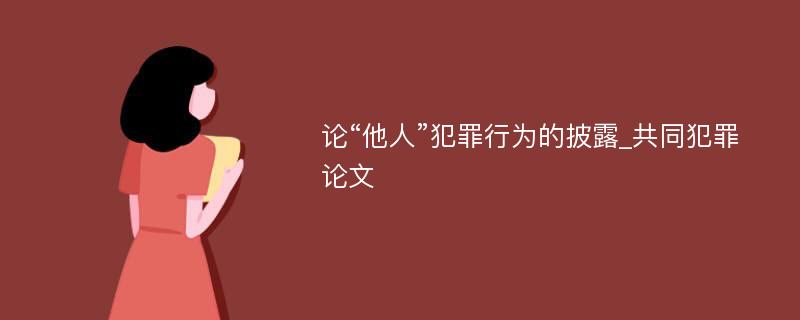
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犯罪行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043(2005)-5(下)-0014-5
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认定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在犯罪人单独犯罪的情况下,认定其是否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不存在任何疑难问题。例如,李某单独犯抢劫罪,事后被司法机关查获,李某揭发了王某的故意杀人犯罪行为,无疑属于立功。但在涉及共同犯罪的场合,犯罪人对自己罪行的如实交代,可能同时意味着揭发了他人犯罪行为。在这种场合,如何认定犯罪人是否揭发了“他人”犯罪行为,还需要研究。例一,甲与A共谋杀人,并共同实施了杀人行为,事后,司法机关仅抓获了甲,甲如实供述了自己与A共同杀人的事实。甲的坦白是否同时属于揭发了他人(A)的犯罪行为,因而构成立功?例二,乙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B行贿10万元,B接受了甲的贿赂。事后,乙因为犯挪用公款罪被检察机关查获。被逮捕后,乙主动交代了自己向B行贿10万元的事实。乙对于其行贿罪成立准自首,问题是,乙是否揭发了他人(B)的受贿犯罪行为,进而构成立功?例三,国有公司主管人员丙,出于为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与其他负责人商议,向国家工作人员C行贿50万元。丙因贪污罪被捕后,主动交代了国有公司向C行贿50万元的事实。在单位犯行贿罪的情况下,丙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丙主动交代所在国有公司向C行贿的事实,是否也属于揭发他人(C)的受贿犯罪行为,因而构成立功?例四,丁持有数量较大的毒品,但没有证据证明丁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故意与行为,司法机关只能认定丁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丁向司法机关交代自己所持毒品是从D处购买,因而揭发了D贩卖毒品事实的,是否构成立功?例五,戊曾参与聚众斗殴(不是首要分子与积极参与者,只是一般参与者),后因盗窃罪被捕。在被捕期间,戊主动交代自己参与过E组织的聚众斗殴犯罪,经查证属实。戊是否就揭发E的聚众斗殴罪而构成立功?
如果完全形式地理解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认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供述与对他人犯罪的揭发并不矛盾,因而全面肯定上述各例中的甲、乙、丙、丁、戊构成立功,显然不当。详言之,根据形式主义的观点,甲既供述了自己的杀人犯罪事实,也揭发了A的杀人犯罪行为,乙既供述了自己的行贿事实,也揭发了B的受贿行为,二者并不冲突和矛盾,在成立坦白或自首的同时,也构成立功。但是,这样形式地理解刑法第六十八条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在单独犯罪中,犯罪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只能成立坦白或自首,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人如实供述共同犯罪事实的,不仅成立坦白或自首,而且同时构成立功。这种对共犯人的特别优待不仅缺乏根据,而且导致对犯罪人的处罚不公平。
为了解决类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6日《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指出:“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据此,如果犯罪人检举、揭发的是他人与自己共同犯罪的事实,就不属于立功。根据这一解释,至少有两种情形可以得到合理的认定。
第一,上述例一中的甲如实供述自己与A共同杀人的事实的,不属于立功。因为如果甲不如实供述自己与A共同故意杀人的事实,非但不能构成立功,而且也不成立坦白与自首。对于这一结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也不会存在异议,不必赘述。
第二,上述例五中的戊主动交代自己参与了E组织的聚众斗殴犯罪的,属于立功。因为E虽然参与了聚众斗殴,但是,刑法只处罚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而戊是一般参加者,不成立聚众斗殴罪。既然如此,戊就并不与E构成聚众斗殴罪的共犯。由于戊的行为不成立聚众斗殴罪,戊在因盗窃被捕后主动交代自己参与了E组织的聚众斗殴犯罪,当然就不属于揭发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因而属于立功。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聚众犯罪都是共同犯罪,在刑法只处罚首要分子的情况下,首要分子是主犯,其余的参加者是从犯或胁从犯,但立法者根据打击少数、争取教育改造多数的刑事政策,只规定处罚首要分子。[1]根据这种观点,例五中的戊并不构成立功,因为戊仍然是聚众斗殴的共同犯罪人。但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法律是否对某种行为规定了刑罚后果(法定刑),是从法律上识别该行为是否犯罪的标志;如果法律没有对某种行为规定刑罚后果,即使该行为被法律明文禁止,也不属于犯罪。所谓“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2]既然刑法没有对聚众斗殴的一般参加者规定法定刑,就表明一般参加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一般参加者也不可能是从犯与胁从犯。因此,否认戊的行为成立聚众斗殴罪,便可以肯定戊对E的聚众斗殴罪行的揭发构成立功。
但是,《解释》只是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标准,事实上也没有为上述例二、例三、例四提供处理根据。因为“共同犯罪”一词具有不同含义(如“共同犯罪”一词有时包括必要共犯,有时不包括必要共犯),在不同意义上对《解释》中的“共同犯罪”进行文理解释,必然得出不同结论。如在例二中,倘若认为乙与B是贿赂罪的共同犯罪,则乙不构成立功;如若认为乙与B不是贿赂罪的共同犯罪,就会根据《解释》得出乙构成立功的结论。显然,仅以《解释》为根据进行形式的判断,不明确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实质根据,必然有损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第一,如果对任意共犯采取强硬的完全犯罪共同说,认为行贿罪与受贿罪并不属于共同犯罪、单位行贿罪与受贿罪不属于共同犯罪,那么,上述例二、例三中的乙、丙就不仅成立坦白或自首,而且构成立功。但这种结论值得怀疑。因为乙、丙只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行贿与自己作为主管人员的单位行贿事实。倘若将这种行为同时认定为立功,必然与单独犯罪人的立功不协调。
再如(例六),乙以杀人的故意、F持伤害的故意,共同对X实施暴力,导致X死亡。(1)根据完全犯罪共同说中的一种观点,乙并不与F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按照《解释》作形式的认定,那么,乙、F各自交代本人与对方共同对X实施暴力致人死亡的事实的,均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构成立功。但这种结论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乙、F的交代并没有超过坦白与自首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不应当认定为立功。(2)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的观点,乙与F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如果按照《解释》,F交代本人与乙共同对X实施暴力致人死亡的事实的,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故意伤害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故意杀人罪),构成立功。这显然也不能被人采纳,因为F只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而乙交代本人与F共同对X实施暴力致人死亡的事实的,既可能被认定为立功(乙揭发了F不同于自己故意杀人的故意伤害罪),也可能不被认定为立功。显然,这既不公平,也造成混乱现象。(3)根据行为共同说的观点,乙与F构成共同犯罪,均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只是罪名与量刑不同而已。如果按照《解释》,乙与F的交代都不构成立功。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采取行为共同说。[3]以上表明,仅从揭举人与被揭举人是否属于共同犯罪来认定是否构成立功,存在诸多缺陷。
第二,如果认为必要共犯(包括对向犯与多众犯)都属于共同犯罪,认为例四中的丁与D、例五中的戊与E都属于共同犯罪,从而否认丁、戊的行为构成立功,也是值得商榷的。
一般来说,对向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对参与者同等处罚的情形(如重婚罪);第二是对参与者差别处罚的情形(如行贿罪与受贿罪);第三是对当然预想到了参与行为欠缺处罚规定的情形(如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中的购买行为)。(注:参见[日]西田典之:《必要的共犯》,阿部纯二等编:《刑法基本讲座》(第4卷),法学书院1992年版,第261页。严格地说,刑法只处罚对向犯的一方时,不能谓之对向“犯”。但将这种情形称为对向犯,具有刑法学意义(参见[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1997年版,第260页)。)
(1)就双方都构成重婚罪的对向犯而言。根据《解释》规定,不管是重婚者还是相婚者,如实供述重婚事实的,均不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即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因而不构成立功。这一结论可以接受。但是,稍微变换案例就存在疑问。例七,庚为了贩卖毒品,而向G购买了50克毒品。在此案中,庚与G也可谓对向犯,并且触犯的罪名相同。如果庚向司法机关交代:“我从一个人那里购买了50克毒品,然后全部卖给了Y。”就应当认定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问题在于,如果庚向司法机关说明了自己从G处购买了毒品,从而使司法机关查获了G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庚是否构成立功?根据《解释》,庚并没有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因而不属于立功。但如后所述,这一结论并不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
(2)就双方触犯不同罪名(如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向犯而言。如果认为行贿与受贿构成共同犯罪,那么,例二、例三中的乙与丙,就不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因而不构成立功。这一结论也具有合理性。可是,一旦变换案例就存在问题。例八,辛从H处购买了10张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辛与H可谓对向犯,但触犯的罪名不同(辛的行为成立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H的行为成立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如果辛持10张伪造的增值税专票向司法机关投案后交代:“我从一个人那里购买了10张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司法机关查明辛持有的增值税发票确系伪造,即使未能查明出售者,也应认定辛的行为构成自首。问题在于,如果辛向司法机关说明了自己从H处购买了10张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使司法机关查获了H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辛是否构成立功?根据《解释》,辛并没有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因而不属于立功。但这一结论是否妥当,也并非没有疑问。
(3)就刑法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而言,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能否直接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将购买淫秽物品的人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处理?国外刑法理论对此存在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立法者在规定对向犯时,当然预料到了对方的行为,既然立法者不设立规定处罚对方的行为,就表明立法者认为对方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如果将对方按照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则不符合立法精神。第二种观点认为,即使对方的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与帮助,但只要属于对正犯的定型的参与形式,就不具有可罚性;如果超过了定型的参与形式,则应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对方积极地实施参与行为,就能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如主动要求卖主出售淫秽物品给自己的,就可以按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教唆犯论处。第四种观点认为,立法上不处罚对方的行为,实质上是因为对方的行为不具有共犯者的违法性或者不具有责任;因此,如果具有违法性并具有责任,则成立教唆犯或者帮助犯。[4]本文认为,刑法规定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时,当然预想到了购买者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购买行为设置法定刑,就表明刑法不处罚购买行为,即购买行为不构成犯罪,故不能将购买者认定为从犯或者帮助犯。(注:当然,如果购买者甲唆使原本没有贩卖淫秽物品意图的人乙贩卖淫秽物品给自己,则可能成立教唆犯。但这不是因为甲购买淫秽物品构成犯罪,而是因为甲教唆他人贩卖淫秽物品而成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解释》可以得出合理结论,即购买者揭发贩卖者的行为属于立功。可是,如果认为购买者也是共犯,只是刑法不处罚而已,则购买者并没有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犯罪事实,故不构成立功。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多众犯是指以多数人实施向着同一目标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包括聚众共同犯罪与集团共同犯罪。就聚众共同犯罪而言,刑法有的条文规定了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及其他参加者的法定刑;有的条文只规定了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法定刑。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根据总则规定处罚其他参与行为。因为多众犯涉及的人较多,立法者规定只处罚几种参与行为,正是为了限定处罚范围;如果另外根据总则规定处罚其他参与行为,则违反了立法精神。因此,前述例五中的戊不成立聚众斗殴罪,其对聚众斗殴的交代属于立功。这一结论与《解释》相吻合,也能够被人们接受。但是,如果认为戊的行为依然成立聚众斗殴罪,只是刑法不处罚而已,那么,根据《解释》规定,戊的行为便不构成立功。如前所述,这种结论难以被人接受。
不难看出,以是否共同犯罪来区分犯罪人是否揭发了“他人”犯罪行为,并不能妥当解决所有问题。
第三,如果为了根据《解释》认定乙、丙、丁、戊是否属于立功,进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讨论行贿与受贿是否共同犯罪、购买毒品与贩卖毒品是否共同犯罪、一般性参与聚众斗殴的人与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是否共同犯罪,必然会因为共同犯罪概念具有不同含义难以得出合理结论。例如,倘若一概肯定认为行贿与受贿构成共同犯罪,那么,不仅意味着只要一方(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另一方必然构成行贿罪(或者只要一方构成行贿罪,另一方必然构成受贿),而且意味着行贿人也要对受贿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认定共同犯罪的目的,就是要贯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可是,在我国,一方构成受贿时,另一方并不必然构成受贿罪;(注:参见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此外,还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只有一方成立犯罪的情形。)反之,一方构成行贿罪的,另一方也并不必然构成受贿罪。再者,即使行贿方与受贿方都分别成立行贿罪与受贿罪,行贿方也不可能对受贿方的行为与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仅仅对自己的行贿行为与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如若一概否认行贿与受贿属于共同犯罪(即只要对向犯的罪名不统一,就不是共同犯罪),就会导致否认必要共犯的概念与理论,从而造成许多困惑(如为什么作为对向犯的重婚罪是共同犯罪,而作为对向犯的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是共同犯罪)。(注:关于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是否存在共犯关系,在国外也存在争议(参见[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有斐阁1996年版,第628页)。)由此可见,刑法理论必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共同犯罪”概念。正因为“共同犯罪”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仅以是否“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为根据认定是否立功,不能妥当处理立功问题。
其实,揭发他人罪行是否立功,与揭发人是否与被揭发人构成共犯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赖以确立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根据与赖以确立立功成立条件的根据并不是同等问题。所以,应当基于立功制度的实质根据,而不是仅仅根据是否共同犯罪来认定是否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刑法之所以设立立功制度,其实质根据有两点:一是从法律上说,行为人在犯罪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表明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痛恨,因而其再犯罪的可能性会有所减轻。二是从政策上说,行为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利于司法机关发现、侦破其他犯罪案件,从而实现刑法的确证。自首、坦白则表明犯罪人对自己所犯之罪的有所悔限,有利于司法机关对自己所犯案件的处理。可以肯定的是,立功是独立于自首、坦白之外的一种刑罚制度。其一,立功并不以自首、坦白为前提;其二,立功具有独立于自首之外的法律后果;其三,自首并有一般立功的,属于具有两个法定从宽情节,自首并有重大立功的,则是对犯罪人更为有利的从宽情节。众所周知,对犯罪行为不能重复评价,同样,对有利于犯罪人的量刑情节也不能作重复评价。既然如此,立功的成立,就要求有独立于自首、坦白之外的条件。换言之,认定自首、坦白的根据,不能同时成为认定立功的根据。由于自首、坦白要求犯罪人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所以,不管犯罪人是单独犯罪还是与他人共同犯罪,凡属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或者说,犯罪人的交代没有超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的,便不可能构成立功。只有当犯罪人所交代的事实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的,才可能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进而构成立功。
在例一中,如果甲不交代与A共同故意杀人的事实,就不可能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换言之,甲交代与A共同故意杀人的事实,也仅止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为如果甲只承认自己一人杀人,非但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反而属于隐瞒事实。所以,例一中的甲不可能构成立功。同样,在例六中,乙以杀人的故意、F持伤害的故意,共同对X实施暴力,导致X死亡的,不管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以及何种共同犯罪,与F各自交代本人与对方共同对X实施暴力,都没有超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因而不属于立功。
在例二中,如果乙只是交代“我向他人行贿10万,至于他人是谁,我无可奉告”,那么,司法机关在没有查明受贿者的情况下,不可能认定乙成立行贿罪。换言之,乙的这一交代并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只有当乙交代“我向B行贿10万元”时,司法机关据此查明B受贿10万,才可能认定乙的行为构成行贿罪,进而认为乙“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这并没有超过自首、坦白的范围,仍然不构成立功。至于乙与B是否共同犯罪,是何种共同犯罪,对认定乙是否立功并没有实质意义。
在例三中,丙主动向司法机关交代国有单位向C行贿50万的事实,成立对自己的行贿犯罪的自首(是否单位犯罪的自首是另一回事)。因为丙对单位行贿也负有责任,即在单位行贿罪中丙也是犯罪主体(丙并不是因为单位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而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所以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丙对行贿事实的交代,没有超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因而只成立自首,不构成立功。
在例四中,司法机关只能认定丁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丁如实供述自己持有毒品的时间、数量、品种,并说明毒品从他人那里购买的,即使没有说明贩卖者为D,也应认为丁如实供述了自己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事实。如果丁向司法机关说明自己所持毒品是从D处购买,因而揭发了D贩卖毒品事实的,则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非法持有毒品)的范围,宜认定为立功。同样,在例七中,如果庚向司法机关交代:“我从一个人那里购买了50克毒品,然后全部卖给了Y。”司法机关应认为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如果庚向司法机关说明了自己从G处购买了毒品,从而使司法机关查获了G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庚便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应构成立功。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例八中,由于辛向司法机关交代了“我从一个人那里收买了10张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司法机关据此查明辛持有的增值税发票确系伪造,可以认定辛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辛向司法机关说明了自己从H处收买了10张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使司法机关查获了H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则超过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因而属于立功。
在例五中,戊虽然曾参与聚众斗殴,但由于不是首要分子与积极参与者,只是一般参与者,并不受刑罚处罚。所以,相对于盗窃罪而言,戊主动交代自己参与丁E组织的聚众斗殴犯罪,显然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盗窃罪)的范围,当然应认定为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