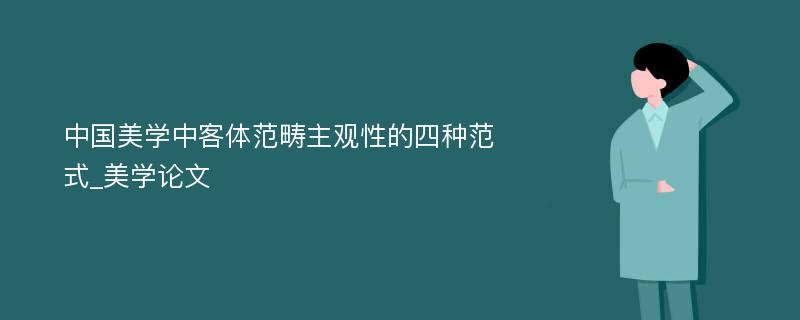
中国美学客体范畴主体化的四种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客体论文,四种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人在审美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历史地追溯考察了中国古代“物”、“象”、“景”、“境”等客体范畴的形成与演变;指出这些范畴既是审美对象的概括,又是主体心灵化的结晶;通过有关心目可感之“物”、拟容意想之“象”、物色融情之“景”与象外神游之“境”所分别体现的具象感应型与意想型、非具象整体外向型与内向型等四种范式的分析,阐明了中国美学客体范畴主体化的民族特色。
关键词 审美 客体范畴 心物 意象 情景 境界 主体化
自有审美活动,就有了审美主体与客体。所谓审美客体,指作为主体的人所认识、鉴赏或创作的具有一定审美属性的对象,是与审美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构成审美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研究审美客体范畴,是美学理论的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数千年前早已发现了美,在开天辟地的创业中感受到美的生活对象、自然景物,创造出可供欣赏的艺术对象,同时发展了自己的审美意识。经过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具体到抽象的概括,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如以“物”、“象”、“景”、“境”指称客体对象等。
今天,我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格局中重新审视这些范畴,深感它们根本不同于西方美学的客体范畴,既非绝对理念,也不是纯客观事物;而是经过一定程度主体化的对象,成为可感之“物”、意想之“象”、融情之“景”、神游之“境”。它们与“心”、“意”、“神”、“情”等主体范畴相生相合,形成素有影响的心物论、意象论、情景论和意境论,代表了客体范畴主体化的四种范式。[1]
一、心目可感之“物”
区分客体与主体,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创建美学的前提。客体概念“物”的产生,“心物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古代认识论的成熟和美学的确立。从上古音乐理论《乐记》的“感物动心”说,到文艺美学专著《文心雕龙》深入论述“感物吟志”、“神与物游”,都明确地以“物”为客体对象范畴。
由于中国文化素重“合”,相信事物有分即有合;因此,在区分主、客体的同时,更注重“心”与“物”的关系;在提出客体范畴的同时,便将它主体化了。“物”就是这样一个主体化的客体范畴,它表示具体可感之物纳入主体心目中所形成的客体对象。“物”与“心”相感相生的关系,便构成中国美学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最基本的范式。
从概念的形成和演变看,“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始为具体动物之名,进而扩展为普遍意义的客体概念,引入美学领域成为审美对象范畴。其间所不变者,是它始终表示主体所感知的客体。
考察汉字“物”的语源,可知它原初是具体动物“杂色牛”的名称。王国维《释物》篇由卜辞考证云:“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又“因以名万有不齐之庶物。”《诗·小雅·无羊》中的“三十维物”,就指三十头杂色牛。《周礼·春官》谓“杂帛为物”,乃引伸义;《说文解字》所称:“物,万物也。”为后起的常用义。约定俗成,习以为常。反其本,原来人们关于对象的认识,乃是从与人有关的具体可感的事物开始的。
我们读《诗经》、《楚辞》,每每感慨其中写到那样多的“鸟兽草木之名”,诸如关雎、蟋蟀、芙蓉、木兰等等;而很少有像唐诗“感时花溅泪”一样概言花鸟之句。这种现象表明,古人比兴寄托的对象,首先是各种具体的事物,然后才有所综合概括。另一方面,中国人审美认识的发展,不脱离具体可感的对象。譬如,“美”概念的产生,与先民对“羊”的感受有关;“韵”范畴的发展,关联着具有音乐感的对象。凡心目有感之物,皆可化为人的审美对象。《周易》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以可感之“物”泛指普遍的客体对象。《左传·桓公二年》载:“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其比象之“物”,已染上了人化的审美色彩。《乐记》指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这段话代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感物动心”说,明确地将“物”视为与“心”(主体)发生审美关系的客体对象。
为什么特指杂色牛的“物”,能够一变而为普遍的对象,再变而为审美客体范畴呢?这也许标志着“物”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畜牧业昌盛和农耕兴起的时代,也许如《说文解字》所云:“牛为大物。”与人们生活相关而随处可见的庞然大物“杂色牛”,自然被当着客体对象的典型代表。也许选择“物”是一种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之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2] 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依然遵循着人类认识的这一普遍规律,即将自然之物“人化”为主体意识到的对象。况且,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不像西方那样用抽象的概念表示客体对象(如英语的object),汉字的象形系统承传着具象思维的特点。这样,中国美学很自然地选取典型的具体可感之“物”作为客体范畴。
中国美学的客体范畴“物”,在主体化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范式在于:一方面指向现实客体,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可感性;只有被主体心目感知的对象,才能与主体构成心物感应关系。
例如,陆机在《文赋序》中自云“恒患意不称物”,就是担心主体与客体不能相应。《文赋》所言之“物”,或表示现实观照的对象,或指主体内化的物象。前者如“瞻万物而思纷”句,指的是对自然景物的观赏;后者如“物昭晰而互进”句,指内化的物象在脑海中接连涌现。都是主体审美感知的客体对象。
中国古代常以通称的“物”或某一类物的名称,来表示观照的对象、想象中的物象,乃至艺术化的形象,造成同名异实与异名同实的种种现象。这是中国美学的模糊之处,也是中国美学的巧妙之处。它表明物象与物的天然联系和亲缘关系。钟嵘《诗品序》指出:“物之感人。”刘勰《文心雕龙》论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虞世南《笔髓论》要求“虚心纳物”,郝经《文说》提到“物感于我”。这些有代表性的言论涉及主体感知与构思中内化的物象,均以“物”名之,意味着以现实为本而指向客体;其所指客体又处处与主体对应,揭示着心物感应的关系。由此表现出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具象感应型的范式。
二、拟容意想之“象”
中国美学又常以“象”表示客体对象。“象”与“物”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都有具体可感的特点。主体内化的对象,或称“物”,或称“象”,或联用称为“物象”。但二者并不等同,相比而言,“象”更多地倾向于主体的想象,表现为拟容取心的意象,也就是说,其主体化程度更高。
因此,“象”的产生和“意象论”的提出,构成了客体范畴主体化的又一范式。
让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象”范畴形成的轨迹,它大约也经历了由特指物名到普遍意义的形象概念,再到审美客体范畴的历程。
“象”的本义是一种特指动物。《说文解字》曰:“象,长鼻牙南越大兽。”后世何以用“象”表示一般形象呢?《韩非子》解释说:“人希见其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此说可以概括为:象以意想。
“象以意想”之说代表了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象”的理性认识。首先是表明在先秦时期,“象”已由动物大象的特指名称,扩展为普遍运用的表示想象之物的概念。其次,这说明“象”是由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罕见活的大象,便通过想象拟其形象以满足审美需要。其三,此说还揭示出“象”是由主客体两方面因素构成的:“案其图”,指根据客观对象的图形;“以意想”,指人的主观意识发挥想象。
模拟事物的形貌,便产生“象”。因而可以说“物”是“象”的原型。《左传·僖公十五年》有云:“物生而后有象。”其《宣公三年》又有“铸鼎象物”之语,记录了古人对自然物模拟的行为。故《释文》曰:“象,拟也。”《周易·系辞》指出:“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汉代王充《论衡》提到“刻画效象”,唐末荆浩论画主张“度物象而取其真”(《笔法记》),明代屠隆言及“综物为象”(《澹思集序》),王夫之则曰:“象者象其形矣。”(《尚书引义》卷六)他们都认识到,“象”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物”的写照;它因物而生,拟物而成,寓物以意,取物之真,是主体模拟现实客体的产物。
作为审美客体的“象”,又是主体意想的结果。《周易》早已提出“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诗人屈原在《远游》中曾道出“思旧故以想象”之辞。王充《论衡》分析“象”的虚指性说:“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玄学家王弼则认为:“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就是说,意想是产生“象”的动力,“象”是意想的对象。故曹植写道:“虑神思而造象。”(《宝刀赋》)刘勰《文心雕龙》指出:“神用象通。”林琨在《象赋》中描述“象”与“想”的关系说:
物标万象,即拆之于混沌,亦闻之于惚恍;虽处中而可求,信居外而能想。
其意为,“象”虽有恍惚的特点,却是物的标志,想的对象,能通过想象在主体内心把握。故曰:神用象通,象以意想。
综合以上两方面,可知“象”既是客体物象的模拟,又是主体意识的创造。因“拟容取心”,而意象顿出。是审美对象化与主体化的统一。
由于中国美学的“象”,是以具象的形象为起点,经过典型化的概括和主体化的创意而得,它就不仅成为艺术形象的共名,而且积淀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有着与西方美学概念不同的特色。西方美学的“形象”(image)概念,或译“意象”,虽也具有“心想图形”的意思, 但缺乏具象渊源,缺少如“象”这样的内涵丰富的基因,故偏向于抽象与理念化。例如美国的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意象纯粹是虚幻的‘对象’。”[3]中国美学则不然, 既认识到“象”的虚拟性,又执着于其具象性,更欣赏它的情趣性。如书法家卫恒十分看重“象”的审美价值,提出“睹物象以致思”(《字势》)的创作原则。画家宗炳主张“含道应物”与“澄怀味象”并举(《画山水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以“神与物游”论艺术构思,又指出其中奥妙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盖指具有一定审美心胸的艺术家,选取映入内心的相应的客体为对象,通过“运斤成风”似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主体化的审美意象。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美学的“象”,实在是拟容意想之象,其拟容取心、意想形物的方式,体现为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具象意想型的范式。
三、物色融情之“景”
“景”是中国人创造的更为纯粹的、更有整体空间感的美学范畴。相对于“物”、“象”等客体范畴,“景”虽晚出而后来居上,能囊括众多个体物象构成自然人化的审美空间,体现出审美对象的扩展,形成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范式。
自然风景,物色万象,本来就呈现在人类面前;但是,谋求食物的原始人无暇顾及,贸易至上的西方人漠不关心。据载,大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才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意大利的但丁被称为自古以来“第一个”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的人。[4]
然而在但丁以前,中国人早已发现了自然景色之美。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山水,在天人相合的古朴观念中化为人伦美的象征。如果说,比但丁早1800年的孔子提出“乐山”、“乐水”(《论语》),还是以山水为“比德”的对象;那么,比但丁早900年的陶渊明等人游览山水, 就显然是以自然风景为审美对象了。例如,《世说新语·言语》与《晋书·羊祜传》都记有晋人游观“风景”之语。陶渊明《时运》诗序云:“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然交心。”他们明确提出了观赏“风景”与“景”的概念,标志着中国人率先发现了山水风景之美,当视为美学史上关于审美对象认识的一次飞跃。
无论在东、西方,关于对象的认识,都是从现实需要开始的。当人们的眼光从物质生活转向自然山水时,物色美景才姗姗而出。在中国古代,《诗经》、《楚辞》、汉赋等作品中写到的山水草木,侧重于比兴寄托的个体物象描写,尚缺整体的景观意识。大约在魏晋时期,由于世道变更与玄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士人渐次收敛了功利之心,寄意山水,游观风物;随着南皮之游,新亭之饮,兰亭之会,兴起了独立地观赏自然风景的审美意识。他们发现,那光与影笼罩下的物色风光、山岚水气,仅仅用一般的对象概念,仅仅用具体之“物”与有形之“象”来指称不够了;于是他们选择了非具象的“景”,来概括更有物色群象的整体美感,更有大自然的空间感、朦胧感的审美对象。
“景”的本义是日光。《说文解字》曰:“景,日光也。”班固《西都赋》“激日景而纳光”,乃用其本义。或因日光之伟,景被引申为“大”。《诗·小雅》中“景行行止”的景,意即为“大”。景又是“影”的古字,《荀子·解蔽》“水动而景摇”的景,当含光与影之义。自然风物,离不开光与影的照射辉映;在日光月影映照下的物色群象,莫如用“景”来指称更为恰当。
例如,曹植有《公宴诗》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谢安《兰亭诗》写道:“薄云罗景物,微风翼轻航。”张翰由眼前风景兴发思乡之情而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第一位著名的旅游家兼山水诗人谢灵运提出:“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他们笔下的“景”,显然比“物”“象”概念更适于表现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更适于融汇寄寓山水的观赏情趣。谢灵运将“良辰、美景”与“赏心、乐事”对举,既表明“景”属于客体对象,又表现出主体审美意识的化入。中国诗人墨客用非具象的“景”概指自然山水群体对象,创造了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新的范式。与“物”、“象”所代表的个体感应型和意想型范式相比,“景”范畴的主体化,是审美对象的扩展与深化,具有空间整体化、自然情趣化与艺术原质化等特点。
首先,是空间整体化。从主体观照中的客体对象看,“景”所表示的自然风物,不再是一头牛、一棵树之类的个体形象,不再是一桩桩游离之物,而是审美主体对一组客体群象的整合。如陶渊明描写的山中秋景:
和泽同三春,华华凉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和郭主簿》其二)
陶诗描写的秋山之“景”,是诗人游观中自然风物的整体呈现,也是审美主体对客体群象的有机组合,逸峰、奇岑、芳菊、青松,在秋高气清中和谐统一为具有空间感与整体美的风景。
其次,是自然情趣化。“景”范畴的产生是山水美感的结晶,是人类对实用功利的超越,有了独立的风景意识。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审美对象从一般对象中分离出来,使自然之景情趣化。如《晋书》记载羊祜登岘山观风景的嗜好说:“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他由宇宙无穷而前人湮灭,生发出“使人悲伤”的感慨。再如提倡欣赏“美景”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又提出“玩景”一语,其诗云:“弄波不辍手,玩景岂停目。”(《初发入南城》)“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无论是羊祜的人生感叹,还是谢灵运的玩赏意趣,都不再以山水为物质对象或道德的比附;而是把山水风景视为独立的审美客体,视为能融入主体情趣的自然对象。
第三,是艺术原质化。“景”范畴在艺术论中进一步扩展,不限于指山水景物,而概言与“情”相对的审美客体,艺术化的对象。中国诗人画家从描绘自然山水,到创造新的情景世界,盖将人生原质一往深情地艺术化为可观可赏之“景”。诚如王国维指出: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
(《文学小言》)
王氏此论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也是对中国传统情景论的一种分析概括。所谓“二原质”,即指艺术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情”为主体意趣心怀,而突出审美情感;“景”囊括物色形象,融为艺术化的客体原质。关于“情、景”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心物论”与“意象论”。随着审美意识的发展,具有整体美感的“景”更受艺术家的青睐,被撷入诗论画论之中。自《文心雕龙·物色》提到“窥情风景”之后,唐人倡言艺术化的“诗景”、“画景”。如韩冬郎《冬日》诗云:“景状入诗兼入画。”《文镜秘府论》记载唐人诗学说:“文章是景,物色是本。”荆浩在《笔法记》中将“景”列为画法“六要”之一。对“景”的艺术媒体特质作了初步揭示。明代谢榛更深入肌理,悟出“情景”乃艺术生命的原质,提出“景媒情胚”说:
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
(《四溟诗话》)
其后王夫之论及情景“有在心、在物之分”(《姜斋诗话》)。李渔明确指出:“情为主,景是客。”(《窥词管见》)又说:“情自中生,景由外得。”(《闲情偶寄》)清楚地区分了情景的主客性质。另一方面,中国艺术论更注重情景相融相生的关系。王夫之提出“景生情,情生景”(《姜斋诗话》);吴乔认为“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围炉诗话》)。说明“景”其实是主体融情于客体的一种艺术创造,虽非具象,而更有整体美。
综上所述,可见“景”范畴与“情景论”的形成,意味着中国美学主、客体理论的成熟与深化,其物色融情的特点,标志着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整体外向型的范式。
四、象外神游之“境”
从“物”到“象”,从“象”到“景”,构成了客体范畴演变范式的很有趣味的系列,即随着主体化程度的提高,其整体化、心理化与艺术化的程度也逐步提高。那末,这个系列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呢?中国美学的这个范式系列继“景”之后出现的,是主体化与心理化程度更高的“境”。
“境”,或称“意境”、“境界”,是近世以来研究中国文艺美学所谈论得最多的范畴之一;“意境”论也被公认为中国美学的代表理论之一。但解说纷纭,在此勿庸赘述。其实,无论从创作或欣赏来看,“境”所呈示的都不过是客体对象充分主体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与心理空间。当主体情意和客体对象两相交融,物我感会,虚实相生,展开多重审美内涵的象外空间而令人神游遐想,这就是“意境”的创造,也就构成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一种非具象的整体内向型的范式。
考察“境”的本义,可以发现,它原来就与审美有所关连。在古籍中,“境”与“竟”通用,“竟”为本字。《说文解字》曰:“乐曲尽为竟。”原本与艺术有不解之缘。其俗义为疆界,《诗经》毛传:“疆,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曲之所止也,引申之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以后逐渐被“境”所取代。它本是表示乐曲终止的时间概念,一转而为表示疆土边界的空间概念;再转而为表示精神领域的抽象概念,例如《庄子》中提到“是非之竟”和“荣辱之境”。在逐步引申时,原初的音乐感、时间与空间感不知不觉积淀于其中,成为它转化为美学范畴的基础。
汉魏文人开始有了审美境域的认识。扬雄《太玄》提出“穷乎神域”之语;传为蔡邕的《九势》论书法曰:“须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他以味美之境喻音乐美的境域。其后,《世说新语》记述画家顾恺之倒食甘蔗的逸闻说:“渐至佳境。”南齐书法家王僧虔《论书》提到“亦入能境,居钟毫之美。”这些言论虽是吉光片羽,却标志着审美概念“境”的萌芽。
在唐人笔下,大量出现了表示审美对象的“境”。诗人李白兴致勃勃地写道:“偶逢佳境心已醉。”(《和卢侍御通塘曲》)王维的诗被《河岳英灵集》评赞道:“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诗僧皎然提出“诗情缘境发”(《秋日遥和卢使君》)。画论家张彦远认为绘画应当“境与性会”(《历代名画记》)。传为王昌龄的《诗格》明确论述了诗的“三境”:“物境”、“情境”与“意境”。宋、元、明、清时代,“境”与“意境”的理论更为丰富。至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对“意境”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何谓意境?王氏评价元剧指出: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宋元戏曲考》)
后人多据此以为,佳作即有“意境”,情景交融就是“意境”。倘问:既有“佳、妙、优、好”之赞语,又有“心物”、“意象”、“情景”之范式,为什么还要以“境”论艺呢?
究其所以然,原来“境”所揭示的整体内向型的心理空间,是“物”、“象”、“景”所代表的诸范式无法取代的。“境”范畴的产生有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
首先,是基于古老的礼乐文化与儒家美学的来源。中国自古崇尚天人之和,传统诗乐以引人进入和谐的精神境界为旨归。儒家孜孜追求尽善尽美的伦理境界,渗透于文学艺术,成为意境的人格内涵之一。清代学者以“神理意境”赞美《诗经》(《养一斋诗话》)。意境,正是对中国文人向往美善相乐的心理空间的一种理论概括。
其次,道家美学也是意境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庄子》所描写的游心物外的境界,表现出对超乎世俗的自由自在的理想的向往。唐人成玄英注疏《庄子》曰:“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主张“境智相会”。道家美学精神,流宕于中国山水诗画之间,成为清逸淡远的审美意境的思想导向。
另一方面,“境”范畴的形成,显然也受到佛家“境界”学说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有云:“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梵语“般若”其意为“智慧”。此句以“绝境”极言心灵智慧的玄妙,盖出自佛学。东汉以来,佛经翻译中用“境”表示宗教化的心灵空间。如《成唯识论》:“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僧肇《维摩经注》:“冥心真境,妙存环中。”其所谓“境界”,本是佛学心理概念“十八界”之一,却在虚拟心灵空间上与中国学者的内省思维一拍即合。中国文学艺术以诗情画意为尚,正需要一个表示审美对象空间的术语。“境”概念的引入,正好可以囊括主体在想象中创造的、欣赏者可以心领神会的情、景、意、象等等。于是中国学人扬弃了宗教迷信,化佛境为诗境。唐代诗僧皎然吟道:“月彩散瑶碧,示君禅中境。”(《答俞校书冬夜》)他将禅境与诗境合一了。以后白居易等人言及诗境、绘境,可以说是更纯粹的艺术境界。
中国美学化的“境”,是一个主体化程度相当高的客体范畴。大致有三方面涵义。一是指自然境界。如柳宗元《小石潭记》所写“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之境;白居易《三游洞序》所写“晶荧玲珑,象生其中”之境。它们虽指自然观赏的对象环境,却不可以物、象、景取代,因其中渗入了更多的主体成分,涵盖更宽。
二是主体心境。如张说诗曰:“惟应心境同。”(《清远江峡山寺》)王昌龄《诗格》提出“视境于心”;司空图论及“思与境偕”(《与王驾评诗书》)。元代方回《心境记》甚至说:“心即境也。”中国美学所指心境并不是纯主观的心灵,而是纳入了相应客体景物的心理空间。
三是艺术境界,即诗境、画境等。如杜甫诗云:“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八哀诗》)韩愈《桃源图》赞文章绘画之美,说:“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指的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对象空间。
“意境”理论乃融贯此三义而成。“意境”可简称“境”,它确乎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美学范畴。说它指客体,它却在主体心中;说它指主体,它又是审美观照的对象。这种主客相融的现象,有些像西方心理学家描述的“心理场”;也有些近于现象学美学家所说的“现象”。如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在向知觉呈现自身时,就是最佳的现象。”[5]中国美学的“境”与之并不相同, 却有审美对象整体内向呈现的特点,因而超过其它客体范畴,成为审美对象的最佳范式。
“境”与物、象、景等客体范畴相比,其特点主要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境”的容量更广阔,空间感更强,整体化程度更高,故能总揽万象众景,形成深印于心的意想天地。其二,“境”的妙处主要在象外,在于虚实相间,悠远空灵。如刘禹锡所说“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令人想象回味不尽。其三,“境”的主体化、心灵化的特征更明显。“象”与“景”虽也染上了感情色彩,但在观照中指向客体。“境”则不然,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人间词话》)盖因它将对象纳入主体空间,具有主客合一,象外神游的特点。
当然,“景”与“境”都属于非具象的整体性范畴,又有密切联系。前人关于情景论的阐述也可视为构成“境”的某种探讨。如宋人范景文《对床夜语》评杜诗“情景相触而莫分”;王夫之《姜斋诗话》论“情中景,景中情”的关系。黄容之《看山阁集闲笔》概括“情景相生”说,方东树《昭昧詹言》概括“情景交融”说等等。“境”不仅包含了“情、景”,而且更为思深意远。金圣叹指出:
“境”字与“景”字不同。“景”字动,“境”字静;“景”字在浅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
(《杜诗解》)
比较“物”、“象”、“景”、“境”这一组美学范畴,的确可见一种后来居上的现象。从这些客体范畴主体化的不同范式来看,开始是具象感应型范式,以“物”为客体;进而是意想型范式,以“象”为代表;再发展为非具象的整体外向型范式,以“景”为对象;最终形成整体内向型范式,推出主客合一的审美对象范畴“境”。由此体现出中国美学的民族文化特色。
收稿日期:1997—06—16
注释:
[1]“范式”:语本《文心雕龙》, 今指某种特定的历史形成的规范。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52页。
[3]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出版,第58页。
[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294页。
[5]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3页。
标签:美学论文; 范式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说文解字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读书论文; 姜斋诗话论文; 风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