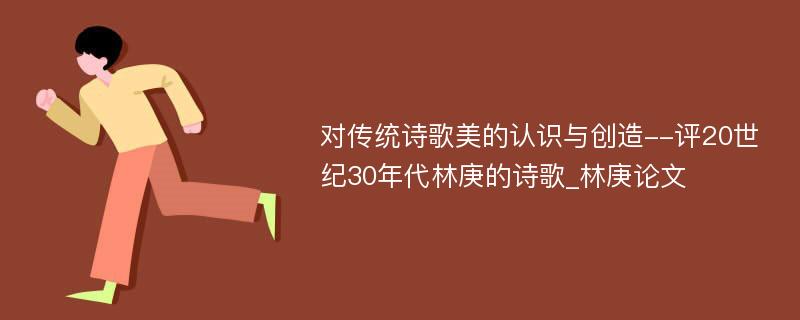
传统诗美的认同与创造——评林庚20世纪30年代的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年代论文,传统论文,世纪论文,评林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3—0114—07
因为学术成果丰厚,林庚的诗人身份逐渐被学者光彩淹没了。其实林庚首先是位诗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是《现代》诗群中虽不显要却十分活跃的歌者,诗作数量有限诗品却很高。他不但以《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它》等四部诗集,筑起了诗坛上一道清远、雅洁、美丽的艺术风景线;而且以诗情、诗艺方面对古典诗美的沉潜认同与坚守,以自己的独特价值创造,打破了现代诗群源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发生发展机制的错觉,表明真正的中国新诗完全可以不依赖西洋文学影响而独立存在,从而显示出东方民族艺术的恒久魅力。难怪有人认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许比任何人更重些,因为它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1](P185), 称林庚为优美的闲雅的“中国气息的诗人”[2]了。
林庚是东方现代诗的寻梦者,是传统诗美的守望者、创造者。
“路上”的诗情
断言林庚是古典诗美的重铸者,依据当然既涵括其诗艺具有东方化倾向,又涵括其诗情与传统诗意味特质具有一致契合性。那么林庚诗拥托出了怎样的诗情形态呢?也许了解一下诗人的生平创作道路对搞清这一问题会有所帮助。
林庚,字静希,福建闽侯人,1910年生于北平。书香门第出身的文化氛围与开明自由的空气,夯实了国学基础同时也孕育了林庚心中的诗歌生命;所以1928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课外的书海泛舟唤醒了诗人的诗心;1930年转入中文系,获得了更恰适的成长背景,与诗友创办系刊《文学月报》,诗名迅速传遍清华园,此时诗人写旧体诗,第一首词《菩萨蛮》即语意浑成,不弱于古调,深受俞平伯赞许;“九一八”事变后写的“为中华,决战生死路”抗日战歌在全校风靡一时,之后曾随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抗日。
请愿回校后林庚悟出古诗类型化语言难以表现现代人情感,以往自己“并不是在真正的进行创作, 而是在进行着古诗的改编”[3 ](P278),于是告别旧诗始作自由诗。被解放的诗情的自由喷发成就了诗人,使之短期内即走向了成功,在1933年与1934年分别捧出《夜》、《春野与窗》两本自由诗集,其声名鹊起。1933年林庚毕业留校任朱自清的助教,兼任北平《文学季刊》编辑;1934年毅然辞职去上海,幻想靠专门写诗生活,当年秋返北平先后任教于北平国民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大。1935年始改写格律诗,并发表《质与文》等系列论文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它》两本格律诗集。抗战爆发后,赴厦门大学任教授,从事古典文学教研活动,同时也致力于新诗理论研究,开设“新诗习作”等选修课;1947年回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解放后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著述丰厚、蜚声宇内,先后出版有《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天问论笺》等专著,以及诗与诗论合集《问路集》;并一直关心新诗研究,1950年后参加自由诗与格律诗讨论中的某些观点,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林庚的生平与创作道路纵向描述表明,诗人20世纪30年代与时代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他关注时代风云变幻,但沉静内心性情等因素的限制却使他始终处于时代的边缘,从未置身于火热生活激流,步入时代的中心,“在他里边,分析社会认识社会的理智,似乎还没有开始活动,直观的诗人林庚,是不大了解现代社会的机构的”[4]。 加之林庚涉足诗坛时,正值开掘人的内心与深层体验、追求纯化的《现代》诗风盛行;所以顺应这一艺术潮流,诗人便理所当然地走向了对诗情的提炼与抒发,将情感作为诗歌生命的第一要素,无意中一开始即进入了对新诗艺术本质的探寻。诗人认为“人类的永恒的情感,才是走向纯艺术的第一步”[5](P171); 对于诗内容“永远是人生最根本的情感;是对自由、对爱、对美、对忠实、对勇敢、对天真……的恋情,或得不到这些时的悲哀”[6]。受这种观念支配, 诗人将笔触伸向了深邃细腻的灵魂深处进行开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心灵敏感精神丰厚的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情思天地、体验世界,再现了一个暗夜寻梦者在寻找“路上”心灵的孤独寂寞与渴望吁求。也就是说,林庚当时写诗,是怀有“一个初经世故的青年”心绪,去展示“内心深处的荒凉寂寞之感”,展示心灵中萦绕着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5](P170 )它有对光明未来与美好理想的追求;但却朦胧得常停浮于观念的空想的层面。在这片“路上”的诗情中,找寻不出什么微言大义与冲天气魄;因为它缺少洪钟大吕的震撼力,因为它“若即若离的人间味”里现实主义气息十分微弱。但它们所展示的心灵世界真诚深邃,丰富无比,以特殊的形态与视角保持着与现实间时浓时淡或浓或淡的联系。
任何生命个体都维系在社会群体与氛围中,多事之秋的“时代病”笼罩,使初涉诗坛的林诗染上了感伤的时代情绪色泽、跳荡着幻灭的心灵哀音。虽然诗人缺少直接突入生活获得正确认识的心理机制,但锐利敏感的直觉又使他能在某些时候把握住社会片断的本质真实,准确捕捉“九·一八”后动荡现实与人们心灵的信息。《月上》中“每个风尘的脸/带着不同的口音与切望”,活画出了农村破产经济恐慌的逃难情形;透过《风沙之日》的云层,诗人看到了“惨白的是20世纪的眼睛”;至于《二十世纪的悲愤》“乃知黑夜卷来/令人困倦/漫背着伤痕,走过都市的城”,对现代都市罪恶的诅咒与否定已溢于言表。但在沉重的现实面前,诗人无力做彻底的扩张与批判;所以只好返归内心,饮啜生命的寂寞与孤独。众所周知,寂寞孤独是种可怕的情感,可林庚却一度十分酷爱它品味它,他说“我是天性愿意忍受一些悄悄与荒凉的;而且我也曾经在苦中得到过一些快乐;乃使我越发对于寂寞愿意忍受下去”[3](P180), 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的爱我”(《古园》),感到“眼前只有影子混来/在那里欺骗慰藉”(《冬风之晨》);因而独恋暗夜与黄昏,“烛光摇动着一团黑影/直闪过不定的明年”(《除夕》),对未来的不可知中要“今宵有酒今朝醉”(《夜行》),不管将来,不问明朝,幻灭的情思淌动中已有刹那主义的享乐之嫌。诗人之所以身陷寂寞孤独,除了源于社会挤压,其它的原因诗人已在诗中提供了答案,“才出世的苍蝇啊/你怎样与人认识的呢/生于愚人与罪人之间/因觉得天地之残酷”(《在》),原来诗人心目中社会之人只是愚人与罪人的凑合,将自己剔除人群者必被社会与人群所剔除,空余下寂寞孤独。
林庚的寂寞固然源于荒诞时代的挤压,但更是热爱青春的智者对心灵问题探寻而产生的寂寞。林庚的一些诗就是对生命价值与自由境界叩问追求的形象诠释,就是物象与心象融合的哲思超越。因为诗人深知忧伤与寂寞于世无补,所以在展示其同时更在寻求着超越的途径。《夜》即是逃离寂寞的心象图。“夜走进孤寂之乡/遂有泪像酒/原始人熊熊的火光/在森林中燃烧起来/此时耳语吧/墙外急碎的马蹄声/远去了/是一匹快马/我为祝福而歌”,孤寂让寻梦者流泪;但死寂里的马蹄声却隐喻了对寂寞现实的逃离,宁静而热烈而急骤的三层意象转换,透露出诗人跃动的渴望光明之心。而《无题二》则抒发了人到中年的忧伤感受。“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吗/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黄昏的影子里哪里是呢/晚霞的颜色又是一番了”,它道出时光的流逝、自然的变迁、人生的失落永远也难以追挽与弥补,人必须体味领会那些无法拒绝与逃避的承受,这是谁都要独自品尝的美丽而忧伤的人生滋味,抽象命题的昭示中透着一种从容与镇静的超脱。进一步说,林庚就生活在希望之中,他对美好的事物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与向往。在《五月》里,他建构“芦叶的笛声吹动了满山满村”的理想化牧歌世界,在黑夜里,他听到渴望已久的“额非尔士峰上刻碑的声音”,看见“平原之歌者/随风而走上绿草来”,“踏着欢欣之舞步”(《时代》),这烛照生命之光正是引导诗人摆脱苦闷、迈向理想世界的原动力。再如“破晓中天旁的水声/深山中老虎的眼睛/在鱼白的窗外鸟唱/如一曲初春的解冻歌(冥冥的广漠里的心)/温柔的冰裂的声音/自北极像一首歌/在梦中隐隐地传来了/如人间第一次的诞生”(《破晓》),跳跃的意象并置,整体烘托出一种欣喜向上的情思,它传递的是晨醒前似梦似醒的纷繁心象,尾句一出,那种对青春向上的展望、对人——人间获得新生的欢愉喜悦,已昭然若揭。诗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是多向度辐射的,在有关春天题材的诗中体现得最为强劲有力。对春天,诗人似乎情有独钟,具有特殊的敏感,竟写下那么多关于春天的诗,如《春天》、《春野》、《春晨》、《春雨之梦》、《春天的心》、《欲春之夜》等,不胜枚举。人说只有热爱人生的人才会热爱春天,在诗人笔下春已累积成希望、欢欣与美的象征与代名词。《春野》里生长着葱郁的生机;《春雨之梦》满溢着土地对春天的生命渴望;《春天的心》充满生命苏醒的欢欣,“春天的心如草的荒芜/随便一踏出门去/美丽的东西到处可以捡起来的……江南的雨天是爱人的”,它境界高远,句式的跳荡中春的温柔、缠绵与欢欣已缓缓渗出。
现实的严酷黑暗,希望又显渺茫,自然而然地林诗中表现出对过去的眷恋回顾。痛苦的抑或欢乐的、绚烂的抑或黯淡的,所有逝去的在诗人笔下都幻化成美好的记忆,慰藉着诗人空虚之心。《那时》的童年乐园敞亮透明,清新爽朗,“与友伴嬉戏在小山间”,天真烂漫欢乐无比;与如今的险恶冷酷的人生格格不入。《秋深的乐园》里流露出童年乐园荒芜的惆怅。《斜倚在……》更满贮着田园牧歌气息与“欣欣的古意”,“斜倚在荒原暮景的山坡/有童子唱着古代游牧之歌/远处的笛声与牛羊的低叫/随晚风流出芳草的深笑/这时正有:一行白鹭/从天边带着晚红/跌入野霞飞处”,它的境界温馨如画,优美似诗,英雄美人,其乐融融。这个境界也许是现实的存在,也许只是虚幻的创造;但无论怎样它都属于艺术的真实,既表现着诗人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取向,又说明了诗人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执著。
可见,林诗建构的情思世界,乃是一个远离时代风云的知识分子寻梦“路上”的个人化诗情,它视野狭窄,现实气息微弱,格调也嫌感伤纤巧,具有“短诗派”作品的短处;但它决非毫无价值的浅斟低唱,诗人的许多体验感悟已融会了现实因子与人类群体经验的深层,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时代与人们心灵的面貌,引起人们的精神共鸣,提供不尽的人生启迪。也正因为这种“路上”的诗情与时代现实的中心情绪“若即若离”,才保证了诗人对时代、现实审美意义上的观照,使诗获得了空想观念的色彩,为诗平添了一份空灵、朦胧、闲雅与清丽,从而与内向性的古典诗情特质达成了契合,还给了读者一份亲切。
“晚唐的美丽”
林庚诗歌艺术的传统色彩远远胜于其意味的传统色彩。戴望舒认为“旧诗倒给了林庚先生许多帮助”,林庚“不过想用白话发表一点古意而已”,是“拿白话写着旧诗”[7], 这无疑是因心灵与艺术的隔阂而造成的误解贬低,好在它无意中道出了林诗的优卓之处,即流贯着强劲的东方古典风。林庚开始写诗时的确受过西方现代诗先驱们的影响,波德莱尔的作品曾使他热血奔涌、周身颤栗,并因此知道自己是活人而爱上文学;但强有力地推动他诗艺发展成熟的乃是古典诗歌艺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长期浸淫,使诗人不但内心萌生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更在实践中努力运用古诗的形式技巧,表现现代人繁复微妙的心灵内宇宙,重铸古典诗美,为新诗送来一份“晚唐的美丽”。这种古典美在诗情之外的艺术天地遨游中有更为内在彻底的表现。
其一是意象选择的古典性。林诗呈示着浓郁的抒情倾向,它常以景以物抒情,用意象暗示表现生命的体验与感悟,间接、客观、朦胧。林诗这种抒情倾向与传情模式都暗合了整个现代诗派的追求,以至当时人们就称林诗为“中国所流行的意象诗派”,只是诗人在这种意象艺术追求中已加入独特的创造:常用传统意象传达现代情绪,或者说常用古诗的境界与意象表现心灵,引入体验的象征内涵。稍作检索就会发现,林诗中除常起用远山的狮吼、冰裂的声音、春天等几组热烈明朗的意象,以求与诗人追求渴望的乐观明亮情怀对应外;大量存在的是黄昏孤灯、荒村枯树、细雨秋风、静夜斜阳等古诗常见意象,同诗人孤独寂寞的心灵相契合。这一趋向赋予了林诗整体象征的深层意蕴以及完整的境界,能够唤起人们蛰伏在心底的稔熟的审美体验积累,让人倍感亲切。如“邻院的花香随着晚风/黄昏的家门蝴蝶飞出了/没有梦的昨夜留恋什么呢/无声的荒草变了颜色/远处杜鹃啼/暮色沉重下/双燕如青春的影子/掠过微黄的窗外”(《春晓》)。随着缤纷意象花瓣的飘落转换,诗曲折地暗示出了诗人由寂寞而悲愁而欣悦的心理情绪流程。这种以意象暗示的写法避开了浪漫的直抒,是象征诗的典型写法,间接婉转而又含蓄;但它的意象几乎全出自旧诗,尤其五六句愈见古典诗之神韵,内涵也明朗而定型,子规啼夜的杜鹃固定寓意,令人一下子即可捕捉到诗人的悲愁心境。《春野》以春风流水暗示诗人心灵的欣喜也是象征笔法,但“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这种景色渲染,与“柔和得像三月的风/随无名的蝴蝶/飞入春日的田野”这种境界、画面、比喻,在古代田园诗中都屡见不鲜,多而又多。
需要指出的是,林庚诗的意象艺术追求,并非无益的复古。因为林诗的意象语汇的外形是旧的、古典的,而境界情感的内生命却是新的、现代的。对这一点稍留意一下林的春天诗与古代的春天诗就会清楚。同写春天,古诗多以春天的系列意象烘托情感,意象本身的地位醒目突出;而林诗意象的缤纷错落已让位于现代人生命的自由自觉、现代人生的解放与舒展。前者让人承受的是某种心灵触动,后者却会让你感动而切近,如《春天的心》中桃花、眼睛、水珠、江南的雨天等传统意象,已成为现代情绪、现代人青春躁动复杂情绪的载体,这也正体现了林诗现代性之所在。
其二是语言的简隽暗示。在林庚看来,多余的诗句会减小诗的力量,尤其是形容词更容易把原有的气象限制住;所以他写诗常为锤炼语言而呕心沥血,在注重意象的跳跃外还十分注重语言的删繁就简,精益求精。在写《窗》那首诗时他“不断地把七八行诗变成两行,一行,到有一句可用仿佛才可以喘过一口气来”[6]。《破晓》更是数易其稿, 堪称千锤百炼的结晶,前八句跳跃的意象并置有蒙太奇之奇妙,那是一种气韵生动、美妙绝伦的意象流转,至结句“如人间第一次的诞生”则已是前八句水到渠成的喷涌,在无穷的韵味里陡增了诗的雄厚。
为追求诗的凝练简隽,诗人还起用了一些陌生的手段,一是有时故意把向度相反或相对的两类意象或情感等因素拷合一处,使其相生相克,给人以多重复调感,收到尺短意丰的效果。《春晓》即以花香、晓风、蝴蝶与荒草、暮色、杜鹃两种相反色调的意象对比交织,凸现寂寞又欢欣的两种不同的感受。《时代》也混合了抑郁与欢欣两种对立的情思,诗人因时代丑恶而忧郁,又因时代中萌生打碎丑恶的力量而欢欣;正因为有了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所以才有了如此宏大的题目。如果说《春晓》、《时代》等是凭借意象、情感的特殊组合爆发出张力;那么《春天的心》则是靠语势的对立转换而寻找张力的。“美丽的东西到处可以拣起来/少女的心情是不能说的”,“含情的眼睛未必为着谁/潮湿的桃花乃有胭脂的颜色”,这四句诗里却隐含着语势的转换变化,前二句间是相反的平衡语势,一正一反,一轻柔肯定,一轻柔否定,两行相联完整又妥帖,三四句间则相互描写,花与眼睛相互衬托印证,出人意料又美妙绝伦,透着一种心的愉悦,相反的平衡、相互的描写这不同语势的对比相合,适口、活泼,妙不可言。林诗这种意象、情感、语势的有跨度的矛盾对立架构,既拓宽了诗的内涵量,扩张了诗的聚点与情绪宽度;又以特殊的张力促成了诗的活泼变化、仪态万千。
二是时而创造令人眼花缭乱、不可重复的比喻,将一切事物化作内心世界的暗示联想。除却路易士的《你的名字》外,笔者从未见过像林庚那样比喻繁富的诗。如“人的娇小/宇宙的涵容/童年的欣悦/像松一般的常沐着明月/像水一般的常落着灵雨/像通彻的天宇/把心亮在无尘的太空/像一块水晶石放在蓝色的大海中//如今想起来像一个不怕蛛网的蝴蝶/像化净了冰再没有什么滞累/像秋风扫尽了苍蝇的粘人与蚊虫嗡嗡的时节/像一个难看的碗可以把它打碎/像一个理发匠修容不合心怀/便把那人头索性割下来”(《那时》),一连串绵延不绝的比喻,清新爽朗干脆痛快,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再如《自然》中“独角鬼追逐着风/来去如寻找/吹过如留恋……”一连串“如”的连用,将具象与抽象、景语与心语交错得闪烁迷离,难辨泾渭,流动而不确定。奇的是林诗不少“像”、“如”的连用根本不是为创造比喻,而是想让一切印象、意念与形象呼唤出共同的回声,把一切事物都化成相关的暗示联想,显示意象的联系,这无疑增加了林诗语言的新鲜与纯粹。
其三是“现代绝句”的创造。有一点令不少人迷惑不解。当林庚具有散文诗情趣的自由诗渐趋艺术峰巅、声誉如日中天之时,却于1935年逆流而上,反叛戴望舒等人提出的自由诗不乞援于音乐的纯诗观,反叛散文化,并阐述韵律主张,开始格律诗创作,以致遭到了戴望舒、钱献之等人的围攻。实际上林庚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在新诗黄金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的自由诗成了继诗界革命后的又一次革命高峰;但革命即短命,它与那些口号诗同样泛着散文化弊端,而散文化太重的诗尚不及旧诗的境界,因此新诗在革命后应走向建设,不能让散文革了自己的命。怎样建设呢?历史上诗歌每次散文化热潮后必有诗化过程,如楚辞后乃有五、七言诗这种传统艺术回顾,为诗人指明了方向。他认为深入活泼,但只宜深入不宜浅出,一浅出就会倒入散文的泥淖,它只宜表达刹那的心得,来不及酝酿发酵的创作;只有韵诗才行有余力从容自然,具有深厚的蕴藏,具有文质一统后谐和均衡的成熟气象,也只有它才能把新诗从散文化困境中解救出来。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林庚开始创作四行诗和兼具四行诗、自由诗长处的节奏自由体,并在实践中寻找新的音组与节奏。他认为平仄只是应该去除的装饰性外在物,汉诗节奏上有种类似“逗”的节奏点,发现“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以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8 ];同时以五字音组为基础尝试九字、十字、十一字、十二字以至十五字的诗行探索。如《秋夜的灯》、《道旁》、《北平自由诗》、《四月》、《井畔》、《古意》等都可视为典型的现代绝句,都吻合了诗人的理论主张,外形整饬对应,音乐感强。如《秋深》这样写道:
北平的秋来故园的梦寐轻轻像帐纱
边城的寂寞渐少了朋友远留下风沙
月做古城上情人之梦吧夜半角声里
吹不起乡愁吹不尽旅思吹遍了人家
首句点出怀乡之思,次句裸现游子寂寞之心,朋友稀疏平添了一层寂寞,而深秋风沙所起的焦躁更加重了寂寞之深,尾句则发出无奈之感叹。它不但意象群落古典气十足,诗行排列更是别致,实现了诗人五字节奏最自然的理论主张,那整齐划一的字数、贯穿又自然的韵律、字句繁富的重叠,正适于表现深厚的意蕴,从而把乡思的寂寞写得含蓄内敛,层层叠叠,环环推进,意味深长。其实林庚1935年以前写的一些自由诗也都具有格律诗成分,如《洗衣歌》即似清新欢快的劳动歌谣,轻松活泼,有着极强的音乐性。
林庚的新格律诗理论主张与见解在当时出现是相当深刻的,只是它在自由诗盛行的特定环境下有些不合时宜,因而被人们忽视了。对诗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悲剧。
林庚诗歌在艺术上确实古典气十足,用“晚唐的美丽”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与那个阔大的时代相比,林庚的诗歌天地是狭小的,声音是微弱的,有些诗只是印象毫无深意的排列;但它毕竟以独特的存在留下了一代知识分子心灵跋涉的清丽幽邃的诗情,真诚而又真实。尤其是诗人以一种严谨的艺术态度,为后人创造了一片不可一目十行浏览必须句句细读的优卓艺术景观,令人沉醉流连,让人丰富提高,为《现代》的总体格调中吹送进一股沉郁而雅丽的北国信风。
(今年是著名学者、诗人林庚教授90华诞。本刊特发表此文,谨表祝贺)
收稿时间:1999—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