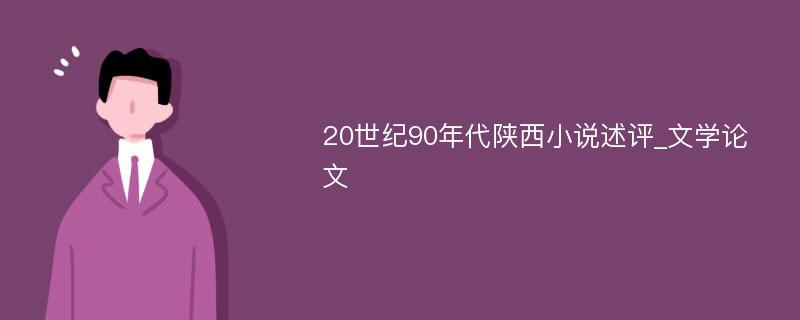
九十年代陕西长篇小说评论之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陕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带来了评论的繁荣,为我们审视陕西评论队伍的实力与不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同时也为窥视陕西长篇创作的得失提供了一面折光镜。
长篇小说所独具的形式因素(大容量、高密度、广阔的时空范围、自由的描述方式等)和反映时代、揭示生活方面的特殊优势(可以涵括比较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包含较深的思想意蕴,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走向等),决定了长篇小说的评论具有其他评论所难以替代的作品,比如——
由于它的份量比较重,力度比较强,因而比较引人注目,容易对创作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比较易于造成一个阶段乃至一个时期评论的热点,从而引导评论的走向;
同时,正如长篇小说的创作比较容易推出作家一样,长篇小说的评论也比较容易推出评论家。只要回顾一下柳青的《创业史》之于刘建军,贾平凹的《浮燥》之于费秉勋,陈忠实的《白鹿原》之于王仲生,我的这一断语也许就不难成立了。
当然,从事长篇小说的评论又有特殊的难度,至少,其评论对象的庞大篇幅对评论家的韧性、概括力和宏观把握能力就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加之由于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目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评论正在急剧萎缩,让评论家耐心地读完几十万字的大部头再去评头品足,显然要比评论几万字的中篇小说或万把字、几千字的短篇小说费劲得多,这里匮乏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有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阵地以及平和、沉稳的创作心态。正因为如此,在论及全国近几年开始出现的长篇小说取代中短篇这一趋势时,一些评论家不无遗憾地指出,眼下长篇小说崛起后,批评界却迟迟没有从相应的角度尽其职责,就此而言,长篇小说热也许有些生不逢时,它很难指望得到类似于当年中篇小说崛起时批评界所曾给予的呼应。
全国如此,那么我们陕西的情况又如何呢?
二
就长篇创作而言,陕西近几年来势头之猛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与之相应的是,陕西评论界也出现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二个活跃期(第一个活跃期是八十年代中期以“笔耕文学评论组”为代表的中年评论家群体对省内外中、短篇小说的评论)。
在一系列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作品研讨会和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我认为最近这一活跃期中有两件事带有某种开创性的意义。
一是对《白鹿原》的评论。据我很不完全的统计,陕西评论界围绕这部煌煌巨著在省内外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发表了数十篇评论文章。仅《小说评论》93年第4期的专辑就刊出12篇论文和1篇综述。其篇数之多,为几十年所罕见。也许是作品本身惊人的探索勇气为评论者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陕西评论界在对《白鹿原》的研讨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热情。
一批论者从比较广阔的背景上,对这部全景式的作品进行了全景式的观照。其广度、深度和力度都较前有所进展和突破。
有的论者秉承了作家本人闯禁区的勇气,对某些久悬不决、噤若寒蝉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有胆有识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和发现。我省评论界长期以来比较沉稳的总体面貌似乎有所改观,接纳“异端”的绅士风度似乎也有所强化。我们尽可以对这些具体观点持保留态度,但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对这种探索精神和这种久所翘望的真正的“百花齐放”局面表示真诚的欢迎。
有的论者努力运用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评论,从社会学、文化学、文艺美学、比较文学、阐释学、叙述学等多种角度对审美对象进行观照,尽管有时也有失之皮毛之虞,但陕西评论界知识结构不够新,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的原有格局却开始有所打破。
还有的论者侧重从艺术规律、特别是叙述形式和语言特色的角度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开始改变了我省评论界以往比较侧重思想内涵的社会学分析,比较忽视对形式——技法的美学、文艺学分析的弊端,开了新生面。
和《白鹿原》的研讨同样具有开创意义的是畅广元教授主编的《神秘黑箱的窥视》一书。它选择了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五位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和李天芳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让作家、评论家和青年学者共同就每一位入选作家的创作实践与创作心理进行对话:年轻的学者首先写出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论文;作家在读过这些论文之后,既可以对它作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评说,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感悟;然后,评论家再对二者进行评论。我以为,这部“三极对话”的著作对陕西文学评论事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一,它从作家的创作心理这一“神秘的黑箱”入手,来探寻陕西作家创作的规律和艺术的奥秘,这就为陕西评论界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支点——创作心理学。
第二,通过中年和青年评论家的对话,使后者的学术锐气,比较新的知识结构与前者的理论功底、人生阅历实现互补,从而为陕西评论界引入一股清新的朝气和强烈的现代意识。
第三,通过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不仅有利于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而且可以使广大读者感受到一种相对客观的“呈现”,从而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去把握作家的创作。
通过对《白鹿原》的评论和《神秘黑箱的窥视》一书的编撰,我省的文学评论,特别是对长篇小说的评论[①],向深化、广阔化乃至成熟化的方向迈出了切切实实的一步,开始显示出这样一种久所期盼的目标和风格:力求坚定,不随风摇摆;力求准确,从生活和作品出发;力求真诚,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文过,不媚俗。但与此同时,也豁露出我省长篇小说评论所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
首先,是缺乏把长篇小说的勃兴作为一个整体现象的研究。
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陕西长篇创作的总体态势、特点、优劣及趋向的研究。二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特征的研究。对具体作品和个别作家的研究固然必要,但若忽略了整体研究,往往事倍功半。
比如,陕西的长篇与其中短篇一样,历来有现实主义的传统,近年推出一批新作仍然继承了这种传统,但若与《保卫延安》、《创业史》相比,其现实主义已明显地开始有所深化、变化和发展。弄清这种变化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态,它们分别具有那些价值和不足,又应该向什么方向深化,这对于我们陕西作家自觉地探索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实现新的突破显然至关重要,而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超越具体的作家、作品,对陕西长篇创作进行总体性和比较性的研究。
又如,从近年我省推出的一批长篇新作来看,在驾驭这一体裁方面或多或少暴露出种种力不从心或捉襟见肘的现象。有些作家是在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均不足于驾驭长篇的情况下匆促上阵的。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对长篇体裁的研究不够恐怕有一定的关系。八十年代中期,陕西评论界一度曾对小说文体学有所涉及,并将它运用到对当代陕西小说以及外地小说作品的分析中去,但那时我们的审美对象主要是短篇和中篇,至于长篇小说则几乎没有多少成功的实践。而今天,面对我省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的新鲜实践,陕西评论界的一项当务之急便是结合本省以及全国长篇小说的最新实践,认真研究长篇小说的现代文体特征。比如,长篇小说中应该如何运用视角;如何经营意象;如何考虑结构;如何更新长篇小说的传统叙述方式;如何使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仅成为一种“叙事的艺术”,而且做到“艺术地叙事”,即艺术地构成小说文本,如何对长篇小说这一体裁进行艺术上的调整;等等。对于这一研究所客观存在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李洁非说过一段对我们很有启示的话:
实际上,这个问题(按指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引者注)在整个现代世界小说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以及《城堡》这样一些现代作品诞生以来,长篇小说的的文体概念——特别是它的结构方式——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把这些作品与《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甚至于包括《包法利夫人》、《罪与罚》在内的传统或半传统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多少共同点。据我所知,西方批评家很早以前就研究过长篇小说文体的“现代”含义和“传统”含义之间的差异。但在我国,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来得太迟。直到几年前,我们在长篇小说上仍然遵循着“巴尔扎克模式”,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缺乏敏感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四
其次,我们还缺乏对我省长篇创作的形式——技法的认真研究。
应该说,上文所述长篇小说的现代文体特征研究本身就是形式——技法体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我其所以将后者专门单列出来加以强调是因为第一,文体特征只是形式——技法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后者所包容的内容要远为宽泛。第二,前述的文体特征研究主要系指对长篇小说体裁的整体性理论研究,其形而上的成份要多一些;而形式——技法研究则侧重于对我省长篇作品的形而下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的评论界似乎形成了一些较为普遍的薄弱环节,诸如缺乏新的参照系,缺乏新的知识结构,缺乏多元化的视角,缺乏多侧面的审视,等等。特别是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往往是撇开形式直奔内容,在浓墨重彩地描述完内容之后才回过头来对形式作一番隔靴搔痒的轻描淡写,形式成了内容所随意选择的对象或木偶。这种倾向,在当前我省长篇小说的评论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大多数评论仍然集中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人物形象这样一些热点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对通向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作家所采取的形式和技巧,包括结构、手段、语言等,论者就寥寥了,而且往往是作为一种次要的补充性成分在对内容的重点评论之后才予以提及。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长篇小说语言的研究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原有的批评框架中比较缺乏对文学形式的精细研究的话,那么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则是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尽管教科书早就把文学定义为“语言的艺术”,尽管美国文学理论家理查德·泰勒正确地指出:“风格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而具备的一种功能”,[③]尽管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思想存在的家园”,“谁把握了语言,谁就把握了文学本质”,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十分重视作家“精通叙述艺术”的能力,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似乎语言是短篇小说的专利品,至多延伸到中篇,而一旦涉及长篇,作家便只能倾心于讲故事、讲谋篇、讲人物,再也无力去顾及语言,评论家也是倾心于讲故事、讲结构、讲人物,同样无暇去评论语言。这种现象在我们陕西创作界和评论界也不例外。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就总体而言,我们陕西作家在叙述形式和叙述语言方面急待提高(我省作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同秦腔的文学性与京剧、昆曲、越剧之间的差距有类同之处)。尤其是长篇,它对作家艺术修养的缺陷来说无异于一面放大镜,而对其语言修养的缺陷而言则是一面高倍显微镜。不近,近年来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便如贾平凹和陈忠实正在不同的方向上对文学语言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探索,特别是后者对关中方言的运用和改造尤其引人注目。正因如此,当我近年来读到薛迪之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论《白鹿原》语言的“张力”时,就象我读到李小巴专文论述同一作品的“叙述形式”、晓雷专文探讨陈忠实“翻鏊子的艺术”一样,感到一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清新感和亲切感。但恕我直言,这方面的探讨(无论是有关长篇小说的形式、手段还是语言的研究),不仅数量仍属寥寥,深度也未尽人意。
五
第三,我们的长篇评论中还缺乏一种面对实际、坦言直陈的气氛和勇气。
陕西的评论界,就总体而言,是一支严肃的、有正气的集团军。其标志,一是评论界内部关系比较融洽,文人相亲远多于文人相轻,评者相助远多于评者相诛。二是外部关系也比较协调,评论家与作家既相互尊重,又“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一般情况下评论家能够从作家和作品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独立的艺术评论。
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和地方。
其一,当前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整个文化艺术界都陷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境地。为了走出困境,纯文学刊物只好出卖版面刊登“企业文化”宣传品,纯艺术报刊甚至明码标价出售版面刊登“有偿稿件”。与此相配套的是,近年来由作者本人(包括作者拉来的企业家)出资与文学机构联合召开的各类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研讨会多起来了。这固然不失为无奈的现状之下繁荣创作和评论的一条路子,但我担心,在这样的研讨会上我们的评论家是否还能够坦然面对作品的实际和自己心目中那杆神圣的批评标尺,直言相告作品所存在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难怪北京作家陈建功要召开一个自带餐费的讨论会以示与这类“专说好话”的讨论会划清界限,据说到会者相当踊跃。
其二,我们的评论界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因此,当政治生活中的“翻鏊子”现象不幸又再度出现时,我们的文学评论界恐怕也很难以顶住而不违心地参与其中。近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与其去探究个别人为什么要违心,不如集体来反思我们的文学评论是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真正具备了“独立法人”的资格、品格和特征,我们的“评论自由”是否真如我们所乐观估计的那样已经完全实现。
其三,当面对一种潮流化的力量汹涌而来时,我们评论家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力量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忠于作品的实际,忠于生活的实际,忠于职业道德和良心?我一方面高兴地看到,当某些领导同志对陕西有的作品的看法和我们评论家自己的看法不尽吻合时,我们仍能坚持护卫自己的艺术见解,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当今中国是难能可贵的。但与此同时我又困惑地发现,陕西评论界对本省重要作品的评价,比如对近年“陕军东征”的五部长篇的肯定性评价,居然如此铁板一块。据我眼力所及,近年来陕西报刊上对这五部作品很少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不仅与外地某些批评的呼声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且与我在会下、报刊之外所听到的“民间评论”也不尽吻合。比如,这几部长篇巨作何以能超越当今严肃文学门可罗雀的困窘局面,大踏步地走向市场,甚至创造长安纸贵的奇迹?
是对人生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的成功描绘引起了多层面读者的共鸣?
是大量吸收新潮小说的语言句式适应了更大范围的读者?
还是细腻生动、不乏渲染的性描写迎合了商业主义的需要?
抑或是对古代禁书的现代模仿收到了广告的诱惑功效?
在这诸多因素中,哪些是严肃文学走向市场必需的革新与越位即超越自身的传统地位,哪些是严肃文学面临危机时无可奈何的俯就与牺牲,哪些又是纯功利性的廉价拍卖?
据我所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近期出版的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评论界以至广大读者的意见并不一致,特别是对性意识在我们的长篇新作中的集中表现和过分渲染,担心甚多,微词不少。但奇怪的是,一旦到了研讨会上,一旦写成文章或纪要发表,对立意见就消失了,至少梭角就磨平了,舆论自然而然也就同一化了。多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舆论一致并不是好兆头。现在反映出来的对五部长篇的正式评价如此一致,我感到需要冷静思考一下,在它背后有没有被掩盖起来的某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倾向?
注释:
①《窥视》一书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评论了我省一批长篇近作的得失,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邹志安的《爱情心理探索》系列长篇、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等。遗憾的是,由于该书出版较早,最近问世的几部影响更大的长篇新作未能涵括。若能按照《窥视》的体例对这几部新作再来一次“窥视”,将功莫大焉。
②见《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
③《理解文学要素》,四川文学出版社会1987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