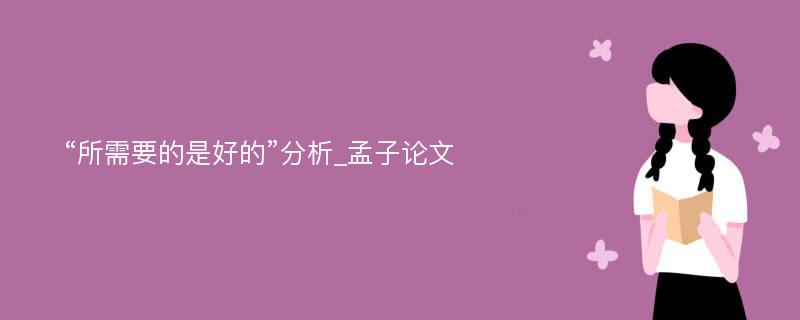
“可欲之谓善”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谓论文,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伦理学作为道德哲学,其基本任务是“明善”,即说明何谓善及善之为善的木质。但是,从上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摩尔《伦理学原理》开始,直觉主义者就认为善是“不可定义”即不可“明”的,否则就必然会犯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此书就哲学而言,是西方20世纪哲学主流——分析哲学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就伦理学而言,则是西方20世纪伦理学主流——元伦理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摩尔此说已成为西方主流伦理学的不刊之论,“明善”自此之后就被逐出了西方主流伦理学的理论殿堂。
本文力图说明,以“明善”为基本任务的传统伦理学确实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缺陷——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并希望以此作为进一步反驳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之说的基础。
一、“可欲之谓善”的两歧
作为世俗的、理性的伦理学,其对“善的本质”的思考和证明,必然会诉诸人本身、诉诸人的行为及其目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思想家们的基本思路是:值得追求的就是善,如果用中国传统的理论命题来表述,就是“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然而这一命题中的“可”,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值得”,对此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可能,并正好南辕北辙。
可欲,值得欲求的,可以指应当欲求的。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承认,生命的保持与仁义的践履都是他所欲求着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以至不得两全之时,“应当”舍生而取义。“应当”欲求的,就是善。
可欲,值得追求的,还可以指事实上所欲求着的。从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可以推断,只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值得追求的,所以才付诸行动、实际地欲求着。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欲求着富贵,厌恶着贫贱。由此可以推断,富贵是“可欲”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实际地在欲求着富贵。事实上所欲求着的,就是善。
“可欲”的这两种理解,有着根本的差异。“可欲”之“可”如果理解为“应当”,那么,“善”就是在“价值”意义上被理解的;如果理解为“是”,“善”就是在“事实”意义上被理解的;如果理解为价值之应当,则意味的是人的欲求目标的选择问题,这就是承认,在事实上人们所欲求的目标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但这些所欲求的目标在价值上有所不同,善乃意味着一个人作出的选择应当是那些价值上占优的目标;如果被理解为事实之是,就意味着善是当下自成、圆满自在的:无论一个人在欲求着什么,他在欲求着这一行为,就已经确证了他所欲求的目标是“可欲”的,因而他所欲求的就是“善”。这就是说,“善”是一种被给予的事实。
是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化,使得思维发现自身在思维价值问题时存在着两歧,当思维试图明确地把这一两歧揭示出来时,无非是在呼唤新的生活世界和努力理解现代社会。最先意识到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之本质不同的,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前夕的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休谟,但他在《人性论》中含含糊糊地表达出的困惑和疑问,表明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真正深刻地理解到这一问题、并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作为其道德哲学理论建构之前提的,是康德。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一个附注中说:“以其为善(sub ration boni)这个语词是义涉双关的。因为它可能是说我们之所以把某种东西表象为善的,乃是我们欲求(愿望)它;但也可能是说:我们之所以欲求某种东西,乃是因为我们把它表象为善的;这样,或是欲望是作为善之客体的概念的决定根据,或是善的概念是欲求(意志)的决定根据。”(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当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善的,总是与我们的欲求相关,总是在表达着我们的欲求,此乃谓“可欲之谓善”。但是,康德指出这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既可以是因为我们欲求着某对象、目标,所以这对象、目标就是善的,也可以是因为我们把某一对象、目标当作是善的,所以我们才去欲求它。这一区别决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持前一理解,等于主张以当下自在的欲望作为“善”的根据;持后一理解,等于主张“善”是决定我们应当欲求些什么的根据。
出于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道德直觉,人们大概很难认同善是当下自成的事实,否则无论一个人做什么,是月黑杀人夜、还是风高放火天,统统都是善的,这实际上取消了一切善恶之别。生活常识和道德直觉告诉我们,善,是价值之应当,意味着行为有价值,意味着价值目标的选择乃至人的自我实现。当然,这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一种意见。这也就足以说明,对“可欲之谓善”的两种理解有着极为根本的差异;区分这两种理解的差异、并从逻辑上一贯地坚持这一区分,决非易事。
二、对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相应考察
孟子的“可欲”,指的是价值之应当,整个儒学传统中的“善”,都指价值之应当。
孔子说:“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显然,这里与“恶”对举的“志于仁”就是“善”,“善”就是“志于仁”。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这里说的正是:事实上人们欲求的对象或目标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利与义(这儿的“善”应当指“义”)。相关于这两类欲求对象而付诸行为的可以概括为两类人,区分善人与恶人的基本标准就是看,是欲求着义、还是欲求着利。孟子此话的结论是:义,是应当欲求的,利,是不应当欲求的。
但是,对于任何主张“善”是价值之应当的学说而言,必须在理论上进而去证明“为什么”,即为什么义在价值上优于利,乃至说明这一“价值”意味着什么。那么,孟子用什么来说明义在价值上优于利,乃至这一“价值”意味着什么呢?——事实!孟子居然用某种“事实”来说明这些。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说。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所谓人性本善,指人生来就具有善的本性。如此,善就成了被给予的事实。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性本善指人“固有”仁义礼智,也就是说,作为人的本性,就是被给予着仁义礼智这一事实。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传统思想主流,使得人性本善的学说早已深入人心。人们虔敬地奉持着这一学说,在道德冲突的困境中总是诉诸这一学说来寻求信念的支撑。然而,这一学说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谬误,尽管是一个有其美好一面的历史性谬误。
“可欲之谓善”,如果“可欲”指价值之应当,就不是当下自成的事实;如果“可欲”指事实之是,就不是需要选择的价值。孟子既然主张善指价值之应当,那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义在价值上优于利,这里的前提是,作为事实,人们既欲求着义,也欲求着利。而孟子的性善学说对此的解释却是,因为仁义是一个被给予的事实。价值之为价值,本来应是对事实的规范,却被理解成被规范了的事实。
这样的讨论也许太抽象,那就不妨从朱熹注“可欲之谓善”的文字来作点具体分析。朱熹注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孟子集注》卷十一)这话的意思是,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必然之理,事实上,若善,必定是可欲的;若恶,必定是可恶的。通俗点说就是,善必定会在人们的心理是引起欲求的意愿,恶必定会引起厌恶。
朱熹这些话很符合人们通常的道德直觉,而且,对此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证:在事实上,善,肯定是可欲的,否则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些志士仁人。志士仁人们自然是以善为可欲的,故在其生命实践中欲求着善而成其为志士仁人。但是,既然是讲事实,在经验生活的领域内讨论问题,就需要分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
朱熹认为,善必定会在人们心理上引起欲求的意愿,恶必定会引起厌恶,这是“天下之理”。“理”,在理学中意谓不必去作多余的讨论,只要取其普遍性和必然性就够了。因此,朱熹的意思可以表达为,作为事实,人人都是欲求着善,决不会欲求恶;人人都是厌恶着恶,决不会厌恶善。但是,这是一个普遍、必然的事实吗?这个逻辑上在先的命题是一个普遍、必然的事实吗?
概念都有其时代生活的内涵。贯通不同的时代,生活才得以成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这就往往使得人们用自己的生活来理解完全不同内涵的生活。作为对概念的理性分析,必须结合历史生活的事实去分析。朱熹的注所使用的概念是善恶对举,不同于孟子的普利对举,而在儒学传统中,更多的是义利对举。也许在不同的场合,这些不同的对举着的概念自有其相区分的必要性,但儒学主流传统中这些概念的基本意指是一致的:善,意味的是仁义,恶,意味的是功利。那么,问题明确起来就是:仁义是人们所欲求的,功利是人们所厌恶的,这是一个普遍、必然的事实吗?
这是事实,但不是普遍、必然的事实,因为还存在着相反的事实:功利也是人们所欲求的。孟子本人就说过:“生,亦我所欲也”,这是与“义,亦我所欲也”对举成言的,大概可以理解为“利,亦我所欲”。其实,作为事实,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以致招来弟子孟更“不以泰乎”的责难(《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宋受赠金七十镒,在薛受赠金五十镒(《孟子·公孙丑下》),总不能说孟子只欲求义,不欲求利吧。也许儒门中人会反驳:以生命之持存乃行仁义之根本(就如同今人所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云云)能证明“生,亦我所欲”,但这不能解释成“利,亦我所欲”。对此,笔者可以举出,孔子也说过“利,亦我所欲”一类的话:“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他老人家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做市场的守门卒我也干;如果求它不到,还是我干我的吧。此语表明,孔子以为,一、利在事实上是可欲的,也是他老人家之所欲;二、虽然是其所欲,但若求也求不到,还是去做那些想求而又能求得到的事情吧。此义后来孟子发挥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其意还是:虽所欲也,不可求也。可见,事实上利总是被欲望着的。
任何理论学说都必然要求思想上的逻辑一贯,孟子既然承认“义,亦我所欲”、“利,亦我所欲”,那么相应地,“可欲之谓善”就是一个价值命题,意味着义比利在价值上具有优先性;因此,孟子就不能说人性本善(人的本性就“是”善的,是一种事实判断)。孟子既然主张人性本善,这样,“可欲之谓善”就是一个事实命题,孟子就不应该有对利的欲望,然而,孟子却承认他对利也有欲望。“可欲之谓善”应当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不能同时都是。然而孟子混淆了事实与价值之不同,结果就成了价值之为价值,本来应是对事实的规范,却被说明为被规范了的事实。
这不只是一个逻辑错误,而是一切传统伦理思想所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谬误:不能在思想上区分出事实与价值的本质不同。这一历史性的谬误在根本上是传统社会的生活世界的谬误,并成为与传统社会的生活世界相适应的传统的理论思维的界限标识。
三、对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相应考察
上面已经引用过康德对“可欲之谓善”之两歧的准确表述。可以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主要是针对英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建构起来的,虽然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边沁和穆勒晚于康德。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在内容上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伦理学,反映着新的生活世界的伦理取向,在思维方式上也是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典型代表,但在事实与价值问题上,在关于价值问题的思维方面,却不折不扣、完完全全地重复了上述历史性谬误。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是休谟之后的产物,考虑到休谟已经表达出对事实与价值之不同的困惑,那么我们就能体会到在思想上区分出事实与价值的不同、并逻辑一贯地坚持这一区分,确实十分困难。
功利主义伦理学就是主张以人的当下自在的欲望作为“善”的根据的。其关于价值问题的思维原则是:因为我们欲求着某对象,所以这对象就是善的。穆勒认为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就是承认只有快乐,因为它是目的而认其为可欲的事物,而且一切可欲的事物是因为它自身本有快乐,或是因为它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方法而成为可欲的事物。(注:穆勒著,唐钺译:《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7页。)在穆勒乃至所有功利主义者的语汇中,快乐以及免除痛苦就叫幸福,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所以凡能增进快乐及避免痛苦的事物对人来说都是可欲的,都是善的:“换言之,至于目的的问题是关于什么东西是可欲的。功用主义的主张是:幸福,因是目的,是可欲的;并且只有幸福才是因它是目的而可欲,一切别的东西只因它是取得幸福的工具而成为可欲的。”(注:穆勒著,唐钺译:《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7页。)
也许,幸福确实是人生的目的,因为不管人们对何谓幸福有着纷繁的理解,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欲求到自己所欲求着的东西称作幸福。但是,伦理学作为对人类生活的哲学思考,任务在于回答为什么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穆勒这样回答:“只有人真正见到这个东西才能够证明这个东西是见得到的;只有人听到了这个声音才能够证明这个声音是听得见的,我们经验的其他来源也是这样。同理,我觉得只有人真正欲望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可欲的那个意见所可有的证明。”(注:穆勒著,唐钺译:《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7页。)显然,穆勒对“为什么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的回答是,因为人们事实上欲求着幸福,所以幸福是可欲的:“假如人的本性就使他对于凡不是幸福的成分或幸福的工具都不欲望,那末,这就证明只有这些是可欲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有其他证明,也用不着其他证明。”(注:穆勒著,唐钺译:《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1页。)但是,伦理学的任务就在于证明“为什么”,穆勒之所以认为用不着其他证明,原因在于他在思考价值问题时犯了错误:没有区分开不同意义上的人生目的。揭示出这一错误的,正是与穆勒同为英国人的摩尔。他说:“穆勒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目的’,即在值得(用本文的术语,则就指‘应当’——引注)想望(指欲求——引注)的东西的意义上的‘目的’和在所想望的东西的意义上的‘目的’,尽管这种区别是这一论证和他全书的前提。”(注:摩尔著,长河译:《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页。)
没有人能比摩尔更彻底地揭明穆勒混淆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思维错误,所以笔者照引如下:一、“事实上,‘值得想望的’并不像‘可见的’意味着‘能见的’一样,意味着‘能想望的’。值得想望的东西仅仅意味着应当想望的或者该想望的事物。”(注:摩尔著,长河译:《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页。)“‘值得想望的’一词的正确意义是表示这样的东西,对它的想望必定是善的;如果把这个词看作跟‘可见的’这一类词相似,那么,它就会具有另一种意义。穆勒把这两种意义混淆起来,从而企图确定善的东西跟所想望的东西的同一。”(注:摩尔著,长河译:《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页。)二、“如果所想望的东西事实上就是善的东西,那么善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们行为的动机;从而不存在像穆勒那样煞费苦心地去寻找采取行为的动机的问题。”(注:摩尔著,长河译:《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页。)“穆勒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想望某事物(一个伦理学命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想望着它。”(注:摩尔著,长河译:《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页。)
穆勒以至整个功利主义伦理学犯了混淆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思维错误。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回答何谓幸福,但这一问题只能是在“为什么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穆勒既然取消了“为什么”的问题,那么幸福也就成了某种事实——增进快乐及避免痛苦。然而,取消了“为什么”的问题,就没有了何谓幸福的问题,因为不仅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存在纷繁的差异,而且人们对快乐及痛苦的感受也差异纷繁。
总之,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不同是一个历史性的谬误。“可欲之谓善”,在孟子本指价值之应当,却说成了是人的本性所规定了的事实;在穆勒本指事实之是,却说成了这就是人生应当欲求的价值。所以,以“明善”为基本任务的传统伦理学,确实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缺陷——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但是,摩尔却以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取消了这一问题,取消了伦理学的基本任务——明善。要说明这一点、要坚持伦理学以“明善”为其基本任务,就必须克服上述理论缺陷,就必须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揭示出“事实”与“价值”的内在关联,而这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元理论的层面上深入考察“是与应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