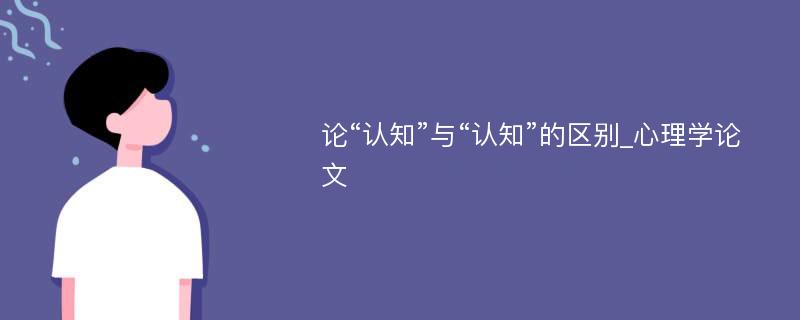
再论“认知”与“认识”的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认知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论“认知”与“认识”的分野》〔1〕一文中,我们论述了“认知”与“认识”的分野并阐明了用“认知”取代心理学中“认识”一词的进步意义,并对赵璧如先生《论用“认知”取代“认识”的问题》〔2〕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1995年以来,赵先生又相继发表了四篇关于“认知”取代“认识”问题的论文〔3〕,其中后二篇是专门针对我的论文。在本文中,我想进一步阐明用“认知”取代心理学中的“认识”的必要性,并对赵先生的观点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认知”的确不同于“认识”
在《论“认知”与“认识”的分野》一文中我们曾经指出,“认识”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有时是指动态的“认识过程”,有时是指静态的认识结果。
哲学中的“认识”的不同含义在哲学工具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表现得很清楚。梅益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对“认识”的界定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或观念地再现现实的过程及其过程及其结果。”(第716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场合也交替地使用认识的不同含义。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现实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这里的“认识”明显是指认识的过程;他又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99页)这里的认识则明显是指认识的结果。毛泽东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这里的认识是指认识的过程;他又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263页)这里的“认识”是指认识的结果,与“理论”同义。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哲学中的“认识”的确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远非仅指心理学所要致力研究的认识的心理过程。由于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在翻译国外心理学著作时,曾一度将cognition译作“认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哲学中的“认识”与心理学中的“认识”的不同含义,所以就逐渐用“认知”取代了“认识”,用它来专指认识的心理过程。这反映了人们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理解的深入,是概念精确化和规范化的标志,因此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认知”这一术语何时产生,笔者未能查考到。但据赵先生考证,“认知”术语最早出现在我国20年代的心理学著作中。例如,在陈大齐著的《心理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14页)中,英文cognition就被译为“认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知”的概念的出现无疑也早于“认识”。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尚书·说命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莫不如此。高觉敷先生指出:“知行也是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双范畴。”〔4〕直到20世纪初,在心理学传入我国之后,在我国思想家的著作中,用知来代表认识和认识过程的仍很常见。现在,在谈及人的心理结构时,人们仍称“知、情、意、行”。可见,“认识”并非常赵先生所说的那样,是我国心理学者“长期使用的规范的概念和术语”,而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它本身带有明显的“借用”的痕迹,是我国心理学发展初期的产物。
目前,“认知”的术语不仅流行于心理学界,也为语言学界、哲学界、教育学界和科技界广泛接受,其含义决非赵先生所坚持的“再认”的念义。例如,曹焰等编《英汉百科大辞典》(人民出版社1993年)对cognition的译法是:“认知,认知力。”(第556页)饶宗颐编著的《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现代出版社1988年版)对cognition的译法与上书相同。可见,将cognition译为“认知”决非我国某些心理学家所杜撰,而是反映了翻译界的新趋势。对于认知的界定,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出版)解释为“认识和感知”(第262页)。韩朝安主编的《新语词大词典》则说:“认知是心理活动最一般和最广泛的范畴。”(第392页)可见,“认知”已经作为规范的译法和科学的术语为语言学家接受,而且赋予了不同于赵先生所坚持的“再认”的含义。在哲学界,“认知”的术语也颇为流行。黄颂杰等译的《新哲学词典》(安东尼弗卢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对cognitive的释义是:“认知的1.指与理解、信念的系统阐述和知识的获得相联系的心理过程,因而与意志过程如意欲,愿望相区别。”(第94页)徐昌明主编的《新英汉哲学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对cognitive的译法是,翻译哲学术语时采用“认知的”的译法,如将cognitive subject译为“认识主体”;翻译具有心理学色彩的术语时采用“认知的”译法,如将cognitive consonance译为“认知协调”,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认知与“认识”的区别。在教育学界,祝洪喜主编的《英汉教育词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设有认知目标、认知学习等冠有“认知”的词条23条,设有认识、认识规律等冠有“认识”的词条5条。赵宝恒等编《英汉双解教育词典〉(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冠有“认知”的词条有8条,冠有“认识”的词条无。
在心理学界,“认知”这一术语更是深入人心,它经常出现在我国心理学家撰写的论文、著作和工具书中,而且不含有赵先生坚持的“再认”的含义。例如,潘菽和荆其诚主编的《大百科全书·心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没有关于“认识”的词条,却设有认知发展、认知发展阶段、认知方式、认知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等词条。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设有与“认知”有关的术语24条,并指出“认识”即“认知”。可见,“认知”的术语已被国内心理学界广泛接受。同时也表明,赵先生所说的“认识”是心理学界长期使用的“基本概念”的说法不能成立。
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也是“认知”术语的使用者与倡导者。他说:“认知(cognition)本来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普通的术语,过去心理学词典或心理学书把它理解为认识或知识(knowing)过程,即和情感、动机、意志等相对的理智或认识过程。它包括感知、表象、记忆、思维等等,而思维是它的核心。”“现代认知心理学家对于‘认知’的理解,仍是各种各样的。美国心理学家霍斯顿等人归纳为五种意见:1.认知是信息加工;2.认知是心理上的符号运算;3.认知是问题解决;4.认知是思维:5.认知是 一组相关的活动,如知觉、记忆、思维、判断、推理、问题解决、学习、想象、概念形成、语言使用等。这里,实际上,只是三种意见:1、2是狭义的认知心理学,即信息加工论:3、4认为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是思维;5是广义的认知心理学。〔5〕朱先生不仅指出了认知是指认识过程,而且指出了思维是认知的核心。
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曾经指出:“认知心理学的‘认知’这个词原来是认识的意思。‘认识’与‘认识’在英语里是同一个字。大概第一个翻译‘认知心理学’的人就这样翻译了,因而大家都讲‘认知心理学’。这样也好,可以使现代认知心理学所讲的认知和一般人常说的认识有所区别。因为,‘认知’这个词的意义已被现代认知心理学用歪曲了。现代认知心理学企图用‘认知’的概念去说明一切心理活动,企图以自己代表全部心理学,这样就使‘认知’这个词远不是原来的意义了。”〔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1)潘菽认为“认知”与“认识”同义,而绝非记忆过程的一个环节;(2)潘菽并不反对使用认知的术语,而是一位的狭义的认知论者。藩菽所不同意的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企图用“认知”的概念去说明一切心理活动,而我国目前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我国心理学家虽然在广义上使用“认知”的概念,但并未企图用它去说明一切心理活动,更没有出现赵先生所说的“全盘认知心理学化”的现象。虽然近年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日渐增多,但人格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等其他研究方向也在蓬勃发展,并未出现认知心理学独家垄断的局面。
荆其诚主编的《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则是在广义上使用认知的概念:“认知(cpgmotopm认知)是全部认识过程的总称,又称认识。它包括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语等,及其发展过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第397页。)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也在广义上使用认知的概念,该书将学习理论分成两大体系:刺激--反应理论和认知理论(第55页)。使用广义的认知概念的还包括港台和海外的华裔心理学家。台湾心理学家张春杰指出:“心理学家对认知行为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三方面的问题:(1)认知行为究竟指哪些行为?对此问题的一般答案是;认知行为主要包括知觉、记忆、想象、辨识、思考、推理、创造等较有组织的复杂行为。(2)认知(cognition)的活动就是‘知’(knowing),个体在生活环境中究竟如何获知,知之后在必要时又如何用知?(3)认知是心理活动,是内在的历程,在方法上应如何研究个体内在的知之历程(knowing process)。”〔7〕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1)张先生在解释中没有使用“认识”的概念,而是使用了“知”的概念,将认识的产生过程称为“获知”,将认识见之于实践的过程称为“用知”。(2)张先生持广义的认知的观点,他不仅指出了认知的范畴,而且指出认知是“获知”与“用知”的心理活动的内在历程。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认知在当前是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概念。认知的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认知是指人的信息加工活动,广义的认知是指认识的心理过程。目前,我国学术界多是在广义上使用“认知”的术语,并以此取代心理学中的认识。实践证明,这一替代并没有造成概念上和思想上的混乱,而是有利于科学地界定认识的心理过程,有利于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完善。上述的讨论也表明,“认识”并非象赵先生说的那样,是我国心理学界长期使用的基本概念。勿庸讳言,心理学在一段时间内曾借用过哲学中的“认识”的概念,但在发现心理学中的“认识”与哲学中的“认识”的不同含义之后,就逐渐用“认知”取代了它。
二、赵先生错误地理解了“认知”
赵先生的五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首先肯定“认知”的含义是recognition(再认),然后批判用“认知”取代“认识”的不合理性。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因为,正本清源,搞清recognition的准确译法,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十分重要。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先看这个词的英文释义。《Webe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Dictionary》对recognize的释义是:“to recall knowledge of:make out as or perceive to be something previonsly known.”《Oxford Avanced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1980)对recognition的释义是:“know,(be able to)identifyagain(sb or sth)that one has seen,heard,etc before.”这两部词典对recognition的释义都是:再次确认或认识以前曾经认识过或感知过的事物。因此,应当译为“再认”。
从recognition这个词的构成上看,recognition是个合成词,它由前缀“re-”和词根“-cognition”构成。 “re-”表示“再、又、重新”等义, “-cognition”表示“认知”或“认识”,两者合在一起应译为“再认知”或“再认识”,即“再认”,译成“认知”无论如何也难以达意。
赵先生还列举了拉丁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对recognition的对应词。但仔细考察,将这些词译成“认知”仍是错误的。拉丁文recognitio、法文recognition与英文recognition同源,其含义自不必说,德文wiederkenntnis也不能译为“认知”,因为它是个合成词,由前缀“wieder-”(表示“再”、“又”)和词根“-kenntnis”(表示“认识”或“理解”)两部分组成,因此应译为“再认”。对于俄文词узпаванё,它的动词完成式为узнавагв。《俄英词典》(莫斯科,1981)明确指出它是"know (again)"的意思,因此也应译为“再认”。
赵先生认为,“认知”和“再认”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记忆过程同一基本环节的内涵的:再认是从重复性的侧面来表达的,只能简单地说明重复的次数;认知则是从经验和体验的侧面来表达的,能揭示它的本质属性和表明它的具体感受,有熟悉感。笔者认为,赵先生的这一理由仍然不能成立。因为,从本质属性的角度看,重复性恰恰是recognition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它道出了记忆与感知的区别,也揭示了再认与回忆的区别:如果从经验与体验的角度看,“认识”一词在生活中无疑也具有“有熟悉感”的含义,如“我认识某人”,“那个地方我认识”。那么,能否用“认识”代替“再认”?显然不能。因此,说“认知”反映了recognition的本质属性是不能成立的。
赵先生认为,有再认含义的“认知”是记忆心理学的“传统规范概念和术语”,只是到70年代后期,个别心理学者开始错误地将“认识”这一基本概念的英文改译为“认知”,开始出现了泾渭不分的混乱现象。但是,在这一时期内,绝大多数心理学者还是坚定不移地继续使用把“认知”与“再认”同义的译法和用法。只是到1986年,在荆其诚和张厚粲译的司马贺著的《人类的认识:思维和信息加工理论》(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出版后,在我国心理学领域才开始出现用“认知”这一专门术语取代“认识”这一基本概念的倾向。只是在这样的场合,有的心理学者为了避免原有的“认知”与新出现的“认知”在使用上的矛盾和混乱,所以在分析记忆环节时,才开始只使用“再认”的。这里有三点值得指出:(1)就连赵先生自己也承认,在解放前很长一个时期内,一般心理学工作者大多数是使用再认的术语,只有个别的才使用认知的术语。(2)即使在50-80年代初,有再认意义的“认知”也不是十分流行的。例如,朱智贤(1980)在其名著《儿童心理学》中论述儿童的记忆能力时就采用了“再认”的术语。(3)赵先生对荆其诚和张厚粲两位先生的指责也不能成立。诚然,这两位先生在传播认知心理学方面功不可没,但认知这一术语的普及却并非在他们的著作出版后才开始。在上文中我已经提到,我国的一些老心理学家,包括赵先生所景仰的潘菽和朱智贤先生,都正式使用过“认知”的术语,并明确指出认知是认识过程,并没有提到认知是再认。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将recognition译为“认知”不正确,用“认知”去意指“再认”也并非规范,那么,赵先生的“认识与认知是一种一般和个别,繁体和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便不能成立。进一步,指责用“认知”取代“认识”是“本末倒置”,“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体”,是在“制造概念和术语、理论和思想上的混乱”,同样不能成立。
赵先生不仅反对用“认知”取代“认识”,也反对“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术语。理由是:认识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基本规范术语,认知心理学这一术语“具有以偏概全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缺陷”,因此在译法上存在着“重大原则性失误”。他认为,由于认知心理学应改为认识心理学,相应地,认知科学也应改为认识科学。
这一观点不成立是因为:“认识心理学”并非我国心理学的基本规范术语。笔者查阅了国内出版的绝大部分心理学工具书,没有查到“认识心理学”的术语,但却收录了“认知心理学”的术语。不仅心理学的工具书是如此,哲学与教育的工具书也是如此。例如,颐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都收录了“认知心理学”的术语。
赵先生将cognitive psychology译为“认识心理学”并标之为心理学长期使用的“基本规范术语”也是不对的。众所周知,在心理学史上,虽然许多心理学家都对人的认识进行过研究,但cognitive psychology这一术语的出现却只有三十年的历史。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V·奈瑟的著作《Cognitive Psychology》出版,标志着认知心理学正式诞生。V·奈瑟本人也被称作“认知心理学之父”。我国心理学在建国后走了一条曲折的路:1958年被打成“伪科学”,1965年遭到姚文元的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心理学被取消。而这段时间正是国外认知心理学迅猛发展的时期。直到70年代末,认知心理学才正式传入我国,并从一开始就固定使用了这一术语,这是勿庸置疑的客观历史事实。
三、在心理学中用“认知”取代“认识”是心理学发展的既成事实
赵先生坚持认为,“认识”是哲学与心理学共同使用的基本概念,而“认知”则是用来表示记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专门术语。勿庸讳言,在认知心理学兴起以前,尤其是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内,心理学曾借用哲学中认识的概念,但认识的确是一个哲学概念而非一个心理学概念,这一点我们已反复作了说明。连赵先生自己也承认,心理学与哲学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认识的。心理学中所讲的“认识”与哲学中所讲的“认识”含义不同,主要指认识的心理过程。因此,在心理学中,为了更准确地界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们便用“认知”来意指认识的心理过程,这无疑十分必要,也十分恰当。因为“认知”与“认识”原本同义,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和朱智贤都持这一看法。而且在目前,用“认知”取代心理学中的“认识”,特指认识的心理过程,这一做法已经为心理学界广泛接受,也为其他学科认同,成为“时髦”。如果按照赵先生的意见,统统改回去,倒真的会造成混乱了。
然而,语言毕竟是思维的工具,是交流的工具。语言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语言及其意义的改变必须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有规范化方面的需要,但最重要的动力却来自实践。同时,实践也是检验变化合理性的标准。科学的术语尽管也有约定俗成的成分,但术语最好能准确地反映概念的含义。一直到60年代以前,心理学与哲学在认识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重要的问题原来是哲学问题”的情况也存在。但是,60年代以后,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产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对认识的研究与传统的认识研究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的确是“旧貌换新颜”,具体表现在:
1.在研究对象方面,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的高级认识过程,如知觉、注意、记忆、判断、思维、推理,问题解决、概念形成和言语等。研究的重点是个体的认识过程,即个体“获知”与“用知”的历程。当代认知研究虽然也关心人的认识结果,但主要侧重于人的认知结构、认知策略和认知方式的研究,如意象、命题和图式等。
2.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当代认知研究提出了研究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的学说与方法”。
3.在研究方法上,当代认知研究强调心理学实验。认知心理学家关心人类行为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信息输入和反应输出之间的内部过程。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直接观察内部的心理过程,只能通过观察输入和输出的东西来加以推测,所以,认知心理学家便通过可观察到的现象来推测观察不到的心理过程。他们采用会聚性证明的方法进行研究,即将各种不同性质的数据会聚到一起,从而得出结论。这些会聚性的方法包括:(1)反应时方法;(2)计算机模拟与类比;(3)口语记录法;(4)生理心理学与病理心理学的方法。由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使当代的认知研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比过去千百年来哲学与心理学的认识研究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的成果,从而促进了“认知科学”的产生,使人类认识过程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4.与以往的哲学、心理学的认识研究不同,诞生于70年末期的认知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科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的渊源相对较远。从认知科学的产生上看,信息科学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为认知科学家运用信息方法研究认知过程提供了基础: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认知科学提供了研究手段,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为认知过程的分析提供了模型,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则为认知科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到1982年,H·A·西蒙等出版了《人的内部宇宙:一门探索人类思维的新科学》,总结了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成就和主要原理,认知科学正式诞生。故而,认知科学不是从哲学中脱胎出来的,而主要是当代心理学、语言学、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联合的产物。
虽然当代的认知科学不是直接从哲学中脱胎出来的,但不等于说它与哲学无关。相反,认知科学的发展最终可以为揭开人类的认知与智力之谜作出贡献。所不同的是,与哲学的认识研究不同,在认知科学家看来,以往象意识等被人们视为只能用思辨的方法去研究的传统的“哲学问题”,现在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从而使我们对人类认知和智力的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真正成为一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科学。这种科学与以往的认识研究有了天壤之别,因此人们便以一种新的名称称谓它,将认识的心理过程称为“认知”,将以认识的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称为“认知心理学”,将研究人类认知和智力的本质和规律的跨学科科学称为“认知科学”,以示区别。这种做法在大陆、港台、日本莫不如此。因此,笔者认为,用“认知”取代“认识”是心理学发展的既成事实,这一取代符合科学发展的趋势。
令人高兴的是,在我国,认知科学及其分支近年来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如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人工智能、认知工效学和思维科学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单位都成立了认知心理研究室和实验室,设立了认知心理学的硕士点与博士点。1995年,在全国科技代表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在讲话中谈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及发展趋势”时,提到6项科学,认知列第二位。他指出:“认知科学是在神经科学、心理学、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哲学的交界面上发展起来的,它以人类的智能和认知活动为研究对象。”“认知科学的出现表明在人脑功能的研究方面,不再只是思辨式的,而是建立在严格实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早已把认知科学列入“七五”重大项目,而且还列入“八五”国家攀登计划中。
四、心理学应否同哲学分离,应否有自己的概念、术语?
在赵先生的几篇论文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用“认知”取代“认识”就意味着心理学要同哲学分离,尤其是要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分离。赵先生将我们在《论“认知”与“认识”的分野》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归结为“心理学与哲学、首先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离,不再共同使用认识的基本概念”,将我们的立场归结为“归根结底旨在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心理学在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认识论基本原理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导原则的发展过程中,根据历史的继承性、延续性和多方面联系性的原则而与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认识论)共同统一地使用认识这一传统规范基本概念的正确性。”这实际上经不起推敲。这里的问题是,讨论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必须先搞清哲学的含义。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对哲学的释义,哲学有两重含义:第一,作为学科,它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第二,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对人们的各项实践活动都有指导作用。在谈到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时,人们主要是针对后一重含义而言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往往交替使用这两重含义。笔者认为,讨论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必须讨论心理学与哲学这两重含义的关系。笼统地谈论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在讨论心理学与哲学分离的问题时,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结论。
1.就哲学的学科含义而言,心理学应否同哲学分离?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早在一百多年前心理学就已经同哲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使心理学同哲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是W·冯特。在1874年出版的《生理心理学原理》第一版序言里,冯特写道:“我这里献给大家的这本书是想规划一门新的科学领域。”19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冯特提出实验法是心理学的主要方法,而心理学是一门基于经验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这样,冯特使心理学摆脱了非科学的过去,割断了同旧的精神哲学的联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冯待的贡献,心理学史专家墨菲曾评论说:“在冯特出版他的《生理心理学原理》与创立他的实验室以前,心理学象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生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1879年它才成为一门实验科学,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和一个名字。”〔8〕
心理学虽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同哲学分离,但是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仍带有它脱胎出来的母学科的痕迹,半是哲学,半是自然科学。研究者们试图用一种理论说明所有心理现象,结果纷争迭起,学派林立,那时的心理学严格说来不太象一门科学。行为主义为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干脆矫枉过正,宣布不以意识为研究对象,只研究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真正使心理学在科学的道路上取得突破的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由于通讯技术和信息论的出现,使心理学家看到了信息通道的特性与人类认识过程的特性的相似性。于是便利用通讯和信息的概念来描述人的认识过程,输入、输出、编码和信息加工等概念被移植到心理学中。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以及后来出现的“物理符号系统”的假设和“认知的计算理论”,使人类认知与计算机运行之间产生一种功能的类比。心理学家根据信息加工理论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就可以模拟人的认识过程,从感知觉到记忆、思维、言语和问题解决等。由于计算机的运行特性是已知的,因此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已知的物理系统的特性加深对人脑这一与计算机功能类似但其过程却不甚清楚的系统的理解。这样,认知心理学基本上避免了由于被试的主观经验、个体差异和报告误差给实验的客观性、准确性所造成的困难,较好地解决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客观性方面的尖锐矛盾,为科学地研究人的认知提供了前提。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旨在说明:心理学同哲学分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在心理学诞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谁还对这种分离的必要性发生怀疑或反对分离,那将是十分可笑的。
但是,心理学和哲学在学科上分离并不意味着将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它们之间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联系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为哲学研究提供材料,哲学概括和总结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心理学是“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但心理学毕竟不同于哲学:心理学只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活动和规律,它不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和关于整个世界的观点,同样哲学也不具体研究人脑产生心理现象的过程和规律。两门学科虽然都研究人的认识,但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同,二者不能混淆和相互替代。因此,心理学理应有自己的概念和术语,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认知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已经存在新近又重新被确认的心理学的概念与术语。
2.就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含义而言,心理学(也包括其他科学)永远也不可能同哲学分离。因为任何心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要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任何心理学理论都有自己的哲学倾向,有的(如行为主义、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心理学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以某种哲学立场来对待他的研究。因此,正如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由于其哲学思想的缘故最终将运动的根源归结为“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一样,心理学家如缺乏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其科学研究就很容易走进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的误区。但是,说心理学与哲学二者紧密联系不等于说二者等同,更不是说二者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一致。哲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层含义上说)与心理学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世界观、方法论与具体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包办与替代的关系。心理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也理应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研究,心理学除了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外,还应该有自已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因此,我们所讲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分离只是就学科的含义和具体科学研究的层次而言的,而不是企图摆脱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谈心理学与哲学的分离不是反哲学,更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去搞什么所谓的“纯粹心理学”,相反,具体的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会给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在心理学中,用“认知”取代“认识”,特指认识的心理过程,是学科术语严密化、科学化的标志,而不是欲摆脱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在心理学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例如,在前苏联心理学中,著名心理学家列昂节夫提出了“活动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意识是在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通过活动认识周围世界,形成个性品质,反过来活动又受人的心理、意识的调节。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指导下提出来的,但却没有采用“实践”的术语。他不是照搬或照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句,而是领会了其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建立起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事实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心理学的指导,不在于具体术语上的变化,而在于理论的实质。心理学界在用“认知”取代“认识”这一历史变化中,人们都十分明确地指出:认知就是指认识的心理过程,并没有因此而否认马克恩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心理学的指导作用。这一改变,已为许多学科接受,同时,这一改变也不具有政治上或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含义。
注释:
〔1〕张积家、杨春晓、孙新兰:《论“认知”与“认识”的分野》,《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2〕赵璧如:《论用“认知”取代“认识”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3〕赵璧如先生的“二论”到“五论”分别载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社会心理科学》1996年第3期。
〔4〕高觉敷:《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5〕朱智贤:《心理学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362页。
〔6〕乐国安:《论现代认识心理学》序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张春兴:《张氏心理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8〕杜·舒尔茨著、杨立能译:《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标签:心理学论文; 认知心理学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