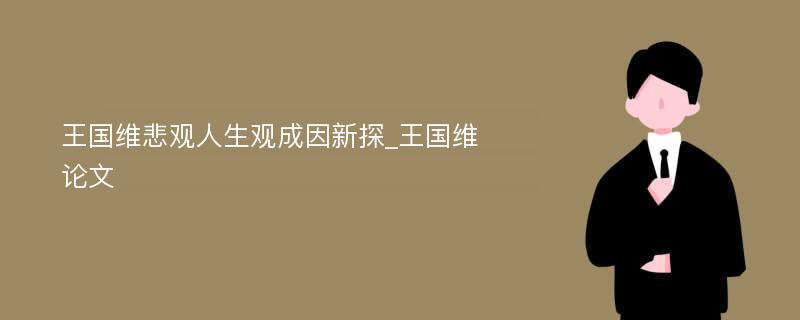
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成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观主义论文,成因论文,人生观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有的研究论著在涉及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及其悲剧观念时,几乎都认为是由于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哲学观念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但研究者却忽视了王国维的矛盾文化心态对其悲观主义人生观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何以能在王国维心中扎下根,并对他的悲剧理论以至整个审美理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同时代的其他文论家或美学家身上却并不明显或几乎看不到,显然,这与王国维自身的个体因素有直接的关联。
王国维一开始接触叔本华的学说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可谓一拍即合。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当他再回头读康德时,才读懂了原来极难理解的康德哲学与美学思想。无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及唯意志论思想对王国维的人生观与学术研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梁启超对西方唯意志论哲学思潮亦有接受,在他的文学观念中也有表现,然而,梁启超的思想中却很少有悲观主义的成份。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在蔡元培著作中也有反映,但他却摒弃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王国维却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原因何在?这不得不考虑王国维的矛盾文化心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王国维的矛盾文化心态对其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第一,传统思想观念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观念的矛盾。在王国维50年的不算太长的人生生涯中,始终交织着新旧思想之间的矛盾。王国维是在心境极为不佳的情况下接触到叔本华著作的,他在《三十自序》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国维的性格因素对他选择叔本华确实有影响,叶嘉莹先生曾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及其悲剧性结局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二是他生来就有一种“忧郁悲观的天性”和“富于悲悯之心的情怀”,由于时代变故的刺激,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叶先生将王国维的“忧郁”性格归结为天生就有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认为,王国维性格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他的家境的衰落以及社会的动荡变化。由于不断思考“人生之问题”,使他走向哲学研究,同时他还读过翻尔彭之《社会学》、器文之《名学》、海甫定之《心理学》,这些西方“新学”都促使他对中国封建正统思想以及传统思维方式作出了清醒的分析,甚至是猛烈的批判。虽然王国维没有动摇封建统治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对正统封建道德的批判却带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蔡元培曾高度评价王国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认为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注:《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359页。)。在《论性》、《释理》、《原命》、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等文中,王国维虽从纯学术观点出发来讨论传统伦理道德,但他对儒家道德观念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他认为孔子的“仁义”之说无哲学基础(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在《释理》一文中,他从与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比较角度对宋儒的“天理”说发起挑战。王国维认为本体论上不存在什么“客观天理”的“真”,而“天理”与伦理学上的“善”也没有关系。他还有感于学术的不能独立,对正统儒学给予了激烈批判:“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学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他大胆地预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71页。)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自觉的,他所依据的参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哲学中以康德、叔本华哲学为代表的“意志自由”说(注:虽然王国维在宣称康德、叔本华学说“可爱不可信”之前就对它们产生了怀疑,但所受影响已深入到他的思想之中。)。伦理学上的“自由”学说是王国维批判正统思想的有力武器,因此,我们认为,虽不能将王国维简单划入资产阶级行列之中(注:我们认为王国维的思想十分复杂,因此不同意聂振斌先生将王国维划入资产阶级思想家行列中的提法。因这一问题不是本部分的中心问题,此处不详细讨论,有关聂振斌的观点请参看《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但从他对封建伦理思想的批判言论中可以看出,王国维是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他虽不像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那样公然举起反对封建宣传启蒙的大旗,但他所做的工作却一点也不逊色。
王国维对近代社会政治革命的不明朗态度造成了他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一直没有被人们充分重视,李泽厚的看法很有道理:“由于中国近代思想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他们两人(指梁启超与王国维——引者)的代表地位和时代意义在康(有为)、孙(中山)、章(太炎)等巨大身影的遮掩下,显得暗淡得多。但因此而完全忽视和否定他们,则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433页。)但另一方面,王国维毕竟是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专制思想的局限,新思想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旧观念又有较多的残留,其结果必然造成王国维心理上的极大矛盾和痛苦,“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是他矛盾文化心态的形象而又确切的表达。难以解决的心理冲突不能不影响他对人生的悲观主义态度,《〈红楼梦〉评论》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文章中所表现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也可以看作是王国维思想矛盾的理论展示。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影响到体现王国维悲剧观念的《〈红楼梦〉评论》,但其思想是一个整体,因此为说明王氏思想上的矛盾,对其后期转向稍作说明。),王国维的思想轨迹又出现了新的转向,他的学术研究也更多地向传统回归,甚至表现出极大的落后性。在后期的生活中,他所结交的大多是清廷的遗老。在逃亡日本期间,还写下《颐和园词》、《蜀道难》、《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三首长诗,以表达他对灭亡了的清王朝的怀念。《颐和园词》开篇云:“汉家七叶钟阳九,澒洞风埃昏九有”,把满族统治者称为“汉家”,可见出他对统治者的臣服心理。1922年,王国维应诏回京,做了退位11年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北伐军进攻华北,他拖着长辫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昆明湖自杀。王国维的最后自杀显然是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的最好说明。“义无再辱”表面看来似乎是为“殉清”而死,但背后所掩藏着的应是他的无法摆脱的思想矛盾。周作人对王国维的评价可以帮助我们证实这一看法,周作人说:“王君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他是很有尊敬与希望,不知道怎样一来,王君以了无关系之‘微君’资格而忽然做了遗老,随后就做了‘废帝’的师傅之职,一面在学问上也钻到了‘朴学家’的壳里去,全然抛弃了哲学、文学,专治经史。……在王君这样理智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以后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之一途了。”(注:岂明(周作人)《偶感》之二,《语丝》第135期。 )周作人作为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学者,他对王国维的理解应该是可信的。
第二,王国维对西学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态度是其矛盾心态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其悲观主义人生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王国维接受“新学”的目的不在于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因此,他对西方新思想的态度不同于洋务运动领袖所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次,王国维引进“西学”的意图显然也不是为了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不是为了推进政治改革的革命进程,从这一角度来讲,他又同维新派判然有别。他所要解决的是长期萦绕于其心中的“人生问题”。因此,王国维虽然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等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对之并不持完全赞成态度,认为“上海、天津所译书”,大多都是非人文的数学、历学等“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无丝毫关系也”(注:《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第106页。)。另一方面,王国维反对为政治上的功利主义目的学习“新学”,他曾指出严复翻译《天演论》虽然达到了“一新世人之耳目”的效果,然而“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在于纯哲学,而存在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学等其所最好者也”(注:《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他还反对用急功近利的观点看学术问题:“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矣”(注:《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由此看来,王国维选择康德、叔本华哲学正是看中了它们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并以之做“武器”来探讨人生及所谓的“纯学术”问题。但是,王国维后来发现叔本华等人的学说仍然没有帮助他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甚至当时就对它们产生了怀疑。他在30岁所写的《自序》(二)中对于这一困惑讲得十分清楚: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感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事实上,也正如王国维所言,他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确实持有怀疑。康德认为自由属于本体世界,“自由”对现象世界而言,它是处于经验界的因果律之外,是一种本体原因,谓之“自由因”。王国维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吾人所以从理性之命令(即指康德的‘道德律令’)而离身体上之冲动而独立者,必有种种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个人之精神,必存于民族之精神,而此等表面的自由不过不可见之原因战胜可见之原因耳,其为原因所决定,仍与自然界之事变无以异也。”(注:《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第144页。)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由因”只是“表面的原因”。康德认为自由是“纯粹理性之能现于实践”,王国维则认为“理性之势力”能否“现于实践”实在很难说清楚。对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说,他同样存有疑问,他在《原命》中说:
动机律之在人事界,与因果律之在自然界同。故意志之既入经验界,而现于个人之品性以后,则无往而不为动机所决定。惟意志之“自已拒绝”或“自己主张”,其结果虽现于经验上,然属意志之自由,然其谓意志之拒绝自己,本于物我一体之知识,则此知识,非即“拒绝意志”之动机乎?则“自由”二字,意志之本体果有此性质否,吾不能知;然其在经验之世界中不过一空虚之概念,终不能有实在之内容也。
康德、叔本华的理论虽然使王国维在思考人生问题的路途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然而,他从理智上毕竟看出了他们学说中的可疑之处。这样一来,王国维便在学术思想的层面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发现“新学”也不能为其长期思考的人生问题提供明确答案,他的后期转向很能说明这一点。罗振玉曾说过,当王国维放弃西学而转向国学研究时,曾“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烧之”。在编辑自己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时,他对自己35岁以前的作品“弃之如土苴”。就是这样在“可爱”、“可信”之间的矛盾中,王国维的人生痛苦感丝毫没有得到任何缓解。从其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心迹:“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安得吾丧我,表里同澄莹。……何为方寸地,矛戟禁纵横?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兖兖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端居》)《欲觅》一诗同样传达出王国维对人生问题索解而不得的困惑、迷惘乃至于失望的心境:“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栖鸦噪暮寒。”表现这种矛盾、失望心情的诗作尚有很多,如“宇宙何寥廓,吾知则有涯。面墙见人影,真面固难知”(《来日二首》)等。
王国维到文学中寻求“慰藉”的原因在《自序》(二)中已讲得十分清楚,也就是说,对“新学”的矛盾心理使他产生了排解不开的“烦闷”,他通过哲学研究发现世界的虚无性和人生的无意义,而他又要努力寻找世界的意义,因此就求助于诗,希望通过文学获取内心的平静。刘小枫的有关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王国维这一转向的原因及意义:“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世界的虚无恰恰应该是被否定的对象。必须使虚无的现世世界充满意义,这正是诗存在的意义,正是诗人存在的使命。诗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他必须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常常说,一个没有诗的世界,不是属于人的世界。人多少是靠诗活着的,靠诗来确立温暖的爱,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揶揄。是诗才把世界的一切转化为属人的、亲切的形态。”(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但事实证明王国维最终仍然没有摆脱内心的冲突和矛盾。
作为一个学术中人,王国维对他所信奉的学说的矛盾心态应该是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因为康德、叔本华的学说本身所存在的弊病是明显可见的。问题是,王国维从“忧生”的角度对之进行解读时,感到它们是最管用的武器。然而,从客观的角度看,它们又不具有客观真理的性质,因而“觉其可爱而不能信”,这种矛盾才真正是让王国维产生极大痛苦的原因。由此可看出,王国维对西学的矛盾心态是他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反映,也是形成他悲观主义人生观和美学观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王国维对社会现实政治的认识也具有矛盾性,这是他悲观主义人生观形成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整个近代社会80年代的历史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充满着矛盾,新旧价值观念也同时并存。时代的转型在王国维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他既有保守的封建性的思想观念,又有进步的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主张,这种思想上的二重性来自于他对社会现实变革的理解,但反过来又影响他对所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因此,他常常以充满着或惊奇或兴奋或失望的眼睛来看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政治变革。当然,这其中更多的还是失望。
王国维一生执着于“纯学术”研究,基本上不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对现实采取超然的态度。但他对于列强侵略下的中国社会的惨烈现实和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不可能无动于衷,在诗词创作中曾抒发过强烈的忧患感:“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翁埠潮回千顷月,超山雪尽万株梅。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题《友人三十小像》)另在《八月十五日夜月》写道:“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海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这两首诗都是有感于国家遭受外敌入侵,山河破碎而发。我们不能说王国维完全不关心国家政治,只能说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往往通过他对人生感悟的表达而曲折隐晦地表现出来。对于维新变法,他也曾公开发表过很有见地的主张:“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一分就算一分。”(注: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但从总体上说, 王国维对近代社会的一系列变革,特别是对待封建专制制度和近代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如前所述,王国维青年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说使其思想具有启蒙色彩。在这种较为先进的思想的影响下,他对走向末世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满意的,在其早期论文中多有锋芒毕露的批判。然而,王国维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本身具有极大的矛盾性,他虽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但在行动上多少带有这一阶级的某些特点,即资产阶级由于近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不能正常发育,在行动上常常处于摇摆状态,因而,他虽对走向末世的封建制度不满,但又不主张社会革命。因此,当辛亥革命发起时,他没有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但当辛亥革命失败的时候,他却认为失败的原因是革命本身的混乱所致。他甚至还认为,辛亥革命同军阀混战一样,是造成社会动荡百姓疾苦的原因:“自辛亥之冬至于今日,不及五年,成败起灭,均在我辈眼中,‘成家与仲家,奄忽随飘风’,作此语时,当在孙公未败之前,今一一皆验。后之视今,亦今之视昔,苟不以辛亥之前之政局有成家仲家之鉴,则必蹈其覆辙,此天理之必然,无可勉强者也。”(注: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页。 )经过几次大的动荡之后,王国维对社会变革产生了变还不如不变的惧怕心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现实状况使他对西方世界的发展也持悲观态度,他在《论政事疏》一文中说:“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时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甚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源以半出于此。”正是建立在对中外社会现实的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王国维最后才走向政治上的彻底保守。当辛亥革命废除封建帝制后,他对曾演出一场复辟闹剧的张勋如此评价:“三百年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因而对其覆灭倍感痛惜,所谓“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是王国维心迹的表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王国维给末代皇帝溥仪做“南书房行走”也是具有必然性的。特别是当他所寄希望的皇帝被赶出禁宫,虚名也难保之时,他就在矛盾困惑中终于走向了绝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以及他的悲剧观念所产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固然部分地来自于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的老庄学说,但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以及对现实的矛盾心理所构成的矛盾文化心态是他能够接受以上思想的根本原因。因而,考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不能忽视这一重要方面。理解了以上问题,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也就不难找到。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已有很多论述(注: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已有的主要观点是:殉清说,殉中国旧文化说,避祸说,窘于经济说,受西方悲观主义哲学影响说等。),而我们认为他的自尽主要是由其无法摆脱的矛盾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标签:王国维论文; 叔本华论文; 康德论文; 悲观主义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哲学家论文; 美学论文; 人生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