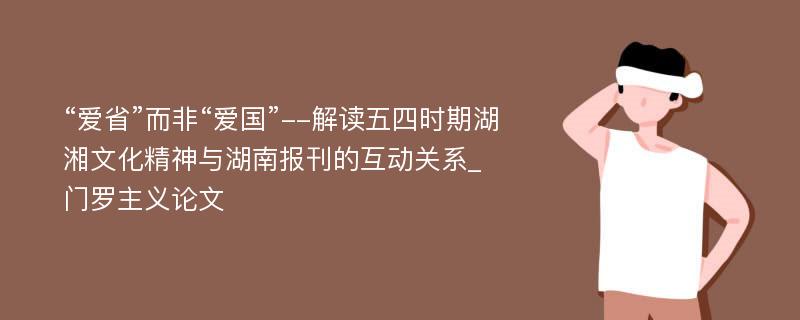
“爱省”而不“爱国”——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爱国论文,而不论文,湖南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时期湖南的报刊话语中,反对来湘主政的外省军阀与主张“湘省自治”构成一条自始至终掀起惊涛骇浪的巨流。从文化动因分析,湖湘文化“政治本位”的精神特质还是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规约作用。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政权更迭不休。北洋军阀把湖南作为攻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则把湖南作为北进的前沿。战火不断,生灵涂炭,军阀统治,毒如虎狼,湖南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表面看来,“祸湘”的军阀、武人似都是外省人,这就使当时的湖南人产生一种给湖南社会带来灾难的都是外省的军阀统治者的判断,因而掀起一拨又一拨的驱除来自外省的军阀统治者的斗争。从1915年至1920年,湖南人驱汤、驱傅①、驱张,一个个外省军阀都被赶出湖南。这种“排外”有湖南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的影响,自曾国藩的湘军平定东南半壁江山以来,“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存则中国存”成为湖南社会中普遍的文化心理。毛泽东曾说:“呜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1]湖南人本求是匡扶社稷、平定天下的,“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哪能容得外省的这些屠夫、武人在此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呢?
但透过这个表象,其实湖南人民反对军阀统治,主张“湘省自治”的根本原因还是对当时统治中国的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政府极度失望和仇恨所致。
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有state和nation之别。陈独秀就是持这种国家概念的典型代表。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他说:“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Patriot),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那么,陈独秀所说的“爱国主义”是何面目呢?陈独秀推崇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兹之所谓独夫者,非但专制君主及总统,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以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为什么呢?因为国民诸种劣性,“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至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了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2]陈独秀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独特的爱国主义视角,是一个以改造国民性为首务的启蒙思想者的爱国主义主张,他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考虑民族主义的。他当时所指的国家概念是state而不是nation,因为他认为当时袁世凯等辈执掌的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不能保障人民权利,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他反对对这样的国家即state表现盲目的爱和去为它献身。在1914年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乎?”[3]而民族和国家要强大,要不被列强欺侮,国民个体要有良好的素养是根本,尤其要具有独立的自强的人格。他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4]因此他认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5]
毛泽东的国家概念在五四时期也是state而不是nation。他首先同样也把国民的思想、道德素养看作是强国之本。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他说:“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6]毛泽东不但对愚弱的“群众”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腐败政府更是深恶痛绝,对腐败政府统治的国家更是极度失望。他曾这样倡导说:
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觉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7]。
如果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还以为青年毛泽东要分裂中国。这其实是毛泽东等辈对当时中国政府昏庸腐败无能的一种极其失望的政治选择。不论是陈独秀,还是毛泽东,他们不管出于何种角度,他们的国家概念在当时都是state而不是nation,不论是由国民性的落后决定的state,还是由腐败政权统治的state,都值不得去爱它去护它,去为它献身,相反它的亡掉、垮掉倒是nation的幸运。这种思想和感情导致“省治”思想产生,导致“割据”思想产生,导致反抗政府的种种行为的产生。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中,毛泽东历数“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事实,认定是“中国”牵累妨碍了湖南的发展。
湖南人在当时中国倡自治最烈,湖湘文化的“政治本位”价值取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政治本位”者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北洋军阀在湖南执政黑暗腐败,民不聊生,那么就应当赶跑他们,建立个“湘人自治”的政府,来维护湘省和湘人的利益,舍此皆为末。其次,“政治本位”者十分强调“天下”、“国家”、“社会”这样的关键词,敢于担当,既然救治国家非我所及,那么还不如先把一个一个省治好,脱离腐败昏庸的中央政府,从而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再次,“政治本位”者有十分强烈的主政意识、执政意识和从政意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是典型的话语表述。我们还是先从湖南《大公报》说起。
湖南《大公报》是因主张反袁从《湖南公报》分裂出来的。创刊号即表明该报以反对帝制为主帜。在《本报宣言》中就宣称:“惟知以拥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在创刊号上筹安会就是主要的靶子,当日专电三则,有两则是关于筹安会的。一则为《筹安会愈唱愈高》,另一则为《筹安会必无效果》。国内要电排在前两则也是关于筹安会的,一则为《杨皙子见诮日人》,另一则为《满人亦入筹安会耶》。国内要闻则是一篇长篇综述,题为《国体问题溯源记》,主要内容为“古德诺之谈话”、“筹安会之发起”、“反对者之论调”,也是一篇讨伐檄文。
时湖南由袁世凯亲信汤芗铭主政,湖南《大公报》处境可想而知。该报并未因汤芗铭的恐怖统治而改变反袁的立场,1915年9月10日和11日在“选论”栏中,连续转载了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编者按语说:“此论见诸北京国民公报、天民报,昨拟录置新闻栏内,以于我国现时局绝有关系,又与本报论调吻合,特次录。”梁启超在文章中驳斥了力主君主立宪的各种论调。湖南《大公报》是全国较早转载此文的报刊。以梁启超的影响力,起到了登高一呼的社会效应。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通电反袁,湖南《大公报》即于报端公布其消息。张平子回忆说:“汤督商诸沈金鉴,传语警戒本报,我们未予置理。汤乃勒令报馆每日送稿检查,并订定检报办法七条。本报至此,只好将其检去者‘开天窗’,且署‘检查员删去数字’。阅者皆能察之。”[8](187)李抱一在该报1916年7月30日《痛言》一文中说:“各外报谓中国反对帝制报纸仅上海之新中华报、天津之益世报、长沙之大公报。”而“当时湖南各报唯湖南《大公报》公开反袁,在全国也相当突出。它从社论、时评、新闻到副刊《艺海》,都以反袁为主”[9](68)。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黎元洪任总统,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1917年8月6日段祺瑞又任命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9月5日傅良佐率军开进长沙。傅良佐在湖南主政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于11月被迫离湘。傅良佐在湖南统治时间不长,但统治苛酷不亚于汤芗铭。他在长沙宣布戒严,“戒严办法”的第一条就是:“凡认为与时机有妨害之集合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类,一律禁止。”还规定:“凡往来邮件、电报,应予检查或拆阅”,“接战地域内,不论昼夜,得侵入家宅、建筑物、船舶中进行检查”,等等。在这样高压恐怖的情势下,湖南《大公报》敢怒不敢言,但其对现实统治的愤懑还是难以抑制地表达出来。1917年“双十”节湖南《大公报》发表《国庆日》的评论,写道:“当此风雨飘摇之日,料国中与记者表同情者,当大不乏人。呜呼!固犹是国庆日也,何以吾人心理感触骤然变易至此?吾尝比较已往之五国庆日,惟第一国庆日国民有兴高采烈之象,然党争已起,识者已引为隐忧;第二国庆日正当袁氏削平东南,人民喘息未定,惟冀苟安旦夕;第三国庆日则袁氏方厉行专制,国民多数,已忧共和运命之不长;第四国庆日则袁氏方制造民意,图谋帝制,国民疾首蹙额知祸之至无日;第五国庆日正值共和光复,国民对于民国前途,颇抱无穷之希望。岁岁之情形惟不同,然细察之则其毫无善状则一,其一年不如一年则一。虽然,前此吾人对于方来,固犹有一种希望之表示也,惟今兹之国庆日,吾人如卷入洪涛急湍之中,四顾茫茫,不敢有希望之目的物。微特共和前途不敢有若何之希望,即中国存亡之问题,亦不敢决。吊唁之不暇,而何庆之可言?呜呼!犹是国庆日也,何烦冤袭人,骤至于此。虽然,隐忧启圣,多难兴邦,国人倘群知今日之可忧也,则庶乎国庆日其将终有可庆也。”其指不言自明。
傅良佐被驱后,经过一番角逐,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一介武夫,暴戾成性,其统治之暗无天日比汤芗铭、傅良佐过之而无不及,激起湖南人民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920年6月张被赶出湖南。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对新闻舆论的钳制,也更为严厉。被封闭的报刊有《湘江评论》、《女界钟》、《新湖南》、《正义报》、《公言报》、《正声日报》、《华瀛觉报》等。被杀害的新闻工作人员有《华瀛觉报》的经理谭笃恭。
于是,一些“驱张”的团体就到外地办刊物来宣传“驱张“,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湖南的报刊的“驱张”主要是大量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行和劣行。湖南人民的第一次驱张宣言应为发表在1919年11月23日至26日湖南《大公报》上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再组宣言》,“宣言”如此写道:
人将灭吾国而奴吾族,而吾犹自得,杳不知其所以。任彼佥壬,植党营私,如昏如醉,辞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躙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惟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残喘苟延,可为太息![10]
对张敬尧虽未指名道姓,但所列“祸湘”罪行历历如数,明眼人一看便知。办在外地的报刊则点名道姓,直言不讳。“驱张”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反军阀运动,是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运动的主力是学生和教育界,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起了核心领导作用,毛泽东成为实际的领袖人物,在这次运动中,他实践了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政治策略,“湘人治湘”、“湘人自治”成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口号。
张敬尧被驱后,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打着“顺应民情”的旗号取得了湖南的统治权。这时十月革命进一步影响着湖南人,“民治主义”口号很流行,这些因素和湖南社会对刚刚挣脱的北洋军阀统治极端憎恨的现实背景交织在一起,于是“湖南自治”运动就勃发起来,它是当时湖南历史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展。在“驱张”运动中报刊舆论就提出了“自治”的政治主张。《湖南》在创刊号发表的“特别启示”就强调该刊的主旨是要“陈述地方惨痛,研究善后事宜,发扬自治精神”,其选稿范围是“报告湘灾确情”、“讨论善后问题”、“提倡民治主义”。在“发刊词”中进一步主张:“划分区域,实行自治,使本地人治本地之事”。《天问》发表的《湘人驱逐张敬尧宣言》中也提出了“举湘政决诸湘民”的要求。毛泽东、彭璜等拟定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则提出了“湖南建设问题”的粗略方案,该“宣言”写道:“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此(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持其所信,向前奋斗”[11]。湖南《大公报》在张敬尧的高压恐怖统治之下,不宜直接发表“湖南自治”的意见,但也从没放弃“民治主义”的主张,如1920年元旦发表评论《民国九年底希望》,“希望九年内人民能自觉、自动、自决,发展民治主义底真精神”。这种“自治”的政治主张在驱张后逐形成湖南的政治风潮。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建立“湖南共和国”是湖南社会一种普遍的愿望。青年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是最激进、最极端的。关于“湖南自治”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近20篇文章,光在湖南《大公报》就发表了10篇文章。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抱一丝一毫希望,诅咒它快点死去。在1920年10月10日写的《反对统一》一文中,他写道:“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12]当时毛泽东认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他明确表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13]基于这样的思考,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半自治”,而主张“全自治”的所谓“湖南门罗主义”。所谓“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来的,他在1823年为反抗欧洲俄、普、奥三国所组织的神圣同盟干涉中美、南美诸国独立而发表宣言称:美洲大陆不许任何欧洲国家殖民,凡欧洲国家意图控制拉美各国命运者,都被视为对美国的不友好表现,同时美国也不干预欧洲国家。这
主张被称之为“门罗主义”。“湖南门罗主义”是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提出来的。在1920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上,他撰有《湖南“门罗主义”》一文,写道:
湖南当这南北不曾统一又没有任何方面外力侵入的时期,正是集合群策群力实行全省自治的绝好机会。我前天已经说过了,我们湖南人如果真要想在此期间内建筑一个崭新的“新湖南”,那么,就不可不大家严守着湖南的“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是甚么?知识阶级的人谅必都知道的。我因为想要大家都明白这个主义的内容,不妨再把他申说一下。门罗主义就是:
我用心干我应干的事;
我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
我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的事。
合了这三个条件,便是门罗主义。[14]
毛泽东在1920年9月6日湖南《大公报》上,即发表《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一文,呼应最切。他在1920年10月3日湖南《大公报》发表的《“全自治”与“半自治”》一文则写道:“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中更放声疾呼: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15]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说“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可知“自治”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反对“官治”,主张“民治”,也是“湖南自治”运动中的一条报刊舆论主线。这条线索是随着“自治”运动的推展而逐步明晰和强化的。在反对“官治”,主张“民治”这一点上,湖南的知识界基本是统一的,与上层统治层形成尖锐矛盾。毛泽东是最早看破谭延闿之流假“民治”、真“官治”的本质的。在张敬尧被驱仅两天后,他就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指出:“于今张敬尧走了,我觉得这种‘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心’,往后正复不少。这些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我们便可以依从了吗?不论是湖南人,或非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对“非张敬尧”的担忧即为后来谭延闿、赵恒惕的统治所验证。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他对这两个口号进行了辨析,他这样写道:
“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那么,奉天的张作霖,直隶的二曹,河南的赵倜,陕西的陈树藩,安徽的倪嗣冲,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豫人治豫,陕人治陕,皖人治皖……比那“非湘人治湘”的汤芗铭,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非闽人治闽”的李厚基,“非粤人治粤”的莫荣新……到底有什么区别?[16]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思想与谭延闿、赵恒惕及官绅们以“湘人治湘”相标榜的“湖南共和国”思想的本质差异,他并不把“湘省自治”就理解为“湘人治湘”。他的思想应理解为有两个要点:一是必须实现湘人高度自治,完全的自治,摆脱“中国”的牵累;二是必须是完全的、彻底的“民治”,必须由湖南的民众来决定湖南的命运,既“不愿被外省人来治”,也“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
毛泽东这时的思想处于向马克思主义的急剧转变期,促成这一转变的最重要的实践因素就是他投身其中的湖南自治运动。倡“湖南共和国”,强调“湘人自治”是他第二次从京、沪返湘之后所投身并主导其中的政治运动。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的10篇文章,都集中在1920年9月至10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这正是他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会友们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应该说,毛泽东不是把建立“湖南共和国”、“湘人自治”一开始就看作是虚幻的事情,就把它看得无足轻重,就认定它是不会成功的,相反,他对它曾经寄予着很高的期望,并且全身心地积极投身其中。应该说,湖南自治运动为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的先锋青年最终选定“走俄国人的路”、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上了最生动的一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涅槃新生的火候。
总之,“爱省”而不“爱国”,重“省”而不重“国”,在湖南社会驱除军阀、倡导“自治”的运动中,成为报刊一个基本的舆论导向,但这个“国”是state,不是nation,是北洋军阀把持的政府,是黑暗腐朽的中国社会,而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中,湖湘文化政治本位的价值取向最为充分地表达出来。斗争的焦点是一个“政权”的问题,无论是“湘人治湘”、“非湘人治湘”,还是“官治”、“民治”,都是一个由谁执掌政权的问题。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政治本位即权力本位。湖南社会几乎都认定,一个社会的好坏,它的民众命运的升沉起伏,都是由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决定的,尤其是由主政者决定的。因此他们奋起驱赶一个又一个军阀统治者,希望通过“湘人自治”来达到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好政府的目的。在这样的一场斗争中,湖南民众,尤其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代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人生抱负、志在主“苍茫大地”“沉浮”的先锋青年,更表现了强烈的从政意识、主政意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成为他们在这场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中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①傅为湖南吉首人,毛泽东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中,说他“以湘人而凭借北势”,因亦视为北洋军阀势力,该文登1920年9月6日、7日湖南《大公报》。
标签:门罗主义论文; 湖南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湖湘文化论文; 大公报论文; 毛泽东论文; 张敬尧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