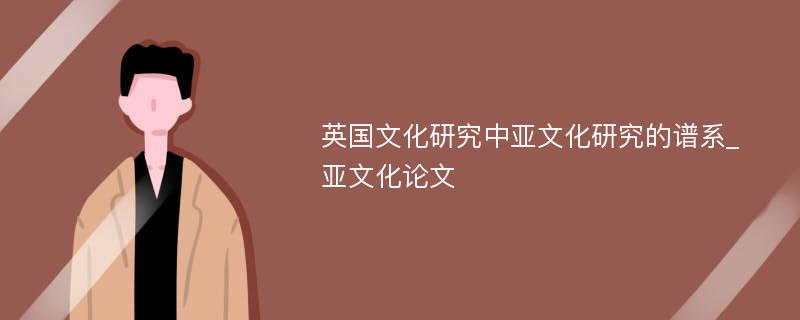
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研究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英国论文,亚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亚文化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有些语汇诸如“80后”、“90后”、“宅”等都已成为生活用语,而诸如“萌”、“萝莉”、“腐女”等则不断在网络世界中流传与建构。此外,《蚁族》一书的出版,也带出了另一重亚文化的面貌。尽管新的社会现实不断发生,但是既有的学术研究却仍显得相当缺乏(不过,有趣的是,与亚文化相关的硕、博士论文则处于增加状态)。
关于亚文化研究,二战后所开展的英国文化研究带出了新局面。面对二战之后英国资本主义的重新构造、社会结构的丕变、流行文化与亚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拉开一条分析与批判的理论轴线。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主义者雷蒙·威廉斯(R.ayrnond Williams)等人的研究,1964年伯明翰大学新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英国文化研究进入学院。其间,霍尔(Struart Hall)堪称英国文化研究的灵魂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霍尔与中心成员重新在西方马克思理论、结构主义乃至符号学中撷取资源作为社会批判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他们开启了包括媒介研究、亚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局面。尽管英国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中或可说是一个仍在发展中的“显学”(但也包括误读①),不过,其亚文化研究谱系仍少有人论及。在本文中,笔者一方面将梳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理论范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将讨论这些变化对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及亚文化研究的内涵,希望通过这些梳理来丰富亚文化本地化研究的视角与可能性。
一、寻找理论资源之旅
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乃至战后英国社会的重构有着密切的关联。1956年11月苏联入侵匈牙利,同年,英国介入苏伊士运河战争。面对英国内外的政治局势,不同时代的左翼分子展现出不同的批判观点与关注议题。老一辈的左翼分子关切苏联入侵匈牙利,他们将矛头对准苏联,例如苏联入侵事件后脱离共产党的汤普生(E.P.Thompson)便批判苏共的斯大林路线。然而,对当时在英国读书的霍尔、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来说,英国介入苏伊士运河战争对这些来自牙买加、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冲击更大。到底当今英国的面貌如何?为何一个帝国力量又重新出现?除了政治经济层面的追索之外,他们也尝试跳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消费资本主义崛起、新型广告杂志大量出现的战后英国社会的型构②。也在这个时空点中,几部重要作品逐一浮出,例如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霍加特所关切的是为消费主义所包抄的工人阶级文化为何已然消逝。而威廉斯则尝试重新定义文化:文化不再是代表文明的经典文学、戏剧等,而是环绕在我们日常生活周围的现实。
1964年伯明翰大学新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第一任主任为霍加特。在霍加特的就职演说中,他揭示出文化研究中心的方向将是研究当代社会中被忽略的媒介与文化现象③。然而,他的任期并不长,1968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之后,霍尔便实际上总掌新兴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直到1979年离开伯明翰大学。霍尔在新兴文化研究中心的十年间,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最具活力的时期。霍尔与中心成员重新探寻批判的理论资源,其中,社会学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新兴文化研究中心初期的理论资源探索的起点。中心成立之际,恰逢西方社会学研究范式转移的关键时刻,站在社会总体观点的功能论与微观社会学正进行激烈的竞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范式同样论及文化,然而,英国文化研究如何取舍?二战之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以及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美国社会学界占了主导地位。然而,对新兴文化中心来说,美国的社会学不过是在欢庆一个资本主义新国度的诞生,在这个新国度中,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然解决,剩下的仅是社会不同意见的表达与说服④。除此之外,无论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还是贝尔的论述,虽然论及文化,不过,在他们眼中,不是认为文化履行社会运作的功能,就是认为文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趋近相同。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乃至民权运动的风潮,结构功能论开始受到怀疑,此时也正是微观社会学崛起的时刻。微观社会学的崛起,与韦伯传统的复兴有直接关联。符号社会学诞生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米德(George H.Mead)、布鲁默(Herbert G.Blumer)与高夫曼(Erving Goffman)共同形塑了这个美国本土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不同于帕森斯功能论将社会整体视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符号互动论将分析单元移转为社会行动。经过米德等人的奠基,舒兹进而修改韦伯对行动的定义,提出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对舒兹来说,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行动的根据,是从客观的事实跳跃到主观意义的脉络;所谓的意义脉络,是由生活世界建构科学知识的过程,这个世界包括人类所有日常生活事务的总和⑤。对文化研究来说,这种转变尝试对文化进行两种类型的解释:第一是社会与历史对文化现象的影响;第二是与这些现象相关的意义⑥。而这正与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与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两本书所关切的问题一致⑦。此外,通过俗民方法论,更可以凸显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实存的文化(lived culture)⑧。在社会学转向的情形之下,俗民方法论成为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个研究方法也带出了该中心的亚文化与女性研究。
韦伯传统的复兴,也使该中心追溯到“海德堡学圈”,西方马克思主义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一浮现,诸如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⑨。除此之外,法国马派理论家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名,特别是他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法)受到广泛关注,阿尔都塞也因此成为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中受到讨论的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态度,如同霍尔所说的:“当我们从理论层面切入文化研究时,整个中心基本上相当避免落入化约论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阶级化约论扭曲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使得它无法严正地处理文化层面的问题。”⑩
除了马克思的遗产,法国的结构主义也在二战后达到高潮。结构主义的形成,奠基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与法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1)。涂尔干的关怀在于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索绪尔则致力建构系统化的语言体系。结构主义在40年代开始发挥影响力,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人类学以及拉康与罗兰·巴特的新符号研究都在当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二、意识形态问题的浮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找寻前述思想资源的过程中,霍尔也在这些资源中寻求理论与现实的对应。他1971年参加“英国社会学学会”所发表的《偏差、政治与媒体》(Deviancy,Politics and the Media)就尝试定位媒介/社会的位置。在这篇文章中,霍尔拒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媒介仅仅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认为媒介是控制文化的一环(12)。所谓的控制文化是指不同政治力量乃至社会成员都在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表述权力,在此过程中,媒介成为一个兵家必夺的重要战场。然而,他如何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乃至结构主义的资源深化关于控制文化的讨论?在1973年发表的对文化研究乃至媒介研究都有深远影响的《编码/解码》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凸显意识形态与突破巴特符号学的企图。
如他所说,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旨在打破美国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仅重视传播效果与讯息的传播方式,忽略其间意识形态的作用与重要性(13)。在意识形态方面,他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分配/生产架构了媒介内容编码/解码的过程,在此,媒介内容的生产是一个如同链条的流程。对霍尔来说,讯息的生产与接受是相关但非同一的关系,在传播的总体过程中,它们处于不同的时刻点(14)。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编码者已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媒介内容是否为接受者所理解,这取决于编码者—生产者和解码者—接受者所处的位置是否对等(15)。紧接着,霍尔开始处理符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符号的处理与意识形态紧紧相连。尽管巴特的神话学以索绪尔的符号学为基础并将之作为批判消费社会的理论武器,不过,前者的局限在于仅能逐一拆解消费社会的一个个神话,无法带出现实社会中相对抗的、也是霍尔最重视的意识形态问题。霍尔在俄国语言学家沃洛西洛夫(V.N.Volosinov)那里找到思想资源。在沃氏那里,语言符号是多义的,并且是历史与社会斗争的中介,而同时也无法自外于阶级斗争(16)。
接下来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尽管已得到重视,然而,在理论上究竟应该走向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对于这两种理论孰优孰劣,英国文化研究内部曾有过不同的评价,不过,从《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以下简称《仪式抵抗》)以及霍尔与克里切(Chas Cfitcher)等人于1978年合著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与法律及秩序》中,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的讨论逐渐滑向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该书源自1972年8月15日滑铁卢车站的一宗谋杀案,案发之后,不仅英国各大媒体大加报道,政府官员也对之不断发言安抚人心,一时之间,此案引起人们普遍的恐慌。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发展衰退、阶级对立也趋于尖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英国政府面临一场领导权危机。这样的领导权危机,也正可通过谋杀案发生之后人民的恐慌,重新塑造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共识。在这部著作中,相当有趣地融合了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理论路径,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政府机构、媒体等作为社会型构的单元进行分析,贯穿其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则以葛兰西动态的、历史的文化领导权加以讨论。英国文化研究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得到进一步厘清。霍尔不仅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1980)中提出著名的“葛兰西转向”,还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中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分析的重要性。
三、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研究:现实与理论
在厘清英国文化研究理论路径后,我们接下来便可进到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研究。就社会现实来说,战后的英国亚文化中,首先出现的是50年代的泰迪族(Teddy Boys,或称Ted)(17)。泰迪族的服饰装扮以20世纪初爱德华时代的华丽造型为典型,而这个群体的服饰多因裁缝师的手工缝制而造价不菲,事实上,这些以白人劳动阶级为主的年轻人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此外,这个团体也与摇滚乐产生紧密的关联。这个战后首先出现的亚文化团体内部因为成群结党,也出现相互斗殴的事件,而这些事件被媒体夸张地报道。其中,最为重大的事件莫过于1958年诺丁山(Notting Hill)暴动,这一事件的产生原因在于泰迪族对黑人小区的暴力攻击。到了60年代初期,泰迪族逐渐分化为摩登族(Mod)与摇滚客(Rockers)。“Mod”是“modernist”的简称;后者指50年代新兴爵士乐者与歌迷(18),这个群体的标志包括美国非洲裔的灵魂乐、牙买加的斯卡(SKA)、节奏布鲁斯(R&B)在内的音乐、裁缝师手工缝制的服饰与意大利速可达(Scooter)摩托车。摩登族的兴起与英国新兴的披头风咖啡店(beatnik coffee bar)有直接的关联。披头风咖啡店原本针对中产阶级以及艺术学校的学生,后来却成为摩登族的空间。其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酒吧晚上十一点就关门,而这种咖啡店则营业到凌晨。此外,这类酒吧还设有点唱机(jukeboxes),在这里,年轻人可以投币点选自己所喜爱的音乐,披头风咖啡店因此成为年轻人愿意彻夜驻足、认同的空间。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速可达摩托车成为摩登族的必备工具:只有个体得以自由移动的摩托车,才能在公共交通系统都已停止的夜晚穿梭。此外,摩登族之所以热衷黑人音乐,主要原因则是摩登族经常彻夜聚集,而黑人的黑色则被视为夜晚的象征。
摇滚客则是指以劳动阶级为主的飚车族。随着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马龙·白兰度1953年的作品《飞车党》(The Wild One)中穿着皮衣飚车的形象特别影响了这个群体(19)。这个群体通常在购买摩托车之后,重新将之改装为赛车的外装。飞车党除了出现在公路或都市空间,也出现在狂飙起点或终点的咖啡馆。此外,飞车党狂放不羁的形象在舞厅并不受欢迎。事实上,摩登族与摇滚客是两个风格迥异、相互敌视的团体。摩登族被认为是柔弱、傲慢、讲求派头、效法中产阶级文化的;而摇滚客则是野性、颓废甚至是肮脏的。摩登族认为摇滚客是一种粗野的男性形象,反之,摇滚客则认为摩登族太过虚荣。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期摩登族繁衍出硬派摩登族(Hard Mod)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特色在于更往黑人文化靠近,例如牙买加的斯卡或是黑人出没的夜店。这种转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导向的嬉皮文化出现。因为嬉皮中产阶级导向的音乐等文化形式与摩登族格格不入,摩登族改以黑人文化作为元素并转化为硬派摩登族,而硬派摩登族很快转化为光头族(Skinhead)。光头族强调工人阶级的认同与骄傲,他们服饰中的工作靴就是一个重要象征(20)。此时,60、70年代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黑人与白人之间求职的竞争加剧,而在种族歧视的情形下,黑人成为弱势群体,也在求职竞争压力下,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再次割裂。这些割裂也展现在青年亚文化中,例如牙买加的黑人歌曲《年轻、天赋与黑色》(Young,Gifted and Black)不仅被改为《年轻、天赋与白色》(Young,Gifted and White),甚至也出现了白人挑衅黑人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光头族的文化不再加入黑人元素,取而代之的是成为不同足球队的球迷,相互叫阵甚至成为足球流氓。光头族的出现,已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得种族问题浮上台面,而这些问题也展现在青年亚文化中。光头族日后的发展,也随种族问题出现不同的群体,例如有的转化为新纳粹,参与反对黑人与亚洲移民的活动;不过,也有的站在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大致从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亚文化朋克迅速形成。朋克的特色是标榜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反抗权威等价值理念。与前述泰迪族一路繁衍下来的英国亚文化略有不同,从纽约、洛杉矶到伦敦,朋克成为在西方世界中逐渐流传的亚文化。朋克的形成与较为吵闹、强烈的音乐有直接关联。就英国来说,60年代末成立的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代表。面对逐渐下滑的经济景况,性手枪乐队以原始粗糙却具生命力甚至有暴力倾向的表演方式,以及崇尚虚无主义、高唱无政府失序混乱状态的内容,吸引了大批的学生与工人阶级听众。值得注意的是,性手枪乐队的作品在当时虽然被禁,却也因此在地下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音乐革命潮流。
面对亚文化兴起的现实,英国文化研究如何开展?英国文化研究首先揭开其所侧重的意识形态分析,进而与既有观点进行对话。战后英国在经济重新发展的过程中,富裕(affluence)、共识(consensus)、迈向中产阶级(embourgeoisement)成为时代的关键词(21)。所谓的富裕是指工人阶级都能够成为手头宽裕的消费者,共识是指对两党政治、混合式经济发展乃至福利国家社会安全网络的接受,而迈向中产阶级则是结合前述因素,通过经济发展,打造一个阶级区分消弭的中产阶级社会(22)。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亚文化的既有研究中出现了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亚文化是富裕社会的产物,是年轻消费者通过消费所形成的自我认同(2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亚文化的形成与战后崛起、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介乃至“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特别是50年代商业电视的出现更是扮演了关键角色(24)。在这种观点中,亚文化仅是大众媒介崛起的副产品,这类观点也视亚文化为大众社会的负面产物。第三种观点则从社会经验的断裂对亚文化的形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这种观点认为,因为二战的因素,许多年轻人是在父亲被征召上战场或是待在避难所这样非正常家庭的环境下成长,因此产生了反叛的亚文化(25)。此外,类似的观点则是二战后英国的公共教育年限拉长,年轻人大部分的时间与同侪相处,这也促成了亚文化的形成(26)。
对于新兴文化中心来说,研究者们尝试与既有观点进行对话,其中,柯恩的《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群》一文对新兴文化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带来相当重要的影响。柯恩主要讨论了英国伦敦东区战后重新发展的过程对原来工人阶级社群的阶级认同乃至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伦敦东区原本是传统工人阶级社群小区。不过,在重新改建的过程中,小区的居住空间改变,就像柯恩所指出的:“在不知不觉中,这里已经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环境结构,完全以财物和私有权、以个人身份和财富差异为概念基础等等。而原来劳动阶级的环境结构,则是以社群、集体认同、集体缺乏拥有权、财富等概念为基础。”(27)
外在环境中产阶级化,不过,住在里面的人却非中产阶级,尽管如此,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却随居住空间的改变有所变化。一个阶级保持传统的劳动阶级认同,而另一个朝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认同也开始萌芽,这两种阶级认同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种裂缝不仅存在于父母辈的生产和劳动意识形态与消费的意识形态之间,也渗透到青年亚文化中,他们不仅形成不同的同侪团体,更以所认同的同侪团体的装扮占据居住空间内部以及外围的城市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亚文化并非如同前述的几种观点所说的是一种截然不同于成人文化的文化样态。相反地,亚文化与父母文化或父母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脉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于父母文化中的矛盾,青年亚文化以巧妙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父母文化所衍生的一连串亚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核心的主题进行千变万化的变形——从意识形态的层次来说,这种矛盾存在于传统劳动阶级的禁欲主义,和新的消费享乐主义;存在于社会动员菁英份子的未来,和凑在一起的新无产阶级。摩登族、风衣族、庞克(按:朋克)族、光头族,各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企图回溯结合一些遭到父母文化破坏的社会凝聚元素,并且从其他阶级派系中选取某些元素,象征其他与之形成矛盾的选择。”(28)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柯恩开启了一种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分析方式。对于新兴文化中心来说,柯恩的贡献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通过他的研究,霍尔等人将亚文化研究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相结合,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审视亚文化;另一方面,新兴文化中心也从微观社会学的层面研究亚文化,特别是结合巴特等人思想的符号学解读被视为亚文化核心的风格。从宏观的层面来说,二战之后的英国,官方的论述集中在经济的重新发展,然而,柯恩东伦敦的研究中,恰好指出在此现实环境之下所发生的阶级认同断裂,而且这种断裂不仅出现在成人文化中,也延续到青年亚文化中。对新兴文化中心来说,亚文化正是以青年们所创造的仪式对社会进行抵抗,正如霍尔等人所合编的论文集名称所显示的那样。
主张将亚文化放在宏观结构面进行审视的霍尔等人,也提出观察分析的三个层面:结构、文化、个人生活史(biographies)(29)。结构是指某个阶级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互动关系;文化是指反映社会情境的样态;个人生活史则是指个人在前述的结构与文化中所形成的个人认同乃至有别于集体的生活经验(30)。这三个层面分别关注了宏观的结构面与微观的个人层面。值得一提的是,新兴文化中心不仅关注与劳动阶级相关的亚文化,也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中产阶级亚文化中。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年轻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已不再是讲求节约勤俭的价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生活风格和需求的满足(31)。在此情形之下,新兴中产阶级也产生了不同于工人阶级的亚文化,例如反权威主义、道德多元等。就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而论,无论是劳动阶级还是中产阶级的亚文化,都成了卫道者眼中的权威危机。在讲求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下,劳动阶级被期待成为认真工作、守法、受尊敬的劳动阶级公民,而中产阶级则被期待成为理性节欲、职业至上的个人;然而,不同阶级反文化的出现,恰好说明主流意识形态遭到挑战(32)。在道德恐慌的情形之下,不仅官方对亚文化进行更为严苛的管理,大众媒体也加入道德恐慌的论述中。
在《仪式抵抗》之后,亚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作品莫过于何柏地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以下简称《亚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思路,也可以看到《仪式抵抗》中理论架构的影子,结构、文化、个人生活史这三个层面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地呈现。
对何柏地来说,亚文化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风格。而他也借用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说的“拼凑”(bricolage)来形容亚文化的构造。所谓的拼凑源自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部落的观察,在他眼中,原始部落有一套不同于“文明人”的语言系统,这套语言系统看似缺乏逻辑,实际上却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33)。在何柏地眼中,不同的亚文化群体有不同的风格,各式各样的服饰或口号,都像是一个个崭新出现的符号,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的过程。这些风格的形成,也都是撷取(或者说拼凑)自当下的文化质素为己所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质素的出现,与战后英国的政治经济脉络有直接关系,例如好莱坞电影在英国风行、大量移民带来异质的文化元素等。亚文化群体的自我命名乃至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随着社会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风格表达了对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抵抗。
四、英国亚文化研究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并非建立亚文化研究范式的第一个群体。在此之前,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便已着眼于芝加哥这个工业与移民城市中的亚文化问题。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重新翻转文化的定义并将意识形态等元素带进亚文化研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所建立的研究范式,日后出现了支持与反对的不同声音。反对的声音认为,《仪式抵抗》与《亚文化》两部经典之后,社会结构已然迅速改变,全球化乃至后现代现象的出现,再加上媒介的迅速变迁特别是网络世界出现,亚文化的构成形式都与英国文化研究所面对的战后乃至70年代的英国社会有所不同。支持的声音则认为,尽管环境不变,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政治经济脉络的分析仍深具价值。
有趣的是,无论支持与反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仍是论战双方所必须引据的历史。笔者无意强调英国文化研究的“正统性”,既然英国文化研究强调一种本地化的批判,其亚文化研究也并非一种举世皆准的理论模式。不过,其亚文化研究架构仍有作为参照系的价值,最重要原因在于结构、文化、个人生活史可以带出现实社会的型构并进而进行批判。放在中国大陆既有的亚文化研究脉络下来看,亚文化研究或可粗略分为两个方向:第一种是从社会功能论的角度出发,关切的是亚文化如何在良好的引导之下达成社会整合并使社会秩序有效维持。它对亚文化经常出现价值判断的负面描述。事实上,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也并非它的最终关怀。第二种则尝试通过个案研究展示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近年来逐渐出现的以亚文化为题的硕、博士论文中,具备这样的研究企图者不在少数。不过,我们也将注意到,在这些论文中,抵抗、商业化、主流文化、后现代等成为关键词。然而,抵抗、商业化、主流文化、后现代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发生的?特别是论者经常强调抵抗是亚文化的重要元素,不过,抵抗却成为暧昧不明的语汇,抵抗的对象是什么?英国文化研究所侧重的意识形态等结构因素仍有其参考价值。如果不厘清这些结构因素,我们将看不到亚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也看不到抵抗的对象乃至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经常被提及的主流文化也将不知所指为何。结构的分析是必要的,如果回到文章的开篇笔者所列举的许多新兴名词,这些名词其实指涉了不同面相的社会生活,其中部分属于城市流行文化,有的则指向了艰困的现实城市生活。只有通过结构的梳理与厘清,我们或许才能看到亚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位置,如此一来,才能更清楚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在此一特定时空点之下的意义。
注释:
①这些误读包括:首先,将英国文化研究扩大为西方文化研究;其次,将英国文化研究视为涵括许多当代西方思潮的理论或称之为“伯明翰学派”。事实上,英国文化研究相当强调本地化的批判,也就是说有其“英国性”(必须指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也不断扩充,例如少数族裔问题也进入了其研究的视野),无法扩大为西方整体。这种误读或许与中文世界对英国文化研究相关作品的译介有相当的关系。它们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展,这段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内部正在进行理论资源的追寻、整理甚至论辩,或许因此英国文化研究被认为是一种理论或是一个学派。然而,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前述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本地化批判。1975年的《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1978年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与法律及秩序》(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乃至代表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出现的《迈向复兴的艰难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翼危机》(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 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1988)较少为中文世界所关注,而这些作品恰好代表英国文化研究的批判传统。此外,将英国文化研究理解为一个学派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同霍尔与陈光兴对谈时所说的,“人们常常谈起‘伯明翰学派’,但是我所能听到的,尽是我们早在伯明翰便已经争论不休的题目,那就是我们从来不曾是‘学派’。也许,在伯明翰也许曾经出现过四、五种不同的理论途径,但是我们从来不曾试图统合这些理论途径,也不想树立另一个理论正统”(参见霍尔、陈光兴《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唐维敏编译,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版,第140-141页)。
②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etters,London:NLB & Verso Editions,1979,p.362.
③④⑥⑦⑧(13)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in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d.),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London:Routledge,1992,p.21,pp.20-21,p.23,p.23,p.24,pp.118-119.
⑤石计生:《社会学理论:从古典到现代之后》,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307页。
⑨Sm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in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d.),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p.25.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62.
⑩霍尔、陈光兴:《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第52页。
(11)Andrew Milner,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London:UCL Press,1994,p.77.
(12)(16)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p.169,p.171。
(14)(15)Smart Hall,"Encoding/Decoding",in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University of Birmingham(ed.),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p.130,p.130.
(17)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eddy_Boy。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_(subculture)。
(19)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er_(subculture)。
(20)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kinhead。
(21)(22)(23)(24)(25)(26)(29)(30)(31)(32)John Clarke,Smart Hall,Tony Jefferson & Brian Roberts,"Subcultures,Culture and Class",in Sm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Hutchimon,1983,p.21,p.21,p.18,p.18,p.19,p.20,p.57,p.57,p.64,p.62.
(27)Phil Cohen,"Subcultural Conflict,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in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p.81.译文引自Graeme Turner《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北亚太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8)Phil Cohen,"Subcultural Conflict,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in Sm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pp.82-83.译文引自Graeme Turner《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198。
(33)Dick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7,p.103.
标签:亚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中产阶级论文; 霍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