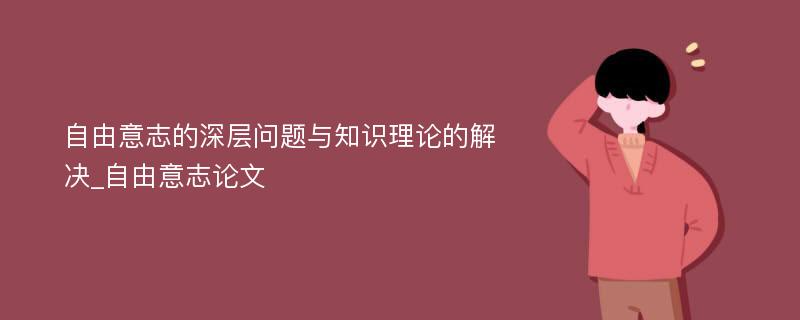
自由意志的深问题及其知识论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论文,解决方案论文,自由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自由意志:浅问题和深问题
自由意志问题一直是行动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而棘手的问题。在对各种形式的决定论的承诺和对自由意志的肯定之间,似乎有一道跨越不过去的鸿沟:根据因果决定论的观点,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其行动受因果法则的支配,因此任何一个行动的发生都是为先前的事件和因果法则所决定的;然而,意志自由却意味着未来的开放性:即便给定所有先前的事件和因果法则,我们的行动也可以与实际发生的有所不同(我们有能力做出不同的行动选择);因此,如果因果决定论是成立的,自由意志如何可能?
而且,人们还发现,即使因果决定论不成立,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也仍然是一个问题:自由意志意味着对行动的选择与控制,而不是行动的随机性。正如凯恩所说,大脑或者身体中的非决定的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与我们所说的自由与责任完全相反”。(Kane,p.7)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自由意志方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问题:自由既不与决定论相容;也不与非决定论相容;无论世界是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似乎都难有自由意志的一席之地。(参见同上,p.8)齐硕姆也曾对人的自由的形而上学问题做出这样的概述:“人是负责任的行动者;但是这个事实似乎与关于人的行动的决定论观点……相冲突;它似乎也与关于人的行动的非决定论观点……相冲突。”(Chisholm,pp.47-48)似乎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理解无论如何都会陷入困境之中:相容论(compatibilism)的倡导者们试图调和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他们肯定了决定论,却无法有力地说明未来的开放性如何可能。而对于不相容论(incompatibilism)来说,又有两种情况:处于不相容论一端的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否定了决定论,却同样难以在非决定论的意义上解释和肯定自由意志;处于不相容论另一端的强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则干脆把自由意志看作一种幻觉,进而否定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
然而,自由意志问题却一直是人们挥之不去的牵挂,因为它关系到人的尊严和责任,关系到道德的评价与法律的奖惩。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虽然对自由意志问题的研究尚未实质性地突破这个两难局面,但是在近50年的艰难探讨中,一些行动哲学家开始尝试进一步澄清自由意志的概念;而且,与之相伴随,一些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也相继出现。
通常,对自由意志概念的理解有以下两个基本的要点:第一,我们的选择并非完全由因果法则所统辖;第二,我们拥有某种对未来做出选择(或者使未来以某种方式出现)的能力。(参见Honderich,pp.292-293)然而,一些行动哲学家注意到,这种自由意志可以进一步在两个不同的层次得到理解:浅层次和深层次,即行动自由(freedom of action)的层次和意愿自由(freedom of will)① 的层次;一个人的行动自由涉及到自由地按照他的意愿行动,而他的意愿自由则进一步关系到自由地意愿其所愿。
与此相对应,自由意志问题也可以被区分为浅问题和深问题。例如,齐硕姆曾经提出要将“我们是否自由地去做我们意愿或者打算做的事情(whether we are free to accomplish whatever it is that we will or set out to do)”的问题,与“我们是否能自由地意愿或者打算去做那些我们确实意愿或者打算去做的事情(whether we are free to will or to set out to do those things that we do will or set out to do)”的问题区分开来。(Chisholm,p.55)而法兰克福则通过“行动自由”与“意愿自由”的概念对之做出了相应的区分。他认为关于能够自由行动的行动者(an agent who acts freely)的观念与关于拥有自由意愿的行动者(an agent whose will is free)的观念是不同的。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由行动)既不是拥有自由意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它不是拥有自由意愿的充分条件,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没有自由意愿的动物也可以自由行动;它也不是拥有自由意愿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当一个人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因而不能通过其行动实现某个意愿时,他仍然可以自由地意愿这个意愿。(参见Frankfurt,p.135)凯恩则通过“浅自由(surface freedom)”和“深自由(deeper freedom)”的概念区分了上述两种自由:“浅自由”关系到自由地按照意愿行动,它肯定的是我们作为行动创造者的地位;而“深自由”则关系到自由地意愿,它所肯定的则是我们作为意愿创造者的地位。(参见Kane,pp.2-3)
行动哲学家们做出这种区分,一方面是要表明,自由意志问题的研究中,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深问题,而不是浅问题;另一方面是要借助于这种区分和这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理解,推进自己的研究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理解之下,“自由意志(free will)”这个涉及到人的某种能力的一般性问题,转换为“自由地意愿(freely will)”和“自由的意愿(free wills)”这样的较为具体的问题。与此同时,对自由意志的这种深的理解,也使一些行动哲学家如威勒曼得以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问题转换为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问题。
二、深问题:从戴维森到法兰克福和威勒曼
1.戴维森的“标准模型”及其“深度”问题
戴维森模型所涉及的主要是与自由意志问题密切相关的行动主体性(agency)问题。在行动哲学的研究中,关于行动主体性问题的解决主要有两个进路,一个是事件因果关系(event-causation)的进路,一个是行动者因果关系(agent-causation)的进路。前者以事件为基点,试图将行动主体或行动者的角色还原为先行于相关行动并且构成相关行动原因的事件的角色。这一进路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戴维森。后一个进路的主要代表有齐硕姆、泰勒(Taylor)和奥康纳(O' Connor)等人。他们将行动者看作是行动的不可还原的和原初的原因,认为行动是由行动者自身而不是他内部的某一部分(如欲望、信念、选择等)所引起的。
戴维森关于行动主体性问题的事件因果关系的解决,对行动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人们称为解决行动主体性问题的“标准模型”。在戴维森看来,(1)解释一个行动就是建构这个行动的基本理由(通常是信念、欲望);(2)基本理由将行动理性化,并且是行动的原因;(3)为信念和欲望所引起的行动是有意图的,意图是理解行动主体性的关键;(4)行动主体性的定义是:“一个人是一个事件的行动主体,当且仅当有一种关于他所做事情的描述使得陈述他有意图地做了这件事情的语句为真。”(Davidson,p.46)
戴维森的方案受到了由法兰克福等人提出的一系列反例的挑战。这些反例所蕴涵的对戴维森方案的质疑,主要指向这样一点:在与行动相关的因果链条中,我们只能看到引起行动的信念和欲望,却看不到行动者的作用。从前面谈到的关于自由意志的深问题和浅问题的区分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戴维森方案所涉及的问题还不够深:它只表明了行动是由信念和欲望等心理状态引起的,却忽略了信念和欲望背后的、有能力选择或者持有信念和欲望的行动者。
威勒曼指出戴维森关于行动主体性的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有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作为关于行动主体性的一种因果解释,它将行动主体自身丢在了相关因果链条的外面。在戴维森的模型中,因果的链条从理由(信念和欲望)到意图再到身体的运动,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事件跟随着一个事件,却看不到行动者的作用。“当理由被描述为直接引起意图,而意图被描述为直接引起运动时,不仅行动者被排除在外,而且任何可能扮演行动者角色的心理的东西也被排除在外了。”(Velleman,1992,p.463)
第二,戴维森的模型没有对行动和单纯有动机的活动做出区分。而威勒曼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为一个理由所引起”和“为那个理由而做出”。后者不仅关系到行动之为理由所引起,而且关系到行动在行动者那里得到辩护,或者关系到行动者的理性能力的运用。一个理由要成为行动者行动的基础,它必须“向那个主体辩护那个行为,……而且它必须因此调动他的某种理性倾向从而让他去做得到辩护的事情,让他的行为举止与辩护相符合。”(同上,2000,p.9)尽管在戴维森的模型中一个人的行动可以为理由所引起,但是威勒曼认为,它可能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被引起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为了那个理由而做出的。信念和欲望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而引起行动,但是它们并非必然作为行动的理由而起作用。
由此可见,戴维森的模型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行动主体性的充分解释。关于行动主体性以及自由意志问题的研究需要有进一步的“深度”。
2.法兰克福:“高级欲望(higher-order desires)”
法兰克福认为解决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作为一个人(person)”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其特殊的意愿结构。虽然人类和动物都拥有欲望和动机,然而,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拥有形成“二级欲望(second-order desires)”的能力。“除了想望和选择以及被驱动去做这做那以外,人还可以想望持有(或者不持有)特定的欲望和动机。他们能够想望……与他们之所是不同。”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在二级欲望的形成中表现出来的反思性自我评价(reflective self-evaluation)的能力”。(Frankfurt,p.129)
所谓二级欲望就是关于持有或者不持有某个一级欲望的欲望。就“A想望‘想望X’(A wants to want to X)”(X指一个行动)这种形式的陈述句而言,第一个“想望”表达的是一个二级欲望,而第二个“想望”表达的是一个一级欲望。当A想望对X的欲望成为驱动他有效地行动的欲望时,他就是在想望使他的那个一级欲望产生效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被想望的一级欲望就成为了他的意愿(will),或者说,他是在想望那个一级欲望成为他的意愿。法兰克福将那种让某个一级欲望生效或者成为行动者的意愿的二级欲望称为“二级意志”(second-order volition)”。他认为,对这种“二级意志”的拥有才构成了对于人来说最为本质的东西。(Frankfurt,pp.129-131)
在法兰克福这里,低层次欲望(desires)之成为意愿(wills),就在于其与高层次欲望相一致,因为正是高层次欲望使得低层次欲望成为我们所想要持有的意愿。这样,自由意志的那个深问题,即能够意愿我们所意愿的事情的问题,就通过不同层次欲望间的某种一致性关系得到了解决:当我们的一级欲望与特定的二级欲望相一致时,我们就持有了我们想要(二级)持有的意愿(一级)。在这里,我们的意愿是自由的——是我们想要持有的。
由上述可见,法兰克福关于自由意志的“分层理论”与戴维森模型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它涉及到行动者对其行动动机的反思式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的解决方案比戴维森的模型更深了一步——更靠近了对自由意志的那个深问题的解决。
然而,法兰克福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他的二级欲望仍然是可以与行动者脱离开来的东西,从而行动者自身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说明。正如威勒曼所说,“自治行动的分层模型似乎仍然是不充分的。在这个模型中,主体对其一级欲望的觉知唤起了关于这些欲望是否应该使他得到激发的二级欲望,但是后者并非必然是对前者的理性力量的反应:它们不是对一级欲望的作为行动之理由的能力的反应。因此,主体的高级欲望所扮演的是主体仍然可以与之分离开来的因果角色。”(Velleman,2000,p.13)
法兰克福的解决方案没有对行动者想要实现一级欲望的不同类型的原因进行区分。在法兰克福的解决方案中,行动主体是出于对自己压抑心理的反应,还是出于对一级欲望作为理由的力量的反应而赞许一级欲望,是无关紧要的。而威勒曼认为,对于行动主体性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行动者对其一级动机持有赞许的态度,而在于“他对那些动机持赞许态度”的理由。(同上)
在威勒曼看来,对一级欲望的单纯的赞许和出于理性能力而对一级欲望的赞许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行动主体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对一个动机的有利反应就将这个动机看作是主体的意愿。只有通过将一个动机作为行动的理由而对其做出的有利反应——由主体的理性能力做出的反应,我们才能将这个动机看作是主体的意愿。自主性所要求的,似乎不仅仅是一般的高级动机的能力,而是特殊的高级动机,这些高级动机在一级动机被感知为理由时才能强化行动者的一级动机。”(同上,pp.13-14)因此,对于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解决而言,单纯的二级欲望本身还不足以将行动者的欲望转变成行动者所意愿的意愿。为了弥补法兰克福方案的不足,威勒曼进一步提出关于行动主体性问题的知识论的解决方案。
3.威勒曼:知识论意义上的行动主体性与自由
一方面,威勒曼想要避免将行动追溯到行动者内部事件的戴维森式自然主义行动主体性模型,这一模型付出了牺牲行动主体的代价;另一方面,他也想要避免那种将行动者看作引起行动之原始要素的齐硕姆式行动者因果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带有非自然主义的味道。在对法兰克福方案的优点和不足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威勒曼试图寻找一种特殊种类的、与行动者功能同一的事件,即“可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或者附随在事件因果关系之上的行动者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同上,1992,p.467)
威勒曼将“行动者与他自己的行动的特有关系”看作是“一种认识关系——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同上,“新版Practical Reflection导言”)这里的一个重点是威勒曼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特殊结构的基本预设。在其1989年出版的《实践的反思》(Practical Reflection)一书中,他举了照镜子的例子来说明人类自我意识的这种特殊结构。正如“看向镜子中的脸事实上是在做着两件事情——试图看它自己和将它自己呈现出来以被看到”(Velleman,1989,p.3)一样,威勒曼指出,实践的自我知识(practical self-knowledge)是自我实现的;在行动中,关于一个行动的知识和这个行动的执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通过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威勒曼同意安斯科姆(Anscombe)的看法,即认为在行动的意图中包含了行动者关于其行动的知识:当行动者有做某件事情的意图时,意图的内容就构成了行动者关于他自己将要做什么的实践知识。意图的内容、关于相关行动的描述、行动者关于自己相关行动的知识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意图和信念一样都是知识的表达。当然,对于意图中所包含的知识而言,“事实与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之间的因果次序,与为理论知识所特有的这二者之间的因果次序是颠倒的。”(同上,“新版Practical Reflection导言”)意图表达的是关于行动者将要做什么的实践知识。这种包含在行动意图中的知识,就是威勒曼所说的第一种实践的自我知识:行动的命名(action naming)。这是关于某个行动的直接事实的知识,并通常是行动者对“你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根据意图而行动就是实现包含在行动意图中的关于行动的第一种实践的自我知识。
然而,在威勒曼看来,对于行动主体性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种类型的实践的自我知识:行动的理解(action understanding)。这是与某个行动相关的、构成了行动者做出这个行动之理由的一系列事实的知识。理解我们为什么做出某个行动,就是为这个行动提出一个理由系统(rationale),也就是对“我为什么做x”这种形式的问题给出一系列的回答,如:
我在做什么?
我在倒旧茶。
我为什么倒旧茶?
因为我在清空茶杯。
我为什么清空茶杯?
因为我在泡新茶。
这种综合的、全面的自我知识是由“一系列描述”构成的,其中每一个描述都是对此系列中的前一个描述所描述的同一个行动所问的“为什么”的回答。在威勒曼看来,知道我们做什么,就是通过将我们的身体运动置于某种动机和环境的解释语境中来把握我们的身体运动;为了一个理由而行动,就是实现这种“更全面的实践知识”,就是将构成行动之理由的相关事实整合起来。实践知识的可靠性在于,行动者对这种知识的拥有是与他对这种知识的实现相联系的:行动者“倾向于做他们此刻认为他们此时要做的事情”。(参见同上,1989,第1章;2000,导言;以及“新版Practical Reflection导言”)
威勒曼指出,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做我们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人类行动的构成性目标(constitutive aim of action)或者行动的高级理性目标(higher-order rational aim of action),就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knowing what we' re doing)”。他认为行动虽然是为低层次的欲望和信念等等所激发的,但是这些欲望和信念及其与行动的关系却要受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一行动的构成性目标(它自身就是目的)的控制:这种行动的构成性目标通过“对行动的激发进行控制”而将身体运动转变为自主行动。
他将行动的辩护与信念的辩护做了类比:信念的构成性目标(求真)决定了信念之正确性的标准,而后者又决定了信念辩护的理由。威勒曼认为,对于行动而言,我们也必须首先找出其构成性目标,然后我们才能获得“内在于行动本性的正确性标准”,而这个标准则决定着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行动的理由。正是这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行动的构成性目标引导着我们按照自己关于行动的知识而行动,它通过将我们引向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对我们做什么加以控制。(Velleman,2000,导言)威勒曼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有意图的行动是我们的发明,而“我们对它们的发明是在于我们对它们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由于对它们具有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上的权威。”(同上,“新版Practical Reflection导言”)
威勒曼的知识论方案确实捕捉到了行动主体性的一些重要特性。与戴维森和法兰克福的模型相比,他的解决似乎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那个深问题。他不仅仅将诸如信念、欲望和意图之类的命题态度当作行动的理由和原因,也不仅仅一般性地诉诸于高级欲望,而是在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结构的一种预设之下,诉诸于行动者的实践的自我知识,并且将与之相关的行动的构成性目标作为对将行动者的行动理性化、以及将作为行动动机的欲望转化为行动者所意愿之意愿的基础。
在威勒曼的方案中,命题态度和行动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命题态度不仅在行动的产生中扮演了因果角色,而且还与其它倾向性的或者环境的因素一起构成了行动所由以做出的理由;它们是行动的理由,因为它们是行动者对他自己行动的实践的自我理解;而行动者做出行动就是实现这种实践的自我理解,这是由自身就是目的的行动的构成性目标所决定的。这样,威勒曼的方案就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避免了法兰克福方案的困难和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勒曼向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的时候,他也同时将自由意志的问题确定为了一个知识论问题。
威勒曼区分了讨论自由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是知识论的。
在形而上学的视角之下,他对自由意志的看法与新近得到热烈讨论的心理学家韦格纳(Wegner)的看法非常接近。(参见Wegner,2003,2004)他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经验来自于我们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能从自由意志经验推出形而上学的自由,形而上学的自由是一种错觉。
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指“可能不存在我们必须那样描述未来以使我们能够正确描述它的独特方式——至少,没有哪种方式是在自然法则之下由目前的世界状态所必然决定的”。(Velleman,2000,p.34)如前所述,在威勒曼看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我们行动的构成性目标,我们通过做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而实现这个目标。虽然我们的行动是被决定的,可是构成我们关于自己行动的知识(行动的命名和行动的理解)的描述却并非如此。我们有资格以不同的方式描述未来。我们所享有的就是这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或者开放未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行动者的自我知识是自主性的,因为它是特许的愿望思维(licensed wishful thinking)。而行动者的思维之所以是特许的愿望思维,是因为它们是自我实现的。”(同上,1989,p.69)
威勒曼提出知识论方案的目的是进一步解决行动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深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知识论视角自身的局限性,也带给了威勒曼方案一些问题。通过对威勒曼方案的行动命名问题和行动辩护问题的指出,我想要在下一节表明,单纯出于知识论方面的考虑,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在行动时拥有为行动的辩护所需的自我知识;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引入某些别的东西。
三、威勒曼方案的问题及其启发:行动时我们知道什么?
威勒曼方案的第一个问题是行动命名问题,它涉及到第一种实践的自我知识——行动命名。这个问题是说,当一个人的相关信念为假时,这个人在行动时就不能正确命名他的行动。“我知道我正在泡茶”和“我知道我牙痛”(或者“我知道我相信外面在下雨”)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自我知识。后者报告的是一个内部现象,我的相关知识的真与外部环境无关;前者报告的则是与外部环境相关的行动,因而不具有第一人称的权威性。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进一步扩展了的例子:
我倒掉杯中的液体,错误地相信它是昨天剩下来的旧茶,而我想要(我的意图是)泡一杯新茶。我的同事问,“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倒旧茶。”他又问,“你为什么倒旧茶?”我说,“因为我在清空杯子。”“你为什么清空杯子?”“因为我在泡一杯新茶。”于是,我的同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问:“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经过他的解释,我才知道,原来我杯子里的液体并不是昨天剩下来的旧茶,而是我的同事刚刚给我泡好的他新近从杭州带回来的龙井茶。我于是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倒掉了新泡的龙井茶。
问题在于:当我带着倒掉旧茶的意图而倒掉了杯子里的新茶时,我知道什么?在行动命名的意义上,(1)我不知道我在倒旧茶,因为事实上我倒掉的是新茶,而知识通常被看作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2)我不知道我在倒新茶,因为在我的倒掉旧茶的意图中没有包含这样的知识;(3)而且,我不知道我的身体运动,因为我的身体运动本身并非那个构成行动之辩护的理由体系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行动时,我们通常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运动的(某些特殊情况除外,如学习某种技能)。例如,当我带着开灯的意图去按开关按钮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手在向哪个方向移动多少距离,而我所知道的是我在开灯。当有人问“你在做什么”时,我不会回答说“我在以如此这般的方式移动我的手臂”,而是说“我在开灯。”行动命名意义上的自我知识是包含在行动者的意图之中的。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不知道行动时我们在做什么,而且是在相关信念为假时,我们不可能知道行动时我们在做什么。在相关信念为假的情况下,第一类实践的自我知识似乎是不可能的。
当谈论在“知道我行动了”(Knowing that I Acted)和“知道我做了什么”(Knowing what I Did)这两种情况下的第一和第三人称的非对称性时,奥布赖恩(O' Brien)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即使当行动是通过行动者的意图而得到描述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说行动者通常在他关于他做了什么的知识方面具有权威性。奥布赖恩的思考是基于对行动的意图和行动的结果之间的可能的不一致性的认识。他举了在斯诺克比赛中想要把球打进角袋的人的例子:“虽然我们确实想说行动主体对于他们是否行动了具有权威性,可是我们却似乎难以主张行动主体对于他们是否将球打进了角袋具有相对于其他人的权威性。”(O' Brien,p.362)
当然,奥布赖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即在基本行动(basic action)的意义上,我们对自己的行动具有权威性。关于基本行动,奥布赖恩是指“那些行动主体无需做任何其它事情而可以直接执行的行动;它们是行动者为了做任何其他事情而必须要执行的行动。”(同上,p.363)奥布赖恩倾向于将身体运动看作是基本行动(与戴维森关于原始行动[primitive action]的看法相近)。然而,这个意义上的自我知识很难被看作具有行动命名的意义。
然而,与在持有相关错误信念的情况下行动者在第一种知识方面的无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行动者关于自己的行动确定地知道许多重要的事情。这种确定而丰富的自我知识就是威勒曼所说的“实践的自我理解”。当我将液体倒出茶杯、错误地认为它是旧茶时,尽管我不能正确命名我的行动,我却能够在一种十分重要的意义上理解我的所作所为:我能够给出对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的问题的回答。
这似乎是我们的实践自我知识的一个奇特性质:行动理解相对于行动命名具有优先性。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优先性?行动理解是仅仅在于对那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的问题的回答吗?或者,在这种自我理解中存在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吗?当我们并非确切地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理解的是什么?
这也涉及到威勒曼方案的第二个问题,即行动辩护问题。根据威勒曼的主张,实践的自我理解包含对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这种形式的问题的回答。然而,对于我们的任何一个行动而言,我们能提出的这种形式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回答可以有无限多:当一个问题得到回答时,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为什么”的问题。然而,这个提问和回答的系列必须停止在某个地方,否则带有辩护力的理解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行动的理解并非仅仅在于对那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的问题的回答;必须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给这个问答的系列一个终点,行动的辩护才有可能,而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知识论的考虑所能够提供的。
解决行动命名问题和行动辩护之理由系列的无限倒退的问题的希望,也许在于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实践自我知识的目的论结构。从目的论的视角看,构成行动者第一类实践自我知识的,不是行动的命名,而是行动目标的命名,而构成行动者第二类实践自我知识即行动理解的,是关于一系列手段-目的关系的知识(对那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的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到一系列手段-目的关系)。简言之,当我们行动时,我们知道行动的目标以及这个目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之间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系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行动时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做出行动以实现我们的自我知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行动理解相对于行动命名的优先性,我们才能在因为拥有错误信念而不能正确命名行动的情况下理解我们的行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终止行动辩护之理由系列的无限倒退才有了可能:行动者关于其行动目标的知识合法地终止了这种倒退,从而使得行动的辩护成为可能。
上述关于威勒曼方案的两个问题的讨论表明,目的论的视角对于自由意志深问题的解决也许是不可缺少的。
注释:
①在英语中,“will”作为名词有“意志”、“意愿”等含义。下面的讨论将进一步表明,在“意志自由”这个总的概念之下,将与“行动自由”相对应的freedom of will翻译为“意愿自由”,对于清晰地理解当代行动哲学关于自由意志问题讨论的一些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