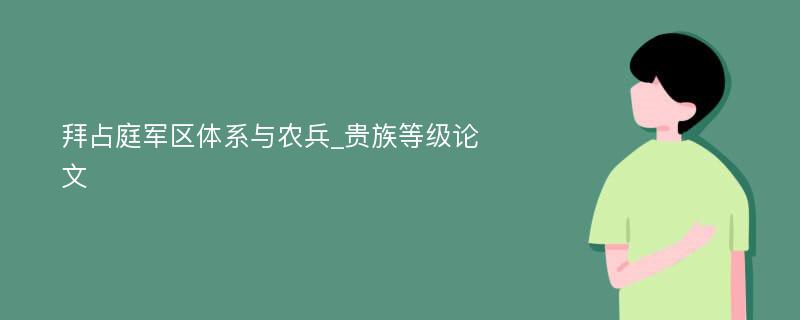
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区论文,拜占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是公元7—12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即按军区、师、团、营等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域。这种军政兼容、兵农合一的制度促使拜占廷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对加强拜占廷国防力量,稳定社会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拜占廷学者对军区制问题仍未给以足够的重视、特别对军区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识不足,没有对之开展必要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军区制的起源入手,对军区制的发展和农兵阶层的形成,特别是对这种制度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
拜占廷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公元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试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目前,已有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拜占廷军区制形成于公元7世纪。学者们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然而,关于拜占廷“军区制”名称来源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塞姆(Θεμα)一词源于阿尔泰语Tuman,意为“万人”[①a]。这种意见之不可信赖在于,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影响一般认为是从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军区制在公元7世纪末已经普遍存在于拜占廷全境。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来源于希腊语“Θεσηs”一词,据著名的拜占廷学者N。伊科诺米基斯考证,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②a]。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45—959年)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①b]。
军区是由公元7世纪末拜占廷的“总督区”(exarchates)演变而来。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城由总督统辖。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早在公元4世纪,迦太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公元533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该城以后,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主要集散地[②b]。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拉文纳在公元4、5世纪日耳曼各部落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逐步取代罗马和米兰的地位,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中心。公元540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地位[③b]。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们均于公元6世纪中期被确定为总督区。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体制有别于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527—565年)统治时期拜占廷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拉文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德人的军事压力,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总督区的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的一元化领导,使总督统一指挥区内军事和行政活动,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④b]。
总督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军区,并在拜占廷全境广泛推行,与当时拜占廷面临周边民族军事入侵的巨大威胁、边关吃紧的形势有密切的联系。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廷边疆地区,特别是东部边境便遭到外族不断入侵。查士丁尼一世死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波斯军队从东面侵入拜占廷的亚洲属地,先后夺取了叙利亚、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重镇,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从北面大举南下,侵入帝国腹地。西哥特人则在西面夺取了拜占廷的西班牙属地,伦巴德人也迫使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势力龟缩于拉文纳城内[⑤b]。公元7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的兴起和扩张,拜占廷的东部局势更加紧张,四面告急,战事不绝,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据当时的史家记载,人们惊呼“世界末日来临了”[⑥b]。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皇帝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610—641年)开始逐步建立军区。最先建立的军区有亚洲领土上的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军区也分别建立。上述几个亚洲军区在反击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屯兵东征、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基地。自公元7世纪中期,军区制在帝国境内逐步推行,至公元8世纪中期,拜占廷大部分国土均被置于军区制管理之下,全国共建立六大军区,即除了上述五个军区外,还有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军区。此后不久,又逐步组建起海上军区,辖治爱琴海上大小岛屿[①c]。
军区虽然是从总督区演化而来,但是又与后者有区别。其一,它们的管理结构不同,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与其他省区无异,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而在军区内,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附属于军事系统。与总督相比,军区首脑“将军”拥有更大的权力。其二,总督区制度下没出现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组成。但是军区制下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他们成为中期拜占廷(公元7—11世纪)的社会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廷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
拜占廷军区制的推行经历了摸索和试行的过程,军区制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优势并不是从一开始即为统治集团所认识。当时,拜占廷帝国受到四面之敌的压力,原驻守北非、两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和意大利的军队纷纷撤向帝国腹地。这就促使京城附近地区的驻军和防务重新进行部署[②c],军区制的推行由此逐步展开。同时,公元7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和拜占廷北非、西亚和巴尔干部分领土的丧失,也使拜占廷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作为国家税收和兵力主要来源的小农大量破产,小农经济全面衰退,而且作为国家统治阶级基础的贵族及其大地产也遇到毁灭性打击。因此,军区制的推行意味着拜占廷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拜占廷王朝采取了三项重要步骤,最终确立了军区制,也完成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一,各地区分别建立新军区。拜占廷军区制首先是在其亚洲属地上出现的。公元7世纪初,由于波斯人入侵,拜占廷东部前线吃紧。随着边防部队的后撤,皇帝伊拉克略在帝国小亚细亚地区首先建立了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其他皇帝又建立了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军区。根据公元9世纪的资料记载,亚美尼亚军区组建于公元629年,它包括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黑海西南岸至小亚细亚中部卡帕多利亚的广大地区,辖治17个防区,统兵不足万人[①d]。亚美尼亚军区以西,自阿里斯河中下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为奥普西金军区,它可能先于亚美尼亚军区3年建立,所辖防区略少,地位也略低于亚美尼亚军区,统兵约6000人[②d]。亚美尼亚军区西南至爱琴海沿岸地区为阿纳多利亚军区,由于它地处波斯人进兵的主要方向,地位极为重要,故与亚美尼亚军区列同一等级,该区有34个要塞,统兵15000人。色雷斯军区的辖区位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西侧,其重要性在于防御斯拉夫人的侵扰,由于其作用与上述三个军区比较略差,故史料记载不详。根据在该地区出土的拜占廷印章,学者们甚至认为它不是独立的军区,或是附属于奥普西金军区,或是由奥普西金军区将军兼任该军区首脑[③d]。基维莱奥冬军区为拜占廷小亚细亚沿海军区,负责防御海上入侵,管理沿海要塞和海军基地,兵力仅3000人。由于当时阿拉伯海军势力羽翼未丰,尚未构成对拜占廷的威胁,故而海上军区的作用也不甚重要,其将军的年薪仅10金镑[④d]。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军区的设立是在紧迫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和平环境中从容不迫完成的。早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就在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对帝国军队进行调整,将原罗马军团按军事功能重新编制。到公元5世纪,帝国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驻守多瑙河前线,一支沿幼发拉底河巡逻,两支驻扎首都地区,听候皇帝调遣。至公元6世纪,由于查士丁尼一世西征的需要,野战军的人数略有增加。但是,6世纪末和7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使拜占廷军队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损失极为严重,帝国西部地区军队的2/3被击溃,东部地区军事力量也有1/7被摧毁[①e]。帝国的军事防务体系遭到彻底破坏,漫长的边境防务线被撕开,大片的领土落入敌手。残余部队零零散散地撤向内地,并在驻扎地建立起军区。军区的建立使混乱的局面得到初步整顿,为后两个步骤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第二,完善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拜占廷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上沿袭公元5、6世纪的旧制,但在拜占廷军队遭到重创而节节败退之际,军队内部的组织系统也被破坏。因此,各军区建立后,首先着手重新确定军事等级编制,调整军队内各级官兵的关系。由于各军区建立的时间有前有后,其人数也不同,因此在编制上也不一样。但是,一般看来,军区是由2到4个师(Toυρμα)组成。师由5到7个团(Báυδου)组成,其下还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若为骑兵,则人数在50—100人,若为步兵,人数在200—400人之间。依此推算,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3000人左右[②e]。
军事序列的确立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军事权力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使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其二,在此基础上,各级经济关系得到确定。根据公元7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军区将军的年收入为40—36金镑,师长的年收入为24金镑,团长、营长和队长分别为12、6、1金镑,一般士兵年收入为12—18索里德,相当1/6—1/4金镑[③e]。当然,各军区地位不同,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为一级,其将军年薪为40金镑,二级军区将军年薪为30金镑,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10—20金镑,仅相当或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④e]。经济等级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军区制的确立。但是,由于拜占廷军事失利、领土减少,以及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无力逐年支付军饷,于是在军区成立之初,采取每隔3年或4年分批发放军饷的办法,这一点为多种资料所证明[⑤e]。
第三,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进而形成农兵。这一步骤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促进了农兵阶层的发展,而这个阶层是军区制的基础。应该指出,以田代饷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以之举。公元7世纪上半期拜占廷国土丧失严重,特别是在帝国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的北非、西亚地区的丧失,使国库年收入减少了2/3—1/2以上。埃及行省的收入长期以来约占帝国财政收入的3/8,加上伊里利亚地区的收入可占帝国总收入的1/3。因此仅北非地区陷落阿拉伯人之手就使拜占廷损失1/3的收入。据粗略估算,伊拉克略一世统治初期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的1/3左右[①f]。如果按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11万金镑计算,伊拉克略时代年收入仅为36667金镑,相当2639952索里德。这笔收入远不能弥补拜占廷财政预算的赤字,因为仅阿纳多利亚一个军区的年度军事预算就超过123万索里德,几乎占了国家年收入的一半[②f]。显然,拜占廷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支付军区的军饷,迫于无奈,只好以田代饷,将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充作军饷,按照军种和级别颁发给各级官兵。
亚洲诸军区首先采取以田代饷的办法,其主要原因,一则该地区首先建立起军区,二则该地区有大量弃耕农田。小亚西亚和埃及地区曾是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谷仓,这里水系充沛,土地肥沃,气候适于农耕,因此农业一直比较发达。但是公元6世纪元、7世纪初的战乱和瘟疫使当地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大量土地抛荒。这些土地就成为军区制下军役田产的主要来源。
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不论何种兵种、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田产,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在服役期(一般为15年)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Στρατlωζlκá κτηματα)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卖买,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股役,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服役,或参加边境防御战和远征,或修筑军事要塞、架桥修路,或营造舰船。第二种是间接服役,即由一户或几户农兵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兵的给养。这种形式的军役义务与前一种一样,在文献中被称为“兵役土地”(Στρατεíα)[③f]。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事编制,听从军区命令,随时集中,从事军事工程劳役或随军作战。
三
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成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廷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周边民族之间的和平。以此为起点,拜占廷在其中期历史中获得多次重要的军事胜利,其中又以瓦西里二世(Basil,976—1025年)的赫赫战绩为军事实力发展的顶点。显然,军区制的推行对扭转拜占廷的危急形势起了主要作用,表现有二。
第一,军区的军事化结构解决了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学者们估计,公元4、5世纪的拜占廷军队总数可达65万人[①g]。但是,由于连年战争,人力资源消耗严重,至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末期,军队人数已减至15万人,以至拜占廷在对波斯的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力不足6400人[②g]。为了弥补军队人力资源的巨大缺口,早期拜占廷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日耳曼人雇佣兵,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也被迫充作雇佣兵的军饷[③g]。巨额军饷连同其他开支就成为拜占廷国库难以支付的沉重负担。当时,拜占廷年收入约为11万金镑,其中80%用于军费开支[④g]。军区制将本国公民作为军队的主要兵源,使军队建立在广泛的本国人力资源基础上。这一制度将成年公民按照军队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屯田于边疆地区,平时垦荒种地,战时应招出征。这样就使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另外,拜占廷政府为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长期推行移民政策,如公元7世纪末年,迁入奥普西金军区的斯拉夫人达7万人,仅762年迁入小亚细亚军区的斯拉夫人多达21万之众[⑤g]。军区制下的农兵大多屯田于边疆地区,因此其参战的目的具有保家卫国的性质,战斗力明显提高。而且,农兵占用的军役田产可以世袭,故使拜占廷的兵源世代维系。另一方面,军区中除高级将领,如将军,从国库领取薪奉外,其他各级官兵均自备所需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而不依靠国库供给,从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二,军区制下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早期拜占廷国家曾在罗马军团的基础上进行过军事改革,组建起边防军、野战军和御林军三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边防军(Limitanei)驻扎于特定的边疆地区,野战军(Comitatenses)为机动部队,随时奉旨调动,而御林军(Praesentales)则驻守都城,负责皇室和朝廷的安全[①h]。但是,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军权和行政权分离,军队首脑仅负责战事而不介入行政事务。行政长官则控制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这种军政权力分立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和君士坦丁一世改革的突出特点,曾有效地消除了罗马帝国后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但是,在公元6世纪后期,由于军政权力相互斗争,拜占廷地方管理陷于混乱,常常出现军队出征御敌而得不到行政长官支持的现象,至于两方内讧、互挖墙角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军区制的推行扫除了地方管理中的推诿现象,将权力集中于将军一身,使之能集中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而行政长官或作为将军的幕僚听命于将军,或被挤出权力机构。地方统治一元化和军事化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早期拜占廷皇帝旨在削弱地方势力,增强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也曾扩大了朝廷各部门的权力,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时刻,庞大的官僚体系运作迟缓,难以对随时变化的军情作出及时反应。特别是当大规模入侵令某一驻守边关的部队难以应付时,军队中枢指挥机构不能立即抽调其他部队前往增援,经常贻误战机。而军区制是依据防务需要建立的,军区首脑按本区实际情况统筹谋划,或调动军队或组织生产,并以其控制的军、政、财、司法等权力,相对独立地指挥,故可使下情及时上达,也可迅速执行中央命令,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廷国防力量。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②h]。
军区制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结果。
其一是农兵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的兴衰对于拜占廷历史的演化影响深远。拜占廷是农民占主体,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社会,因此,尽管由于其具有特殊地理位置而使工商业收入可观,但是,其农业生产仍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经济的盛衰决定拜占廷国力的强弱。早期拜占廷的土地占有形式分为国有和私有地产两大类。其中前者成分复杂,包括皇产、教产、市产、军产,而私产地多为大地主的庄园[③h]。在国有地产上的主要生产劳动者是小农,他们也是拜占廷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公元6世纪后半期,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小农大量破产,纷纷逃亡,弃耕荒地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战事最频繁的小亚细亚地区,昔日盛产谷物的田地被战祸夷为荒野。这种小农大量破产的现象已被学者们公认为是公元5、6世纪拜占廷社会的一个特点[④h]。为了稳定小农阶层,保持国家税收来源,查士丁尼一世通过大量法令,强迫小农固着于土地上,取消他们原有的迁徙自由,甚至明确规定农民必须子承父业,不可从事其它职业[①i]。然而,查士丁尼一世的强制措施并未奏效,大地产对小农土地的兼并和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加速了小农破产的过程。
军区制则为小农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军役土地制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负有军役义务的小农阶层。农兵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负有从军作战的义务,他们以小农家庭经营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小生产就成为农兵经济的主要形式。农兵除了担负赋税以外,还要为从军作战作好一切准备。当农兵的长子继承其父的军役义务和军事田产后,其他的儿子便补充到负有军役义务但不从军作战的自由小农中。这样,农兵和自由小农并肩兴起,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而帝国法令也将两者同等看待。据此,现代拜占廷学者认为“农兵和自由小农属于同一阶层”[②i]。
自公元7世纪军区制推广以后,拜占廷的农兵阶层逐步形成,与自由小农同步发展。小农阶层在军区制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不断壮大。公元7、8世纪颁布的《农业法》反映了当时拜占廷农村中小农迅速发展的真实情况。该法共有85条,其中2/3的条款涉及小农问题[③i]。小农数量的增加还与拜占廷长期推行的移民政策有关。移民之举既可开发利用大片荒地,进而为恢复国力扩大了物质基础,又能充实壮大小农阶层,扩大了税收来源。由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兴起,拜占廷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公元9、10世纪的年收入最高时可达58.4万金镑,相当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年收入的5.31倍[④i]。以军区制下兴起的农兵为主体,包括自由小农在内的小土地占有经济在公元9、10世纪之交达到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在此期间,拜占廷的某些君主已经认识到小土地占有者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皇帝利奥六世(Leo,886—912年)曾在其法令中提出:“朕以为有两种职业对国家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一为农民,一为兵士。朕以为此二业当在各业之首”[⑤i]。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920—944年)也明确指出:“此种小土地占有者予国利甚巨,因其缴纳国家税收,提供军队服役之故。倘若此类农民数量减少,其利必失”[⑥i]。
其二,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势力兴起。公元6世纪末,随着小农大量破产和外敌长驱直入帝国内地,拜占廷大土地贵族也几乎全部消失,以至到公元7世纪时,拜占廷不存在世袭大贵族。军区制的确立为新兴军事大地产和贵族势力的重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拜占廷统治的阶级基础是封建主阶级,国家统治集团依靠的主要阶级力量是大贵族。为了获得封建贵族的支持,拜占廷历代皇帝都在贵族中扶植亲信,委以重任。军区制的推行就使地方贵族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公元9世纪中期,在拜占廷文献中开始出现大贵族家族。他们以祖辈获得的封赐为基础,以大地产和军事权力的结合为特点。至公元10世纪,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即出现了一大批“权贵者”(Δυvατós),他们主要是由军队高级军官,如军区将军和中央高级官员构成,其官职和爵位均为世袭[①j]。这个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兴起必然在经济上侵害小农经济利益,构成对小农阶层的巨大威胁。
事实上,贵族的大土地经济具有比小农经济更优越的外在条件。拜占廷的直接劳动者基本上是农民,他们又因纳税的不同方式被称为国有小农和私有农民。国有农民在国有土地上耕作,受国家的直接控制,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其中相当大部分在公元7世纪以后即转化为军区制下的农兵。他们本应直接缴纳给国库的租税也随之转化为军役义务。而私有农民则在大地主土地上耕作,因此,大地主控制着私有农民的经济,并以各种手段将农民本应上缴国家的租税截流下来,只将其中很少一部分上缴朝廷。他们常常获取某种特权,逃避国家税收,从而将私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全部侵吞。同时,他们还掌握着军区内农兵的命运。在大地主千方百计扩大田产、增加私有农民数量、进而减少国家税收的同时,中央朝廷为维持原有的税收量,就必然加重对国有农民的剥削,导致小农经济因负担过重而难以维持,直至破产。在大地主和小农、大地产和小地产这两种经济势力的消长较量过程中,天平必然倾向前者。
从本质上看,大地产和小地产的矛盾是拜占廷社会的基本矛盾,大地主始终是以小地产为其兼并扩张的主要对象。虽然,由于小农负担国家主要赋税和兵役而使小农经济成为拜占廷帝国统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军区制下的小农经济仍然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特别是当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兴起之后,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即大大加速。大地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代价,将小农土地吞并,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制,使小农人身部分依附于大地主。公元10世纪以后的资料表明,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迅速沦为大地主的农奴[②j]。到11世纪,拜占廷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
以农兵为主体的拜占廷小农经济的瓦解过程是与军区制的解体过程同时发生的。军事贵族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廷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因此,公元9、10世纪的拜占廷皇帝们不断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以便加强控制。公元7世纪建立的全国6大军区至8、9世纪即分立出另外4个军区。到公元10世纪时,军区的数量达到25个,到11世纪时,上升为38个,仅在原亚美尼亚军区境内就分划出10个小军区[①k]。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这种分权措施实际上将军政权力重新分离,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②k]。至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军区”和“将军”等有关军区制的“名称从此几乎完全消失了”[③k]。
四
拜占廷军区制从其出现到瓦解共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军区制对拜占廷历史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④k]。
第一,军区制适应拜占廷对外战争频繁、边防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通过地方统治军事化,部分地解决了兵源和财源枯竭的困难,缓和了外族入侵的危机,为拜占廷军事力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公元7世纪,拜占廷军队击败波斯人,打垮阿瓦尔人,征服斯拉夫人,并将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大军扩张的势头阻止在小亚细亚和东地中海一线,使危如累卵的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这一系列军事上的成就不能不被认为是推行军区制的结果之一。不仅如此,以7世纪的胜利为基础,拜占廷军事力量得到调整和加强,因而,公元8、9世纪期间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获得多次重要胜利。拜占廷学者高度评价这些胜利,认为“保护欧洲免遭阿拉伯人侵略之主要屏障的荣誉无疑应归于拜占廷军队”[⑤k]。同时,拜占廷军队在防御斯拉夫人入侵和征服保加利亚人的长期战争中也屡屡获胜,并最终击垮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一些西方学者将公元7到11世纪拜占廷军队的多次胜利归功于某些皇帝,如尼基佛鲁斯三世(Nikephoros,963—969年)和瓦西里二世(Basil,976—1025年)的卓越军事才能,或归功于拜占廷军事艺术的改进,如步兵和骑兵混同作战等[⑥k]。这些意见均忽视了军区制为拜占廷军事力量复兴提供的制度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保证。
军区制衰败之后,拜占廷军队一厥不振,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罗斯人和诺曼人雇佣兵。为这些雇佣兵提供的军饷成为晚期拜占廷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在拜占廷境内肆意妄为。公元12世纪,诺曼人雇佣兵的反叛就给拜占廷中心地区的巴尔干半岛造成持续数十年的兵祸[①l]。至公元13世纪初,拜占廷几乎衰落到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的地步,因而在数千十字军骑士的攻击下,城防坚固的君士坦丁堡便轻易落入敌手。从此,拜占廷帝国就沦为东地中海的弱小国家,失去了昔日雄风,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直到灭亡。
第二,军区制的推行促使小农经济勃兴,国家税收增加,同时,军区制带来的安定局面又为以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的繁荣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小农经济是拜占廷国家的基础经济部门和税收主要来源,“小农在国家税收方面成为拜占廷帝国财政的脊柱”[②l]。学者们估计,拜占廷国家收入的95%来自于农业,仅5%来自于城市工商业[③l]。纵观拜占廷历史,国家年收入的数量时有起伏,但以军区制推广的几百年为收入最高的时期。早期拜占廷税收是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直到晚期拜占廷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征收的形式有所变化[④l]。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除定期缴纳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负担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军区制促进了小农生产率的提高,使他们有能力完纳捐税。在年景不利的时候,连保制也能帮助经营不善的农民度过难关[⑤l]。学者们估计,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政府财政年收入比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年收入高4倍以上,比晚期拜占廷年收入高40余倍[⑥l]。这里,我们还应考虑到拜占廷国土变迁的因素。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的收入来自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亚、非、欧各洲其他省区的广大疆域,而9、10世纪时拜占廷的年收入仅来自于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换言之,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在较小的领土上获得了较多的收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军区制对拜占廷农业经济产生的有利影响。
军区制的推行对拜占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小农经济的复兴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拜占廷农村与帝国境内大小城镇均保持密切联系,小农不仅从城镇市场上获得必需的手工业品,而且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农副产品。小农经济的复兴意味着城乡间更频繁的物质交流,同时也意味着工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军区制下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拜占廷工商业在8世纪以后趋于繁荣,城市发展更加迅速,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特拉比仲德等城市都名列中世纪欧洲最大城市之列。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其工商业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这座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金桥”充分发挥出它的地理优势,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在这里,百业俱兴,商贾云集。公元8世纪,“拜占廷商业经济史才真正开始”,“而9、10世纪,其商业活动处于鼎盛”[①m]。
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经济出现持续滑坡,财政危机不断,国库入不敷出。中央政府为维持税收总量,采取增加税收量和新税种等手段,加重对税户的剥削。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加速了晚期拜占廷经济的恶性循环。公元14世纪时,拜占廷年收入不足1万金币,仅相当于中期拜占廷年收入的2.18%。王室已无力举办任何庆典,甚至皇帝约翰五世(John Palaiologos,1341—1391年)的婚礼也不得不因陋就简、操办得十分寒酸。当时的史官记载,整个王宫“连金银杯盘都没有,一些杯盘是锡制的,其余的用陶土制成”,“婚礼上皇帝穿戴的衣帽礼服的服饰也仅有黄金宝石的样子,其实都是皮制的,或染上金色,或饰以彩色玻璃……到处可见类似具有天然魅力的宝石和绚丽多彩的珍珠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些都骗不过众人的眼睛”[②m]。
第三,军区制通过推行军役土地制和屯田稳定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使人口流动中的无组织状态得到控制,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政府便采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以稳定社会各阶层。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兵,农民的子孙必须从耕,并以取消隶农迁徙自由的方式将农民固着于土地[③m]。但是,这一政策并未奏效,破产的小农大量逃亡,或涌入城市寻求生路,或逃进山林结草为寇,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规模最大,几乎推翻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尼卡”起义就是以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为重要力量。类似的大规模起义和暴动在当时史不绝书。军区制通过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有地可种,有家可归,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一制度从解决小农生计和加强地方管理入手,重新调整拜占廷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拜占廷移民政策,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斯拉夫人各部落从多瑙河一线南下巴尔干半岛也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人口流动的话,那么,拜占廷政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便是将这种无组织的人口流动重新组织于军区中,并通过保留和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因势利导地化解了斯拉夫人大规模流动引起的社会问题。军区制不是以严酷的立法实现社会各阶层和居民职业的固定化,而是通过制度的创新,着重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生存环境问题,进而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区制瓦解之后,拜占廷社会再度出现人口流动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本国的小农破产逃亡,而且外国的移民,如土耳其人、诺曼人、瓦兰吉亚人等,也迁徙不定,在拜占廷境内造成兵匪横行的局面。而这一点也成为拜占廷最终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四,军区制的推行促进了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兴起,他们形成了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分裂势力,甚至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左右朝政或改朝换代。这是军区制对拜占廷政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大地主对小农土地的侵吞是小农经济衰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刺激了大土地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公元10世纪的拜占廷政治生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当时,一些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他们以小农保护者的形象出现,斥责大地主“像瘟疫和坏疳一样降临到不幸的村庄,吞食土地,侵入村庄的肌体,将它们逼近死亡的边缘”[①n]。公元922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所在公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还规定,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②n]。996年,拜占廷王朝再次颁布类似的法令。实际上,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然而,拜占廷统治者未能真正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大地主,一方面,皇帝们要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打击大军事贵族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主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他们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同归于尽。因此,上述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政府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
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就构成了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公元10世纪末,羽翼已丰的军事贵族就以小亚细亚军区为基地发动叛乱,其中又以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的“两瓦尔扎斯叛乱”影响最大[③n]。公元11世纪期间,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兵临首都城下,而且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此期,至少有五位皇帝是以哗变的方式爬上皇位的军事贵族[④n]。晚期拜占廷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Kantakouzenos,1347—1354年)左右朝政数十年,他曾以其雄厚的家资帮助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os,1328—1341年)在王朝内战中击败老皇帝,登上帝位。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他重金雇佣土耳其人,击败对手,自立为皇帝[①o]。显然,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对中央集权的削弱是晚期拜占廷内乱不断,最终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军区制是早期拜占廷经历长期动荡,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逐步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廷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而渐臻成熟的成功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当时内外形式的需要,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困境,因此,成为推行于全国的管理方式。特别重要的是,军区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军区制的发展也有助于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产生和兴起,因此,军区制从其形成之初自身内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廷统治者即要通过推行军区制有效地应付外敌入侵,就不能不依靠和重用军事贵族,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军区制的演化和军事贵族的努力发展,小农土地必遭吞并,小农经济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廷王朝越是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保证中央集权统治,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拜占廷统治者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廷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也促成了拜占廷国家的灭亡。
注释:
①a A.莫发特:《古典、拜占廷和文艺复兴研究》A.Moffatt,Classical,Byzantine and Renaissance Studies,堪培拉1984年版,第189—197页。
②a N.伊科诺米基斯:《“塞姆”词源》 N.Oikonomides,The Etymology of Theme,引自《拜占廷学会学刊》,总第16期,1975年,第5—6页。
①b君士坦丁七世:《论军区》 Constantino Porirogenito,De thematibus,由A.皮尔都西译注,梵蒂冈1952年版,第5页。
②bJ.H.汉佛雷:《汪达尔和拜占廷时期迦太基考古》J.H.Humphrey,The Archacology of Vandal and Byzantine Carthage,引自J.彼得利《古迦太基的新发现》J.Pedley,New Light of Ancient Carthage,安纳布尔1980年版,第85—120页。
③bR.A.马库斯:《拉文纳和罗马》 R.A.Markus,Revenna and Rome,引自《拜占廷》,总第51期,1981年,第566—578页。
④bA.贵卢:《公元七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地方主义和独立势力》A.Guillou,Regionalisme et independance dans l Empire byzantin au VIIe siecle,罗马1969年版,第2章。
⑤bI.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史》第2卷I.KαραΥlαυ υ óπουλοs,Iστορíατου Bυεαυτου Kρáτουs,萨洛尼卡1992年版,第20—35页。
⑥b雅尼:《教会史》帝国第1卷,由E.米勒译注,牛津1860年版,第3页。
①cI.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中期地图集》I.KαραΥταυυóπουλοS,X áρτατ μεοηs BυζαυτωηSΠερτóδου,萨洛尼卡1976年版,第9页。
②c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M.F.Hendy,Studies of The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A.C.300—1453,剑桥1985年版,第619—620页。
①d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2卷Theophanis,Chronographia,由C.伯尔译注,莱比锡1885年版,第89页。
②d亚美尼亚军区首脑官员年薪40金镑,而奥普西金军区将军年薪为30金镑,见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178—179页。
③dC.阿斯德拉哈等:《色雷斯的拜占廷铭文集》C.Asdracha and Ch.Bakirtzis,Inscriptionsbyzantines de Thrace,引自《迪尔森考古》第35期,1980年,第241—282页。
④dH.阿尔维勒:《拜占廷和海洋:7到15世纪拜占廷海战、政治和海洋法》 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nes de Byzanceaux VIIe-XVe,巴黎1966年版,第81—85、131—135页。
①e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3卷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牛津1964年版,第355页。
②eJ.哈尔顿:《拜占廷大区长》J.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波恩1984年版,第172、276页。
③e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182页。
④e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书》第2卷Constantin VII Porphyrogenete,Le livre des ceremonies,texte etabli et traduit,巴黎1935—1940年版,第494、696—697页。
⑤e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书》第1卷,第493页。另见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182页。
①f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620、626页。
②f每金镑等于72索里德,见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183页。
③f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377页,另见M.F.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619页。
①g阿加塞阿斯:《五卷本历史》 Agathias of Myrina,Historiarum Libri V,由R.盖伊代尔译注,柏林1976年版,第5章第13节。
②g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史》第1卷,第638—639页。另见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607—686页。
③g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619—623页。
④gS.仁西曼:《拜占廷文明》 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伦敦1959年版,第96页。
⑤g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2卷,第432页。
①h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史》,第292—294页。
②hG.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 G.Ostrogorsky,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State,牛津1956年版,第86页。
③h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史》,第396—402页。
④hG.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农民历史问题研究》 G.Ostrogorsky,Qeelques problemesd 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byzantine,布鲁塞尔1956年版,第三章。
①i雅尼斯:《编年史》ΙωáυυηS,χρουογραψíα,波恩1831年版,第417—420节。
②i《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剑桥1952年版,第208页。
③i《农业法》 The Farmer's Law,由W.阿什尔尼尔译注,引自《希腊研究学刊》总第32期,1912年,第68—95页。
④i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96页。
⑤i利奥:《法令》 ΑεουτοS Βαστλτκá,雅典1910年版,第11条,第2款。
⑥iI.泽波斯:《希腊罗马法》第2卷I.Zepos,Ius Graeco-Romanum,雅典1931年版,第209页。
①jI.泽波斯:《希腊罗马法》第1卷,第201页。
②j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农民历史问题研究》第四章。
①k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中期地图集》,第30页。
②kJ.菲尼:《瓦西里二世和军区制的衰败》 J.V.Fine,Basil II and the Declin of the Theme System,引自《斯拉夫拜占廷和中世纪欧洲研究》第1卷,索菲亚1989年版,第44—47页。
③k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第368页。
④k参见拙作《拜占廷军区制的主要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90年第6期,第61—66页。
⑤k柏尼斯等:《拜占廷》 N.Baynes and H.Moss,Byzantium,牛津1948年版,第303页。
⑥kC.W.奥曼:《战争艺术史》 C.W.Oman,The History of the Artof War,伦敦1898年版,第5章。
①lP.沃比:《东方的诺曼帝国,十一至十三世纪》 P.Aube,Les Bmpires nomands d'Orient,XI-XIIIe siecle,巴黎1983年版,第4、5章。
②l《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208页。
③l亨迪:《拜占廷货币经济史研究》,第157页。
④l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农民历史问题研究》第235章。
⑤l该项制度规定,荒芜农田的税金由其邻居和所在村社代缴,见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第87—99页。
⑥l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96页。另见格利高里《罗马史》第1卷DρηγóραS ρωμαlκη lστορíα,由L.索篷一世译注,波恩1892年版,第317页。
①m《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132页。另见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167页。
②m格利高里:《罗马史》第2卷,第788—789页。
③m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史》第1卷,第415—430页。
①n②n泽波斯:《希腊罗马法》第1卷,第210、233页。
③n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廷国家史》第2卷,第430—441页。
④n即提奥多拉(Theodora,1042年)、伊沙克一世(Isaac Komnenos,1057-1059年)、米哈利七世(Michael Doukas,1071-1078年)、尼基佛鲁斯三世(Nikephoros Botaneiates,1078-1081年)和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us Komnenos,1081-1118年)。
①o O.D.M.尼科尔:《拜占廷的坎塔库震努斯家族》 D.M.Nicol,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antakouzenos,华盛顿1968年版,第35—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