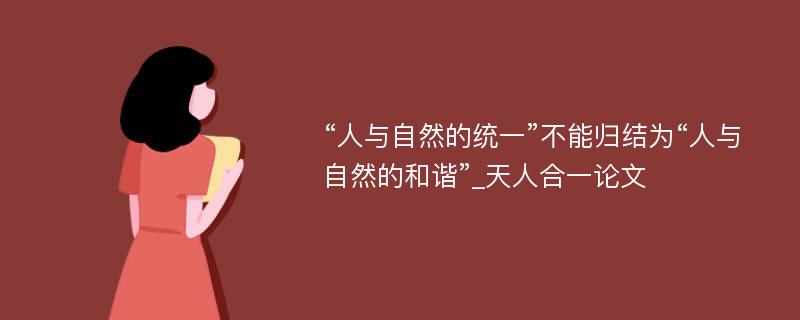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约为论文,人与论文,自然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伦理学”是在20世纪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其中的“深层生态伦理学”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归咎为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工具理性,希图重建一个以自然主义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模式。这些生态学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从东方古老的宗教文化中找到了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因而被称之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也借助这一契机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对话:在对话中,很多学者把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简单地归约为“天人合一”,有人甚至武断地认定“天人合一”就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学说”。笔者认为,这种论点过分拔高了传统文化的生态学价值,没有顾及中国传统天人哲学的真正内涵,也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现代生态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只是出于一种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而以情感的认同代替理性的思考,做时髦的迎合,故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难有所作为。
一、“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但对其内容却是见仁见智,并无定说。如果将天人合一思想核心确定为“合”、“和”或者“和谐”,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但如果将它说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或者“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则很难让人信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天”和“人”的理解以及对这一命题的个案分析。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或命题出现得很晚,是北宋哲学家张载首次提出的(如《正蒙·诚明》:“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在此以前,老庄、孔孟、荀子、《易传》、《中庸》、《吕氏春秋》、《黄帝内经》、董仲舒等都各有自己的天人观,如庄子的“与天为一”(《庄子·达生》:“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荀子的“天人之分”(《荀子·天论》:“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中庸》的“与天地参”,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等等。虽然人人都言天人,但内容却千变万化。现代学者之所以把“天人合一”总结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因为传统哲学大多涉及“天”与“人”的关系,而这些观点或理论的基本走向就是“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为二”。不过,传统的“天”既包括了自然之天,也包括了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义理之天,其内涵因人因时而异,因而需要区别对待。与此相对的“人”的涵义虽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但也有单个的人、整体的人的区别,有时则指“圣人”。至于天人合一中的天人关系,则更需要根据个案来分析,不能把“合一”两字大而化之地处理为“合而为一”。
从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开始,到宋代的理学家王阳明,包括道家、儒家和禅宗,在每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几乎都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天人观:他们之间有继承、有并列,也有创新,关系错综复杂。这里仅根据其主要论点,作大致的归纳。
1.天人相类,或天人相副、天人同构。此论认为人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复制出来的,所以人副天数,结构相同。以《黄帝内经》、董仲舒为代表。《黄帝内经》以人为“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故“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素问·宝命全形论》)等等。这个理论在董仲舒那里更为系统繁复。董仲舒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人和天是同类。“人之体形,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同上)因为同类,所以形体和精神同构。由此又可以推出天人相副:“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所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云云。
2.天人一体。天人一体比天人相类逻辑上更进一步。天人一体,故同质;同质则源于同气;同气相求,故同类相感。这主要是阴阳家的理论,后融入各家中。《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吕氏春秋》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又云:“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吕氏春秋·制乐》)。董仲舒则推而广之:“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又云:“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幷见”(《春秋繁露·王道》)。这就是“天人感应”说中典型的祥瑞说和灾异说。
3.天人同性,即天地之性亦人之性,尽性则可以知天。这一观点由儒家思孟学派提出,被理学家张载发扬光大,是儒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中庸》的“至诚”和《孟子》的“尽心”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修性”。张载明确地指出“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横渠易说·系辞上》)。而圣人可以以一己之善性体万物之共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西铭》),将仁爱理想推及宇宙万物。
4.天人同理,“天道”即“人道”。此论以老子开其端,理学集大成,是中国传统天人观的基本内容。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儒家甚至认为礼乐亦本于天地之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礼记·礼运》)宋代的理学家以“理”为“道”,从本体意义上论证人伦源于“天理”、“人道”即“天理”。有关材料颇多,此不赘述。
由于中国传统天人学说流派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交叉性,如果仅作论点的列举和引证难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因此,从价值取向角度思考也许更具说服力。以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来说,佛教属于印度传统,它把宇宙生命归纳为“六道轮回”,“天”和“人”不过是“众生”中的两“道”而已,故不涉及天人合一的问题;只有本土的儒、道两家才以天人问题为哲学话题。在价值倾向上,儒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政治性和伦理性的,所以儒家把天作为“神灵之天”、“道行之天”和“义理之天”来看待;道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境界论上的,所以道家的天多含“自然之天”的内容。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区分,有时也难免彼此混同,因为各派学说有融合的关系,如先秦老庄和魏晋玄学也含政治性的因素,先秦思孟学派的“尽性知天”也是境界性的。至于宋明理学,吸收了道家和禅宗的本体论和修养论,其天人学说最后走向了境界论。
这里有必要提到道教。道教是当代西方生态学家最为推崇的“自然主义”的宗教,其理想就是“天人合一”,但内容却“杂而多端”。以外丹而言,东汉方士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里以“模拟自然”的方式,借周易中的卦爻之象,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法,配以阴阳五行昏旦时辰等火候,论述了炼丹的基本原理。晋代的葛洪通过“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理论,证明服食金丹可以“长生不老”(《抱朴子·内篇》)。唐代一些炼丹家还用天文学的一些术语附会炼丹的名称,用老子“法天象地”的原理以“天地不朽”来实现肉体生命的不朽。另外,道教符箓派中常有道士通过斋戒“存神”与诸天神兵将感应的仪式,其理论源头是“天人同气”和“同气相感”。陶弘景的解释是:“太清之气,感化无方……各相接引,不徒然空立。可以理得,难用言详。其仙灵将官,皆此类也。”(《登真隐诀》卷三,第22页)从这里看出,道教的天人合一论既是自然主义的,又是泛神论的。到了宋元之际,道教内丹学盛行,在理论上主要吸收道家哲学、易学、阴阳家和佛教禅宗的思想成分,以人体为“丹鼎”,以精气神为“药物”,配以方位、火候诸说,变成了一种以境界论为主,杂以自然论、泛神论、道德论等的多极化的天人理论。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同时,它们又综贯着一条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天”的绝对性和权威性。中国传统由于缺乏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所以中国的“天”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上帝的功能,成为人类的生活理想和精神之源。因而中国的天人合一也就始终保持着一种宗教式的情结,即所谓敬天意识、顺天意识、法天意识和同天意识。“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即是敬天意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即是顺天意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法天意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是同天意识。这些意识均基于天的不可逾越的权威和无与伦比的神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带有“媚神求福”的色彩,它所反映的是小农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是生产力低下时祈求“风雨时至”、畏惧“过则为菑”的心理;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参见蔡仲德)。
另外,中国哲学家论天道均不是目的,其落脚点必是人道,所谓“善言天者,必应于人”(《素问·气交变大论》)。所以,中国哲学的重心是人生。冯友兰有鉴于此,而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可谓得其精髓。由此而论,天人合一尽管保持着一种对天的宗教式的情结,但其核心内容则是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生活的终极根源。虽然天人合一的理论也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政治、伦理和精神境界为本位的,因而,天人合一的核心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哲学理论。
二、“天人合一”与西方深层生态伦理学的接轨及其误读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把“天人合一”融入生态学理论的首先是西方的一部分生态学家,中国学者不过是步其后尘而已。20世纪以来,在反思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过程中,西方一些学者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仅仅致力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技术控制等方面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人与自然的危机首先是文化的危机,因此,只有实现全人类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的全面变革,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希望。这是现代西方自然保护主义的“深层生态学”的基本思路。在这场反思中,有关学者对西方固有的传统观念作了深入的批判,帕斯莫尔(Passmore)、卡莱考特(Callicott)、 怀特(White)、海德格尔(Heidegger)、怀特海(Whitehead)、纳什(Nash)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其中,当代著名的深层生态学家纳什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总结,他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和科学思想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参见纳什,第38页)
深层生态伦理学者认识到,要突破西方文化传统的禁锢,必须借助于外部的文化权威。他们发现,东方文化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迥异于西方传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有着主客混融的、整体的、有机的、人性化的特点;东方的道教、佛教、印度教甚至儒家文化中都蕴含生态智慧,因而视这些东方传统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古代先驱,或称之为“传统的东亚深层生态学”。(Callicott,p.87)
其实,在这场可称之为“东方生态伦理学的发现”中,西方生态学家所关注的是那些与他们所构想的新型生态伦理有关的思想资源,而并没有刻意对中国的传统生态思想作总结归纳。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对“天人合一”的“拿来主义”的理解,恰恰是字面性的,并没有去追究“天人合一”的原初含义。生态伦理学家德维尔(Devall)和赛辛斯(Sessions)认为,“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是东方整体的自然观的表现,是对西方主客二元论的反叛,可比之于普利高津的自发的自组织系统。(参见普利高津,序言)又如在纳什那里,道家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的意思被解释为“万物中的每一物都拥有某种目的、某种潜能,都对宇宙拥有某种意义”,于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物学鸿沟和道德鸿沟都荡然无存”(纳什,第136页)。诸如此类的解释多是“格义”① 式的方法:只是字面相对应,内容上却出入很大。另外,也不难看到,这些学者在很多场合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理解东方思想的:他们在用现代生态主义的立场“发掘”东方的智慧时,将东方文化中那些古老思想的潜在意义迅速“升格”为现代性的观念,而实际上那些思想未必是古人的本意,像主客混融、整体观、有机观,像“自组织系统”、“人与大自然的生物学鸿沟”等现代学科所使用的词汇,这些显然是从阐释学的层面来表达的。因此,我们虽然不难理解西方学者的思维进路,但我们也不敢贸然肯定他们真正地读懂了“天人合一”、读懂了《庄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将此类解释看成一种文字或文化的“嫁接”甚至“误读”也未尝不可。
遗憾的是,我国近年来关于“天人合一”的大量文章和著作正是接过西方生态学家的话题而发挥的。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只能算作是一个泊来词,其蕴含的词义仅仅限于深层生态伦理学的范围,而非中国固有的天人思想。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所涵盖的思想资源比现代生态学的意义大得多、宽得多、也复杂得多,故如果简单地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明显是一种带有实用目的的归约式处理,不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在宣扬文化的虚无主义,也不是否认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生态智慧。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可以通过语义的创造性转化而获得现代性的意义。这里只是要强调,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应该立足于其思想的历史基础,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意发挥。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问题。很多学者其实很清楚中国传统的天人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实用目的而迎合时尚。迎合时尚乃学术之大忌,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记得在20年前的中国哲学界,还是以“天人相分”为时尚,荀子的“人定胜天”和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被作为“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可是今天西方的生态伦理学传来,人们却迅速找到了新一轮的学术“热点”,“天人合一”一时走俏:人们几乎是“谈分色变”,“合一”就好,把严肃的学术问题当作了政治和商业的工具。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环境问题与现代世界性的环境生态危机性质大不相同。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由于人口数量不多、生产能力有限,环境破坏只是局部性的,这同现代世界性的人口爆炸、工业污染、物种灭绝、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等等环境问题相比不可以道里计。在西方工业革命前,世界几大文明区实际上都是以“绿色文明”为标志的:不独中国如此,希腊、印度、非洲、美洲等地亦然。中国古代有保护动物和生态的具体措施,但因为生态问题不严重而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环境保护只是被视为王者“仁政”的一部分,即如晋代的儒者何承天所说:“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行火俟风暴,畋渔候豺獭,所以顺天时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数罟,行苇作歌,霄鱼垂化,所以爱人用也;庖厨不迩,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钓不纲,所以明仁道也。”(《达性论》,《弘明集》卷四)在环境问题尚未危及人类生存的传统社会,中国的环境保护思想主要停留在这种儒家的仁爱理想的层面,而作为在野的道家,其“自然主义”更是境界性的,充满着理想色彩。
今天的全球性环境生态问题已经威慑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国起作用的生态学理论实际上还是所谓的“浅层生态学”,强调的是通过技术、法律和制度的改良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很多此类措施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当前欧美很多发达国家的生态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观,西方的主流意识却并未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批判主义思潮之一的深层生态伦理学说只是在野的少数派,未能成为当今解决环境问题的主流意识。在以强调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的事情是“向西方看齐”,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有意无意地转移环境成本,使得这些国家也不可能立即摆脱科学主义的羁绊而越位进入“以自然为中心”的后现代发展模式。所以,从现实性来看,西方的深层生态学还只是一种遥远的后现代主义理想,其操作性到底有多大还未有定论。另外还应该看到,现代环境及生态问题是一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故仅仅将其归咎为某种文化意识如科学理性或主客二分是片面的。总之,过高地估价深层生态伦理学进而否定西方主流文化传统,认定“未来的世界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似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缺乏辩证的和多元的文化发展观念。
注释:
① “格义”是早期中国僧人和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一种方法,即用中国本有的《老》、《庄》、《易》上的词汇配拟外来的佛经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