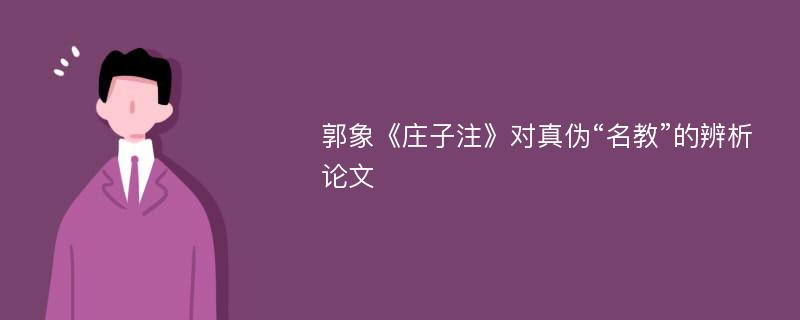
[庄子·道家·道教研究]
[主持人按语]
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中,两篇涉及道教、一篇涉及儒家名教。如果说道教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神学化的结果,其终极关切是成仙永生,那么,郭象通过诠释《庄子》而为儒家的价值观念所作的辩护,则是道家思想名教化的产物。从原初的老庄之学到道教以及郭象对《庄子》的精彩诠释,固然体现了道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元性,但这种丰富性和多元性的历史开展,实质上却是以背弃老庄这两位道家先哲的思想本旨为“代价”的。
先来看老子。不错,《老子》第59章确曾言及“长生久视之道”,但须知其所谓“长生”并非永远不死的“永生”,而应被理解为长寿。另据台湾学者杜正胜研究(《从眉寿到长生——中国古代生命观念的转变》),后世语汇中的“‘长生’往往表示‘神仙不死’,此义却为春秋以前所无”,而“不死的奢望”则当是战国以后接着春秋时代之“永保其身”和“难老”“毋死”等观念逐渐发展出来的。第33章云“死而不亡者寿”,可见老子并不以不死为寿。至于老子对儒家名教的态度,即便第19章“绝仁弃义”云云或为后出,第38章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段,也已把他对名教的批评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
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四个最严”为统领,落实“四有两责”,切实履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职能,落实“控、防、打、建”一体化要求,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再看庄子。如王船山所言,在生死问题上,庄子的真正态度是:“‘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言无暇也,非以生不可悦、死不可恶为宗,尤非以悦死恶生为宗。”(《庄子解·至乐》)推而言之,庄子既不悦生又不恶死,他只是无暇无心于此而已,故《天下》篇说他“外死生、无终始”,故《至乐》篇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相较于老子,庄子对名教的批评更为激愤深刻:从人性自然的角度说,儒家的名教乃是“落马首,穿牛鼻”“以人灭天”而至于使人丧其本真的枷锁;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按庄子“盗亦有道”的逻辑,名教实为“盗之道”,只会被窃国者用以“守其盗贼之身”,故《盗跖》篇甚至痛斥孔子为“盗丘”。
后世多有道教徒和以儒解老、以儒解庄之徒自许为得老庄之真者。不过,我想假如某一天老庄与这些家伙在路上遇着了,结果一定是“纵使相逢应不识”,老庄对他们大概也只会说两个字:讨厌!
邓联合
2019年9月25日
(邓联合,1969年生,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道家哲学研究。)
郭象《庄子注》对真伪“名教”的辨析
廉 天 娇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郭象《庄子注》对“名教”的辨析,主要基于其自然观,合乎自然的即是“真名教”,背离自然的即是“伪名教”。他的“名教”思想也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名教”与“自然”结合的理论旨归,最终在于塑造理想的圣人人格。在现实中,发挥合乎自然的名教的真正功用和价值,最终实现个体精神的独立自由。
关键词: 郭象;《庄子注》;名教;自然
一、郭象“名教”观提出的背景
“名教”这一概念,原本是出自儒家,主要含义是“名分、教化”。孔子最早提出的“正名”,《论语·子路第十三》:“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134这里的“名”指的就是“名分”,“名分”是包含了尊卑、长幼等人伦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规范,如三纲五常,进而引申为一般的社会秩序及与之相应的礼仪规范。此外,汤用彤还说,“对于人物的评论,叫作‘名论’,又叫作‘名目’,所有政治上施设,都系于职官名分的适宜,人物名目的得当,这是致太平的基础,此与礼乐等总称之曰‘名教’”[2]102。因此,在魏晋之前的“名教”更多涉及儒家推崇的道德准则。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4]85-86
“真名教”即是合乎自然的名教。他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名教合乎自然:其一是名教自然而然的产生,其二是名教当中的人伦秩序也是自然产生,其三是名教出于人的“自性”。
同时,儒家贵名教,道家重自然,所以对名教与自然的选择,也是对儒道两家思想的选择,继而才产生儒道是否会通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玄学家们为了克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把时代政治问题,转化成名教与自然的玄学问题。“名教与自然”这对范畴反映了人们在现实与理想中的困难抉择,反映在哲学层面,蕴涵着必然与自由、实然与应然等深刻的哲学内涵,本身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人们只有着眼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才能找到一条摆脱苦难的出路。郭象对“名教”与“自然”内在统一性的诠释,正是为这一困境寻找出路。郭象《庄子注》对“名教”的辨析,是基于其自然观形成的。他的“自然观”从宏观宇宙层面,揭示“不为自然”的万物生成状态,再推及到个体事物在宇宙苍穹之下的自生,最后遍及到各个事物之间自性的不同,皆用“自然”一以贯之。这样世间的一切发生和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不禁思考,为何所谓的名教会役使人们,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工具呢?郭象眼中的名教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吗?名教与自然是否真的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就像竹林名士号召的那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后,如何才能使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呢?抑或是名教与自然本来就具有统一性呢?接下来对于“名教”的真伪以及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阐述。
二、郭象对真伪“名教”的诠释
郭象在《庄子注》中并没有像嵇康那样,明确提出包含有“名教”二字的话语,但是根据“名教”的定义,可以看到郭象在注中的确谈到不少关于礼乐、君臣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内容。不过,郭象所说的“名教”,实际上存在真假名教之分。当然,这并非就文本考据来谈真假,而是依据其思想义理来说。郭象认为,“名教”真伪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合乎自然。其对真伪名教的辨析,旨在为“名教”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提供理论依据。
(一)合乎自然的“真名教”
选择2016年3月—2017年2月入科且无中心静脉穿刺经验的进修医生40名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20名,对照组20名。实验组中,男性12名,女性8名,年龄24~32岁;对照组中,男性13名,女性7名,年龄25~34岁。实验组和对照组进修医生中心静脉穿刺相关理论基础知识摸底考核平均成绩分别为(62.7±10.1)分、(63.3±9.8)分。
其一,郭象的“自然”观包含有“无为、不为、自为”等方面的意思,但在某种意义上,郭象也认为“人为”也是“自然”。譬如,他在《大宗师注》中说:“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4[124]这就是说,郭象不仅把“天然”看成“自然”,而且认为“人为”也是“自然”。为何“人为”也能够成为自然?这就对应郭象“万物自生”的观点,“自生”是“非我生”“非他生”“非有因”“非有故”的,万物皆是自然而然生成。因此,在他看来,名教亦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非人们为了私利随意制定的结果。他在《知北游注》中说:“物有际,故每相与不能冥然,真所谓际者也。不际者,虽有物物之名,直名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无物也,际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则为之者谁乎哉?皆忽然而自尔也。”[4]401这就是说,物的“名”皆是物之本身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而不是“物物者”所赋予的。没有“物物者”,物不能“自物”,都是“忽然而自尔”的,这样名教也是“合乎自然”产生。
其二,郭象进一步说,名教当中的君臣关系等人伦之道,也是自然的,“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4]30。这说明,君臣上下的名教政治、手足之间的亲疏远近是自然生成的社会秩序规范,如此的自然秩序乃是天理,绝非是某人人为设立的结果。并且郭象在解释《大宗师》中的“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时,注曰:“刑者,治之体,非我为。礼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知者,时之动,非我唱。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4]131同样是说明,刑、礼、知、德这些礼法名教皆是为了满足人们自身本性的需求而自然而然产生的,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礼是国家自行运转的结果,知是时世发展的必然之事,德是万物之情的自然流露,都不是有某个主体来制定和创作的。从第一个论点上来说,名教也是自然。
庄子指出天下的两大戒,命和义:子爱亲的天命以及臣事君的义务。但是庄子却从这些责任义务中看到了异化现象,郭象也注曰“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这样的条条框框只会限制人,不仅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丧失自由,而且还会被专制主义的君主利用,变成了统治压迫百姓的工具。在这样的礼法名教束缚下,如果人们承担这些责任义务,势必要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于是庄子和郭象,同样都希望克服名教异化的现象,逃离“假名教”的桎梏,找到一种内圣外王之道,把自然与名教结合起来。
(二)背离现实的“伪名教”
“伪名教”指的是自汉末以来在现实生活中被严重异化而违反自然的名教。对于“名教”抨击最强烈的当属竹林玄学时期的阮籍、嵇康,尤其阮籍视假名教为“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所以才号召“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要超越的只是被异化的名教。杨立华在分析阮籍、嵇康对儒家传统态度发生巨大转变时说:“嵇康等人在高平陵事变以后所批评的和反对的儒家,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家传统,而是被以司马氏为核心的政治利益群体拿来当作‘意识形态’所谓的儒家。”[5]26由此可以看出,竹林名士们只是打着老庄的旗号,来反抗司马氏家族倡导的礼教,但是他们内心仍然渴望建立与自然相结合的名教。
对方是一个女人,声音虽然也甜,但显得猛,反问她:你是谁?皇甫一兰一愣,心想她打电话给我却问我是谁,打错了吧。皇甫一兰毕竟是淑女,有教养,再加上在服务行业工作训练有素,于是礼貌而客气地说:我是皇甫一兰。对方阴冷的声音似乎从牙缝挤进了她的耳鼓:我说你是婊子、骚狐狸、害人精,声音这么嗲,难道就是为了勾男人魂、喝男人血、吸男人精,让男人包二奶、养小三的?你这个人人可上的公交车,省省吧,叫你男人把你的责任田种好就行了,别再像大集体时大伙都能耕种几镢头。啪!手机挂了。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将明世所无由识,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处子者,不以外伤内。[4]15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黑暗,“名教”成了约束人们的枷锁,所以,魏晋玄学发展过程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正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名教本于自然”;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元康玄学时期,以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对于这一演变过程,其动因究竟是什么?名教与自然真的冲突吗?为何一定要在名教与自然之间作一个选择?余敦康说:“哲学与政治虽然关系密切,却不是某个政治集团的狭隘的传声筒,力求反映时代精神,着重从普遍的利益的高度对现实政治进行全面的调整。”[3]316竹林名士们对现实名教的不满,是由于魏晋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幌子,把名教变成压迫民众的政治工具,这里的名教并不是真的名教,而是被异化的“假名教”。人们不得已在名教与自然之间作出选择。
经过医生的检查,有的宝宝的只是小脚丫脂肪较多,看起来像扁平足而非真正的扁平足,那妈妈们大可放心。很多小脚平时显得是“平足”,不过当小朋友翘起脚跟站立是,你就会发现足弓出现了。
其三,郭象为了论证名教的合理性,认为名教是遵循人性需要的一种必然,并把礼法名教视作是“性”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结果,“所谓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4]174(《骈拇注》)以及“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赏罚而九,此自然先后之序也。治道先明天,不为弃赏罚也,但当不失其先后之序耳”[4]257(《天道注》)。郭象认为,仁义就是人的自然情性,君臣地位的尊卑,先后次序,也和天尊地卑一样的道理,天之高,地之卑,这些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内在原因是各自的“性分”不同所定的。所以,在现实世界中,遵循人伦规范和社会秩序就是遵循自然之性。由此,郭象将仁义等道德规范内化为每个个体内在的情性,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了。
三、“名教即自然”的理论旨归
郭象的“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玄学体系是熔传统儒家的名教与道家老庄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为了能够将“名教”与“自然”真正结合起来,使人们相信“名教”就是“自然”,“庙堂”就是“山林”,真正的“外王”必然也是“内圣”,因而他塑造出“游外冥内”“内圣外王”的圣人人格。郭象在肩吾问于连叔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段,注曰:
那道白光如天空中滑落的电,挂着尖锐的破空声,准确地插入了土狼王张开的大口中。他听到土狼王的筋肉在白光的冲击和挤压下,传出败革一般的“扑扑”声,又听到包裹在筋肉内的骨头,在与白光的碰撞和摩擦中,发出“咔咔”的碎裂声。然后,白光停在了土狼王的体内。
如果齿轮在啮合点处存在轴向力,力作用线平行于轴中心线,但与轴线间存在偏心距,此时,轴向力会产生一个偏心力矩,从而会引起C截面产生附加挠度。偏心力矩作用下悬臂梁弯曲示意图如图8所示。
郭象《庄子序》用一句话概括了“名教即自然”的结论,即“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神器”代表的是国家政治,即名教。“玄冥之境”是万物在没有外界干扰情况下,通过自为而相因达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想境界,也代指自然。大致说来,郭象在《庄子注》中,围绕着“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这条主线,为“名教即自然”找到其理论归宿——即塑造圣人的理想人格。
5、由于进埔站#1、#2、#3接地变和#1、#2站用变保护装置都是使用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的ISA-351F型分散式微机保护测控装置(以下简称351F),为了避免同类型设备产生同类问题,以及装置定值整定错误或二次接线错误的情况出现,故对#3接地变和#1、#2站用变保护装置及公共测控屏II上的二次回路进行检查。结果发现:#3接地变、#1、#2站用变都有告警信号发出,而没有上送后台机和集控监控机。
郭象也看到了现实当中的“伪名教”的弊端,所以他在为《庄子》作注时,也赞同庄子说的,那些只注重形式,而没有内涵的仁义礼乐形式,实质是本性扭曲的产物。他在解释 《庄子·马蹄》中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时,注曰:“凡此皆变朴为华,弃本崇末,于其天素有残废矣。世虽贵之,非其贵也。”[4]185这与老子说的“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意思较为接近。但是老子那时候的“礼”已经是“礼崩乐坏”了,徒有礼的形式,而没有内容,甚至背离人的本性,这与西周时期创立之初的“周礼”并不相同。所以庄子的思想也是与老子一致的。那么郭象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也是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认为司马家族所尊奉的“仁义礼乐”无非是“变朴为华,弃本崇末”,是残害自然天性的,且导致诸多弊病。因此,不能固守这样的“伪名教”,它会导致道德虚伪,徒饰外表,而无实质内涵,约束人性。《田子方注》中有“礼义之弊,有斯饰也”的说法,如果刻意标榜仁义,反而会扰乱社会局面。撇开《庄子注》不说,单看《庄子》里面的内容,似乎能够发现庄子和郭象都面临相同的困境,即礼法名教的异化,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但仅仅否定“仁义礼乐”就行了吗?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吗?其实行不通的,所以面对背离现实的“伪名教”不在于否定,而是寻找出路,理想合乎现实。譬如庄子的《人间世》中有一段关于仲尼的话:
“神人”出自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王晓毅在《郭象评传》一书中,曾对“神人”概念作了说明:“神人不是指有特异神通的神仙,而是生活在最高境界,通晓宇宙奥妙,却以无心态度顺应自然的顶级人物。”[6]297郭象在《逍遥游注》里提到的圣人,也能无心以顺物:“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穷万物之妙数,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磅礴万物,无物不然。”[4]17王晓毅对郭象的“圣人”观进一步解释,圣人的本质就是“神人”,它只是“神人”众多名称之中的一种而已,名称不同,代表了“神人”在不同领域的活动行迹。“圣人”的活动领域就是政治方面,具有最高政治智慧和洞察力的君王才是圣人。尤其这样的杰出君王,多指儒家所称颂的“尧舜文武”。“尧舜者,世事之名耳。为名,非名也。故夫尧舜者,岂直尧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实焉。今所称尧舜者,徒名其尘垢秕糠耳。”[4]17 既然“圣人”也是“神人”,那么“外王”即是“内圣”。《庄子·大宗师》里有关于“游外游内”的说法“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 郭象注解时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宏)〔冥〕内,无心以顺有。”[4]147内圣外王之道的关键就在于“内外相冥”,只有无措于心,顺物之自然,才能“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如果心为物所累,就会“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所以郭象说,《庄子》全书的大意就在于“游外(弘)〔冥〕内之道坦然自明”。“游外弘内”的最终目的是将“内圣”与“外王”合二为一,以消除自然与名教的分离,印证出世间、即世间之理。
总之,郭象既赞同庄子的神人,又提倡儒家的圣人,将两种理想人格结合起来提出了“兼综儒道的圣人”这样的人格模式。圣人是将道德品质和自然之性结合起来,虽然身居庙堂,日理万机,但仍旧心系山林,大隐隐于市,具有旷达情怀,这样入世何尝不是出世呢?郭象成功地将儒家的入世思想以及道家的超越思想,第一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对理想人格的阐述,也达到了名教与自然的结合。圣人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无论君王或者平民,都可以塑造完满的人格。此外,郭象尝试要在现实中发挥“名教”应有的功能和价值。至于如何重建既不脱离社会现实,而又顺应时代变化且合乎人性自然的礼法名教,就成为郭象致思的重点。“名教”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才能在现实社会发挥应有之义。
四、“名教即自然”的真正功用
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内在统一性的思想,最终目的不是消除名教,而是建构一套合乎人之自然本性的理想的“名教”秩序,以此发挥合乎自然的名教真正的功用与价值,从而为个人身心的安顿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提供一定的条件与基础。
真正的名教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且是出于人的“自然情性”的,就像代表名教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既是起源于人之自然情性的需要,也出于人之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正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221(《孟子·公孙丑上》),名教原本出于人的真实性情,郭象在《大宗师注》里谈到“仁义”时说:“仁者,兼爱之迹;义者,成物之功。爱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义,义功见焉。存夫仁义,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犹未玄达也。”[4]155仁义仁爱皆是无心,自然而然流露,如果刻意去记住的话,反而不能无心顺物。因此,郭象主张要任其自然之性,“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尔极,而天下无患矣”[4]206,任其自然之性,能解决“天下无患”,如果“反其性而凌之则乱”。 所以,郭象不是将“名教”之外在礼仪道德强行纳入自然人性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而是从“名教”必须要符合自然人性,并且要任其自然之性的角度,来寻找二者的契合点,从而有效发挥名教的作用。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创新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才是企业创新的基本要素,企业高管则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源。激励企业高管创新意识,有助于引领企业人才进行科学创新,让企业在激励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现代企业普遍采用薪酬激励方式激励企业技术创新。高管薪酬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的学者中尚未达成一致。
此外,郭象还试图通过君臣民的关系来说明“名教”所起的作用。他在《天道注》里说:“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4]252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就好比工人、斧头、刻木,工人的主要职责是使用斧头,而斧头的用处就是刻木。对比地看,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臣子的职责是管理百姓,各司其任,将整个国家社会管理井然有序,每个人在不同的职位发挥自己的作用,各当其能。郭象还说:“天下何所不(无)为哉!故主上不为冢宰之〔所〕任,则伊吕静而司尹矣;冢宰不为百官之所执,则百官静而御事矣;百官不为万民之所务,则万民静而安其业矣;万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则天下之彼我静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为而成哉?是故弥无为而弥尊也。”[4]249还有,郭象在《在宥注》中说:“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4]203以上皆说明,冢宰、百官、万民要各安其位,互不相扰,做到“人安其分,将力受任”。这些都是天理自然的,从皇帝到庶人,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君主不能取代臣子,臣子也不能僭越君主。如此看来,名教的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哪里还会被异化?所以,郭象的“名教”并不是纯粹为司马氏集团统治作辩护的工具,相反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观点,引发人们对“名教”的内在实质的重视,这样才能以符合自然人性的“名教”,去矫正现实中早已失去精神实质的工具化的“伪名教”,从而使名教的功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总之,“名教即自然”意在调和当时社会礼法名教与人们追求自由的心态的矛盾,在郭象这里,“名教”不脱离自然,个体的外在道德规范中,也透露着内在的自然情。魏晋之际的社会状况,是统治者打着名教的幌子,欺世盗名,致使社会混乱。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实际上是希望名教能脱离现实的枷锁,恢复到合乎自然的状态,从而使国家政治施行时,能以具体时势和人性的需求为切入点。
五、结语
郭象的“名教”观,是基于其自然观建立起来的。“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属于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范畴,更重要的是与现实的契合。郭象《庄子注》中“名教与自然”内在统一性诠释,既阐明了“自然”蕴含在一切事物之中,又进一步论证了“名教”存在的合理性,使“名教与自然”真正意义上实现结合,也使儒家、道家在魏晋时期会通融合;他既继承了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又将道家思想的“无为”“自然”等思想巧妙地融入其中,所以在郭象的玄学体系中,名教即是自然,自然亦是名教。此外,郭象的“名教与自然”观涉及的一些命题,如“天理”“性”“命”为宋代理学家所继承,并成为理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因此对宋明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王晓毅.郭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收稿日期: 2019-08-23
作者简介: 廉天娇(1992—),女,河南沁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道家哲学、儒家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600(2019)11-0001-05
【责任编辑:郭德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