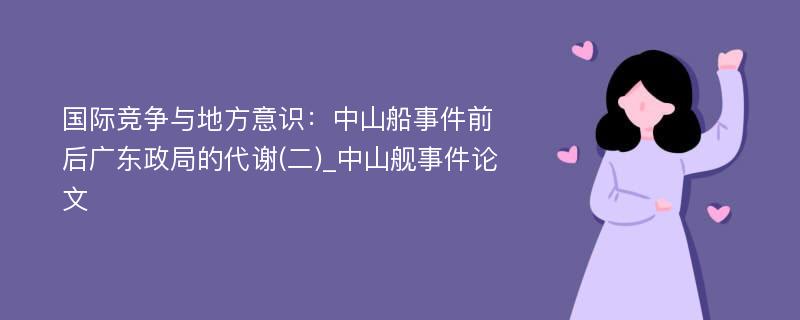
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广东论文,新陈代谢论文,国际竞争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中山舰事件后的广州政局
3月20日事件过程各家叙述已详,此不赘。当时上海各报对事件的认识进程却值得关注:《申报》到3月30日(据3月23日港讯)仍说事件乃李之龙试图组织工人政府失败,(注:《广州政局急变之内幕》(3月23日港讯),《申报》1926年3月30日,第9版。)次日发表毅庐发自3月21、23、25日三封长篇通信,算是了解到事件乃是“民党左派分裂”,蒋介石转变了信任共产派态度,依靠左派打击极左派。(注:《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毅庐3月21、23、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版。按毅庐明确了李之龙是在睡梦中被捕,可知消息来源相当可靠。)《时报》之报道则仍说何应钦和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并联络李济深、朱培德、谭延闿等欲采取行动,蒋为其所迫,乃派兵搜索各右派要人住宅。但因党军中本有两派,出发后各派均借机搜捕对方(故实际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左派和苏俄顾问的行动皆被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矫令行事),及搜得之文件表明左派将在北伐开始后发动政变夺权,“蒋氏察悉共派阴谋,态度复立变”而转为反共。(注: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报刊载关于中山舰事件之内容甚众,独此一篇被全文收入台北“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第247-249页)之中。按此文所说党军各部矫令行事也非全然无据,蒋介石自己就承认,“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这些本非“事实真相”的叙述说明,对一般外人而言,要接受一贯亲俄左倾的蒋介石突然反共,实在相当困难,故不得不努力搜集各方传言,以圆其说。
事稍平息后,3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这是一个妥协的决定,最后查办“不规军官”一条至少部分是针对包围苏俄顾问团等行动,它既可为逮捕李之龙的行为正名,也为后来逮捕欧阳格埋下了伏笔。(注:两人后均释放也说明中山舰事件偶发的可能性甚大,即使真有“阴谋”或“预谋”,不论出自哪一方,应都不在海军和中山舰这一层次。)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蒋介石的一贯态度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应尽可能妥协,(注:蒋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就对孙中山进言:“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见《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236页。尤其黄埔系统内左右双方都是他借以兴起的部下,俱难轻易舍弃。蒋在3月21日即觉“人才缺乏,实无改造一切之工具,孤苦伶仃,至于此极,可堪痛心”。二十天后,他仍感“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因为这牵涉到“以后政治方针究应如何决定”。但蒋也认识到,自3月20日的行动后,“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焉。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这应是发自内心的老实话。团体己分裂的现实迫使蒋不得不在二者中选择依靠其一,鲍罗廷以为,蒋在采取了3月20日行动后就“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这一观察大致接近真相。(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4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9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按蒋介石稍后对汪精卫说,黄埔出身之军官对共产党行为固多不满意,“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拆]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其自杀也”。(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041,卷号85)这话在那时不能认为是虚伪,蒋确实希望黄埔学生能超越于国共之上,以收鱼与熊掌兼得之效,他后来要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党而以国民党左派身份继续效力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但早已不满的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这一方式,尽管蒋与中共的合作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矛盾却不能不以决裂告终。)
此前苏俄推动的军事改革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这一次蒋也借中山舰事件削弱苏俄在军内的实际控制权。对此苏俄方面基本接受,苏共中央代表布勃诺夫到广东后承认,中山舰事件的确有苏俄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设置参谋部、军需部和政治部等“军事集中管理搞得太快”,引起军官上层暗中反对。他认为,上述三部及党代表和顾问就像“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当俄国(即外国)顾问对中国将军表现专横时,等于提醒中国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曾发生让中国主官或军校校长在队列前向俄国顾问报告的情形,实在过分,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布勃诺夫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注: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68-172页。按这里所说的参谋部原书译为“司令部”、军需部原书译为“后勤部”,据内容看应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和军需部。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6-187页;苏俄内部相反的观点则见于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5日,同前书,第222-225页。关于布勃诺夫使团对事件的看法,并参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72-376页。)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后来也同意,“蒋介石将军的3月30日行动是由我们军事顾问们的错误引起的”。(注:除季山嘉等的过火行为外,俄方承认的“错误”还包括在黄埔军校讲授马列主义而不讲授三民主义。这些行为造成的“满腔怒火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蒋介石这时就成了他们的客观工具”。(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2页)类似的见解也见于穆辛在关于中共在广州任务的提纲,参见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同前书,第210页。)
在这样的认识下,苏俄方面自然希望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一度担任广州苏俄临时负责人的索洛维约夫从北京到广州前已与加拉罕取得共识,“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他注意到,蒋在3月20日态度不很合作,但在24日得知布勃诺夫使团要走而鲍罗廷尚不知何时返回后,主动表示要与布勃诺夫面谈。谈话的结果强化了上述共识,尽管“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约夫却以为,既然错处主要在苏俄方面,“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做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这需要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威望”,只有鲍罗廷具有这种威望,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信任他,他能胜任这个任务”。(注: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77-179页。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得到布勃诺夫使团的确认了,参见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8页。)
索洛维约夫反映的是不少在粤苏俄人员的共识,美国记者索克思恰在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到广州,他在舞会上与俄国人交谈,后者以为一切都完了,中共党人多藏匿或逃逸,反共势力兴高采烈,扭转局势的惟一可能是鲍罗廷返粤。(注: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p.336.)鲍罗廷受命立即从北方返粤,这意味着他在与季山嘉的竞争中最后胜出。4月29日鲍罗廷抵达广州,未见中共而先往见蒋。张国焘闻讯到鲍府等候,显然不满鲍罗廷的态度。数日后鲍罗廷告诉张,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国民党中派,且都有较强的反共意识。若孙中山在,也会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张国焘发现,鲍罗廷最关切的是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及苏俄是否会因此被迫离开广东,而视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地位等为次要问题。鲍罗廷并确信自己有维持与国民党关系的办法,那就是他手中有钱。(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12-515页。按物质援助的确是任何国民党主政者之所必需,不过以此为基础的关系,其延续性也视双方在供需上的相互满足而定,一旦鲍罗廷的钱不足国民党所需或其找到足以取代的财源,这样的关系便未必能持久。)
在以往蒋介石与在粤各军的资源争夺中,鲍罗廷始终支持黄埔军,后者是俄援的主要接收者,(注:Vera V.Vishnyakova-Akimov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tr.by Steven I.Lev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20.)这是蒋、鲍关系尚好的基础。同时老革命家鲍罗廷算计甚深,他带回了久已离粤的胡汉民。(注:据伴随胡汉民的朱和中回忆,莫斯科最初打算将胡汉民召回苏联,是鲍罗廷决定将其带回广州。但胡汉民在广州日子并不好过,观望月余,其外交部长职也被陈友仁代理,遂于5月11日避走香港。(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第373-378页))胡在莫斯科时屡有相当激进而左倾的表述,若蒋介石不与苏俄妥协,鲍罗廷也可尝试拥胡汉民任领袖;若蒋逼俄退出而使国民党右转,他本人将立刻面对资望高于他的胡氏,后者本国民党“右派”代表,在反“左派”方面尤具“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同时,包括物资弹药和军事技术的俄援是黄埔军力量的重要支柱,失去俄援则黄埔军力量顿减。而中共和左倾的青年军人在黄埔军中的潜势力仍不可小视,宋子文、谭延闿等新老中间派均持调和态度。这样,不论文斗武斗,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均无独自胜出的把握,除联俄外也别无出路。
其实蒋介石在逐王懋功后与汪精卫谈季山嘉专横时,已“料其为个人行动,决非其当局者之意”。3月22日,当苏俄参议来问蒋中山舰事件的作为是“对人”还是“对俄”,蒋“答以对人”。俄参议表示“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并称要将季山嘉等遣送回国,(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2月27日、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7、8页。陈洁如则说,事发后俄方曾有人来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汪精卫还是针对苏俄,蒋介石答是针对汪精卫。(Chen Che-yu,My Memoirs,pp.302-303;中译本,第195-196页))结果双方很快达成继续合作的协议。
蒋介石与苏俄的妥协当然不仅着眼于权势之争,他是那时较少认真考虑了帝国主义威胁和攘外与安内关系的国民党领袖。如果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正面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一个革命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蒋介石早在1925年7月就认为,沙基惨案的发生表明“英帝国主义者与我实际上盖已入于交战状态”,故“我政府亦惟有认英帝国主义为当前之大敌”。(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页。)在面临帝国主义近在咫尺的直接威胁时,革命事业也有邻近的大国援助这一象征作用并不低于物质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较强,他在1924年谈及联俄时就对一些“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表示不满。(注:《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44页。)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既可针对俄国人,也可针对任何外国人。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他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各国担心,美国亦其一。1926年初,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在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后,宣称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恨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注:Lewis S.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vey,L(May 1926),pp.181-182.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在1926年1月7日曾接见美国记者,谈约两小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之虚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94页),或即指此次见面。))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的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注:参见Jenkins to Kellogg,Mar.27,Apr.7,May 19,May 25,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893.00/7358,/7400,/7469,/7473;MacMurray to Kellogg,May 4,1926,SDF 893.00/7439。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维持摇摆不定的状态。)到1926年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恰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著称。(注:Jenkins to MacMurray,June 11,1926,SDF 893.00/7522.)《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注: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p.20.)这或能反映那时多数外国人对蒋的观感。
蒋的表现与五卅事件后全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外在大环境非常合拍,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日渐流行的倾向。1926年初即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注: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现代评论》第3卷第56期(1926年1月2日),第19页。)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得民心,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那时北方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明显更敏锐的政治识力,已意识到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据报载,1926年2月,广东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对峙之势,在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而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和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陈公博和谭平山等支持蒋,而李济深、伍朝枢、宋子文等则附和后一见解;汪精卫初偏于蒋,后“为谭、孙所战胜,亦表赞同”。结果会议决定向海关税务司妥协,蒋即“突然辞职,宣言不问政治”。(注: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执中:《粤战未起前之局面》,《晨报》1926年3月16日(3月1日稿),第5版。两则报道内容相近,后者较详。)
这一会议的情形目前虽仅见于报纸,但与蒋介石那时的一贯识见相通,他更早就认识到攘外可以安内,主张在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蒋在1925年7月初上书国民政府说,“中国革命,其浅近目标,固在军阀。舆论皆谓内政不修,无以对外。实则内政之坏,大半由于军阀得帝国主义强力之助,方敢肆行无忌”。故“今后革命目标,应注重此点,认定帝国主义为当然大敌,誓与奋斗。盖必先杜绝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之途径,则军阀不攻而自倒。故今日革命,以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的,而对军阀不过为一枝叶问题耳”。他特别指出,与英帝国主义战,“无论胜负谁属,皆足引起全国及全世界革命群众之注意”。(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465、468页。)
到7月下旬,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进而阐述说,打倒帝国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即使英帝国主义真与我们开起战来,我们据大陆与他相持,他未必能离开海岸线制胜我们。”英国所恃为军舰大炮,只要离海岸线一百里,军舰即失作用;除铁路沿线外,中国一般道路狭小,大炮难以移动,其余军用品也输送不便,只要再离开铁路,英军便难取胜。有意思的是蒋的表述中也有一些晚清观念的“再生”,他列举的英军可以战胜的原因也包括吃面粉的英军不能在吃米的南方持久,以及英军“穿不惯草鞋,走不了山路蹊径”等,(注:本段与下段,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99-112页。)大致是当年夷狄离不开大黄、腿直不便走山路等说法的现代翻版。
在蒋看来,中国革命“是今日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吾党革命目标,与其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所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只有“我们能打倒帝国主义,才为革命的真成功;我们敢同帝国主义作战,方为革命的真起首”。他说,“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北方军人必有爱国者,西南军人亦必有爱国者”,若大家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共同救国”,就可以逼迫帝国主义“本国自己的军队直接来同我们打仗”,革命军就是“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来打一仗”!到“外国与我们革命军开仗的时候,我们革命军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因为,无论中国“哪一省一处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世界革命一起,帝国主义再没有幸存的道理”。
从这些言论看,前述报载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中蒋介石的发言基本符合其一贯主张,他的确希望通过与帝国主义直接开战而获取全国的支持;并且他也认为,如果在中国内地打持久战,帝国主义未必不可战胜。苏俄带来的“世界革命”观念进一步武装和提升了蒋介石的思想,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战,则中国任一军队与帝国主义开战,不仅可以博得全国同情和政治支持,更能点燃“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这就意味着世界革命基地苏俄的卷入和参与。由此看来,国民党领导的革命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蒋介石此时不与苏俄决裂,所思虑者应较为深远。(注:到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大部之后,一方面其控制地域的广阔使得苏俄物质援助显得数量渐少因而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时国民党也开始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以各种方式直接摄取钱财),另一方面列强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竞相做出亲南方的政策转变,致使实际层面的“帝国主义威胁”大大减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乃能决定与苏俄以及中共决裂。详另文,一些初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若前述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属实,则不仅与中山舰事件有所关联,且反映出广州当时权势之争的某些面向,尤其各类人物的分野值得注意。在讨论中支持蒋的谭平山和陈公博皆粤籍少壮新锐,谭乃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仍未失势(直到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才与其他共产党一起退出政府);而陈也是前共产党,他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让邓演达找到他,“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一面限制共产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其成员有12人,蒋、邓、陈外,还有谭延闿、朱培德、何香凝、陈果夫、邵力子等,并在何香凝家里开过一次会。(注:陈公博:《苦笑录》,第66页。按邵力子似与鲍罗廷同时于4月29日抵粤,则此会召开应在此后。)
不过这一“左派核心”还缺少当时广州政治中一个重要团体,即作为孙中山亲戚的宋氏家族。不久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陈洁如多年后仍记得蒋对此大感兴奋,表现得非常激动,盖其“从未想到”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名流共餐,真是“妙得难以置信”。蒋告诉陈,“这些年来我与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一直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密切”,现在终有机会接近他的亲属;与宋氏家族的亲近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建立“重大功业的开端”。(注:Chen Che-yu,My Memoirs,pp.305-318,引文在pp.305-306;中译本,第197-208页。)此事若与前引陈公博说蒋组织“左派核心”的聚会共观,则其重要性更高,两次聚会都参与者确有一直左倾的何香凝。从陈洁如对当时气候甚热的描述中,可知这次吃饭应在前次“左派核心”的聚会之后。在旁人看来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尚乏充分的自信,他也相当清楚广州的实际权力核心在哪里。
若把中共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同情者作为左派,则陈公博所说的“左派核心”加上宋氏家族,恰好是那时广州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注:在穆辛当时的分类中,就视蒋介石为一方,而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为另一方。他虽认为双方的关系已破裂,但仍将两者皆看作“国民党左派”,主张“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团结包括汪、蒋在内的整个左派。(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0-211页)但穆辛认知中双方关系的“破裂”显然有误,破裂的只是蒋、汪关系,蒋成功地维持了与其余诸位的合作关系。)可见此时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已隐居主流,中山舰事件后正是这些人出来收拾局势,调解各方。其中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三人是那段时间几乎每份关于广东局势的苏俄文件都要提到的人,既说明三人的活跃,也无意中印证了苏俄对二、三军的持续关注。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中,那段时间他也是不时与谭、宋、朱三人议事。在3月26日蒋又一度辞职出走时,就是宋子文漏夜赶往虎门将其挽留。(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6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9页。)这里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第四军的李济深,他在苏俄文件中仅偶尔被提到,在蒋的记述中更几乎不及李济深,偶尔碰面也只说点场面话,体现出“蒋李交恶”其实余波未息。
不过,上述温和而偏左之人虽已显出结合之势,其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等各方面都差距甚大,更群龙无首。正因此,蒋才得以倚靠此派力量分击左右两派,同时将此派逐渐置于其控制之下。周恩来后来总结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和加伦均离粤,陈独秀也不在,左派除汪精卫外群龙无首,当时各方军政力量皆不欲蒋得势,惟无人牵头,致蒋坐大,并击败左右两方,其权力基础乃得以巩固。(注: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第119-121页。)此说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凸显出汪精卫临阵逃避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蒋介石早就感觉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有着与“旧势力”瓜葛太深和魄力不够等“书生”缺点。事发后汪隐匿不出,蒋即认为“此种不负责任之所为,非当大事者之行径也。无怪总理平生笑其为书生”。(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3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9页。反之,蒋自己早在1924年尚未得势时就表示,他“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参见《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收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页。)不过,汪精卫那时也有其困窘之处。索洛维约夫一面指出汪有遇事不够理智的性格弱点,同时也承认,在汪已感觉在蒋介石面前丢脸之时,苏俄向蒋让步更使汪感到受委屈,尤其循蒋之意召回汪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觉受了侮辱,故而隐匿不出。(注:参见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178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汪精卫在3月20日当天曾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注:陈公博:《苦笑录》,第60页。)蒋在4月给汪的信中也承认,“一年以来,吾兄对党对国之功绩,为总理逝世后之第一人,此不论何人不能否认”。(注:但蒋同时又指出汪的“优柔寡断”使其“大权旁落,竟使事事陷于被动地位”。蒋介石致汪精卫,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关键在于当时广东政治行为模式已大变,党内的“历史”早已不那么受重视,基本被当下的事功所压倒:不过几个月前,是否积极参与东征决定了杨、刘的命运,是否积极参与讨伐杨、刘更决定了胡汉民、许崇智等几位在党内同样有“地位和历史”之人的退隐。汪本人正是在这讲究事功而轻视党内“地位和历史”的趋势中上升到党政军第一的位置。然若论那段时间的具体事功,汪似不如蒋,其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俄的支持。一旦苏俄据事功之需而定取舍,失去支持的汪精卫自然也难以仅靠革命“历史”以维持其“地位”。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作为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作个人争权,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来说,蒋确实代表着国民党改组以来相对蓬勃向上的少壮力量,而且是那时位居前列又不具地方色彩的领导人当中惟一的军人。蒋介石并不欣赏的罗加乔夫就看到了蒋的独特之处:“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他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故应该“为国民革命运动留住蒋介石”。(注: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4页。)尽管苏俄方面一直注重对二、三、四军的工作,他们仍然清楚,论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谭、朱、李均不能与蒋竞争,而汪、胡则缺乏军事素养。在“革命”主要意味着武装夺取政权时,军事知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鲍罗廷敏锐地观察到,“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北伐”,以此为“汪的主要罪状”。在看见蒋“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鲍罗廷也只能一面指出北伐的不易成功,一面表示将给蒋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助其北伐成功。(注: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69页。)1926年初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将北伐列为最近就要实施的要事恐怕还可推敲,但这无疑有助于使军事总监变为总司令;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事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略,就必然大大增强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包括对财权的整体支配。这就牵涉到当时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文武之争,在这方面蒋介石和李济深利益基本一致,故李在事件中既不支持蒋,也不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自己就发现,事前并不赞成他对苏俄顾问采取行动的谭、朱、李各军长,在3月22日获悉他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处理后,“皆赞成余意”。(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据蒋日记,谭延闿在3月20日明确对他的举动不以为然,蒋则认为这是其“书生浅见”。参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0日,同前刊前页。)这里各军长赞成的大概就包括前述限制党代表权限的内容。其实蒋、李之争仍在继续,蒋对握有军权的“地方主义”也不能不有所让步。他在4月11日呈请设置中央军校副校长,以李济深兼任。同日日记中便“深思广东现局甚难处置,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固难调融,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4月1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9页。毛思诚所编书改为“广东现局,右派与共产两者之间显树敌帜,土匪与地方主义常伏暗礁,深用焦虑”。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45页。)这里很明确地将“地方主义”作为比左右派分裂更难解决的困难,非常能呈现他内心关注之所在。
不过,蒋至少在文官方面成功地打击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经过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一般认为向右派“妥协”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实际的结果是张静江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为江浙籍且曾参与西山会议的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参与广州政权的领导工作;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关系密切的广东入伍朝枢、吴铁城等或被逐或被捕,孙科在表态与这些人分手后才免于放逐的命运(当然也因为他是孙中山之子)。用朱培德的话说,以广东人为主的既存政治“重心”已失。鲍罗廷更明言:“除少数例外,广东人不适合作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东本地人排除在外。”(注:邵元冲等的回到中央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妥协的后果之一,当邵受命担任国民党青年部长、戴受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大多数真正的国民党左派试图抵制,而多数共产党人则因略知真情而先有了思想准备。(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2-278页)按本段所说广东,原件均译为广州,疑为误译,径改。又孙科一度被派往浙江联络孙传芳,蒋介石告诉未及与闻此事的谭延闿,此事“是弟提议,彼即赞成,并催其速行”(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6),但在驱逐伍朝枢后得以继任其遗下的广州市长。)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中山舰事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左倾的汪精卫被驱逐,右倾的胡汉民一度返回广州又失意离去,在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偏右领导人后,国民党有竞争力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广州“消失”,蒋的地位明显提高。(注:关于蒋介石这段时间的作为,还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1926年4月,谭延闿致信蒋介石商量军事预算问题,蒋复函说,“本月预算似应确定,请由吾公主持一切,不必事事商量,使弟更不安于心”。但蒋随即“贡献”了三条具体处置意见,虽然他最后又说“未知尊意如何?请与益之、任潮二公核定,弟无不遵照决议”,然前面三条口气相当直接,并无太多商量余地。(注: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7。)可知蒋此时已大权在握,代理汪精卫的谭延闿宁愿“事事商量”(几天后蒋才于4月16日正式当选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到5月下旬,蒋自己也忍不住说:“我近来听许多同志谬奖说,黄埔军校已成为党的重心。”(注:蒋介石:《中执委全会闭会演词》,1926年5月22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1页。)黄埔军校与蒋的个人关联众皆知晓,“近来”二字尤说明问题。
五 结语
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不久前获得正式领袖地位的胡、汪转瞬即淡出权力中心是非常重大的代际转折,后来所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此时皆开始出现在前台;他们中除蒋介石外皆能说英语,故能与仍处权力核心的鲍罗廷直接交流,孙科和陈友仁以同样原因此时至少与宋、孔一样重要,邓演达则能操德语故可与苏俄顾问中高阶的铁罗尼对话,也是权力核心的成员,凸现了俄国顾问的势力仍相当强大。(注:李宗仁于1926年5月到广州,仍发现那里崇俄风气仍甚,“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李宗仁回忆录》,第322页)。李宗仁的观察相当敏锐,实际上这个权力核心本身也是一个不随意开放的社交圈子,得以参与其中确实有助于政治竞争的上升,参见前引陈洁如所述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使蒋大感兴奋事。)这些皆是孙中山的幕僚和亲戚,绝大部分相当年轻,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他们基本偏左。(注:相对而言,这些人中只有孙科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然孙科多次主持广州市政,在民、财两权的“统一”方面主要是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且,在所谓右派之粤籍人士中,向有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之分,两者势同水火。“太子派”的聚会地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南堤俱乐部,胡汉民派不敢入内,而廖仲恺和宋子文倒是常客。可知少壮的“太子派”本相对亲近左派。参见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现代化》,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97-98页。)
但蒋介石掌权的道路还不平坦,鲍罗廷观察到,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本希望“使军队保持平静,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则要求蒋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限制共产党;蒋“成了他们的俘虏”,以“保持军内团结”为由要求军内共产党人退党,以国民党身份工作,于是共产党更怀疑他右倾。蒋介石“每天都向我抱怨,说什么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注: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其实蒋在与鲍罗廷达成妥协后即以捕吴铁城逐伍朝枢并公开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表明其已再向左转,鲍罗廷的回报是承认蒋所获取的权力并支持北伐。
此时新败于湖南的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外在形势的变化促使北伐进入实施阶段。盖唐部若被消灭,则两广将立刻受到北军威胁;唐如果退入广东或广西,这一新增的“客军”会使当地形势更为复杂。从全国看,北洋军正倾全力攻冯玉祥,在南方的兵力较弱,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尽管广东政局仍不稳定,这些因素致使本可安居广州以巩固其地位的蒋介石做出迅速进兵的决定。如前所述,战事既然成为主要政略,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即大大增强。蒋在6月5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后即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正式确立其领袖地位。
不过,在北伐誓师之初,蒋并未让黄埔军出击,(注: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作为总预备队留在蒋身边,这既增强了蒋的安全感,也削弱了军长何应钦直辖的力量。何应钦只能率领第一军余部驻守其潮汕地盘,同时防备可能来自福建方面的攻击;后因北伐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整体格局激变后改为向福建、浙江方向主动进攻,是为北伐的东征军。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年,第10-15页。)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注:据李宗仁的回忆,第四军先出兵是在他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而其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了不禁“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李宗仁回忆录》,第310页)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素以不怕死著称的黄埔第一军并未安排在北伐第一线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它提示着蒋介石一直鼓吹北伐或不过希望借此营造一种引而不发的态势,或并未充分认识到战机已至,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广东的领袖地位,然后再定是否北上。这一方略后来证明对蒋相当不利,(注:蒋大约未曾预料到湖南作战取胜会那样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急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去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但北伐的最终取胜(尽管并非完胜)表明,“后孙中山时代”政治新陈代谢的结果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是有利的。
标签:中山舰事件论文; 鲍罗廷论文; 国民党左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民国档案论文; 申报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