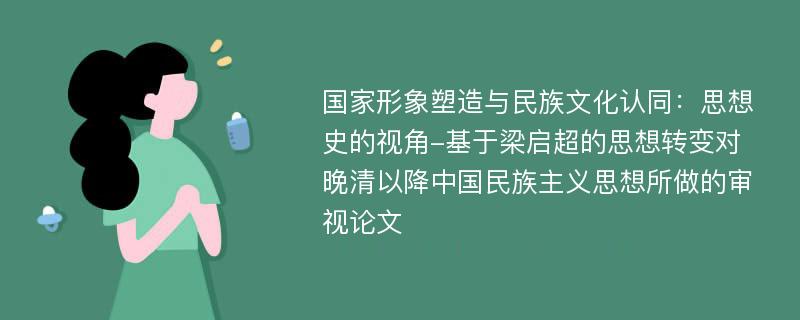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
——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李武装
摘 要: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关键词: 梁启超 思想史 民族主义 国家形象 文化认同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自晚清以降,中国人就开始为着从“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型模”向“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转型而努力,纵然这一“现代”转型是用他者的“坚船利炮”逼出来的。经过几代人的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我们今天早已完成了从“站起来”(民族独立)到“富起来”(经济发展)的时空转换,并试图在“强起来”(更多指向“文化—文明”层面)的呐喊声中重回“世界文明”之巅——这不仅包蕴着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而且延展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射线。立足思想史视角,这毋庸置疑也是对近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大尺度考量和大视野审视。
十分吊诡的是,早在1903年,梁启超(1873-1929)就对中华民族不期而遇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展开检讨,从而对“大国崛起”之路开出别样的民族—文化—思想方案,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梁启超用这种双向“自由”与双重“独立”规约夯实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搭建起他个人的“民族主义”景观,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基本透射出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源”与“流”。因为单就字面而言,梁启超发表于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首次使用了“民族”一词,而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则首次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词,至于其真正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那只有从他的思想辐射中寻找答案了。
基于此,本文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期待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民族文化认同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需要先行指出的是,本文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一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强调,“没有必要把‘民族主义’打上一个负面标签,再把它与爱国主义区分开来”[2]。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最大的对象莫过于头顶上的天与脚底下的地了。这是他们的生存空间,是他们的环境。这天是太伟大了,日月星辰云霞出入其间,给大地带来光明与黑暗,也带来梦幻与联想;地虽然没有天那样神秘,但地也同样极为伟大。海水、湖泊、河流、平原、森林,还有那千奇百怪的动物、花草均在这大地上,成为人触手可亲的真实的世界。原始人最为崇拜的对象无疑就是天地了。
一、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流变的逻辑同构性
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肇始于晚清。甲午海战的惨败、八国联军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不羁,一并使得1900年左右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在保国、保教和保种的“中国之声”助推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所谓“真正意义”,是指那时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自觉吁求,亦即对中国国家—民族形象塑造的自主性审视。比照而言,1900年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想(如果确实存有),主要是以“夷夏之辩”“变夷为夏”等为文化区隔和心理关照的,整体上要么呈现为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不断融入与改造汉族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的过程,要么递嬗为汉族皇权主义观念不断以开放包容姿态接纳少数民族观念以使自己更加充满活力之历程。因此,尽管之前的中华大地不时上演着“异族乱华、华平异族”等事象,但“文化冲突”始终不像西方入侵以来那么强烈、那么广泛,也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所以我们并不能按照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回应”模式(为行文方便,后文有专门论述)去审视。纵然在文化心理上,某些汉族知识分子可能存有或多或少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但毕竟是自发和非自觉的且从未真正遭遇到“他者”的挑战,所以也只能被纳入到帝国朝贡体系或者“中心—边缘”模式去玩味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兴起的缘由主要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营造的升级版“文化冲突”。进而言之,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出场是以“西方中心主义”全面颉颃“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为基本前提的,因为在遭遇西方诸帝国主义冲击之前,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文化视为普世主义的,即认为中华文化优位于其它一切别国文化,并以此界河诉诸“夷夏之辩”;遭遇西方现代性之后,中国人不得不用特殊主义的失落感替代曾经的普世主义优越感,而这种兴衰转化,渐次积淀凝结起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
钢梁与架构柱连接采用铰接方案,为方便现场安装,采用螺栓连接方式。该站架构及支架为钢筋混凝土电杆,采用地脚螺栓连接的形式,在构造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具有安全可靠、价格低廉、施工方便等优势。由于将混凝土电杆端部的钢圈嵌入法兰盘焊接,并加设了加劲板,同时将混凝土电杆受力钢筋连同内部混凝土保护层延伸至钢圈端部,使得构件的受力状态类似于钢管混凝土,充分保证了柱脚在压弯剪或拉弯剪复合受力状态下的强度。
1. 孵化器的运营以综合孵化模式和专业孵化模式为主。调查显示,孵化器的三种运营模式中,物业支持模式只有1家,占4%;综合孵化模式有16家,占64%;专业孵化模式有8家,占32%。目前孵化器企业的运营模式以综合孵化模式为主,专业孵化模式为辅。
综上所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先后经历了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实质是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排满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杂糅)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之蜕变历程。可以说,这三种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体现了梁启超的思想变迁历程,而且比较典型地折射出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的基本格局与状貌。立足思想史视角,我们的追问有二:一是在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精当把握;二是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如何博弈的,这种博弈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的道路选择。对这些追问的进一步思忖必将证成如下论断: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不能抽象地预设个人权利的自由优先还是具有公共情怀的德性先在,更不能离开具体国情和历史背景来讨论思想的启蒙重要还是国家的救亡重要。事实上,这些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是无法选择的,而后人往往基于现实需求或自我论述需要对历史上的那些思想者们横加指责,实在是我们所不齿的。
然而1918年访欧后,梁启超在各种“西方衰落论”(主要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怂恿下,开始站在反西方现代性立场上质疑起进化论和国家主义思想了。而为了寻觅到新的思想替代支点,他不得不基于中西比照视野调和起西洋物质文明和中国精神文明、西洋制度文明和中国道德文明,并最终在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和春秋三世说思想的重新审视中,点赞认肯起中国文化精神的既有价值和意义了。很显然,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转变为以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底色的新的世界主义者了,即从“民族国家”论者转向“文明国家”论者了。
这里重点提及的是,在培植或激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众多大师中,梁启超实在是绕不过的旗帜性人物之一,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国家—民族”形象塑造乃至“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求解,具有逻辑同构性。文献史考察显示,1898年之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常常纠结于传统的天下主义(俗称“普遍主义”)与排满的种族主义之间:一方面,在其恩师康有为“春秋三世说”影响下,梁启超主张破除种界,倡导“平满汉之界”并以天下大同为鹄的;另一方面,他却为联合所有黄种人以抗衡白种人的“泛黄种族主义”奔走呼告,并在实际政治行动中力挺排满革命。所以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比较混乱甚至充满了矛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普遍”的天下主义思想与“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杂糅。然而在1898到1918年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却历经了两次大的转变。
中国近现代思想关于“挑战—回应”模式的大讨论从而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彰显,则属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助推力。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民族间的战争和杀戮,种族冲突更是绵延不断,然而实话实说,并未形成系统而深刻的民族主义学说;直至孙中山革命派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其本质已与中国古代的种族主义所指迥异其趣:与其说革命党人的满汉之争是传统中国种族主义冲突的延续,不如说是革命党人阐发自己革命行为合理化的一种历史性叙事策略。而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无论学术界如何质疑“挑战—回应”模式,但它的确是我们阐释现代中国转型的一个基本思路或切入点。因为这一模式不仅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至关重要的是,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就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而言,“挑战—回应”模式的助推力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人不得不学会用西方的形制和观念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威胁;另一方面,中国人由此而生的情绪抵触和文化认同悖论,敦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主探寻中华“民族—国家”的未来出路,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大力催生。
二、梁启超的政治民族主义转向:民族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论辩
史料显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心情极其复杂,加上日本加藤弘之强权自由思想的影响,梁启超不得不开始建构自己的“权力自由观”了。他说,“天下无所谓权利,只有权力而已,权力即利也。”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权力”呢?盖缘于梁启超对“民族危机”“国将不国”的深刻领悟。试想,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国启蒙领袖,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该是何等失落?他对“民族之自由”和“民权”的渴望又是何等之强烈?当然,梁启超的“权力自由观”并非西方的“权利自由观”,后者是完全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自由观,而梁启超的自由观更多属于集体(国家)自由观。相应地,他本人也更应隶属于国家本位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了,因为在梁启超眼中,彼时中国所急者在政治自由之参政问题和民族自由之民族建国问题。
我们认为,梁启超关心国家自由和公民参政自由,强调为了前者可以牺牲后者的思想,正好区别于现代西方社会力挺的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思想,其根本原因,可能更在于梁启超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国家”性质之不同理解:一方面,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是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的保障;另一方面,个人关心国家利益,具备文明、现代的公民意识和德性则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基础和动力。在近现代中国,个人德性的提升和养成(“新民”的形成)首先是为着挽救濒临危亡的民族和国家,即“救亡”先于“启蒙”;而现代西方个人主义夯实的自由主义并不需要直面“救亡”问题,个人、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才是他们需要直面的问题。质言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呐喊中,根本就来不及思考个人、政府和国家之间的权利问题,抑或说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根本就不允许他思考此一问题,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将导致无政府主义甚至民族—国家的灭亡。
为了建构自己这种国家本位的民族自由思想,梁启超首先对“自由”投入了太多的溢美之词。他说,自由是普世的“天地公理”和中国时势之必需,“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紧接着在1902年的启蒙新作《新民说》中,梁启超尽管依然视自由为欧美诸国“立国之本原”,但自由的内涵与外延理应发生改变,即无论是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还是经济自由,都不应仅仅局限于西方自由主义者言说的个人之自由——那是一种野蛮之自由,而更应该隶属一种集体之自由——一种文明之自由。这种文明之自由之所以适用于中国,皆因自由乃“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他甚至认为,自由不是一种制度,而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一种德性、一种理想。因为在诸多自由形态的比照中,梁启超认为心灵之自由处于最高层阶,而要达致心灵自由,不仅要“克己复礼”(孔子思想),而且要“自胜而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看得出来,梁启超这种自由观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衣钵,而且接纳了道家思想重心灵自由的价值旨归,至关重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思想也被融合进来了。可见,梁启超的民族自由主义思想实乃国家—民族危机情势下,中国传统儒道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进化论思想交互照面、碰撞融合的必然结果。
立足思想史视角,我们需要考究的是,梁启超这种以自由奠基的“新民共同体”思想,究竟是现代意义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古典意义的道德共同体?抑或说,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究竟应该隶属自由主义所阐释的禀赋着富强、民主、自由等质素的“程序共和国”,还是应该归属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钩稽的具有集体道德基础的“公民共和国”呢?进一步的追问是,国民所认同的应该是一个世俗的政治族群,还是拥有公共善的道德共同体呢?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自己的这种转变直言不讳。在该书中,他不仅直接批判了曾经一度非常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径直揶揄了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学说。他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二者既是西方现代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又是祸根。所谓祸根,是指其在个人层面不断造就并带来现代人对权力和金钱的极端崇拜,在国家方面造就人们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顶礼膜拜。而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梁启超又不得不把目光停留在素有“世外桃源的中国”,其目的可能有二:一方面,希冀从中国文明中发现治疗西方现代性病症的药方;另一方面,希望找寻到有利于世界发展的“中国样本”,此样本并不限于中国自己的觉醒,更应禀赋其对全人类、全世界的独特文化贡献。
韩国学术研究机构很注重学术道德标准教材的开发,其中以“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开发的《学术道德标准教程》一书最具代表性。作为学术道德教育标准教材,该书分为人文社科版与理工版。主要内容包括:研究人员社会责任的类型及重要性;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类型、调查及认定;研究数据的管理,包括研究数据的概念、所有权、收集与甄别、分析、储藏保管、出版发表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出版伦理的定义,正确的学术引用方法,作者的资格,同事的评价,重复发表等;研究指导人员和被指导人员的关系与作用,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与作用,研究责任者和参与研究员的关系与作用,研究室文化的建立,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团结的研究团队等。
还是王晖先生一语中的,他说,梁启超的国家观念有别于一般的现代国家观念,他所定制的国家是作为一个具有道德一致性的自治共同体,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国家就是一套制度安排、一个官僚化的统一体,政府不代表也不体现公民的道德共同体。在梁启超那里,国家观是与其“群”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群”是一个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忠于这个共同体是其成员的道德实践的一部分,也是其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因此,“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梁启超的国家观念的差异,可以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观的冲突,而不是对于同一种国家的两种不同态度。”[5]事实上,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权利理论与梁启超理想的“三代之治”的道德社会事实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无独有偶,许纪霖先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启超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更接近西方共和主义的“公民共和国”理想,而与现代自由主义的“程序共和国”有所隔阂。梁启超趋向于社群主义的个人主义,这样的个人主义并不构成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相反,近代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近代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同时诞生的,二者之间在一开始并不存在后来所具有的那种冲突和紧张关系,它们是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同一个过程,集中体现了晚清时期个人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的统一性关系。[3]
而那些认为梁启超一味否定西方个人本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只强调国家、民族自由和公民参政自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剥离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或者说,用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学说来质疑梁启超政治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显然属于怀特海所说的“措置具体感的谬误”。对此,张汝伦先生论述到,“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在西方产生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国家独立和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追求和保护基础上,晚清的中国,国家、民族的独立危机重重,资产阶级力量微弱,远未成熟,个人权利优先意识缺乏社会基础和历史准备。只有到了国家独立(辛亥革命)之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才会成为现实的需要和思想家的主要话语。”[6]
众所周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日本并开始接触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有关西方国家、民主、民族方面的著作,加之他对中国改良和国民性的自主深彻反思,使得他逐步放弃了公羊三世说包蕴的天下主义思想,而转向以现代民族国家和反帝国主义为基调的“现代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即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是1903年游美之后,通过考察海外华人世界和美国民主,以及进一步反思资本主义垄断竞争,梁启超开始拥趸国家主义和开明专制论。这一时期,由于他一味执着于“国家至上”原则和“国家理性”充斥的“大民族主义”,反对革命派单纯排满的“小民族主义”,所以也逻辑使然地放弃了原来信奉的国民自由和民主思想,转而执着于国家是以国民忠诚为前提的威权共同体思想。
三、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转向:回到“文明国家”
如果比照1903年到1904年的《新大陆游记》和1918年到1920年的《欧游心影录》,就可以清楚看到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变化。《新大陆游记》虽然也有对美国民主制的怀疑和批评,但彼时的梁启超更多是带着寻找拯救中国的初衷到美国“取经”的。因此在比较视野下,他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中国人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接受专治不能享受自由等等。但到了《欧游心影录》时,梁启超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判中国文明及其未来发展的思想就发生了改变,由于此时的梁启超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西方没落论”思想(此思想深受“一战”的影响),所以他不得不从整个人类文明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不得不从西方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寻觅人类的救赎和重生之道。梁启超指出,西方不再是普遍主义的标准,不再是中国追随的偶像,中国不仅应回归自己的文化本位,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应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思忖“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显而易见,梁启超此时的思想已经从一味“追求现代化”转到“反思现代性”,并渐次“重估中国文化价值”之路上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梁启超后来的“价值的发现”。
对此问题,学术界曾展开了激烈论辩。有学人分析认为,在梁启超关于“群”的共同体中,国家对于国民来说,不是工具性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我目的的“群”。国民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不仅拥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志上的自由,而且也有对共同体尽其忠诚的义务,这就是公德。[3]但问题正如张灏先生指认的,梁启超对西方古希腊雅典的自由与现代英国的自由思想不加区分,使得近代英国自由思想中对个人独立和权利的强调被忽略了,进而导致梁启超把西方的立宪政体看作是一种确保公民参与的政治措施,而不是将它看作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措施。如此这般,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就演变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特色——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个人主义并没深深根植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中,而是民族自由主义占了上方,即“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存在一个普遍的偏向,即将民主看作是发挥近代民族国家作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4],从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和国家理性的地位远比自由主义重要。
调查及记录两组患者主斥的术后髋关节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法)进行疼痛程度的评定,重度疼痛:7-10分、中度疼痛:4-6分、轻度疼痛:1-3分、无痛感:0分。
不难发现,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从一个国家主义者再次变成了世界主义者了,但与其早期的世界主义思想已不能同日而语。早期的世界主义不仅以华夏中心主义和“公羊三世论”为基础,多少带有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而且认为中国文化是普世主义的,高于西方文明的;而此时,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并非奠基于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认为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洋文化,各有其优劣。他写到,国家不再是其本身的目的,国家是凝聚国民以促进整个人类进化的手段;富强不是最终目的,有助于全人类才是其最大责任;中西文明是平等的、应该互补的,当下的责任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7]。他一方面批评了那种画地为牢,以为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的保守思想;另一方面批评了那种沉湎西风,把中国视为分文不值的崇洋媚外心理。进一步,梁启超指出,学习西方和中国传统,其要旨乃冲破文化的外在条件并直击思想的根本精神。只有从精神层面我们才能真正抓住不同文明中那些“普世主义”价值,抑或文化只有在对比中才能彰显各自的价值。梁启超的这种思路不仅成为他后期治学的基本理路——以西学来阐发中学和以传统来拯救现实,而且径直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模式之一。
回到文化民族主义,我们发现,梁启超在民国建立以后,就已经转变了其对民族国家的暂时诉求,开始致力于“文明国家”的努力中去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国性篇》(1912)、《〈大中华〉发刊辞》(1915)、《中国与土耳其之异》(1915)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一个国家的存亡,关键不在于诸如政府之类的政治形式,而在于其“国性”,“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忘”。所谓“国性”,乃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国语、国教和国俗,“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既成,则亦不易灭。”[8]显而易见,此时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在于以往“文明国家”所积淀的“国性”,而非现代“新民”运动所依赖的西方现代性。传统文明必须成为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否则,即便中国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假如失却原有的“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等“国性”,中国便是真的“亡国”了。换言之,中国要战胜西方帝国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民族国家阶段,必须恢复其“文明国家”地位,必须把自己的立国之基建立在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之上,而这一点恰好构成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还是甘阳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总结到位,他说,“如果梁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辞》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9]。
四、直面中国现实的反思性结语
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其民族主义思想先后经历了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事实上也体现了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格局和流变形态。立足更大历史尺度,它毋庸置疑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视域;而从思想史视野出发,它不仅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axiality)和“现代性”(modernity)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的可能进路,而且契合着当下国内精英们重新界定“文化自信”内涵、重新澄明“文化中国”本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思想语法。并不限于此,较之于那些一味沉迷于“现代化目的论”的多数人,晚年的梁启超无疑属于那少数的启蒙先觉者之一。尽管如此,还应当承认,在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弱势的那个晚清时代,中国人很难找回曾经的自信,很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保持实质的平衡,更遑论理论的圆融一贯,特别是面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技术成就,任何民族与个人都有可能倒戈西方,进而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制和观念来“筹划”自己的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更何况身处积贫积弱时代的梁启超。在这个意义上,谨慎理解和历史看待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及其转变,可能更为客观,更为中肯,毕竟历史的高度决定思想的深度。
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Lamb.)、北美短叶松(Pinus banksiana Lambert)、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和毛白杨(Populus tomectosa)。
就本论题而言,伴随中国现代化经验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也不能立足中西对抗视野“强制阐释”中国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而必须基于中国文化自身和本土语境思考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化了。因为中国除了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形态——独立主权、清晰疆界、民主法制等政治体制外,还存在一个其它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特殊事象,即作为一个从未中断抑或死亡的“文明体”,中国至今仍赓续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因此, 以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应当属于新时代大国形象塑造与民族姿态彰显的可取路径,也是追寻中国文明新形态——文明国家的一条比较稳妥的思想进路。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追求现代“文明国家”进程中,我们是否可以放弃“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形态呢?显然不能。因为在“新全球化”与“后全球化”交互时代,国内外情况异常复杂,一方面,现代化越深入、文化交流越广泛,认同迷失现象越严重;另一方面,西方话语霸权抹黑、威胁中华民族形象的势头有增无减,且花样翻新,这不仅是对文化——民族之归属需求规律的背离,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颉颃。由此,笔者认为,如果说曾经的中国属于“古典的”文明国家,那么现在的中国则吁求“现代的”文明国家,而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依然是“文明国家”不可超克的基本前提。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无论是塑造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还是澄清新时代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抑或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条优选方案当是: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惟如此,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从苏联引进了吉林、太原、兰州3个中型氮肥厂;1958年,化工部安排建设省级、专区级、县级氮肥厂的设计任务和建设小氮肥示范厂的任务,示范厂采用自主开发的技术生产合成氨,并联产碳酸氢铵,从此开启了我国氮肥工业创新发展的历程。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91.
[2]马戎.不必将民族主义贴上负面标签[N].环球时报,2015-04-28(15).
[3]许纪霖.政治美学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05(1).
[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16-217.
[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M].北京:三联书店,2004:985.
[6]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4.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8]郑师渠,等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0.
[9]甘阳,等.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N].21世纪经济报道,2003-12-29(2).
中图分类号: D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2-0192-06
作者简介: 李武装,男,哲学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文化语境研究”(18BZX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