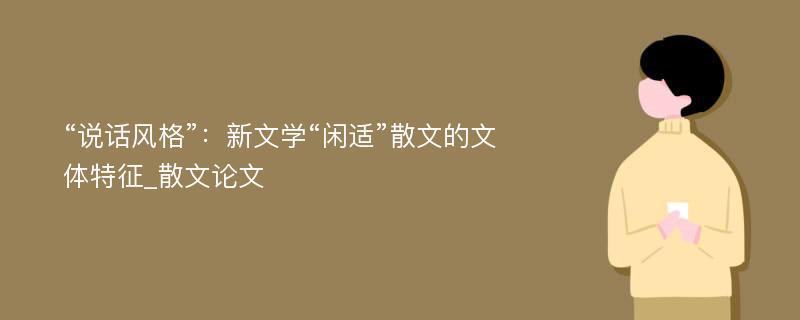
“谈话风”:新文学“闲适”散文的文体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闲适论文,文体论文,散文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闲适”一直是作为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其自身的发展,而“闲适”文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散文”这种文类,因为追求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闲适”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生活哲理与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也就是说,正是“闲适”散文促使创作主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观念与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闲适”散文作家往往崇尚老庄式的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人文精神,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发端于“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的“闲适”散文正是对清闲安适公开的文学追求,是对宁静平和、超然物外的古典境界的营造。因此在文体形式上,它采取的“谈话风”的小品样式,正如厨川白村描述过的那样:“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随笔)。”(注:引自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而这种优雅闲适的essay文体的生成又具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文学表现内容的“闲适”,一是作为文学表现形式的“闲适”。
在表现内容上,新文学的“闲适”散文大多取材于身边琐事。尽管林语堂说过小品文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注:林语堂:《〈人世间〉发刊词》,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大多趋向于谈“苍蝇之微”,所以郁达夫曾引用当时许多人挖苦《人间世》“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话,对林语堂作了嘲讽。只要翻开“闲适”散文作品,随意浏览一下,就可发现大量此类题目:《蚊子与苍蝇》(周作人),《妓女与妾》(林语堂),《男人》、《女人》(梁实秋),《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叶灵凤),《眠月》(俞平伯),《红叶》(孙伏园),《谈吃与画饼充饥》(张爱玲),《“春朝”一刻值千金》(梁遇春),《听话的艺术》(杨绛),《吃食和文学》(汪曾祺),《谈病》(贾平凹),《衣》、《食》、《住》、《行》(林斤澜)等等。应该说,作家自由选择题材的过程,其实也是作家创作心理中的“闲适”意趣寻求自由表达的一种物态化过程。正是这些“衣”“食”“住”“行”的身边琐事才最能体现作家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态度;同时,作家们“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也通过对身边琐事的抒写,“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注: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于是,在“闲适”散文的题材选择上也相应出现了二种不同的层面:物态化层面和情态化层面。这二个层面交织一体,集中体现在“闲适”散文大致相类的意象群上。
意象是主体审美情感同外在客观物的一种互感和同化,是物我双向交流的一种审美策略。在个体文化心理结构中,作家的审美情感、审美态度同他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如网状般联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所以,意象的选取和生成,实质上也体现了作家的某种人生态度和个人理想。在“闲适”散文中,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是这样一些意象:
一、“水”——“雨”意象。由于现代“闲适”散文作家大多出身于江南水乡,所以他们对“水”有着一种天然的情分,就如周作人所说的:“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平常对于水不觉得怎么新奇,要去临流赏玩一番,可是生平与水太相习了,自有一种情分,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注:周作人:《北平的春天》。)柯灵对浙东水乡更是渲染得如仙境一般:“代可曾到过浙东的水村?——那是一种水晶似的境界”,“明镜般的湖泊,一片烟波接着远天。”(注:柯灵:《野渡》,《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与“水”相关联的“雨”也是“闲适”散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周作人多次感叹“雨还是故乡的好”(注:周作人:《夜航船里》。)。早在1902年8月,他初到南京时就在日记中写道:“吾乡雨极多,故一闻雨声,不觉神爽,殊不可解。”汪曾祺对西南联大读书时昆明的雨季更是记忆犹新、赞叹不已:“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注:汪曾祺:《昆明的雨》。)无论是“水”意象还是“雨”意象,从表面看,似乎都凝聚着作家的思乡情结,正如汪曾祺说的:“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注:汪曾祺:《昆明的雨》。)(尽管汪曾祺的故乡在江苏高邮,但青年时的生活已使他将昆明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其实,从深层次看,却仍是作家对植根于潜意识中的“闲适”情趣的倾慕,对“现在”都市的下意识拒绝和对经验生活中乡村所固有的那种安逸、平和情境的依恋。这种心态在周作人的《苦雨》一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在他给孙伏园的这封信里,先回味了在故乡卧在乌篷船里听雨玩水的美境:“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然而对照北京的雨,作者不由得黯然神伤:“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因为不仅“雨具不很完全”,而且园墙被淋坍,“梁上君子”光顾,甚至夜间睡眠不安,“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一边是“梦似的诗境”,一边是大雨带来的无穷烦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故乡“雨”、“水”的偏爱之情,而这种心情几乎成为一种情感潜流流贯在他的许多“闲适”散文中。如《乌篷船》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收信人“子荣”正是他自己使用过的笔名),作者向“子荣”描述了坐在乌篷船上的“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闲适”的乡村景色;“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闲适”的生活态度;“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闲适”的生活方式。这里,作者对水乡生活的把握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他笔下,水乡的声、色、景、韵与作者悠闲自在的心境态度交互融合,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这种水乡生活体现的优雅、闲适的心境不仅仅属于周作人的散文,柯灵笔下的浙东水乡也处处浮动着轻灵秀雅的吴越女儿般的风姿:“午后昼静时光,溶溶的河流催眠似的浅唱低吟,远处间或有些鸡声虫声。山脚边忽然传来一串俚歌,接着树林里闪出一个人影,也许带着包裹雨伞,挑一点竹笼担子,且行且唱,到路亭里把东西一放,就蹲在渡头,向水里捞起来系在船上的‘揉渡’绳子,一把一把将那魁星斗似的四方渡船,从对岸缓缓揉过……。”(注:柯灵:《野渡》,《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美学家阿米尔的话:“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境。”(注: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九章,《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确实,浙东水乡的自然风景渗透着作者如“水”般恬适、闲淡的心境,而作者那无边的乡思,那童年时乡村生活的记忆,那文人骨子里对山水依恋的“闲适”情趣也正是通过江南的“水”、江南的“雨”这些意象传达出来。
二、“烟”——“酒”——“茶”意象。周作人早年写过许多有关“酒”的诗文,如《谈酒》等,到了晚年,他又连续写下了《吃酒的本领》、《我的酒友》、《古代的酒》、《过年的酒》等一系列关于酒的散文,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柯灵等人的散文中也大量出现“酒”意象;同样,“喝茶”、“茶与友谊”、“茶与文学”、“寻常茶话”等也是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汪曾祺、贾平凹、黄裳等喜爱的散文题材;“烟”更是梁实秋、林语堂、吴组缃和汪曾祺所嗜好,也是他们散文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之一。这些意象的选择也与文人士大夫的闲适情趣有关。对此,我们可以从“闲适”散文中关于“酒”所带来的无限趣味的描述中窥知缘由。比如周作人本人并不善饮酒,但他散文中对“酒”这一意象所体现的艺术化生活情趣的把握却无懈可击,他说:“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注:周作人:《谈酒》。)柯灵更是活灵活现地描画出浙东人饮酒的神韵:“端起碗来向嘴边轻轻一啜,又用两个指头拈起一粒茴香豆或者海螺蛳,送进口里去,让口子自己去分壳吃肉地细细咀嚼。酒液下咽啯然作声,嘴唇皮咂了几下,辨别其中的醇味,那么从容舒缓,不慌不忙,一种满足的神气,使人不得不觉得他已经登上了生活的绿洲,飘然离开现实的世界。同时也会相信酒楼中常见那幅‘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实在并没有形容过火了。”(注:柯灵:《酒》,《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散文集》(一)。)和以上两位作家所注重的饮酒过程中悠闲自适的生活情趣稍有不同,梁实秋欣赏的是“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注:梁实秋:《饮酒》。)但无论是周作人、柯灵,还是梁实秋,他们对那些易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琐细现象都进行了津津有味的细致描述,因为在他们看来,非如此生活不会变得有声有色有光泽,非如此人们就不可能在生活之中消除疲倦,获得精神的放松。
三、“小吃”——“菜肴”意象。“闲适”散文作家是很讲究“吃”的,且不说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也不说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单是汪曾祺笔下的咸蛋与咸菜就够诱人,且看:“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注: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端午的鸭蛋》。)“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互不雷同。北京的水疙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不老。‘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我吃过苏州的春不老,是用带缨子的很小的萝卜腌制的,腌成后寸把长的小缨子还是碧绿的,极嫩,微甜,好吃,名字也起得好。”(注:汪曾祺:《吃食和文学·咸菜和文化》)中国的“食”文化渊源流长,但是像“闲适”散文作家那样从家常小菜、街头小吃中“吃”出滋味、“吃”出乐趣,确实别有情调。如何理解“闲适”散文中的“美食”意象呢?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将中国人的美食习惯说成是“中国的国民生活的枯燥”所致,他认为“上自上层阶级起,他们的趣味,就只有吃鸦片,打牌,与蓄妾;足迹不出户牖,享乐只在四壁之内举行,因此倒也养成了一种像罗马颓废时代似的美食的习惯。”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上层阶级的讲求美食似乎还有其它原因。从“闲适”散文作家不满足于“吃饱”、“吃好”而追求“吃的艺术”看,他们已将“美食”和“饮酒”、“喝茶”、“抽烟”一样当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这种生活的小艺术品能够使生命永远充满着诗意般的滋润,即便风沙磨砺,也不会变得粗糙;即使急浪翻卷,也会在生命的岸边留下一些小贝壳,让人玩味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闲适”散文所选择的意象尽管在深入领悟之后能使读者读出作者内心的感情涟漪,但是,由于“闲适”散文的本体功能主要在于传达作家的“情趣”而不是形而上的“意义”,所以,在意象的选择和审美生成方式上,“闲适”散文看重的往往是一些生活化的物象实体。除以上谈到的一些意象外,又如“乌篷船”、“野菜”、“蛤蟆”、“衣裳”、“男人”、“女人”等等均如此。这种从表面上隐去主观色彩的意象选择正是“闲适”散文家所追求的充满艺术情调的冲淡的美的表现。关于这种艺术格调化的生活情趣,周作人曾引述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观点说:“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蔼理斯对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注:周作人:《生活之艺术》。)笔者认为,“闲适”散文意象选择上的主观意念退隐现象正是出于这种“禁欲与纵欲的调和”,因为在那些作家看来,调和、冲淡的生活才是一种真正艺术化的生活,而这种艺术化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萎缩干枯,只“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并且“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注:周作人:《生活之艺术》。)罢了。以“闲适”的态度去喝茶酒,或以喝茶酒的心境写“闲适”散文,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冲淡、平和的风格特色,正如周作人所说:“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注:周作人:《两个鬼》。)因此他们在选择散文意象时往往隐去了表面的激情,而以一种客观的物象掩饰或节制着内心的冲动和狂热,营造出一片宁静、安详、玄远的古典化氛围,这就是周作人所追求的古希腊的节制均衡之美。
如果我们把“闲适”散文的意象看作是一种图式化的文本的话,那么,它的指向功能应该是双重的:一重是物理事实的指涉,另一重则是审美价值的指向。以前者而言,“闲适”散文作家大多津津乐道于经验生活中的日常具象,无论是对故乡风物的精细描述,还是对喝茶、饮酒之类生活化细节神情毕肖的审美观照,都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乌蓬船》中,作者就是以一种灵动的笔法回味着江南水乡欸乃的橹声、柔柔的水趣。顺着作者对岸旁乌桕、河边的红蓼、白蘋、渔舍及各式各样桥的介绍,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作者所描述的“梦似的诗境”,身临其境地体味了作者向往的悠闲心境。从后一重功能即审美价值的指向功能看,“闲适”散文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于平淡中见平淡”。由于意象的生成是物我双向交流的一个同构契合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克莱夫·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基于“闲适”散文作家的价值观念、人生关注的独特性,“闲适”散文意象体系的美学价值并不体现在理性语义的“寓意”上,这一点与杨朔、刘白羽等的散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杨朔散文中的“茶花”、“雪浪花”、“泰山”、“荔枝蜜”、“香山红叶”等意象无不体现着一种理性的寓意和作者的社会理想;相反,“闲适”散文中的意象则只是一种情绪符号,一种恬淡、空明、玄远的生存体验和感悟,一种对世俗的超越和回归。
完整地把握“闲适”散文的文体特征,还必须对它文体构成的另一层面——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段作出分析。在“闲适”散文的表现形式即叙述方式上,周作人所推崇的“禁欲与纵欲”相“调和”的精神则有形地表现为“自由”与“节制”的统一:既舒缓雍容又纯净简洁,既自由畅达又节制有度,既是自娱自乐、自言自语,又不忘是对读者说话,这是一种随意而又有节制的“谈话风”。
散文应该是所有文体中最无拘束、最自由的文体,作家们可以在这里放弃任何文体学的目的和规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能怎么写就怎么写,“生活有多么丰富,散文也应该有多么丰富”。(注:王彬:《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序》。)有人将散文比作“散步”,认为“应用文是赶路,散文是散步。赶路有目的地,有固定的路线。散步不一定需要目的地,随兴所至,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也不一定要固定的路线,一路行来,停花依柳,东张西望,路愈曲折愈富于情趣,不必顾虑到达目的地需要多长时间。”(注:罗大冈:《散文与散步》,《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散文既没有诗歌格律的束缚,也没有小说结构的框架,更没有戏剧舞台的限制,它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自由表达,是对秩序的反动,正如余秋雨所说:“小说、戏剧、诗歌的写作便是作者对自己生命的艺术化装扮……但是,人毕竟还有卸除装扮的需要,愿意它离开游戏现场,静静地看一看,想一想,与自己和旁人闲谈几句,这便是散文的诞生。”(注:余秋雨:《散文茶座》,《散文选刊》1993年第10期。)这段话说明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类”。而在所有的散文体式中,“絮语”体的“闲适”散文又是最为随意、最为自由的。美国有一位名尼姊(Nitchie)的文艺理论家,在她编的一册文艺批评论里说:“在各种形式的散文之中,我们简直可以说Essay是种类变化最多最复杂的一种。……关于这一种有趣的试作的写法及题材,并不曾有过什么特定的限制。尤其是那些不拘形式的家常闲话似的散文里,宇宙万有,无一不可以取来作题材,可以幽默,可以感伤,也可以辛辣,可以柔和,只教是亲切的家常闲话式的就对了。”(注:Nitchie: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P270.)确实,家居式恬淡的心境与“絮语”的笔调相结合,使“闲适”散文呈现出尤为放松、随意、自在的特点,由于它们的读者首先是作者自己,同时又是听作者絮谈的友人,这样就显得不拘形式、亲切自然,就像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自序》中所表白的:“这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比口说或者也更为明白一点了”,“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林语堂也说:“闲适”散文“絮语式”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心里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注:林语堂:《八十自叙》。)王了一更是坦诚地说自己写小品是“想到就写,写了就算了……
。”(注:王了一:《生活导报和我(代序)》,见《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确实,读着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王了一、汪曾祺等的散文,我们总像在听博学长者的闲谈漫语。周作人的散文说古论今,娓娓道来,从乌篷船写到儿童玩具,从故乡的野菜写到北京的茶食,从希腊的情歌写到日本的话本,笔触所及,皆见情趣。梁实秋的《年龄》一文从自己对高龄的向往和肃然起敬,写到植物的年轮、人的岁月痕迹,然后又联想到女士的整容、古代皇帝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接着又谈到探究别人(尤其是女人)年龄之毫无必要,最后借用邱吉尔与胡适的两件轶事说明由祝人长寿反容易引起误会作为全文的结局,娓娓絮谈,信笔写来,文笔舒徐自如,潇洒倜傥。同样,汪曾祺的散文也写得很随意,不讲章法,有些篇章看似写得很笨拙,象《国子监》、《果园杂记》、《葡萄月令》似乎有点初学作文的笔法,但在侃侃而谈之中,却舒展着洗练、飘逸之气。
然而,随意并不意味着漫无边际,毫无节制。“闲适”散文在感情的处理上,往往化浓为淡,化热为冷,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节制”的“中和美”的独特品格。在文字的表述上,“闲适”散文既不铺张渲染,也不过分严谨;既不淡而无味,也不刻意修饰;既不过于谐趣,也不过于庄重,行文有节,褒贬适中。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曾要求文学作品有“节制”、“守纪律”,即“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这种美学追求在理论上虽然不尽恰当,但确使他的散文独具特色:想象的节制,使他的散文不事铺张,趋于较严格的写事,娓娓而谈,隽永得体;情感的理性驾驭,使他的散文绝少无病呻吟的伤感及夸饰的浪漫,恬淡自然,别有况味,如《北平年景》中的一段:“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少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远在天涯海角,逢年过节,只有伉俪一对,可谓凄凉之极,但作者却哀而不伤,情感如涓涓细流,澄静平和,其间略带一丝海外游子久别故园的寂寞、酸楚和苦涩。梁实秋的散文大多如此,貌似情感淡然,实则韵味深远,构成了一种浓郁的情韵美。同样,周作人的散文向来以平和冲淡著称,这也是他努力压低了嗓门,用带着“涩味”和“简单味”的淡笔消解了内心的狂热和激情,从而能平和自如地回味着生活中的艺术韵致。这种中和节制的文体美在他的《雨天的书·自序》中表现得很突出:“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望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在这种不温不火回旋往复的语言节奏中,我们能体验到周作人散文特有的美,这种美不是激昂跌宕的壮美,而是宁静安详的氛围,是有节制的、古典化的肃穆与玄远。在他的笔下,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尼采式超人的悲哀或鲁迅式撼人心魄的悲剧意识。美对于周作人来说,乃是生命和
谐的、有序的情致,是田园式的格调: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现代人的浮躁,一切都停留在永恒的凝固之中。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和贾平凹的散文文体也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一种“节制”、“中和”的美。无论是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故乡的食物》、《吃食和文学》,还是贾平凹的《静虚村记》、《五味巷》、《河南巷小识》,它们都时时受到一种不偏不倚的情感的控制,含蓄、沉稳的态度使得创作主体与客体间的距离保持得不即不离,恰到好处。中国人平淡无奇的生活在他们眼里体现了一种自然的、无冲动的、永恒的魅力,体现了生命自身的含蓄、平衡的特征。他们正是从这种有节制的、规范的生活秩序里,窥见了其中衍生出来的和谐的美。
总之,新文学的“闲适”散文无论从选材的广泛、琐细,还是意象的客观、含蓄,无论从语言文体的随意自由还是节制有度,都极好地体现了创作主体闲暇悠适、雍容优雅的文人名士精神。应该说,“闲适”的主体精神与“小品”散文的表现形式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标签:散文论文; 汪曾祺论文; 林语堂论文; 周作人论文; 梁实秋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昆明的雨论文; 柯灵论文; 乌篷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