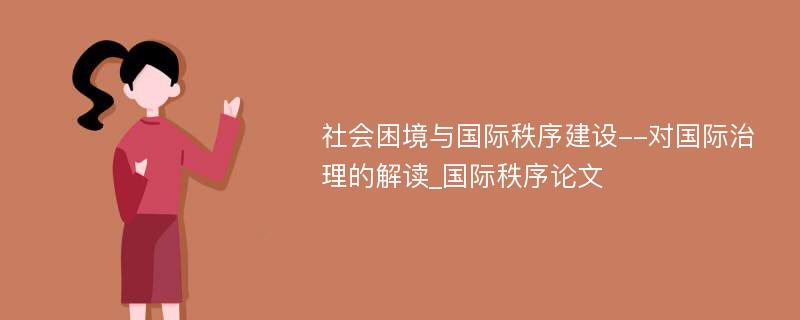
社会困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国际治理的一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困境论文,秩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后,“治理”(governance)及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学中成为 一个研究热点。但一般地将“国际治理”等同于“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 out government),容易得出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政府作用和国家主权日益削弱、民族国 家疆界日益模糊这一前提之上的结论。笔者认为:“没有政府的治理”如果仅以表征国 际体系中没有或者目前尚未能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权威的“世界政府”是正确的,但超越 历史地质疑民族国家在国际治理中存在的价值,进而宣告主权国家已是即将破碎的“艺 术品”则是误导性的。(注: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 ”,Foreign Affairs,No.4,1996,pp.45—61.)沃尔兹强调:“全球政治或世界政治还没 有取代国家政治。”(注: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Poli 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该刊系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会刊) ,1999.)那么,“治理”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以解读国际秩序呢?本文提出,国际 治理的基点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建构的难题(社会困境)是其内涵延展 的核心,“治理”概念的形成即是对从社会困境导出秩序的一种正确理解。
作为集体行动的国际关系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注:Jon Elster,TheCement of Society:A Study of Social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在一个由国家这一人类政治共同体形式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秩序建构同样依 赖国家间的集体行动。人类具有某种合作的能力,然而合作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注 :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我们 只要看看国家间战争、核武器扩散、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等等现象,就能显见:国际 社会中公共权威的缺失和政治经济权力分散导致的多中心状态,使国家间集体行动的结 果绝非是一个“合作扩展”的自发秩序,更一般的情况则是国家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 态”。但正如布尔所说,“无政府状态”也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注: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探究这一“社会”的意涵,需要我们从国家参与集体行动而 形成博弈关系的分析中展开解释。可列出三类一般的关系:(注:我们可以把将要分析 的三种关系用下面的两国博弈的图表来显示,这里的数字选择是任意的,仅表示国家的 偏好,即8>5>2>-2>-5>-8;A和B的符号表示两个不同的国家行为体,A1、A2和B1 、B2分别指代A国和B国的两种行为选择。
零和博弈的关系零差博弈的关系复合动机博弈的关系
B1 B2 B1B2B1B2
A1(5,-5) (-8,8) A1(5,5)(8,8)A1(5,5)
(-8,8)
A2(8,-8) (-2,2)A2(-8,-8) (-2,-2) A2(8,-8) (-2,-2)
一是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国所得,另一国必有所失。 这是一种纯粹竞争的情形,双方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实主 义理论就是将“无政府状态”看成了高度竞争性的环境,因而,自助(self-help)就当 然地成为每一个国家为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负责的手段。这一理论强调权力和安全的“ 高级政治”。
二是零差博弈(zero-difference game)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国所得,另一国也 必有所得。这是一种纯粹合作的情形,双方的目标是相容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经济相互依存论和集体安全论一定意义上推崇这一类型的关系。前者认为全球一体化 的发展,使每一个国家都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 突显了国家之间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低级政治”。后者指出只要国际社会以集体力量 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来建立安全保障体系,那么国家 之间就能维系“一国为大家,大家为一国”的局面。
在现实中,很少情况是完全符合上述两类关系的。人们通常认为零和博弈的情形是存 在的,但即使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境内,也不存在纯粹竞争的关系,因为国家双方都可能 有所失(尤其是现代战争的成本日益增高,更不用说是核战争的全面毁灭)。鲍德温指出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零和博弈情况很少。”(注:[美]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 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零差博弈的情形在国际关系史中也是不常见的,例如结盟通常因一方的背叛或双方的不 信任而破裂。这种纯粹合作型关系的脆弱性也可从一战后的国联构想不能阻止二战的爆 发中可见一斑。因此,要分析第三种更为基本的关系。
三是复合动机博弈(mixed-motive game)的关系。这是一种贯穿于零和与零差博弈之中 的关系,它意指在某种情境内,一国在倾向于选择“合作”还是选择“竞争”时总是面 临着冲突或两难选择,结果既可能是产生国家间的合作,也可能导致实际的冲突。
该类型关系所含的结果是一种相互依赖甚至不确定的状态。这可以在一个国际关系的 典型案例——“安全困境”中得到说明:国家间潜在的不安全威胁会使每一个国家都陷 入寻求军备力量最大化的紧张对抗态势,因为每一个国家密切关注别国力量增长的同时 ,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以求得绝对优势,但如此行为却又使别国以同样的逻辑行 为而直接导致对抗,无疑,对抗的结局是大家都不能摆脱对安全的担忧。冷战时期美国 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完全体现了这一困境:如果选择合作(停止军备竞赛)对双方的安全 都是有利的,但问题是当一方不确定或不信任另一方的偏好和选择时,怎样来最优地行 为?从单方来看,自我保护的最好选择是竞争(继续竞赛),但这样做使双方都越来越趋 近战争的边缘(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杰维斯最早提出安全困境的概念, 但他也指出,“安全困境可以解释一些战争,但却不能解释所有的战争”,(注:Rober t J.Art and 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 lishers Inc,1992,p.3.)尤其是当考虑到安全困境中存在的合作现象,例如美苏在古巴 危机之后通过军备控制的协调所维系的“威胁的平衡”。而事实上,冷战后随着国家间 对外交往关系的深入,安全困境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总是主导性的,但这也不等于说合作 已经成为国际体系内的普遍现象。现实的复杂往往在于竞争“比合作蕴涵着更丰富、深 刻的代价得失与正负功能。它可能是伟大的动因,也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注:郑也 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 40页。)在这意义上说,复合动机博弈的关系是国家间集体行动的基本关系,或者说是 一个常态的关系;国际秩序的建构最终也是这一博弈关系推演的产物。
国际秩序的难题:社会困境
在一个互赖关系日益复杂的国际社会,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国际秩序的存 在。但在复合动机博弈关系内,秩序的生成却是一个公共的难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 离集体行动而构造出秩序,但集体行动又潜在地面临着问题,例如“安全困境”就表明 国家在某种两难选择的情境内会出于自利的考虑而对合作摇摆不定。17世纪英国政治哲 学家霍布斯就此提出了著名的秩序解说,(注:[英]托马斯·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 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即国际秩序的建构始终被“锁定”(lock -in)在国家个体无法自我解除的竞争张力中:在不确信其他国家会合作的前提下,个体 选择合作是非理性的,因为这无助于改变竞争的“丛林规则”——每个国家都想征服压 制别国直到威胁自己安全的力量不复存在。
现实主义者径直推出了“自助”的理性法则。沃尔兹论说道:“在(无政府)结构所产 生的特定约束力存在的情况下,理性行为并不导致所希望的结果。在各国被迫要照料自 己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会照顾系统的利益。”(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王红 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30页。)换 言之,国家追求自利的“自由”与潜在的一个更好的秩序是不相容的,与其有更好的秩 序而无“自由”,毋宁有“自由”而无更好的秩序。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秩序解说,在瓦 奎兹看来,只是用了语辞学的技巧劝诱人们走向“退化”(degenerate)的一种理论范式 。(注:John A.Vasquez,“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 sive Research Programs: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 lancingPropos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2,1997,pp.899—91 2.)
然而,现实主义理论之流行本身也表明了它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因为 秩序作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它不能由个体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而直接供给 ,其中面临了三个问题:一是外部性的问题,即市场不能反映个体行为对其他个体所造 成的外在成本;二是产权问题,即市场只能对已经得到确认和保护的财产权进行自由交 换,但对没有确认的或是不限制使用的物品的产权就会失灵;三是“搭便车”(free-ri ding)问题,由于外部性的不可消除和产权收益的不清晰,个体不会自愿地为秩序付费 ,而是选择不支付成本就享用其他成员付费后供给的秩序。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国家 个体在秩序供给问题上产生了如“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所描述的两难选择 :如果大家都为秩序付费的话,大家都能享用秩序带来的收益,但又想自己如若能逃避 付费则是最好的,即使不这样想而是主动先付费,事实上也不能阻止别人不付费,甚至 可能就会被别人利用(成了“笨蛋”),如此还不如不付费,其理由是“别人让我无法不 这样做”。
现实主义理论描述了没有政府权威的组织和市场组织失效前提下的秩序供给的困难, 但强调国家“自助”某种意义上就是想消除国家间的集体行动,而这在一个所有国家交 互作用的国际社会中又是不现实的。借用亨廷顿的话说:这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 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国家“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注:[美]塞缪尔·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 89年版,第7页。)在霍布斯的构想中,个体真正憧憬的状态实为一个确保大家都安全和 幸福的社会秩序,但“个体在选择集体地而非个体地实现目标时的行动”(注:[美]詹 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著,陈光金译:《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3页。)时,自利的短期理性考虑阻碍了相互“自我制约”(self-constra int)的出现,进而不是秩序的产生,而是构造了竞争和冲突的群体内耗。因此,霍布斯 是抱着对秩序的憧憬来揭示问题的,而不是把这种群体内耗的状态看成既定的事实。
将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延伸至国际社会,我们可以作两个案例分析,一是国际法的维护 问题,二是全球环境问题。国际法是国家可预期的共同行为框架(比如为国家间的经济 贸易创造了交换的规则,为国家间的冲突提供了战争之外的解决途径等),因而维护国 际法是每一个国家都愿意分享的集体利益,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国际法可能对某一国家 而言是要付出短期成本的,例如当该国使用一项国际法条款来支持自己对他国行为的合 法性时,也就同时鼓励他国在日后用同样的条款来针对自己,如此,日后该国是用实力 优势威胁他国依据这一条款的行为(也就等于不承认条款的合法性),还是暂时忍受他国 使用这一条款可能使自己担负的成本,进而为自己以后再使用这一条款留有余地。无疑 ,选择规避短期成本将会使国际法受到破坏,也就使已有的秩序复归无序。
全球环境问题也是同样。获得一个良好的全球环境是每一个国家都偏好的共同利益, 但为此却需要共同的行为(各国都要为保护环境而付出成本)。如果一国将本国的资金投 放于维护全球自然环境,可能不得不冒这样的风险,即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却享受 不到付出代价后的全部好处,而是轻易让别国“搭便车”。然而,各国都选择短期的利 益满足(例如砍伐热带雨林或为发展工业而不顾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这就陷入了将来 大家都为全球环境的恶化而支付更大的成本(甚至移居出地球)。
上述案例体现了两种情形,一是在国家行为的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之间有一个阻碍合 作的“藩篱”——是选择短期成本的行为然后获得长期的共享利益,还是选择规避短期 成本而担负延滞的巨大成本(无利可享)?二是在国家行为的短期收益和长期成本之间有 一个阻滞合作的“陷阱”——是选择短期的利益满足(不支付成本)而陷入支付更大的延 期成本的消极性结局,还是选择限制短期的利益实现(支付成本)而长期享受共同的积极 结果?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短期自利理性容易形成集体非理性结果的矛盾,两种情形 的“共性”是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在由理性个体所构成的群 体中,如若每一个体都追寻自我利益,则将导致一种大家都不愿接受的非理性集体结果 ,并通过“积累效应”表现出来,即如果一国不顾及他国而按自我利益行为的时候,眼 前的短期收益是最大的,但这样行为却对他国造成了消极性结果,随着互动过程的推演 ,意识到这一点的国家为避免利益损失也倾向于选择如此行为,同时这种选择的增加进 一步加快了消极性结果的积累速度,当这些结果最终积累到某一点时,所有的国家都将 陷入一个“公共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并不得不为此付费的境地。
社会困境与国际秩序:国际治理的分析性概念
哈丁和奥尔森都曾提出集体行动无法摆脱社会困境的悲观结论。(注: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No.162,pp.1243—1248.[美]曼瑟尔 ·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看,这一结论确实有某种合理性。因为在一些集体行动的情 境内,即使合作意味着可能由此而实现对大家都有利的共同目标,但潜在的两难选择会 使国家在自助还是互助之间犹豫不决,结果就如奥尔森所说:“当一些个人拥有共同的 或者集体的利益时——当他们分享一个意图或目的时——个人的、没有组织的行动或者 根本无力增进那一共同利益,或者不能充分地增进那一利益。”(注:[美]曼瑟尔·奥 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7页。)但这只是 社会困境迷惑人的一种“表层现象”。埃莉诺等人的研究表明:现实世界中,很多社群 (community)已经成功地组织了集体行动并克服了社会困境,这为国际社会汲取成功经 验、找到消除社会困境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注:Elinor Ostrom,Joanna Burger,Chris topher B.Field,Richard B.Norgaard,David Policansky,“Revis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Global Challenges”,Science,1999,No.4,pp.278—282.)
社会困境有其“深层结构”:一是存在“次优结果”(pareto inferior),这意味着从 “次优结果”向“最优结果”(Pareto superior)改进的可能性,且改进是在所有国家 的利益不减少前提下的整体利益增加,正是这点才构成了国际社会进步的动力;二是“ 自助”之外的摆脱困境的手段选择空间依然存在,否则困境本身就成了人人都不需再作 思考的悲剧,这显然不是人们对国际社会的常理预期。用谢林的话说:困境指的就是不 经协调的个体行为产生了一种“无效率的均衡”,处在该均衡当中的个体原本可以通过 “组织”(organizing)而达到更优结果的均衡。(注:Thomas C.Schelling,Micromotiv es and Macrobehavior,New York:W.W.Norton,1978,p.225.)理解这点,需要进一步展 开复合动机博弈关系的分析:
首先,复合动机博弈意味着国家在选择行为时不是一个单方的行动,而是与他者相互 依存的一种策略行动(strategic action)。策略行动是通过有利于自身的方法,通过影 响别国对自身将如何行动的预期方法来影响别国的抉择的行动。(注:Thomas C.Schell 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160.) “依存”既表现在行为的收益结果相互关联,同时也表现在国家在选择行为时对这种关 联的识别(recognition)。而识别十分重要:一国总是要首先想到其他行为者将以何种 方式行动,然后在这个信念基础上做出选择;而且,其他行为者同样也会预期前者依托 信念之上的行动是什么,进而以这样的信念识别为基础做出反应,这里,信念的互动是 一个螺旋式演化的过程。所以,国家作为行动者是由两种属性决定的,国家具有的利益 偏好(preferences)和对其他行动者偏好的某种信念(belief)。如果立足这点,那么假 定一国出于道义原则而选择纯粹合作和假定一国只要实力够强就能选择纯粹竞争都是不 可取的,具体的选择结果往往是策略互动的依赖性产物。
其次,国家在复合动机博弈中选择行为时还必然地受外在体系结构的制约。沃尔兹在 麦迪逊讲座论文中指出:“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跨国间的力量分配是极其不平衡的。 ”(注: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Political Science an d Politics(该刊系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会刊),1999.)这种不平 衡的重要方面是国家在体系结构中所能采取的行动有差别。行动的选择离不开资源。资 源包括了地理、自然资源、人口、军事力量等的“刚性资源”(hard resources)和政府 素质(领导能力)、道德、文化等的“柔性资源”(soft resources)。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通常表现为国家动员资源达成政治目的或施加影响的能力,即一般所说的一国“实力投 射”的能力。这种能力从本质上而言不是单向度的,它所决定的国家行动是在影响他国 行动并对影响反馈再作用的过程关系中实现的,(注:国家行动能力是由影响他国的行 动(the acts)、施加影响时所需的资源(resources)和对他国行动反馈的反应(the resp onses to the acts)三个部分构成的复杂物。对此的一个精要分析,可参见K.J.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Hall Inc.,1983,pp .144—146.)所以行动还必然地涉及在这种过程关系中所确立的国家的地位、行为的成 本和收益以及国家对行动产生的结果的评估等要素。
最后,复合动机博弈还涉及信息结构。信息结构决定的是一国对他国信念和行动的确 信内容,国家总是依据可获得的信息而展开行为选择的推理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策 略互动正是国家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在相互的信息沟通中达成信念的一致。但 信息结构既有推动国家相互作用的一面,又有其限制性。国家通常所面对的信息是复杂 的,它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它认为是最关键的相关要素,换言之,国家并不能掌握关于未 来的全面知识(例如对相关资源、潜在交易伙伴、未来的交易成本、可行的选择方案等 的不确知)而完全理性地计算行动成本和收益或评估其结果。这样,现实中国家的行为 理性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理性,显示了国家提高自身对信息判断能力的必要性。基 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时代国家权力时指出:国家对信息的掌控取决于对信息的编辑、筛 选、阅读和提示,而国家及时、正确地传递信息(signaling)的能力决定了国家行动的 可信度和效度。(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 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1998,No.5,pp.81—94.)因此,信 息结构既是外在的,又是国家可以塑造的,掌握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决定了国家行为实现 “满意状态”的程度。
可见,国家在复合动机博弈关系内都有应对外部环境所赋予的“机会”和“限制”这 两个方面。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虽然战争总是一个缠绕人类和平的阴影,但每次大国 战争结束之后,人们都希望战胜国合作和制定制度以建立稳定的新秩序,例如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1648)、乌得勒支和约(1713)、欧洲协调(1815)、国际联盟(1919)和联合国(1 945)等秩序维持机制的确立。国际体系只要其内在的构成要素进行着互动作用,那么系 统赖以维系的基本条件就是从互动中生成的秩序。这种秩序即使从国际法(现实主义所 认定的脆弱机制)的角度看,践踏国际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因为就算是最强国也会认识到某种自我克制的好处,违背规则或规范通常会付出长期的 代价:它们的威望和影响将减弱;作为盟友,其他国家不愿意信任它们;它们越规侵害 的国家可能某天会报复等等。(注:对于国际法在无政府体系结构中的作用分析,可参 见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Abbott W.Kenneth,“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Lawyers”,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89,No.14,pp.335—411.)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际秩序就不是国际体系外在给定的某种固定特征,而是从国家 间集体行动的“组织”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就等于“国际秩序”。 诚如米尔纳所言,世界政府的缺失只是意味着国际政治在技术上(technically)说是无 政府的,但这不等于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极端(认定是无法改变的给定状态),国家 总是由一张利益和价值的复杂网络联结在一起。(注:Helen V.Milner,“A Critique o f Anarchy”,in Robert J.Art and Robert Jerviseds.,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1992,pp.29—35.)如果硬要把“无政府状态 ”看成是“秩序”,而不是米尔纳所说的技术意义上指称的“世界政府的缺失”,那么 其本身就是国家自己造就的一个社会困境。(注:温特的分析是有价值的,他指出:国 家作为施动者其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了结构,而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 ,所以无政府状态作为秩序是不合适的,充其量它只是某种观念分配的结构,因此他认 为无政府状态从霍布斯式的结构到洛克式的结构再到康德式的结构本身即预示了国际社 会秩序“优化”的可能性。可参阅[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所以,布尔要用“无政府社会”一词来表达:秩序是为 保存“国家社会”(a society of states)而维护国家的主权、避免战争和确保稳定的 财产权。(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p.5—9,16—19.)换句话说,国 际秩序是一种导致特定的预期结果、促进某些目的或价值的制度安排。
熊玠道明:“秩序表明各国对在它们相互关系中有限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抱有 共同的强烈要求。”(注:[美]熊玠著,余逊达、张铁军译:《无政府状态与世 界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强调“有限的”,就是因为 社会困境是秩序的难题所在,这当中包含了基欧汉所说的很高的治理成本,(注:RobertKeho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ter 5.)但无论如何,“有限 的”也不能阻止国家对秩序的“强烈要求”。这里,国际治理就成了“要求”转化为“ 现实”的途径。杨指出:治理是“促使世界政治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之间解决冲突、增 强合作,或更广义地说,消解集体行动问题”的一个过程。(注:Oran R.Young,Intern 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14.)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依存、策略互动以及体系结构和 信息结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为国家之间从互动中发展出制度来强化合作与减少摩擦提 供了激励。
这里的条件是,首先每一国家都应有平等参与集体行动的自由选择权,其次国家在集 体行动中进行“互惠”的策略行动(培育预期和信任),最后通过国际制度的建构来塑造 合作的价值观与信念。因此,社会困境在国际社会中得以消解将依赖两个层次的作用: 一是通过完善国际交流(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机制来改变国家对社会困境的 个体认知(perceptions),也就是让信息的传递使各国都确信“背叛”选择可能造成巨 大的消极性后果,而不是真正符合其长期利益的“优先选择”,进而使其调整对他国行 为的预期、交换相互间的信任以及强化对合作的认同;二是经由国际制度(internation al institutions)来建立一个可调节的中介,因为借助制度可以改变国家行为的收益结 构、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同时它也能使国家之间在建立制度、监督和实施制度的过程 中形成一个相互试错和学习的互动机制,从而产生国家对自身短期自利行为的内在规约 (确保合作动机的持久性)并促使国家采用共同策略来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由此,如果 国家把集体行动的“组织”当做一个前提,那么就可以在实际上改进短期自利理性和长 期集体理性相互依赖所发生的外在结构。
因此,国际治理即集体行动的“组织”,包含了这样的意涵:构造一种动态均衡的国 家行为模式和从社会困境中导出合作性秩序,且合作性秩序必须是创造一种集体“最优 结果”所需的个体间稳定的、可预期性的行为互动模式。该模式又体现为三个层面:一 是经由国家主观意愿的协调而产生国家行为的基本规则和规范;二是经由国家利益的协 调而产生规则和规范得以运行的机制(mechanisms);三是经由上述两个层面的互动而实 现社会价值(资源)的分配,反之,后者同时又强化前者,就是价值分配实际方式的进一 步规则化和价值分配内容的进一步平等化。(注:[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张胜军译 :《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北京,新华出版社,20 00年版,第55页。)因此,国际秩序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结果是动态性的,它随集体行 动“组织”的发展而发展,进而,一个公正合理、互惠合作的国际秩序是可以预期的, 但这必然在国际层面具体化为国家间通过一种理性集体行动的过程而产生的效果。
鉴于此,国际治理的一个分析性概念可界定为:主权国家在建构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 中所形成的某种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集体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借助于集体性的“组织” 过程而使国家间达致共同目标的工具理性意义(instrumental meaning)上的行动。控制 论者莫伊谢耶夫曾说,“自发势力和秩序,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有目的集体行动的必 要性——这是整个人类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所要彻底研究的矛盾。”(注:[苏]莫伊谢耶 夫:《人和控制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9页。)这对国际治理同样是有意义的 。国际秩序的难题在于社会困境,困境确实导源于国家的自利理性,但困境也为国家如 何处理短期自利理性和长期集体理性的问题提供了选择的空间。治理的关键效应就是减 少国家交互作用中实现共同收益的交易成本,强调集体行动需要对自主(利他或自私倾 向兼备)但相互依存的行动者进行“组织”,由此产生对国家群体具有“社会”意义的 秩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治理”概念的生命力,在于促使人们摆脱固守的国际社 会的行动逻辑——无政府状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级制的组织安排等;进而,在 理念上建立这样的思维模式:不是从“无政府状态”,而是从“社会困境”出发探讨秩 序的理论;不仅从“权力的配置结构”,更要从“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出发寻求秩序 建构的途径。新的时代已经提出了问题: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全球化世界,我们不仅需要 有效的治理,而且也需要正确的治理类型。无论是原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西方国家,还 是新秩序的倡导者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在对集体行动的治理逻辑进行构思和将构思转变 为实际的组织形式的过程中展开秩序建构的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