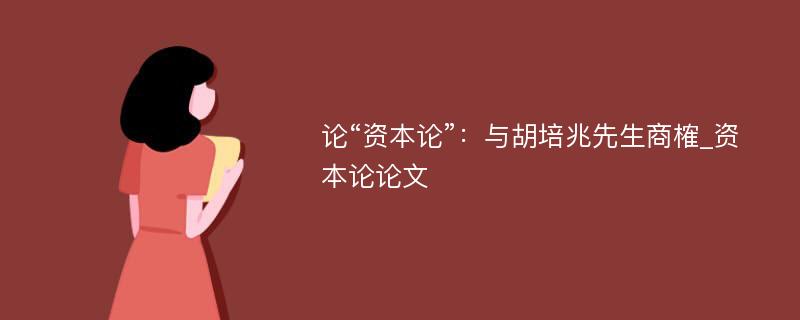
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胡培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6-0030-05
近读胡培兆先生《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看〈资本论〉——纪念〈资本论〉出版140周年》[1],文章认为:“从今天世界的现实看,《资本论》的有些原理和结论就已过时”。胡先生提出的很多观点的确是与时俱进,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在我看来,胡先生举出的例证,有不少似乎并非如胡先生所断言的那样,是《资本论》中“已经过时”的原理。基于此,我将自己的困惑梳理为六个问题,向胡先生以及学术界请教。
一、“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已不适用了吗?
胡先生断言:“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已基本不适用。劳动力价值由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原理,反映当时的真实……现在不同了,发达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普遍升值……最低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是这些国家社会保障的基本标准,就是失业工人也有温饱保障。如英国现在失业工人每周有64英镑的保障。就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当然要高过这个连失业工人都有的生活水平。而且现代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因子增加,智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有更高的生活条件,如教育费用、一定量的高蛋白食品、家用电器、白领服饰、书籍、年假旅游等等。没有这些条件,就会压抑智力的发展和再生产。因此劳动力价值不能再限于马克思时代填饱肚皮了。”
概括上述观点,胡先生否定“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理由①,大致有三条:(1)马克思时代的劳动力价值与现时代的劳动力价值,在量上已经有很大差距(后者大大高于前者)。由此可知;胡文的立论隐含着一个假定:马克思把劳动力价值构成看作一个既定不变的量。(2)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构成,只限于“填饱肚子”。(3)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构成中,没有包含劳动力的教育和发展费用。(4)马克思否认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我认为,胡先生的这几条理由与马克思的原意并不相符:
其一,马克思的确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2],但他并没有把劳动力价值构成看作是“既定不变的量”。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的量,“必要量”并不是“不变量”。比如马克思说:“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3],“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4]
其二,马克思并没有断言,劳动力价值只限于“填饱肚皮”,比如马克思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5]
其三,马克思认为,在劳动力价值的构成中,必须包括教育费用等用于促进劳动力发展的费用。比如马克思说: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因素有:“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6]
其四,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劳动力价值也会相应提高。比如马克思说:“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7]
综上可见,我认为胡先生断言“劳动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已基本不适用”,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再以降低劳动力价值为条件”吗?
胡先生断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再以降低劳动力价值为条件。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生活资料价格从而降低劳动力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前提的。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周劳动小时虽然由马克思时代的一般72小时缩短到一般40小时,但不仅劳动力价值大幅提高,剩余价值量更是大大增加。这是因为现代知识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比马克思时代大得无比,以致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并增不悖。”
归纳起来,胡先生质疑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理由大致有三条:(1)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工作日长度不变”为前提的;(2)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工作时间大大缩短,而且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大幅提高了;(3)马克思没有料到,现代知识劳动在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比马克思时代大大增加了。我认为,胡先生提出的这些理由,还不足以撼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
其一,“工作日长度不变”只是马克思为了便于分析问题的一种假设,并非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马克思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8]可见,相对剩余价值的要害并不在于“工作日长度不变”,而是在于“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假定“工作日长度不变”只是为了便于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中,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量变化的四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工作日长度可变”。马克思说:“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9],“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10]
其二,不能把生活资料数量的增加或者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同于“劳动力价值的大幅提高”。马克思说:“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本身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景下、即使劳动力价格下降了,“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11]可见,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胡先生之所以怀疑劳动力价值还能否降低,就在于他把生活资料数量的增加,等同于劳动力价值的提高了。
其三,用“单位时间里创造更大价值”来质疑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12]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胡文的结论似乎暗含着这样一个命题:降低劳动力价值意味着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其实,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并不等于“侵占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工人用更少的时间为自己生产出了更多、更丰富的生活资料;后者是指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马克思对此不仅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侵占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已经被舍像掉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13]
三、有必要对资本作道德评估吗?
胡先生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范畴和统治范畴,是剥削手段,吸血鬼。今天资本范畴已经走出社会制度禁区被普遍使用。它不过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对资本家的理念也要转变。现代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家,和各行各业一样,是褒称。现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由资本家筹资、投资和组织、经营、管理创造出来的。没有他们,哪能有今天这么多企业和这么多的职工就业?不能再一言以贬之:‘剥削者’。”
胡先生认为,之所以要对资本和资本家赋予“褒义”,归纳起来的论据,大致有三条:(1)由于资本已经是普遍存在,所以对资本家的看法也要转变;(2)过去“资本家”是贬义词,但今天的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家,所以应当改为褒义词;(3)现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由资本家创造出来的,没有资本家,哪有职工的饭碗。我认为,胡先生其实是在用道德标准评价资本家。在我看来,用道德标准来评价资本以及资本家,是一种极为狭隘的境界,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第一,我们过去把资本家“贬”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今天又把资本家“褒”成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大善人。这种跳跃式的思维方式,根源于把道德评估作为认识资本的唯一标准。其实,资本追不追求剩余价值,存不存在剥削,这只是在表述一个事实,属于事实判断;至于这种剥削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坏,则属于道德评价的范畴。尤其要强调的是,对资本的道德评价,总是与资本在既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功能以及人们对这种功能的评价有关,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抽象的“公平和正义”。不能把资本的性质与功能混为一谈:存在剥削是资本的本性,促进经济发展是资本的功能。
第二,马克思在对待资本以及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时候,从来不主张,也没有用道德评价去代替历史和理性的分析。《资本论》中的批判精神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历史评价。
第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4]可见,马克思明确反对用“褒”或“贬”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资本家。至于资本有没有剥削,资本家是不是剥削者,这不是一个“褒贬”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是不是”的实证问题。
第四,胡先生说:“没有他们(资本家),哪能有今天这么多企业和这么多的职工就业?”这个说法,怎么看怎么都像是我经常听到的资本家的自白:“我养活了N个工人”云云。资本家这样认为,我认为并不为过——因为他们只能站在资本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具备马克思主义专业知识训练的学者这样看问题,我就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我认为,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似乎已经相去甚远了。
四、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已被计划所代替了吗?
胡先生断言:“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自由放任阶段的一种竞争态势。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目标日益加强的条件下,无政府状态已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说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是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有两个并行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市场供需不平衡是绝对规律,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也是绝对规律。这两个规律的交互作用,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
实际上,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计划”与“市场”,都是有特定含义的,不能混为一谈。国家干预不能简单等同于“计划”,这应当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当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局部层面实现了“计划”,在某个方面含有“计划”的要求,这并不足为奇,但这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计划性”毕竟不是一回事;至于国家干预在未来是否会逐渐演化成“计划”,这恐怕还有待实践来回答,不能凭空想象,随意断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15]单个企业为什么能“实行节约”?因为单个企业能够做到“有计划”;整个社会为什么存在“最大的浪费”?因为整个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的竞争状态。即使在今天,断言“无政府状态已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恐怕也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正如当代英国著名学者梅扎罗斯(I.Meszaros)强调:“资本的盲目扩张驱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不会放弃自身的本性,不会在全球范围内采纳与合理限制的必然性相符的生产实践”。[16]
此外,胡先生把“均衡”和“非均衡”都看作是市场经济中比肩并行的规律,我认为,这种不分主次、模棱两可的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不然。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的宋小川说得好:“均衡只是一个特例,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况’,是由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过渡的一瞬。均衡是暂时的,不均衡是永恒的。……非均衡是个大量、普遍的现象,市场买卖活动在不均衡的情况下进行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7]
一般说来,任何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都是不均衡的经济。但是,产出大于投入还只是不均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因为,不均衡最终出现的充要条件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软肋。需求或市场从根本上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命脉,所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如果其产品没有足够的消费者,作一个世界最高效的生产者就毫无意义。”[18]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均衡的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的确有所增强,但把这种“增强”说成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这种“增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总体上的无政府状态。至于胡先生说:“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吧?既然波动“难免”,那么有谁能百分之百地打包票说“波动”就一定不会演变成“萧条”,甚至演变为“大萧条”呢?
五、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是劳动价值理论吗?
胡先生认为:“不能再以单一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谁创造价值,价值就归谁。我仍然坚信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真理,全部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但马克思始终把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分别开来,只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不承认劳动是财富创造的唯一要素。事实上,劳动要能创造价值,就必须同时创造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创造除了劳动之外还需要资本、土地等客观要素,没有这些非劳动要素的投入,劳动是无法创造价值的。也就是说,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它们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通过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帮助了劳动创造了价值,因此它们也要参与价值分配。马克思当时提出剩余价值的剥削理论,是有特定的社会背景的。”
胡先生说:“不能再以单一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言下之意,有人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这个人是谁呢?按胡文针对《资本论》的命题逻辑,这个人显然是指马克思。在树立了这个标靶之后,胡先生作了这样的论证:既然“参与使用价值创造的还有非劳动因素”,那么劳动就不能成为价值分配的唯一因素。我认为,胡先生的说法未免言不及义、文不对题:
(1)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价值的创造者(劳动者)就必然占有价值成果;相反,他总是不断强调: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生产成果的分配。换言之,劳动者固然“应当”占有其所创造的价值成果,但决定价值分配的现实依据并非劳动,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2)胡先生在这里的论点(价值分配)与论据(使用价值的生产)之间,缺乏逻辑关联。胡先生要论证的,原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到底是什么”?而拿出的证据却是“ABCD各因素”都参与了使用价值的创造。换言之,本来要证明的问题是“价值分配”,可是提供的证据却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把参与了使用价值的创造,作为参与价值分配的依据,这种广为流传的“要素价值论”是很肤浅的。如果“要素价值论”能够成立,那么自然力对财富创造的贡献就应当归自然力本身(比如土地、机器和资本),而不应当归资本家独占。显然,资本家之所以能独占自然力的贡献,并非在于“谁生产就应当归谁所有”,而是在于“谁投资就应当归谁所有”[19]——这是“要素所有权”的结果,而并非“要素价值论”的证明。
其实,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分配的依据并不是“谁创造,谁占有”,而是“谁投资,谁占有”。创造价值的,并不一定能占有或充分占有自己创造的价值;决定价值分配的是“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是参与使用价值创造的“功劳大小”。
至于胡先生说:“马克思当时提出剩余价值的剥削理论,是有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这个背景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难道换一个什么“不特殊背景”,马克思就不再承认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了吗?
六、今天已经没有剥夺者可剥夺了吗?
胡先生断言;“‘剥夺剥夺者’到今天,已经没有剥夺者可剥夺了。资本家的第一个资本是通过暴力手段从农民和殖民地那里剥夺而来的,以后不断扩大的财富是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资本家是剥夺者。于是无产者完全有理由通过革命手段把被剥夺的财产从资本家手里剥夺回来。这叫‘剥夺剥夺者’。现在大家确认按生产要素分配,正常情况下的分配所得就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剥夺者,也就不再存在‘剥夺——剥夺者’的问题。”。
胡先生完成了一个转换:在资本的本性并未改变的情况下,从承认原来的确“存在剥夺者”,摇身一变为现在“不存在剥夺者”——这真是一个惊险的跳跃。据我所知,但凡否定马克思剥削理论的人,其逻辑基本上都是这么一种理路:先肯定过去的资本家存在剥削,然后话锋一转,说:既然资本在今天已经“合理合法”了,那么剥削也就从此人间蒸发,不复存在。至于为什么“合理合法”是衡量剥削与否的标准,就能够令剥削者洗心革面,则讳莫如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合理合法”只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作为“事实判断”。换言之,“合理合法”属于“应当怎样”的问题,而“有无剥削”则属于“是什么”的问题,不能把前者作为后者是否存在的证明。至于胡先生断言今天“已经没有剥夺者可剥夺了”,对于这种类似于“历史终结论”的如此乐观的预期,我认为并不是可以凭愿望、意志就能让人们坚信不疑的。如果“合理合法”并不是剥削是否存在的衡量标准,那么,要断言现在已经“不存在剥夺者”,就还得提供另外的证据。在我看来,“合理合法”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动态的范畴,过去“合理合法”,现在未必“合理合法”;现在“合理合法”,将来未必就“合理合法”。把现在“合理合法”的事物绝对化、永恒化,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美国著名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在苏联解体后,曾乐观地预言“历史已经终结”。然而时隔不久,他对自己的预言又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最近,福山悲观地说:“我错了”,我是一名“叛徒”,现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②。看看福山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之否定”吧,或许我们能从中感悟到一些什么。好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别急着给《资本论》下“病危通知书”,让历史来评判《资本论》吧!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收稿日期:2008-05-10
注释:
①胡先生用“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取代“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恐怕未必确切。
②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6年3月19日,转引自卫建林:《世界向何处去?——卫建林同志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第1-14页。
标签:资本论论文; 相对剩余价值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