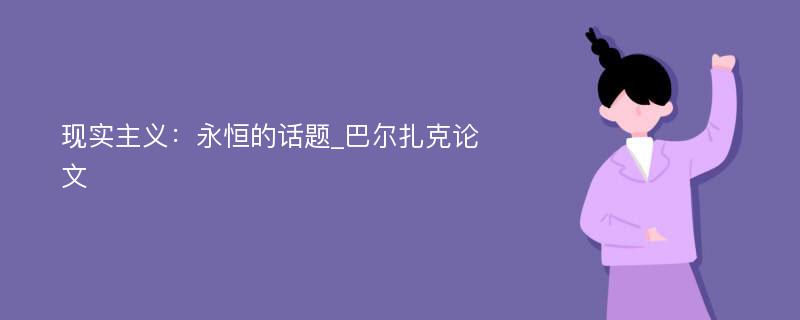
现实主义:永恒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东来,关于现实主义的议论趋于沉寂。近年来有人针对当前的文艺现状提出现实主义重构论,或者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论,是一个有深沉的理论意蕴的话题。笔者十余年前曾经写过一篇现实主义专论,把它定位在“一个艺术哲学原理”(《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至今, 我仍然认为提“重构”或“深化”,不应只是“创作方法”的回归,而应是对一种创作精神或美学原则,即对一种艺术哲学的重新探讨。因为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方法或“创作方法”(某种配方和操作程序),而是一种艺术哲学(创作精神与美学原则)。
从形而下的具体分析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思维,那么,现实主义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一个冷凝的但曾是热门的话题
现实主义是一个冷凝了的但曾是相当热门的话题。近十余年来,由于国门开放,诞生于本世纪的各种西方思潮涌来,文艺理论批评话语不断翻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理论批评话语,似已悄然退出批评话语场。那末在今天后现代语境中重提前现代的这个语符或语码(code这个词的第一义),是否不识时务?我认为理论命题的探讨与服装行业的趋时不可同日而语,其理由是:从地域上看,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入后现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模式;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刚刚进入这个过程,离后现代还相当遥远。从时序上看,历史的发展有其继承性,文学艺术的发展更有其自律性。文学艺术的历史是一个循着自己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文学的“法则”(code这个词的又一义),不是一朝一代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任意变更的。
“现实主义”作为新的艺术流派的名称,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艺术界。中国文人尝试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艺术观念来解释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艺术现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说中国文人探讨了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问题,此话并不过分。回眸本世纪初,接触西方思想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已把“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介绍到了中国。梁启超(1873—1929)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文中说:人常不满足于现实境界而欲感受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则理想派小说尚焉”;人怀抱之想象、经历之境界往往习而不察,故“欲摹写其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这大约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的最早的中文表述。
稍后,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1908?1910?)第二则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写实主义”是realism最早的中文译名,即“现实主义”。 近四十年来,文艺界常有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讨论,说句戏言,这“两结合”的发明权,在中国实在应当归在王国维名下。
西方吹来一股清新的风。西方艺术观念的导入,使中国原来关于诗文的模糊、朦胧、迷离的感悟式点评,顿时显出窘态和局促。于是,中国文论家们渐渐学会运用一套可操作的简明精确的批评话语,来观察和分析中国两千余年的文学和艺术现象。
中国人探讨了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但是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压倒一切话语的“最强音”,则主要是在本世纪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如果说中国人在本世纪初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现实主义”艺术观念,那末三十年代又再度从北方二度引进了“现实主义”观念。这第二次引进,在作为艺术观念的“现实主义”前面加了一个政治概念,即“社会主义”。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前苏联形成并定型。1934年8、9月间,前苏联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不仅把它定为创作方法,而且同时也成了批评方法(?)。所以,这二度引进的“现实主义”创作与批评方法,就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不再纯然是一个艺术观念了。
五十年代,就现实主义探讨而言,在中国是颇具戏剧性的。
五十年代前期,由于前苏联领导层的变更,文学艺术领域出现“解冻”。就艺术理论而言,提出了一个宽泛的“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西蒙诺夫)。五十年代,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苏联的年代。中期,中国文人相应地提出一条“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思路(何直即秦兆阳)。这是一种试图使现实主义复归本义的努力。但是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中国特有的社会景观,现实主义理论被推到了至尊的地位。茅盾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夜读偶记·后记》。1959年10月)一文中提出了这个绝对化的模式,他欣慰地看到在这个理论模式影响下,极短的时间内集体写成了一批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五五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中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及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这真可谓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大跃进”群众运动。颇为壮观,烈烈轰轰;也甚为滑稽,空空洞洞。而指导这场文学研究群众运动的基本的文学观念,就是被推上了独尊皇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成了一个好斗的排他性的理论观念。“开放”的大门很快关闭了,“广阔”的道路愈走愈窄了。这大约是当年开始形成的斗争哲学在文学理论上的套用或移用。
“现实主义”,一个艺术观念从幽远的历史中走来,与中国当时现实的政治运作相结合,渐渐偏离了艺术理论的正道。作为一个艺术观念的现实主义理论探讨,焉能不趋于沉寂?!
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僵化了因而沉寂了,固化了因而冷凝了。整个六十与七十年代,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这个理论命题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与讨论。对于整个美学和文艺学领域,那是一个沉闷而寂寥的荒芜年代。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似乎总是与中国政治的命运休戚相关。七十年代末,中国政治家重新面对中国的现实与世界的现实,采取了开明的现实主义政治态度,中国开始了又一个新的时代。而就文学艺术而言,则是一个准确含义上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文学重新面对现实,写出了一批虽然稚嫩艺术上远非成熟但思想上已显新意的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赞誉。于是八十年代初,文艺理论界重新开始了关于现实主义艺术观念的探讨。我在那篇现实主义专论中曾明确提出:十九世纪,确曾出现过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个壮大的现实主义艺术流派、一种几近定型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态。那是上世纪的文艺景观。本世纪呢?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理论各异,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哲学原理,即作为一个艺术原则、一条美学原理、一股创作倾向,那末起源于上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念是唯一正确地解决了艺术与现实之审美关系的哲学概括,“现实主义艺术哲学有永恒真理的价值”。但是,我认为这种艺术哲学不是一件排他的好斗的“理论武器”,“一部世界艺术史或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可能是什么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现实主义艺术哲学的兼容的气量与亲和的脾性,使它能够“不断吸收、容纳、消化其他各种艺术思潮、流派和理论探索中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涵量,以不断扩大、开拓和增强艺术反映现实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七十年代末,“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总体目标再一次郑重地提出来时,文艺界曾有人(徐迟?)试图提出“文艺现代化”与之相适应。以文艺现代化促进社会现代化?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了。“现代主义”呢?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时序上是同步的,但仅仅在时序上;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对应关系。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艺术思潮(主要在于表现方法)、文化思潮、社会思潮,不论是哪一个流派(未来主义似乎例外),是一股人文思潮,总体上是对于失落的人文家园的回眸与眷恋,因而本质上倒是反现代的。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近年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评介与引进,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思潮的灵敏的反映与反应,并不是什么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这个物质进程的“必然产物”——虽然时序上又几乎是同步的。现代化(工业化、科技化)是一个物质文明进程(“文明”,对应于技术体系),而并不是一个文化进程(“文化”,对应于价值体系)。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它离不开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本民族原有的意义体系。中国文艺界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理论上的研究与探讨,使人们大开眼界。就创作领域而言,对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模仿与借鉴,或可概括为先锋文学和前卫艺术,那也是从西天飘来的彩色的云,光彩炫目;但总是不若地下喷涌的丰沛的泉,沁人心脾。评介、探讨,模仿、借鉴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切不可忘了脚下民族文化的底基与底蕴。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涌进国门,文艺批评话语不断翻新,此时,诞生于上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念遭到冷落,甚至奚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进入了第二个沉寂期。如果说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沉寂期是由于把现实主义艺术观念抬到了至高至尊的地位,由于把它作为一个排他性的艺术观念而作了过度政治化的阐释;那末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第二个沉寂期,则是由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过度迷恋造成的自主意识的失落。今天重提现实主义话题,不仅是针对文艺创作现状这个一时一地的现实,而且应当把它作为一个纯然的艺术观念,探讨它的产生背景和哲学意蕴。
一个艺术的却有着科学背景的话题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观念、一个批评术语之所以议论蜂起,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前面总是连带着修饰语,就如同它总是戴着一顶帽沿下垂的帽子,使人难见其真实面孔。格兰特在《现实主义》这本批评术语小册子里开篇就指出:“现实主义”,是批评术语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最为奇特的一种”。而且这个术语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吸收修饰语以提供辅助语意的倾向”。我们见到的“现实主义”,几乎都是带着修饰语即戴了帽子的现实主义,格兰特按字母顺序排列,从批判现实主义(eritical realism)到梦幻现实主义 ( visionary realism),轻易地排出了25种带帽子的“现实主义”。这25 种现实主义中,还不包括他下面接着提到的“田园现实主义”、“唯灵论现实主义”、“自我内心深处的现实主义”和“大都会现实主义”等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为了追溯这个术语的本源和探讨本义,我认为把它前面的修饰语即头上所戴的帽子统统脱掉,才能见到现实主义的庐山真面目。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出现于文艺思想史,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指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可以确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时期。这个论断是准确的。以文化社会学观点研究欧洲主要是英国小说起源的瓦特同样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术语,与法国的一个艺术流派有关,“‘现实主义’一词首次公开使用是1835年,它被作为一种美学表达方式,指称伦勃朗绘画的‘人的真实’……”(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 页)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为这个新出现的艺术流派正式命名并形成一种新颖的艺术理论,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1850年,当批判现实主义高潮已开始消退的时候,法国小说家向佛洛里(1821—1869)才初次用“现实主义”来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其后,与向佛洛里站在同一艺术立场的迪朗蒂(1833—1880)与人合作,于1856—1857年创办了《现实主义》月刊,仅出六期就停刊了。向佛洛里于1857年出版了名为《现实主义》的论文集,可谓现实主义宣言书。(参看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5—356页。2、 郭华榕:《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7—90页)至此,“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新异的艺术流派和一种新颖的文艺理论,登上了文艺思想史的舞台。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为什么出现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文艺界?过去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作过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社会学的角度固然重要,但科学的理性文化对艺术的审美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应忽视。我倒认为,研究十九世纪科学的理性文化对艺术的审美文化的影响,对于说清楚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之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兴起,有更为确凿的证据。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有一个科学背景。十多年前,我在那篇专论中曾经指出:“十九世纪的实验自然科学给予文艺创作以现实主义的影响。”当时因为限于篇幅,未曾展开。后来,我发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正是促成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形成的直接原因: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其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曾经极大地影响和规约过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艺术创造灵性和艺术操作行为。就这一视角,我曾力所能及地作过较为详细的考释,撰写过《现实主义的科学背景》一文(《文论报》,1993年12月11日)。后来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我更加确信:正是十九世纪的科学成就促成了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降生。
十九世纪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最有代表性的科学进展,无疑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科学发现,即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这三大科学发现都出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参看徐纪敏:《科学美学思想史》第八、九章)。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取得的科学进展,极大地震撼并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罗素在研究上世纪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洲思潮)的时候认为:十九世纪的精神生活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都要复杂,原因之一是“从十七世纪以来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学,取得了胜利”。尤其是生物学,“生物学的威信促使思想受到科学影响的人们不把机械论的范畴而把生物学的范畴应用到世界上”(罗素:《西方哲学史·从卢梭到现代》)。
这就是十九世纪的简明的科学背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以及通过深受科学影响的社会思潮,或者统称为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的精神家园,催生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艺术流派的诞生。通常认为,现实主义在欧洲是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的,其脚印亦甚为清晰: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斯汤达尔的《红与黑》(1830),英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俄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836)。法国是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策源地,所以还应当提到斯汤达尔的《巴尔玛修道院》(1839)、欧仁·苏(1804—1857)的《巴黎的秘密》(1842—1843)和福楼拜(1821—1880)的《包法利夫人》(1851—1856)等等。
这一张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与艺术流派孕育与成熟的简明时间表,与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时间几近同步,它们都形成和定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实属必然。科学探索、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影响和渗透了作家艺术家的精神生活,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一个壮大的现实主义艺术流派,应当说这是当时欧洲复杂的精神生活中的正常现象。
如果说这种从宏观角度论说十九世纪中叶三大科学发现与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亲缘关系甚为粗疏,尚属揣测与推断,那末从微观即从当时法国三位现实主义大师的个案,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对他们的创作灵性、审美情趣乃至艺术操作行为的影响。
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雄心勃勃,声称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要用笔来完成。他认为法国社会是位历史家,他要做书记,用他的笔描绘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图卷。1834年,他计划写作一整套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包括已发表的小说,总计137部长篇。1841年, 他统称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为“人间喜剧”。第二年他在总序中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从中不难看出他受同时代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1769—1832)和圣提雷尔(一译圣伊莱尔,1772—1844)“统一图案”(或称“原始图案”)理论的影响。圣提雷尔认为,“自然界按照一个图案创造了一切的生物,这是一个在原则上相同,但在细节上变化无穷的图案”(转引自林德宏:《科学思想史》第199页)。大自然千差万别,有无“统一图案”先在? 这是十七、十八世纪生物分类学诞生以后即引起争论的问题。巴尔扎克曾经关注过生物学界就“统一图案”问题的长期争论。他说在他关注生物学上的这场争论之前,“统一图案”学说“已经深入我心,我曾注意到,在这一点上,社会和自然相似”。巴尔扎克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作了比较,认为社会上有士兵、工人、行政人员、律师、有闲者、科学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人和教士各色人等,就如同动物界有狼、狮子、驴、乌鸦、鲨鱼、海豹和绵羊等各种动物一样。“贝丰(一译布丰)想写一部书讲述全体动物,他完成了一部卓越的著作(指《自然史》),我们不是也该替社会写一部这类的作品吗?”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撰写着他的法国“社会史”。当然,作为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不可能不看到社会与自然的区别:“社会环境有一些自然界不许有的偶变,因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
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巴尔扎克以他的热忱和执着投入这一描摹法兰西风俗史的过于庞大的工程,终于完成了“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间生活”等等场景的摹写,他自称“在这六个部分里胪列着构成这个社会的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我们的祖先也许会说,这是这个社会全部事实和功业的集成”。
巴尔扎克在实施他的伟大工程的时候,遵循的艺术原则只有一条:“只要严格模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
巴尔扎克完成了他为自己定下的历史使命,用他的笔征服了世界,完成了一部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现实主义历史图卷。恩格斯在上世纪末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几乎与他的自我评价相同:巴尔扎克是位“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1888)
巴尔扎克1841年产生“人间喜剧”这个宏大的艺术构想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呢?当他这个想法在脑海里还像是一个美梦、一个幻想的时候,这个美妙的梦幻就对他发号施令,具有束缚力和驱动力,“非听从它不可”了。巴尔扎克追溯了这个梦幻而实在是庞大的系统工程的最初的动因:
这个意思的起因是人类和动物的一次比较。
(“人间喜剧”前言。1842)
另一位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对于社会的看法,他的文学主张,与巴尔扎克的生物学眼光颇为相似。普列汉诺夫对文学作过卓越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他在谈到福楼拜的时候,却看到了福楼拜受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影响。普列汉诺夫说:福楼拜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他作品中的人物,对于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福楼拜说:“对待人的态度应该像对待剑齿象或鳄鱼一样,难道可以因为前者的角和后者的颚骨而感到愤慨吗?把他们展示出来,拿它们制成标本,放在酒精瓶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一切。”普列汉诺夫据此指出:“福楼拜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他所描写的社会环境,正如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样。”(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
左拉(1840—1902)被称为自然主义的宗师。自然主义直承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变种,或者说现实主义的极致,现实主义的僵化和异化。朱光潜曾经提及,法国人总是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夏勒伊在《艺术与美》一书中说:“现实主义,有时也叫做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摹仿自然为目的。”同时,在法国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哲学和美学基础都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丹纳根据实证主义发展出来的美学观点(《西方美学史》)。英国人,也常常以“现实主义”翻译“自然主义”;欧洲其他国家,通常也认为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提并论是合理的。(参看《现实主义》第42页)
左拉研究过巴尔扎克,认为“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了”,“作家和科学家的任务一直是相同的”,都是回到自然,进行实验(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在《实验小说》一文中,左拉认为巴尔扎克不满足于对搜集的事实进行摄影,而是要实验,《贝姨》“只是小说家在观众眼前所作的一份实验报告而已”。左拉把法国生理学家伯纳德(1813—1878)发表于1865年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已有中译本)作为他的思想和创作的指导和向导;在伯纳德的《导论》中,左拉发现他关于文学的整个思想都已被论述过了,因此他“打算在所有论点上都以伯纳德的战壕来保卫自己”。左拉声称,伯纳德的实验方法既然被应用于化学和物理学中以研究无生物,也被应用于生理学和医学中以研究生物,那末实验方法同样可以被应用于文学方面:“如果实验方法可以获致物质生活的知识,它也应当获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方面的知识……。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实验小说就是目标。”(左拉:《实验小说》)
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的同胞,写过左拉传记的法国作家巴比塞(1873—1935)也看到了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左拉创作的直接影响,他说:“作为一个笃信真正的实验科学、实证科学的时代的儿子,左拉比巴尔扎克或福楼拜更自觉地向自己提出一项任务,那便是使文艺通过仿效科学方法的途径,来为客观地认识社会这一目的服务。”(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59页)
是的,这是一个实验科学、实证科学的时代。那末为什么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首先出现呢?英国十八世纪就孕育并诞生过笛福(约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理查逊(1689—1761)的《帕美拉》和菲尔丁(1707—1750)的《汤姆·琼斯》等等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小说”(novel,这个词的本义是新颖、新异, 用以标示这种新的文体,以区别于原有的“散文虚构故事”—fiction )(《小说的兴起》第2页)。在经济领域, 英国还领导过两次工业革命。为什么是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率先在艺术领域里举起现实主义的旗帜呢?这仍然要从科学背景,即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影响方面去寻找原因。
整个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与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家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进展有关,这里开出一份清单:居维叶的《比较解剖讲义》第6卷(1805)、 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和伽尔·施布尔茨哈伊姆的《关于神经系统的研究》(1809)、居维叶的《关于四脚兽骨化石的研究》(1812)、 拉马克的《无脊椎动物志》(1815)、马兼迪的《脊髓神经元的作用》(1822),杜特洛谢弄清楚了植物是由细胞构成的(1824)、居维叶和圣提雷尔围绕动物“统一图案”在科学院的争论和圣提雷尔的《动物哲学原理》(1830)等等。(伊东俊太郎等编:《简明世界科学技术史年表》第86—92页)法国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的诞生,无疑与当时法国生物学界的这些成就有着某种内在的血缘关系。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比如英国成了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策源地?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法国十八世纪后半叶和十九世纪前半叶那浓郁的科学创造氛围,孕育并促成了这个艺术思潮和流派的降生。就重大科学成就而言,从1751年到1800年,英国是37项而法国是54项;从1801年到1851年,英国是92项而法国是144项。(《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页)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与流派酝酿成熟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在重大科学成就方面,法国都领先于领导过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英国。
因而,现实主义是一个艺术的却有着科学背景的话题。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是历史的书记员,这是文学研究的第一视角。这种从外部原因寻找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努力,一度被称之为外部研究。文学艺术是艺术创造系统自身延续和演变的结果,思潮和流派均有其继承和新变,这是文学研究的第二视角。这种从内部原因寻找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研究,一度被称之为内部研究。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每一时代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乃至科学方法论,对作家艺术家同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文化现象早已显现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内;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中却没有任何反映和反应,这是研究者视而不见的一个“盲区”。科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我称之为第三视角。因为是不同创造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可权且称之为“中部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将愈来愈扮演重要的角色,科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也应当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对象、研究的内容。
一个现世的实在是永恒的话题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坛出现诸多与现实主义迥然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最初的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也曾试图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中找出他们理论的科学依据。本世纪初科学失去了古典物理学的现实主义,现代科学提供的世界图景已不再是上世纪实验自然科学所面对的清晰可辨的经验世界,“现代艺术和现代科学,二者都同时诞生在本世纪最初十年期间。同过去的时代相比,这二者都失去了它们表现手段的直观明确性。”“量子力学的主—客体问题,就对现代艺术许多流派的信徒们提出了一个直接的要求。立体主义的理论家们常常把立体主义的风格同相对论的空间—时间观念联系在一起……”(L.舍费尔:《自然科学与人的价值》。《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0期)但是与上世纪不同,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理论家们并不执着于科学,他们需要一个能够解释变幻莫测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甚至根本无法说清的许多艺术现象的总体理论。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弗洛伊德(1856—1939)通过对梦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他的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释梦》(1900),标志着这个理论的诞生。所以,潜意识理论与二十世纪同龄,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潜意识理论是一个科学假说,这个假说不仅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其影响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也都是不可估量的。弗洛伊德曾经相当自负地说,他的潜意识理论标志着世界和科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可以向你们担保,只要认识潜意识的过程,你们就已经为世界和科学的一个决定性的新倾向铺平了道路。”二十世纪是属于弗洛伊德的?与十九世纪冯德(1832—1920)创立实验心理学相比,应当说潜意识理论是心理科学的一个巨大的进展。二十年代初就有人认为:冯德的影响在过去一直是巨大的,而弗洛伊德却拥有一个巨大的现在,并且还将拥有一个更加巨大的未来。潜意识理论从心理学通向社会学、人类学,进而影响人文领域的文学艺术,是一条畅通的路。“向内转”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理论家们求助于弗洛伊德,真可谓得其所哉了。
“现代主义”,虽不确切但仍然大体上可以用它来概括本世纪的西方文艺思潮与文学运动。就文学角度而言,较为准确的说法,是指1880—1930年间在西方文坛上出现的诸多流派,“它们包括始自象征主义的一系列文学运动:后期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旋涡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其经典作品出现于二、 三十年代。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反传统”,反对现实主义传统。现代主义诸流派把视线从社会现实转向心灵世界,即“向内转”,标榜表现自我,追求新颖的新异的表达方式。这里列举几个流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向内转”这个基本倾向。
象征主义宣言发表于1886年,认为诗歌的目的在暗示“另一个世界”,主张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象征主义主将韩波(1854—1891)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诗人的首要任务是“认识自我”,探索自己的灵魂。表现主义盛极于二、三十年代,以德国为主,主要成就在戏剧。表现主义者主张表现自我,认为“自我”是宇宙的中心和真实的源泉,“现实必须由我们创造出来”;认为艺术创造过程就是表现内心世界的过程,是“从内向外”而不是“从外向内”。意识流小说是诗歌象征主义在小说中的发展,深受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亨利·詹姆斯(1843—1916)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不无道理。意识流小说的特征是以流水般的回忆、联想和梦幻勾勒出人物的下意识轨迹;名列这个流派榜首的经典之作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追忆逝水年华》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1882—1941)的《尤利西斯》(参看《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思潮·西方现代派文学》)。超现实主义在二十年代的西欧兴起,法国作家布勒东(1896—1966)是其代言人,他宣扬“下意识的写作经验”。1920年,布勒东在维也纳会见过弗洛伊德;1924年,他写《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宣言》中称他潜心研究过弗洛伊德,对他的精神分析方法也已入门。布勒东试图“一劳永逸”地给超现实主义下个定义:“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学自发现象,主张通过这种方法,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 页)这是现代主义诸流派中向内转,乃至转向潜意识层次去反映主体世界的最为典型的表述。
“向内转”,现代主义以心灵取代了现实,以主观取代了客观,终于取代了现实主义。这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一种大调整,诚如韦勒克所说:当这一调整业已完成,批评家可以宣称内在的意识流是唯一的现实主义方法,因而“主观经验……是唯一的客观经验”之时,“公认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意义就翻了个个儿。”(《现实主义》第65页)
“翻了个个儿”,还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还是挣不脱主体与客体的正常关系。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艺术哲学问题。两个问题在进行哲学思考时,可以贯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其哲学层次上的表述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终极关系。认真研究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历史,都会发现它与哲学思潮的姻缘关系。格兰特认为要弄清“现实主义”的意义,必须追溯到哲学,其结论是“‘现实主义’是从哲学借来的批评术语”;从时序上看,它刚好与同时期的积极进取的“唯物主义”结伴而行(《现实主义》第5页)。瓦特也认为, 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对于小说具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具体化的对应关系,而在于“现实主义思潮的总体特征”。这种“现代现实主义”自笛卡尔以降就产生了,这种思潮认为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笛卡尔和罗素,曾经被我们的两分法、营垒说划入二元论、唯心主义;但是从思潮史的角度看,瓦特却把笛卡尔赞为“现代哲学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把罗素誉为“当代哲学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小说的兴起》第340、337页)。由此我认为,把人类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仅仅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的哲学,是过于简单化了。
左拉在《共和国与文学》一文中认为:“在一切文学争论的根底,总有一个哲学问题。”(转引自《现实主义》第28页)就现实主义文学而言,文学作品与其摹仿的现实生活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实质,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小说的兴起》第4 页)而认识论说到底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现实主义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哲学?
十多年前,我在那篇专论中曾试图论证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哲学。从科学(包括人文科学)要求的精确用语而言,方法一词系指门路、程序(有密码吗?)、规则和技巧等等;文学艺术创作中并不存在可以标为“现实主义方法”的人人皆可操作的路数和规程。现实主义是一种哲学,说得准确些,是一种艺术哲学。最近发现,这个见解似乎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有人预见到了。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就曾担心这个术语可能被“凡夫俗子”所误解,第一个在自己的旗帜上书写“现实主义”字样的向佛洛里,就曾嘲笑过未来的现实主义者可能会把它当成“公式”:“我承认从未研究过包含这些规则的密码,依据这些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现实主义作品。”(转引自《现实主义》第29—30页)
现实主义首先是哲学,“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是现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所倡导的基本观念;“知觉”是主体与客体的接触、“反映”和组织,这里就有了两项,即“主体”与“客体”。哲学现实主义应当承认客体的先在性。文学现实主义同样承认社会生活的先在性,当作家艺术家切入生活(现实、“客体”)之前,生活(现实、“客体”)已先期契入了作家艺术家的心灵(意识、“主体”)。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不过是摹写现实,记述人类的普遍经验,并最终为人类普遍接受而已。
自有哲学以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现代哲学虽然倾注全力研究主体乃至转向语言;但即使是语言哲学,词语与现实的一致性命题也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果说十九世纪已经解决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即客体的先在性和主体的后生性问题,因而本世纪主要的智力努力集注于主体内部复杂状况的探寻,这也是正常的。艺术哲学与之相似,如果说上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与积极进取的哲学同步,解决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先在性与后生性问题;那末同样,本世纪的艺术创造侧重于心灵方面的探寻,也同样是正常的。我曾经把外部世界称之为“外宇宙”, 内部世界称之为“内宇宙” (《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内宇宙里有一片广阔、深邃和瑰丽的星空,这里即是本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家搜寻与探测的浩瀚无际的心灵空间。但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内宇宙不正是那外宇宙的倒影吗?
现代主义艺术深入到主体内部去探求,去表现;但是它并没有也无法回避与丢弃客体,只是暂时地(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上也可以称之为“暂时地”)遗忘罢了。主体与客体这两极,你可以强调这一极,也可以侧重那一极,但不应否定任何一极。瓦特认为笛卡尔提出的二元论命题,成了近三个世纪以来欧美思想界的一个中心课题。尽管二元论看待现实的方式会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导致任何对现实的全盘否定,不管是对自身的现实,还是外部世界的现实。同样,尽管不同的小说家分别对意识内部和外部的对象作了不同程度的强调,他们也从未完全否定过任何一方”。对于名列意识流小说榜首、本世纪上半叶极为重要的那两部作品如何评价?在我们的评介文字中,几乎都认为《追忆逝水年华》是表现沙龙主人公“潜意识”的成功之作,《尤利西斯》是以大量的内心独白表现“潜意识”的杰作,因而把它们看作表现“潜意识”的范本。普鲁斯特与乔伊斯遗忘了外部世界、否定了客体那一极吗?瓦特认为:《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内省的纪实小说”;“然而,这是一种将第三共和国的外部世界表现得如叙述者记忆中的内部世界一般生动的内省”。《尤利西斯》呢?“乔伊斯的在如此众多方面均为小说发展之顶峰的《尤利西斯》,在对二元的那两个方面的处理上无疑是登峰造极的:在它的最后两部中,对于莫莉·布卢姆的昼梦及她整理她丈夫抽屉场面的生动表现,乃是大胆地将叙述的方式调整到二元论的主、客观两极的真正的典范。”(《小说的兴起》第340—341页)这是迄今我所看到的对这两部小说的最为准确也最为深刻的评价。
对于现代主义诸艺术流派的创作论,一个相当流行的描述是说艺术家似精神病患者、艺术创作如白日梦。但是,这仅具有比喻的意味,不具备论证的价值。人到晚年更成熟。弗洛伊德晚年撰写自传的时候,已经清醒地看到他创立的潜意识理论用以解释文学艺术创造的限度。他认为艺术创造是在想象的王国里进行的,这里不同于现实的王国,如同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必须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能的需求,而不得不痛苦地从享乐主义原则退缩到现实主义原则。”在这个“避难所”里,“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艺术家毕竟不是与现实无法协调的精神病人,所以弗洛伊德说:“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艺术创作似“白日梦”:“他的创作,即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但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既懵懂又清醒,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从事创作,并时时意识到鉴赏者的眼睛,处处意识到审美规则的无形制约需自觉遵循,所以弗洛伊德说:“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梦的那种自恋性的、非社交性的产物不同的地方,是它们被安排去引起旁人的兴趣,并且还能引发满足读者自身的潜意识愿望;此外,他们还利用形式美的那种可感知的乐趣,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用他自己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艺术家、艺术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至少在他晚年看来,并没有越出现实主义理论的框架:“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寻找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及其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作时的思想和动机,换句话说,找出他们与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转引自高宣扬:《弗洛伊德传》第275—276页)弗洛伊德晚年用他自己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文学艺术创作,倒是与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相去不远。艺术能够被鉴赏者接受(主要是感受)、被理解(应当说感悟),或者说被“解读”,其原因就在于有“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真正的作家是为全人类写作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也就在于有“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
那位晚年自审时的弗洛伊德,似乎比那位早年创立科学假说时的弗洛伊德向后退了一步,但无疑更加成熟了。
现代主义诸流派,在艺术地表现世界的另一极即心灵世界方面,以新颖乃至怪异的方式作了许多尝试和探索。这种“向内转”的努力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二战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其研究旨趣转向语言,被称为支离破碎的语言玩弄。与本文论旨关系不大)。到七十年代末,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向外转”倾向。钱中文在《会当凌绝顶》一文中回眸了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趋势:解构主义者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1986)中已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文学理论研究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宣布1979年是欧美文艺理论大转折的一年。米勒说:“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转引自《文学评论》1996年第1 期)米勒所说的文学研究兴趣的转移,并非指研究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趣有所转移,其“所指”正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文学研究兴趣已经转移,其背景就是七十年代末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退潮。
文学艺术创作亦复如此,经过一个世纪在潜意识领域的探索和寻觅,各种表现手段都已经试验过了。探索者已经疲惫不堪,但那个被遗忘的一极依然存在。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应当运用语言的张力,透过语言的棱镜尽力逮住、折射流速极快的生活之流。西方的电影艺术界的注意力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大转移的趋势。前些年,我国一些年轻导演在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一些“怀旧”题材在国外电影界引起轰动;但是长此以往,显然使国外影评界感到似曾相识,无甚新意。重复使人感到疲劳,疲劳令人产生厌倦。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蓬特卡罗认为中国确有“世界级”、“大师级”导演,但他们老是拨弄“古董”,显然是浪费才华,“因为主宰当今国际影坛的已不再是‘怀旧’题材,世界各国的电影精英都在全力关注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大到政治风波,小到凡人琐事,无不体现着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见《南国早报》1996年8月3日)这显然并非出于商业动机,也不是人为的“规划”和“调整”,而是艺术规律即电影艺术自身发展的大势所趋。
“向内转”,“向外转”。但是“向内转”时不要忘了有个外(宇宙),“向外转”时不要忘了有个内(宇宙)。十九世纪是“写什么”?二十世纪是“怎么写”?我看没有这么简单。不论“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一个“写”字就把主体与客体连接起来了。所以不管你叫它什么,艺术总是离不开一个恼人的东西:生活、社会、历史,或者叫它现实。真正的文学艺术杰作,它不仅仅是历史的形象画廊;也应当是地域的风俗史;而且是民族的心灵史,同时也是人类的心灵史。
世间的一切在时间的湍流之中变动不居,作家艺术家应当忠于现实。现实,面前波澜壮阔汹涌奔腾的河床,以及遥远的朦胧迷离的上游——历史,乃是上帝,作家艺术家都是它的仆役:它的书记,它的长工。
国外一位作家在他的刊物的终刊号上宣告:“现实主义已经死去了,现实主义万岁!”(《现实主义》第68页)这是对于近150 年来围绕现实主义理论论争的最为精当的总结:就形而下的意义而言,作为一股文艺思潮、一个艺术流派、一场文学运动,它于上世纪末已经死了;就形而上的意义而言,作为一条美学原理、一类创作精神、一种艺术哲学,它将永生。
现实主义死了,现实主义万岁!
标签:巴尔扎克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艺论文; 社会论文; 艺术流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