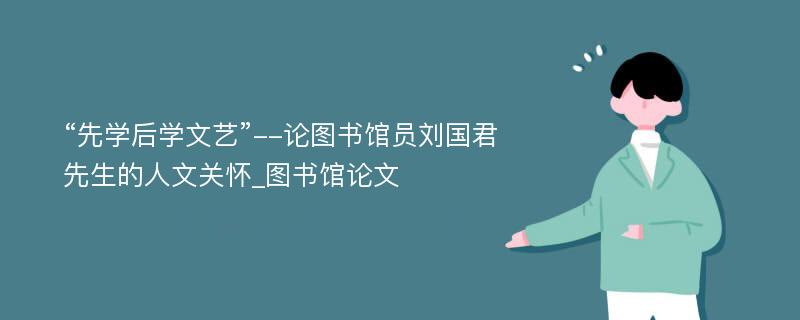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略论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刘国钧先生的人文眷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学家论文,文艺论文,人文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刘国钧先生(1899.11.15-1980.6.27)是一位略可比于美国“图书馆学之父”M·杜威和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的人物。历史成全着值得成全的人,他的人生步伐大体合着历史的步伐:他出生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轫期,他的处女作《近代图书馆之性质》(1919)的发表也正值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之滥觞;他没有辜负历史,在80余年的人生和60余年的图书馆事业生涯中,他把自己成就为卓越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富于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家。
在刘国钧先生诞辰100周年前后,国内图书馆学界对其事业践履和学术造诣已作了多方面的介绍和探讨,这里再度撰文是想从这位杰出前辈的生平、事业和学问、著述中揭示一种人文精神——以这种精神作一种策励或勖勉,也许对于处在急功近利时潮下的图书馆事业界和图书馆学界不无裨益。
1 刘国钧先生的人文教养
凡在图书馆史和图书馆事业史上成一大家的人物,都不是那些囿于一时功利或蔽于一技所长之辈。著名的古代西方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历任馆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中国古代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是历时两千余年而依然不无生机的道家学说的始祖。法国、德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先驱G·诺德、G·W·莱布尼茨是历史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中国最早的目录学家刘向、刘歆也都是学养深厚的经学家、文学家。一如历史上的先贤,刘国钧作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领域的大师有着丰赡的人文教养和真率的人文胸怀。
刘国钧早年留学美国,在他学成归国时不仅以优异成绩获得威斯康辛图书馆学院毕业文凭,而且取得了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他对近代西方学术中有价值的东西孜孜以求,却从未忘怀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热衷于科学方法的研讨和引进,但又总能够赋予科学方法以人文的灵魂。他写过许多富有实证性和实用价值的有关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论著,他也写诸如《两汉时代道教概况》(1931)、《老子王弼注校记》(1933)、《老子神话考略》(1935)、《曹操与其时代的思想》(1940)、《历史哲学之需要》(1941)、《建安时代之政治思想》、《建安时代之人生观》(1941)、《人文教育之精神》(1942)、《改进高等教育管见》(1942)、《史地教育与精神国防》(1942)、《中国文化之发展》(1942)等文字。他显然对老子学说和魏晋时代的玄学情有独钟,但对古籍的研究却是为了今日“中国文化的发展”。魏晋时代战乱频仍、政治险恶,然而也因此刺激了那个时代的士人的思想解放。刘国钧先生思古而忧今,其心志所寄固在于国家的治乱,而思想自由、学术进取也当是其希望所在。
处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刘国钧先生倡说“精神国防”,出于对民族灵魂陶冶的关注,他分外看重旨在培养人文精神的文科教育。他指出:
“文科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学术的进步,知识的扩展,精神的修养,文化的创造。它的成就是理论的,无形的,人品的,而不是实利的。……文史哲三门都是民族精神的源泉,一国文化的精华。要了解一国的文化或其人民之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理想,经济机构,以及做人的标准,行为的目的,都得取径于此。”[1]
“人文科学重在指示人生道路和目的。这就是古人所谓‘器识’。‘器识’是指人之胸襟怀抱而言,抱负要远大,胸襟要宏阔。古代的教育最注重养成这种人生态度。所以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文科教育的基本精神。器识是人格的中心,培养一种抱负远大、器宇宏阔的人格,乃是文科教育的理想。”[2]
刘国钧先生一生致力最多、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然而正如他所引古人之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他是把“抱负远大、器宇宏阔的人格”的陶炼放在具体的事业和学术研究之先的,而且,正因为他能够做到“先器识而后文艺”,因而带着非同寻常的人文教养从事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才得以使自己成为一位非同寻常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图书馆学家。他信从西哲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格言,但也有着清醒的人文意识——他认为,“力量应当做理性的工具,不当成为人生的主宰和目标。”[3]
2 一种富于人文关切的图书馆观
早在1921年发表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刘国钧先生就曾指出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可用“自动”、“社会化”、“平民化”三语概括,并强调说:“近日图书馆之事业多半为社会化之性质。即其注重之对象已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役之人。”[4]13年后他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再次指出:“现代图书馆所注重的对象,已由书籍变为它所服事的人;它的兴趣已由静止保全图书变成活动的指导人们阅览图书了。”[5]
这个说法是他在比较近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的异同时提出的,从中可以把握他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总的看法,即他的图书馆观或图书馆事业观。“人”是这一图书馆观的中心词,“服事”人的真切内涵是教育人——让阅读图书馆书籍的人自己选择图书以依其资质、兴趣的方式教育自己。刘国钧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谈论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时就说过,图书馆优于学校教育的地方在于它让人“顺着个人才性读书”,并因此使人自觉地培养其“习惯和品格”、陶冶其“性情”、确立其“理想”。此后他多次称图书馆为“一种教育的利器”、“一直接之教育机关”。他以赞赏的口吻说:“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公共图书馆者,公共教育制度之一部也。”[6]为他所赞赏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精神,其实正是他所认同的一般公共图书馆的精神。抓住这一精神方可理解刘国钧先生心目中的图书馆事业,也方可理解他心目中的图书馆学。
历来多有人把刘国钧先生所构想的图书馆学归结为所谓“要素说”,然而,真正说来,这归结并不确当。他的确曾就“图书馆成立的要素”论说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他从图书、人生、设备、方法、等四方面说图书馆的要素,后来又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把先前所说的四要素更准确地表达为五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和设备,(5)作法。不过,无论是四要素,还是五要素,刘国钧先生谈“要素”的前提都在于把图书馆看作有一种“精神”贯注其中的整体。分析图书馆的“要素”并不是要孤立地对待每一要素,而是要说明“图书馆学乃是一门包含着许多科目的科学”,它因这些相互关联的科目而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他没有忘记:“图书馆学有其实践的目的——改变现实使它更合于人们的理想。它企图改造的现实乃是人们的文化生活、人们的思想、知识、技能,乃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现象。”[7]
刘国钧先生没有就此展开作更多的论说,但没有问题的是,他所说的“改变现实”,并非由图书馆或图书馆活动直接作“改变现实”的主体,而是图书馆活动和图书馆学是通过对“人”的改变而去改变现实的,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教育和影响“人”,这是图书馆活动和图书馆学的职分所在,也是其灵魂或精神之底蕴所在。此外,“改变现实”是要“使它更合于人们的理想”,而“理想”则涉及人生的价值取向,涉及某种终极意味上的人文眷注。这些意味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却已蕴含在已经说出来的那些话语中。
3 一种贯穿人文意识的图书分类探索
在与图书馆事业诸要素相应的图书馆学诸科目中,图书分类是刘国钧先生着力最多的科目。诚如刘先生所言,“盖分类法者图书馆之一工具耳”。[8]然而,尽管如此,他对这一工具的探索依然带有清醒的人文意识。
1929年,刘国钧先生积数年之研究,出版了自己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他提出,完整的分类法应由四部分构成:分类表、理论的基础、索引和分类条例。其中,以分类表最为重要。这部分类法——改传统的以题裁为主的分类为学科或理论为主的分类,将书籍分为十大类:总部(目录图书之学)、哲学部、宗教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历史地理部(中国)、历史地理部(世界)、语言文学部、美术部(艺术)。其体制虽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布朗的“主题图书分类法”有所参考,而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和杜威的“十进分类法”的参考尤为突出,但毕竟自成一系统。最可注意的是刘国钧在分类法的导言中提到的图书分类原则,其首要原则即是:“分类表对于任何书籍,均当有收入之可能。是以类目宜丰富。对于任何科目,不宜有所轩轾。是以类目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9]
这一原则初看上去似乎在淡化书籍评判选择上的人文倾向,而实则贯穿着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的人文意识。类目的全然形式化——不分轩轾,不寓褒贬,仅以学科类目所属为判——俨然是一种对图书内容漠不关心的姿态,但在这不关心里却蕴含了一种事关民族乃至人类文化、思想、学术事业的大的关心。图书馆不是说教的机构,它不刻意对图书作评判和以此对读者作引导,本身即在终极的意义上体现了对读者的鉴别力的信任和对读者“顺着个人才性读书”的尊重。“不宜有所轩轾”、“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的图书分类原则合于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也合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文价值取向,而对老子道论、魏晋玄学的欣赏和对五四新思潮的信奉,却正是刘国钧先生的人文教养的根底所在。有趣的是,在《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导言”中,刘国钧先生简述图书类目次第而及于“美术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文学之一要素曰美,而美非仅表现于文也。音乐、书画、建筑、雕刻、皆美术也。故总为一部而殿之以游艺,命为美术,盖人生之极境焉。”[10]
以“美”为价值追求的艺术被殿于诸类图书之后,却又予以“人生之极境”的评说,这同图书分类“不宜有所轩轾”、“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的分类原则似多少有所相违,但审美和艺术的超功利性也正意味着对陷于轩轾之分、褒贬之判的世俗目的的摆脱。“人生之极境”是一种人文评价,从这里可大略窥见刘国钧先生所企慕的人生境地。
1949年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一直在以政治为统帅的意识形态的统摄下,图书分类法受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极深。“不宜有所轩轾”、“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的图书分类原则显然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刘国钧先生被迫承认自己的图书分类思想为“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图书分类一直由切近于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主导其中,这期间出现的各种图书分类法无一例外地属于一级组织领导下的集体编制。对图书分类的这种形态作出较为允当的评价也许还有待历史的他日,但没有问题的是,对刘国钧先生说来,真正属于他自己个人独立编制的图书分类法却只有初版于1929年而在1936年出了修订版的那一部。
4 一种有着人文眼光的图书史观
图书研究是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他的中国图书史研究显得分外突出。他先后写过《可爱的中国书》(1952)、《中国书的故事》(1955)、《中国书史简编》(1958)、《中国的印刷》(1960)、《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等书,并在《光明日报》连载过《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1962.2)一文。这些著述中渗透着他的历史观念,也相当程度地透露着他的人文眼光。
刘国钧先生为图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11]这个定义涉及两个方面:就图书“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言,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图书不能不借助“文字或图画”、借助“一定形式的材料”而言,它是一种工艺产品。前者是图书的内容,后者是图书的形式。由“知识”说“文化”,这“知识”便是广义上的,它当然包括人的认识所得,但也不把人的情致、意志排除在外,刘国钧先生指出:“一定社会一定历史时代的图书必然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理想和希望。所以从一定的图书中可以认识一定的时代,而一定的图书出现之后也可以或多或少影响时代的发展进程。”[12]
这里所说的“态度”、“理想”和“希望”关联着人的信念、操守、心愿、信仰和情趣,不属于狭义的认识或知识范畴,而更大程度地取决于人文意义上的价值选择或价值取向。刘国钧先生虽然没有就此展开作较多的说明,但联系他40年代引用古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对“文科教育之精神”的论述,可以说,所谓“态度”、“理想”和“希望”都是被作为“器识”而非一般“知识”看待的。所以,他心目中的“图书”正如他心目中“时代的生活”是有着人文的切近感的,是不为狭隘的功利尺度所局限的。既然图书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工艺产品,那么,图书史的研究便应兼顾历史中出现的图书的内容和形式。刘国钧先生说,如果只注意图书的内容,历史地研究图书,所研究的就将是思想史、科学史;如果只注意图书的形式,所研究的又将是技术史、工艺史。真正的图书史的研究是把图书既作为文化现象又作为工艺产品的研究,因而是把图书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研究。就此他提出图书史的研究当有三项任务:其一是了解图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意义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由此以树立批判地对待文化遗产的观念;其二是了解各门类各学科的图书是怎样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分别产生出来的;其三是研究图书的四个构成因素——文字、材料、形态和制作方法的发生、发展过程,亦即研究书籍制度的发展过程。对书籍制度的沿革的考察,使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史研究有了一条较清晰的线索。在他看来:中国图书的材料、形态和制作方法“曾经起过几次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由于这两大发明,书籍材料和生产方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便使我国书籍制度的发展形成三大阶段——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叶制度。”[13]
以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为契机把中国书籍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这构成描述中国图书史变迁的一个大的轮廓。结合图书内容,整个中国图书的历史被划分为四个时期:(1)从远古到公元1世纪末(远古到东汉初年)造纸术发明之前的时期;(2)从公元2世纪到8世纪(东汉初年到唐代中叶)印刷术发明前的写本卷轴时期;(3)从9世纪到19世纪中叶(唐代末到晚清鸦片战争)印刷术发明后手工业印刷时期;(4)从19世纪中叶到当代的机械化印刷时期。对中国图书历史演变的这种划分,大体上是立足于书籍制度或图书的形式方面的,出自图书馆学的角度如此考察图书应当说顺理成章而无可非议。但在图书史的研究中,刘国钧先生毕竟没有忽视图书内容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微妙变化。例如他注意到,春秋中叶以前的文献“实质上都是档案,这和以教育当时和后世的人为目的而传播思想、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是很不相同的”[14];他也注意到,晚请时期的西学东渐和与此相关的鸦片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日益加速的急遽转变的时代”,这“不能不引起图书和出版事业的重大变化”[15]。实际上,春秋中后期之际,即老子、孔子出现的时期,是中国人的人文眷注的重心由“命”向“道”转移的时期,而西学东渐和鸦片战争的发生则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囿于民族本位的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开始。这两个时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文意识出现巨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图书在内容上判然有别于以前的时期。刘国钧先生没有对这两个时期人文观念的变化作较详尽的论说,但他能敏锐地看到图书之历史发生在这里的转折,则足以证明他有着怎样的人文眼光。
5 一种见于图书馆事业之践履的人文胸襟
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的造诣上固然可堪称为一代大师,但他首先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践履者或实践家。1920年,21岁的刘国钧先生从金陵大学一毕业就留校从事图书馆工作,此后60年的人生经历从未脱开过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无论是两度任职于金陵大学图书馆(1925-1929、1930-1943),还是先后在北平图书馆(1929-1930)、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1-1980)负责图书馆学期刊编纂或图书馆教学与教学管理,他从来都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他的治学方式和工作实践处处表现出一个献身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学人的人文“器识”。就其从事图书馆的实践活动看,1943-1951年间刘国钧先生主持筹建西北图书馆的过程显得分外突出。
1943年2月,刘国钧先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委会主任,筹委会由陈东源、袁同礼、刘季洪、蒋复聪等10人组成。这是抗战期间民族文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刘国钧先生以其至诚的爱国热诚和对民族图书馆事业的责任感竭尽全力为之奔走操劳。从洽设通讯处、选聘职员、调查书价、编制预算,到确定馆址、征购书刊、订制设备、拟订管理规则,以至开馆阅览、筹办刊物、编制目录、兴建馆舍、订立工作计划、筹划职工福利等,他躬行实践、备受苦辛。这期间,他编制了《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1943),并撰写了《西北今后之图书教育》(1944)、《馆藏汉简初释》(1944)、《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1947)等文字。这些文字配合于他的实践活动,从中可多少窥见一位真诚而极具胆识的图书馆事业家的人文胸襟。他把国立西北图书馆定位为“国家而兼具地方性之图书馆”,认为其目的在于:(1)配合开发西北之方针,搜集有关资料以供学者及从事人员之研究;(2)访求西北各省之文献古物,加以整理,保存与展览,以引起公众对于西北文化之认识与爱好;(3)采购各国最近科学家名著,搜集各国杂志,以互助及寄存方法,便利各学校员工之使用,而供学者之参考;(4)采集境内如蒙、藏、回等各民族之著作,加以研究与翻译,以增进各民族间之认识,而沟通各民族之感情;(5)辅导各地方图书馆及其他社教机关,或指导其方法,或借给其图书,以图推进图书馆教育而提高民众程度。并进而提出:此图书馆“要做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16]
这三个“中心”和五个项目的提出,非急功近利、仅热衷于一时之成绩而自负于技术操作者所能为。其所展示的人文胸襟正与他一生所守持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人文教养相配称,也与他贯注于图书馆观和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精神相协应。
收稿日期:2003-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