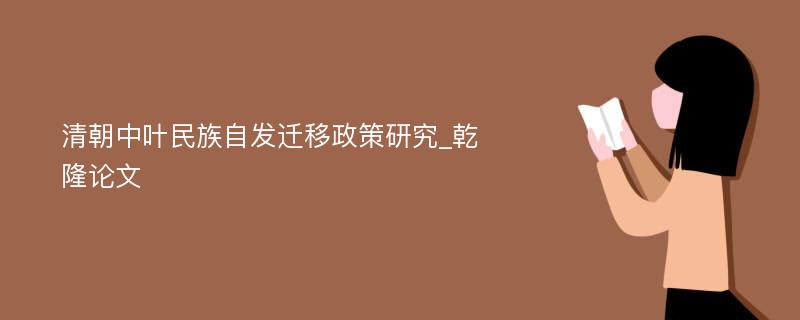
清中期民众自发性流迁政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发性论文,民众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4)-01-0053-15
在人口学上,人口流动是指人口短期离开常住地后又返回的行为,人口迁移则是相对长期(半年以上)离开常住地并在新的地区定居下来的行为。需要指出,在当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流动和迁移的定义则又涉及户籍变更与否,只有公安部门允许变更户籍地者才会被视为迁移。本文中的自发性流迁涉及“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两种行为。就清代而言,在“人口流动”群体中,不少人并非短期离开家乡,而欲长期迁移至外地,但政府往往于路途堵截,或不允许在新进入地区定居、入籍,他们被视为流民,具有流动人口的特征,当然其中的一些人最终获得转化为移民的机会。而“人口迁移”的主体则是指政府允许迁出、并最终于迁入地入籍的民众。民众自发性离开家乡到另一地区谋生并非政府所组织和主导,甚至政府采取了限制措施。它是百姓根据自己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对外地生存环境信息的掌握做出的决策。关于广泛意义上的清代人口迁移,不少学者已有关注。而集中分析“自发性”流迁的论著尚比较少见。本文将主要考察清朝,特别是清中期政府针对谋生性人口流动和民众自发前往外地寻找新的生存条件所采取的措施,借以认识制度对人口流迁的作用。
一、清朝流迁制度说明
(一)清朝政府对人口流动、自发性迁移限制的一般性政策
就中国近代之前的人口迁移政策来看,除了王朝初年因有大量荒地有待开垦,政府为将流离失所百姓尽快吸引到农耕活动之中,恢复残破、凋敝的经济,采取鼓励人口迁移政策之外,多数时期出于赋役征派和社会治安考虑,对人口流迁持防范、反对和禁止态度。清朝自发性流迁的各个环节政府均有管制措施。
1.流迁者出外须持有印票、印照等手续
印票、印照一般由家乡所在地政府或特别授权官署颁发,上填写有持有者的籍贯、年貌及随行家眷相应信息。出县境等远途之人需要申领。清朝规定,凡民人无票私出口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①这些印票不仅供路途使用,而且流入地也要将其作为准入和安插依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规定:各省棚民单身赁垦者,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倘有来历不明,责重保人纠察报究。②
对民众私自向海外迁移,中国历朝政府都持禁止和控制态度。清朝前中期尤其严格。雍正五年六月规定:闽粤海船只许从厦门、虎门出入。海船回时,按票照稽查。如有去来人数不符或年貌互异者,按顶替私回论罪。③乾隆五十七年规定,渔船出入口岸,务期取结给照,登记姓名。倘进口时藏有货物,形迹可疑,严行盘诘。④北方民众渡海赴东北也要票照。乾隆六年,奉天府尹吴应枚奏办理流民条目中有一条为:海船到奉,船长将格票呈验;开船时,查点人数,毋许遗漏一名。如有暂留,须报明存案,附入另户。⑤
2.路途居住管理
清朝的做法是:客店令各立一簿,每夜宿客姓名、人数,行李、牲口几何,作何生理,往来何处,逐一登记明白。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往来无定商贾,责令客长查察。凡客商投宿旅店、船埠、寺庙,该店主、埠头、住持询明来历,并将骑驮伙伴数目,及去来日期逐一注明送官。若有疏纵,各治以罪。⑥
3.流入、流出地控制
谋生性流迁者受雇于人,流入地雇主及其所在保甲负有管理责任,当地官员也要时常稽查。稽查办法主要有:
甲、将流入者纳入当地保甲体系。按照清代法律:关外沿柳条边之蒙古地方有内地民人种地居住者,交与扎萨克等,十家内设立一长,逐户严查,不许闲人存留,取具十家长保结。广东省穷民赶山搭寮、取香、砍柴、烧炭、种麻、种靛等项,令各州县每寮给牌,遇有迁徙消长,赴县消除;违者寮长照脱漏户口律治罪。浙江、江西、福建等省棚民在山中种麻、种靛、开炉、扇铁、造纸、做菰等项,责成山地主并保甲长出具保结,造册送该州县官,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查,并酌拨官吏防守。该州县官于农隙时务会同该营汛逐棚查点,毋得懈弛。⑦
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山区有商人募工伐木。嘉庆十九年(1814)上谕:州县查明境内木厢纸厂处所,发给该商执照,将所雇工匠姓名乡贯,造册交乡约甲长查察。其外来佣工,亦令先投乡保等,问明姓名乡贯,另册呈报,按照保甲之法,认真稽查,以进增删。⑧
乙、流入地担保制度。民众在流入地谋生,当地应有人担保。乾隆年间,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棚民中“单身赁垦之人”,须有认识亲族担保,方许租种。“如无人保结者,即令押回原籍”。⑨
流出地管理有担保制度和该管官连坐制度。乾隆十年,政府允许在台湾谋生者将妻子搬移过去,但要地方官“取具邻佑保结”。清中期,对内地人向台湾的迁移加强管控。乾隆二十六年,覆准:拿获偷渡人犯,查明本籍解回,一名至十名,及十名以上者,将本籍地方官分别议处。⑩
从形式上看,清朝政府对民众流迁的管理手段较以往并没有放松的表现,有些显得更为细密,甚至严厉。不过,也应看到,官府力量有限,而民众迁移流动又多是前往人口稀少、荒地较多的政府控制薄弱地区,制度的抑制作用又表现出有限的一面。即政府所建立的行政管理藩篱并非总能发挥其功能,有时只是一种摆设,基本上是失效的。
(二)入籍政策
外来人口进入某一地区,只有入籍才能获得固定居民所享有的权益(如子弟进学和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也要承担相应赋税义务。
清代的基本政策是:“凡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11)一般来说,居住年久、置有财产、有业可就是外来者入籍的基本条件,有时还要求已在当地婚配或有家室。
(三)清朝人口压力与流动迁移势能
清代,特别是中期以后,人口自发性流动迁移比较活跃。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历史演进至清朝,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在广大内地已很成熟,至18世纪中国的人口数量也跃至新的台阶。18世纪初已经超过两亿,19世纪初则突破四亿。(12)可以说,在18世纪,广大内地省份普遍进入了“人满”状态。人均耕地不足,无地农民增多。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势头很强。这种局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清代之前曾出现过局部“人满”)。而清朝较明朝疆域大大拓展,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增多(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为内地人口向周边地区迁移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现实可能。同时,内地的丘陵、山区也成为民众寻求新的谋生方式的区域。面对这种民众全面外迁形势,清朝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清代有不少移民是由政府所组织的,如清初向四川移民、乾隆以后向新疆移民等。在笔者看来,这与人口自发性流迁有别。通过集中考察自发性流迁行为,更能认识民众的迁移意向和特征。那么,清朝中期政府对民众的自发性流迁制定了哪些应对措施?态度如何?效果怎样?本文作一分析。
二、关外、台湾等地抑制人口流入与容许迁移并存的政策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中期(以乾隆和嘉庆年间为主)限制内地民众前往东北垦荒。其目的不完全在于治安。在清廷看来,东北乃其龙兴之地,土地山林等资源应属旗人所有。汉民耕垦于平川、采挖于山林,是与旗人争利。另一个限制迁移地方是台湾,主要从治安秩序、土客关系角度考虑。清朝政府中期对这两个地区外来人口流入实行的是限制为主导的政策,设法阻挡欲迁入者于关口、港口。但清政府并非一味采取屏蔽和驱逐政策,而是有条件地放人,同时允许已流入者转化为入籍人口,变成固定居民。甚至许可有基本谋生和生存条件者将原籍家眷搬迁过来,形成标准的迁移人口。
(一)出关者抑制和转化政策
1.抑制流入与实施驱逐
从清初至康熙初年,清政府对前往奉天开垦者持招徕和安插政策。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仍规定:有民愿开垦者,州县申报府尹,给地耕种征粮。(13)。当然这些垦荒者既有本地原有居民,也有从内地来的流民。他们成为清政府于当地设立州县的人口基础。乾隆四年(1739),民众出关尚不存在大的问题。山海关守关者通过向出关民人索费而放行。按照规定:“民人领临榆县印票,赴守关章京处放行。每票一纸,只身者索钱三十三文,有车辆者五、六十文、百十文不等。其钱系城守、都司、兵役与揽头、店主、保人分肥”,无论何人,“但得钱文,即为出保”(14)。这种做法虽属违规之举,但它也说明当时尚未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
对东北增强控制流迁的政策始于乾隆五年。乾隆帝指出: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他要求兵部侍郎舒赫德前去,与盛京将军额尔图详议具奏。舒赫德寻奏: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理合肃清,不容群黎杂处,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已立有产业,未便悉行驱逐,须缓为办理。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数年之后,集聚之人渐少,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今若明降谕旨,无知小民,恐将伊等悉行驱逐,难免不生他故。此奏获准。(15)这被视为东北“封禁”之始。(16)“封禁”有关闭通道、冻结民众出入之意。从此后清廷的政策看,它难称为“封禁”,而是高度控制内地民人的出关行为和进入规模。
(1)关口控制
内地去往东北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陆路以山海关为主要通道,也有绕道蒙古八沟等进入。在清代,直隶百姓进入东北主要是陆路,而山东民众既有陆路也有水路。
乾隆五年,舒赫德等拟定的关口限制措施包括:一、山海关出入之人,必宜严禁。向例在奉天贸易及孤身佣工者,由山海关官员给与照票,始行放出。其携眷者概不放行。……其在山海关附近三百里以内居住及出口耕田者,亦应一体给票,俟入口时缴销。若至应入口之时并不进关者,由原给票之官员处行文奉天地方官催令归还。二、严禁商船携载多人。查奉天所属地方海口,因通浙江、福建、山东、天津等处海界,其商船原无禁约,该地方官给与船票,经过各海口照例查验,钤加印记,始准开行。(17)乾隆十五年对内地新流入东北之民提高了控制力度: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并行山东、江浙、闽广五省督抚,严禁商船,不得夹带闲人。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乾隆二十六年,朝廷令直隶山东等省督抚,转饬边关海口,嗣后赴奉天民人内,查系并无贸易,又无营运者,严行查禁。(18)乾隆四十年,盛京将军上奏将失察流民私行渡海之奉天、山东沿海州县巡查各员严行议处。(19)乾隆四十二年规定:如有藉称寻亲出口赴奉天并无确据者,不许给票。如滥给滋事发觉,即将给票官降二级调用;山东登莱等处有票船只,如有夹带无照流民私渡奉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船只入官。(20)我们认为,这些禁令频发,表明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守关、守口官弁无意疏漏和有意纵放(在受贿情况下)行为均存在。这也为民众不断进入东北提供了可能。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六年进入吉林地区的流民不得不由蒙古八沟地方绕行。可见近处关口的抑制作用是存在的。
嘉庆年间,继续实行禁止民人出关垦荒之策。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规定:各处无业贫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21)嘉庆十六年,嘉庆帝要求直隶、山东、山西各督抚转饬各关隘及登莱沿海一带地方:嗣后内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关门务遵照定例,实力查禁……如此各省关禁一律申明,使出口之人渐少,则私垦之弊,当不禁而自除。(22)
但对经商者并不限制,多数情况下出关投亲靠友之人也会从宽对待。
必须承认,尽管清朝中期通过关口控制内地民人进入东北有漏洞,但其阻挡效果不能忽视。至少民众大规模的出关流迁行为较少发生(除灾荒年景经皇帝特许外)。
(2)进入者限期离开或赶逐政策
应该说,清政府对已进入东北境内者并未以简单方式迅速或粗暴地驱离。流入盛京的内地百姓,若已定居,以允许入籍为主;不愿入籍者限期(十年)离开。而进入吉林等东北远地者(主要是没有户籍的单丁)则采取有条件递解或限期离开之策。
乾隆六年,清政府规定: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处为满洲根本,毋许游民杂处……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不许于永吉州之山谷陬隅造房居住。仍查明本人原籍年貌,五人书一名牌互保。五人内如有一人偷挖人参、私买貂皮、擅垦地亩、隐匿熟田及赌博滋事者,将犯枷责递解外,仍将连保四人一并递解;若连保人有愿回籍者,给引回籍,并令地方官按季查明人数,陆续将回籍之人尽行裁汰。(23)这一政策仅限制未入籍单丁的居住地选择,但允许其从事佣工等谋生活动;只有当其从事违规性谋生行为及触犯法纪时才予以驱逐(递解)。至于有家室之民则没有居住地点限制。
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复准地方官所奏:宁古塔界内,地方偏小,外来流民,不便准其入籍,应将流民逐回。如有愿于吉林伯都讷地方入籍者,即将该处丈出余地,分给伊等,交纳地粮。可见,这是将宁古塔的外来者引至更适于耕作的伯都讷定居,并非无条件驱离。乾隆三十四年覆准: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俱系陆续存住,在二十七年定议之前,定限一年,尽行驱逐。(24)对居住年久者允许继续留住,只将近几年新来者限定一年之内离开。
乾隆帝四十一年十二月谕军机大臣等,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民居住,今闻流寓渐多,著传谕户部尚书傅森查明办法,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可见,这次对当地的新进入者的控制增强。这一政策得到落实。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吉林和尔苏边门,拿获流民三户,共四十三名,并引进民人三名,“照例逐回”(25)。可见,当地政府对流民零星进入地区,为防患于未然,实施逐离。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抑制外来民众在该地区拓展生活空间的势头。
2.适度让步与允许身份转换
所谓适度让步是指在控制政策实施过程中,对聚集关口者,特别是内地受灾流民,经由皇帝授权,载明放行出关;允许身份转换是指准予以不同形式进入东北各地的内地人入籍为民。
(1)对关口流民的让步政策
乾隆嘉庆时期,对内地受灾百姓出外谋生者多有让步做法。当然,这一变通政策只能由皇帝作出,并下令实施。乾隆八年,直隶天津、河间等地受旱灾,众多流民聚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关口,希望出关谋生,遭到拦阻。乾隆帝下诏指出:伊等既在原籍失业离家,边口又不准放出,恐贫苦小民,愈致狼狈。著行文密谕边口官弁等,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但不可将遵奉谕旨,不禁伊等出口情节,令众知之,最宜慎密。倘有声言令众得知,恐贫民成群结伙,投往口外者,愈致众多矣。著详悉晓谕各边口官弁等知之。乾隆九年,因河南、山东有灾,乾隆帝再令山海关等隘口,放行出关谋生贫民。(26)可见,这一放行政策是特殊情形下的妥协,而非控制民众流迁政策发生改变。不过,也应看到,清帝知道,放行措施虽是临时、权宜之举,但对流入者来讲,一旦出关,他们就不是短期居留的避灾之民,绝大多数人会设法转为永久性居民。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乾隆帝谕令:京南河南等府,偶被旱歉,曾经降旨,凡有出关觅食贫民,毋许拦阻,原为轸恤灾民起见。山海关外盛京等处,“地广土肥,灾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而清政府这项政策使不少灾民受益。甚至在控制外来者严格的吉林地区也安置了“万五千余人”。因“吉林屡丰,流民均获生全”(27)。这无疑会诱使流民定居下来。实际上,他们从家乡来到关口,就是想获得迁移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七年这一对灾民的“格外施恩”、“一时权宜抚绥之计”,在此后延续下来。嘉庆帝于嘉庆八年(1803)五月指出:乃近年以来,民人多有携眷出关,并不分别查验,概准放行。但他发现,不仅灾荒年份内地有人出关,而上年“直隶收成丰稔”,“直至今春尚有携眷出关者数百余户”。因此他斥责守关副都统“漫不经心”,令“交部议处”。以后,“除只身前往之贸易佣工、就食贫民仍令呈明地方官给票、到关查验放行、造册报部外,其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若“遇关内地方偶值荒歉之年,贫民亟思移家谋食、情愿出口营生者,亦应由地方官察看灾分轻重,人数多寡,报明督抚据实陈奏”,即由皇帝定夺是否放行。这一谕令似有收紧乾隆五十七年民人出关管理松弛之意。然至同年六月,又有“贫民亟思移家谋食,相率赴关”。嘉庆帝认为这些外来者“系尚在未经定限以前,若令仍回原籍领票,该民人等力有不能。如任其拥挤关口,概不放行,则日聚日多,成何事体?”故派员前往,会同守关官员“查点欲行出口之户现有若干,逐一放行”。当然,“自此次定限之后,断不得携眷出口”。需要指出,嘉庆八年五月所定政策中限制较严的只是“携眷出口”者,即有明显迁移打算者,而对“只身前往之贸易佣工、就食贫民”并不限制。不过,灾荒年“就食贫民”中多数为“携眷”之人。(28)
从以上政策和民众行为可见,乾嘉时期,内地直隶、山东民人无论家乡有无灾歉,出关谋生的势头很强。即他们并非要以流民身份短暂离乡,而是欲迁移至这块有诱惑力和生存潜力的地区。表面看起来,清政府所实施的将内地百姓堵截于关门与让步式放行政策有矛盾之处。我们认为,前一政策的立足点是保护“龙兴”之地和旗人利益;后一政策则是帝王之恩,最高统治者感到其有为民众提供谋生途径之责,至少应有为民解困的姿态。这一矛盾是由一族和一国的立场差异所形成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流入百姓主要是为了谋生,是当地发展的积极因素,不会带来民族冲突和统治威胁。
(2)流入地百姓的身份转换政策
乾隆初年,东北地区,特别是奉天一带已有大量内地流民进入,并且形成聚落,硬性驱逐并非良策。所以,清政府采取了对居住年久者允许入籍的政策,不愿入籍者则宽限离开。
乾隆五年,针对“外来民人,安居年久,有曾入州县档册者,亦有未经载入者;似此若不清查,复严保甲,不但地方不能肃清,征收地丁钱粮,必多隐匿”,舒赫德等拟定的处置办法是:应饬令无论旗民,一体清查。除已入档者毋庸议外,其情愿入档者,取结编入档册;不愿入档者,即逐回原籍。该地方乡约若隐匿不首,严究治罪;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29)
乾隆六年,奉天府尹吴应枚对流入民众提出的解决方案更为具体:一、愿入籍者,准取保结,经照编入;二、不愿入籍,一时又未能回籍者,暂作另户编甲,陆续给照回籍;三、游手好闲、生事不法者,照例治罪外,递解回籍;四、商贾工匠,从前在奉寄居者,地方官给照,无照不许存留;五、旗人披甲当差者,雇人耕种,须家长雇主结报,门牌注明,去来随时报明领催乡保,牌上无名者不准存留。对出关佃种经商者也有规定:关外佃种民人,照原编牌式,另给一牌;无牌,不得擅放进边贸易。乾隆帝批准其奏,此政实行后,“群黎感悦”(30)。这一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使流入百姓获得了去、留选择机会,其中大部分人得以合法定居、谋生,成为入籍之民。
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规定,奉天流入者中,“所有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三项为旗民所资籍者,准其居住”(31)。这项政策更具有务实特征,既满足了内地劳动力求职、谋生之需,也满足了东北当地旗人,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对佣工的需求。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指出: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于满洲风俗攸关。但承平日久,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必致各失生计,是以设州县管理。这更是对流民定居权的承认,流民人口由此转变为迁移人口。政府设州县管理流迁之人,而这些流迁者又成为当地州县存在的人口基础。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在吉林安置了一万五千名内地灾民。按照政府本意,内地灾情缓解后,他们还应回籍。吉林将军恒秀乾隆五十八年为此上奏,因“今年内地有秋,饬令回籍”。然而,这并非灾民出关之意,故其“咸云甫经全活,移回转苦失业,路费亦艰”。恒秀希望做出让步,“请照例造入红册,自来岁为始,交丁银”。乾隆帝批准其处置意见。(32)它无疑使这支有一定规模的流民转化为定居之民,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清廷严格控制外来者在吉林定居增加的政策。
嘉庆年间,尽管清政府仍对民众流入吉林一带实行相对严格的控制,但对违禁进入者不得不做出让步,乃至允许其成为固定居民。嘉庆五年,清政府议准:郭尔罗斯地方,流寓内地民人二千三百三十户,均系节年垦种,难以驱逐,应划清地界,定为规制,不准再有民人增居。(33)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吉林地方官员查出伯都讷所属拉林河西岸地方,流民私垦田地一千九百余亩,聚集人一千余户。“若一时全行逐回原籍,该流民不惟栖止失所,恐不免于饥寒”。对此解决办法是,“加恩将此项查出私垦之田,分给流民,仍照前次办过成案,入于红册,于明年起征”(34)。这意味着认可这些流民的居住权,他们甚至由此得以入籍。嘉庆十三年,长春厅查出流民三千一十户。嘉庆帝指出:“若概行驱逐,未免失所。著再加恩准照前次谕旨,入于该处民册安插”。但要求“自此次清查之后,该将军务遵照原议,除已垦之外,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嘉庆十五年,吉林厅又查出新来流民一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六千九百五十九户。嘉庆帝对此非常不满: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各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之多。因而下令:除此次吉林、长春两厅查出流民,姑照所请入册安置外,以后“责成该将军等,督率厅员实力查禁,毋许再增添流民一户”。如有阳奉阴违,“即交该将军咨明理藩院参奏办理”。(35)可见,清政府的基本做法是,严控外来者进入所限制地区。而流迁者的扩散能力很强,每次政府发现,已形成规模,难以驱逐,只好认可这一现实,将其纳入当地户籍管理体系中。
整体来看,直到道光以后,清政府才逐步放松对出关垦荒移民的限制。咸丰年间,清政府知道原有控制政策已无法坚持,承认旗人及牧丁对大凌河牧厂的私垦,到光绪二十八年,东西厂全部开放。清末,政府对东北移民开垦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招徕。光绪三十二年,设立锦州丈放局,将垦地放给一般报领者。宣统二年,清政府于黑龙江讷漠河一带,设立招垦行局,组织内地灾民前来垦荒,令被灾省份,就赈抚项下拨给川资,到江以后,一切垦荒费用,均由江省垫给,酌分年限收还。是年即安排一千三百余名。(36)
应该说,清朝中期政府对内地民众前往东北垦荒的政策是:入境从严,通过陆路和海路入口加以控制。但仍有不少人从陆路和海路以合法和违规的方式进入。流迁者一旦进入并于当地立足,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又采取宽严相济策略,即允许置有产业者入籍,不愿入籍者给予较宽裕的时间返回原籍。实际上,清朝中期政府对内地人出关既有怕多的忧虑,又有过严限制影响当地旗人需求之虞,因而,它不会实施真正的封禁之策。
(二)内地民众向台湾迁移的限制
清朝对内地向台湾的自发迁移政策经历了清初禁止、康熙时期收回台湾后允许、康熙五十年后限制、乾隆十一年允许已在台内地民人搬移家眷、光绪元年弛禁这样一个过程。总体上看是一个宽、严结合的政策。当然“宽”是有条件的,针对在台湾居住年久、有谋生产业和条件者,允许其将内地家眷搬迁过去;同时对偷渡者严厉禁止。
清初,在政府禁海政策之下,福建、广东等沿海民众向台湾迁移受到严格限制。台湾收回之后,政策逐渐放松。康熙后期因外来者自由入台产生土客冲突及治安问题,开始实行欲来者须在当地申领印照的政策,禁止无照偷渡。康熙五十七年,朝廷复准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疏:“凡往来台湾之人,必令地方官给照,方许渡载;单身游民无照者,不许偷渡。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别严加治罪,船只入官,如有哨船私载者,将该管官一体参奏处分。”(37)
雍正初的政策为,准许闽粤人前往耕种,但“所有妻眷,一概不许携带,止许只身在台,而全家仍在本籍。盖在台湾为游民,而在本籍则皆土著”。这里,清政府将流动人口(单身游民)和迁移人口(改变家庭居住地)分得很清楚。
雍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曾上奏建议:在台人民,其贸易雇工无业之人,全无田地,一概不准搬眷往台。若实在耕食之人,令呈明地方官,查有耕种之田,并有房庐者,即行给照,令其搬往安插。至佃户之中,有住台经五年,而业主又肯具结保留者,准其给照搬眷,其余一概不准。雍正帝批其“胸无定见,而为此游移迁就之词……仍照旧例行,待朕再加酌量”(38)。雍正帝留下了变更的余地。雍正十年,经广东督臣鄂弥达上奏,部议准令在台流寓之民,搬取家眷团聚。雍正十一年规定,在台湾的流动人口,其并无家室产业,如佃户佣工贸易之人,取具房主、业主、邻佑保结,附于保甲之末,汇报督抚稽查。(39)可见,雍正年间对待向台湾迁移者采取的政策比较宽大:在当地有固定谋生方式,特别是置办有土地等产业者,允许其赴大陆搬移家眷;而对单身贸易佣工之人,允许其在台谋生,并编入保甲。
乾隆初年延续了雍正朝政策。乾隆十年规定:粤省在台湾人民,情愿携眷者,止许搬移妻子,令地方官取具邻佑保结,照内填注名数;如地方官不查明,混行给照,照滥给印结例,议处本人,严加治罪。(40)因这一规定中没有强调必须是置办有产业者才能携眷赴台,可理解为是一种放宽的政策。乾隆十一年,政府扩大了在台之人搬移家眷的范围,规定:在台人民,果有祖父母、父母在籍,准其赴台就养。如祖父母、父母在台,准其子孙赴台侍奉;若本人在台,而内地妻少子幼,并无嫡亲可托者,亦准其搬移聚处。即赴台侍奉祖父母、父母之子孙,果有幼少妻子,亦准一体赴台。乾隆十二年再次实行搬眷政策。该年六月,清廷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所奏:台湾客民搬取家口,请定限一年,地方官查明给照过台;逾限,不准滥给。(41)这一规定提示我们,清政府对在台客民搬眷并非采取完全放开政策,可谓断续进行。而乾隆二十六年规定更说明了这一点:台湾流寓民人,搬眷过台一年期满,内外各地方官,毋再滥行给照。(42)乾隆五十三年,闽浙总督福康安上奏指出:在台的内地只身民人,或携眷移往居住,查有内地官给执照者,即收留编入民籍(43)。它或许表明,乾隆年间清廷虽允许台湾客民搬移内地家属,但并非可随时搬移,而是地方官上奏获批之后才实行或解禁一次,限期执行。过期不准搬移或暂停,累积数年再度实行。
对偷渡去台湾者,则采取惩罚措施。何谓偷渡?按照清朝法律:“不请印照者,照偷渡例,杖八十,逐回原籍;地方官滥给印照,照例参处。”“人照不符,照私渡例治罪”(44)。实际上,偷渡是那些台湾没有任何亲属,不符合去台条件,得不到印照私自前往者。按照官方说法,“奸民偷渡过台,一由内地客头之包揽,一由在台回至内地民之接引”。故此,“如招引多人偷渡,本人照客头例,发边卫充军”(45)。乾隆二十六年规定:台湾流寓民人,搬眷过台一年期满,内外各地方官,毋再滥行给照。有遇拿获揽载偷渡船只,将搭载大船及雇佣小船各船户均照客头包揽过台之例治罪。偷渡流人台湾者,拿获后究明由何处出口入口,将失察之员治罪。至兵役澳甲,拿获偷渡人犯,十名以上,同船户客头并获者,每十名赏银四两;十名以上,照数追加。赏项令地方官于偷渡船只变价内支销。(46)通过在迁入地搜捕偷渡者,进而株连出入口管理之人和承载船只,控制偷渡行为。乾隆三十八年,广东、广西地方督抚奉旨:严禁闽粤两省渡台民人,仍将有无查出偷漏之人,于岁底汇奏一次。节经饬行沿海文武实力查禁。三年中,查获偷渡者三十二起,抓获人犯三百七十二名,分别定拟军遣杖徒。(47)乾隆五十四年,仍饬专管各汛口员弁兵役每日将所泊商渔等船,查验字号船牌,按旬列报。一有无照船只,即行根究。(48)这种禁令抑制了不少人的赴台谋生行为,却难以杜绝。
可见,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向台湾移民的限制重点放在偷渡上;对在当地有正当谋生手段者,不仅允许编入保甲,而且可以将内地家眷搬移过去。禁止偷渡,表明政府要控制迁往台湾内地人的规模。若外来人口流入过多,谋生没有着落,则会引发治安问题。
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在沈葆桢建议下取消台湾移民限制,谕令指出: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习俗异宜,曾禁内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予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著一律弛禁,以广招徕。(49)至此,实行了近一百九十年之久的民人渡台必须领照并经查验的规定才算完全废止。(50)
(三)限制向易引发土著和客民冲突地区迁移
1.控制汉民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
清朝对于出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者,有严格的禁令:凡湖广沿边苗民俱以塘汛为界,民人责令有司稽查,苗人责令游巡官员详查。若民人无故擅入苗地,照越度缘边关塞律杖一百、徒三年;苗人无故擅入民地,亦照民例充徒。(51)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佑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52)这项政策实行的原因是:各省番、苗与内地民人言语不通,常有肇衅之事。此外,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台湾番境者,杖一百。凡台湾民、番不许结亲,违者离异。(53)乾隆二十六年,专门制定台湾“番界苗疆禁例”,凡台湾流寓民人自去年停止搬眷之后,不准内地民人偷渡,亦不得与番人结亲;即已娶生子者,禁止往来番社。其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偷越例治罪。(54)
我们认为,这一政策对汉族人口的流迁至少数民族地区有一定限制作用。而从清代民族地区所出现的客民和土著之民不时有经济利益冲突,可见其抑制汉民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政策作用有限。
2.棚民政策
清代的棚民实际是一种经济性移民。其最早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山区。这些外来者“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此外,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55)可见棚民和寮民之名均是根据其居住方式所得。作为流动者他们没有能力建造正式稳固的住宅,只好就地取材,搭建临时栖身之所。
(1)控制措施
雍正帝对棚民管理非常重视。雍正三年,对江西、福建、浙江三省棚民实行区别对待,居住年久者编入保甲。编册之后“续到流移,不得容留”(56)。雍正帝在十三年七月发给内阁的谕令中指出:浙、闽、江西等省有棚民州县,“朕皆留心拣发牧令前往,俾司化导董率之任”,“向闻棚民留住之地方,皆责成本处地主、山主出具保结,并非来历不明之辈,始许容留”,而且地方官员,须于每年岁底亲往查点一次。然而,“今闻法久废弛,有司等视查点为具文,而地主、山主亦以保结为虚应故事”。故雍正帝要求该督抚等,“转饬有司,实力奉行,毋或怠惰”(57)。棚民允许在流入地从事所营之业。
清代中期以后,不仅山区有棚民、寮民存在,广东沿海的岛屿也有寮民身影,且形成规模。乾隆五十五年,广东总督上奏建议,撤毁雷、廉交界海面之涠洲及迤东之斜阳地方寮房,将民众递回原籍,以免其与洋盗串通滋事。乾隆帝指出,沿海各省所属岛屿,多有内地民人安居乐业。若遽饬令迁移,使数十万生民流离失所,于心何忍。而且如办理不善,“转使良民变而为匪”。为此,“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外,余均仍旧居住”。对“零星散处”的贫民,“尤不可独令向隅”。但各督抚应“严饬文武员弁编立保甲”,加强控制。可见,乾隆帝比地方官高明之处在于,兼顾治安与民生两个方面,而非一味为保境内无事,限制民众谋生空间。当然,乾隆帝也有严厉之处,一旦发现有“盗匪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出,将所居寮房概行烧毁,俾知儆惧”。对山东沿海岛屿的外来谋生者则加强控制。乾隆五十七年上谕:“据福宁所奏,山东一省海岛居民二万余名口,各省海岛想亦不少。当遵照前言,不准添建房屋,以至日聚日众。仍应留心访察,勿任勾结匪徒,滋生事端。”(58)
棚民垦荒在一些地方造成水土流失,因而政府不得不有所控制。浙江各府多有棚民租种山场,导致水土流失。嘉庆二十年规定:浙江“只身棚民,租种年限已满,及本无租山资本,藉称佣工,在山逗留者,均驱逐回籍。”(59)咸丰元年,浙江巡抚常大淳奏言:“浙江棚民开山过多,以致沙淤土壅,有碍水道田庐。请设法编查安插,分别去留。”(60)
(2)入籍管理
政府既然允许棚民在当地居住谋生,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即是否允许其入籍?我们看到,雍正以后,棚民入籍政策制定出来。
雍正三年,根据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所奏,政府对江西、福建、浙江三省棚民实行安辑政策,内容包括:见在各县棚户,请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册,责成山主、地主并保长、甲长出结送该州县,该州县据册稽查,有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棚民有膂力可用及读书向学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61)这意味着移民入籍有一个渐进过程,要取得完整的入籍权利,需要二十年时间。
嘉庆二十年清廷规定:浙江省棚民,核其租种,已逾二十年,现有田产庐墓,娶有妻室者,即准令入籍。其年份未久,已置产缔姻者,俟扣满年限,亦准其呈明入籍。若并未置产缔姻,租种山场尚未年满,及租票内并未注有年份者,应暂为安插。年份未满者,俟年满饬退。(62)
综合以上,清代中期尽管为百姓的自发性经济性流动迁移设置了诸多限制,但这一政策有严厉的一面,也有变通的另一面。特别是民众一旦进入禁垦之地成为事实,并有业可就,政府往往做出让步之举,而非驱逐。由此,流民得以转化为移民,获得了合法谋生机会,改善了生存条件。这对边远地区开发、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还应指出,民众所进入的地区虽然人口相对较少,但却多有土著之民于其地生活。除吉林、黑龙江之外,多数土地是有主之地。外来人口进入可能导致客、土冲突,它是限制政策出台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对东北来说,限制内地民众移民,清廷有更为复杂的考虑。
我们说,尽管清政府抑制民众迁入政策具有很大的弹性,具有人性化的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限制的作用是存在的,即流迁者很难形成大规模迁移之势。
三、西南和口外相对宽松的自发垦荒迁移政策
总体来看,清政府除了限制内地百姓向东北、台湾和一些易于发生土著和外来者冲突的地区迁移外,基本上采取的是宽容自发性垦荒移民的政策。尽管清政府实行了印照管理,即移民应持有迁出地地方官所出具的证明信件前往迁入地,其目的主要是加强管理,而非刻意限制民众的垦荒流动和迁移行为。
(一)对入川自发性垦荒移民的政策
四川明末清初遭受严重战争创伤,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清政府在康熙、雍正年间曾招募周边百姓前往耕垦。而自发前往者亦复不少。政府给自行前往者以方便,试图使他们沉淀下来,成为入籍之民。因此,这些外来者从一开始就具有移民行为。
康熙中后期,湖广民众前往四川垦地者甚多。这些百姓离开家乡之前,将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可见,他们是全家同往,表现出永久离开家乡的迁移意向。但其中的问题是:在四川垦地满五年起征之时,他们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亩争告者甚多”。其行为具有“回迁”特征,以此逃避应纳地粮。为抑制移民随意回迁引发的房地产纠纷,清政府出台流出、流入地管理办法: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借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再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63)它是一种变无序为有序的做法。清政府此意在于,将从湖广前往四川耕垦之民变成当地入籍之民,而不得仍视湖广之籍为籍。它具有抑制迁入者异向回迁或返迁的意义。
民众赴川应持有当地官员颁发的印照,以证明其身份。但无照者也有,远道而来,接受抑或排斥成为两难。雍正五年户部议复:楚民入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放。近年自湖广、福建、江西、广东来川者,竟无执照可验。穷民挈眷迁移,若勒令回籍,必致流离失所;任其接踵而来,又恐奸良混集。伏乞敕下各省抚臣,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按插。福建、湖南也照此办理。(64)那些当下无照已至者,应该也被接收下来。
乾隆初年,对自发入川移民的宽容政策仍在实行。而且又有两广移民加入,甚至江西、福建人也加入进来。乾隆六年,两广总督马尔泰上奏: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许其开明眷属姓名人数年龄,报本地方官查明,给票所往,不必候川省关移。并饬知沿途管县,验明人票相符,即予放行。到川,编入烟册,移知原籍存案。获准。(65)这实际是一种更为务实的做法,缩短了迁移者的等待过程。可见,该项政策是对迁出、迁入两地所言,要求原籍当局不为百姓离开设置限制,入川后即时编入户籍册籍中。至少从公文上看,这些政策为民众自发迁移创造了途径。
对于官方管理者来说,没有印照手续者应被拦截下来,这可谓依法行政,并非苛刻之举。乾隆十五年,湖广总督永兴、湖北巡抚唐绥祖等地方官会奏提出“入川民人,无本籍印票者,递交原籍安插”,乾隆帝指出: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等类,固应尽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与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务期杜奸匪而便民生,两有裨益。(66)应该说,这既是对地方官行政方式的引导,也为无印票入川贫民提供了极大方便。乾隆帝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以更为灵活和现实的态度和举措对待自发性入川之民。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贵州巡抚周人骥上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帝指出: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封疆大吏,当体通达大体,顺民情所便安,随宜体察。(67)乾隆帝深知,在家乡生存困难的穷民对赴外地谋生、寻找机会充满期待。地方大员应体谅到这一点,为其流迁提供有利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二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以“川省荒地,业经认垦无余”,建议“嗣后各省民人,藉词赴川垦地者,不必给票,并转饬沿途关津,查无照票者,即行阻回”。乾隆帝则不以为然: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土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其邻近该地之湖广、江西等省,均系朝廷子民,抚绥本无异视。(68)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让民众在迁移“市场”上自我权衡来决定是否固守乡土还是流迁,由此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人口分布得以调整。
应该说,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时期,政府对民众向四川的自发性流迁给予较大的政策性便利,由此使民众行为的“人口迁移”特色更为突出,而非简单和临时性“人口流动”:变卖财产全家离开故乡,从当地政府获得证明身份的印照,进入四川验明身份后即有入籍资格。
(二)改土归流地区的自发性移民政策
雍正年间,西南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制度,为内地民人流迁带来了机会。
《明史》载:土官争界,争袭,无日不寻干戈,边人无故死于锋镝者,何可以数计也。春秋、战国时事当是如此。若非郡县之设,天下皆此光景耳。(69)清中期改土归流之制实行后,藩篱消除,民众来往障碍大大减少。
湖北西部宣恩、咸丰、利川等地,自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以来,久成内地,附近川黔两楚人民,垦荒者接踵而往。或称“流民日增”、“逐队成群”、“前后接踵”,其中以垦荒居多。(70)但乾隆初年当地“田土拐带案牍日见纷纭”。乾隆十七年,湖广总督永常上奏提出管理办法:嗣后外省及各属人民入施恩施者,请照入川给照之例,开造眷属清册,呈报本籍,给照前往,交与该地方官查验,收入保甲,一体编查。其现在落业民人,凡有夫妻子女者,无论流寓久暂,悉予编保;其单身游手之徒,限三月内查明,取具亲邻保结,方准编入;其老荒山场,概行封禁。乾隆帝同意这一方案。(71)可见,这些规则比较温和,没有苛刻之处。它表明,以前流迁之民多为无印照者,本地官府对其籍贯及本人、眷属年貌等信息无从掌握。而印照制度借鉴入川之例,只要有印照,即可入籍,成为合法谋生、居留之民。已在当地有正当职业且有家室者,一律允许编保,纳入户籍管理体系之中。单身之人,有亲邻保结,也可获得居留资格。总之,这些政策虽具有约束性,甚至为迁入者带来不便,但它并无限制正当民众迁入之意,更无驱逐条款。
需要指出,地方官所划出的“封禁”之地,落实效果并不好,不少民众前往垦殖。乾隆三十八年湖北巡抚陈辉祖为此上奏,请令民间自行首报,分别升科。乾隆帝指出:“方今生齿日繁,地利所在,自必趋之如鹜。且现在既有私垦之事,可见前此之官为封禁,仍属有名无实。又不如听其耕辟升科,俾小民获自然之利。而在官复有籍可稽,较为两得。陈辉祖所奏,亦属可行。但只令自行首报,不复官为核验,愚民惟利是务,谁肯全数开呈?弊将百出。若只系垦多报少,尚属藏富于民,亦可不计”。为免使地方里正串通胥吏,藉端挟制即须官为查丈,才能彻底清厘,而查丈之事,亦非易办,乾隆帝决定暂缓进行。(72)可见,当时朝廷对民众垦荒升科比较谨慎。这些迁移耕垦的百姓不但未被驱逐,反而获得免于“升科”的待遇。
直到道光年间,清政府一直实行这一政策。道光二十六年上谕:贵州附居苗寨客民,既经编入保甲,其分户另居者一律编查。着该抚饬令各地方官督率村寨保长人等,将客民旧户迁徙若干、现存若干,其旧户内有子孙分户另居若干,逐一查明造报(73)。迁移者已被视为当地固定居民。这一政策对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具有调整作用。
(三)口外移民
清朝原本对民众前往口外也有限制,以实现蒙汉隔离局面。但它并未被认真实行,身为土著贵族的蒙古王公也乐于把牧地租给外来汉民耕种。(74)
清代康熙中期之后,山东民众赴蒙古种地者众多。康熙五十一年,已达“十万有余”。官员中有主张驱逐者。康熙帝反对这种做法,但同时认为应加强管理: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种地者,该抚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移送稽查,由口外回山东去者,亦查明造册,移送该抚覆阅稽查,则百姓不得任意往返。(75)这与对湖广前往四川垦荒民众所采取的政策一样,意在使迁入者有定居之心。雍正五年,雍正帝翻检史册,认为康熙帝“圣虑周详”,属“抚民怀远之至意”,故要继续采用。雍正初年,为加强管理,清政府陆续添设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同知各一员。雍正帝于五年下令:“嗣后再有出口种地之人,俱著该同知一面安插,一面移咨本籍,查无过犯逃遁等情,准其居住耕种,年终造册报部。”(76)雍正八年奏准:山西、陕西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甚多,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查。即于种地民人内择其诚实者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有拖欠地租并犯偷窃等事及来历不明之人,即报明治罪。(77)清政府在当地设官并建立保甲体系,就表明认可流迁者在当地的谋生行为,由此他们实际具有了户籍之民的身份。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指出:山东无业贫民,出口往八沟、喇嘛庙等处佣耕度日者,难以胜计,藉以成家业者甚多,远近传闻,趋之若鹜,皆不惮千里挈眷而往。(78)至少从民众行为方式看,他们是想迁移到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认为,它与清政府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的迁移环境有很大关系。
就总体而言,清代政府对内地人口增长、失去土地民众生存艰难的状况有所认识。中期以后,除了在东北和台湾实施具有弹性的迁移控制政策外,其他地区则认可民众谋生性自发迁移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地民众的生存压力。
四、结语和讨论
清代中期,由于内地省份人口总量增长较快,人口压力凸显,民众向人口稀少、尚未开垦地区寻求谋生途径的势态明显很大。这一时期政府实际控制疆域和有效管理的疆域扩大,为民众向边远地区流动迁移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我们同时还认为,清代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政策实行之后,自发性迁移流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已非逃避赋役者。因而除了个别敏感地区之外,清代中期,政府对民众谋生性流动迁移并未实施很强的限制,当然必要的管理(如持有印照等手续)是需要的。
清代中期,政府对民众自发性流迁行为实行了区别对待政策。
在东北、台湾以控制进入为主导,但又非实施“封禁”政策。政府允许内地灾荒流民出关谋生;对以各种形式流入东北地界者给予其或入籍定居或宽限返乡的选择;东北有定居亲属的内地民众可前往寻亲。对在台湾居住年久、有业可就者不仅可取得定居权,且允许将内地眷属搬迁过来。不过清中期政府总体上对东北持控制迁移政策,在台湾则长期实施偷渡禁令,由此抑制了内地民众大规模进入,延缓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在南方山区,政府基本上采取允许棚民进入谋生的政策,当然出于治安等考虑要将其纳入保甲等管理体系中,居住年久者还可获得入籍等权益。对自发入川、出口外等地开垦的民众,清中期政府基本持放开政策,只要有家乡政府所颁发的印照即可上路,至迁入地被获准耕种和入籍。另外,湖北、湖南西部实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也允许民众按照入川方式前往谋生。
清朝政府对自发流迁民众的这一政策具有释放内地“人满”农耕区人口压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口分布的外部扩展(向边疆迁移)、内部充实(开发江南山区、川楚陕交界山区等)的调整得以实现。
清代民众的自发性迁移是在利益比较中所作出的选择,也符合人口学上的推拉理论条件:内部人口压力增大、生存条件艰难是重要推力,而外部存在的肥沃可耕区域则形成一种难以抵御的吸引性拉力。这种自发性迁移将有助于实现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供给和需求市场的存在也是政府限制内地民人迁入政策难以全面落实的一个因素。即东北、口外地区的农耕活动(当地贵族和地主拥有土地)对内地劳动力的供给有需求,因而政府不会、也难以实施严苛的“封禁”政策。但也应承认,由于个别地区限制性人口迁移措施的存在,移民的应有规模受到压缩。
①《大清律例》卷20,兵律,关津。
②《清史稿》卷120,食货。
③《清世宗实录》卷58,雍正五年六月。
④《清史稿》卷120,食货。
⑤《清高宗实录》卷137,乾隆六年二月乙丑。
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⑦《大清律例》卷20,兵律,关津。
⑧《清仁宗实录》卷286,嘉庆十九年二月丙子。
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⑩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11)《清史稿》卷120,食货。
(12)王跃生:《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7年第4期。
(13)《清圣祖实录》卷91,康熙十九年八月壬戌。
(14)《清高宗实录》卷102,乾隆四年十月丙戌。
(15)《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
(16)刁书仁:《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7)《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
(1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19)《清高宗实录》卷996,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丙戌。
(20)《清高宗实录》卷1028,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己巳。
(21)《清仁宗实录》卷201,嘉庆十六年十月丁巳。
(2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23)《清高宗实录》卷150,乾隆六年九月戊辰。
(2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25)《清高宗实录》卷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乙已;卷1131,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26)《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丁丑;卷209,乾隆九年一月癸巳。
(27)《清高宗实录》卷1417,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癸丑;卷1440,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28)《清仁宗实录》卷113,嘉庆八年五月乙未;卷115,嘉庆八年六月辛卯。
(29)《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
(30)《清高宗实录》卷137,乾隆六年二月乙丑。
(3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32)《清高宗实录》卷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丁丑;卷1440,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3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34)《清仁宗实录》卷190,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丙戌。
(35)《清仁宗实录》卷196,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壬午;卷236,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36)《宣统政纪》卷40。
(37)《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甲申。
(38)《清世宗实录》卷61,雍正五年九月庚辰。
(3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4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41)《清高宗实录》卷265,乾隆十一年四月甲申;卷292,乾隆十二年六月癸酉。
(4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43)《福康安等奏清查台湾酌筹善后事宜》,《台案汇录》庚集卷2。《台湾文献丛刊》本。
(44)《清高宗实录》卷322,乾隆十三年八月丁亥;卷1345,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乙亥。
(45)《清高宗实录》卷322,乾隆十三年八月丁亥。
(4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4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3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682页。
(48)《清高宗实录》卷1345,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乙亥。
(49)《清德宗实录》卷3,光绪元年正月戊申。
(50)李祖基:《论清代移民台湾之政策——兼评〈中国移民史〉之“台湾的移民垦殖”》,《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1)《大清律例》卷20,兵律,关津。
(52)《清史稿》卷120,食货。
(53)《大清律例》卷20,兵律,关津。
(54)《清朝通典》卷9,食货9。
(55)《清史稿》卷120,食货1。
(56)《清世宗实录》卷34,雍正三年七月辛丑。
(57)《清世宗实录》卷158,雍正十三年七月戊申。
(58)《清史稿》卷120,食货。
(5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60)《清史稿》卷120,食货。
(61)《清世宗实录》卷34,雍正三年七月辛丑。
(6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63)《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64)《清世宗实录》卷58,雍正五年六月戊子。
(65)《清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戊寅。
(66)《清高宗实录》卷167,乾隆十五年六月戊子。
(67)《清高宗实录》卷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庚申。
(68)《清高宗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壬申。
(69)王士性:《广志绎》卷5。
(70)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461—462页。
(71)《清高宗实录》卷429,乾隆十七年十二月。
(72)《清高宗实录》卷92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己卯。
(73)《清宣宗实录》卷428,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乙巳。
(74)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
(75)《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76)《清世宗实录》卷53,雍正五年二月庚辰。
(7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
(78)《清高宗实录》卷1009,乾隆四十一年五月甲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