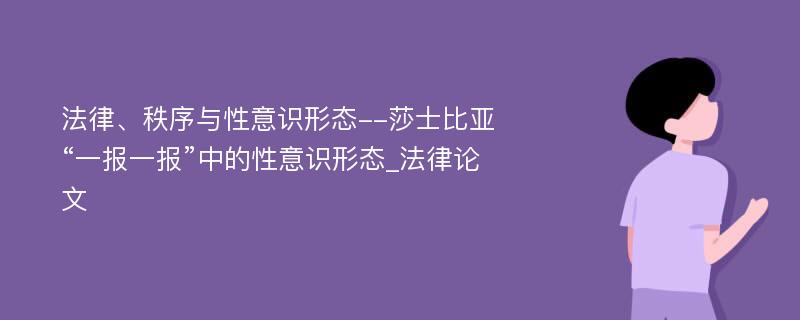
法律、秩序与性意识形态——莎剧《一报还一报》中的性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性意识论文,秩序论文,法律论文,莎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报还一报》中,公爵文森修作为统治者深感法律与人情的尺度不好把握。一方面,他自责由于自身的纵容,使严峻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法纪完全荡然扫地了”(朱生豪297)①。因此,他将权利暂交给安哲鲁,寄希望安哲鲁能够凭借他的名义重整颓风。另一方面,他也质疑是否有人,包括“平日拘谨严肃,从不承认他的感情会冲动”(朱生豪297)的安哲鲁,在权利的光环下,能真正地保持正人君子的“本性”。自此,一场法律与“本性”的斗争拉开帷幕。本文即探讨莎剧《一报还一报》中法律希望对身体与欲望进行规范从而产生的冲突,而这一冲突最终以欲望——确切地说,是男性的欲望作为一种内在的、本质的生物特性因而不可抑制地胜出而告终。这也宣告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冲破政治力量的束缚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然而,在法律与欲望的交锋中,男性的性欲望被构建为自然的、生物的、毋庸置疑的,而女性的身体与欲望却成为了法律与男性欲望角逐的场所、手段与目的而被物化。随着莎翁作品走上神坛,上述性意识形态在前意识层面成为毋庸置疑的生物特性及社会现实,成为性别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石之一,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帮助延续着不平等的男女等级社会。
安哲鲁上任后就用手中的权力,立即着手规范身体与欲望。他首先宣布关闭维也纳城郊所有妓院,城中的妓院要不是有人说情,也差点被关了。同时作为惩戒,又下令将未婚却偷吃了禁果的克劳狄奥处死。安哲鲁欲规范身体与欲望的种种措施遭到不同阶层大众的普遍诟病。如在经营窑子的咬弗动太太手下当酒保的庞贝就直言,要关闭窑子,除非将维也纳所有的年轻人都阉了;而如果要将风流鬼都杀了,则不消十年工夫,就要无头可杀了(朱生豪308-309)。而克劳狄奥的朋友路西奥则表示不解——“官府把奸淫罪看得如此认真吗?”(朱生豪294)克劳狄奥的妹妹依莎贝拉则认为她哥哥的罪恶并不超越人情,本性的引诱就是谁也避免不了:“问一问您自己的心,有没有犯过和我的弟弟同样的错误”(朱生豪315)。连安哲鲁的宠臣爱斯卡勒斯也说:“我知道你在道德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可是你要想想当你在感情用事的时候,万一时间凑合着地点,地点凑合着你的心愿,或是你自己任性的行动,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自己也很可能——在你一生中的某一时刻——犯下你现在给他判罪的错误,从而堕入法网”(朱生豪301)。
社会各阶层均认为安哲鲁的法令不近人情,人的本性——性是不得也不可能压抑的。而唯有安哲鲁,在大众看来,也许是理性的化身,是唯一能以理性规范身体与欲望的人。如路西奥就是这样评论安哲鲁的:“这个人的血就像冰雪一样冷,从来不觉得感情的冲动,欲念的刺激,只知道用读书克制的工夫锻炼他的德性”(朱生豪299)。然而当安哲鲁也以身试法,企图以权力迫使克劳狄奥的妹妹依莎贝拉就范,以交换她哥哥的性命时,在法律与人性的对抗中,法律的失败显而易见。安哲鲁作为政策与法令的制订者与实施者,以及唯一有可能对抗肉体欲望的男性,他的“沦陷”象征着肉体与欲望在这与法律的交锋中的完全胜利——贤德如安哲鲁,面对美色与贞洁也不能自己。
伊格尔顿曾这样评论过这场法与肉的较量:空洞的法律条文,无视肉体的主张与冲动,法令与欲望(包括法律本身想要达到的愿望)脱节,反而导致欲望不受节制(Eagleton 48)。在伊格尔顿看来,统治的智慧在于正视肉体的欲望,引导欲望朝着正确的方向宣泄,而非无视欲望的存在,一味压抑。乍一看伊格尔顿似乎道出了该剧的精髓。然而,伊格尔顿并未意识到,他所谓的肉体的主张与冲突以及欲望,更多指向的是男性的肉体欲望,而非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本文第二部分将集中论述被物化了的女性身体与欲望。
二
首先,女性的身体与欲望被忽视与压抑,并被演绎为具有颠覆宗教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潜力,因而充满危险。社会各个阶层对安哲鲁新颁法令的诟病无非集中在安哲鲁想要规范、控制性欲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不近人情,甚至是幼稚。然而,所有人,包括依莎贝拉,均未意识到如果说男性的性欲望如他们所想,不可全然抑制,然而女性的身体与欲望呢?至少在剧中,依莎贝拉是需要完全磨灭肉体的欲望,将身体献给上帝。她的贞洁成为了秩序,包括宗教秩序及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石。如作为修女,她洁身自好。“我倒希望我们皈依圣克来的姊妹们,应该守持更严格的戒律”(朱生豪298)。
依莎贝拉对自己能够守住戒律表现出充足的自信。当安德鲁向她提出用她的肉体换取他的权力以保全她兄弟的性命时,依莎贝拉是如此回答的:“为了我可怜的弟弟,也为了我自己,我宁愿接受死刑的宣判,让无情的皮鞭在我身上留下斑斑的血迹,我会把它当作鲜明的红玉;即使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会从容就死,像一个疲倦的旅人奔赴他的渴慕的安息,我却不愿让我的身体蒙上羞辱”(朱生豪322)。依莎贝拉宁死也不愿让肉体被玷污,尽管她拯救兄弟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面对欲望,依莎贝拉展示出了她超强的控制力。她拒绝将身体交与安哲鲁以换取自己兄弟的性命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依莎贝拉的贞洁又成为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基石。某种意义上而言,宗教秩序与社会秩序都有赖于女性对自身身体与欲望的控制。然而,社会秩序的基石,于莎翁而言,于伊格尔顿而言,却仰赖对男性欲望的正视及适当适时地给予宣泄的渠道。甚至剧中人物依莎贝拉也是如此认同的。她自信能守住戒律,也能超脱欲望,却认为包括安哲鲁在内的所有男人,都不能幸免于欲望的冲击;这也是她之所以为自己的兄弟辩解的原因,“如果你所说的脆弱,只限于我兄弟一人,其他千千万万的男人都毫无沾染,那么他倒是死得不冤了”(朱生豪323)。可见依莎贝拉深陷双重性道德标准的意识形态。很明显,不可压抑的是男性的肉欲,而女性的身体与欲望在剧中却成为了法律与男性欲望角逐的场所、手段与目的。实际上,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书写与针对男性—女性欲望采用的双重标准在戏剧解读时均不容忽视。
剧中依莎贝拉的身体成为了男性欲望与法律斗争的场所,也是宗教、法律与男性欲望的目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源头。不仅安哲鲁要用法律的公正交换依莎贝拉的身体;公爵在剧尾的时候也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依莎贝拉的欲望,“要是你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朱生豪380)。似乎也暗含着新的动摇社会秩序的危险又将要临近——这一切只缘于依莎贝拉的身体。这一点,在伊格尔顿的论证中得到了意外的承认:“法律与欲望有相似的冷漠之处:安哲鲁对依莎贝拉的欲望与法律中的执行条款一样冷酷且毫无人情”(Eagleton 49)。法律意欲在身体上题写。此时,男性的身体奋起对抗法律的冷漠与欲望,然而女性的身体与欲望却成为了法律与男性欲望的共同所指。最终,当男性的欲望在与法律的争斗中被合法化,其主体性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时,女性的身体与欲望却被物化,成为这场斗争中的场所与目的,法律继续在女性的身体上书写,而男性欲望也自此获得在女性身体上书写的有限的合法权。
不仅如此,女性的身体也成为化解男性欲望与法律的争拗的有效手段。公爵没有直接喝止安哲鲁的行为以伸张法律的正义,而是安排心仪安哲鲁的、本是其未婚妻的玛丽安娜隐秘中替换依莎贝拉成全了安哲鲁的欲望。而对安哲鲁的惩罚也只不过是罚他娶了玛丽安娜。至此,男性欲望的沟壑在与法律的周旋中得以填平。在公爵重归权位后,法律与人情的两难天平已向人性倾斜,法律显然必须考虑欲望的要求,确切一点说,是男性欲望的要求。公爵重归权位象征着秩序重回维也纳,以及“仁政”——考虑到男性欲望的仁政的开始。然而,读者在公爵最后对依莎贝拉肆无忌惮的要约中感受到的不是人文精神对女性的关怀,而是男性欲望不受约束的泛滥。
另外,不少读者认为咬弗动太太是剧中具有颠覆主流性意识形态能量的角色,笔者却不敢苟同。其一,其名字“Mrs.Overdone”就已暗示着她不过是男性欲望的被动承受者;其二,咬弗动太太的淫乱并不具有颠覆性,这是因为她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与欲望,而是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打仗的打仗去了,病死的病死了,上绞刑架的上绞刑架去了,本来有钱的穷下来了,我现在弄得没有主顾上门啦”(朱生豪292)。对咬弗动太太的刻画与对依莎贝拉的刻画并没有脱离将女性分为圣母与妓女的老套路。而剧中其他女性,如玛利安娜不过只是被操纵的木偶;朱丽叶与克劳狄奥私通后被安哲鲁斥为犯了比克劳狄奥更为深的罪孽,随着她的怀孕,她的母亲身份淹没了她的女性身份,她的身体带给社会的危险性被解除。
三
英国文学传统的象征人物莎士比亚,一直以来,都是“普世”价值观的代言人。本文的分析对被塑造为“普世”价值观的人文主义精神进行了更为冷静的关注,特别是这一人文价值观所折射出的性别政治问题。而要论证“普世”价值观背后所隐藏的性别政治问题,需要考问的是,是否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观?德里达指出,“不存在本质特征,只存在影响——即构建本质特征其带来的影响,或是解构本质特征带来的影响”(qtd.in Butler 1)。通过莎剧传递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批评家们对莎剧人文主义关怀的肯定,人文主义精神被构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而这一本质特征又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基石。
辛菲尔德认为,任何文化产品均非无辜,都不可能撇清与自身所处的体系的关系(Sinfield xxvi)。正因为如此,文化唯物主义者一直视文化产品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而文学作品,在班尼特看来,是重现及传递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一价值观将男性与女性角色冻结于理想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世界(Bennet 169-170)。因而,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理论家而言,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意识形态的分析,不是发掘作用于莎翁的意识形态,而更多是去探询一个本身受意识形态作用的,有时效性的主体的作品在性别意识形态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那么何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指为了达到维护特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用相应的手段作用、吸引、困扰以安排社会主体。意识形态总是将特殊的、复杂的及受特定历史、社会因素制约的意象与前意识构建为毋庸置疑的、简单的普世真理,这些‘真理’被打扮得象社会现实一样的真实”(Kavanagh 146)。要挑战特定的社会秩序——本文指向的是莎剧的“人文精神”中的性别秩序,首先要指出“毋庸置疑、简单的普世真理”背后的社会建构,及这一建构的影响及其策略。
上文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在与法律的交锋中,那种关于男性的欲望不可压抑的想法在与法的斗争中其主体地位被确立,其重要性连法理也要让步。男性欲望不可抑制这一看法因而被构建为毋庸置疑、简单的普世“真理”,且被打扮得像社会现实一般真实,从而使这一父权形态的性意识形态更加深入人心。随着莎士比亚的作品走上神坛,批评家们——包括伊格尔顿——欢呼的是莎翁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胜利。然而这一胜利更多的是男性欲望的胜利,女性的身体与欲望由于在这场法与肉的交锋中成为斗争的场所、手段与目的而被进一步物化而并未获得相同程度的正视及解放。所有这些正是父权性质的人文主义精神被构建为本质特征所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福柯对权力的重新解读使我们对构建的策略有更清醒的认识。福柯认为,人们过去习惯于将权力等同于法律权力,到今天已不完全如此。他反对将权力视为压抑人的司法机制,强调权力是具有创造性及技巧的。权力的运行机制会带来反抗与局部的斗争,与此同时,新的知识与反抗也产生了。而福柯更感兴趣的是权力的运行机制而不是谁拥有权力(qtd.in Smart,Feminism and the Power of Law 7)。
《一报还一报》剧中,让人感兴趣的不是法律作为权力机制的运行,而是人文精神与生物学作为权力其运行的机制、运行的技巧及带来的反抗以及新的知识的建立。通过与法律的交锋,中世纪时抹杀基本人性与肉欲的宗教与法令受到了挑战与反抗,对肉体与欲望的重新认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及生物科学知识其地位获得承认。然而,在新的知识产生的同时,新的反抗也产生了。如果说《一报还一报》在当时考问的是中世纪时抹灭人性与肉欲的宗教与法令,且在与法律的斗争中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扎根并稳固,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的语境下重读经典更多的应该是关注新知识,即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扎根后带来的新的反抗。这种反抗来自当代的女性主义学者对知识与知识的力量的重新审视。这其中就包括对占据主流意识地位的人文精神的审视。如史玛特就指出:“过去二十年女性主义明白清楚地探讨及削弱了知识是中立的及不分性别的观点。……首先被问的是知识是否是具有普遍性、中立性、客观性?研究表明,以主流地位出现的知识都具有其特殊性,是分性别的及主观的”(Smart,Law Crime and Sexuality 75)。本文的分析也充分说明,关注人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具有其主观性,是分性别的,然而它却以普遍的、中立的及不分性别的知识的姿态出现。从男性角度出发的知识被呈现为普遍的、并作为对世界认识的中立的及客观的知识回授给女性。随着莎士比亚作品因为颂扬人文主义精神而被奉为经典,这一价值观也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延续着男女有别的等级社会。因此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理论家而言,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更多是去解构一个本身受意识形态作用的、有时效性的主体的作品在资产阶级性别意识形态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及关注解构这一主体的作品带来的新的影响。
《一报还一报》最终以法律与人情的喜剧式和解结束——安哲鲁被迫娶了玛丽安娜以作为“惩罚”;克劳狄奥与茱丽叶则获得赦免;依莎贝拉带着她的贞洁重回修道院。公爵也复位,并且通过他的小试验,既赢得了名望,又获得了统治智慧,学会了如何把握法与人情的尺度。秩序重归维也纳,似乎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在本剧皆大欢喜的背后,男性的欲望被描述为内在的,不可控制的;而女性的身体与欲望由于在这场法与肉的争斗中成为斗争的场所、手段与目的而被进一步物化。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并非反对人文主义精神,而是反对有性别差异的人文主义精神。只有解构被构建为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其背后的性别歧视,才能发掘出女性的价值观,为知识构建不同于男权知识的本位基础。
注释:
①本文所引作品引文以朱生豪的译文为准,另参考了J.W.Lever,ed.,Measure for Measur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89)中的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