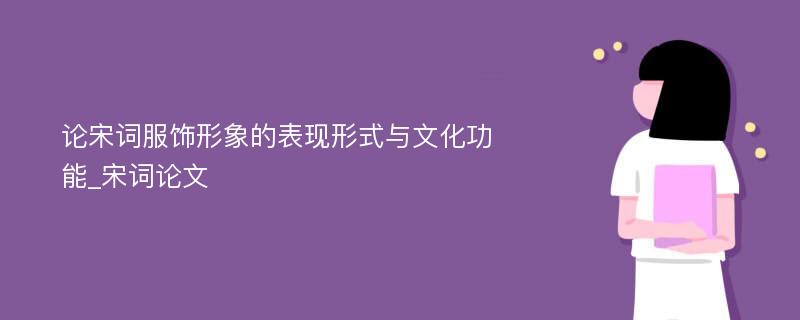
论宋词服饰意象的表现形态与文化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宋词论文,形态论文,功能论文,服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4-0123-04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服饰作为一种意象,被作家用来充实文学内容,使作品思想感情的表达更为生动传神,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从文化的角度看,“服饰器物是社会文化中最为普遍、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特征的内容”[1]。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由纯文学而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视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2]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文化产物,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我及其文化[3]。有宋一代,词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无论被尊为正宗的婉约词还是被贬为非正宗的豪放词,借绚丽缤纷的服饰以增强抒情的含蓄委婉与记事的真实感人,是它们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翻检《全宋词》,我们发现其中有关的服饰意象所占比例之大令人非常惊讶。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全宋词》收录的一千三百余家词人的近两万首作品中,通过服饰描写使作品产生艺术魅力的竟达三千九百余首,几近全部篇目的五分之一。仅将服饰意象作为宋词词牌者就有很多,既有直接选择某种服饰作词牌者,如《绿罗裙》《红罗袄》《金缕衣》《双带子》《绣带儿》《合欢带》《菩萨蛮》《女冠子》《百宝妆》《钗头凤》《御带花》《绮罗香》《玉珥坠金环》等,也有因服饰引发相关行为作词牌者,如《解佩环》《试香罗》《戛金钗》《选冠子》《惜红衣》《红袖扶》《题醉袖》《劈瑶钗》《湿罗衣》《翻翠袖》《系裙腰》《拂霓裳》《脱银袍》《夜捣衣》《送征衣》《翦征袍》《握金钗》《惜分钗》《貂裘换酒》《五彩结同心》《玉女摇仙佩》等。这些词牌的命名表明它们最初的来源无疑与服饰紧密相关。与前代其他文学样式比较,宋词更侧重用审美的眼光对日常生活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体验,平民化与大众化倾向极其突出。可以说宋词服饰意象不仅拥有丰富的表现形态,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
一、服饰意象是宋词审美观照的感性载体
凡是美的事物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出现的,“美的享受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4]。从审美角度看,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诗经》还是浪漫主义的《楚辞》,在描写人物尤其女性美时都曾借助服饰。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诗经·出其东门》),“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楚辞·山鬼》),都把服饰美作为人物外形美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由于它最早产生于胡夷里巷和歌楼酒馆,最初的作用也是娱宾遣兴,这就使它从起源就带有浓郁的抒情娱乐的特点。宋代士人的审美追求与前人相比,“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的质量和内容”[5]。宋词中对女性的描写,往往以宴会上的歌女或词人身边的侍女为主角,如晏殊“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石榴裙带,故将纤纤玉指,偷捻双风金线。”(《贺明朝》)晏几道“云随碧玉歌声转,雪绕红裙舞袖回”(《鹧鸪天》)。苏轼“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南歌子》)等。在他们的笔下,女性美是通过各种色彩明艳、制作精美的服饰来表现的。“色彩的感觉,是美感的最普及的形式。”[6]通过色彩缤纷的服饰来烘托人物和渲染气氛的写作方式在宋词中几乎触目皆是,反映了宋人比较普遍的审美风尚。
宋词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意象不仅给读者提供了视觉的舒适愉悦,也为后世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服饰潮流与时代风尚。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汴州人在上元夜前夕预赏圆月,‘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遭遇了国破家亡夫丧的惨痛经历后,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词,回忆当年在繁华的汴京度元宵佳节的情景:“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而豪放词人辛弃疾用“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青玉案·元夕》)写元宵夜闹花灯的热闹场面,用“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汉宫春·立春日》)写立春风俗,《宋史·礼志二十二》载:“立春,奉内朝者皆赐幡胜”,可知宋代皇帝在立春日赐百官金银幡以增节日的喜庆。上述词中的“蛾儿”、“雪柳”、“春幡”已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而是作为特定的意象,展现出宋代社会的服饰潮流。
北宋徽宗末年,世风浮靡奢侈,俗词艳曲十分流行。有一个名叫曹组的御用文人,颇受重用,徽宗曾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而曹组正是靠自己敏捷的才思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获得宠幸的。他在代表作《醉花阴》中写道:“九陌寒轻春尚早,灯火都门道。月下步莲人,薄薄香罗,峭窄春衫小。梅妆浅浅风蛾袅,随路听嬉笑。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此词写元宵灯会,但词人欣赏的不是火树银花的灯火,而是将目光凝聚在夜晚外出赏灯的美貌女子身上。她们“峭窄春衫”的穿戴,“梅妆浅淡”的装饰,都恰到好处且甚惹人眼。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宋迄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可是人类的审美观念无论古今却何其相似。这些美丽的服饰,既符合词人的审美心理,也顺应世俗的审美习惯。由于这些服饰的描写大都是率意而为、脱口而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词人从姿态各异、风姿绰约、娇媚动人的佳人身上所获得的审美感受,使现实社会世俗生活的一面未加雕饰地表露出来,因而广泛流传于民间。
二、服饰意象是宋词体现人物身份地位的显性标志
华夏民族是著名的“礼仪之邦”,礼是儒家所倡导的思想准则与行为规范。《礼记》对服饰及其穿戴就有严格的区分和全面的记述。两性有别,贵贱有等的儒家传统文化观念在宋词中也都得到了最为逼真的体现。即使在宋室南渡后,由于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词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代替婉约词人成为词坛的主体,他们不再像婉约词人那样惯写风花雪月和儿女情长,而是“以劲健遒逸为审美取向”[7],表现爱国热情和战争风云。在这种形势下,服饰意象似乎很容易被金戈铁马和刀光剑影所淡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服饰意象在豪放词中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豪放词中有大量奢华的服饰意象。如辛弃疾《鹊桥仙》:“豸冠风采,绣衣身价,曾把经纶少试。”“豸冠”即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下》云:“法冠,一日柱后。高五寸,以为纚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8]古人认为这种神兽能辨善恶,别曲直,故将它的形象用在法官身上,希望法官为民请命,秉公执法,既标明身份,也提醒着装者,带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再如刘过《沁园春》“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貂蝉争出,千官鳞集,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张元干《喜迁莺令》“文倚马,笔如椽。桂殿早登仙。旧游册府记当年,衮绣合貂蝉。”《宋史·舆服志五》记载“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奉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9]上述词中所描写的“玉带”、“猩袍”、“貂蝉”、“衮绣”等都表明穿戴者享有达官贵人的身份和地位。
不仅如此,按照男女有别的礼的规范,服饰所用的图案必须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刘子寰在《醉蓬莱·寿史令人》中描写一位贵族女性时用这样的词句:“象服鱼轩,疏封大国,齐眉千岁。”“象服”是古代贵夫人穿的一种特殊礼服,上面绘有各种图形作为装饰,“鱼轩”是古代贵族妇女所乘的车子,用鱼皮作为装饰,此词通过“象服鱼轩”两个特定的意象不但简明交代了祝寿的对象,而且突出了她的女性身份和所处的高贵地位。
与奢华服饰意象对应的朴素服饰意象在宋词中也颇引人注目。如苏轼《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刘克庄《摸鱼儿》“便披蓑、荷锄归去,何须身着宫锦”,叶梦得《鹧鸪天》“旁人不解青蓑意,犹说黄金宝带重”,胡寅《水调歌头》“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插钓鱼竿”,史浩《采莲舞》“草软沙平风掠岸,青蓑一钓烟江畔”,吴潜《祝英台近》“争似得江湖,烟蓑雨笠,不被蜗蝇系”等。“芒鞋”、“蓑衣”、“箬笠”和“羊裘”等服饰的材料均取其自然,它们的简陋随意直接显示出穿戴者的普通平凡。因此,文人常以此抒发返归自然、寄情山水的洒脱情怀,或表现他们远离污浊官场和喧嚣尘世的愿望及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
三、宋词服饰意象的内涵扩充与意蕴延伸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交流工具,而服饰作为人类不可缺少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服饰生发的语言,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的基础用语外,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作者可以进一步地注入其他概念或思想,如借比喻、拟人、暗示、象征、典故等手法来委婉含蓄地抒发感情与表达意绪,将其内涵和意蕴加以扩充、延伸。如晏几道的名作《临江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借“两重心字罗衣”的服饰意象不仅衬托了小苹之美,更暗示了作者与小苹之间已不是单纯的主客关系,而有两心相印之意,使服饰的外在形式寓含了内在意义。柳永《凤栖梧》中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王国维引申为追求事业的三种境界之一,赋予包含哲理的深刻象征意义。而它的原型意象大多是用来表现离情别绪的,如柳永《锦堂春》“坠髻慵梳,愁蛾懒画,心绪是事阑珊。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杨无咎《品令》“因甚自觉腰肢瘦,新来又宽裙幅”,晏几道《鹧鸪天》“歌渐咽,酒初醺。尽将红泪湿湘裙”,欧阳修《解仙佩》中的“有个人人牵系,泪成痕、滴尽罗衣”。这组词使我们发现,当人们为情所苦、憔悴难堪之时,“衣带渐宽”与“泪湿罗衣”正好能够被作为抒发离情别绪的特定意象,它们可以作为一种载体,将抽象的无形的情感化为有形的可感可触的对象,有利于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为了使词这种“诗余”、“小道”负载更丰富的内容,宋词人常常在描写服饰意象时用典故。如司马光《锦堂春》“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秦观《蝶恋花》“不必琵琶能触意,一樽自湿青衫泪”,均借用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来浓缩作者遭遇坎坷、仕途失意的落寞、悲凉和忧伤。晏几道《武陵春》“九日黄花如有意,依旧满珍丛。谁似龙山秋兴浓,吹帽落西风”,晏端礼《安公子》“帝里重阳好,又对短发来吹帽”,都用了“吹帽”的独特意象。“吹帽”典故最早出自《晋书·孟嘉传》:“(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知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体现了一种沉醉忘我、不拘小节的大家风度,同时也作为象征重九登高的典故在重阳词中频频出现,以表达在这一特殊节日里文人雅士的风流情怀。再如李弥逊《柳梢青·赵端礼生日》“蓝袍换了莱衣,庆岁岁、君恩屡锡”,借用“老莱衣”的典故表示孝养父母;刘克庄《贺新郎》“叹今人、布衣交薄,绨袍情少”,借用范雎顾念须贾赠绨袍的典故表示不忘旧恩情的高尚品质。可见这些服饰意象已包含着深邃的历史文化意义,词的内涵和意蕴也因此显得更为浑厚悠远而富于韵味。
在抒情方式上,宋词服饰意象继承了《诗经》比兴的优良传统,常用象征、比喻、借代等各种修辞手法来抒情达意。如王炎《临江仙·落梅》“吹香飘缟袂,脱迹委红裙”,李曾伯《声声慢·和韵赋江梅》“修洁孤高,凌霜傲雪,潇然尘外丰姿。一白无瑕,玉堂茅舍俱宜。飘飘羽衣缟袂,都不染富贵膏脂”,用洁白的衣袂来形容梅花,象征词人对高洁品质的执著追求。吕渭老《如梦令》“百和宝钗香配,短短同心霞带”,用“同心霞带”作为男女相爱的象征。而朱敦儒《临江仙》“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用分钗和破镜的典故比喻人世间亲朋好友的离别;李纲《喜迁莺》“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用“毡裘”借代少数民族;辛弃疾《摸鱼儿》“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用“翠袖”借代红颜知己;刘克庄《贺新郎》“问如何、十载尚青衫,诸侯客”,用“青衫”借代读书人等等,都赋予服饰更丰富的内涵。
四、服饰意象折射出宋词的生成机制与宋人深层文化心态
服饰作为人类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每个时代,从事各种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们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描述风土人情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或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笔触探进服饰的领域。但与宋前文学作品相比,宋词的服饰意象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已超过了前代且具有典型性。这种现象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宋代独特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又蕴蓄着宋人特有的文化心态。
首先,萌芽于晚唐五代的词在宋代所以能够获得迅猛发展,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宋太祖赵匡胤因“黄袍加身”而圆了帝王梦后,曾对文武大臣曾发表了一番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10]北宋一朝,虽有边患与党争之忧,但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相对比较稳定,故宋真宗曾曰:“天下无事,而大臣和乐,何过之有。”[11]最高统治者的耳提面命为文武大臣们享受荣华富贵提供了政治保障,使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消遣享乐。而对普通人来说,追求自由和寻找快乐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因此,在众多的宋词人中,无论是显赫文士还是落魄书生,都在词中大量表现了纵情游冶的享乐心理。前者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他一面高举诗文革新运动的大旗,提倡“道统”与“文统”,一面却手持彩笺书写下贪婪酒色、沉溺娱乐的急切心情,如《定风波》“粉面丽姝歌窈窕,清妙,尊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贪燕乐,自觉,年来白发满头新”;后者如长期在下层社会厮混的风流文人柳永,吟咏的也是“舞裀歌扇花光里,翻回雪、驻行云。绮席阑珊,凤灯明灭,谁是意中人”(《少年游》)。与前代文人相比,宋词人更趋向于从世俗生活中寻找人生的乐趣。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词作者提供了优裕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文人们才能踊跃写词;而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人们的视野才会拓宽,这就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来源。”[12]据史料记载,宋代的京都拥有民户百万,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以其人烟浩攘,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数万,不欲繁碎。”[13]三鼓前夜市不闭,五更又复开市,举凡天下货物无不毕集,瓦舍勾栏还演出百戏伎艺,繁华热闹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即使在南渡前后,虽然经历了金灭北宋的大浩劫,但此时仍是南宋文化的一个繁荣时期,“从朝廷大内到地方政府,乃至一般的官宦、富裕人家,弥漫着浓郁的纸醉金迷的享乐气氛”[14]。不仅仅文人士子可以置身于富庶奢侈的生活环境,在酒色歌舞中放纵声色,即使普通平民也有条件浸染其中,感受声色犬马带来的世俗的感官刺激。《渑水燕谈录》载:“华阳杨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15]。正是这种环境和氛围使词人们异口同声地夸赞生活的美好,更细腻地体味以至沉醉于温柔富贵乡的香艳和迷蒙。为了使这种刻骨铭心却也转瞬即逝的快感永驻心间,他们便在词中不厌其烦地刻画描述以满足享乐愿望。宋词中所描写的丰富多彩的服饰意象,不仅从侧面反映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市民阶层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宋词所具有的“娱乐性、艳情性、软媚性和通俗性”[16]的特点。
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性,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又暴露出词体在反映现实生活广阔性上所受的限制。当代著名词学家詹安泰指出:“过去的人都把‘宋词’和‘唐诗’、‘元曲’并提。如果就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看,宋词是比不上唐诗和元曲的;不但比不上唐诗和元曲,就是和宋代的诗、文比起来也有逊色。因而宋词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没有出现过诗中的杜甫和曲中的关汉卿这么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把宋词的评价提高到和唐诗、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而认为它可以为宋代的代表文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17]的确,歌儿舞女美丽的容貌、漂亮的服饰,达官贵人精美的宴席及雍容华丽的官袍玉带,在宋词中被这样津津有味、不厌其烦的展现,这也很容易使人感到厌倦并进而对宋词的价值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观照,把作品和那个特定的时代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思考而获得客观的评价。即应该从两个方面衡量宋词的价值,一是它是否表现了阶级矛盾、民族危亡的重大主题,一是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及世人的情感状态。宋词中涌现的大量服饰意象,如果用前者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令人失望;但从后者看,又很令人欣喜。因为在宋代这个道学风气极为浓厚的朝代,无论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还是南宋抗战词人辛弃疾、陈亮,抑或是经历了国破家亡重大人生变故的李清照、张炎,他们的词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服饰意象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热爱,在他们笔下,这些服饰意象都是有情、有境、有性灵的。从享受人生、珍惜生命的角度看,正如杨海明先生所言:“唐宋词人对于个体生命的分外珍惜,以及他们所愈加信奉的‘善待今生’和‘享受现世’的人生理念,就正体现了人的自我价值有所‘升值’的趋势。”[18]而“从文学艺术的职能看,将真实地体现有宋一代‘时代生活和情绪’的长短句歌词看作‘一代之文学’,还是十分合适的”[19]。唯有如此,对宋词的认识和评价才不致发生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