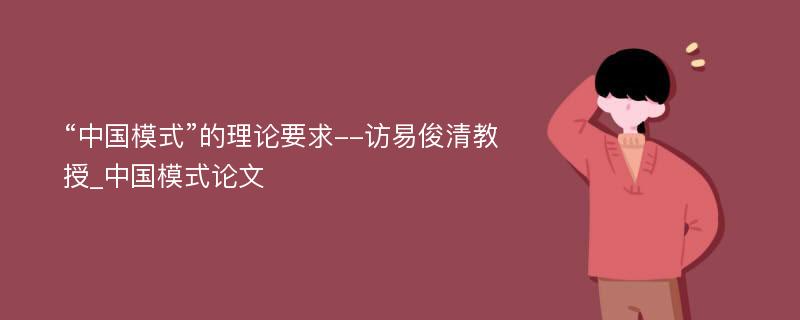
“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衣俊卿教授专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专访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家简介
衣俊卿,(1958—),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现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具体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
①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
“中国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而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记者:衣老师,近几年“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概念在国内外政界、经济界和理论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自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受到更大的关注,您是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讨论中,基础理论研究能够作些什么贡献?
衣俊卿:我认为这是十分积极的现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种既向世界和国际开放,又自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正在展示出特有的发展活力、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一方面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另一方面也要时刻保持理论的警醒,在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要看到中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依旧薄弱,看到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困难和压力。具体说来,如何使“中国模式”在普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如何使“中国模式”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对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等等,既是紧迫的实践课题,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一句话,“中国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而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记者:您能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自觉”这一命题作些解释吗?
衣俊卿:是这样的,当我强调要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时,并非断言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不具备理论内涵。恰恰相反,一方面,“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本身就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丰富内容;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分别从中国的视角或全球的视角,从经济的维度或政治的维度,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发展潜力等,作了许多理论探讨,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还有许多现实的和发展中的重大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和解决。实际上,目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认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并努力从中国的实践中借鉴经验,探索自己加快发展的途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态度上,既有能够相对比较公正和客观地评价和认识的明智人士,也有很多心怀戒备、警惕或敌意的人士,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问题持否定的评价,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国内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认识实际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其中既有过分偏重西方的模式而限制“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把“中国模式”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的偏颇做法;也有出于爱国主义热情,甚至出于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中国模式”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既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他国可以效仿”的乐观结论,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不好推广”的谨慎结论。总体上看,真正从人类社会演进和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中国经验,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相对比较少。这是我们应当正视的问题。我们常常强调要推动理论创新,要在深层次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寻求突破,在这种意义上,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最需要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
②“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
记者:从您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深层次理论研究相对缺乏,您能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吗?
衣俊卿:从总体上看,目前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而缺少哲学、价值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深层次研究。其结果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分析一般比较简单、比较直接,大多是从中国的经济成就、社会稳定等直接后果来论证这一模式的成功和价值,而缺少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视野,综合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存价值、文化价值的深度理论分析,缺少社会历史理论上的更高的升华,因此,往往无法展示出“中国模式”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全球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我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状况入手,来揭示造成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理论研究停留于一般的应用理论层面的深层次原因。我在《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发表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当做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而我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开放价值,强调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
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
我提出这一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我发现,“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本来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发现了这两个向度的分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而明显缺少自觉的“世界向度”。具体说来,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常常缺少自觉的国际比较和全球对话的维度,较少考虑如何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进入国际学术商谈和理论对话,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这样无疑大大降低了我们在事关人类社会进步和全球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发言权。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研究状况同我们上述探讨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状况密切相关,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记者:您的这一观点非常重要。经您这样一分析,问题的确很明显,目前大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确实属于单纯的“中国向度”的研究。您能把这种“单向度”的理论研究的缺陷具体分析一下吗?
衣俊卿:我认为,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宗旨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指导中国的实践,这并没有错,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一个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实践和创新不断发展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模式”这一发生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国度中的伟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理应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积极的理论贡献,它的深层次的理论诉求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在比较、碰撞与对话中,对之加以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而不能孤立地讨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那种缺乏自觉的“世界向度”,单独在中国的语境中或者仅仅在应用经济学的层面上解读“中国模式”,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把这种局限性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形是,两批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各自相对独立地、分别地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常常出现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或者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让人感觉这些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其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例如,有的学者更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限性的扬弃,忽略了民族文化通过积极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来推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丰富世界文化的内涵。这种脱离世界化而孤立地强调民族化和本土化,很容易降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甚至在逻辑上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导向海外一些学者的逻辑,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其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我以为,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绝不是要求这一理论只是与中国的实践有关的地方知识,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可以断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上的一些局限性妨碍了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论价值的阐发。
③高度关注国际对话中的理论阐释力和话语权
记者:那您能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应当如何自觉地推动“中国模式”的理论自觉作一些阐述吗?
衣俊卿: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探索解决的大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也是初步的和表层的。我想,至少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应当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冷静的、全面的和准确的判断与定位;二是要找到合适的途径对这种价值和意义进行合理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升华。而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自觉地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放视野,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互补的格局。
记者:请您分别阐述一下您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和基本的观点。
衣俊卿:关于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冷静的、全面的和准确的判断与定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应当避免把中国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所具有“中国特色”和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启示意义和价值对立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模式’他国可以效仿”的结论,还是“‘中国模式’不好推广”的结论,都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的意义上所得出的简单化的结论,其中都内涵着把某一种发展模式视作唯一正确的或合理的发展模式的理论预设。实际上,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都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这里,过分强调某一模式的特色和不可复制的唯一性,就会把这一模式变成纯粹的和狭隘的地方经验及地方知识,而过分强调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会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事实,用某一种作为真理化身的模式去剪裁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内涵。
在重大理论问题的国际主流理论对话和思想交锋中,在现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声音、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声音、左翼激进理论思潮的声音之外,应当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中国的理论声音。
显而易见,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消极的和有害的。合理的和全面的观点应当是,一方面,尊重各种发展模式的特色,既不否定,也不全盘照搬某一种模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揭示出各种发展模式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在交往、交流、学习、选择、借鉴、碰撞、交锋中汲取发展的营养和有益的要素。实际上,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正是在各种发展模式的交互作用中选择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探讨和强调“中国模式”,不是为了在全球推广我们的模式、取代其他的发展模式,而是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和国际交流,既丰富发展自身又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作出积极的推动。
记者:这也就是您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互补的格局吧?
衣俊卿:是的。基于对“中国模式”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判断与定位,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找到合适的途径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合理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升华,也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解决路径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通过积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来升华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这一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是全球化视野中的理论对话、思想交锋和文化交流。全球化进程越来越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又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其他有生命力的理论)在任何国度的发展和创新都既要关注本土问题与民族问题,又要同时关注世界问题与全球问题,特别要在相互关联的视野中关注本土问题与世界问题;都既要积极吸纳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又要积极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增加活力。
具体说来,这种围绕着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所开展的全球化视野中的理论对话、思想交锋和文化交流,强调的不是封闭的、自说自话的“话语权”,而是国际对话中的理论阐释力和话语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正如“蝴蝶效应”所形象地揭示的那样,不同地域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复杂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本土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任何世界问题同时也是本土问题。例如,就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微观到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石油问题、期货问题、股市问题、环境问题等,宏观到价值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等,都既是中国问题,也同时是世界问题和全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重要的不是固守我们自己的话语方式和独特价值而防御性地与众不同,不是在国际上主流理论对话和思想碰撞之外独自阐述我们的见解,而是要基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基于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在积极主动的国际交流与对话中,在全球普遍关注的话语、价值和重大问题上形成我们的理论影响力。特别是在事关人的存在、自由、尊严、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国际主流理论对话和思想交锋中,在现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声音、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声音、左翼激进理论思潮的声音之外,应当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中国的理论声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模式”的深层次的理论诉求。
记者:感谢您接受本报专访!也感谢您对开展关于“中国模式”的深层理论研究的独特见解。
衣俊卿:这只是一些初步的见解,很不成熟,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衣俊卿论文; 中国道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中国特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