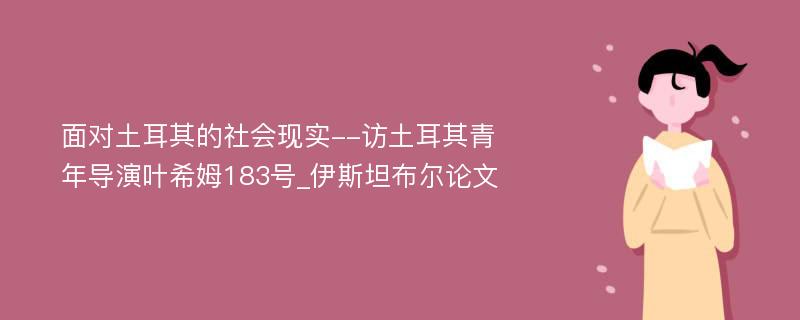
直面土耳其的社会现实——访土耳其青年导演耶希姆#183;乌斯塔奥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耳其论文,直面论文,乌斯论文,导演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土耳其电影在年轻一代导演的努力下有了明显的复苏。由于每年的影片产量极低,面临经费上的困难,迫使这些年轻导演以更高超的专业技能,以对本国社会和政治现实更敏锐的观察,表现出一种新的成熟。除了努里·比尔盖·杰伊兰(《五月的云》)、泽基·德米尔库布兹(《第三页》)、德尔维什·扎伊姆(《大象与草》)、伊尔马兹·阿尔斯兰(《伤口》)这些名字,耶希姆·乌斯塔奥卢也证明了她是土耳其新浪潮中最值得期待的导演之一。
建筑师出身的耶希姆·乌斯塔奥卢,名下已有两部故事片和几部短片。她的第一部故事片《轨迹》,在1994年的伊斯坦布尔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土耳其电影年度奖,但却从未在国内影院发行。故事讲的是一位警探在伊斯坦布尔的城郊调查一起罪案的经过。影片营造的怪诞氛围,在强烈可感的建筑美学的影响下而得到强化。1999年,乌斯塔奥卢的第二部故事片《去往太阳的旅程》标志着她导演生涯的转折点,也为她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除了获得1999年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电影节的最佳土耳其影片和最佳电影导演奖之外,《去往太阳的旅程》还在1999年柏林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欧洲影片以及和平奖,并在世界各地获得超过20种以上的国际奖。
《去往太阳的旅程》讲述了两个年轻人的友情故事,虽然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库尔德人,但原本都住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安纳托利亚,且阴差阳错地来到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库尔德青年贝尔赞的暴死,使得他的土耳其朋友穆罕默德,通过去往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旅行,痛苦地意识到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对立冲突的社会现实。
《去往太阳的旅程》并不是涉及库尔德问题的第一部土耳其影片。1982年,谢里夫·格伦代替当时被羁押狱中的耶尔马兹·居内伊执导了《约尔》,其中有几个段落表现了军队对库尔德人叛乱——即所谓的“走私行为”——的残酷镇压。在荣膺1982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但却被禁影了15年之后,于1999年在土耳其的电影院发行上映。赖斯·切利克摄制于1996年的《让那里也被照亮》,也描写了土耳其军方与库尔德叛乱势力,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战斗,一位土耳其军官与一位叛乱者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在冰雪覆盖的高山上展开。
但是,《去往太阳的旅程》通过一种不同的手法,标志着土耳其电影在看待库尔德问题上的转变。不再拘泥于军方与反叛者之间尖锐对立这种典型关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是通过一个普通村民,换言之,即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加以表现的。穆罕默德借助他与库尔德人结下的情谊,逐渐地体味出土耳其的社会现实。通过把这个友情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伊斯坦布尔,《去往太阳的旅程》也探讨了在当今土耳其也很少触及的问题: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库尔德人,为逃避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恶劣处境和战火,他们寄希望于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到更好的未来,可到头来,还是终结于这座城市的贫民窟里。借再现出这样一个“另类的土耳其”的机会,耶希姆·乌斯塔奥卢在土耳其非常敏感的问题——对库尔德人群体的歧视——上采取了明确而无畏的态度。
被宣扬为“一部和平和友谊的影片”,这样一个公开而又明确的讯息当然不会让土耳其人无动于衷。媒体对该片的反应可谓是天壤之别。一些报之以热情的批评家强调的是导演敢于面对问题的“勇气”。而另一些批评家则持相对的否定态度,争辩说影片只表现了在库尔德问题上实行军事镇压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主流批评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去往太阳的旅程》是一部拍给西方观众看的影片,代表的是土耳其的东方观。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被捕,由此引发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美国的发行商都不愿推出这样一部影片。1999年4月,民族主义行动党在国内选举中获胜,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仍然不利于影片的发行。经过一年多的协商之后,《去往太阳的旅程》终于在2000年3月得以在数量有限的独立电影院线上映,但也只发行了8部拷贝。影片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东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都上映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
《去往太阳的旅程》由此成为探讨土耳其文化特性的年轻导演们的参照物。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的卡齐姆·厄兹(《土地》)和侯赛因·卡贝拉(《博兰》),都是在借鉴《去往太阳的旅程》的前提下,试图在土耳其拍摄出库尔德影片。
在奔波于外国电影节展映她的影片的间隙里,耶希姆·乌斯塔奥卢在家中与我晤面,畅谈《去往太阳的旅程》。
电影人:《去往太阳的旅程》是如何立项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主题?
耶希姆·乌斯塔奥卢:1994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影片《轨迹》之后,土耳其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乱。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目睹了安纳托利亚人民的被迫迁徙。促生此片的主要是两条我从报上读到的消息。头一条说的是“十字标记”村庄。地处土耳其东南部的这些村庄,凡被标上这样的标记者,不是遭焚毁就是被驱遣,原因就是它们不和当局合作,特别是那些不参加“保护”系统(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些村庄从政府接受钱财和武器用以自卫或与叛乱武装作战——尼古拉斯·蒙索)的村庄。库尔德人的村庄有的参加了这个系统,有些则没有。不合作的村民的户门上就被涂上了这样的十字。
然后,我又读到了一条关于“流动的村庄”的消息,有个大的建设项目牵扯到了这些村子,这个工程肯定会给土耳其整个东南部地区提供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但是,有很多村民将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除此之外,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迹也会因此而荡然无存。同时,战争还在进行。看着我们周围那些安纳托利亚人民流离失所,我开始思考战争。而当时,可以说是战火正酣。我感觉,我们当时并不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关于库尔德人民的情况,我们只能从官方严密控制的媒体获知。所以我决定写一个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故事,以便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我写出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年轻的库尔德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土耳其男人。通过处理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这个土耳其人做了一次沟通之旅,一步一步地,由浅入深地发掘出移民生活的种种状况。于我而言,这是土耳其社会不得不揭示出来的主要问题。
对我来说,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并非天真幼稚之人,所以我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我多次去往土耳其东部,为的就是见到定居在那里的本地人。这使我完成完整脚本的时间大大延长。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做出了决定,要和生活中的真人合作,不在专业圈子里挑选演员。面对这样的主题,我不想有任何矫饰或做作,我必须得和那些有相似经验和类似背景的人一起工作。
电影人:《去往太阳的旅程》集中讲述的是伊斯坦布尔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他们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库尔德人,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乌斯塔奥卢:正像我说过的那样,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发现主题或形成主题的过程。整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库尔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增进彼此的了解并结下友情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帮助观众理解故事的两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于我而言,影片更多关注的是库尔德问题的发掘,更进一步说,是库尔德人的身份认同。
故事从身处伊斯坦布尔中心的穆罕默德开始,他是个很天真的土耳其人,幼稚地梦想着能在这座大城市生活下去。没想到的是,他的肤色竟然成了问题。就因为比一般人偏黑一些,他被别人当成了库尔德人对待。之后,他遇到了贝尔赞并与之交上了朋友,贝尔赞才是地道的库尔德人,而且不像穆罕默德那么天真。他有着强烈的身份感或个性。故事就围绕着贝尔赞展开,他是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家乡被赶出来的,失去了那里的所有朋友。后来,贝尔赞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示威集会上被警察打死。穆罕默德决定按照传统习俗,长途跋涉,将最好朋友的尸体运回他出生的村庄。他承担了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实际上承担的是别人的梦想——这使他在旅程结束时成长为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如何成人的故事。他看到了现实,我们则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是从他的视角来讲述的,这个视角与我的视角很接近,从西到东的旅程反映的是对土耳其的社会现实由浅入深的认识。
电影人:你所谓的“土耳其社会现实”指的是什么?
乌斯塔奥卢:影片中反映出来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以及国内迁徙带来的后果——安纳托利亚人民多半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周边的贫民窟里——以及他们怎样成了“失踪人口”,遭受折磨,失去他们在“流动地区”的家园,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它们应该得到讨论。
电影人:你是想说,在土耳其,之所以有针对库尔德人的歧视,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吗?
乌斯塔奥卢:是的。土耳其存在对库尔德人的偏见。首先,从主流意识形态看,他们比土耳其人黑。只要你是这种肤色偏黑的人,再加之出身于社会底层,你很容易被当作移民看待。你会和当局发生各种各样的麻烦。我就是想在《去往太阳的旅程》中打破这种对库尔德人的偏见,以及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这是种族主义,是种族歧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择穆罕默德,一个肤色很黑的土耳其人,贝尔赞,一个库尔德人,并把他们捏合到一块儿的原因。片中穆罕默德的女朋友自扮自身,她就是个库尔德人,但她的肤色却很白。歧视不单单与肤色有关,还牵扯到一旦知道对方是库尔德人之后,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这一点使问题有了相当的普遍性,尽管影片是把它作为国内问题来处理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都会联想到他们自身社会存在的类似问题。
电影人:《去往太阳的旅程》的演员都来自何方?
乌斯塔奥卢:他们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着眼于通过电影、戏剧和音乐表达他们的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我在筹拍这部影片的过程中与这个组织逐渐熟悉起来。这是我为了解库尔德文化、他们的身份感以及他们的语言去实地走访的第一个地方。我几乎天天去。就当时来讲,他们对拍电影不很热心,可我却观看到了纳兹米·基里克的戏剧。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天生的演员,才华横溢。然后我又见到了内夫鲁埃·巴兹。我把故事做了一定修改以适应他的年龄。试镜之后我选定了他们3个。他们都很有能力,只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训练他们。排练期大概用了一年。
演出人员来自真实的生活。我从没用过任何一位临时演员,即便是在伊斯坦布尔。所有你在影片中看到的人都是在他们生活的地方被摄入镜头的,要么就是来自街头巷尾。
电影人:审查制度方面就没遇到困难吗?
乌斯塔奥卢:拍摄曾被叫停一段时间,我们只得3个月后再开始。影片杀青时我们向文化部申请发行许可,没太费事就拿到了。那是在1999年柏林电影节全球首映之后,影片在电影节上获了两项奖。然后,1999年的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电影节上放映了此片。我们尝试与发行商接洽,但是,都吃了闭门羹。我们面对的是主流发行商针对此片的“封港令”。一年之后,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因为影片的主题时间性很强,所以我们决定靠自己发行。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迪亚巴克尔以及其他城市的小影院联系,我们自己给影片下了“开港令”。在4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7万土耳其人观看了此片。
电影人:土耳其媒体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乌斯塔奥卢:媒体的反应相当冷淡。我认为影片需要更多的讨论,而这一主题在1999年的时候无疑显得更加重要(1999年2月,阿卜杜拉·厄贾兰,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在肯尼亚被捕并被引渡到土耳其,对其进行的审判从6月份开始——尼古拉斯·蒙索)。在土耳其,对我这部影片的主要批评,说它是拍给西方人看的。除了一些写得很好的影评文章之外,批评家们都不急于接受《去往太阳的旅程》。影片承载的社会评论的分量,对媒体而言,显得过于沉重了。否定性的评论也涉及到影片的美学方面。
电影人:这么多土耳其评论家排斥这部影片,你做何解释?
乌斯塔奥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因循守旧。批评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土耳其是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国家,所以,要做自我批评很难。当今的土耳其人民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他们不愿意听到存在严重问题这样的话。我也在一些旅居海外的土耳其观众中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环境优越。他们不愿意知道土耳其面临着这样的国内问题。他们愿意相信土耳其已是一个很现代的国家。他们看到这样描绘他们的祖国,感觉心里别扭。
电影人:另一方面,有些评论家赞扬你为“土耳其的肯·洛奇。”
乌斯塔奥卢:批评家说什么的都有。我喜欢肯·洛奇最早期的作品,它们反映的是工人阶级及其社会问题。土耳其的一部分批评家也喜欢拿其他导演的作品进行这种类似的比较,比如塞奥·安耶洛普洛斯或伊尔马兹·居内伊。可居内伊的时代已经过去太久了。长期以来,批评家们一直在等待土耳其电影发生点儿什么。他们说我的影片有着与居内伊的作品同样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手法。
电影人:土耳其媒体中有对《去往太阳的旅程》热情赞誉的,尤其看重导演敢于直面这类问题的“勇气”。但是,他们中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种主要意见。第一种认为,这部着眼于平民,或者说普通市民的影片,只反映了土耳其现实问题的一个方面。
乌斯塔奥卢:我不同意。我的影片表现了存在于土耳其社会的压力。它并不涉及土耳其军方与库尔德工人党叛乱武装之间的战争。我要揭示的是日常存在的种族主义,以及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这些压力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发挥效用。当然了,更早还可以推及奥斯曼帝国时代;但与这些问题联系尤为密切的,是将土耳其共和国确立为现代国家,视所有其他种族为“他者”,而不是理念相同的异族,而我们大家却要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下“生活在一起”。像以前的历朝历代那样。
电影人:持否定意见的批评家还有另一种论据。指《去往太阳的旅程》是拍给西方观众看的。他们中的一位,在论及影片的种族定向,尤其在讨论到影片在古奥斯曼客店或在东南部地区选取日落景观时,甚至还引用了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你如何解释这部影片在国外获奖,好评如潮,却在国内遭到如此冷遇呢?
乌斯塔奥卢:我无法理解批评家何以觉得《去往太阳的旅程》是为西方观众制作的。这是一部起用实际存在的本土人演绎土耳其现实的影片。我们为影片的公映而去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在土耳其被视为土耳其人的首都——尼古拉斯·蒙索)。那里的观众都很惊奇。我们在凡城(靠近伊朗边境的省会城市——尼古拉斯·蒙索)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影片也在阿迪亚曼和乌尔法上映。我永远忘不了当地人的反应。他们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他们中有人在哭泣,有人想与我们攀谈。有些人感触很深,甚至感动得无法言语。他们在大银幕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如果说影片能在感情上打动生活在相同境况,面对着在故事中看到的相同问题的广大观众,怎么能说这是一部拍给西方观众看的影片呢?这也不是一部“东方的”或探讨“东方主义”的影片。它是放给我们看的,我们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