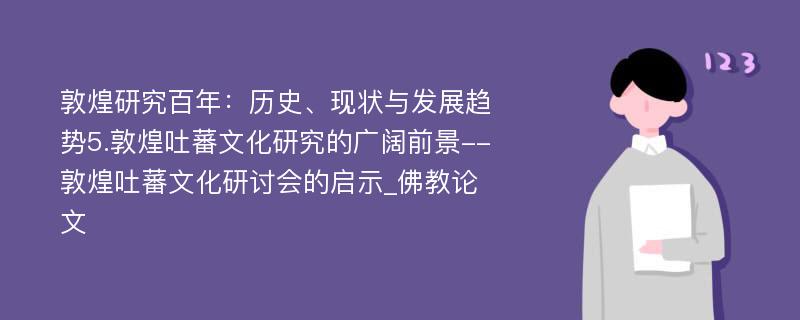
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5.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前景广阔——“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敦煌论文,文化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地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会议回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成就,分别从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敦煌与吐蕃历史、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敦煌吐蕃文献、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作了深入的讨论,解决或初步解决了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语言学、佛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同时在一些领域有了重大发现和突破。这次会议为我们展示了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研究,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象雄语、苯教文献,对藏族早期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国内外藏学界百年以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成果丰硕。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在回顾以往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前人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从敦煌藏文文献中挖掘出一些吐蕃原始宗教和自然崇拜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更为重要的,康巴地区一直保存着较多的藏族原始宗教(多为苯教)的遗迹遗物,近年来在西藏地区又发现大量的苯教遗迹和文献,在这次会议上都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使藏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足可以改写藏族历史。
敦煌与吐蕃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百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最活跃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对吐蕃历史的系统研究,实际上也就是从敦煌藏经洞文献面世之后开始的;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和敦煌藏文文献是记录反映吐蕃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以往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了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在吐蕃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次会议向我们展示,敦煌藏文文献和敦煌石窟资料在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仔细调查、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吐蕃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敦煌吐蕃时期的石窟艺术,历来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这次会议上有几篇关于吐蕃时期石窟个案的研究,无论理论和方法,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突出的创新,也为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特别是会议上公布的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的研究成果,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艺术的风貌,对敦煌石窟中相关内容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目前国内外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总数已近15000多件,其中海外8000多件,国内甘肃以外各地(含台、港地区)共300余件,甘肃省内藏6600余件。百余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和研究过的仅千件左右,主要在社会文书和佛教史传类文献方面。而大量的佛经和佛教文献都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敦煌藏文文献与汉文文献一样,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而佛教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佛经。百余年的研究工作也大致相似:佛经和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十分薄弱。法藏敦煌文献已经公布的2200多号藏文文献中,1299号以后的基本上是佛经和佛教文献,而这一部分文献基本上没有人进行过研究;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也基本上没有进行过研究。因此,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才重新起步,有如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随便选取一份文献,甚至一个名词,一个专题等,都可以进行研究(实际上这种方法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当年我们作汉文文献,一起步就显示出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母语比外国学者明显的语言优势。研究藏文文献也是一样,无论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藏族学者都表现出研究自己母语的独特优势。会议上有关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藏文写经中的报废经页的研究等,都让人耳目一新。另外,会议上在对国内外以往的研究(包括一些权威性的研究)的不足和失误方面的评议和指正,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会议上还将建立吐蕃写本研究的文法体系定向问题重新特别提出;吐蕃文献浩如烟海,建立自己的文法体系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关于敦煌吐蕃时期汉文文献的研究,以往也有大量成果,而以后无论是佛教文献还是社会文书,都需要与藏文文献的结合研究。而且,敦煌吐蕃文献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无论是对敦煌吐蕃时期历史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对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意义。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进行大吐蕃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新课题。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吐蕃时期所占领的中国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及中亚地区的情况。吐蕃最强盛时期,统治有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亚的大批疆土。敦煌之外,青藏作为吐蕃本土保存了比较多的遗迹,而西南地区现存的遗迹也为数不少,但对这方面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也是刚刚起步。当然,在敦煌吐蕃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这次会议上也只是涉及了一部分,更多的研究领域还有待开拓。
这次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也为笔者个人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几年,由我主持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先后被列为敦煌研究院重大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敦煌藏文文献和敦煌吐蕃时期的石窟以及百余年来国内外研究状况,对敦煌这一地区在吐蕃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一文,基于敦煌吐蕃历史文化遗迹遗物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从敦煌历史文化底蕴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在敦煌的政治制度、吐蕃封建经济的确立、以译写佛经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文化事业、吐蕃史传在敦煌编纂及其意义、敦煌石窟与吐蕃佛教文化、吐蕃在敦煌的文化交流、吐蕃统治对周边及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证,提出了敦煌曾经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的论断。特别指出吐蕃在敦煌完成了封建经济改革和封建化过程,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了大量佛经并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各地,吐蕃灭亡后及统治敦煌结束后汉蕃各族文人仿效唐朝的官修史志制度在敦煌编纂吐蕃史志三个方面的史实和意义。令我特别激动和兴奋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西藏大学图书馆的西热桑布先生发表了《卓卡寺所藏吐蕃时期〈喇蚌经〉之考》,公布了西藏山南隆子县卓卡寺新发现吐蕃时期的《喇蚌经》,即吐蕃热巴巾和朗达玛时期的赞普御用经书,内容为《十万般若颂》;我一眼看出《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在纸质、尺寸、书写格式、装帧形式等各方面的一致之处,认定《喇蚌经》就是在敦煌抄写后运到西藏供奉给赞普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在《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演讲中,根据敦煌方面的记载,已经论及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了大量佛经并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各地;经核对,《喇蚌经》除上前述与敦煌写经的一致之处外,更重要的是部分写经校经人名题记与敦煌博物馆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经完全相同;进而通过对敦煌市博物馆藏《十万般若颂》的考察,与会的汉、藏族学者们都赞同或默认了我的这一推论。因此,《喇蚌经》是西藏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敦煌写经,它是唐代吐蕃和敦煌历史上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以及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历史见证,无论对敦煌研究还是吐蕃研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另据透露,西藏首府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和山南地区桑白县的巴郎却康、洛扎县的色卡古托寺等处也保存有吐蕃时期的写经。西藏保存了一千多年前的敦煌写经,这就从空间上为敦煌吐蕃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另外,我在多年从事敦煌石窟营造历史的研究中,对敦煌晚期石窟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敦煌石窟的晚期,由于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兴起和广泛流传,给徘徊二百多年的敦煌石窟营造,展现出一个崭新的时期,石窟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莫高窟和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五个庙等地的西夏、蒙古和元代的壁画,可以说是敦煌佛教壁画的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时期。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藏传佛教艺术所注入的活力,我称之为敦煌石窟营造史上的复兴时期,并写进了2002年出版的《敦煌石窟营造史导论》,但因资料所限,对这一问题并未做出深刻的阐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近年在西藏西部的石窟艺术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次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他们发表了这一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敦煌石窟晚期的艺术提供了很大帮助。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艺术,展示了与敦煌晚期石窟艺术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使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这是敦煌吐蕃文化的延续。如果说,敦煌石窟在她的最盛期,迎来吐蕃对敦煌的管辖,因而对吐蕃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到敦煌石窟濒临衰竭的晚期,是吐蕃的佛教艺术反哺敦煌,给了敦煌石窟艺术新的活力!这就又为我们从事敦煌学研究和藏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本组稿件的组稿、审稿,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大力支持)
标签:佛教论文; 藏文论文; 敦煌石窟论文; 文化论文; 吐蕃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敦煌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献论文; 敦煌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