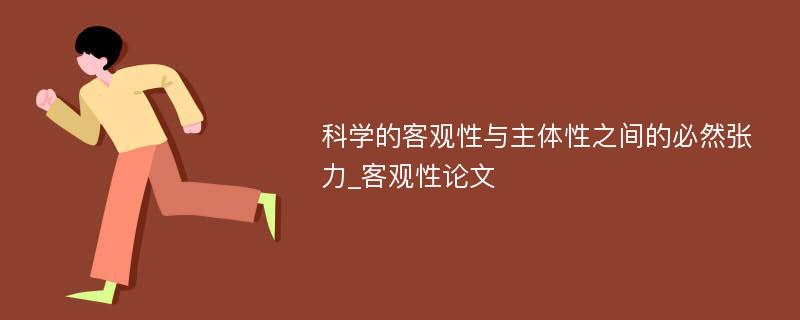
必要的张力:在科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观性论文,客观性论文,科学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3-0030-10
一、反对科学主观主义
科学包含主观性,主观性在科学中拥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流派,比如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后库恩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文化相对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却把科学的主观性推向极端,从而走向主观主义乃至观念论。我们要立即申明:科学中的主观主义或科学主观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反对。
例如,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不是客观的,人消融了客观性。凯库声称:“在人的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我们只能像旁观者一样目睹自然的美丽的舞蹈。但是,在今天,我们处在划时代的尖顶:从是被动的自然观察者到是主动的自然舞蹈动作的设计者。正是这个信条,形成了远见的中心信息。”①威尔金森在探讨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的限度和客观性的限度时,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某一水准上,某种将以基本的方式包含在人的本性中的东西,可能消融和代替客观性,而人正是因这样的客观性认为它自己是从外部考察自然的;因此,自然将不在人之外,而是要依赖人对它的解释:宇宙是人工制品。②
这显然是从本体论上否认科学的客观性,或者说否认科学的本体论的客观性。这种主观主义的观点是违背常识和理性的:它不仅与宇宙史、自然史格格不入,而且恣意夸大了人的主观性的作用——没有客观实在或自然界,你能凭空设计理论?你又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能制造宇宙本身?你能制造的,至多只是宇宙观或世界图像而已。
一些学者认为,科学理论是主观的,是纯粹的虚构和捏造,与自然界毫不相干。爱丁顿提出,科学理论是我们嵌入或投射到自然界的:“我们业已发现,在科学进步已经达到的最远处,精神不过是从自然界中重新获得它自己嵌入自然界之物。在未知的海岸边,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脚印。于是便设计出一种又一种的深奥理论去说明它的由来。终于,我们成功地再造出脚印的主人。嗳,原来就是我们自己。”③萨根(C.Sagan)在《恶魔经常出没的世界》中也有相关论述。④这一切,显然是从认识论上否认科学的客观性,或者说否认科学的认识论的客观性。
我们在讨论科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时,对此已经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和必要的澄清,此处再适当强调一下。迪昂承认:“任何物理学理论的形成总是通过一系列润色进行的,它使体系从无定形的第一批草图逐渐达至比较精致完美的状态;在每一次润色时,物理学家自由的首创精神都受到变化多端的环境、他人的观点和事实教导的东西的忠告、强调、指导以及有时是绝对的命令。”但是,他也严正地指出:“历史向我们表明,没有一个物理学理论是纯粹虚构、凭空捏造的。”⑤索卡尔针对科学中的主观主义思潮驳斥道:
学术界流行的主观主义的学术理论,恰恰是由那些试图模糊明显的真理的内容构成的,其最荒谬的部分是通过含糊和矫饰的语言,把所有存在都给抹杀掉了……如果所有的都是叙事或“文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了;甚至物理学也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分支。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的都是修饰或“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相容性也是多余的了。一种被人们早已抛弃了的理论诡辩也同样能够充当理论的功能。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论的一个优点;隐晦、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⑥
科尔从三个主要方面批评了建构论者:第一,他们无法说明为什么有些成果被接纳为核心知识,而其他成果却被忽略或被拒绝;第二,在分析问题时,他们把社会影响同认识影响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的观点就显得多余了;第三,他们无法说明特定的社会因素与特定的认识成果之间的联系,只是停留在一般论证上,而一般论证是需要靠具体的解释来支撑的。⑦
由极端的科学主观性导致的主观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观念论(唯心论)。对此,I·G·巴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说:许多著述者认为,新物理学为形而上学的观念论提供了证据,或者甚至为唯灵论的宇宙观提供了证据。已经提出的论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观察者的新作用被认为具有精神高于物质之意。例如有人认为,空间是我们在其中观察客体的秩序或安排,时间只是我们用以测量存在事件的次序,它们没有独立的客观实在性;原子现象也依赖于主体和精神。对此的答复是,“观察者的涉入”指的是观察过程,而不是这类心理状态。“参照框架”指的是测量器械,而不是指头脑或人。的确,我们讨论的是相互作用和关系,而不是孤立的物体,但我们是用物理工具进行研究的。是测量工具,而不是作为人的观察者影响了所获得的测量结果。况且,承认主体在材料中的作用不一定导致我们忽视客体的作用。第二种主张是,现在的物质无实体。物质显而易见的坚实性和持久性曾使我们相信其实在性。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原子由虚空和几率波组成,质量远非不灭,它只是非物质的能的暂时形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非物质”一词的模糊性做出评论。“非物质”一词产生了容易导致误会的“精神”和“心灵”这样的含义。其实,能量、电场、辐射以及几率波与台球般的原子模型一样,都具有物理属性,并且总是与实验观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牛顿时代,有人认为引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因为它是无形的和远距离发生作用的。我们不要把物理语言和日常经验(所谓物质的坚实性和持久性)混淆在一起。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原子世界的组成是不可用日常语言描述的,它们不具有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的属性,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使用“非物质”这样的词汇。第三个论点是,现代物理学具有数学的特征,这表明实在基本上是精神性的。有人甚至认为,科学理论是纯粹思维的结构,宇宙更像一个巨大的思想而不是机器,世界应该被看做是宇宙心灵的思想。确实,现代物理学的符号体系是高度抽象的,形式属性的确起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用(例如对称性、拓扑学形式、变换不变性、广义化的多维空间)。但是,如果将其说成是“纯数学”的,则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因为它的公理并不是任意杜撰的,而且它总是要经受实验检验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观察与物理理论的数学方程式之间只有十分间接的关系。⑧
至此,我们打算较为详细地探讨一下自然定律(自然规律)或科学定律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在讨论“自然定律或科学定律是自然界固有的,还是人创造的?”提问时,我们已经涉及这一点,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关于自然定律的含义和对其的理解,保罗·戴维斯认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自然定律”或“自然规律”可以被视为具有以下特征:它们是普遍的,即时时处处有效;它们是绝对的,即不依赖于观察者的性质;它们是永恒的,被认为是建立在用以表达物质世界的数学结构之中;它们是无所不包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视为处在它们的范围之外。⑩波塞尔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将自然定律理解为那些有关自然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最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陈述。自然定律不仅表示了世界的规律性,而且是我们理性地把握宇宙变化的保障。定律这个概念随之也就成了近代科学的关键,成了人们理解自然的钥匙。在此,最大的困难出现在自然定律的必然性上。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坚信,与那些纯系偶然的事件相反,自然界出现的现象是必然的,亦即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些物理现象中的必然性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说明和解释它们。(11)显而易见,这些论述都肯定了自然定律的客观性——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客观性。
与此相反,自然定律是主观的言论,长期以来也不绝于耳。休谟断定,自然法则或自然定律不是“真实世界”的特征,而是人的心理习惯投射或施加在自然之上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思想,也能轻易地被主观主义和观念论当做口实。皮尔逊似乎是休谟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他认为科学定律是人的想象的结果和理智的产品,而不是“死物质”的固有的惯例。科学定律与其说应该与在人之外的物理世界相关联,还不如说与人的创造性的想象相关联。(12)但是,关于自然定律的这种主观主义和观念论的观点,科学界普遍认为难以置信。科学家坚持,自然规律(包括统计规律)是世界的内在特征,由人类的探索所发现(而不是施加上去的)。比如,保罗·戴维斯发表了这样的可以被科学家广泛认同的见解:
理解自然规律是真实的,这一点很重要……我相信,任何认为自然法则不过是人脑类似折射的意见都是荒唐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数学事实。另一方面,教科书中称为法则的那些表述当然明显是人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是用来反映——虽然不完美——实际存在着的自然性质。没有自然规律是真实的这种假设,科学就会降低为荒谬。我不认为自然法则只是我们的制造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去发现世界的新事物,有些是我们从未觉察的事物。一条强有力的法则的标志是,它超越了对它所解释的那种现象本身的可靠描述,与其他现象也连接起来……科学史表明,一旦一条新的法则被接受,它的结果就会飞快地展示出来,这条法则会在许多新的背景中受到检验,常常会导致发现新的、没有预料到的、重要的现象。这就使我相信,在科学活动中,我们在自然中发现新的规律和新的联系,而不是把这些人为地写在自然中。(13)
在这个问题上,对自然定律秉持一种温和的客观性解释是可取的。也就是说,自然定律是在经验事实的启示或引导下,通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对自然固有的秩序所做出的某种理想化的、近似的把握,并表述为普遍性的命题。相当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站在这一立场上。马赫把自然定律视为“在我们经验的引导下,我们对我们的期望所规定的限制”,“不管它是作为行动的围栏,作为自然事件不变的路线,还是作为关于通过跑在事件前头以互补的方式预期事件的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道路标记”。在肯定自然定律的客观性的同时,他也指出其主观性的一面:“自然定律是我们心理需要的产物,为的是在面对自然界到处寻找我们的道路,这样在面对自然过程时我们不会处于被隔离和受阻碍的状况。这清楚地在这些定律背后的动机中显示出来,定律总是符合这种需要以及流行的文化状态。”(14)彭加勒在批判柏格森的观念论时,充分肯定了自然定律的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客观性。他说:
柏格森的世界没有规律;能够具有规律的只不过是科学家造成的、或多或少歪曲的图像。当我们说自然受规律支配,这被理解为,这个图像依然是栩栩如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这种描述并且仅仅按照这种描述来推论,否则我们就会冒失去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规律的观念本身的风险。因为这种画像能够被分开;我们能够把它分解为它的元素,区分出相互不同的时刻,并辨认出独立的部分。如果有时我们过分地简化了,把这些元素减少到太小的数目,那这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不管怎样,这并没有改变我的论证的本性和它们的含义;它仅仅使说明更为简洁而已。(15)
此外,他也指出科学家在认识自然定律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明确地体现在他的“定律即是微分方程”和“具有统计规律的特点”的命题上:“牛顿向我们表明,定律只不过是世界的目前状态和它的紧接着的后继状态之间的关系。从此发现的所有其他定律概莫能外;总而言之,定律就是微分方程。”“定律是今天的现象和明天的现象之间的恒定关系;简言之,它是微分方程式。”分子运动论也告诉我们,“物理学定律从而会采取全新的形式;它不再只是微分方程,它具有统计规律的特点。”(16)彭加勒还讨论了“规律的演化”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对自然定律的客观性的重申。
有趣的是,自然定律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客观的自然序的反映,而“序”(order)的语源和语义却包含某些主观性的东西。正如米奇利揭示的:理解任何事物就是找到其中的序,对人的思想来说,序的观念似乎必然带有计划、打算的语境。序和计划(planning)之间的关联出现在我们用来描述序的词的范围内。序本身和方向二者也意味着command(命令)、design(设计)、system(系统)、arrangement(排列)、construction(建构)、structure(结构)、formation(形成)、plan(计划)、scheme(图式)、law(定律)、rule(法则)、program(纲领)、mechanism(机制)和organization(组织),这一切都意味着某种类型的有意的组成(intentional composition)。(17)“序”的这种客观和主观的双重含义,也许是“张力”主张的一个绝妙的隐喻。
二、反对科学客观主义
极端的科学主观性或主观主义是错误的进路,激进的科学客观性或客观主义难道就正确吗?表面看来二者南辕北辙,实则是殊途同归——步入同一条不利于科学自身发展的死胡同。这是因为,后者把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视为排除人的、与人无关的科学,从而妨害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志向,阻梗科学家追求真知的热情,遏制科学家探索未知的动力,限制科学家的思想驰骋的自由,削弱科学家的创造发明的精神。因此,我们要像坚决反对极端的科学主观性或主观主义一样,明确拒斥激进的科学客观性或科学客观主义。
激进的科学客观性或科学中的客观主义观点是这样的:科学研究的客体即外部世界是绝对独立于研究者且与研究过程毫不相关的,科学理论完全是由客观的外部对象及其关系机械地决定的,唯有客体才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因,作为认识主体的科学家是被动的和逆来顺受的。例如,伯恩斯坦认为:所谓客观主义,是指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或框架。该模式和框架代表了这样一种诠释信念:“有一个独立于我们信念和爱好的世界,它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而将它自身强加于我们,并且压制我们的所想、所说和所为。”“在此之外,将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会有理生意义。”(18)胡塞尔是如下概括客观主义的特征的:
它的活动是在经验事先给予的自明的世界的基础上,并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的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对一切理性物是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自在的东西。普遍地去实现这一目标,被认为就是认识的任务、理性的任务,也就是哲学的任务。由此达到最终的存有,除此而外,再也没有理性的其他意义。
不用说,激进的科学客观性或科学中的客观主义观点也具有上述含义和特征。不过,具体到科学,我们还可以开列得更有针对性一些。在固守主观主义立场的学人看来,“在研究事物的过程中,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精确的描述和价值中立性,是位于现代科学中心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关键因素。处于这一情意丛中的关键因素是追求透明度的意愿,这种观点认为,事物可以通过不在其客体上留下标记的观察和描述方法而被认识:事物是透明地呈现的”(19)。哈丁把“强客观性”原则界定为:认知的主体应该放在与认知同样的因果水平上。(20)辛普森指明,科学在日益增长的坚持客观性为中心的路上似乎走得太远了,甚至达到荒谬的立场——“完全的客观性应该排除观察者”。(21)萨立凡揭橥,客观主义者眼中的理想的科学家,与尼采所述的“客观者”完全相像。按照尼采的说法,这种人只不过“是一件仪器,一个奴隶,虽然他的确是最高尚的奴隶”。(22)
这样的“科学的客观性是一种神话”(但是它并不是反科学者罗斯扎克等人意义上的神话)!戈兰在做出这一断言后紧接着指出,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们并不比律师和神学家更能摆脱自己的兴趣和情感。律师和神学家已经表现了对人、集团和理想的热爱和忠诚,科学家也是如此。无论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原始意识,并以其文化背景为条件唤起我们的潜意识,以驱动自我意识。(23)拉维茨也强调:
科学哲学家正在日益承认获得科学知识的过程的复杂性,正在辨认出普遍接受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和内容的未被解决的和不可解决的问题……进而,科学和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地相互渗透,使得“纯粹性”的主张变为空洞的。一旦存在对问题选择(从而对结果选择)的外部影响,科学“客观性”便丧失了重要的维度。(24)
克莱姆克则正确而全面地列举了科学客观主义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正如艾伦(W.Allen)所说:客观性是主观的,主观性是客观的;至少后一点确实为真,我疼痛的事实并非不比我重160磅客观。其次,“客观知识”是认知者收集的个人的即“主观的”经验的“理性重构”。现代认识论植根于这种难解之谜。再次,恰如波兰尼所言,如果我们仅仅希望客观的真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应该把我们的全部理智力量用于研究星际尘埃,仅用若干分之一微秒研究我们自己(或其他事物),因为客观地讲,人本身在事物的客观序列中没有宇宙学的意义!显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种对客观性的严格要求。最后,不仅知识、客观性和真理,从而还有方法论,原来是价值,或者至少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它们是道德理想或至少立足于道德理想。无论如何,对知识的追求表达了价值;于是,可靠的和不可靠的知识主张、好方法和坏方法之间的差别等,部分地是标准的判断。(25)
这样看来,激进的科学客观性确实是不现实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误入歧途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客观主义是十分有害的。这里仅仅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科学的客观主义排斥人,削弱人的自我意识和科学的社会责任感。科学客观主义必定导致“目中无人”的荒谬,因为我们的地球、尤其是人在渺无际涯的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埃,根本不值得关注。再者,正如胡塞尔揭露的,在科学客观主义中存在一个盲洞,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盲洞。无自我意识,则无责任感。为有责任感,必须保有有意识的主体。但是,经典科学的客观主义消除了意识,消除了主体,消除了自由以换取决定论的统治,从而使有意识的主体的概念、责任的概念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概念。于是,科学实践把我们引向不负责任和完全的无意识。幸运的是我们还是有私人生活的个人,是公民,是具有某种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的存在物,我们可以在另一种生活中具有道德律令。(26)
科学客观主义甚至断然把认识主体排除在认识之外。薛定谔针对激进的科学客观性心怀隐忧不无道理,他的告诫值得人们的深思。他说,客观性原则也时常被称为对我们周围的“真正世界的假设”。这是一个相当简化的概括,我们采用它以便掌握自然界中无限复杂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该原则并严格系统地表述它,我们将会把认知主体排除在努力去理解的自然界之外,而自己退回去扮演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旁观者,这样一来,世界就成为一个客观的世界。但是,这个方法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变得含混不清。首先,我自己的身体(与我的精神活动有非常直接的密切的联系)组成了我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构建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其次,其他人的身体也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其他人的身体也与意识领域相连,或可能就是意识领域的一部分。虽然我绝对无法接近他人的意识领域,但是我毫无理由怀疑他们的存在。因此,我愿意把它们当作客观事物,当作构成我的周围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此外,既然我自己和他人没有区别,相反地在意图和目的上完全对称,我得出结论,我自己也是构成我周围世界的一部分。由于我们想要获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客观的世界图画,就必须把自己置于画面之外,扮演一个无关的旁观者。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悖论:一是发现我们的世界是无色、冰冷、无声时的震惊,二是在寻求意识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位置时一无所获。当今科学完全陷入“排除原则”(把认知主体排除在客观世界之外)的深渊,而对由此所产生的悖论茫然无知。其实,我只被赋予一个世界,而不是存在与感知分开的两个世界。主体和和客体是同一个世界。(27)
其二,科学客观主义不利于科学认识的发展,因为它否认认识对象的无限性、认识视角的多样性、认识方法的丰富性、认识结果的多元性。(28)戴维斯开门见山地指出:经典科学的理论视野是客观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即使在应用于自然现象时也会遇到困难,同时它对理解科学的意义施加有害的影响,妨碍这种理解的发展。(29)科梅萨罗夫表明,经典科学的理论视野即客观主义有两点害处。首先,许多可以得到的材料证明,至少在它对于自然现象的应用方面,它能够成为质疑它主张的实际真理内容的论据。其次,由于渗透元理论的上下文,它妨害对科学意义的理解,事实上它甚至可能阻碍其发展。(30)波兰尼则从科学认识的过程和方法的角度,阐明科学客观主义的危害:
以主客观相互分离为基础的流行的科学观,却追求——并且必须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它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因为现代人为知识所建立的理想是:自然科学的观念应该是种种陈述的集合,它是“客观的”,它的实物完全由观察决定,尽管它的表述可以由习惯形成。这一观念源于根植于我们的文化深处的渴望,但若必须承认对大自然的合理性之直觉也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合乎道理的、确实必要的部分,那么这一观念就会破灭。(31)
其三,科学客观主义助长(贬义的)科学主义(32)的蔓延。克莱姆克看到,激进的客观性或客观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试图把伦理学转化为科学,或用科学解释价值判断;固守科学价值中性的观念。(33)帕斯莫尔发现,客观主义导致无节制的定量化:为了是客观的,人们必须定量化。(34)胡塞尔明锐地揭示,一旦客观主义的假象被变成世界观上肯定的东西,方法论上可能的下意识的东西,就会变成科学主义信条怀疑的道德。一种破坏客观主义假象的批判,能够抵制科学的狭隘科学主义的意识所造成的这些实际后果。(35)
三、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
事实表明,极端的科学主观性和激进的科学客观性在科学中都行不通。那么,我们何去何从呢?最明智的做法也许是,既坚决反对极端的科学主观性,又明确拒斥激进的科学客观性,在这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以及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实证论和存在主义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秉持温和的科学客观性立场,并在不动摇客观性基础的前提下给主观性保留足够的地盘,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他们的高度创造性。泡利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颇有智慧的思想:
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二者在人类思想史上都极其富有成果,虽然它们哪一个也不符合于真正的真理。一个极端是客观世界的概念,它在时空中按照不依赖于任何观察主体的规律而运动;这是现代科学的指导原则。另一个极端是主体的概念,它神秘地体验了世界的统一,它不再面对任何客体,也不面对客观世界;这是亚洲人的神秘主义。我们的思想大致在这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之间摆动;我们必须承受这两极产生的张力。(36)
I·G·巴伯也有同感:“在一切研究中,主观和客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切领域中,都存在着主体的个人涉入;将具有普遍性的事件与独特的事件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客观性和个人涉入、规律性和独特性等问题上,我们既要避免实证主义所犯的错误,又要避免存在主义所犯的错误。“作为主体间可检验性的客观性不排除个人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斥对规律模式的承认。主客体都有助于所有领域的知识,而且所有事件都能看做是独特的和有规律的。”(37)
为什么要在科学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呢?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的,科学或科学理论本来就赋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要素和本性。许多学者对此有明锐的共识。从科学理论和概念的特性来看,正如拉图尔所说,主观性和客观性代表了任何观点和理论的不得不经历的力量试验的两个极端,存在着主观的个人和客观的代表:“是客观的意味着,不管怀疑用多么大气力割断你和你表明的东西之间的联系,联系还是存在。”在这个方案中,信念是主观的,但是知识是客观的。一方面如库恩所说:“不能强迫把自然装入任意一组概念的盒子内。”另一方面如H·I·布朗所言:“我们使用的概念不是被装入实在内部,更确切地讲,概念是人的发明。”科学概念不在于存在像客体照片一样的概念的心理图像,而是描述我们考察和处理世界的方式的观念之理论结构的一部分。(38)从科学认识的具体过程来看,皮亚杰敏锐地洞察到:
认识既不能看做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的和不断的建构;也不能看做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并且这些结构还通过把客体结合到更大范围之中(即使仅仅把它们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而使它们丰富起来。换言之,所有认识都包含有新东西的加工制作的一面,而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就是使这一新材料的制造和下述的双重性事实符合一致:在形式水平上,新项目一经加工制作出来就立即被必然的关系连接起来;在实在水平上,新项目而且仅仅是新项目,才使客观性成为可能。(39)
当代科学社会学家则立足于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或公共知识和当地知识的区分,以说明前者基本上是客观的知识,而后者却是包含诸多主观因素的个人知识——这两部分知识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特征。“核心知识实际上具有被普遍认可的特征,科学家将其正确性视为理所当然的,并将其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经验事实与核心知识不一致,那么题目往往会被忽略或拒绝接受。由于科学家把核心知识看成是正确的,他们也就认为核心知识的内容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在前沿知识中,对于同样的经验事实,不同的科学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科学家并没有把前沿知识当做真理,而是当做个别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如果我们眼前只有核心知识以及科学家对核心知识的态度的话,我们就会以为科学只是传统观点的地盘;然而,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前沿知识的话,我们就很难证实大部分传统观点。”(40)
从科学是内部的心智和外部的世界的相互作用上看,情况也是如此。布蒂(E.Bouty)宣明,科学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是符合思维规律和外部世界的产物。因此,它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观的,另一方面是客观的;二者是同样必要的,因为要改变心智规律是不可能的,就像要改变宇宙规律是不可能的一样。这个相当奇特的形而上学断言能够在两个可能的方向上被追踪:第一个方向在一个阶段导致理性论,按照理性论,普适规律也许只是反映了心智规律;第二个方向导致宇宙实在论,其中一个原理也许是,作为普适规律的心智规律,必定是绝对不变的。(41)海德格尔也就此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42)值得仔细玩味。其实,奥斯特瓦尔德早以隐喻的形式道出了他的先见之明:
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除了在形成关于世界知识中的主观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因素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直接加以考虑的客观特征,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着客观部分。为了形象而清楚地描述与我们心智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为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细粒集聚在两个筛子中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容许通过第二个筛子。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粒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粒变成相等的东西的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43)
怎样在科学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呢?看来,坚持一种温和的科学客观性的观点是明智之举。帕斯莫尔正是这样行事的:他在毅然决然地反对反科学的怀疑论者力图推翻客观性的概念时,也冲淡了客观性观点,给主观性做出某些让步。首先,把科学描述为“客观的”,并非主张科学家总是正确的,甚或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较弱的主张——只有当他们背离把事情弄正确的方法时,他们才走向错误。两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不存在已经确立的方法,不管它是使事情正确的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只存在使科学家较少犯某些类型的错误的可能的方法。其次,科学家从来没有终止是人,他们具有人的情感、人的弱点。他无论如何不能避免波兰尼所谓的对理论的感情的、私人的、有人性的评价。设想科学家的客观性在于他具有像上帝一样的理智且摆脱了人的情感,是完全错误的。犯错误对于科学中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第三,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使他自己摆脱他的理智环境、他所处时代的预设或范式。科学家是社会的人,在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中工作,处在较广阔的经济和政治的社会之中。科学家不是绝对的“局外人”。无论他办好多少事,他总是以诞生于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的人的眼睛观看。第四,说科学家“把理论带入实验和观察的检验”中,并不意指他永远处在与纯粹的资料对立的状态,如果“纯粹资料”意指像英国的经典认识论的“感觉资料”、摆脱了任何种类的任何误差风险或任何先入之见的实验直接记录的话。一些反对感觉资料或“基本句子”(protocol sentences)的科学哲学家走得太远了,甚至认为常识判断也包含理论。但是,肯定为真的是,科学家认为他的资料不仅在原则上可修正,而且多半是依赖理论的。(44)马奥尼既断言客观性和感情中立不是科学家的特征,也主张要对过度的激情加以抑制。他说,科学的奖励系统和我们的文化对知识的尊崇,几乎不可能使对真理的追求成为严正的和超然的努力。除了感情中立不能实行外,任何人在那个词的专门意义上成为“客观的”也是不可能的。作为信息的处理者,我们是固有地有偏见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无感情的观点,遭到严肃的质疑。许多人争辩说,科学家的激情促进了他坚忍不拔,促动了他的疑问。从这种视角来看,激情是科学的必要前提条件。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诉诸激情的微妙平衡——激情的充分强度为研究提供刺激,而过度的激情则威胁客观性、整体性和灵活性。(45)
为了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不少人选取走某种形式的中问道路。科尔正是这样力图在科学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或者在科学实在论和偏激的社会建构论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他一方面承认,作者的特点和社会因素对于认识一致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坚持,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的经验证据、理论和模型,即论文的认识内容,对论文是否被接受也有独立的重要影响——但是建构论者却否认这种影响。他进而申明:
如果我们把自然界请回来,不是把它当作影响科学内容的唯一的或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是当作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就能使科学社会学致力于探讨它的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社会过程和来自经验世界的证据是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各种知识成果的……尽管自然界也许不会完全决定一个十分有用的科学发现的内容,但在某些情况下,自然界对于一个可能被接受的有用方案还是会施加严格限制作用的……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一个新的科学成果的命运。在这两种因素中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作用,都会导致对于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产生片面的、不现实的理解。(46)
凯勒试图在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科学既非“自然之镜”,亦非“文化之镜”,而是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映。在放弃主流科学观的“镜式”哲学或“真理符合论”的同时,她试图解释作为工具的科学在历史上成功地起作用的方式。她说:“由于‘自然’对我们来说只有通过描述才是可以达到的,并且由于描述必然被语言(因而也被文化)建构,因此没有描述可以与实在相‘符合’。”这意味着一种观念上的转变,即从将科学视为对实在的真理复制式的描述(representing),转变为将描述本身视为对实在的干预(intervening)。(47)马尔凯(M.Mulkay)希图在习惯观念和知识社会学强纲领之间走中间路线。他的新知识社会学的轮廓考虑了库恩、汉森和其他人关于自然和科学的新观点:自然的均一性是科学描述的制造物,事实是依赖于理论且在意义上是可变的,观察是一个积极的诠释过程,知识主张是被协商的。马尔凯断言,物理实在强制、但并非唯一决定科学家的结论。虽然他争辩,科学知识是文化偶然性的产物,但还是采纳了几个“习惯的”的观念:科学是自主的研究共同体,能够在物理实在和社会实在之间划界,存在科学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以及对科学的影响。马尔凯描述的新科学社会学强调协商,没有异化、精英统治、出于私利利用或冲突的中心地位。(48)多尔比提出科学的新图像:它既吸收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也保留了传统科学图像的核心价值(49)——这也是中和之道。
上述作者选取的平衡点或遵循的路线指向或多或少是有差别的,有的还不无偏颇之处,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尽可能在对立的两极力图保持某种张力或走中间道路的。我们的主张是,张力的平衡点或路线的指向应该偏向客观性一极——张力的平衡点绝不在中点,更不会偏向主观性一极;同样地,所走的中间道路也应该靠近和趋向客观性一些。
注释:
①M.Kaku,Visions,How Science Will Revolutionize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Anchor Books Doubleday,1997,p.5.
②D.H.Wilkinson:《作为人工制品的宇宙》,李醒民译,《世界科学》1992年第2期。
③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3页。
④R.Dawkins,"The Values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Values",W.Williems ed.,The Values of Science,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1977,Oxford:Westview Press,1999,pp.11-41.
⑤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
⑥索卡尔:《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载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蔡仲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63页。
⑦科尔:《科学的制造》,林建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⑧I·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1-364页。
⑨有人坚持:“不存在自然定律(law of nature),只存在科学定律(law of science)。”参见S.Aronowitz,Science As Power,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348。在此处,我们同样不拟在“自然定律”(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和“科学定律”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而认为它们基本上是同义词,均指科学借助经验和理性对自然秩序的理论性的认识和普适的陈述。这是因为,“没有办法把客观的、外部的规律性与在给定的历史时刻经验地、概念化地和想象地探索那种规则性的主观的、人的形式分清”。参见J.S.Perlman,Science Without Limits,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Knowledge,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5,p.169。
⑩麦克格拉斯:《科学与宗教引论》,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11)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6、47页。
(12)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50-159页。
(13)麦克格拉斯:《科学与宗教引论》,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14)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58、459、461页。
(15)彭加勒:《最后的沉思》,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页。
(16)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8-89、95、115页。
(17)M.Midgley,Science as Salvation,A Modern Myth and Its Meaning,London and New York:a Division of Routledge,Chapman Hall,Inc.,1992,p.9.
(18)伯恩斯坦也阐述了相对主义的含义。他说:所谓相对主义,是指没有独立存在的中心框架和元语言。也就是说,在对科学进行考察时,并不存在硬“事实”,相反似乎“怎么都行”。参见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95-296页。
(19)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20)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蔡仲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9页。
(21)G.G.Simpson,"Biology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Science,1963(139),pp.81-88。这位作者还认为,一些科学家排除观察者在科学实践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对科学来说,保全基本的客观性概念就是要承认,科学的客观性具有生物学的组分。
(22)萨立凡等:《科学的精神》,萧立坤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9页。
(23)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24)J.R.Ravetz,"The Merger of Knowledge with Power",Essays in Critical Science,Lodon and New York: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1990,p.25.
(25)E.D.Klemkeet.ed.,Introductory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0,pp.226-227.
(26)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6-97页。
(27)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罗来鸥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16-117、121、126页。
(28)我觉得,在这方面,视角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它对科学客观主义似乎有点矫枉过正。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者坚持认为,存在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和假设体系,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都能解释世界,因为不存在权威性的客观的选择方法。也就是存在很多认识事物的方式,每一方式都导致不同的观点。他们通过将客体还原为“视角的客体”,将存在还原成“为我的存在”,将存在等同于文本,将事物转换为意义,对“客观性思维”实施摧毁。他们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世界;客观性思维的错误恰恰在于,它通过把每一事物还原为存在(被再现的唯一客体)而使世界枯竭,从而否定了世界的丰富性。参见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29)P.Davies,The Mind of God,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Ultimate Meaning,London:Simon & Schuster Ltd.,1992,p.372.
(30)P.A.Komesaroff,Objectivity,Science and Society,Interpreting N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Age the Crisis of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1986,p.372.
(31)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24页。
(32)李醒民:《就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答客问》,《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2004年第4期,第94-106页;李醒民:《科学的意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1-451页。
(33)E.D.Klemkeet.ed.,Introductory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0,p.228.
(34)J.Passmore,Science and Its Critics,Duckwor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8,p.94.
(35)胡塞尔进一步阐述说,客观主义不会被一种新的理论的力量所破坏,而只能被客观主义所掩盖的那种东西的说明所破坏:被认识和兴趣的联系的说明所破坏。参见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4、136页。
(36)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1页。
(37)I·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261-262页。
(38)N.Sanitt,Science as a Questioning Process,Bristol and Philadelphia: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1996,pp.65-66.
(39)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页。
(40)科尔:《科学的制造》,林建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41)G.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Translated by A.Goldhammer,Boston:Beacon Press,1984,p.2.
(42)海德格尔说:“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进程——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或人类中心主义。”参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02页。
(43)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概论》,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44)J.Passmore,Science and Its Critics,Duckworth:Rutgers,University Press,1978,pp.81-82.
(45)M.J.Mahoney,Scientist as Subject:The Psychological Imperative.,Cambridge,Massachusetts: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6,p.9.马奥尼断言客观性不是科学家的特征,着实有点言过其实。
(46)科尔:《科学的制造》,林建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4-35页。
(47)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48)S.Restivo,Science,Society and Values,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4,p.14.
(49)多尔比这样写道:科学的传统图像是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可靠知识,这个图像具有它的根本假定,这些假定受到有效的批判,尤其是当代人的批判。新图像表明,科学仅仅是在近代社会中合理性的信念的突出形式。随着社会从对学问的贵族统治的依赖向观念的自由市场的运动,科学也从建制化的国际正统做法,向竞争的当地生活形式的文化多样性的语言学编撰运动。新图像不是完全劝说的。科学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方式要求,科学至少包含关于实在的近似的真。在科学研究中,争论发生在较旧的哲学取向的观点和作为社会建构的较新的科学观之间。较旧的观点询问大问题,但对它们的回答却不令人满意。较新的观点则提出比较有限度的、各得其所的问题。参见R.G.A.Dolby,Uncertain Knowledge,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