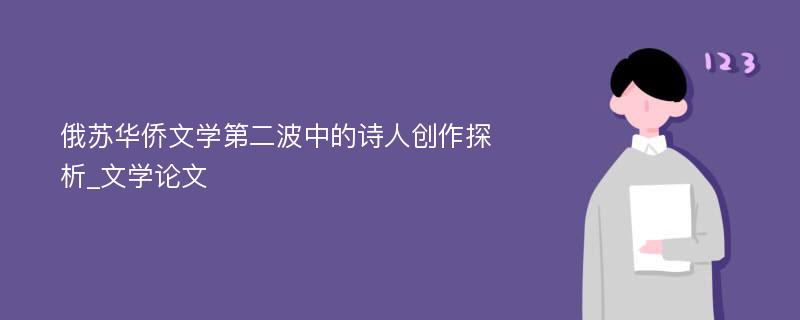
俄苏侨民文学第二浪潮诗人创作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侨民论文,探析论文,浪潮论文,诗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俄苏侨民文学”的回归与定位成为俄罗斯文坛,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生活中的热点现象之一。根据文学家侨居国外的“资历”,人们一般将“俄苏侨民文学”分为三个浪潮。第一浪潮以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作家布宁、扎依采夫、施米廖夫等为代表,第三浪潮的代表人物有诗人布罗茨基、作家索尔仁尼琴、阿克肖诺夫、索科洛夫等。第一浪潮和第三浪潮中的优秀诗人、作家日渐被人们认识,其中不少对中国读者来说已不陌生。而在这两次浪潮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被俄罗斯评论家称为承担某种“桥梁”使命的“第二浪潮”。“第二浪潮”的作家是一群随二战的战争风云飘逝的作家。在俄罗斯,对这一时期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兴趣已经兴起,而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大家、名家极少。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以及整个第二浪潮本身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学现象,在俄罗斯文学、文化发展中的位置和在保存俄罗斯民族诗歌的连续性、继承性和丰富民族诗歌传统文化中的作用都理应受到应有的关注。
在近半个世纪中,有不少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第二浪潮诗人创作的诗集相继问世。其中最完整的可推1992年在费城出版的第二浪潮移民诗人诗选《岸》。它包括了奥丽加·安斯杰伊、伊凡·叶拉金、尤里·伊丽斯克、德米特里·克连诺夫斯基、尼古拉·莫尔什、鲍利斯·纳尔齐索夫、瓦莲金娜·辛凯维奇、鲍利斯·菲利波夫、伊戈尔·齐诺夫等四十多位诗人的诗作,因而,可以说,具有某种概括、总结的性质。在此之前,在西方曾有第二浪潮诗人的作品集出版,如1953年在纽约出版的《在西方》,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国外文学》,1960年在莱茵河—法兰克福出版的1920~1960国外诗人诗选《四处流亡的缪斯》以及1966年在华盛顿出版的俄侨现代诗选《结合》。
近年来,在俄罗斯境内也竟相出版俄苏侨民诗人的诗选。其中主要是第一浪潮诗人的作品,直到1994年和1995年,在莫斯科才分别有三本第二浪潮诗人的集子问世:四卷本1920—1990俄侨诗选《我们曾居住在另一个行星上……》(包括第一浪潮和第二浪潮)和《用诗歌回归俄罗斯》,以及俄侨抒情诗选《在异岸》。其中,《用诗歌回归俄罗斯》收集了二百多位这一时期诗人的作品。同时,还发表了有关几位最显赫的诗人的文章和资料。但从总体上说,对第二浪潮诗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此,我们着重评介第二浪潮中的两位重要诗人,并通过对这两位代表人物创作的透视,将第二浪潮的诗歌置于21世纪文学—诗歌(从“白银时代”到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大背景下来观照。
德米德里·约瑟夫维奇·克连诺夫斯基(克拉奇科夫斯基)是“俄苏侨民文学”第二浪潮中一位资深诗人。1893年,克连诺夫斯基降生在彼得堡的一位艺术学院院士家中。诗人曾在著名的皇村中学学习,后到圣—彼得堡大学深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皇村中学的精神氛围的熏陶,为诗人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孩提时代,克连诺夫斯基就开始作诗。从1914年开始,年轻的克连诺夫斯基已在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诗作。1917年,第一本诗集《调色板》问世。但后来,从20年代开始,诗人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十年后身处战时难民营的克连诺夫斯基又重新开始诗歌创作,且一发不可收。
抒情诗《生活的痕迹》(1950),《迎接天空》(1952),《捕捉不住的同路人》(1956),《触摸》(1959),《离去的风帆》(1962),《零散的秘密》(1965),《单调而冗长的重负》(1969),《诗人手记》(1971),《温暖的夜》(1975)等九本诗集相继问世。而且,每一本诗集中只收录诗人的新作。1967年,出版了一卷颇有分量的选集。而十年后的1977年,在诗人逝世后,出版了最后一本选集。克连诺夫斯基的抒情诗作为联系“白银时代”和20世纪中期诗歌的桥梁,在传达印象、情绪和对往事的回想时,都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情感。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俄罗斯古典诗歌所具有特质:情感真实自然、表达方式准确,同时“高峰派”的“物性”和“物质性”的痕迹也十分突出。通过这种“物性”,透射出隐秘的象征世界。随着时期的推移,诗人的沉思体抒情诗被哲学意蕴所充实和丰富。这一切都反映在他艺术创作逐步完善的变化过程之中。
俄罗斯、异邦和孤独是“俄苏侨民文学”作家共同的三个重要主题。这三个主题也贯穿在第二浪潮诗人的创作中。当然,诗歌的“永恒主题”——爱情、死亡和上帝也从来没有被他们遗忘过。深沉的抒情诗人德·克连诺夫斯基不断表现的也正是这些主题。
早在诗集《生活的痕迹》中就已显露出他诗歌创作的所有关键主题和情节:祖国和自然,生命与死亡、上帝、爱情、创作等等。而且,这些主题在诗人创作中相互交错,紧密联系,有时,在同一首诗中,不同的主题相互融为一体。
哀诗《在黄昏冷漠的画面里》,诗人用诗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风景画,并通过这些画面抒发自己对人生道路,对人类逝去的年华,对生与死这一永恒主题的哲学思考:/你能在失去的生活轨道上寻找……/……/……减轻的疲倦……/死亡痛苦的天惠。/这是一种高尚、安谧的排除孤独的方式,是对逝去生活的无奈。这种处世哲学在诗人同一时期的其他诗歌中也常常表露出来:/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边缘,/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就这样独处/永远的美好……“(《欢乐》)孤独和寂寞的心情常常困扰着这位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的诗人,他苦苦寻求对孤独和寂寞的解脱。最终,在面对上帝中,他找到了这种解脱。因为在诗人的眼里,是上帝将希望赐给世界,赐给人类灵魂,上帝是将人类灵魂从黑暗和空虚中拯救出来的光明源泉。1945年,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感到了你(指上帝)的呼吸……/我感到你手的温暖。/(《致至高无上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将这种庄严、神圣的救世主的主题,用一种优美的抒情笔调融汇在爱情和创作的主题中:/你在我心中燃起似彩虹般美妙的一切……/你给热血以欢歌般的跳动/且你不时原谅、保护我。/
1952年诗集《迎接天空》问世。在诗中表露出诗人对他心目中天国的向往和对宇宙和世界至高无上之极致的渴望。诗人心目中的天国是一种摆脱了丑陋的尘世,摆脱了地球上的平凡生活的世界。同时,诗人又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球生活中”的每一点滴小事上,深深地依赖,而又不时地排斥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现象。它反映出诗人矛盾冲突的心理:/啊,我知道,/只有贴近我那地球上的平凡生活,/世界才清清澈澈地呈现在我面前。/(《日常生活》)
收录在诗集《捕捉不住的同路人》中的《致祖国》、《当我回来》等诗歌紧紧围绕着“俄罗斯”这一主题。祖国的形象在这些诗歌中笼罩着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诗人哀悼祖国的毁灭,哀悼祖国孩提和青春年代的一去不复返,同时,对俄罗斯语言,对祖国的诗歌,对祖国诗歌的创造者始终坚信不疑,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这位远离祖国,四处漂泊,渴望回家的游子,“在黑暗、可恶的异邦那黑暗、可恶的深邃的夜中”,一如继往地延续祖国诗歌创造者们的神圣事业:/在我们之间的——是门与栓,/但在我漂泊的命运中,/我用崇高的语言为你效劳,/在异邦,我效忠于你。/窒息动荡的岁月一年年逝去……/一只亲切的手伸过来,/我穿过海洋,跨越百年,/由远方来到了你身边。/(《致祖国》)
这只象征着祖国母亲的手,预示着祖国对诗人的拯救。与此同时,这首诗中还出现了以深刻的宗教感情为基础的“捕捉不住的同路人”形象——保护天使:/轻轻飞起,用翅膀将我遮盖,/捕捉不住,又轻轻盈盈。/莫非是从另一个地方,/伸来你亲切的手?/
诗集《触摸》出版于1959年,其标题形象,构思独特,感情饱满。这是对刚刚开放的春天小花的触摸,是对亲爱的“手”的触摸,是对忐忑不安捕捉不住的字眼的触摸,是对人类灵魂的触摸,是对天空中奇迹的触摸,归根到底,是对世界的真实的触摸。
生活本身无穷无尽的多样性,生活永恒的变更和复兴,不仅不断给诗人以创作的灵感,而且更激发诗人的深思。在对真理的苦苦追寻中,在探求哲学的抒情概括中,他面对个性永生的问题,坚信无法摆脱的出走和离别已在自己身上消融,变成了与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碰撞,它同样无法避免也无法描述。/因为呓语和苦难,还有这些诗句的痉挛,/都是为了使地球尘世的声音能充实天空的构想……/(《将自己的行星握在掌上……》)
在1962年出版的诗集《逝去的帆》中,诗人再一次面对保护天使,但此时的天使已大大改变了模样:“我的天使,我冷峻的同路人。”
经过诗人诗学思考的哲学空间和时间范畴转换为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和抒情般的痛苦和磨难。因此,他的目光从宇宙的、行星的广阔无垠而转向无边无际的人的内心深处:/我们忘记了一个空间……/我们自己的灵魂空间……/(《我们因此喜爱观望天空》)
这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曾坚定地宣称:“我终究相信能够达到不可能的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诗人的想象力和不寻常的信念,使诗人能在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发现整个世界,发现神圣的、永恒的东西:/如今,离开此处,我发现,/假使没有地球可怕的援助,/我们决不可能,/触及天空奇迹。/(《总有一天(可能很快)……》)
这种热爱生活、坚信生活的欢快主题在克连诺夫斯基的总结性诗集《新诗》(1965—1966)的章节中再一次表现出来:/我感受到了它,/感受到了地球……的欢乐……/
正是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紧接着前几本诗集(《相见了,象许多人相见一样……》《透过五颜六色的回忆……》)爱情的主题以一种生动可感的形象展现出来,使人觉得十分亲切。/让所有的人明白,在我们匆匆的目光中,/映照出刚刚逝去的幸福的颤动,/而涂抹嘴唇的,不是温暖的浆果,/而是那充满激情的亲吻。/(《峡谷中散发着草莓的芬芳……》)
诗人克连诺夫斯基擅于将表面的、貌似平凡的现象与大自然和人类灵魂内在的东西糅合在一起。这种特性使克连诺夫斯基的诗歌魅力无穷。诗人的创造也因此有机地融入19—20世纪从普希金、丘特切夫到勃洛克、阿连斯基、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俄罗斯经典诗歌的行列。
“俄苏侨民文学”第二浪潮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伊凡·维涅季克多维奇·叶拉金(马特维耶夫)。他于1918年生于符拉基沃斯托克(海参威)。其父维涅季克多·马尔特—马特维耶夫是一位未来派诗人。童年和少年时代文学艺术的熏陶无疑对叶拉金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7年,叶拉金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其父被捕,并很快遭枪决。这一沉重的打击在诗人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尽管如此,两年后,他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基辅医学院。但学业未成便爆发了战争,开始了充满无尽苦难、颠沛流离的疏散生活。1943年,战争快结束时,叶拉金流落到德国慕尼黑附近的难民营,1950年又转道美国。从此,在这块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过着远非无忧无虑、远非安祥宁静的生活,直至1987年,在与癌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经受了最残酷的磨难后离开人世。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造就了诗人性格中高傲、自信的一面,同时,也在诗人的性格中留下忧郁、易受伤害的影子。
早在40年代,叶拉金的两本诗集《沿着从那儿走出的路》和《你,我的百年》就在慕尼黑出版。后来,主要是在美国,他的诗集《沿着从那儿走出的路》(1953),《夜的反光》(1963),《歪斜的飞行》(1967),《屋顶上的龙》(1973),《在斧头星座下》(1976),《在宇宙大厅内》(1982),《沉重的繁星》(1986),《土丘》(1987)先后问世。其中最后一本《土丘》是于诗人逝世后在德国出版的。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世界,20世纪人类生活折射在他个人创作活动中的悲剧性经验以及俄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古典诗歌的辉煌成果便是叶拉金文学创作的基础。艰难的生活经验、漫长的战争道路、对祖国的思念、丧失的痛苦、生与死、自然与爱情、艺术的命运与艺术的创造者——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叶拉金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基本主题。
对远方祖国的回忆,对回家的渴望,时常在叶拉金的诗歌中流露出来。诗人在其重要诗作之一《祖国!我们相见那么少……》中抒发了这种强烈的思乡之情:/如果活着,我们一定要回来,/如果上帝引我们回家……/诗人以这首诗作为50年代初在纽约出版的诗集《沿着那儿走出的路》的首篇,不能不说是被这种强烈的渴望回家的情感所驱使。在这本收录了诗人创作初期作品的集子中,悲观的处世态度渗透在每一行诗句中。在那一首首记载了与祖国离别时刻的诗歌中,一切的一切无不染上悲剧的色调:/就连那柳树,也如同自杀者,/从路堤扑向陡坡。/
这感情饱满的风景速写和情绪激动的细节描绘是敏感的诗人对世界深刻领悟和接受的反映,是诗人受尽创伤痛苦而灼热的灵魂的真实写照。
在《围城》一诗中,诗人以简洁而饱满的笔调复现了战争的悲剧,再现了被围困在封锁圈中涅瓦河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的形象:/风狂的碎粒又在/欢呼、翱翔、时隐时现,/亲吻着你注定要失败的/保护之矛。/疲惫、饥饿、战争的你——/在临死前的冲刺中缩成一团。/涅瓦筋疲力尽的脉搏/在你太阳穴上跳动。/
《围城》一诗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B ·俄罗斯·扎依采夫认为,此诗完全可以列入描绘列宁格勒封锁的优秀作品的行列,完全有资格与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O·贝尔戈里兹的同类题材诗歌媲美。
战争的结束使诗人不再把自己的诗句局限在描绘毁灭、痛苦、阴郁、恐怖的画面上。诗人在战争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剧,而是受尽创伤的全人类的悲剧,在叶拉金此后的诗歌中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普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对人死亡的痛楚。
这一时期,叶拉金还创作了自传性长诗《星》。它向人们叙说了被镇压的父亲悲剧性的遭遇和诗人本人漂泊的命运。长诗个性鲜明,洋溢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又充满了象征意义。天空与星星的形象贯穿整个长诗。这些形象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命运朝我猛击,/命运将我击倒!/我们的天空变得黑暗……/我们的星儿不再闪亮。/
诗人将对祖国、对异邦,乃至对整个受难的地球和地球上人类的思考深化在抑郁、苦涩、悲剧的诗歌情调中。因此,他的沉思体诗歌回响着抚今追惜的音调,飘荡着难以摆脱的惆怅:/亚拉巴马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异乡的花草对我们又有何用?/我们就是在坟墓里/用死者的凶恶嘴唇/也要呼喊/“莫斯科!”/
真理、良心、道理、高度的艺术简朴——这一切构成了叶拉金诗歌体系构想的轴心。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无法克制的思乡情感深藏在他灵魂深处。这种情感在诗集《夜的反光》(1963)中再一次坦露出来:/我不知思乡的苦楚,/我喜爱异邦,/在早已离去的俄罗斯的一切中,/我缺少的是俄罗斯的窗口。/当灵魂中变得黑暗,/镶嵌十字的窗口,/夜间亮着灯火的窗口,/至今令我回想。/透过诗中外表的平静和镇定,衬托出诗人对离别的祖国强烈的爱恋。他为她而痛苦,在这些诗句的形象体系中产生出十分广博、内涵丰富的象征形象。这些诗句曾被诗人的好友文学家、诗人B·辛恺维奇称为他“最令人鼓舞、 最优美的诗句”。
诗人对于美国诗歌创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在诗歌的主题的拓展、还是在表现手法的创新等方面都作出了有价值的尝试。他那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和生活的细腻体验,对艺术家使命的执著探寻,使诗歌意象及其展现的风景画面中的光和色更加亮丽鲜明:/红绿灯如宝石般闪烁,/在脚下,如同在黑色的湖泊中,/霓虹灯的反光在柏油路深处的黑暗中/来回移动。/
这些诗句展现的是色彩斑澜的动态的城市画面,但这一幅幅可视的,像电影镜头般移动的画面中突然闯入忧虑的影子,凸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在渺无尽头的雨中,/仿佛地球上一切火光都在哭泣。/
镜头再往后移,则显露出在这个到处反射着霓虹灯广告的城市中“漂泊诗人”的茫然,推出一个孤独寂寞的主题:/也许,从所有的体积中抽出,/在成群的异己中移动,/我摔倒在柏油路上,/扑向反光——扑向夜的反光中的反光。/
这是人类自我丧失的主题,人类在这个世界的“体积和重量”中变成了反光,变成了暗淡的影子。
70年代,出版了叶拉金的两本诗集《屋顶上的龙》和《斧头星座下》。诗人的《夜在沉重的繁星中行走……》是他新十年的总结性诗集。
1982年,诗人创作了《宇宙的大厅里》。该诗反映出诗人对生活和命运的忧心忡忡,对自己注定要生活在时间复杂轨道上的困惑。诗中也有无情的自我剖析和痛苦的反思。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首诗歌《我为电影写剧本》中不时夹杂着略带讽刺色彩的关于艺术探索,关于生活杂乱无序的叙述:/我生活得愈来愈离奇、荒谬,/我陷入毫无意义的梦中,/越来越常想起锁链,/想起瓦解时间的锁链。/
诗人的选集《沉重的繁星》出版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件快事。诗人一直渴望出一本选集,但在美国,就是像叶拉金这样的知名诗人的诗集,出版商也不愿出版。诗人的好友塔季扬娜、安德烈·费先科决定给诗人一份告别礼物——为他出版这本诗集,列昂里特和安克尼娅夫妇立刻响应,从朋友和诗人的崇拜者中筹集资金。л·л·勒热夫斯教授做选集的编者。遗憾的是他本人未见到此书出版便离开了人世。失去多年的挚友,对诗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诗人在给B ·辛凯维奇的电话中说:“最后一位绅士死去了。”诗人在与病魔搏斗中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他的书能传到俄罗斯。叶拉金十分珍视与苏联诗人的联系,因为这是他与他所热恋的祖国直接接触的一种方式。
叶拉金对诗歌的语言的创新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从他在诗歌的语言中可以看到诗的本质。“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创作是他诗歌的源泉,他一直将自己的创作纳入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后期创作的行列。他认为:我们至今仍生活在普希金水晶般高不可测的语言中。在寻找这些“原生的、有理性的语言”道路上,俄罗斯的勃洛克和M ·茨维塔耶娃,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和B·帕斯杰尔纳克,и·布宁和н ·托波洛茨基的经验对他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克连诺夫斯基和叶拉金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但其创作生活的基础是共同的。他们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本世纪现代主义流派的诗歌传统。他们诗歌的本质特征所具有的共性就在于:其创作所涉及的主题十分广泛:对公民、社会和“永恒”主题的表现;对哲学、宗教深刻认识;对世界悲剧性的体验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
尽管在文学诗歌的探索中,两位诗人都取向于“黄金”和“白银”时代,但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强烈、特色鲜明。比如,克连诺夫斯基的沉思体抒情诗在很大程度具有浪漫感情和象征—印象派的性质,在诗中表达了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和感受,同时体现了对物质性现实世界的向往。叶拉金的抒情和抒情叙事诗在现实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准确性、表现力、形象性生动性和雕塑性的追求。
从整体上说,“俄苏侨民文学”第二浪潮诗人跟随其前人——第一浪潮的诗人们,将世纪初和世纪末连接起来。他们是俄罗斯文学古典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他们不仅保留了俄罗斯文学、语言和诗歌中的精神财富,而且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份难得的,风格独特的美学和文化财富。
收稿日期:1998—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