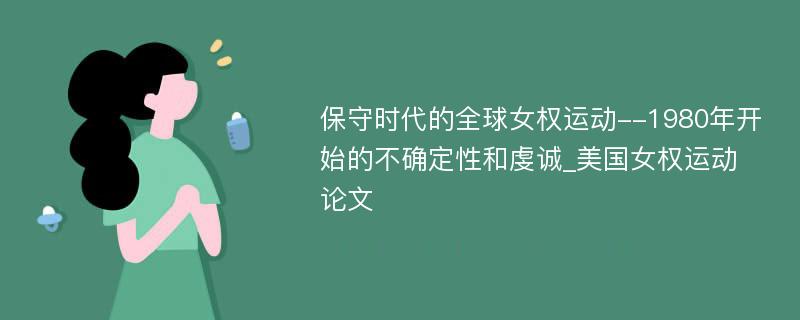
保守时代的全球女权运动——始于1980年的不确定性和虔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不确定性论文,虔诚论文,保守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总统给美国带来了新右派。对女权主义者而言,这一系列灾难性的打击随之达到了顶峰。新政府对反女权主义的议程一路亮起绿灯,道德多数派、海德修正案、菲丽丝·施拉弗利(Phyllis Schlafly)的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已经走在前列。在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右派对各州市的影响下,有关女权主义的立法和政策措施走向了消亡。有谁真正在为女性的权利而战呢?反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就是他们自己。
面对国内的封锁,美国女权主义者的回应是将自身的政治理想付诸于国外的妇女运动之中。国际妇女运动的兴起被看作是美国的活力和思想的大舞台。国际运动——后来被称为“全球女权运动”得到了美国财团以及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妇女团体的支持,从左派到中间派,最终还得到了新右派的支持。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段众说纷纭和乌云笼罩的时期。
1980年之后,美国对开展国际讨论的显著贡献是加强了对妇女遭受暴力问题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否遭遇强奸、家庭虐待或性骚扰的揭露——最早在女权意识较高的团体中开始萌芽。新的反暴力运动取得了胜利,或者说播下了未来胜利的种子,除此之外,对“罗伊诉威德案”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强烈反对,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历经10年时间之后,警方后来采用了经修订的强奸案调查流程,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热线电话和避难所,大学成立了心理辅导中心和咨询项目,心理健康专家开始注意患者生活中的乱伦现象、性虐待以及家庭暴力问题。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将这一观念推向全球。1976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首届联合国妇女大会并没有形成有关妇女遭受暴力的主题。但到了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妇女大会上,讨论该问题的专题小组众多,还制作了数千份的宣传手册。10年后,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联合国妇女大会上,性暴力成为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与会者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这一问题却达成了一致,即要共同反对性暴力。来自美国的与会者高兴地说:“反对性暴力超越种族、阶级和文化,为共同的事业而将全世界的妇女团结了起来。”关于暴力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很多,所以一个人都不能在9天之内参加完全部会议。
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公众对暴力行为的关注,说明女性遭受压迫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对就业、教育和财产权的老生常谈,不再像以前那样引人注目。而且在带有种族歧视、冷漠或以传统和习俗的名义约束妇女的国家尤其明显。整个非洲大陆的妇女对此反应强烈,对于工作中的性别歧视、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虽然与边远地区的女性关系不大,但是殴打、强奸和童婚却是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许多地方,父亲和丈夫可能是同一人,家庭内部随心所欲的酷刑和性虐待,不受任何法律的制裁,而且通常受到当地政府、与国家司法系统混杂的部落规定以及宗教法庭的支持。这种新的关注会把这种折磨人的和极端的权力暴行赶出这些令人费解的国家,也给予了非洲女权主义者参照国际准则的合理性。
1987年尼日利亚女孩欧瓦·阿布巴卡尔(Hauwa Abubakar)的死亡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不起眼的个人悲剧引起了公众关注,并掀起了结束这种不公正野蛮体制的风波,影响甚广。欧瓦是一名穆斯林女孩,生活在包奇州北部。在她9岁那年,与她父亲的债主——一个牛农订婚,并在12岁时嫁给了他。在她多次离家出走后,丈夫砍断了她的手指以惩罚她。当她又一次试图离家出走时,丈夫用带毒的弯刀砍断了她的双腿,并故意让伤口感染。在辗转于医院和当地医生之间数月之后,小女孩最终死去了。她的丈夫被逮捕,并以杀人罪被起诉,但欧瓦的父亲却对女婿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请求将案件作为家庭事务移交当地法庭审理。医院也同样为他开脱罪责,声称女孩是绝食而亡。
该案件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和反政府示威者之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例,因抗议政府官员串谋权势人物和警察进行谋杀,抗议活动持续了数月。政府官员站在受害人的父亲和丈夫一边,他们依据当地法律警告反对者避开丈夫权利这一敏感问题。但女权主义者和持反对意见的男性对“男性卡特尔”的愤怒超过了对尼日利亚立法机关的愤怒。而政府主办的全国妇女联合组织却贸然地低估少女嫁老夫所带来的悲剧后果。其实,反童婚已有很长历史了,要追溯到帝国统治时期——19世纪英国的妇女就被谴责为恐怖的异教徒。当时全球女权主义者支持尼日利亚女权主义者揭露殖民主义践踏她们的问题,支持她们的权利。她们将高压政策和男性主导社会地位背景下的欧瓦被杀联系在一起是合理的,然而,世俗的政见对此却视而不见,反倒依靠宗教政见来约束犯罪。她们还指出童婚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女孩第一次来月经后就怀孕,对她们的生殖能力具有可怕的伤害。
2004年,《女性》杂志认为:“穆斯林与西方人的文化冲突起因于妇女不平等问题,而非民主。”它天真地设想两者可以分开,然而对在尼日利亚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女性和男性来说,与男权相关的冲突总是与因民主引发的斗争不可分割。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父权是一个必然的借口,但这是不够的。男性和女性的关注虽不尽相同,但也不完全相冲突: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关注该谋杀诉讼,但女性对此都很关注。
在同样的年代,类似的事情在印度也发生过,女权主义者在调查殉夫或自焚事件时,拥护者却将这吹捧成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的真情表达。后来揭露这一事件是政治操纵谋杀案,那名妇女其实是服毒或被推入火中致死的。一个表面上的传统仪式却以非常现代的方式得到了支持,都市男性力争借助似是而非的印度复兴主义的报道来提高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使女权主义者的斗争进入了深深的相互理解之中,那就是考虑到特定的地点、时间、参与的双方以及政治权力关系。否则,把反对施暴妇女问题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从而让女权主义者提出补救措施,就会显得多余。在印度,以妇女拥有土地权为例,它在许多地方不被认可或经常受到侵犯,结果它成为反对家庭暴力的一个主要保障。
但在美国,对性暴力的愤怒逐渐蔓延,演变成对其他地方生活的狭隘认识。美国女权主义者将精力、情感和资金投入到全球反暴力运动中,但她们对政治及滋生暴力以外的问题通常很少感兴趣。对全体男性施暴问题的断章取义和夸张报道意味着美国将在全球各大洲引起人们的愤怒,而对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以及地区和宗教冲突的差异却不加考虑。女权主义者以反暴力的名义向外扩张,男性罪恶的思潮如浮油般蔓延。1983年,在由众多的美国人、资助者以及“性奴”反对者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强迫卖淫、自愿卖淫以及同性恋婚姻问题。在1993年召开的维也纳人权会议上,女权主义者在会议日程中加入讨论妇女权利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但性暴力问题才是当务之急,这一问题再次延伸到“性剥削”的问题上。
因此,在妇女于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和卢旺达大屠杀中所遭受的非人经历后,切阴术、性骚扰、强奸都被归为性剥削。同时强迫卖淫和性交易被大谈特谈。工作权、生殖健康、土地权和教育权在耸人听闻的男性暴力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对此,她们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可用的法律资源,也只能高度关注发达国家的动态。安·斯尼托(Ann Snitow)那时正在东西方妇女联合会工作,她从东欧同事那里听到美洲人热衷性交易时,她写下了自己的愤恨;她们的控诉很少提及色情问题,而诸如资金流动和劳工迁移问题也没有引起美国人的愤怒和资助兴趣。劳拉·西科尔(Laura Secor)在向国民报告1993年维也纳大会时,曾经平静地描述会场情形:当时孟加拉国妇女默默地坐在听众席上,而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则在谴责波黑战争中发生的数起强奸案,并称之为“史无前例”。麦金农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故意回避了曾经广泛传播的报道:巴基斯坦男子在1970年孟加拉国战争中实施了大规模强奸,当时妇女被监禁并被强制怀孕。
但谁能反对呢?西科尔发现在维也纳会议上见不到政治上的交锋,甚至没有一位领导人表示这样的看法。她评论道,会议小组的成员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性交易受害者、年老的修女和道德捍卫者,因此,很难以批判的甚至微妙的言辞来进行对话。而谁又能不同意应该终结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呢?其实,当问题越来越严重时,这还是有可能的,如当全球女权主义兴起,女权表达要摆脱父权社会的钳制时,这就成为可能了。
但在同一时间,将父权制作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采用男女受伤害二分法是完全不恰当的。性暴力总是与瘟疫般的战争和叛乱如影随形,并对世界很多地区造成伤害。在非洲,强奸、虐待、残害、囚禁女性和奴役是民兵和恐怖团伙抢劫的标准程序,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到刚果、乌干达北部、卢旺达、苏丹和索马里都是如此。被迫从事性交易的劳工——后来被称之为性奴隶——总是与贫困、官员腐败、跨国劳动力流动以及被迫迁移纠集在一起。暴力也总与政治以及宗教制度和政党密不可分:原教旨主义者在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利用对伊斯兰教法的歪曲解释来实施骚扰、摧残以及杀害涉嫌违反禁令的妇女和儿童。
性暴力是如何成为美国全球女权运动中如此受关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问题的呢?为什么妇女会有性交易而无劳动斗争呢?包括女佣交易在内,哪一种仍然是交易的主要形式呢?为什么不重视非洲某些地区特有的切阴术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呢?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而没土地权呢?全世界有如此多的恐怖、苦难、痛苦和不公平在折磨着妇女: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主题,性暴力是既具吸引力却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无疑会激起令西方观众满足的恐怖。它能在女权主义者中制造一种人为的世界大同主义以寻求国际信誉。一方面,它具有弹性和高度可移植性,无需知道任何一个国家详情、经济背景或政治局势方面的知识,就能一眼识别针对妇女的暴行。有关残暴、逃脱、抓捕、违规行为、酷刑和玷污的故事,已经描述出不同类型的男性恶棍。泰国的皮条客、俄罗斯的黑手党、刚果的士兵、墨西哥的男同性恋,对他们的称呼很精准,因为这能够勾起人们对受害女性的同情心,但很少被要求去理解具体的动机以及机构、肇事者和受害者的真实意图。一位热衷者的描述容易获得普遍的认同:“尽管暴力出现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可以是家庭暴力或战时强奸,妇女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暴力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议程。”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不那么明显,我认为是历史的原因。对性暴力问题的关注通过20世纪全球化进程中对维多利亚戏曲的天真与邪恶的转换,掀起了女权主义者政治潜意识中的激情。19世纪后期,妇女运动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部分地区令人震惊的男性野蛮行为:一夫多妻制、宗教的闺房、童婚、自焚殉夫、缠足以及卖淫。
即使在1939年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国际妇女协会仍然被买卖妇女行为所困扰。当时,希特勒正向波兰进军,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国际妇女协会通过了打击国际卖淫和白奴交易的决议。
没人知道历史会重演:美国妇女被植入了女权主义的DNA,虽被封锁和阻挡在国内,但她们仍然将自己看作是弱势的、能力较差的、身处险境的国外姐妹们的救星。由于性暴力反对者在美国得到了支持,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有些是附带相关的,另一些则是与性暴力毫无关联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者对非洲盛行的切阴术非常关注,并认为这是男性对女性性欲恐惧所采取的野蛮行为。然而,实际情况是,切阴术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习俗,被看作是女性成人礼的一部分,并且是由妇女实施手术的。它在不同的地方和区域也是有差异的,并不总是带有暴力和强制性的。至于卖淫也是如此,也常常与暴力混为一谈,它并非都是暴力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性交易都是被逼的——除了贫困驱动她们那样做,以及其他卑微和剥削的雇佣关系之外。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贩卖都是贩卖妇女。
对这一问题的呼吁也在于它的普遍性。美国的女性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也同样遭受到国民间冷漠、被政府忽视以及警察与罪犯勾结迫害妇女等问题的困扰,她们为自己的姐妹们呼吁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将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女性和生活在独裁或神权统治国家的妇女所处的环境混为一谈,虽从修辞学上来说在美国是有效的,但却忽略了基本的事实。并非所有的国家在对待强奸和家庭暴力问题上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在强奸以及其他暴力问题上,民主国家女性所处的环境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把她们与生活在没有法律可以求助或生活在充满恐怖统治的国家的妇女相比,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些国家的女性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希望。在巴基斯坦,当女性被认为有让家族蒙羞的越轨行为时,就会被兄弟、叔伯和堂兄所杀害,当局对这种所谓的“荣誉杀戮”视而不见。1996年后,塔利班的劫掠使阿富汗成为妇女的“归零地”。在伊拉克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后,什叶派和逊尼派民兵经常诱拐、强奸交战对方的少女,并将她们送回以羞辱她们的家族,而她们最终普遍被“荣誉杀戮”。
然而,政治上的争论却很容易被认同所代替。美国女性不了解斗争双方的利害关系,就不可能取得政治地位,因为男性的暴行被看作是一种自发的力量,而不是受政治力量支持的某一特殊的民兵和军队的行为。当对生活在原教旨主义政权下的妇女的争论从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和待遇问题转变成国际政治中心问题时,这一慢性问题已经恶化。女权主义者很快开始谴责男性暴力是坏人的标志性行为,但是,她们对任何执政党或政权的批判都是有所保留的,以免它们被理解成新帝国主义。塔利班取得政权后,直到阿富汗妇女成功地将美国女权主义者拉入自己的阵营,持续的斗争才开始。更典型的是因一件孤立事件而爆发的抗议。2002年,尼日利亚的另一个女孩阿米娜·拉瓦尔·任美(Amina Lawal Kuram)因未婚生子,以通奸的罪名被判处用石头砸死。在国际政治努力、人权组织施压、尼日利亚民众抗议以及阿米娜的律师欧瓦伊·卜拉伊姆的共同作用下,伊斯兰教法法院最终推翻了对阿米娜的判决。
抵制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全球运动因这一保守的时代而改变。它是证明女权主义运动能够获得右翼支持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督教福音派抓住这一问题,有计划地通过人权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根基,与女权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制定《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并最终由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布什上台后反贩运妇女措施仍然是他外交政策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核心。2003年我访问柬埔寨时,美国正试图制止贩卖妇女问题,有人说这是美国大使关心的唯一问题——在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所有卫生和福利指标(儿童死亡率、作物产量、教育、收入水平)都有了突飞猛进。
于是女权主义者在世纪末取得了一些胜利。从左翼到中间派,再到右翼都是如此,原因也是无可辩驳的。美国人能够同意结束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一件好事,并认为国家也应该在结束对妇女施暴行为方面发挥自身的作用。如何做到这一点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对于所有的复杂认识和众多善意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而言,女权主义革命者希望从压迫者的魔爪下解救出受害者——虽然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幻想。
原文标题:Global Feminism in a Conservative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