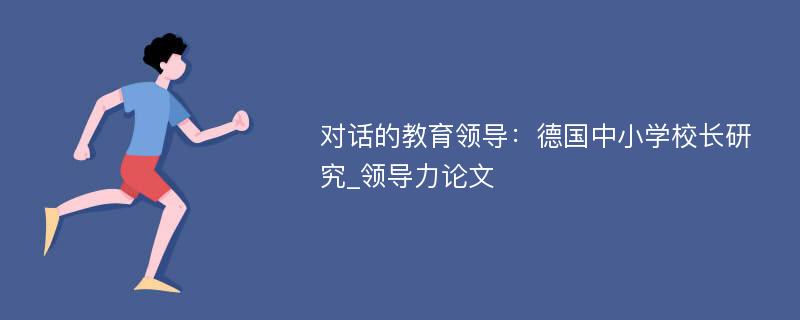
对话的教育领导力——德国中小学校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中小学论文,领导力论文,校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校发展理念
2009年3月12日,应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之邀,德国莱法州(Rheinland-Pfalz)中学校长联合会主席Christel Frey女士在上海教师教育基地作了题为《教育领导在德国——一位德国中学校长的经验汇报》的讲演。[1]这位曾经担任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女士同时是尼德奥姆文科中学(Gymnasium Nieder-Olm)校长,这意味着,一方面,她本人所领导的学校在该联邦州应具有一定的引领效应。另一方面,她个人作为校长在这所莱法州最大的文科中学也应承担充分的统帅角色。这权且作为一种假设。
在报告最后,即对其校长生涯作一番回顾之后,她介绍了该校的学校发展理念。显然,学校发展理念与教育领导应具有某种契合关系。这份学校纲领性文件是她与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充分协商后制定的,共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导言”,其次是“我们的教育概念”,最后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观念”。[2]“导言”的全文简短扼要:“尼德奥姆文科中学的理念是针对学校全体学员的,针对男女学生以及家长,还有男女教师。它试图成为一种如何积极构建与持续发展教学和学校的永久性进程的思想动力与基石”。该校对教育概念的理解也较为泛泛,而占一半篇幅以上的第三部分却耐人寻味。
价值判断、宽容、公平、非暴力以及公正对应我们共同的根本信念。
○我们展开对话,而不是互相谈论对方。
○我们承担社会责任并互相照应。
○我们互相促进、支持和融合。
○我们寻求具有共识性的冲突解决方式。
○我们使民主行为具有切身感并把它注入学校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展开合作并使我们的行为具有最大限度的透明度。
我们视学校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与之融为一体。所有学校共同体的成员细心与人和物打交道。我们爱护设备与家具。所有人要相互理解,重视达成的规则并尊重他人。我们打造一个推动共同体发展的对话文化。我们以同样的程度关照周围的事物:设备、家具以及工具和他人的财物。
闪烁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是“我们”、“对话”、“生活世界”和“共同体”。通篇只字未提“校长”或“领导”,从而推翻了以上对于“引领”与“统帅”的假设,并为剖析德国校长的角色提供一个切入点。
二、校长角色的三重释义
(一)校长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领导
这涉及校长的招聘及其基本资质。
德国中小学校长是由各个学区教育主管部门来招聘,招聘广告刊登在该联邦州政府公报上。应聘者必须毕业于师范专业,而且一定是要对口学校类型的师范专业(比如小学师范专业出身的教师只能应聘小学校长职位),必须具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与经验,必须具备超越师范教育所获得的素质,比如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冲突应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政府教育方针和学校教育理念的执行贯彻能力等等。原则上,候选人不得来自招聘学校。遴选委员会通常由下列人员组成:所在学区教育主管部门代表(遴选委员会主席)、该主管部门指定的校长代表、该校的全校大会代表(14周岁以上的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教师大会代表和人事委员会代表。遴选委员会向该校所在学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推荐人选,通常为一名人选。同时,该校教师大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会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对遴选委员会所推荐的人选表态并面试。在对上述表态与人选推荐的权衡基础上,教育主管部门最终确定人选,试用期为半年。
以上所描述的校长基本资质显示,校长候选人的师范教育背景决定着其对自身作为教师的职业认同。至于这位候选人在应聘之前是否拥有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经历与经验,则另当别论。可见,职业认同远胜于职业履历。正是由于校长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各个联邦州对校长和教师的职责通常采用无差异规范,一般情况下是由各自的“学校法”来厘定两者的职责,也有些联邦州如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是通过《对公立学校教师和校长的基本工作制度》来约束教师和校长,当然亦不排除特例,如萨尔州(Saarland)制定专门法规《校长基本工作制度》来使校长日常工作制度化。
(二)校长首先是教师的业务领导,其次才是教师的行政领导
校长是包括见习生在内的所有学校工作人员的业务领导,并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示对所有工作人员实施行政监督。在有些联邦州,小学和主科中学的校长仅仅是教师的业务领导,在后续的各类学校,校长同时还是教师的行政领导。所谓行政领导,就是校长有权对教师作评价并实施惩戒措施以及人事权(包括教师的岗位与工资定级等)。强化校长作为教师的业务领导角色,是因为校长始终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同时,德国中小学教师的公务员身份限定着校长的行政领导角色。由于各个联邦州拥有各自独立的文教主权,作为公务员的中小学教师由所在联邦州直接掌控,并受制于“公务员法”。就是说,教师的雇主不是校长,而是联邦州政府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各联邦州的文教部或直辖市的教育署)。巴符州(Baden-Wuerttemberg)是特例,州长是该州所有中小学教师的行政领导。
(三)校长与教师首先是合作的关系,其次才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
作为教师队伍一员,校长无法以行政指令的形式责成全体教师展开团队合作,而只能通过平等参与和对话的形式来推动团队合作精神的构建。比如Frey校长,她每周工作50-60小时,所承担的日耳曼文学课程只占用6个课时,其余时间均投入教育领导工作,交谈的比重占到七至八成。这种交流不仅仅针对本校教职员工,而且还面向校内校外各类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家长、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所在地区政府各个行政单位。尤其是与教师的对话形式多样,主要分为单独交谈与集体交谈两大类。前者有求职交谈、评价性交谈、批判性交谈、咨询性交谈、信息性交谈、人事发展交谈等。后者有全体会议、分组会议、专业会议、班级会议、工作小组会谈、人事委员会恳谈等。可以说,Frey校长是以对话实现教育领导。对她来说,信息阻滞甚或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教师合作关系的破裂是导致教育领导失败的主因。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极端的要数维斯巴登市(Wiesbaden)马丁·尼默勒学校(Martin-Niemoeller-Schule),由于校长的专横跋扈而导致两代教师针锋相对,学生却沦为直接受害者,2007年高一学生中竟有三分之一不合格。最终,2007年圣诞夜凌晨,该校的一名18岁学生为销毁自己的档案,深夜陷入学校管理人员办公室。不料,铁制档案柜的火焰却焚毁了整所学校。2008年3月3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对此作详尽报道,并取题为“一个理念的毁灭”。[3]其实,该案例所毁灭并非报道中揣测的学校教育的普世取向,而是Frey校长践行的以对话实现教育领导。
三、对话的三层涵义
通过对当前各类教育管理文献的梳理,涉及“教育领导”的概念竟多达60种之多。[4]“教育领导”概念的不确定性或多或少是“领导”概念对实践的依附性的一种表现。尽管“教育领导”概念尚未明晰,但是,教育领导对学校发展的有效性或影响力却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以确认。[5]教育领导力可以视作教育领导对学校发展的有效性或影响力的衍生物。
对话的教育领导力蕴纳三层涵义:
(一)对话的前提是平等
在我国,关于师生平等的文献汗牛充栋,忽视的却是校长和教师之间的平等,这可归因于国家干部聘任制度。无论是校长的行政领导身份还是“校长”称谓,均注定其与教师的不平等关系。在德国,校长对“同侪之长”的角色定位尤其是角色意识为对话提供可能。
对话通常被理解为以语言为媒介的平等交流。这只是一个狭隘的释义,广义的对话其实就是交往。(二)对话的平台是生活世界
可见,校长与教师的对话应该是以教师专业发展、以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为目的,对话内容主要是教师所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和教师的身心问题。
针对前者,校长与教师需要制定目标协议,该协议应该具有以下特性:针对性,即目标必须针对事与人;可测性,即目标必须是可检验与评估的;行动指向性,即目标必须以具体行动为对象;现实性,即目标必须一目了然而且在内容上要有所限制;时间性,即目标必须拥有确定的时间表。
而后者涉及的是德国学校教师中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即职业倦怠症。80万之巨的德国教师队伍,每年约有5000名至6000名提前下岗,平均提前年数为10年。其中仅6%尚能勉强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早退人员中生理和心理病因各占一半。对于心理高危群体可以采取干预措施,如提高对教师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认可度,改善工作条件和学校社会氛围,加强对师范生实际操作能力如自我减压的训练,提高教师的心理自我调控能力和求助专家的意识等等,[6]或者采用六十年代开创的心理自我聚焦法(Focusing)。[7]
这些措施与其说是建议,不如看作为对校长责任与义务之呼唤要是作为“同侪之长”的校长能够长期与教师保持平等对话、互换心声,这无疑是上上之策。正如奥地利领导学专家Hans H.Hinterhuber所言,“领导的终极使命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们自我发展并且挖掘其潜力,或许还要激励他们追求比自我认定的可能性更高的境界”。[8]
(三)对话的根基是对话共同体
尼德奥姆文科中学要打造“一个推动共同体发展的对话文化”。既然是“同侪之长”,校长给予教师的就不该是行政指令,而是指导、支持与关心。
四、对话共同体的构建
德文中“领导”概念主要以Leitung和Fuehrung来表述,要是把前者理解为国家行政授予的领导职责,后者为个体人格特质所秉承的领导力,[9]那么,“领导力”概念可以说是研究视角从领导者的人格特质[10]和行为转向情境交互[11][12]和整体性的产物,从拥有职权的领导者转向每个个体。
在德国中小学,“校长作为教师之同侪”的制度安排与职业认同,以及视对话为教育领导之媒介,无疑为学校成为民主的生活世界和对话共同体创设必要条件。以同侪角色为基点,以对话来点燃、养成并提升学校作为民主的生活世界的每个成员的领导力,不啻为一条崭新的道路。何况,针对领导力发展的教育措施“并不局限在学校里面;它开始于家庭,并潜在地存在于社会的每个主要的部门和机构中。……在很多方面,领导得到的培养和成型的地点可能更多的是在家里、教堂、运动场上和工作中,而不是在学校”。[13]人人均可时时处处发展领导力,尤其是在学校这个民主的生活世界,每位成员均可充分发挥教育领导力。
上海市建平中学一名高三女生的转学申请书,以及由此发生在她与校长的一次对话,给予该校校长冯恩洪以强烈震撼,[14]从而改变其学校发展理念并推进冯恩洪校长的专业发展。这个突发事件同时也无意间点燃了这位高三女生的教育领导力,人微言轻的学生亦能为对话共同体的建设奉献出一份绵薄之力。于是,从另一侧面来看,对话也是一种“学习型”管理。所谓的“学习型”管理是以共同愿景为基础,以团队学习为特征的对下属负责的扁平化的横向网络系统,强调“学习+激励”,不但使人勤奋工作,而且尤为注重使人“更聪明地工作”,以增强学校的学习力为核心,提高群体智商,使教师活出生命意义,自我超越,不断创新,达到学习财富速增、服务超值的目标。[15]在这个意义上,对话共同体与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具有同构性。[16]由此,教育领导力与学习力遍布在这个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身上,教育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更是隐藏在学校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校长的真正使命便在于,在激发这个生活世界及对话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学习力之基础上整合其教育领导力。[17]
本文得益于与两位德国专家的多次交谈:学校发展国际网络组织缔造者、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创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威州州长咨询专家、多特蒙德市教育改革委员会主席、《学校发展研究》期刊创办人Prof.Dr.Hans-Guenter Rolff先生;德国莱法州中学校长联合会主席、尼德奥姆文科中学校长、莱法州校企协作委员会主席OStD Christel Frey女士。在此致以由衷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