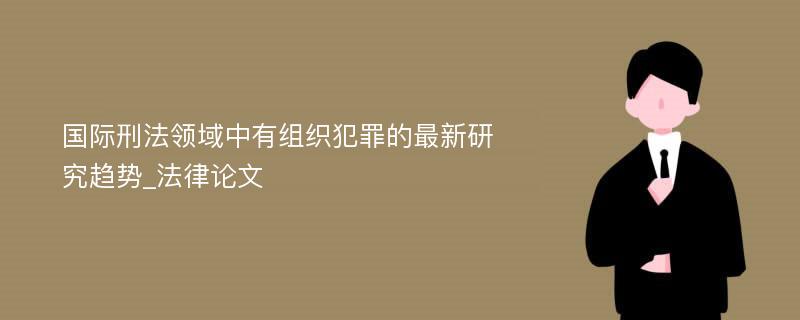
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刑法论文,动向论文,有组织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就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态进行了较为全面、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有组织犯罪的定义。本文列举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有关定义,并总结了有组织犯罪的一般共同因素;二、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方面主要涉及犯罪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刑事责任理论问题,这些理论与传统刑法的刑事责任理论及制度有明显的不同,面临一些新的观念;三、对有组织犯罪的刑罚。这种刑罚显然与传统的个人刑罚不同,那么这种刑罚的体系、执行与效力应是怎样?这正是国际刑法学界所要深入探讨的。四、对有组织犯罪的诉讼,涉及无罪推定原则、证据调查、当事人保护等三个方面的理论更新;五、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合作的障碍主要是各国间经济及司法制度不一致;合作的领域是对跨国的有组织犯罪在管辖、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阶段进行国际警察或司法合作。本文同时也介绍了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有关措施。
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犯罪形式,目前正成为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立法部门和刑法学界普遍予以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商业和旅游的发展,有组织犯罪逐步步出国界,其活动和危害范围远远超出单个国家的范围。由于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上不一致,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常常利用这一点来逃避惩罚。这种新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对于当今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对各国传统的立法和司法形式构成了挑战。如何改革和完善立法与执法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预防、遏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泛滥,是世界各国立法机关和刑法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国际刑法学界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遏制和打击方面的研究动态及一些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在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进行综述,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一、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
传统刑法理论研究者通常将有组织犯罪视为刑法学的边缘现象 〔1〕。然而有组织犯罪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下述两类不同的团体性犯罪中:其一是具有单一的或明确的犯罪目的的组织,如从事不法毒品或少儿淫秽品交易的集团;其二是偶尔从事环境犯罪或不正当商业交易的公司企业都存在着以组织名义从事犯罪行为的个人刑事责任的分担的难题。对于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组织,加入犯罪组织并成为其成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种作法通常也引发其它问题。对团伙(集团)犯罪行为制定适当的制裁或刑罚也产生新的问题:由于犯罪组织的首领或团伙(集团)的犯罪行为是否惩罚一个组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何种惩罚是适当的和有效的?上述问题与犯罪组织是否被看作是刑法的主体和刑罚的客体紧密相关。最近一些国家在刑事立法实践中的作法反映了支持团伙(集团)刑事责任的主张的趋势。〔2〕
有组织犯罪很难给予确切的定义,也很难归纳为某一特定的行为;有组织犯罪常常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犯罪。以犯罪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organization)或“联合体”(combination), 如法国的“犯罪团伙”(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和意大利的“黑手党”(Associazione di tipio Mafiopso)等犯罪组织所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如走私毒品、武器、人体器官、汽车、核材料、艺术及文化品,以及贿赂、诈骗、洗钱、一些垄断犯罪、财务犯罪等。犯罪组织有时为了犯罪组织的利益也实施另外一些“普通犯罪”(common crime),如盗窃、谋杀或绑架〔3〕。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 不同的国际组织及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国际刑警组织第一届反有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将其定义确定为“任何企业或群体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而从事连续的、有时是跨国的不法行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专家认为上述国际刑警组织的定义没有包括“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含义。 德国警察组织( BKA )将“有组织犯罪”定义确定为“任何以尽快积聚大量利润为目的群体在一段时间里通过群体内部的分工并通常利用现代手段有意识地、自愿地决定合作从事不法行为”〔4〕。 来自美国及加拿大的专家认为上述定义没有包括“以暴力手段实现群体的目的”的含义。自那时起,国际刑警组织反有组织犯罪处对“有组织犯罪”作如下定义:“任何具有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有组织犯罪一般包括下列因素:(1)实行贿赂;(2)使用暴力;(3)手段老练、 行动复杂;(4)行为连续;(5)结构严密;(6)纪律严格;(7)意识性强;(8)多重冒险;(9)渗入合法企业;(10)举行入伙仪式。
二、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
(一)犯罪组织内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有组织犯罪的危害通常不是一个个人的故意或过失的不法行为的结果,而是一些人的集合体的不法行为或缺乏有效控制和领导而恶化的过失行为的结果。犯罪组织的首领和管理者远远避开犯罪组织的日常活动,因此而辩称对下级团伙的任何犯罪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下级团伙则辩称他们不知道其所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律,而只是执行上级的指令。打击这种有组织地逃避刑事责任的教条式的方法是扩大对“犯罪行为的实施者”、“过失的刑事责任”、“从属的责任”及“不完全责任(如:同谋)”的定义的解释。司法制度可不同程度地利用这些方法来达到有效地打击有组织地逃避刑事责任的行为。因此研究各种不同形式的有组织犯罪行为的理论、从犯的法律责任及对团伙犯罪的适用均很有意义。国际刑法学界目前对下列问题较为关注:
1.在刑事立法和刑法学中存在什么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共犯和作为他人工具的“枪手”的概念的外延是什么?关于后者,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是否被认为是“无辜的代理人”,或是否存在公认的其它形式的间接犯罪,如胁迫和上级指令?在间接犯罪分子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时,是否有可能指控那些幕后操纵者负有间接犯罪的刑事责任?“代受责任”的概念是否被普遍接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刑事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建立“代受刑事责任”制度的要求是什么?
2.作为主犯之外的从犯的刑事责任(特别是:教唆,帮助和煽动)的原理是什么?从犯刑事责任的要件,尤其是从犯的犯罪意识是什么?从犯对其教唆或支持的犯罪的内容应知道的程度?是否存在过失教唆、过失煽动?教唆犯罪和帮助犯罪的要件是什么?从犯责任是否必须是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是否需要主犯承认从犯有受惩罚的罪行?主犯是否必须受到惩罚或他的行为必须是充分的不法行为?
3.主犯和从犯相互区别的标准是什么?对从犯处以的刑罚是否要比主犯轻?
4.是否存在不需要“主要犯罪”的主犯的假定的从犯责任形式?特别是:是否存在教唆或帮助从犯责任、企图教唆或帮助的从犯责任、提供犯罪的从犯责任、策划犯罪的从犯责任或煽动犯罪的从犯责任?在后一种形式中,一般的策划过程是否就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从犯责任,还是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教唆的行动?在尚未认定为从犯的案例中,犯罪意识的要件是什么?
(二)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
犯罪团伙和犯罪组织的特别危害性得到普遍的一致认可。犯罪群体能够比犯罪个体提供更高级的更先进的装备和后勤;犯罪群体通过增强经济实力使得他们能够渗透到合法商业领域和公共行政管理领域,而上述渗透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源。更有甚者,团伙帮规和控制以及升入团伙内部更高地位的期待使得团伙成员产生遵守帮规并依附于团伙的强烈动机,并拒绝脱离甚至“背叛”团伙。
由于团伙犯罪特殊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心理特征,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构成显著危险。许多国家在其刑事立法中因此将加入犯罪团伙或组织作为“自身犯罪”(per seoffense), 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这种罪名的确定能够作为有利地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武器,因为这种罪名的确定不需要个人的特定犯罪行为的证据,而是加入危险组织其行为本身即为犯罪。另一方面,这种罪名的确定因其没有遵守“犯罪行为”的要求以及其着眼点集中于犯罪者的地位和社会联系的倾向而受到批评。为了评估“加入犯罪组织罪”的优缺点,国际刑法学界就下列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
1.受犯罪组织或共谋的委托所实施的犯罪是否成为加重刑罚的根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适用何种犯罪?
2.加入某一有一定的犯罪目的的团伙或组织并成为其成员的事实是否可确定为犯罪(独立于其他任何犯罪行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加入犯罪组织的罪的原理是什么,是犯罪组织存在的危害性,还是将要从事的特定犯罪增加了的危险性(如企图或预谋犯罪)?“犯罪组织”的定义如何界定?如何界定犯罪组织的形式(最低成员数、内部组织和领导结构)?在特定犯罪中,犯罪组织的成员和共犯如何区别?
3.如果加入某一犯罪组织本身是一种犯罪,如何界定“犯罪组织成员”?刑法中是否作“犯罪组织领导”、“犯罪组织的影响”和“对犯罪组织的长期依附”的假定?有组织犯罪是否需要为组织的犯罪目的的实现而实施的特定犯罪行为?或仅遵守犯罪组织的“帮规”(或秘密地遵守)就构成犯罪?犯意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某人在一个与犯罪组织有关的犯罪行为实施后加入该组织,此成员对上述犯罪是否有关联?或某人在犯罪行为实施前脱离该组织,情形又如何?
4.是否存在有特别的正当理由,如根据宪法确定的结社自由,涉及到从表面上看是宗教或政治团体的有组织犯罪?
5.是否有特别的免责理由,如胁迫、对有组织犯罪目的的不知情?加入犯罪组织罪是否应界定为严格的责任犯罪?犯罪组织成员能否因其脱离犯罪组织或向执法部门提供犯罪组织内部结构的情报而免受处罚?
6.加入犯罪组织罪和代表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关系如何?是否存在“一罪数罚”的问题?
三、对有组织犯罪的刑罚
在查明代表犯罪组织或为犯罪组织的利益而实施的个人行为有过错时,对犯罪组织处以刑罚也是有可能的。有些适用于犯罪个人的刑罚很显然不能适用于犯罪组织——如监禁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在立法中单纯地制定针对组织,特别是商业企业的棘手性犯罪问题的刑罚。国际刑法学界现在正对下列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1.对犯罪团伙和犯罪组织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如果罚金刑是可行的话,这种罚金刑与对犯罪个人处以的罚金有什么区别?针对犯罪组织处以的罚金数额如何确定?犯罪组织资产,特别是犯罪收益能否被没收?没收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没收作为对有组织犯罪的刑罚可行性如何?没收和罚金的法律要件?是否必须查明犯罪组织的不法行为的证据,或犯罪组织成员的犯罪意识能否导致对该组织的刑事制裁?是否存在没收的法定最高限额(如比例性、为获得财产债务免除而受到不恰当的压力而承认犯罪全部没收的禁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否有可能没收犯罪组织的部分资产?部分没收和全部没收的证据标准是什么?没收是否影响到善意第三人?对这种影响有无保护性措施?
2.是否制定专门适用于犯罪组织的刑罚,这些刑罚在何种条件下适用?
3.法律是否可规定针对犯罪组织的刑事性“预防措施”?除刑事制裁外,针对犯罪组织的犯罪行为,能否对犯罪组织本身、犯罪组织成员或犯罪组织头领适用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适用这些处罚的意图是什么?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措施可以用来代替刑罚?
4.对犯罪组织所处以的刑罚的对象(犯罪组织本身、犯罪组织头目或执行官员、犯罪组织的拥有者或股东)?是否有可能因一个犯罪而对犯罪个人和其所属的组织处以刑罚?对犯罪组织的成员的刑罚和对犯罪组织本身处以的刑罚能否累加?出现“一罪数罚”(ne bis in idem)的问题如何解决?
5.对犯罪组织判决的执行是否有特别规定?
6.对犯罪组织处以的刑事制裁的效力(与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相比)如何?何种制裁具有普遍的预防效力?对犯罪组织处以制裁与对犯罪个人处以严格的制裁,如剥夺自由相比是否能产生普遍的预防作用?
四、有组织犯罪诉讼中的有关问题〔5〕
下列三个问题是目前国际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1.“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检察官必须承担证明被告有罪并受刑法惩罚的举证责任。在实践中,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由检察官和被告双方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共同承担的事实确实存在。同时,在有些国家的立法中也确实存在“有罪推定”的规定。无疑,“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都不是绝对的。然而,确定应由被告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无罪的规定也是可行的。尽管在《欧洲人权宪章》第6条第2款中将“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作了规定,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一些关键证据被隐藏和存在获取证据无法逾越的障碍的合理条件下可以接受“有罪推定”。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特定的有组织犯罪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倒置是否会加重责任?法国在1996年5月13 日颁布了一个新的严格的单行刑法,该法规定:与毒品走私者保持经常联系而又不能证明自己的生活财产的来源是合法的人为有罪。这就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生活来源可以构成犯罪的例子,被告因此就有义务证明其收入来源与毒品无关。在法国,这种机制在很长的时间是被用来对付妓女的保护者,事实上这种犯罪通常被看作是有组织犯罪家族的一部分。如果在特别立法中将有组织犯罪的举证责任的倒置比在一般刑法中更推进一步,就有必要研究“有罪推定”的许可限制与保持“无罪推定”的一致。
2.证据的调查
在讨论对有组织犯罪的证据的侦查问题时,就必须首先确定是否违反一般的刑法规定。例如,调查者是否可以搜查在公海上的船只?在刑法的一般规定中,调查者的管辖权只局限在领土范围之内。之所以引发这个问题是因为调查者显然希望查获在船上走私的毒品,并在一旦查明该船只涉及走私时将其抓获。1988年12月19日在维也纳签署的《联合国反毒品走私公约》规定:可以允许要求涉嫌船只改变航线。有些国家已将上述规定结合在国内立法中,如法国1996年4月29 日颁布的单行法中就包含此规定。
在讨论搜集证据的技术问题时,人们必须确定一般刑法规定所设置的限制:(1 )监视走私路线或假冒委托毒品走私的方法以发现已被调查者怀疑的走私者;(2)电话窃听;(3)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审讯嫌疑人;(4)全天候搜查和扣押;(5)讯问不能违反其职业保密义务的证人;(6 )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官冻结犯罪组织银行帐号或没收犯罪组织资产。
这里也涉及到调查的提前介入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犯罪行为实施前,甚至在犯罪预谋阶段就开始调查。前面所列的措施都带有提前介入的特征。
3.当事人的保护
关于公平对待在打击有组织犯罪过程中的合作者,特别法律规定的特别措施是否比一般法律更具有保护性。众所周知,对证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不断增加的威胁,因此就产生了制定特别保护措施的必要性,例如,法律是否允许证人不披露他或她的住所及全名(欧洲法院已决定允许“匿名作证”)。
当证人在受到暴力威胁保持中立时,法律是否规定特别施压手段以防止证人不作证,或鼓励证人撒谎?当受害者是司法官、陪审员或警察时,这种施压手段的程度是否会增加?对有组织犯罪的审判是否可以“跳过”陪审团或选择特别的法官审理?
对于被告来说,当涉及有组织犯罪的审判时,对其个人自由的规定是否更严格?在预审阶段,一个较长时间的保护性羁押似乎是有理由的,但这种羁押是否有法律依据?在那些引进将“电子手铐”作为羁押替代物的国家,这种措施对打击有组织犯罪是否有力?最后,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法律是否规定特别的保护措施?
五、预防、遏制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6〕
预防、遏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面临着难题。首先,各国对“有组织犯罪”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存在一些经济、司法制度方面的障碍。在涉及有政治目的的有组织犯罪(如恐怖活动)中,困惑于70年代条约制定的障碍(主要是政治犯引渡)依旧存在。
国际合作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域外管辖权问题
人们注意到,包括在“有组织犯罪”类型范围内的犯罪通常在超过一个以上的国家的领土上实施。大多数有组织犯罪计划,包括各种形式的走私(毒品、武器、核材料)也包括在此类型范围内。发生在A 国犯罪的收益可能通过洗钱转移到B国,第二次又可能转移至C国,因此就有可能导致在超过一个国家以上的领土上实施“犯罪链”的局面(很令人惊奇的是,1996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反有组织犯罪框架公约》中竟然没有涉及此类问题)。
关于管辖权的延伸引发出下列问题:当存在域外刑事管辖权因素时(罪犯的国籍、受害者的国籍),国家在何种程度上适用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来允许对这种“新的、复杂的犯罪”进行惩罚?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是严格遵守他们的管辖权原则,还是为惩罚域外犯罪而扩大刑事管辖权的范围?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是否感到有必要特别立法来扩大刑法的域外刑事辖权?
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域外管辖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洗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管辖犯罪”,这就为刑事司法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洗钱是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新的、复杂的犯罪”的典型案例,因为洗钱至少有两个因素组成:预先犯罪和洗钱。当洗钱行为发生在一国领土上,而预先犯罪发生在另一国领土上的案例中,洗钱行为发生地国对此案是否有管辖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涉及到域外犯罪的预先犯罪管辖权是否应有一些特别的条件(如双重犯罪原则)?,反之,当预先犯罪发生在一国领土上,而洗钱行为发生在另一国领土上,预先犯罪发生地国对洗钱犯罪是否有管辖权?当预先犯罪和洗钱都发生在国外,一国能否根据某些条件享有管辖权(如:国籍原则、保护性原则、普遍管辖原则)?
在管辖权的冲突、多重起诉和“一罪不数罚”方面,有组织犯罪的复杂性可能导致一个以上的国家对犯罪享有审判管辖权的局面。在所涉及国家都准备实际行使管辖权时,在这些国家之间就有可能产生摩擦或冲突。在过去,曾通过引入“优先顺序”的作法来解决所涉及的国家的共同管辖权的问题的努力,然而,所作的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在国家间达成一致的标准。
超过一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犯罪的共同管辖权问题有可能导致同一罪犯因同一犯罪而受到多重起诉的风险。这就引发了“一罪数罚”的问题(在同一国家同样也有可能发生“一罪数罚”的问题)。一些国际公约,如《申根协定》、《欧盟反诈骗公约(1996)》曾试图解决此问题,但也没有完全解决。
2.对有组织犯罪侦查阶段国际合作
(1)警察合作。有组织犯罪已改变了许多国家犯罪侦查的面貌。 新的刑侦技术(各种监视谈话、人和物体的形象和运动的技术和方法)业已开发并利用,一些有争议的侦查手段(受控制的假释、便衣警察、利用告密者、打入犯罪团伙内部、线人、与犯罪分子作“出卖情报”的交易、鼓励告密和自首、向犯罪分子许诺豁免以换取罪犯与警察的合作等)也在大量使用。有时这种刑侦技术的变革被称为“刑侦的提前介入”,这些手段的目的不在于收集情报,而是将这些情报作为证据将罪犯送上法庭。有人认为这种“新的”侦查手段与“冷战”期间情报机关(或反间谍机关)曾使用的手法相似。
各国对刑事侦查的这种变革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国家基于人权保护的观点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变革,而另外一些国家似乎准备最大限度地牺牲人权来确保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性。不幸的是,警察合作直到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交换情报的基础上,没有条约根据。解决警察合作的第一个国际公约是欧共体成员国签订的《申根协定》,在该协定中关于警察合作的条款就包括“跨国境执行警务活动”的规定。欧盟同时也正在商讨有关此方面的立法(如在海关合作领域)。
警察合作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在国外设置联络官。这些联络官可以安排在派出国的使馆,或被安排在接受国的内务部(或其他部门)。在欧洲警察总部,欧盟成员国将其联络官安排在一个集中的地点:即在海牙的欧洲警察总部。这种联络官的设置有效地促进了警察合作的效率,在有些情况下,刑事侦查可能有来自一个以上的国家的警察官员组成的“联合侦查小组”来实施,在有些领域中,如欧盟国家内部的打击诈骗犯罪,在欧盟工作的公务员(欧盟反诈骗犯罪局)曾协调这种联合侦查小组的侦查活动。
(2)司法合作。 “传统的”司法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对特定犯罪的证据委托被请求国代为收集,以使得请求国对特定的嫌疑人提起诉讼。随着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发展,一种新的司法协助的形式已出现,其主要目的是冻结犯罪所得资产,以保证在罪犯最终被判罪定刑时对其犯罪资产处以没收。由于犯罪收益(特别是跨国犯罪)可能持续很多年,因此就有必要在诉讼程序一开始就对其予以冻结。为此目的已制定出一些新的公约,包括《维也纳公约(1988 )》和《欧洲反洗钱犯罪公约(1990)》,一些未批准加入的国家也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公约的规定。
司法行政联络官。警察联络官的设置是对警察合作的一个显著变革,司法行政联络官也许是对司法合作的一种变革。例如,法国分别在意大利和荷兰设立了司法行政官代表处。与通常被安排在派出国的使馆的警察联络官不同的是,法国的司法行政联络官被安排在接受国的司法部。司法行政联络官的任务是:帮助司法协助请求的制定:协助条约的谈判;向接受国通报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事宜(新的立法、重大案件)及组织培训等。此外还存在一种“更垂直”的模式,在此模式中,司法行政联络官被安排在一个集中的机构(以取代分散到各国的做法),例如欧盟反诈骗犯罪局,欧盟各成员国派司法行政联络官驻在布鲁塞尔。有些国家,如比利时,不是选择派驻司法行政联络官的方式(欧盟反诈骗犯罪局和欧洲警察总部除外),而是在国内设立一个新的“国内司法行政官”来集中处理往来司法协助请求。英国的中心局也有类似的功能。
原告证人合作的障碍。刑事司法制度的另一个变革是使用那些被怀疑是犯罪组织成员的证人,而这些证人获得如与警察或司法当局合作可以免于起诉的承诺。这种与嫌疑人或证人的交易可能对国际合作产生严重的后果。假定X国和Y国针对一个是国际有组织犯罪网的成员A 同时进行调查,再假定X国对A已许诺如A 对他的同伙的犯罪进行检举或在开庭时作证将对A免于起诉,在这种情况下,Y国将很难从X国获得有关A的情报,更不用说获得在A国的管辖权。 这就有可能在两国的司法当局间引发紧张局势。
3.对有组织犯罪起诉阶段的国际合作:域外管辖权
对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起诉前提条件是,必须确保嫌疑人到庭(尽管在一些普通法系国家允许缺席审判)。如嫌疑人逃往国外,域外刑事管辖权就为确保起诉的基本手段,然而,直到现在,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责任人的域外刑事管辖权还没有一个普遍的公约。
“双重犯罪”。在域外刑事管辖权案例中很容易产生“双重犯罪”(标准)的问题,例如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依据“谋杀罪”向另一个属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发出域外刑事管辖权的请求,而被请求国也许认为此犯罪行为是“团伙犯罪”。有关此类“罪名不对称”案例还有:在一个对公务员行贿的案件中,由于不具备双重犯罪标准,域外刑事管辖权根本不可能得到保证,因为被请求国法律规定只惩罚自己的公务员,不惩罚行贿者。在一些地区范围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双重犯罪的条件也进行了变革,例如,1996年9月27 日通过的《欧盟域外管辖权公约》就规定对一些有组织犯罪(如密谋团伙犯罪)不适用双重犯罪标准。此外,在被请求国也有可能对被请求实行域外管辖权的犯罪没有相应的罪名的情况,也许这种情况不构成域外管辖权的障碍,但很显然也会对域外管辖的顺利实施产生障碍。
4.在刑事制裁的执行方面的国际合作:犯罪收益的没收
在大多数国家,对有组织犯罪的处罚有一整套的刑罚:监禁、罚金及行政处罚。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所适用的刑罚中,没收是一种最重要的、“新的”刑罚。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之一是犯罪组织的成员以一种最大限度地逃脱法律制裁的方式进行精心组织,同时也保护他们的资产不被查获和没收。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个罪犯在X国被判罪定刑, 而被处以没收的犯罪资产在Y国和X国的领土上。又如,A向B(X 国的公务员)行贿,所行贿的金钱被汇入B在Y国的银行帐户上,B用受贿的金钱在Z国购买了豪华别墅,即使X国对A和B判罪定刑,并对贿赂物处以没收, 没收的执行就必须依赖于Y国和Z国的合作。现有的两个关于洗钱的国际公约(《维也纳公约(1988)》和《欧洲议会公约(1990)》就包含有处理此类问题的规定。
5.公正审判权国际合作
打击有组织犯罪(国内的或国际的)所采取的措施使刑事司法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但也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如侦查的提前介入。在侦查结束后,罪犯被提交审判,但警察的侦查行为也有可能被提交给审判法官。假定存在对警察的有可能导致嫌疑人被逮捕或起诉的警务活动进行规范的实体法(如警察行为规范),就有可能需要查明在实际的警务活动中这些实体法是否被真正得到遵守。在单纯的国内案件中,这种查明就有一定的难度,因嫌疑人通常不知道起诉他的证据是根据密报还是通过警务活动的提前介入的方式获得的。这种侦查方式的目的就是要对嫌疑人或其所属的犯罪组织进行秘密调查。这种秘密调查也可能有合法的或不太合法的理由:一个合法的理由是有必要保护告密者或可能的证人不受嫌疑人所属的犯罪组织的报复,一个不太合法的理由是掩盖处在监视和诱人上当的边缘的侦查活动。
很显然,当案件需要进行跨国侦查时,这种作法就有可能带来难题:要查明这些情报是如何获得及手段是否合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对被告来说,要查明警察在他的案子中是否使用不法手段是极端困难的。
通常国家对被告并不承担告知从国外获得情报的方法的义务。按《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的“公平审判权”规定, 如一国不向被告披露证据是通过跨国警察合作得到的行为绝对不能认为是对公约第6 条规定的违反。因此,向法院提交的案卷可以不包括有关境外侦查活动的记录。
即使存在警察侦查活动违法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事实,一国法院并不会因此而驳回对嫌疑人的起诉。不同国家的法院在查证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的可接受性方面有不同的作法,其所适用的证据排除规则也不尽相同,此外,在一国内部,不同的法院对境外获得的证据态度也不一样。因此警察就有可能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罪犯交给那些允许境外取证的国家的法院进行审理。 如, 在著名的“CHINOY”案件中,一家英国法院就接受了美国警察在法国国土上未经地方当局许可就实施的不合法的电话窃听所获得的证据而起诉的案件。〔7〕美国缔结的一些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就明确规定, 被告不能根据条约对所获得的证据提出不合法的质疑。例如,美国与开曼群岛共和国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就规定:该公约本身不赋予任何私人有获得、隐匿或排除证据的权利。在美国与瑞士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注释:
〔1〕Thomas Weigend:Section I:General Part, The CriminalSystem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Organised Crime.
〔2 〕典型的有组织犯罪和那些在内容上符合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的犯罪的区别,与暴力活动和政治罪例外有某些相同之处,客观上存在纯粹的政治犯与带有政治色彩的犯罪的区别。
〔3〕见Tiedemann,Freiburgger Begegnung,《Strafbarkeit Vo-njuristischen Peersonen?》,P.P30—54,1996.
〔4〕引自“国际刑警组织第一届反有组织犯罪研讨会”,法国,圣克劳德,1988年5月。
〔5〕《Communication on the Theme of Criminal Procedure》,by Jean Pradel,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Law and SocialSciences,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riminal Sciences inPoitiers,France.
〔6〕《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Explanatory Note 》,byChristine Van 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Professor of Law.University of Anerwarp.
〔7〕CHINOY因毒品走私和洗钱而被美国海关追捕, 美国海关官员在巴黎扮作一名商人并在法国巴黎诱捕并抓获CHINOY 。 该海关官员和CHINOY之间的谈话录音被美国当作域外管辖权的证据向法国提出引渡的请求,然而法国以该证据的获取违反了法国法律为由拒绝引渡。因此,CHINOY被引渡至英国,英国根据美国的请求将CHINOY拘捕并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