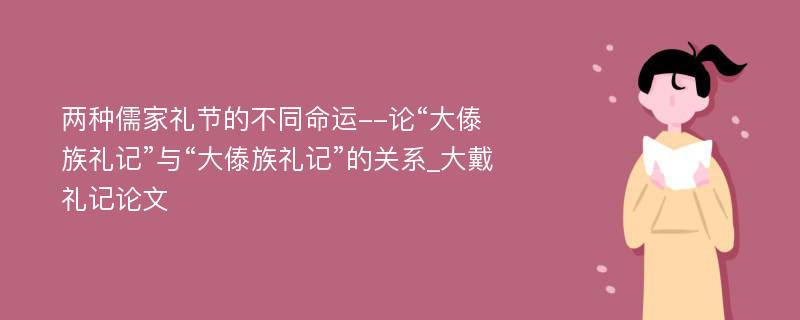
两部儒家礼典的不同命运——论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及《大戴礼记》的被冷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记论文,儒家论文,两部论文,命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二戴学术地位本不相同
戴德与戴圣虽然受学于同门,并且都以礼学名家,但实际上他们在西汉官学中的地位并不一样。这是造成后来大、小戴《礼记》命运不同的主要原因。
班固的《汉书》没有对戴德与戴圣这两位西汉时期的礼学家的生平作具体记载,因此对二戴的个人情况难知其详情。北朝礼学家熊安生说二戴是高堂生的五传弟子,即高堂生传萧奋,萧奋传孟卿,孟卿传后苍,后苍传二戴。这一说法后人有争议(注:见洪业:《礼记引得序》,载《礼记引得》卷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我们还知道戴德当过信都王太傅,戴圣作过九江太守。从官职看,信都王太傅显然不能与九江太守同日而语。九江太守在汉代属封疆大吏,任此职者都不是无名小辈。信都国则只是西汉北部边陲一个小诸侯国,太傅是诸侯王的辅佐。
我们还知道戴圣曾与同门师兄弟闻人通汉一起参加过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举行的石渠阁会议,戴圣当时已是博士,闻人通汉的身份是太子舍人,而戴德未见提及。说明戴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否他当时已经作了信都王太傅,不清楚,但已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学术地位远不及侄子戴圣,否则像石渠阁会议这样颇具权威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他不会被拒之门外。如果他参加了,史书中不会独不提他。遍考史书中提到的石渠阁会议的参加者,礼家唯有戴圣与闻人通汉,没有戴德。这样一次皇帝亲自出席平议学术争论的研讨会,戴德没能参加,说明他不是当时官方礼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汉书·何武传》有一段关于戴圣的记载:
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
据刘汝霖考证,戴圣因行治不法被何武“廉得其罪”,自免九江太守,在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注:《汉晋学术编年》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1页。)。那么所谓“后为博士”,自当在此之后。这至少已是他第二次作博士了(第一次在宣帝时)。
这段记载证实,小戴当时虽然行治不端,但学术名声却很大,被称为“大儒”,以至于在何武到任以前没人敢惹他。在他免官之后,朝廷又再次任他为博士,说明他是继后苍之后西汉官方礼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相反,大戴的情况于整部《汉书》中,除了曾作信都王太傅,别无任何笔墨。
二、《汉书》与《后汉书》未曾著录大、小戴《礼记》成书情况的缘由
大、小戴《礼记》是先秦儒家八派的“记”文的两种选编本,它们分别是大、小戴阐释《礼经》、补经所未备的主要依据。从目前的文献记载看,大、小戴《礼记》编订于刘向校书之后,其内容来源即刘向校书所得之二百余篇“记”。但大、小戴《礼记》的成书情况,《汉书》、《后汉书》都没有记载,没有记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小戴礼学虽然在西汉时已经有了名声,但并未独立门派,立在学官。小戴虽曾两度为博士,但是以后氏礼学的身份出现的。班固于《汉书·艺文志》中说大戴、小戴、庆氏均于宣帝时已立在学官,《汉书·儒林传》又说大、小戴礼学曾立在学官,未及庆氏,互相矛盾。王国维曾考订过这段历史,指出班固的说法有误,西汉并未立过大、小戴礼学博士,更未立庆氏礼学,而只立过后氏礼学博士,班固误将东汉初的情况写于西汉(《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据汉章帝建初四年的诏书看,西汉时确未立过大、小戴礼学博士,庆氏也没有,只立过后氏礼学博士(注:《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四年十一月诏曰:“蓋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认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东汉初年虽然分立了大、小戴礼学博士,但《后汉书》明确说二戴礼学当时未有显于儒林者。一度重新编订《汉礼》、想在朝廷发动一场礼制革新的曹褒,是庆氏礼的传人。班固本人对大、小戴礼学也没有好的评价,曾批评他们谬异偏狭,对卷帙繁多的古文礼书缺乏全面的了解(注: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在这种情况下,班固未给二戴《礼记》以笔墨,自然是情理中事。
第二,《汉书·艺文志》是记载西汉书籍存留情况的主要著作,但它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写成的,主要记载西汉秘府藏书情况,像二戴《礼记》这样的删自秘府藏书的私人“教学参考书”,未被收录也是很自然的。
第三,大、小戴礼学从西汉末年就开始衰落,东汉时谶纬之学的地位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传统的传、说、记之学,像大、小戴《礼记》这样以“记”为本的礼学,自然命运也不会例外。范晔著《后汉书》虽已在南朝刘宋时期,但一因为大、小戴礼学在东汉未显于儒林,二因为大、小戴《礼记》之编订不在东汉,而且大、小戴礼学在东汉很少见有人传习,因此《后汉书》也未予其笔墨。
三、大、小戴《礼记》的来历及其相互关系
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最早提到这两部书来历的是东汉末年郑玄的《六艺论》,其文曰: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郑玄没有说大、小戴《礼记》是如何成书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郑玄笔下,大、小戴各自传承的两部《礼记》,其价值与意义大不相同,戴圣的49篇是“礼”,大戴的85篇只算是“记”。郑玄没有把大戴的85篇看作礼书。这是他注“三礼”只注小戴而不注大戴的主要原因。郑玄的这种认识大概属于门户之见。其实大、小戴《礼记》的内容都有来自二百余篇古“记”,这已被清人关于大、小戴《礼记》内容的考证所证实。两部《礼记》中都有“礼”的内容,也有不属于“礼”的内容,比较杂乱。为何一曰“礼”,一曰“记”?郑玄本习《小戴礼》,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而这种门户之见,直接影响了《大戴礼记》后来的命运。因为郑玄的礼学在魏晋以后如日中天,始终在官方礼学中占据主要位置,郑玄的“三礼”中未收《大戴礼记》,因此《大戴礼记》一直被人冷落。
现有文献中最早提到大、小戴《礼记》的成书情况并提出小戴删大戴的是西晋陈邵的《周礼论·序》,其文曰: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注:《经典释文·叙录》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与陈邵之说基本相同,只是更为详尽。其文曰:
汉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杜佑《通典》的记载也与《隋志》基本一致,只是关于戴德所删取的古记文的篇数与《隋志》有异。与《汉志》相核,还是以《隋志》所记为是(注:《通典》卷四十一曰:“初,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从学者所记四百十一篇。至刘向考校经籍,才获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记》十篇,《王史氏记》二十篇,《乐记》二十三篇,总二百二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七篇,谓之《小戴记》。马融亦传小戴之学,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受业于融,复为之注……”《汉志》记《孔子三朝》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可证《通典》所记有误。见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233页。)。 徐坚《初学记》曰大戴先删自后苍之《后氏曲台记》180篇,成85篇;小戴又删大戴为46篇; 后儒又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成49篇(注:徐坚曰:“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从子圣,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转引自前揭《礼记引得序》。)。此说二戴《礼记》删自《后氏曲台记》显然不足信。与《汉志》相核,其所记《后氏曲台记》篇数亦甚可疑,《汉志》曰《曲台后苍》九篇。即使加上“《后氏说》一篇”亦与其180篇之数相去甚远。
晋陈邵、《隋书·经籍志》、《通典》都说戴德首先对二百余篇《记》文作了整理和删定,“删其繁重,合而记之”,对其内容进行了重新编订。然后戴圣又就戴德删订过的资料重新进行删订,成《小戴礼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礼学思想不尽相同。他们所传的《礼经》17篇之篇次也不尽相同。这种篇次的排列顺序直接关联着个人的学术思想(注:关于二戴的《礼经》(即《士礼》)17篇排列顺序,见前揭《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01页。)。 而小戴的再删订也不会是就大戴的本子删去几篇,留下几篇,而是如大戴当初一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对其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删订,因此才出现两种本子有的篇名相同,内容有出入;有的篇名不同,内容有相同处;当然也有完全相同的篇目,如《投壶》篇。陈邵、《隋志》、《通典》都作这样的记载,不会没有根据。
当然,在整理和删定的过程中掺入一些自己认为是重要的汉人的作品,并不足怪,因为它们主要是作为阐发礼义的依据、补经所未备以及传播礼学的教学参考资料而存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收藏和保留古文献。至于后人多有争论的到底小戴《礼记》原本是否49篇,是否经过马融足三篇之后才足49篇,这并不很重要。小戴《礼记》的篇章不完全是先秦的作品,但肯定都是刘向校书前的作品。个别篇章即使是后人加入,也不影响小戴《礼记》的基本定本来自于大戴这一基本事实。
四、对清代学者否定小戴删大戴说的重新审视
晋唐人的文献屡屡提及小戴删大戴,包括徐坚,虽然对大、小戴《礼记》的内容渊源有异议,但也承认小戴删大戴。这些说法不会没有根据,不可轻意否定,宋元明以来也一直没有人否定过。到清代,突然有人提出疑议。清前期汉学兴盛,考据学风靡一时,经学、史学、小学等诸多领域材料的爬梳,可谓成绩卓越,但于大、小戴《礼记》的研究并不深入,这已被有的学者指出过。但是清人的观点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很多人对这一问题并未深究而接受了清人的说法。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推敲他们提出疑议的理由。
清代怀疑小戴删大戴者主要有戴震、沈钦韩、陈寿祺三人。戴震说:
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礼》。殆因所亡篇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礼》亦列此二篇,则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已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者,则《隋志》不足据也(注:《清经解·东原集》,转引自前揭《礼记引得序》。)。
戴震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大、小戴《礼记》多处内容相同而文字多异。这确实令人怀疑。但仔细推敲,会发现这一条并不能证明小戴一定不会从大戴来。大、小戴受学于同门,但他们后来各自传学,在各自传学的过程中,所编定的《礼记》文各自传抄,文字多异自然难免。而其内容多处两见则更加说明小戴删自大戴之说有可能。我们必须注意,上引晋、唐人记载中多次提到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其意是说戴德删古《礼记》不是简单地丢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而是对杂乱无章的《礼记》文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订,把那些繁琐重复的篇章简册删除合并,以类相从,使其按照新的次序和章节面世。这当然有戴德的思想寓于其中。大戴是这样整理的,那么小戴呢?他与大戴的礼学思想不同,他对《大戴礼记》本的删定自然也不会照原样删去几篇,留下几篇,这样也不合情理。而应该是就大戴已经编订的《礼记》文再次进行综合整理、删定和编次,以体现和符合自己的礼学思想。这种工作在简册时代比现在更容易,更可能。包括各自收入的汉人作品都不同,如大戴收入了《保傅》,小戴则未收。这正是他们的《礼记》文本内容多处两见而文字不同、篇名不同的原因。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汉人的直接佐证。但晋、唐人的记载毕竟去汉未远,不可轻易否定。清人戴震怀疑小戴删大戴的理由最值得推敲,但仔细推敲起来,我以为他的理由并不能站住脚。他只注意到“删”字,而没有注意到这种删订是一种重新编订,而这种重新编订正是造成内容多处两见而次序与篇名有出入的原因。戴震说《隋志》以前未有小戴删大戴之说,有明显错误。前已引有陈邵之说。
沈钦韩怀疑小戴删大戴的理由就更加粗陋,他引《隋志》之言而论之曰:
按此俗说,不知《隋志》何所本。刘向校书在成帝时,戴德、戴圣论石渠在宣帝末年。只可二戴自删,刘向自合,不可云二戴承刘向之本。又大、小戴并授一师,同议石渠,各自名家,圣又何暇取大戴之书而删之?现行《大戴记》与《礼记》重复甚多,则不出大戴明矣(注:《汉书疏证》,转引自前揭《礼记引得序》。)。
首先,他的前提即以为二戴编订《礼记》在宣帝时,这本身是错误的,并无根据;其次,石渠阁会议就现有的材料看,只有戴圣参加了,戴德并未参加,所谓“同议石渠”是错误的;再次,二本重复甚多,恰说明小戴删大戴的说法有道理,不能成为怀疑的理由。
陈寿祺与戴震的观点大致相同,他指出了不少大、小戴篇名不同而内容互见、篇名相同而内容又有出入之处,又引了不少小戴所没有的大戴逸篇,从而证明小戴删大戴不足据(注:详见《左海经辩·大小戴礼记考》,前揭《礼记引得序》中有大段引文,兹文繁不录。)。他仍然是对“删”字的理解过于机械。因为现存本中不易看出“删”的痕迹,就否认小戴曾经对“大戴”重新作过删订,这恐怕有些简单化。所谓“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不是简单地删减,而是一种重新编订和整理。至于篇名问题在哪个时代本不那么重要,观今本《礼记》,若干篇名就是简策首端几字,《论语》等书也是如此。
总之,我认为清人的疑议不必轻信,晋唐人屡说小戴删大戴,不会没有根据。
五、《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
大戴礼学自始就没有在官方礼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东汉以后谶纬之学兴起,二戴礼学共同走向衰微。但由于小戴毕竟是西汉官方礼学的主要代表,因此小戴礼学的最终命运自然好于大戴礼学。
《大戴礼记》的流传情况,《汉书》与《后汉书》都没有人提及。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引有《大戴·礼器》(注:详见《左海经辩·大小戴礼记考》,转引自前揭《礼记引得序》。),服虔于《汉书》注中也提到了《大戴礼记》(注:见《汉书·王式传》颜注引。),但都有没有论及有谁传习。郑玄的《六艺论》论及大、小戴《礼记》,但也没有说有谁传习《大戴礼记》。而《后汉书》中至少明确记载有郑玄曾习《小戴礼》。《卢植传》曰卢植曾作《三礼解诂》,《续汉书》曰卢植作《礼记解诂》。《隋书·经籍志》有卢植注《礼记》十卷(注: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卢植传》,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也是指小戴《礼记》。可见大戴礼学在东汉同样地位不及小戴。郑玄注三礼,影响巨大,使《小戴礼》很快挤入经的位置,三国魏时即立在学官。魏晋以后郑学长期占据礼学的统治地位,因此《大戴礼记》长时期不见有人问津。直到北周,始有学者卢辨为《大戴礼记》作注,但《周书·卢辨传》既未言其卷数,亦未言其篇数。《隋书·经籍志》云:“《大戴礼记》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云:“《大戴礼记》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云:“《大戴礼记》十三卷”,皆未言其篇数,亦未见录卢注本。而唐人司马贞已言《大戴礼记》“四十七篇,见存者有三十八篇。”这是目前关于《大戴礼记》散失的最早记载。其实据今人考证,当时实亡46篇,因为《夏小正》一篇于《隋书·经籍志》已见单行,故司马贞误以为只剩三十八篇。孔颖达于《五经正义》所引《大戴礼》文,据清人考证,至少还应有《文王世子》、《禘于太庙礼》、《佋穆篇》、《别名记》、《王度记》诸篇(注:详见《左海经辩·大小戴礼记考》,前揭《礼记引得序》详引其原文,兹文繁不录。)。孔颖达(574—648年)为唐太宗时人,司马贞为唐玄宗时人,是否《大戴礼》篇文散佚于太宗到玄宗之百年?清人孔广森、孙志祖(颐谷)都根据孔颖达等人的征引认为唐人所见大戴篇目肯定多于今本。那么大戴之篇亡可能发生在唐初至玄宗之百年间。孙诒让则以为隋时传本已如今,因此推测大戴篇亡可能发生在永嘉之乱时。然同样证据不足,只是推测(注:见《大戴礼记斠补·叙》,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大戴礼记》何时由85篇散落为39篇,已成一悬案,目前之史料已无法解开此谜雾。司马贞所见38篇(实应为39篇)已成为今本《大戴礼记》的雏形。
唐初《五经正义》中没有《大戴礼记》。但从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中见引有《大戴礼》,可见当时仍有人传习《大戴礼》。但《大戴礼》始终不能挤入经的行列。后来《九经正义》成,唐末开成石经共收儒家经典12种,都没有大戴的一席之地。
宋代开始有人重视《大戴礼记》,但原有篇目一度被搞得支离破碎。傅崧卿有《夏小正经传》的离分,朱熹注释了其中9篇, 杨简(1141—1226年)注释了13篇,王应麟有《践阼篇集解》。仁宗景祐间编定的《崇文总目》载有两种版本的《大戴礼记》,一本35篇,另本33篇。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新任建安知府韩元吉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成《大戴礼记》十三卷,40篇,较为完备,始于第39,终于第81,与今本所见已基本相同,只因从《盛德》篇中析出《明堂》一篇,遂成40之数,本应39。其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九卷没有注解,其他八卷皆有卢辨的注,可见他是把卢注残本和另一种无注的本子合而为一。淳熙四年(1177年)所编《中兴书目》载入韩刻本《大戴礼记》。自韩本问世后,《大戴礼记》不再散佚。韩元吉在经学史上作了一件颇为有益的事。
宋人史绳祖的《学斋佔毕》言:“《大戴礼记》列于十四经中”。虽然清人认为其说不可考(注:《四库全书总目》引,转引自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后人亦多不信,但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说明《大戴礼记》在宋代曾有人重视过。
元代至正年间,海岱刘贞在嘉兴路学宫又刊刻了一个《大戴礼记》本,清末贵池刘氏玉海堂曾据它影刻。用刘贞本与韩元吉本对勘,可知它出于韩元吉本。元人吴澄(1249—1333年)的《三礼考注》、杨守陈的《三礼私抄》、董彝的《二戴礼解》,皆在治小戴的同时兼注大戴,取得了一定成绩。
明代湛若水(1466—1560年)著有《二礼经传测》,对大、小戴礼进行了比较研究,很见功力。明刻《大戴礼记》还有《汉魏丛书》本,《秘书九种》本,朱善纯本,但都不及嘉趣堂本。嘉趣堂本是嘉靖年间吴郡袁耿据韩元吉本刻成,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即据袁本影印。
清代印刻的《大戴礼记》有朱轼的句读本、卢文弨的《雅雨堂丛书》本、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的《聚珍版丛书》本。朱轼自称曾得宋刊善本,有何焯、阎若璩的校语,卢文弨是校刊名家,戴震是考据宗师,他们的本子自然不会差。清代校订过《大戴礼记》的还有许多人,王念孙、方婺如都有校本,汪中有《大戴礼记正误》,朱骏声有《大戴礼校正》,邹伯奇有《校正大戴礼》,孙诒让集赵翼、孙星衍、丁晏、严杰、刘宝楠诸家校订的大成,撰成《大戴礼记斠补》。
清人给《大戴礼记》作笺释者非常多,较著名的有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汪照的《大戴礼记注补》、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俞樾的《大戴礼记平议》等。其中王聘珍本堪称最善,阮元称其为孔氏诸家所不及。
晚近学者王梦鸥的《大戴礼记选注》及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小戴《礼记》的不同命运说明,在官学控制着学术命脉的时代,不能在官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其学术就难以长期传播和沿续,在历史的进程中必然受到官学的冲击,甚至被淹没,尽管其中不无有价值的内容。《大戴礼记》的内容汉唐学者屡有引及,说明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但因为它始终不在官学主流中,因此最终走向荒疏,文本内容丧失大半。清人虽然力主挽救《大戴礼记》,并作了诸多有益的学术考订,但毕竟不能再复其原貌。
(本文是在许道勋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先生在病中仍对本文的写作给予多方面的关怀,并亲自修改,在此深表谢意。
补记:在本文即将见刊时,许先生不幸逝世,谨以此文寄托笔者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