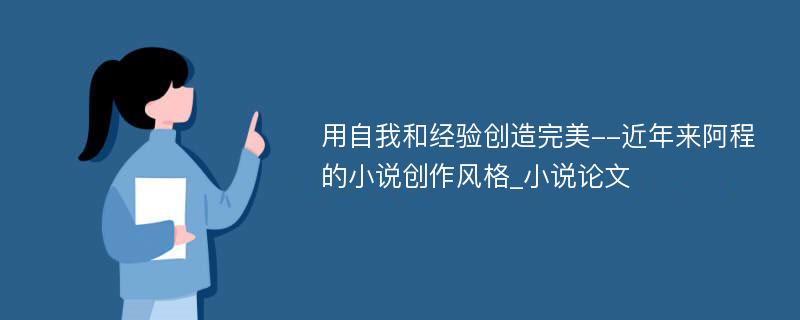
以自我和经验创造完美——阿成近年小说创作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和论文,风貌论文,近年论文,完美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颇有大气的风俗画
阿成的名扬天下似与他的风俗画小说有关。老作家汪曾祺曾如此评论他的获奖作品《年关六赋》,说:“看了阿成的小说,我才知道圈儿里,漂漂女,灰菜屯……可以这样说:自有阿成,而后世人始识哈尔滨”。[1]
偌大一个哈尔滨,自身的传动能力竟然抵不过阿成的一支笔,这个赞誉确实够高的了。不过只要细看阿成近年来的创作,你不但会赞同汪老前辈的见解,还要发展他的见解。因为阿成不只让世人知道了哈尔滨是怎么回事,还让世人知道了北大荒是怎么回事。阿成正在广阔的地域里制作着风俗画。
阿成的精神实在可贵。新时期的作家有一种浮躁之气。他们虽然愿意寻找自我,但又总爱在眼花缭乱的追求面前丢失自我。阿成不然。他虽有北大荒人的迟顿——接触新东西较慢,但又有北大荒人的优良品性——一旦认准了好道,便能坚持不懈地加以实践。《年关六赋》的成功使他坚信一个真理,所有成就巨大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把生身之地当作主要摹写对象的。肖洛霍夫写顿河,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小镇,老舍写北京,池莉、方方写武汉……[2]于是他坚持要写哈尔滨、北大荒。近年来,我们就真的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视域更加开阔的北大荒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这里有长白山余脉“白山王气、黑水霜雪”的奇观景象,也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神秘诡谲的图画。有满族人慓悍的民风,又有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友好的仪仗。在《与魂北行》中阿成让我们见识到了一百年前齐齐哈尔的城市风光:“四周的城墙是用粗笨的木栅栏合围而成的,高达数丈,尖顶,犬牙般参差,狰狞。”当年这里有一种游戏,名曰“斗残”:“赌徒相互对视,用刀,手刃自家的手指、胳膊、小腿、大腿、或割出血,或下片肉,或一刀剁下来。面不改色,亦说亦笑,怯者输。翌日即离城,远路流浪”。此间情景不但域外之人,就连现今的北大荒人也未尝听闻。读者从这些文字更感受到的不单单是野性的力量,更是一种豪勇。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阿成的风俗画小说处在一个较高的档次上。他不像那些浅尝辄止的作者那样仅仅展览耸人听闻的风情习俗,而是努力在奇异的背景中写出整个地域的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格,具有真正文化学的意义。阿成的思索空间很大。这些年他曾多次发问,北大荒人地处边缘,但为什么会几度入主中原,最后一统九州江山。回瞻肃慎子孙们的业绩,他握住了开启历史之谜的钥匙:创世者的精神、王者的气慨。为了在世人面前活现北大荒人的形象,他们的人格特征,近几年来他一直就在描写那些彪形大汉在蛮荒、凄凉、恐怖的环境中的苦斗。《与魂北行》写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大臣李金镛赴漠北开边开矿的事迹。队伍从沈阳到漠河跨越几千里,坐着狗拉的爬犁行进。前有迷天的暴风雪拦路,后有成群成群的饿狼追捕。作者启用幻象,让我们看到一队队“由三四十个骷髅组成的死神之旅,穿着黑色的长裙,戴着黑桦树皮做的尖顶帽子,在暴风雪中姗姗而来。”他们是这条道上一批又一批的前行者,当年被寒冷的死神冻僵,或坐着,或跪着,成了硬硬的石头,最后又遭到饿狼的撕咬和吞食。然而令人感佩的是无数后来者,明知死亡在即,都仍然义无返顾地指向遥远的边陲。终于在长长的国境线上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市镇,使荒凉的黑龙江走进了现代化的行列。《狗皮帽子》在类似油画的雄浑壮阔的背影上突现了一个北大荒人同暴力、死亡、屈辱的斗争。在和几十个同伴一起打死了二百多条精壮吃人的野狗后,在同伴全部倒于血泊之中,只剩下他一个人之后,他提着硬木棒向两个端着枪、逼迫他们进行这种拚杀的日军走去。他要给侵略者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这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王者形象,它定格化地、集中地展现了北大荒人傲岸不屈的伟大人格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本尼迪克特曾说过,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在自身巨大潜能弧上所作的局部选择,都适合于他们在此域的生存。[3]北大荒人所以能成为寒冷、蛮荒之国的永久居民,并创造了从边缘走上中心的奇迹,靠的就是这王者的气魄和力量。阿成能在北大荒的风俗文化的背景上写出北大荒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这表明,他是并不多见的文化小说的高手,他把风俗画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上。
温热的现实主义
阿成有点生不逢时。到了不惑之年,刚刚驰名文坛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文学的自由给文学带来了大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以他们年轻人的敏感、蓬勃的朝气、还有集团军的作战方式迅速把新写实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传统的现实主义象老海碰子手中那杆锈迹斑斑的钢枪一般被踢到陈旧的仓库里。就连池莉、方方、刘震云那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都执著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而把自己跟传统的现实主义划开了界限。阿成在这种环境里写作,简直等于把自己送进了“炼狱”。
好在阿成有成熟年龄的自信。外国那些东西他一点也不生疏。从小就生活在哈尔滨的白俄流亡者中间,还受过整整三年的基督教文化教育,阿成对它们的优越性比无论哪一个青年作家都有更深切的体验。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轻易地成为外国最新东西的俘虏。使他拒绝选择的是如下一种文化信念:中国和西方差着整整一个社会类型,我们还没有进入后现代。因而操作那些话语是“超前的”,是“伪的”。[4]他宁愿把脚跟站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跟中国老百姓说点贴心话,并通过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召唤有良知的人去作一点实际的解决。
阿成像一个纯朴的北方庄稼汉,他怎么说就怎么做。纵览他近些年的创作,其大部分作品都是贴近现实的。并且他对社会在裂变中产生的问题总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即使涉足历史及国外题材,他也要找到与现实的对话点。而他那刻画人物的精微的写实手法、塑像能力,更给他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涂上了浓重的色彩。
令人称道的还有,阿成在坚持写实时注意形成自己的特色。他不似那些以鞭挞丑恶为特点的现实主义,也不向新写实的明星看齐,他不追求任何轰动效应。阿成甚至很少把笔墨分给那些官场人物,至多送上冷蔑的一瞥。他从写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限。在他笔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那些生活的弃儿、边缘人、官场社会和科举制度的下手。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生活窘困,人格萎缩,艰难地挣扎在时世中间。别看阿成对冷漠的人生极尽挞伐,可对这些无助的小人物却十分宽厚。他总是抱着同情去写他们的悲哀,因而其现实主义就较别人多一层温热。在这些作品中《人生写意》简直精采至极。小说的主人公即《年关六赋》里的父亲。他的宽厚、善良在《年关六赋》里便有闪现,到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显影和扩大。其实父亲原不窝囊。年轻时期他也曾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新潮人物。只是经过一次“左”倾文化模式的定位和一次真爱的追求失败后,在悍妻型的家庭管制之下,他的精神才开始萎缩、人格开始崩塌。以至凄凄惶惶、胆胆怯怯,成为别人生活中的影子,连工资都不敢留一分,连父死都不敢去吊孝。父亲由精神到人格的死灭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悲凉意味,也留下了无穷的文化思索。而作者从“儿子”的叙述口吻给予父亲的理解和同情(希望生活能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挺起胸来去爱自己的真爱、去走自己终生都梦想着的路),更让我们的灵魂震颤。在无限赞叹小说的人道主义热肠之余,我们和作者一道相信,这样的小说可以“与世长存”。[5]
这里需要格外加以注视的是,阿成十分注意在小人物的穷蹇命运中表现他们的美好感情,因而总能使读者和他一起去爱他们。阿成笔下的小人物外表呈示着鄙陋的形态,内里却满怀着豪侠、义气、宽厚的品格。至此,《忸怩》的描写也许是最出色的。这部长篇小说深刻地批判了商品化对城市人人性的掠夺和扭曲,生动地展示了两个正直善良的小人物的生存窘迫和尴尬。老叶和小老爷子信奉人们千百年来所希冀的被人当人的生活方式和自由自在的人格理想,结果与以掠夺人的尊严为特征的商品社会发生了尖锐冲突,并被抛到生活之外,成为“盲流群落”的成员。可贵的是他们一方面愤世疾俗、守住自我,另一方面又能从宽广的胸怀对待与自己有过恩恩怨怨的妻子、情人及所谓不干不净的朋友们。在老叶的眼里他们都是商业化社会的奴隶,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向媚俗。可是他们在灵魂深处,仍然给正直、诚实、纯洁、真挚等等美好人性留有一息生存之地。因而他才能给他们的选择以理解,并在那一席之地上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往来。在他看来,人不是上帝,他们不可能完美,只要不是势力小人、流氓大亨,都可以在某一点上成为朋友。即使对老岳,老叶也因其人性未灭的部分而对他探监、给他收尸、帮他完成未竟的宿愿。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他与小老爷子的友情。作为同样的“天涯沦落人”,他们相互理解、帮助、不分你我,达到了至纯至诚的地步。当看到天真的小老爷子为追求理想中的爱,准备把自己流放到异国他乡,在川资不足的情况下,还把房子、煤气罐留给朋友的时候,我们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把对人类伟大感情的爱毫不吝啬地送给他们。总之《忸怩》对小人物悲剧命运及他们美好感情、美好追求的描写,即使它对现实畸形现象的批判具有哲学、文化的深度,又使它对理想的指认超过了《大厂》一类作品的高度。据此,它有资格成为近年来少有的优秀长篇,有资格成为别一种现实主义。它的成功向我们显示:现实主义并没死亡,有才能的作家照旧可以在借用它时发展它,造就出品貌多端、惊世骇俗的作品。
古典的浪漫情怀
当我用现实主义来界定阿成的创作时,我知道自己陷入一种危险。因为这等于让我难以从其他方面来谈阿成小说的审美品性。阿成是个路数十分宽广的作家,包括他自己也作过类似的表述:“我并不是一个时令性、集团性、派别性、主义式、或者容易受人左右,以至什么‘族’式的作家”[6]好在大家都能理解,一定的概念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任何一种创作精神都不是绝对封闭的,都可能与其他精神交接、相融,因而我们还有机会在“古典浪漫主义”的题目下谈论阿成。
阿成作品的浪漫主义情调有目共睹。汪曾祺给他小说作序的时候就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近年来他的作品或魔幻手法,或诗情氛围,或整体充盈浪漫精神的,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原有基点上评判他的创作。
阿成的浪漫主义主要表观为热衷于理想的传达。和那些解构理想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阿成更喜欢从生存的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用他的话说,即“我们都得面对生活”。[7]阿成认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被目标高远的精神先驱们忽视了,这就是十多亿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活着。他们不但需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自己的生存,也需要有一种精神来谐调自己和“他者”的关系,限制那些强硬的“他者”给自己制造地狱。而阿成的理想又浸润着浓厚的古典人文主义色彩。这古典特别为思想意识很先锋的人所鄙视。然而阿成不以为意。在他的心目中好与坏、高与低不在于是否前卫、时髦,而在于是否合用。后现代话语很新鲜,但它们只能使少数知识先知扬名;对于平民百姓却是毫无一丝用处。阿成的感觉也许最具有平民意识、最合当代文化需要的。作为一个底层人出身,阿成曾长期地遭受过权势者的欺凌,因而深知他们对平等、自由、理解、宽容的渴望。今天时间之轮虽然已把中国推向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它的精神文化仍被抑制在封建色彩很浓的机制里,古典人文主义精神仍然是必须加以实践而不能弃置的东西。先锋们以为旧,可对于未曾充分领受过它们的中国底层人来说,却是很新。而且,在阿成看来,凡是经受过人类生活检验的精神、道德理想,都有永恒的价值。难以想象,消解了平等、自由、宽容之后,人生会是什么。因此他宁愿做一个先锋眼里背时的作家,也要守望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给他的追求留下了深深的辙印。这部作品写了哈尔滨的一角——欧洲流亡者的生活。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独特的个性、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还有相互间的理解、尊重及宽容。那个英国绅士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优雅地依着门框,总是露着温和的微笑,与世无争同时对一切人事都表示出谦和的态度。他的形象好象一个一个文化代码,散发着古典人文主义精神,使我们不由得产生出浪漫的遐想和深情的向往。
阿成的浪漫主义情怀还表现在他对现实俗化灵魂的古典式拯救上。近些年商品化所诱发的精神和道德的堕落引起了许多有良心的艺术家的忧虑。许多北方作家反映得更为强烈。在无法给现实以整治时,他们几乎一致地吁请人们关注自己的终极追求,并从已有的人类经验中提取美好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理想来添补人们灵魂的空洞。更不论他们的呼唤有无实际效果,其抑制恶的愿望真真切切地表现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伟大而悲壮的情怀。今年发表的《蟒珠河》具体地展示了阿成近期的创作倾向。小说描写了一个鄂伦春萨满的形象。这个萨满以大自然为居所,并从接受它的陶冶和洗礼中使自己的灵魂超越了物欲而获得了神性。他能从一些微小的征兆中预知灾变,进而为人类造福。最动人的是他那份无私无欲的爱。他可以把心、把珍爱的一切,乃至对神的崇拜给与她,使她像神那般完美。但是他永远只在山上注视她,而绝不与她作人间的接触,绝不给她和她的丈夫、她们的家庭带来任何痛苦。他的爱是人间的,同时也是神间的。作家对他的描写显然是启示人们要以自然的真性,要以神性实现对世俗的超越。从这里我们能看到阿成的崇高的精神追求。
短篇小说《马兹阔夫生平》和《远东笔记》也是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一个表现了失去依托的灵魂对“家园”的寻找,一个表了渴慕美、渴慕爱的灵魂对失去了的旧梦的寻找。令人感动的不仅是两个灵魂寻找家园、寻找美丽的旧梦的执着,还有作品里忧郁、失望的情调。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浓稠的哀伤。由此我们也感受到了阿成追求理想的热烈的深沉。
理想的缺席使人们珍爱理想。而阿成的理想又是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诱人的魅力,因此每每进入他作品的阅读,我们的灵魂都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满足,都产生了极度向美向善的渴望。沉浸在阿成的艺术世界,我们就觉得象是真正地回到了精神的家园。它比一切伪装的高贵、伪装的虚无、伪装的潇洒都高尚。阿成的守望是他的幸运,它使他成为现世不多的好作家之一。
愈加圆熟的艺术
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反小说的制作者不一样,阿成特别忠于小说的艺术。他对小说,对艺术的虔诚信仰只有用宗教精神才能加以说明。杜甫曾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限来要求自己的诗歌创作,阿成之于小说也有点类似的追求。在后现代的眼光看来,小说是一种貌似堂皇的虚假的叙述,属于明日黄花,但阿成却非要让他的小说传世不可。[8]
阿成对小说艺术的追求颇为执著,亦颇为艰苦。在初霞文坛时他十分讲究小说的精致和圆整,人们看后觉得它们简直像雕刻出来的似的。其故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其文字简洁凝练,绝无废话。以至,人们在高度赞赏他语言的功力时还生出一种担心:如此精雕细刻会不会限制他的手脚,会不会使他走向促狭。
阿成有着良好的艺术感受。人们都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阿成以为语言更是小说艺术的家,语言如果缺乏包容量,那么由它构成的小说世界绝不会让回家的读者感到宽敞、厚实而明亮。因而叙述语言的凝练是他有意对自我训练的方式。当感受到能够驾轻就熟地操作语言时,阿成才放宽了自己的写作,进行一种大度从容的叙述。这时我们在阿成的小说里开始看到了一种更新的美学品貌:雕琢的皱褶被熨平了,一切都变得十分妥贴而自然。而在晓畅流利中他的语言又让人体味到别一样的深沉。还有随着过于紧凑的句式被化开,叙述者的主观性体认得到了释放,这样我们又领略到了一种潇洒活泼的情调与氛围。例如下面的叙述语言就能表现出阿成的新的风格:
长长的、细细的松花江,在飞机的舷窗下,在崇山峻岭之间,甩得很柔,以至有点天真和梦幻色彩。
——《远东笔记》
我不懂现代诗。现代诗比较难啃,完全不像煮烂了的五香猪爪,薰鹅,……啃现代诗如啃干枯的树根,是要显示出无比的耐力与悲怆的神态与姿态才行。
——《欧阳江水绿》
我是从那以后,深深感到人生下来,和人的生命历程,是有极大的偶然性的。这一认识让我终生刻骨铭心。
——《蟒珠河》
读过以“沙沙”、“血血”来描写江流,夕照一类句子的人是不会在此找到原有的阿成的。然而人们仍然可以从“用得很柔”、“啃”之类的用语中感受到阿成的语言功夫。最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些新的语式、语调看到叙述的更高境界:从容、自然、深沉、活泼。而且进一步挖掘,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秘密,即尽管阿成从整体的艺术精神上反对先锋的后现代实验,但这并不排斥他在叙述的方式上对先锋的成功经验的借取。正是这适当的借取使他浓厚了小说的新质:从负重的匠心走上潇洒自如的状态。
阿成在小说艺术追求上给我另一个较深的印象是,他注重文本的多重韵味、多重美学效果。如透视观念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复调性等等。就中尤其是他的喜剧性、幽默感十分令人叹服。阿成的幽默令人想到王蒙,也想到王朔。但阿成又不似王蒙,更不似王朔。他有王蒙原有之长:庄重,又力避他们之短:不装、不做作,更近于自然,因而也更机智。
说庄重是因为阿成从来不消解“意义”、不消解对存在的终极追求。他一是把小说当作与人们的对话方式,并通过这种对话来寻找共同的人生支撑点,寻找“灵魂的进步”。[9]像前面论述的《马尸的冬雨》、《忸怩》、《蟒珠河》都可以让我们看到阿成对人生重大价值,对生存理想的可贵追求。阿成的幽默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并从没对整体的庄重有任何干扰。要在他的作品里寻找嬉皮士作风恐怕是徒劳的。
说自然是指阿成从不有意插科打诨、故意制造噱头。人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往往没有任何接受喜剧的准备,没有在肥皂剧中的那种情况:于微笑中等待逗乐。阿成的幽默突如其来而又符合常理。事情常常是这样:我们正聚精会神地倾听一种叙述,可是,突然,我们迎来的都是另外一种结果,就象康德说的,我们紧张的期待落了空。《年关六赋》里的两篇笑料“操你个妈的”,“干日本娘们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个由关爱到恨,一个由羞辱到保护,都是这种情况。
《忸怩》把阿成的幽默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里的幽默各种各样,有轻嘲式的,自嘲式的,揶揄式的,恶作剧式的,反差不和谐式的,滑稽乖讹式的……。对此,我们可以作一篇专题论文。但是不管哪种情况,都有上述的特点,都很自然。比如老叶,小老爷子,李铭几个人的儿童节聚会。小老爷子说到自己童年时总是受辱,有一回他突然变成了英雄,抓起石头去打人。读者痛快地等待他胜利的结局。可随后他说:“我抓起来的不是石头,是落满灰尘的屎橛子。”听了他的话,人们能为这个窝囊的英雄乐断了气。而且在笑声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了他们作为弃儿的童年的悲哀,正像别林斯基所说的,这是那种含泪的喜剧。
我曾追问阿成幽默自然的原因。思索中我一方面感到阿成本身的幽默感很强,另一方面也觉得他的幽默直接来源于生活。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开放性人格特征,弥漫于社会。这种开放性人格特征造就了难以数计的幽默家及喜剧性格,也造成了广布于社会的喜剧气氛。阿成一直沉在生活的深处,他有更多的机会感受生活的喜剧美,他的艺术知觉也有更多的可能去储存大量的喜剧原型。因而当他创作时,它们也会源源不断地走入作者的笔端,用不着他绞尽脑汁地编造、设计。
阿成的幽默反映着阿成重视写实的精神,同时也反映着广阔的艺术视野。他尊重所有成功的艺术经验,从不片面地排斥或张扬哪一种。阿成特点是善于综合,善于融化。就此而言,我们相信他会有更大的成就。
注释:
[1]见《年关六赋·序》第一页,作家出版社。
[2]转自李福亮:《一个自由的精灵在歌唱》第12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见《文化模式》第197页,华夏出版社。
[4]见《小说家》1996年2期第75页。
[5]见《欧阳江水绿·原记》第411-413页,中国文学出版社。
[6]见《欧阳江水绿·原记》第411-413页,中国文学出版社。
[7]见《小说家》1996年2期第72页。
[8]见《欧阳江水绿·原记》第411-413页,中国文学出版社。
[9]见《欧阳江水绿·原记》第411-413页,中国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