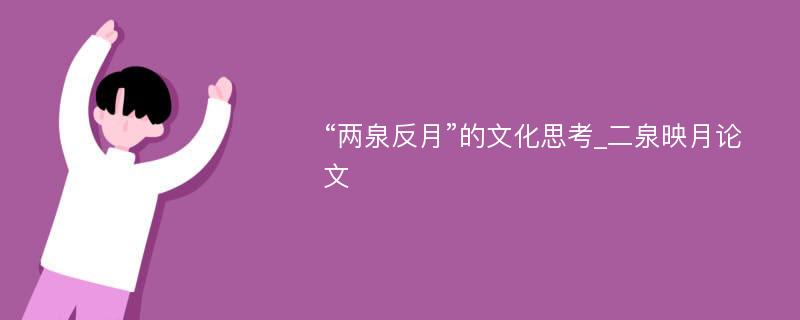
《二泉映月》的文化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映月论文,二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隶属】 民族器乐/作品分析
当那位饱经了人世间苦难与沧桑的民间盲艺术家阿炳(华彦钧)坐在钢丝录音机旁留下了他那首随心而发的二胡曲时,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了千古绝唱并使他那行将终结的生命在录音带的转动中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永生;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随感而发的慨叹竟与其故乡无锡的名胜“天下第二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进而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历史景深。
中国音乐界在对《二泉映月》(以下简称《二泉》)的研究方面可谓成果颇丰,无论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通俗的欣赏介绍方面均不乏典范之作。这使人们的眼前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二泉景观”。笔者不揣冒昧,也想对《二泉》这一作品发表一己之浅见微识。本文将从作品的定名、艺术特色和从不同的美学角度对作品诠释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作品的定名:《二泉映月》与二泉
《二泉映月》与二泉的联姻是由杨荫浏、曹安和两先生促就的。这首本被创作者阿炳称之谓“随心曲”的作品最终定名为《二泉映月》加入了杨、曹两先生音乐学方面的艺术探究。自此,由以泉得名,泉因曲著称,二者相得益彰。
1.“二泉”与二泉
“二泉”与二泉究竟有无联系?笔者认为有是不容置疑的。其联系在于作品深层文化内涵。分析如下: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以山水景观为描述对象的我们称之为“山水文化”的现象,这是各地域自有胜处的山水景观在艺术家心中激发了创作灵感而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地域的不同、气候的差异等诸多自然因素又造成了各地域间在人的整体架构、思想意识、气质性格乃至文化状态方面的各具特色。反映这种地域性人格特点的文化我们称之为“人格文化”。这种“物”的文化(山水文化)思维与“人”的文化(人格文化)思维是构成中国文化思维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山水文化”是人对物的心理感受,它的反映对象是各具地域特色的山水景观;而“人格文化”则反映了受地域等诸自然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具有地域性特点的人格架构,是物对人作用的产物。中国江南一带山水景观的总体特征是秀美,而北方山水景观的总体特色是壮观,这种地域性特色正是“山水文化”艺术表现的出发点;而自古江南多才子佳人,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则是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等诸多自然因素下所导致的不同的整体人格架构,因而在“人格文化”的艺术反映中江南与北方分别以清秀、柔韧和豪迈、悲怆为各自的总体特色。
无锡是一个风景秀丽如画的江南城镇,江南的山水和气候决定了阿炳的艺术人格特色,而江南传统文化又溶入了阿炳艺术创造的血脉之中。二泉是无锡的名胜,由于山水文化的作用使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无锡(甚至可看作是江南)的一种象征,这就如同由于张继那首千古绝唱《风桥夜泊》而使人提到“寒山寺”就联想到姑苏一样。无锡是阿炳的故乡,把其最出色的“天鹅之鸣”定名为“二泉”显然与上述的地域性山水文化有关。定名之后,曲与泉交相辉映。笔者认为这应该说又是一个中国的山水文化与音乐文化两个历史景深成功融汇的范例。
2.“映月”与二泉
显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二泉并不映月这是人所周知的客观实际,因为月光不能绕过泉上的亭子而映入水中,对曲名的争议与思考大都源自于此。笔者按上述的文化学观点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映月”同样是作品的一种文化内涵且加入了恰如其分的艺术修饰。
既然“二泉”只是作品的深层文化底蕴,那么“映月”的产生也必须从与之相应的文化思维角度去分析。杨曹二先生的定名是对《二泉》的艺术升华这一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其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它首先是确定了该曲的地域性音乐文化特点,其次是标明了这一作品在“二泉文化”价值体系上的坐标:在以二泉为描述对象的艺术作品中,该曲不正象那轮在繁星之中的明亮的皓月吗?同时,那于柔美中饱含着内在的韧性和那种蕴藏于音乐发展中的淡淡的情绪与那将清冷的光辉默默地洒向人间的月亮又有何二致呢?于清秀、圣洁之中透出无上的韧性,这也正是江南人格架构的一种体现,自然与江南的人格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笔者判定,《二泉》一曲的定名有其文化学的意境且符合其自身内在的逻辑。
二、《二泉映月》的艺术特色
同时进行了一、二度创作的民间盲艺术家称自己的作品为“随心之曲”,这已经体现出了这一作品在情感方面的艺术特色:它发乎作者内心,是其真情的自然流露。从他所留下的音响中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个饱经人生风雨的老人已经心如止水了。他以淡淡的口吻轻轻地叙说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没有喜怒哀乐的过份渲染,就如同在讲述着一个来自遥远的阿拉伯世界的神话传说《天方夜谭》那样描绘着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坎坷与沧桑。
现在有许多的二度创作者在诠释一度创作时有明显的“超越”现象,因为过分的悲切和激昂既不能表达作曲家本人的意图(依据阿炳留下的音响,后文将进一步论证),又在体现作品内在的已经升华了的作者的人格特色方面造成了可供商榷的空间。因此在艺术表现中所展示的显然成了演奏家本人。对此,笔者不想妄加评判,因为艺术家对作品的诠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并且对作品的艺术处理又均建立在各自理论体系的分析研究之上。但有一点相信是确定无疑的。不同的解释将导致对作品研究的进一步加深,进而作出更为合理的诠释。
在对《二泉》的曲式曲体所进行的研究中,许多音乐学家提出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点,但几乎均以西方的音乐理论体系作为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石,诚然,西方的音乐理论体系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并且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品在深层上最相通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但《二泉》毕竟是一首与古老神秘的东方传统文化渊源甚深的民间乐曲。阿炳每次的演奏大都并不完全相同。因其既曰“随心”则必“有变”,而作品的“变”显然源自中国民间音乐的“即兴性”这一典型特点。
无庸讳言,《二泉》是通过变奏的形式发展成形的(有的专家称其为通过迭奏形式发展的,如杨儒怀的《作品的分析与创作》中所论述的那样),它的每一次变奏均有情绪的自然推进。这既符合人的情感特点又与音乐进行的内在逻辑合轨。从理论上讲,这种变奏风格显然不同于西方理论中所阐释的那种变奏,它没有主题或织体方面大的变形,而只是以一种“加花”(在作品中是通过对部分乐句的变形方式体现的)的手法来完成音乐的“变”和发展。这种永葆主题特色的艺术手法显然也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有关。
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变奏尽管也在体现着人生多变的生命原则,但同时也表明了始终基本如一的生命主线。符合中国的“大团圆”这种美学思维,作品的最终又回复了初始的那种宁静,从而也符合了“起承转合”这一封闭型的中国艺术结构形式。主题的本色保持和最终情绪的复原在深层上也是容入了中国传统美学思维“万变不离其宗”和“万变归宗”的结果,是这种思维的内在体现。
三、从创作美学与接受美学角度看《二泉》
艺术家因文化、传统诸因素的作用而能把自己脑海中的艺术灵感转化为艺术现实,并溶自己的美学思维于其中,完成作品的创作。在欣赏者角度去体会、感悟乃至评价该作品的艺术特色,在欣赏中实现艺术的共鸣,伴着自己的美学思维,创作美学与接受美学的对接完成了作品的艺术使命。
《二泉》是作者在长期的演奏过程中创作完成的,他把自己的艺术灵感放在自己的演奏中不断润色加工使之臻于完善,不仅取之于自身,也取之于欣赏方面的反映。笔者把其创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下文将分别从三个阶段中创作者与欣赏者不同的美学角度进行分析。
1.初创期
作曲家在自己的艺术生活中由于传统的音乐文化和自身的音乐素质的作用而产生了一个艺术灵感。这时作者的情绪是激动的,既充满了对在演奏中形成的艺术灵感又在演奏中得以顺利地诞生而发自内心的欢欣,又有对把自己潦倒半生的经历溶入了自己的艺术而一时为快的心理感受,并在作品中对未来寄予了向往。
由于作曲家本人即是演奏家,可以说作品的构思源于平日演奏时艺术灵感的积累。在对作品的总体的艺术处理上采用的手法是:将细腻的情感发展体现于柔美而激昂的旋律进行中,对每个音符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表现,作品的江南特色与艺术家的个性特色均得到了异常鲜明的体现。
从欣赏的角度去体会,这种风格应该说是较近于常人的情感特点的,因作品中更多的是作者对生活坎坷的直接诉说,有着青年人那种艺术和人性方面的冲动。他那激烈跳动的脉搏在越来越激奋的情绪发展中达到了高潮。之后,作者总结了全曲,用引子反行的旋律和与引子相同的情绪苦笑着结束了自己的讲述。
2.定型期
阿炳创作的艺术特色从初始就显示了江南的道观音乐与民间传统音乐水乳交融的风格。随着对作品产生时那种激动喜悦心情的逐渐平复,作者开始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冷静的思考。他舍弃了一些与思想表达和音乐表现无关的纯表现性乐句,从总体意图上把握全曲。此时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是情绪的起伏已不似初创期的激昂,而加入了一种执着与凝重的成分。他已不再仅仅体现自己的哀怨与悲愤,而注入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在作品已基本定型后,原来对每个音的刻意修饰已转化为对整个乐句的细致把握,无论是语气还是句逗等方面均仔细推敲,个人的艺术特色溶于地域性特色中来体现。
在欣赏方面,通过联想的渠道使这样一幅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对生活已有了较深感悟的中年思想者在低头沉思。他用具有明显家乡风味的柔美语调讲述着他的个人见解。他的情绪随着讲述的发展而激昂起来。但即使在最激动的高潮时也被那种已经成熟的理性力量牢牢地控制在预定的范围内:波涛尽管澎湃汹涌,但没有一滴涌出防护的大堤。最终的回复笼罩在一种无奈的氛围之中,并以这种情绪结束了全曲,与引子遥相呼应。
3.成熟期
我们曾把前两个时期分别看作了以激情为表现特征的青年期和以沉重为主的中年期,那么这一时期自然应看作是以宁静、淡泊、圣洁为表现特征的老年期了。
这就是我们从他本人留下的音响中所听到的。由于他同时进行一、二度创作,所以作品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中,直至最终的定型。这对作品是非常有益的。这一时期他的身体已经衰弱多病,二胡也是断断续续地偶儿操弄,心情上已经完全冷静下来而不再是血气方刚,剩下的似乎只是心平气和心态的老艺人在总结性地回顾自己的艺术创造。他从总体艺术构思上审视了自己的作品,使《二泉》中的个人特色完全融之于作品所体现的地域性特色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切均转化为音乐本体,在其中老人和他的艺术都升华了。
他摒弃了那些浮在音乐本体表面上的情感性因素,达到了与“自然”的和谐与完美统一。他的心与音乐结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形式成了内容,内容自然也就成了形式。这里,在时空中展示的只是那充满了理智与圣洁之感的旋律线条与其化成的音响。
这时以欣赏者的角度去体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似乎已经习惯了一切,仿佛对人生的一切均已不能感悟并获得超脱。他心中的那份圣洁已逐渐升入空中并光芒四射,这种蕴含于作品之中的圣洁性可能与他早年的道观生活有关,中国道文化的“出世”已融入老艺人的灵魂之中。这也似乎与那位遥在天边的日耳曼大师贝多芬不无相似,这位乐圣在与命运搏斗的一生之中,最后同样以圣洁的口吻唱着《欢乐颂》与《庄严弥撒》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的分析虽然是建立在理论的逻辑推理之上,但笔者认为本论点的实证即在于那些二度创作的不同风格体现上。这是对上文所论的又一个落点,因笔者正是在不同的艺术表白中看到了阿炳在其创作中的不同阶段和在其生命、艺术上的不同侧面。
四、结语
中国的音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老的东方文化之神韵。《二泉》作为中国音乐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必然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因素,本文基于此而有所立意,但能论证出多少这恐怕就很难说了。
中西文化各有千秋,音乐也各有其历史的辉煌和内在的妙处。但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相对落后于西方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即至今日我们的音乐理论体系也大都均为对西方的承续为主,因此笔者撰此文的另一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期早日建立中国的音乐理论体系,以便用中国的音乐理论去分析研究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音乐作品,以使之构成真正的“现代中国音乐文化景观”,我想这也正是每一位音乐工作者所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