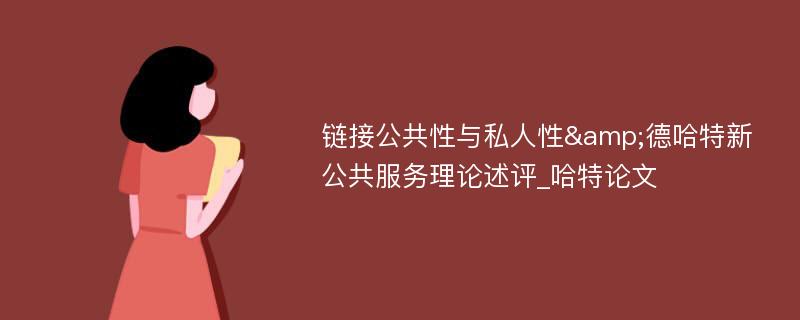
链接公共性和私人性:登哈特新公共服务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服务论文,哈特论文,私人论文,理论论文,链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珍妮特·登哈特(Janet V.Denhardt)和罗伯特·登哈特(Robert B.Denhardt)无疑是少有的活跃在社会科学界的贤伉俪。①体现他们学术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的《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更是他们的代表作,受到世界各国公共行政学界同仁的关注和盛赞。在这部合著的代表作中,他们主要探讨了一个核心主题,即批判和继承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构建一个符合现代民主价值观,并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的公共治理体系和公共行政实践框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表达则是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并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但就像韦伯式的“理想类型”,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倡导的共享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也是在现实经验世界中难以触及的“极点”。
一、新公共服务:一个对威权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反思
从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到韦伯的“理想官僚制”,政府都是作为对社会失序的规范、重整和强制性约束而存在。但自从国家建立以来,以行政官僚强制性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却不断侵入私人领域,出现了国家悖论,即原本为实现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之目标而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却不断做出侵权和越权的反文明行为。有基于此,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股反思国家权力的思潮;而登哈特夫妇所倡导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正是这股反思思潮的重要代表之一。超越现有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局限,构建和重构一个更适合指导现代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框架一直是登哈特夫妇所追求的目标,就像罗伯特·登哈特在他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公共组织理论》中所陈述的那样,“持续的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共行政(组织)理论的过程,将是在你职业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最精细的工作”(Robert B.Denhardt,2011:202)。
(一)一个可选择的替代范式
如果从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算起,公共行政学已经经历了近130年的发展历程。在近130年里,公共行政学思想已经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按照公共行政学界流行的观点来看,以前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而以“统治”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行政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社会的发展趋势;适应市场社会的发展,必须借鉴市场经济中的管理主义方法改造政府、再造政府。然而,公共行政组织毕竟在目标、价值定位等诸多方面都有完全不同于企业组织的特性,管理主义方法在政府部门中并非万能良药。作为对管理主义和传统公共行政的反思,登哈特夫妇试图构建一个超越管理主义的新治理框架——新公共服务理论。
在登哈特夫妇看来,新公共服务就是“关于公共行政将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2010)。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democratic citizenship)、社区(community)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及组织化人性主义(organizational humanism)和沟通理论(discourse theory)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和强调人的价值,而不是像公共管理范式那样把公民看做顾客和一味强调生产率和效率;它强调公共行政人员是仆人而不是主人,认为政府要通过榜样、说服、鼓励或授权来实施共同领导。这种强调权力共享和政府与民众的双向平等互动的思想与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所强调的平行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是一脉相承的,即主权在民,公共行政官僚的“野心”必须用公民的“野心”来对抗。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把公民置于公共治理的中心位置,也是对地方知识和地方实践智慧的尊重,契合了Hayek所强调的环境适应性(adaptation to changes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即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由熟悉环境,并知晓相关变化和可用资源的个人来掌握,因为把所有信息集中到一个中央权威中心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Hayek,1945)。
在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登哈特夫妇(2010)认为新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或新公共管理的、可供选择的替代范式。这三者之间在理论和认识论基础、人类行为模式、公务员回应的对象、政府官员及公务员行为动机、公共利益概念、政府角色、负责任的方式、行政自由裁量权、采取的组织结构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实际上这三类范式之间,特别是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之间更应该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的理论建构重心是不一样的;以威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强调政治与行政职能划分,倡导威权主义政治和官僚制权威;以管理主义为核心的公共管理范式强调的是政府内部的市场化和民营化;而以服务主义为核心的新公共服务则主要聚焦于公共行政人员与公民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双向互动。
当然,服务主义并非一个流行的谚语和词汇,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解释。笔者使用“服务主义”这个词用来意指作为有目的的治理主体的政府与作为自主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政府要把自身定位于服务者,来认识其与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尊重公民在社会领域,以及企业在市场领域的自主治理主体作用,而非传统威权主义政治和官僚制权威所强调的“统治”,或管理主义所强调的“管理”。换而言之,服务主义是与威权主义、管理主义相对应的概念,用以概括新公共服务范式所提出的公共行政思想理念。
(二)一个对民主价值的回归
新公共服务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公共行政价值选择层面。登哈特夫妇不落窠臼、超越了3Es(经济、效率、效益)价值选择范畴,在总结和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价值定位的基础之上,他们将政治民主价值重新注入公共行政学研究,这为未来的公共行政学研究重新指明了方向。他们将新公共服务理论概括为七个方面,即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思考要更具战略性,行动要更具民主性;强调公共责任;强调服务而不是掌控。新公共服务的这些核心理念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重新拉回民主国家的价值定位,也是对最近20年盛行的管理主义思想的一次全面反思。政府应该像一个民主政体那样运作,而不能像企业一样运作;因为作为特殊的公共组织,政府本身就是为了公共性的目的建立的,它的长久合法性身份有赖于其公共性;离开公共性,政府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合法身份。在柏拉图、洛克、孟德斯鸠、霍布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家的视野中,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政治的权利都是源自于“被统治者”——人民的授权;而在现代思想中,政治家和政府的权利都是一种代理的权利,是人民把权利委托于政治家,而政治家则把权利委托于政府公务员,所以,如果脱离了为公民服务,离开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抛弃了对广大公民的最终责任,政府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其身份危机、信心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也就不足为怪。
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视角下的公共利益应该是符合直接民主趋势的,是公共行政官员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之间和公务员之间就共同价值观进行对话的结果,这完全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视角下适用于代议制民主的公共利益观,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个人主义利益观;同时,行政官员和公务员的行为动机并非私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是为社会作贡献的欲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性。基于此,政府的价值定位应该在于民主,而且是与民共享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直接民主。
二、新公共服务:一个理想类型
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的是基于完全民主的“共享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和“共同领导”,但就像是韦伯的理想化官僚制,它只是一类理想类型(ideal type)②,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很难在现实经验世界中存在。事实上,在极力倡导新公共服务理论价值的同时,登哈特夫妇(2010)本身亦对公共行政人员和公民的价值和角色定位存在疑虑。
按照新公共服务的观点,政府对于创立公民能够通过明确表达公共价值观并产生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的舞台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公共行政官员不仅会通过达成一种妥协来回应完全不同的声音,他们还会使公民相互接触以便他们可以逐渐认识到彼此的利益并且从根本上形成更加长远且更加广泛的社区意识和社会利益意识……最为关键的是,公民是否相信政府会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这个问题。
如果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公民都不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和基于共同价值观而采取行动,公民就不可能与政府建立良性的互动;同时,公共行政人员自身的公共价值观假设本身也就值得怀疑。
(一)一个基于奥尔森思想的正向批判
在包括登哈特夫妇在内的公共行政研究者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或暗含的假定,即有共同利益或者有共享的价值观念的个人组成的集团总会为他们共同的利益或价值偏好而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绝大部分社会情境下是不存在的,“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1995);这与社会心理学实验结果也是相互契合的,美国学者谢里夫(Muzafer Sherif,1988)的巢穴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也证明了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和挑战,即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时,群体成员之间才有相互协作、追求共同目标的可能性。而在登哈特夫妇看来,“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即“经济人”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人的行为不仅是自利的问题,还涉及价值、信念和对他人的关心。他们认为公共行政官僚不是主人,他们只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和社区参与的催化剂,是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的,负有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和倾听公民声音并对其话语做出回应的责任;而公民则被视为政府的主人,公民之间具备共享的价值观,相互关心,是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但是,这种利他主义倾向却完全得不到证实,即使是捐赠行为也不能代表利他,捐赠者或者出于获得其他利益,如“沽名钓誉”,或者只是偶尔的“善心”,或者是税收制度约束的产物;同时这种偶尔的“善心”并不能否定“经济人”的根本特点,因为“经济人”本身就是对人性基本特征的概括,而不排除个别的、偶然的“利他式”行为。此外,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公共价值、增进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靠自愿的筹资或捐赠来供养自己”(奥尔森,1995),在人类的历史上,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用于公共目的的公共财政资源最终还是要靠强制性的税收制度来予以获得。
所以,学术界不能、也不应该因为个体偶然的怜悯或同情弱者,对有着不幸遭遇者的偶发善心行为,而不适当地推广到代表性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甚至用利他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做出概括,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网友对个别天生残疾的弃婴③表现得很关心,但与此同时,网友们对大量因车祸、后天疾病、伤害等原因致残的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却不那么关注。综合来看,一方面类似于捐赠这样的善心往往只是“个别现象”和“偶发行为”,不具备普遍性;另一方面这种关心往往也是“三分钟的热度”,很快就消退了,所以称之为“利他主义行为”是不恰当的。从严格定义上讲,利他主义行为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时间的持续性,即关爱他人,特别是救助弱者之心长期存在;第二,平等性,即对所有值得予以帮助和同情的个体的同等对待;第三,爱心的真实性,即关爱是出于个人内心真实的意愿表达,并非是法律强制或社会舆论压力所致;第四,普遍性,即利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须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综合这四个条件,几乎所有的慈善或善心行为都不满足。所以,滥用利他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乱象,是不负责任的研究。
同时,奥尔森(1995)还在他的研究中区分了相容的(inclusive)集团和排外的(exclusive)集团。相容的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此时,集团成员是可能共同努力去追求共同利益的,因为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是正向相关的;而排外的集团成员之间的利益则是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每一个集团成员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公民个体,也包括公共行政人员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同时,公民之间、公共行政人员与公民之间必然存在竞争,有竞争必然就有冲突,这也是由“不可治理性”所决定的。这种冲突的不可治理性就否定了共享的价值和共同利益的普遍存在。此外,奥尔森还区分了大集团和小集团,并综合了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和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的观点,认为人数较少的小集团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更大份额,行动的动机和有效性更强。但事实上,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的关键也还在于小集团的协商成本更低,存在直接民主协商的可能性;而大集团基于协商成本的高昂和成本收益份额的分散,协商一致的可能性很小。综上所述,考虑到此种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新公共服务理论基础的公共利益和共享价值是站不住脚的。
(二)一个反向推理逻辑
当然,很多人都会反对我们的观点,因为他们也能提出同样多的论点来反驳我们的论证和推理。为了深化我们的论证逻辑,我们还有必要运用反向推理来深化我们论点的逻辑和理性。事实上,试图从正向逻辑去论证事物价值的正确与否,会永远没有达成一致或是论出输赢成败;但从反向思考伦理价值问题也许可以为价值优劣判断提供可行逻辑。
从反向逻辑来看,至少有三条路径来反驳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共同价值基础。首先,我们假设公共行政人员都是愿意主动承担公共责任和追求公共利益的,而公民是基于共享价值和公共利益而行动的;那么基于利益纠纷和价值信仰相悖的冲突根本就不会存在,以强制性权力为核心的政府和国家也就没有必要存在,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协商来取得共识,分享共有的价值观和达成一致的共同利益。其次,如果新公共服务所设想的民主、平行多中心治理格局能够存在,那么“无政府主义”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个人和社区将成为权力的中心,那么在难以计数的众多权力中心之间,如何才能避免利益竞争和价值冲突所带来的社会失序?如果不能正面地提出一个实践可行的解决方案,新公共服务的理想价值就不可能实现。最后,从组织平衡的视角来看,组织的平衡必须在组织对成员的满足和成员对组织的贡献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如果整体性的共享价值和共同利益普遍存在,组织也就不需要在贡献和诱因之间寻求平衡,乃至于组织都不需要存在了,因为谋求内部平衡的组织必然会损害组织外部的利益。
在理解理想的公共治理机制方面,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的两极论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他们在对理想政府的本性(the nature of desirable government)方面持相反的观点,霍布斯认为人性是残忍的和相互充满敌意的(cruel and disrespectful to one another),充满控制他人的欲望;而洛克则主张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不受他人和政府的侵犯。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二者也构建了不同的社会秩序,前者认为社会是从无政府到秩序的演进,而后者则认为社会是经由个人自由到压迫的演进过程。但事实上,无论是霍布斯式的政府(Hobbes's leviathan)还是洛克式的政府(Locke's government)都需要某种类似于宪法秩序的防护。然而洛克式的个人自由需要一个前提,即人们本质上自愿并主动避免“囚徒困境”(people escape prisoners' dilemma voluntarily by “natural reason”),因为个体经济理性行为是造成囚徒困境的关键;所以,说服人们采取非个体理性的“合作非占优”策略才能解决合作问题(Arye L.Hillman,2009)。然而,现实却是,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外,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价值和伦理的追求也必须建立在现实经验世界,特别是现实文化信念和人们的需求基础之上,如果不顾现实世界的文化信仰、政治权力结构和人们的急迫需求,价值追求最终也只能停留在价值层面,难以落实到现实的治理实践中。登哈特夫妇在其新公共服务思想中强调要构建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聚集和个人价值追求。登哈特夫妇(2010)认为,公民“被描述为在一个更广大的社区环境中权利的享有者和责任的承担者”;公民能够通过参与社区行动,为了社区共同利益,乃至社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而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公民关注的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公民具有足够的公共利益取向。但这种民主治理理想忽视了人类欲望的无穷性和物质世界资源的稀缺性。在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是相对无穷的情境下,必然存在着人类对资源的竞争;这种资源既包括黄金、白银这样的有形物质资源,也包括权力、才智和美貌这样的无形资源。只要存在着资源的竞争,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大公无私”,也不可能普遍性地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相反,人类个体更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①,损害其他公民个体或社区集体的利益,即人们往往可能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谢秋山、马润生,2012)。
三、在公共行政中链接公共性和私人性
就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来看,区分理想中政府应该做什么(what governments ideally ought to do)和政府实际上做了什么(what governments actually do)是十分重要的(Arye L.Hillman,2009);我们不能否认公共利益、共享价值和共同领导是人类未来社会治理的美好愿景。然而,在憧憬理想化未来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的是立足现实,逐渐改善人类的福利和文明。已有的理论研究不管宣传什么样的价值观,在实际分析运用中都遵循了西蒙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打着“公共”的名义,却在功利主义支配下践行着机会主义行为,最后形成价值是价值、事实是事实,价值与事实相脱离的尴尬局面。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如何有效地整合人类个体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即如何在公共行政人员和公民集体中建构和设计个人利益与公共价值的链接,以及如何协调人类个体价值与共享价值之间的冲突。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机制设计中,要在公共行政领域实现公共性和私人性的链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克服的挑战。从理论上看,多层的、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委托人虚位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从实践上看,在现实国家治理中,政治和行政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把理论上具备公共性的政治和行政权力赋予具备私人利益动机的个人身上,必然会因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而带来伦理的困境,也会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但我们依然试图分享我们不成熟的思考和建议:
(1)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价值定位,即要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存在的是机会主义的公民,在公共领域尝试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链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具体而言,在公共领域也要在承认公共行政人员私人利益的基础之上,通过政治问责机制设计,约束和控制行政权力,让公共行政人员在职务中回归公共性;同时在尊重公民私人合法利益的基础之上,倡导公民为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而行动。比如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外部性,驾车时文明行驶和停靠车辆不妨碍他人正常通行。
(2)针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难题,要把政府绩效的评价权主要交给公民,以公民满意度调查等主观评价法为主要指标,构建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于评级较差的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予以惩罚,如不再允许其提拔和晋升等,而在职务晋升时优先考虑绩效较优者。之所以要以公民主观评价法为主要绩效考核指标,是由于现有的、由行政首长主导和以上级领导和专家为核心的绩效评估体系往往受制于权力,流于形式,并未起到激励和惩罚的作用。
(3)针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公共行政权力的特殊性,要从宪法的高度进一步明确公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明细公民的知情权、创议权、投票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民主公民权利。就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看,一方面,虽然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以及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但并未就公民的知情权、创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做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事实上,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够成为“人民代表”的很少是普通公民,绝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各行各界的精英,如政府的高级官僚、成功的企业家、发家致富的农场主等。从代表性官僚制的理论视角来看,根据社会的总体阶层构成来选出人民代表才有可能最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我国现有的人大代表组成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层,应该予以调整和完善。
(4)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为,作为一个从封建社会中迅速转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文明古国,我国公民意识中的“臣民”、“贱民”思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脑中的官僚主义习气都比较严重,必须要继续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思想普及和强化公民民主权力和义务教育。一方面要在学校教育中增加普及公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相关内容和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要鼓励新闻媒体从事宣传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报道,以及保障新闻媒体从事支持公民权利、批评行政机关违法、违规行为的权力。
当然,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完全赞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共享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领导;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否认登哈特夫妇所提倡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框架。新公共服务理论所提倡的民主行政价值应该成为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规范,成为政府机构的基本价值准则;但价值和事实并不能完全等同,我们所要做的是,努力让事实更符合理想价值,努力挖掘公共行政的真实,而非被过度解构和歪曲重构之后的公共行政。
①另外一对比较知名、活跃的社会科学伉俪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唯一的女性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他们共同致力于治理问题的研究。
②在韦伯看来,理想类型在现实世界中一般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对事物状态的抽象和精致描述,并不意味着必要的和应该去追求的目标。但理想类型作为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为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详见Max Weber.(2009).经济与社会(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在百度搜索中搜索关键词“弃婴”会有超过673 000条的相关新闻,但这其中真正得到网友大量关注和社会大力支持的并不多见。
④机会主义动机并非人类持续的投机行为,Oliver E.Williamson指出,机会主义意味着某些人在某些时间段内具有机会主义的动机。
标签:哈特论文; 公共行政论文; 新公共服务理论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组织公民行为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个人管理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