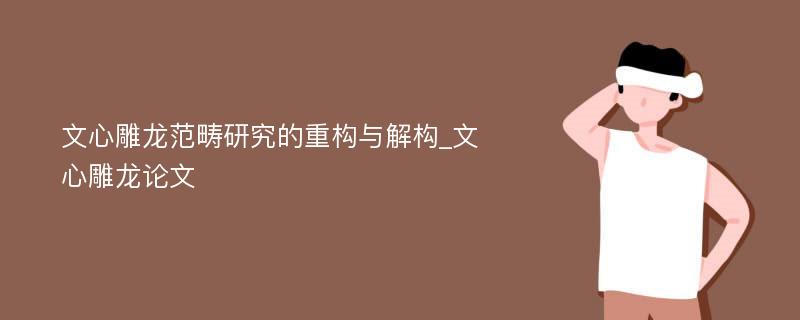
《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重构与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范畴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3-0083-06
范畴研究是《文心雕龙》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这些范畴是刘勰用来表述自己的理论主张与进行思维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今人理解《文心雕龙》理论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就像其他古代理论家一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使用的不少范畴并不具备理论的明晰性。由于古人没有严格的逻辑分类意识,所以在使用许多术语时,其实很难严密规定其内涵,而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并不是思维方面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为了在不同的场合说明不同的问题而各有所侧重,再加上中国古人重视整体的感悟而不太在意对概念的严格界定,所以也就形成了与今人不太一致的范畴特征。因此,要有效地诠释其理论内涵,势必要对其所使用的范畴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自现代学科形成之后,对于其范畴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少重要范畴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诸如比兴、体性、通变、奇正、文笔、雅丽、华实等等。但也有一些范畴至今为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比如折衷、风骨、体要、隐秀等等,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这并不说明这些范畴不重要,也不是投入的研究力量不够。仅就风骨范畴来说,可以说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最为吸引学者的领域之一,自明代的杨慎到清代的纪昀,再到近人黄侃、范文澜,都曾对其进行过论述,更不要说现代学术界对其的重视程度了。可是问题好像越争论越复杂,据香港学者陈耀南统计,截止1991年,关于风骨已有64种不同的说法。[1]而据戚良德统计,自1948年至2005年,仅专论风骨的文章即有209篇之多。[2]那么问题何以会越研究越复杂呢?这除了研究对象自身内涵的丰富外,研究者本身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之是否得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前人研究《文心雕龙》的范畴,往往有意无意地按照今人对于范畴的理解来理解刘勰,同时也按照现代的范畴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的范畴,于是常常认为刘勰所使用的范畴就像今天那样明晰而严密,从而将原本并不太严密的说成是严密的,将原本并不那么明晰的也说成是明晰的,结果往往就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了。的确,《文心雕龙》的某些范畴是严密而明晰的,与我们今天对他们的理解也比较接近,因此也就比较容易说清楚。有的则不然。有些东西从今天的角度看应该属于范畴,可刘勰并没有明确地将其作为范畴加以论述,如果把这些略近于范畴的东西完全当作范畴来看待,就会拔高研究对象。有些范畴则刚刚相反,刘勰认为这些范畴太重要,太想将其说严密了,但事实上这些范畴并不能达到像刘勰理解的那样完美无缺,从而留下了种种的裂痕与矛盾,但今天的研究者由于对刘勰成就的赞叹和《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的折服,往往将这些并未能做到无懈可击的范畴也尽量向严密系统的方面去引申发挥,从而也有意无意地拔高了研究对象。其实《文心雕龙》中有一些近于潜范畴的东西,刘勰在论文过程中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作为其标准与工具,但又没有集中地加以论述,对于此类潜范畴就需要予以重建,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个层面与要点,在深层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与脉络,但作者却并没有将其明确表达出来,今人就有必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把这些要点的内在关联性发掘出来,并建构一个能够容易被今人所理解的范畴体系。这个范畴体系并不是刘勰建立的,但也不是现代研究者主观编制的,而是将潜在的变成显见的,将仿佛孤立的点连成线与整体。这种重建的工作有点类似于傅伟勋所言的创造的诠释学,就是要做到:(一)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二)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三)原作者可能说什么;(四)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五)作为创造的解释家,我应该说什么。[3](pp.51~52)在此,我们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在作者所说的基础上,将他想要说、应该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说出来,就是一种范畴的重建。《文心雕龙》中另一类范畴可以称之为玄范畴,也就是说作者为了某种目的、某种理想、某种功能,将本来不能统一起来的东西人为地统合进某一范畴,从而仅具备理想化的圆满性而并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甚至其自身就显示了逻辑上的不周延与体系上的裂痕,从而存在着范畴上的诸多漏洞。对于这种范畴,我们要进行一种解构的工作,发现其不足与漏洞,并指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总之,既然研究对象的范畴特征呈现了多样性,研究的方式自然也应该是多样的,这样才能切合研究工作的实际。
先看关于潜范畴的重建问题,这可以拿体要的研究为例。目前对体要的研究争议还很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要能否构成范畴?因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的观念可以分为体式、体类与体貌三种类别,是否可以再增加体要一类呢?许多学者认为体要构不成范畴,所以就将其作为一般词语对待,称之为“切实简要”、“体制要领”、“大体大要”等等,认为与《尚书》中的“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意思比较接近。但有的学者却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范畴,体现了刘勰论文的重要思想。二是作为范畴的体要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徐复观认为是“法于要点”,将体解释为“形相”,而将要解释为“要点”,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体论一个重要内涵:“体要之体与体貌之体,必须以体裁之体为基底;而体裁之体,则必在向体要与体貌的升华中,始有其文体中艺术性的意义。”[4](p.129)而杨东林则从王夫之对体要的解释出发,将体要理解为文质关系的把握,认为是为文的法则,并进一步演变为“法式”与“体式”的意思。[5]应该说上述各家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都触及了刘勰体要的某一点或某几点,其不足之处是有的只说点而未能将其内部关联发掘出来,所以不承认他是理论范畴而轻易地加以处理;有的则将其说得太体系化了,有故意拔高的嫌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确在许多地方都提及了体要,并成为其论文的重要术语。但刘勰在使用体要时,并没有将其进行严格的界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各处出现时侧重点不同,但他并未做统一的工作;二是它与其他范畴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功能各异的独立系统。在《征圣》中刘勰说:“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矣。”这里的体要已经从原来《尚书》中的要约重质的内涵演变成了宗经征圣的意思。在刘勰看来,圣人能够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来安排文辞,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无论是繁略显隐,都能做到“文成规矩,思合符契”。那么这里的体要也就是体察圣人是如何根据不同的需要去组织文辞的,只要能达到有效表达的目的,就不必死板地规定必须精炼要约。至于如何去体会圣人“繁略显隐”的用意,那就必须要到《五经》中去体会了,因为经书不仅体现了圣人为文之用心,更重要的还立下了具有不同表达功能的“体”。而后来所有的文体,都源于经书,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按照这个思路,则刘勰的体要其实也就是体“经书”之要了。因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这是刘勰将《尚书》的体要向文体的体要所做的一次引伸。
在20篇的文体论中,体要又有了新的内涵。刘勰在论述过程中尽管没有对体要进行解释,但根据他的具体使用,可以认为此处的“体”是“大体”之意,也就是文章的基本内容与主要功能;而“要”则是“关键”之意,也就是主要的表达手段与体貌特征。这合乎刘勰的一贯思路,也就是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功能以及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试看下面几段文字: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烨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6](《檄移》,p.378)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6](《论说》,p.328)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深;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6](《铭箴》,p.195)
从这三段文字的表述看,都是前半部分论内容功用之体,而后半部分论表达体貌之要,而且刘勰认为把握这些很重要,所谓“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型,辞有风轨”[6](《奏启》,p.423)。这种意识正是源于其宗经的文体观念。可以说在文体史论里,他更强调二者的相符与对应。
而在《定势》篇里,刘勰更强调的是“势”,也就是某种文体的标准体貌特征。他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以立体,即体以成势也。”如果说文体史论里谈的是“因情以立体”,则本篇里显然谈的是“即体以成势”。所以他用了长长的一段文字来谈此一点: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诠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巧,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以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6](p.530)
如果与文体史论中的论述相对照,其实可以发现其一致性,比如《檄移》篇说其大要在“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而此处则言“楷式乎明断”;《铭箴》篇说“体贵弘深”、“摛文也必简而深”,而此处则言“体制于弘深”,也都是讲的体貌的主要特征。只不过讲文体时兼写法,而此时只讲体貌而已。也就是说此处虽未用体要的术语,其实也还是讲的体要的内涵。
由上可知,刘勰是很重视体要的,论五经时要人们明晓圣人之要义并知道经书乃文体之本源;论文章类型时让人们知道体之所写内容与体貌及表达方式之关联;论文章之势时则强调文类对体貌之决定作用等等,应该说谈的都是体要问题。但作者却无论从强调的侧重点还是术语的使用上都是不统一的,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将体要提炼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范畴。但在其各处所论述的内容里,又有诸多的内在关联性,比如对于文体本源的重视,对于文类核心特征的把握,对于各种文类基本体貌的强调,都是为了防止过于追求华丽的效果而影响了文章功能的实现。关于这一点,他在《序志》篇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于各种文章“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时下的状况则是“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就必须强调体要,因为“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圣人就是这样做的。因此重视经典的规范性与本源性,强调文体的各自独特功能与基本体貌,就成了贯穿各点的内在线索。
将此一意思表述最为充分的是《风骨》篇。因为本篇是从正面表达刘勰对理想体貌的看法的,所以就把他对该问题的看法集中表现出来了。要使文章具有风骨,首先就要重视经典对文章的规范作用,所谓:“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只有“熔铸经典之范”,才能够“曲昭文体”。这层意思在对有风骨的潘勖《册魏公九锡文》的称赞里得到了更明晰的表达:“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6](《风骨》,p.513),“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6](《诏策》,p.359),“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6](《才略》,p.699)。在此三段文字中,刘勰认为潘勖之《册魏公九锡文》之所以有风骨,乃在其“思摹经典”、“典雅逸群”与“凭经以骋才”。可见刘勰认为要想有风骨,必须“宗经”之典雅而知道文体之正途。从反面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也就是说,失去了经典的规范,就像人体没有了骨架,仅剩下一堆肥肉而已。至于宗经后文体上所呈现的优势,《宗经》篇里早已说得十分清楚:“故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6](p.23)这“六义”,我以为既是宗经之结果,也是构成骨的“体与辞”之“体”的内涵。前二项之“情深而不诡”与“风清而不杂”可以归属于“风”之内涵,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情均能被刘勰所认可,只有“情深而不诡”才是合乎宗经精神的,“情深”是指饱满深厚之情感,或者也可以说与气相偕而出之情感,但仅有此还不行,它还必须“不诡”,“不诡”就是雅正。前人研究《风骨》,总以为刘勰开始先从诗之“六义”讲起,强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乃是言不由衷的比附经典,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刘勰,他是不可能仅强调情感之充沛而忘记经典之雅正的。“六义”之第六项“文丽而不淫”应该是风骨共有之特征,不必多言。而中间三项“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与“体约而不芜”,则显然属于骨之“体”的内涵,从共同性上讲,三者皆可归之于“正”,亦即“典雅”;若分而言之,则既有义理之正与叙事之真的内容特征,又有行文精练的形式特征。也许正是出于对此二者的强调,刘勰在《风骨》中再一次提到了《尚书》中“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古训,那意思正是着眼于内容之雅正真实与行文之精约简要。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真实雅正与精约简要,才能算是具备了文章之骨。可以说,“不诞”、“不回”与“不芜”是宗经在体貌上的具体落实,而三者归纳起来又可统之以典雅之宗经总纲。我以为,刘勰“风骨”中的内涵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从义理的层面讲,是合乎经典的雅正传统并了解其文体源头;从体貌的层面讲,则是合乎“六义”的文体规定;从言辞的层面讲,则是精练端直的特征。刘勰在讲这些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么清楚的层次感与系统性,但这些意思与要点他的确是有的,只是需要我们替他归纳、整理与重建。这种重建就是将不利于现代读者理解的“潜范畴”转换成比较容易接受的显范畴而已。
再看关于刘勰原有范畴的解构问题,这可以“折衷”范畴的研究为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刘勰折衷学术思想的专题文章约有20余篇,可以说基本都是肯定的看法。这其中可以周勋初的《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7]与陶礼天的《试论<文心雕龙>“折衷”精神的主要体现》[8]作为代表。周文认为折衷是刘勰“研究工作中的基本态度和主要方法”,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这种方法的主要内涵:(一)以圣人与经书为标准的“裁中”;(二)“扣其两端”的比较;(三)平稳妥帖、不偏于一端的兼及。同时还考察了这种方法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运用情况。陶文则在周文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认为“尚中”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同时也受释道思想的影响,折衷思想不仅要求“扣其两端”,而且“圆览”、“圆照”、“圆通”,并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此种思想的儒释道尤其是玄学的来源。[9]这些研究都对刘勰折衷思想的内涵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呢?这就需要找出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我以为在对待折衷范畴上,学者们有过于尊崇刘勰的倾向。周文认为折衷这种思想,“注意到各种文学要素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而在一对对的文学要素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刘勰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分析各种文学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然后衡量得失,处之以权,提出一种平稳可取的方案。他在许多文章中常是采用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陶文虽认为“刘勰并不可能完美地实现自己所制定关于‘论之为体’的标准与要求”,但并未具体指出何处不完美,而是说“然而‘亦几乎备矣’”。其他研究论著也大致持此种态度。
刘勰本人对其折衷方法的确是很自信的,也的确在其批评实践与理论表述中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周密公允,但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他的折衷思想是留有很大裂痕的。如果从其立论的基本根基上入手,几乎可以解构掉他的这一范畴系统。刘勰在《序志》篇中曾记述过自己的两个梦,所谓“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如果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讲,这两个梦可以说代表了两种文学传统与文学观念,一种是追求华美漂亮的六朝唯美文学观念,一种是强调诗教功能的儒家文学观念。其中“彩云若锦”与“丹漆之礼器”的象征意蕴该不会有大的理解偏差。刘勰的折衷方法能否成立与是否使用有效,要看这两种文学观念能否有效地融合起来。而恰恰在此一点上,刘勰的态度是暧昧和矛盾的。从他能够形之以梦寐看,他的确是感受到了六朝唯美文风的优长与动人;可是从撰写《文心雕龙》的原初动机上看,就是为了纠正这种背离儒家诗教传统的“形式主义”文风的。从理论上看,他提出了“雅丽”的总标准,所谓“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也”。但这只能是刘勰的理想,或者说如果只从理论上来讲,可能不失为一种完满周全的状态,可以看作他折衷两种文学传统的一种努力,但是其实际可操作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这种矛盾态度在《辨骚》篇中体现得至为明显。在该篇中刘勰先检讨了汉人对《离骚》的评价,认为“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暂且不论汉人对《离骚》的评价是否得当,但他们采取的立场起码是一致的,“举以方经”、“谓不合传”,这是典型的经学主义立场。到了刘勰这里,他找出了《离骚》合乎经典的四个方面,同时也找出了异乎经典的四个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四同四异”,应该说到此为止他的标准还是一致的。但当他评价这“四同四异”时,显然就有了问题:“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故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也就是说与经典相比,它是不够格的,但是在辞赋中却是最有成就的。所以他认为楚辞是文章的楷模:“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这当然符合刘勰雅丽的标准,但他所说的“四异”中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诸项,又岂是文辞所能概括的了的?果然,他下面称赞楚辞时,就没有单就文辞立论: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志,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刘勰的概括是相当准确而精彩的,也是对楚辞进行的真正的文学评价,这说明了他作为一个眼光独到、感觉敏锐的批评家的优长。但是在此他显然违背了经学主义的立场,因为此处所言的“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标放言之志”、“寄独往之才”,都与上边“四异”中的“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内涵大致相近。何以在上边被拈出作为“雅颂之博徒”证据的东西,到了这里却又成为“辞赋之英杰”的代表?按照刘勰的一贯思路,经典乃是圣人之作,是文章的本源与楷模,人们要使文章达到理想的状态,就必须征圣宗经。而在这里,楚辞既然无法与经典相比,又何以能够成为辞赋之英杰?其实,原因很清楚,他已经从汉人单独的经学立场转化成为经学与文学的双重立场,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说明了魏晋时期文学审美的确比在汉代更受重视。但是从范畴的严密性来看,却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这种裂痕从《正纬》篇就已经开始呈现。本篇批评了许多纬书中荒诞不经的东西,但最后在评价时却又说:“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既然经典就是最好的文章,那么何以能够“无益经典”了却又“有助文章”,可见在此刘勰的态度已经悄悄发生转化,看似不经意间却将经典与文章区分了开来,为下面将要展开的《辨骚》篇之双重标准进行了预设。从刘勰的主观意识上看,他极想将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融合起来,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他将早期的儒家经典进行了文体与创作技巧方面的提升与理想化,以说明其文章楷模的特点与作用,有人将此称之为经典的文学化。[10]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使后来的文学创作尽量向经典靠拢,这又可称之为文学的经典化。这也就是最典型的“扣其两端”而折衷之。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强调实用功能的儒家文学观与讲究愉悦功能的审美文学观本是两种价值取向很不相同的思想体系。这两种文学观念不能说毫无沟通交融的可能性,但是在哪些层面能够沟通,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沟通,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复杂问题。不过从根本上说二者是很难完全融合的。正是在某些层面有沟通的可能性,所以刘勰在许多领域的折衷工作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为从根本上的难以融合,所以为刘勰的折衷范畴留下了诸多裂痕。拿这样的折衷方法去进行具体作家、作品及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评价,也就不能不留下种种的矛盾与漏洞。除了经典与文章的关系外,还有奇与正、通与变、才与学、情与采等诸多范畴,如果认真考究起来,都还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缝隙。这也是为何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能够在理论上获得后人的赞叹,而在指导实际创作方面却很难取得应有的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近关于折衷方法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起色,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毫无保留地肯定刘勰,而是在指出其理论上巨大创获成就的同时,也能从解构的角度对刘勰的不圆满处予以检讨。①
在《文心雕龙》范畴的研究中,无论是进行重构还是解构,都意在将该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最终目的则是更真实地揭示研究对象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效用。重构的价值在于发掘其理论的隐含特征与潜在价值,而解构的作用在于更全面地认识其范畴的理论预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如此做的动机丝毫没有贬低刘勰与《文心雕龙》的意思,而是要更加务实地进行研究。这其实不仅是《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许多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对待古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开创研究新格局的问题。
注释:
①笔者在为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曾将此看法提出以供讨论。后来我的研究生刘尊举曾进一步发挥写成《文心雕龙“折衷”新探》一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章见《文学前沿》第五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