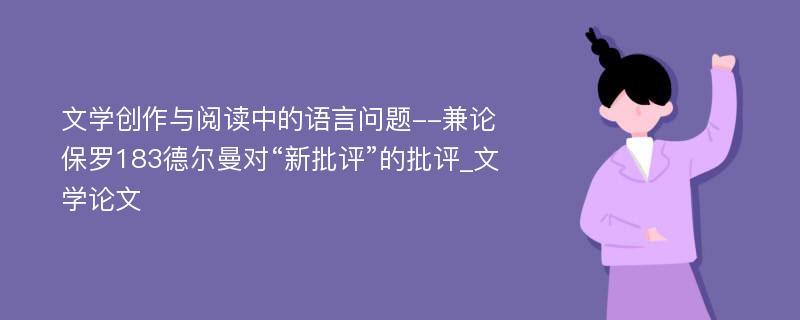
文学创作和阅读中的语言问题——论保尔#183;德曼对“新批评”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尔论文,批评论文,文学创作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尔·德曼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德曼的文学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强调文学语言的修辞性和寓言性本质的语言学思想。也正因为此,他的文学批评被称为“修辞批评”和“寓言批评”,而他所强调的阅读方式被称为“修辞阅读”或“寓言阅读”。出于对语言问题的极端重视,德曼曾经断言,“理论的出现……是与语言学术语被引入文学的元语言有关的……当代文学理论的确立发生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分析]中之后”①。
保尔·德曼曾经暗示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一种“批评语言学分析”(critical-linguistic analysis)② 或“文学性的语言学”(the linguistics of literariness)③,他不仅把语言学视为当代文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而且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赋予了语言学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分析研究保尔·德曼的文学语言观,对于理解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曾指出,“德曼与‘新批评’有许多不解之缘,他们都崛起于耶鲁大学,他们对美国文坛的影响程度也基本相同。在解构批评兴起的时候,也如同‘新批评’盛行之时一样,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参照解构批评的原则来修正自己的言行”④。从文学批评史来看,“新批评”并没有真的像米勒所说的那样让位于解构批评,“细读”是德曼和“新批评”的共同特征,也是它们之间关系密切的原因之一。有人甚至断言,“(德曼)不是‘新批评’的杀手,而是它的最后的继承人”⑤。这些充分显示了德曼与“新批评”之间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关系。
就名称而言,“新批评”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保尔·德曼曾经把“新批评”定义为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并且对它在文坛上的影响力颇为不满。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⑥。尽管如此,为了行文的方便,也出于对诸多共同被称为“新批评家”的某种程度上的承认,本文仍然把“新批评”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流派来看待,与此同时,注意区分开各个不同文论家的观点。
一、语言能否言说任何体验的全部?
“新批评”诸评论家素以重视诗歌的语言因素而著称,他们借用马拉美的名言声明诗不是用观念(idea)而是用语言塑成的。这种对诗歌语言的重视首先来自英国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I.A.瑞恰兹。瑞恰兹敏锐地察觉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质,提出了语言的两种用法,一种是“符号语言”,另一种是“情感语言”,并且指出后一种语言是一种“伪陈述”,它是不能用经验的事实来核实的。
德曼对“新批评”的批评从瑞恰兹开始,而且他的批评集中表现为解构瑞恰兹的语言观。这些批评首先出现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终结》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德曼首先指出:
对于瑞恰兹来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正确理解作品的指称含义(signifying value)或者它的意义;这是一种介于作者的原体验和它的传达之间的、准确无误的一致性。对于作者来说,在形式上努力进行的劳作就体现为建构一个语言结构,从而尽可能准确地传达自己最初的体验。一旦假定作者建构了这样一种交流的方式,它就同样对读者具有意义,然后,所谓的交流就发生了。⑦
瑞恰兹还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同作者的建构活动呈相反的方向,它是通过细致准确地研究作者所建构的含义形式(signifying form),然后追溯到作者的原体验,即那个产生了这个含义形式的体验。在瑞恰兹看来,只有通过阅读追溯到那些同作者的原体验或体验群相接近的那些体验时,正确的理解才可能达到。而由于在这样的过程中,错误和谬见层出不穷,所以,瑞恰兹撰写《文学批评的原理》一书的目的就在于详尽地阐述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但是,德曼认为,瑞恰兹从来就没有对是否可能获取一个正确的理解产生任何怀疑⑧,这正是德曼所不能赞同的地方。
对于瑞恰兹所谓的“准确无误的一致性”,德曼提出了疑问。他指出,瑞恰兹的上述观点似乎是建立在常识之上的,但实际上内含一些很成问题的、本体论上的假设。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诗歌语言能够言说任何体验,甚至包括某种简单的知觉。在德曼看来,这种对体验的全部过程进行言说是不可能的。他强调,虽然关于一个物体的感性意识和关于这个意识的体验是确定的,但是,如何建立一种关于这种体验的逻各斯(或就艺术而言,建立一种形式),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德曼举例说,无论是一个简单的陈述:“我看见了一只猫”,还是波德莱尔的诗《猫》,它们都无法包容叙述者对现实中的那个猫的意识中所携带的所有的体验,在德曼看来,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包含和表现了体验,而是重新建构了体验,因为我们对于曾经发生的体验只有通过语言的重构才能表述。在《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瑞恰兹假定了符号和其所指物体之间的一种完美的连续性。通过一种重复性的联结关系,符号替代了其所指物体”⑨。但瑞恰兹所希望出现的那种能够返回到原初之体验的语言是没有的,因为叙述者用文字所指代的那个“猫”应该是“这里”和“现在”的那个“猫”,而这个“这里”和“现在”必须要由叙述者和读者自己去重新构想,因为它们早已在文本构成之前就消失掉了。也就是说,正如瑞恰兹所意识到的,语言中包含了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所以语言的所指对象要求我们去建构新的时空世界来达到对它的叙述和理解。
因此,德曼强调:一种语言的建构形式理论(a theory of constituting form)和语言的含义形式理论(a theory of signifying form)截然不同。在前者那里,语言不再是一个介于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而是介于一个存在物(文本)与一个非存在物(文本虚构的世界)之间的媒介。而批评的问题也就不再是去发现语言形式究竟指代怎样的体验,而是它如何建构了一个能够引发体验的虚构世界。文学创作就不再是模仿而是创造,不再是交流而是参与。所以,在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之后,再去追溯那最初的体验——那最初的“猫”⑩,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了。这就是说,“作者的原体验”和他所建构的那个传达这一体验的语言结构之间首先就无法实现瑞恰兹所断言的那种“准确无误的一致性”,更不用说一旦这种关系被建构之后,它对于读者有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了。德曼认为,瑞恰兹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论断,主要是因为他对语言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从不怀疑语言能够准确地表达人类的思想,尽管他确实也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但是,他相信这种冲突并不是致命的,只要对语言技巧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瑞恰兹所相信的却正是德曼所深感疑问的。为了证明瑞恰兹的观点是错误的,德曼进一步分析了燕卜荪的语言观并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在对燕卜荪进行分析批评的时候,德曼发现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即,瑞恰兹提出的研究方法在他非常勤奋的学生燕卜荪那里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燕卜荪按照瑞恰兹在《实用批评》中的方法进行阅读之后,居然得出了如此的结论:“非但不是回到作为它的原因的物体,诗歌的符号引发了一种不指示任何特殊物体的想象行为。隐喻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意味’任何特定的行为。”(11) 德曼认为,通过阅读燕卜荪,人们根本无法再谈论任何回到作者的原初体验的可能性了。
在评论燕卜荪的《含混七型》时,德曼特别强调了第七种含混形式,这一种含混形式彻底摧毁了瑞恰兹所信赖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在这里,文本不仅暗示各种不同的意义,而且证明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意义在违背作者的意愿之下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因此,德曼认为由燕卜荪的第七章得出了一个瑞恰兹绝对不愿意听到的答案:“真正的诗的含混起源于存在本身的深层分裂,而诗歌所做的不外乎陈述和重复这一分裂。”(12)
当然,这里所阐述的种种分析都是德曼自己的,不是燕卜荪的,而且德曼也自知,燕卜荪肯定是最不愿意附和他对他的发现所做的这一总结。因为燕卜荪尽管把文学语言的研究推进到了很深的层面,他仍然同意自己老师瑞恰兹的观点,相信文学语言的含混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却不是如德曼所认为的那样令人不安,因为一方面,这种含混多多少少有利于诗歌,增添了诗歌的丰富性和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它也还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也就是说,还仍然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他并没有把第一种和第七种含混同其他五种含混形式区分开来,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燕卜荪并不认为自己如德曼所推论的那样,是对瑞恰兹的一种背叛,虽然他并不讳言自己与老师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分歧。而德曼却认为燕卜荪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分析中所包含的那种颠覆性。“诗歌所言说的这种含混存在于精神世界和感觉实体的世界之间:精神为了证明自身,就必须把自己转化为感觉实体,而后者却只有在分解成非存在物之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识。精神无法与它的客体相一致,这种分裂是永远的悲伤”(13)。至此,德曼指出,表面上来看,瑞恰兹注重的是文本的阅读,是文学的语言问题,但事实上他强调的仍然是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关系,阅读和阐释的任务仍然是追溯作者的原意。而德曼已经证明,读者所能够触及的只有文本而不是作者的原体验,文学阅读是一种特殊的美学体验,不可能构成两个主体之间直接的交流。德曼认为瑞恰兹出于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过分信赖而把诗歌语言降低到了交流性语言的地位,并且否认了美学体验与其他人类体验的差别。
对德曼的批评意见是:德曼在这里批评了瑞恰兹等人用追溯作者的意图来代替对文本的阐释的主张,但是在随后的文章中,他却认为“新批评”不应该否定文本的意向性并特意撰文批评,他是否自相矛盾呢?笔者认为,德曼并不否认诗歌语言的意向性,但是,他认为这种意向性不能够简单地被理解为作者的意图,而且它也不能够被认为是惟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德曼曾经指出:“无疑,诗歌中是有一种感官的维度,即意向性,但是,断言它是覆盖一切的和直接呈现的,这却是对所有一切创造性的、想象性的意识之起源的忽视。”(14) 德曼在这里反对的,一是瑞恰兹用作者的意图来代替文本所蕴涵的一切这样一种绝对的、单一的观点;二是过分强调文学语言中的个人意向即作者的意图的观点。德曼仍希望确认语言中有一种普遍的、抽象意义上的主体性意向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曼对于“新批评”的开创者瑞恰兹的语言观的批判同他随后对“新批评”其他试图压抑语言的意向性以维护诗歌文本的有机整体性的批判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这两种批判甚至可以说是有必然联系的。
对于语言,德曼认为它并不言说任何人类体验的全部,而只是协助人类去重新建构自己那过往的体验,所以,在任何时候,文本与人类的体验都不是相等的,所以,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都不可能回溯到作者的本真体验。德曼的这个论断包含着他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的深层思考。
二、文本是不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有机整体?
瑞恰兹在《实用批评》中采用一种具有实验性质的阅读方法,即要求学生阅读没有作者和标题的诗歌作品。从表面上看来,这一行为本身似乎与他自己那种以追溯作者意图为目的的主张相违背,但事实上,瑞恰兹的“实用批评”正是其语言观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在瑞恰兹看来,文本中所呈现的就是作者的原体验,也就是作家创作中已经实现了的自我意识和其他动机,所以,读者只要阅读和研究作品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了解到作者的名字或作品的标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瑞恰兹在《实用批评》中斩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的做法似乎被兰色姆等“新批评”的倡导者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理论化,从而发展成为某种文本的“本体论”和“有机整体”思想。
对于“新批评”的有机整体观念,许多文论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批评。芝加哥派理论家克莱恩曾经指出,“新批评”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诗歌的整体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上都不是“有形的”,而是语言的,而且任何关于这种整体性的观点都需要一些语言上的阐释(15)。克莱恩的批评切中了“新批评”的要害,揭示出了它把文本这一语言形式误认为是同自然界有形的事物一样的、具有本体特性的客体的观念。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也讽刺道:“‘新批评’家认为一首诗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完整的客体,就好像一个瓮或一座圣像那样有形有实。”(16) 显而易见,“新批评”文论家的错误仍然出于他们对文学语言的高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说是这一文学批评流派贯穿始终的传统。他们中间最具有怀疑精神的批评家也只是和燕卜荪一样,仅承认语言的含混性而已,从没有人敢于质疑语言完整而正确地表现现实的能力。瑞恰兹在读过自己学生的著作之后,于1936年撰写了《修辞哲学》一书,此时他虽然不再像早年那样毫无保留地信任语言,并开始重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仍然认为,假如我们能够解决如下的问题,那么目前困扰着人们的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其中包括:一种思想如何会从属于以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事物?事物及其名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仍没有意识到对此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回答。
德曼指出,正是由于忽视了文本自身的语言性,也即文本语言的修辞性和寓言性,“新批评”才可能断言文本具有“本体论”特性和“有机整体”特性,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错误。威姆萨特等人反对作者意图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作品的自主性,这种维护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其方法上却有不可克服的漏洞。
……如果真能够通过压抑其意图性特征而使文学行动成为文学客体,即这样一种实体真的由于文学批评的需要而可能存在和必须存在,那么,我们仍然没有脱离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文学语言与自然客体具有相同的身份和地位。这种假定出自于对意向性本质的误解。(17)
关于文学文本与自然物体在本体论上的区别,德曼有一个比喻:自然物体和文本分别比作石头和椅子。虽然两者都是物体,但是椅子与石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包含了某种“意向性”。椅子是注定要被“坐”的,而潜在的“坐”这个行为就是椅子这一客体的构成性因素,同时也是把椅子同石头区分开来的内在因素。同理,文学文本由于具有意向性,它就不同于自然客体。而椅子中内含的意向性是由它注定要被坐这一事实决定的,并不取决于某个木匠的主观思维,所以,文本的意向性也并不等同于作者的意图。所以意图性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既非物质性的也非心理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涉及一位主体的行动而不顾及其个体经验上的(特殊)关怀(18)。出于对意向性的本质的误解,威姆萨特等人把文本(或语言)的意向性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意图,并且把这种意图的传递类比为某种物理模式,即把诗人大脑中的心理和精神内容转移到读者的大脑之中去,就好比把酒从坛子里倒进玻璃瓶里。所以他们才坚决地反对所谓的“意图谬误”。因而德曼试图把文本的意向和作者的意图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也就是把主体性同主观主义区分开来。遗憾的是,德曼始终也没有就这种区分做进一步的详细论述,而且,把主体性从作者个体的体验中分裂出来的构想恐怕也只能是某种美好的愿望。公允地看,威姆萨特从文本中排除作者的意图确实是非常鲁莽的和错误的,但是,德曼把文本的意图称为纯粹“结构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对于作者意图的某种否定。德曼虽然敏锐地察觉到了威姆萨特等人的错误,但是他本人却不幸从另一个轨道滑向了类似的错误(19)。
对于“新批评”的本体论文本观和有机整体的思想,德曼还从文本解释学的角度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所谓的有机整体观念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的出现掩盖了人类意识与自然界在绝对意义上的、永恒的“无法穿越的隔阂”。“新批评”把文本比作独立自足的、具有本体性存在的自然有机体,事实上预设了人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客体的某种直接的交流关系。因为假如文本本身就是“有机的”和“本体”地存在的,那么它就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文本是人类通过运用语言而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类与语言的关系在这里就转变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这种转换在德曼看来也是出于一种误解:
对于美国批评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解释:由于批评家们如此耐心和细致地阅读诗歌的形式,他们事实上进入了一种阐释循环,但是,他们错误地把这种阐释循环当作了自然生态过程中的有机循环。(20)
德曼认为造成这一误解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诗歌语言的特殊品质,因此错误地把这一语言所拥有的“特权”当成了语言本身的自然特征。
真正的理解总是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没有这种完整性我们就无法与一种前理解(foreknowledge,或译为“先见”)建立联系,对于这种前理解,我们无法真正地把握而只能够多多少少地有一个较为清醒的意识。诗歌不同于日常语言,它具有我们称之为“形式”的东西,这就说明它已经取得了某种完整性。在接受诗歌语言,尤其是在揭示其“形式”的时候,批评家面对的其实是一种有特权的语言:一种沉浸于自身高度的意向性之中并趋向于完美的自我理解的语言。(21)
这也就是说,诗歌所具有的那种整体性并不是“有机的”或者同任何自然物体的整体性有任何实质关联的。“新批评”虽然认识到了文学语言是反讽的和含混的,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柯勒律治的有机形式观念。他们“把一种阐释循环装扮成一种文学文本具体化而成的客体性‘物件’(thing)”(22),从而造成了理解上的错误。诗歌的整体性只是人们出于理解的需要而预设的,它其实只是一种语言意义上的整体性,所以并不能够以此来证明其自身的“本体”存在。所以“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构成一个符合文学语言的整体性模式,从而能够描述这一语言的特殊方面”(23)。关于混淆语言存在物与自然存在物的本质这一错误,德曼在其批评生涯的所有时期都反复地提出了批判。
德曼对“新批评”有机整体观的批判最后还表现在对其宗教观念的批判上。“新批评”似乎表面上对文本非常关注,但事实上,他们利用象征和语象这些概念把文本极度地抽象化、精神化和神秘化了。意识的内在性和精神性被认为能够因文学象征的世俗超越性而获得具象化。象征体被认为是内在意识的外在表现符号。而通过把“新批评”有机整体观念同他们的宗教情结联系起来考察,问题就明朗了许多。文本之所以会成为独立自主的本体或有机的形式,其根本的原因是构成它们的语言本身在“新批评”家看来带有神性,拥有独立的神的意义。“新批评”理论的发展虽然表面上看来顺应了燕卜荪的方向,开始强调语言的“反讽”、“张力”和“矛盾语”等等,似乎是对瑞恰兹的某种程度上的反对,其实并不然(24)。事实上,“新批评”并没有真正地打破传统的陈旧观念。兰色姆提出的“本体论”观点把文本比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客体,表面上似乎是否定了作者的意图,因而是同瑞恰兹的本意相违背的,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承接了瑞恰兹的观点,即认为文本本身就包含了读者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在兰色姆那里,读者需要从文本中得到的不再是作者最初的体验,而是语言本身直接言说的意义。所以,兰色姆的“本体论”观点显然并不能够从纯粹的美学角度去理解,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内在地隐含了坚定的宗教情结。兰色姆等人一方面否定了瑞恰兹所主张的文本意义等同于作者意图的传统观点,从而使“新批评”同传统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承接了瑞恰兹所相信的文本本身携带了固定的意义以及以文学代替宗教的思想,并且充分发展了来自艾略特的那种混淆文学与宗教的观点。
“新批评”理论中的宗教色彩在“语象”(verbal icon)这个词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icon”原意是指东正教的彩绘圣像,在信徒们看来,它是一种多少分享它所指称的对象的性质或外形的符号。“新批评”理论家之所以把文学作品中的意象称为语象,也是因为相信语言意象具有显示真理和神圣意义的能力。兰色姆认为,语象是“世界的肉体”,是一种“奇迹性”的呈现;而刘易斯则断言,文本中具有“语象向冲突激发的真理”。
当理论发展到布鲁克斯等人之后,关于文本中神性意义的假定似乎已经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理论前提,或者说是某种基本的共识,它构成了“新批评”关于文本的独立自主、有机整体结构观点的隐形基石。这也是为什么“象征”、“客观对应物”、“语象”等等词语在“新批评”的文学批评文本中如此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新批评”的批评家实际上忽略了语言所具有的局限性,他们用人类自身的意识来替代语言所应该承担的传达任务。在“象征”等词汇中,为批评家所重视的不再是语言所产生的功能了,重要的只是词语背后所携带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存在于语言之中,并不以人类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艾略特等“新批评”理论家认为,词语成为能够同自然客体相“一致”的某种存在物,而且,文本的结构被认为同自然客体中的结构有着同样的性质。
通过揭示“新批评”理论家对于语言的过分信任以及他们混淆语言和现实、语言和宗教意义的错误姿态,德曼一方面批评了这一流派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误区,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展示了他自己的否定性语言观,即坚决主张直面语言与现实、人和世界的隔膜,反对把语言视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具有神性意义的实体,并且充分地重视语言对于人类的反作用。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德曼确实看到了一般人所忽略的东西,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也有过分地强调语言的局限性和蓄意抬高语言对于人类的制约作用之嫌。尽管如此,认真研究德曼的思想仍然有助于我们识别以往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误区,并充分重视文学创作和阅读中存在的语言问题。
注释:
①③Paul de Man," Resistance to Theory," 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8,p.11.
②Stefano Rosso," 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 ," 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6,p.121.
④Chris Baldick,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1890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House,1996,p.176.
⑤Wlad Godzich," Introduction:Caution! Reader at Work ! " ,in Blindness and Insigh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pXVi.此书以下简称 BI。
⑥⑦⑧⑨(12)(14)Paul de Man," The Dead-End of Formalist Criticism" ,in BI,p.230,p.231,p.231 ,p.232,p.237 ,p.244.
⑩这个“猫”的例子有很多出处。燕卜荪在《含混七型》的第一章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一句简单的陈述:“那只棕色的猫坐在红色的垫子上”;雅可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合写了著名的论文《评夏尔·波德莱尔的〈猫〉》;在《抵制理论》中,德曼还就“猫”做了另一篇文章。他就当时文坛上对待理论的两种不正确的态度进行了讽刺:“如果一只猫被称为一只老虎,那么它会很容易被戳穿,从而成为一只纸老虎,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一开始它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恐慌……”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例子,伍劳德·高泽西在评论这段话时称这只“猫”为“著名的猫”。
(11)See William Empson,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47.转引自BI,p235.
(13)See BI,p237.德曼的这个结论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德曼一贯的思想,从此构成了他的文学批评的一条主要线索。他在随后的许多文章里一再地重复自己的这个观点。在德曼看来,任何形式的精神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都只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联姻”,在意识和其他一切事物之间存在着“无法穿越的隔阂”( Paul de Man,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E.S.Burt and others ( ed.)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5-146.) 这样,德曼的论述就从文学语言的问题上升到了人类的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从文学批评转换到了哲学沉思。
(15)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swirth.( ed.),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94,p532.
(16)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47-48.
(17)(18)(20)(21)(23)Parl de Man," Form and Intent in the American New Criticism" ,in BI,p.25,p.25,p.29,p.31,p.32.
(19)这个问题涉及主体和主体性等复杂概念,仍然是哲学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曼在后期的著作中论述人类认识论的问题时,把它视为一种不可回避的“错误”。
(22)Paul de Man," The Rhetoric of Blindness:Jacques Derrida' s Reading of Rousseau" ,in BI,p104.
(24)虽然许多人被这种表面的现象给迷惑了。例如,伊格尔顿就曾经说:“虽然瑞恰兹还幼稚地认为诗歌只是一种传达的媒介,这同传统的思想认为伟大的文学就是伟大的人物的产物是一样的。但是“新批评”大胆地打破了这个陈旧的观念。”( See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4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