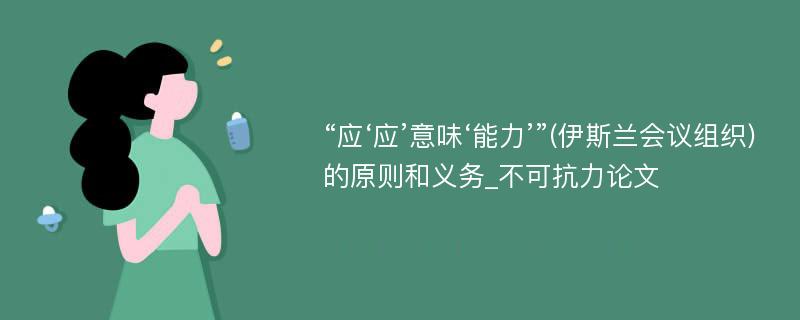
“‘应该’蕴含‘能够’”(OIC)原则与义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论文,原则论文,OI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2-0102-07 学界一般认为,OIC(Ought Imply Can)原则首先由康德比较明确地提出。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说:“纯粹几何学拥有一些作为实践命题的公设,但它们包含的无非是这一预设,即假如我们被要求应当做某事,我们就能够做某事……”①自此以后,康德提出的这一原则——“‘应该’蕴含‘能够’”,就和休谟提出的“‘应该’与‘是’的二分”一起,成为道德哲学中最为著名的箴言。但是真正意义上关于该原则本身的热烈讨论则从20世纪中期才开始。在30、40年代,西方元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将道德语言视为情感的表达,从而把道德判断的形成过程更多地引向非理性层面,并进而拒斥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价值,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和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到了50年代,黑尔所提倡的规定主义提出,以“善”和“应该”为代表的道德语言本质上乃是对人们“行为”的规定,从而再次将理性的行为(而不是非理性的感情)与道德语言联系了起来。而既然道德语言与人们的行为有关,那么对它的探究就不可避免地再次涉及OIC原则的问题(而黑尔也确实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再次肯定了OIC原则)。但是,与过去学界对OIC原则采取普遍接受的态度有所不同,随着西方元伦理学界对该原则关注度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关于其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元伦理学家们也逐渐地产生了分歧。 初看起来,这一原则是正确的,因为一个行为如果是应该的,那么总得是人们能够完成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原则似乎又是错误的,因为有的时候,即便一个行为不是人们能够完成的,但仍然不妨碍它成为义务。那么,OIC原则究竟是否正确呢?多年来,西方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成果。而综观国内学界,相关研究还没有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因此本文拟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OIC原则展开探索,并且结合该原则阐述若干与“义务”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OIC原则解析 在OIC原则中,有“应该”、“蕴含”和“能够”这三个词需要我们给予比较清楚的解释,才能进一步探索该原则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当人们说一个行为p“应该”的时候,就是说在人们所有可供选择的行为中,必须要选择从事行为p,否则就是没有在遵守该行为规范。当然,为什么要在所有可供选择的若干行为中一定选择p,人们往往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不管理由是什么,说一个行为是“应该”就是要指示人们必须去做该行为,这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所具有的意义。并且,说“应该从事行为”p还意味着如果人们在面临该规范性原则指示的情况下,最后并没有从事行为p,而是选择了其他行为,那么人们将会为此承担责任,受到负面的评价,即遭到谴责。正是因为当说“应该”p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人们在众多可选行为中一定要做p,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违背该规定而没有选择行为p,那么还要承担责任、遭受谴责,所以人们常常会认为,至少行为p须得是当事人“能够”做的,否则“应该”既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也给人们赋予了不必要的责任和重担。其次,当说一个人“能够”从事行为p,就是说这个人具备做行为p的能力,即他有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具备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掌握必要的知识,同时他还有机会通过利用、发挥上述能力从而完成该行为。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说一个人“能够”从事行为p的时候,这里的“能够”并不一定是为当事人所清楚知道的。瓦纳斯(Peter B.M.Vranas)就指出:“宣称行为人能够做某事并不预设他知道自己能够做该事。”②也就是说,即便有时候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具备了从事行为所必要的技术条件、知识水平、生理心理素质以及发挥上述条件的机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说他“能够”从事该行为。最后,当说“应该”和“能够”之间存在一种被称为“蕴含”的关系时,就是说如果人们确实肯定地断言“应该”从事某种行为,那么就必须肯定地断言,该行为就是人们“能够”完成的。 在对OIC原则进行了比较清楚的解读之后,我们下面有必要来讨论该原则是否正确的问题。初看起来,OIC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通过说出含有“应该”的规范判断来引导人们从事某种行为的时候,至少表明该行为是人们实际上能够完成,也就是说人们具备了完成该行为所需要的知识水平、技术条件、生理心理素质和恰当的机会,否则就是强人所难。例如,要求子女“应该”尽自己的能力照顾父母,这就是合理的,而要求所有的小学生“应该”学会解答高等数学难题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前者“应该”所要求的内容在被规约者的能力范围之内,而后者则并非如此。因此,也有学者将规范是否具有可行性视为判断规范是否合理的标准之一③,这实际上就是诉诸OIC原则。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还常常通过诉诸OIC原则的一种变形原则来使得自己免于某种义务,而这种做法往往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④。例如,一个人路过河边发现有儿童落水即将溺毙,我们往往作出规范判断说:“你应该下河拯救落水儿童。”但是,如果这个人回应说“我不会游泳,这使得我不能够下河救人”,那么人们往往认为他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从而使得自己免除了下河救人的义务。在这里,人们认同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一个行为是当事人不能够完成的,那么完成该行为就不是其义务。该原则实质上是OIC原则变化了的等价形式,即“应该”蕴含“能够”和“不能够”蕴含“并非应该”具有逻辑上的等值关系。因此,当人们认同此人将“不能够”作为理由来否认自己有“下河救人”的义务时,实际上也就认同了OIC原则。 然而,仍然有不少人对OIC原则持有否认的态度,而且其理由也颇令人信服:首先,虽然在有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能够完成某行为,但是仍然不妨碍该行为成为义务。例如,张三承诺9点在学校会见李四,但是他到了8点55分才从20公里之外的家里出发,这时他已经“不能够”兑现承诺,但是这仍然不妨碍人们认为他“应该”在9点到达学校。可见,作为OIC原则的逻辑等值式“‘不能够’蕴含‘并非应该’”并不成立,因此OIC原则也是不正确的。其次,假设有的人原本既“应该”也“能够”从事行为p,但是为了让自己免除从事行为p的义务,他甚至可以通过使得自己处于“不能够”的境地,从而使得自己不再“应该”从事行为p。因此,坚持OIC原则容易为有些人大开逃避义务的方便之门。 对于上述反驳意见,学者们可以给出下面的解答:第一,当人们通过使用“应该”来指示行为的时候,该应然性判断只是指引人们在实际活动中,在面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时,必须要去做某一特定的行为,因此该规范判断指示的行为必须是人们“能够”做的,否则就是强人所难,无法实现其引导行为的目的。但是在上述例子中,张三在8点55分的时候已经“不能”完成原来“应该”的行为,这时如果他问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坚持说“你应该9点到校”,因为当张三不“能够”的时候,9点到校的义务已经因为无法实现而终止。所以,汉德森(G.P.Henderson)就提出,在人们已经“不能够”的时候,原本的应然性判断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义务已然终止,因此再坚持说当事人仍然“应该”去做他已经不能完成的事情是不合适的⑤。第二,当张三因为拖拉而到8点55分才出发的时候,他确实已经不再有兑现承诺的义务,但是有时候人们还是可以对他说“你应该及时到达”,这时的“应该”已经不再具有引导行为的意义,而是被用来谴责。也就是说,虽然当事人因为“不能够”而使得原来的义务终止,但是如果该“不能够”是当事人有过失地或者故意造成的,那么人们还是会通过再次强调之前的义务来对他们予以谴责(这时当说“你应该及时到达的”时,其含义等于“你本应该及时到达的”这样一个含有谴责意味的句子),而不是坚持要求他在“不能够”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去履行原本的义务⑥。第三,虽然当一个人因为“不能够”而无法完成义务从而使得原义务已然终止,但是如果是行为人的过失或者故意造成了这一状况,那么人们虽然可以说他已经没有原来的义务了,但是一方面他会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没有履行义务而付出代价(承担道德或法律责任等),另一方面他必须为此作出补偿,承担新的他目前“能够”完成的义务⑦。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责备张三因为其过失而导致不能完成义务,另一方面可以考量一下张三目前“能够”做什么,然后提出诸如“你应该打电话向李四致歉并请他稍候”这样的应然性判断,从而赋予其在该情境下的新义务。可见,每一个用于表达“义务”的“应该”都必须要蕴含行为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能够”。 二、OIC原则与义务的形成 根据OIC原则,所有义务都只能指示人们实际上能够完成的行为,因此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超越被规约对象的能力,去制定那些给人们增加不必要负担的规范。也就是说,在制定义务的时候,我们是以人们的实际能力为参照,在人们能够从事的若干行为中选择一个或者一组作为义务。因此,在OIC原则的支配下,“义务”是在关于人们能力的权衡中产生的。但是,有的学者对义务的这种诞生模式是持反对意见的——“义务”不是在考虑人们能够做一些什么的行为中产生,而应该根据“美德”来产生。例如,根据“勇敢”的美德,士兵就有了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义务;根据“节制”的美德,人们就有了厉行节约的义务;根据“诚实”的美德,人们就有了说真话的义务。因此,在确定“义务”的过程中,人们不是要考虑当事人实际上能够做些什么,而始终应该以“美德”为参照标准。例如,即便所有的士兵不具备特定的生理、心理素质而不能做到奋勇杀敌,但是仍然不妨碍我们可以根据“勇敢”的美德制定一条“士兵应该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义务。即便债务人“不能够”按时偿还债务,但是根据“诚信”的美德,他依然有偿付债务的义务。照此看来,即便有的时候并不“能够”,但是根据“美德”,有的行为仍然是人们的“义务”。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并在最近这几十年继元伦理学之后复兴的美德伦理学的观点大致就是如此。而上述观点显然对OIC原则构成了很大的挑战——“能够”不再是“义务”的必要条件,“不能够”也不再成为“义务”诞生的障碍。 上述两种看法分别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义务”形成的不同方式:前一种方式认为“义务”是在人们“能够”做的行为中予以甄选而产生的,因此“能够”是“义务”形成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形成方式下,OIC原则是有效的。后一种方式认为“义务”是参照“美德”形成的,与人们是否能够完成相应的行为没有直接关系。在这种形成方式下,OIC原则是无效的。可见,OIC原则的有效性问题和“义务”的形成问题密切相关。作为OIC原则的反对者,科克斯(John Kekes)认为“义务”不应该在人们实际上“能够”做的行为中进行甄选而形成,而应该在关于基本道德品质的支配下诞生。他举例说,在《苏菲的选择》这个故事中,苏菲原本应该在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被拯救,但是由于她心理遭受极大的压力而越发软弱,已经不能够在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活着而另一个去死,因此她最后放弃了选择而导致三人一同赴死。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不乏这样的案例:精神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而残忍地虐待他人⑧。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如果认可OIC原则的话,因为苏菲不再能够选择、精神病人无法控制自己虐待他人,所以“坚强地选择拯救一个孩子”、“善待他人”就分别成为他们不能够完成的行为,从而也就不能成为他们各自的义务。但是事实上,“一个有理性的人……可能会认为,善良和坚强的人在道德上显然好于残忍和软弱的人……类似地,我们也愿意要我们的孩子、朋友、老师和政治家是有德性而非邪恶的”⑨。因此,我们总是希望苏菲能够坚强起来选择一个孩子被拯救,也希望即便是精神病人也能够保有最基本的“善良”品质而不要虐打他人。虽然苏菲和精神病人确实“不能够”,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拯救孩子”和“不虐待他人”依然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拥有“美德”总是好的。特别是放眼现实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在实际的道德教育中,人们总是首先教授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善良”、“勇敢”、“节制”和“勤劳”等等,然后再告诉受教育者根据这些基本道德品质“应该”做一些什么。因此,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告诉人们要成为具有何种品质的人,并且鼓励他们通过完成在道德品质支配下的义务而确实地成为一个拥有这些道德品质的人。 在科克斯的分析下,OIC原则在涉及“义务”形成的问题上确实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坚持OIC原则而在诸“能够”中确定义务,那么就会出现合义务但是却违背美德的情况,这看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尝试着分析如下: 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美德”为什么看起来如此重要以至于优先于“义务”?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美德伦理学的观点就会发现,该学派关于“美德”的理解具有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倾向,认为“美德”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现实的道德义务的制定应该以这些客观存在的“善良”、“勇敢”、“节制”、“勤劳”等美德为根据——正是因为行为“分有”了上述美德,所以它成为人们必须要完成的义务。然而,如果我们回归现实生活,就会发现“美德”其实是人们在完成“义务”之后获得的。人们首先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中确定“义务”是什么,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遵守OIC原则,在“能够”的行为中确定义务——人们必须考虑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具有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生理心理素质以及为完成该行为而需要的机会等。在人们确定义务之后,就会通过得出一些含有“应该”的规范判断来指示大家去从事相应的行为,即赋予义务。由于在制定“义务”的过程中,人们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在通常情况下普通人的能力,因此一般来说,这些规范指示的行为都是人们能够完成的,而一旦人们按照规范的要求完成了自己的义务,那么人们就相应地具有了某种“美德”。例如人们通过考察一般人的实际能力而得出“应该厉行节约”的义务,而当被规约者实际地服从该规范的指示而采取节约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说他拥有了“节制”的美德。因此,“具有美德”实际上是在人们按照义务的要求从事行为之后而获得的积极评价。相反,如果人们没有完成义务,不管没有完成的原因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够完成或者是行为人能够完成而故意不完成,那么他们都不会被评价为是有美德的人。由于人们规定义务总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幸福、和谐和美好的生活,因此最后被评价为有“美德”的人往往也确实通过完成义务而促使这些目的的实现。相反,那些没有被评价为拥有“美德”的人往往也没有完成义务从而不利于上述目的的实现。久而久之,当人们逐步脱离实际的“义务”来考察“美德”,就会认为“美德”(而不是人们实际从事的义务行为)是和人们的目的——幸福、和谐和美好的生活——最直接相关的东西,甚至其本身就是作为目的最值得追求的,因此“美德”就被视为最为重要的、人人都应该普遍具有的东西,人们世代相传的美德教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可见,实际上“美德”并不优先于在OIC原则支配下的“义务”,而是在不断地就人们对“义务”予以履行而展开评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不是“美德”规定“义务”,而是“义务”产生“美德”。但是,这里的“‘义务’产生‘美德’”又有着特别的含义需要澄清:因为义务是关于人们行为的具有普遍性的指示,所以它涉及的必然是人们在通常情况下普遍具有的能力的考察。也就是说,人们根据OIC原则考察了普通人在理想状况下可能具有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生理心理素质以及为完成该行为而需要的机会等,然后确定了相应的义务,而各类“美德”实际上也是根据这些义务在具体的、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境下被完成的情况而逐步通过归纳、概括形成的。 因此,既然“美德”涉及的是在理想状况下人们能够完成的“义务”,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现“不能够”的情形时,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完成理想状况下能够完成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美德”。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人们总是存在一些能够做的事情,而在这些事情中就可能存在当前的义务,那么只要竭尽所能完成了此时应该做的时候,那么人们尽管因为没有完成理想状况下的义务而没有具备相应的“美德”,但是毕竟还是完成了此时此刻的“义务”。例如,根据人们通常的能力,我们提出“见义勇为”的义务,并且完成这一义务可以被认为拥有“勇敢”的美德。如果在某一特殊情境中,一位伤残人士没有能力参与与歹徒搏斗的行为从而不能“见义勇为”,但是根据OIC原则,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还是可能存在相应的义务(毕竟还有一些事是他能够做的,例如拿出手机报警),只要他做了该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他没有“勇敢”的美德,但是总的来说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义务。现在如果我们根据“美德”提出,即便这位伤残人士不能够,但是他还是有义务要与歹徒搏斗,那么显然这就为当事人设置了不必要的负担。因此,“美德”往往与理想状况下的“义务”相契合,提倡“美德”的目的是要求人们在每一个符合理想条件从而“能够”的时候都要从事相应的“义务”,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当人们不具备理想状况下的能力从而无法完成相应的义务时,根据OIC原则,我们在此时只能存在能够完成的义务。只要完成了,那么尽管我们没有“美德”,但是却也尽到了此时的义务。相反,如果抛弃OIC原则而仅仅根据所谓的“美德”来确定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的义务,那么人们就可能会“应该”从事自己实际上无法完成的行为,从而背上过于沉重的道德负担。 三、OIC原则与义务的不履行 上面的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既然“美德”是在人们理想状况下能够从事的义务中产生的,而在实际特殊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因为现实的“不能够”而无法履行理想状况下的义务,那么只要完成了现实“能够”从事的义务,尽管我们没有“美德”,但是毕竟还是尽到了义务。上述观点很容易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对人们来说首要的不是“美德”而是“义务”——只要人们完成了现实中“能够”从事的义务就完全可以聊以自慰,那么一方面人们就没有动力和理由来追寻“美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促使自己陷入“不能够”的境地而规避原本的义务,代之以从事一些自己愿意而又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义务,并且对此还很心安理得。 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不是从“美德”出发而是从OIC原则出发来制定义务,那么确实在实际生活中会遭遇上述尴尬的局面。例如,如果我们不是从“诚信”的原则出发规定“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偿还债务”,而是根据OIC原则认为在不能够偿债的情况下,只能在当前“能够”的行为中确定义务并要求债务人从事之,那么只要债务人确实从事了这一行为,我们似乎也得承认他算是尽到了义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窘境:债权人受到了损失,债务人完成了自己的义务,美德此时不在场,人们似乎无可奈何。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尝试着通过分析“义务”不能够被履行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来解决上述问题,这一话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初步涉及,现在来详加讨论。 根据OIC原则的逻辑等值式,我们可以承认,当一个行为不能够被当事人完成的时候,那么该行为就不是其义务。而相应地,根据OIC原则,此时的义务只能在当事人能够从事的行为中确定。但是,当一些初始义务成为当事人不能够完成的从而需要变更实际义务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根据OIC原则作出如上推理就草草了事,还需要进一步对初始义务“不能够”被履行的原因展开分析: 首先,人们通常诉诸的“义务”是在理想状况下,考虑到普通人一般具有的能力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因此这时所谓的OIC原则中的“应该”是针对通常、普遍情况下人们的能力而言的。但是具体的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除了存在满足理想状况下的“能够”之外,还可能出现特殊情况下的“不能够”,而且这种不能够往往还是人们无法控制、无法避免的。借用法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当事人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出现而导致实际上的“不能够”从而无法履行初始的义务。例如前面我们举过例子说,有的人本身就是不会游泳,完全没有能力履行“下水救人”的义务。再比如有的人天生精神有问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那么很可能无法自控地伤害他人,无法履行“善待他人”的义务。与他人约定9点见面,虽然当事人留出足够的时间,在7点就提前开车出发,但是由于路上突发交通堵塞还是不能准时到达,因此也不能够履行“守约”的义务。在上述种种情况下,都是出于当事人并非源自主观的故意而造成的“不能够”从而无法履行义务。更准确地说,根据OIC原则,在上述情况下,他们因为“不能够”,而使得原本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义务”了。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向我们询问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而我们还坚持宣称那些原本他们已经不能完成的行为才是当下“应该”去做的,那么就是强人所难,而所得出的规范性判断也无法实现引导人们去实践行为的目的。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因为非过失、非故意的“不能够”而无法完成原来的行为从而使得原本的义务终止,所以固然没有通过完成原来的义务而表现出“勇敢”、“善良”、“诚信”等美德,甚至还可能会带来一些恶果,例如儿童溺毙、无辜的人被伤害、浪费受约人的时间等,但是他们的“不能够”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并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以及受到惩罚。然而,在原本的义务因为“不能够”而终止之后,还会有新的义务产生,即在当事人目前“能够”做的事情中,总有一个或者一组行为是目前的实际义务,而该义务往往是指“通过从事一些目前能够做的行为来对之前因为无法履行义务而可能导致的恶果作出预防或者补偿”。上述三例中,可以说:“尽管当事人不会游泳,但是他有义务帮忙报警或者呼喊会游泳的人来救助;尽管精神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但是他有义务道歉、赔偿医药费、请监护人看管好自己;尽管邀约人意外堵车,但是他有义务及时打电话致歉并作出适当补偿。”而上述种种义务都是当事人当前能够完成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会对此表示不满,例如布朗(James Brown)就撰文指出:“包含‘应该一能够’原则的理论会允许行为人免于被责备,但是也会因此剥夺我们解释对某些状况表达道德上的不满意的明显方式。”⑩但是,在笔者看来,当一个行为人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导致“不能够”从而不能履行义务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对之加以责备和惩罚,因为责备和惩罚的目的在于惩前毖后并让受惩者因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但是在上述情况下,一方面当事人的“不能够”并非本人的过错造成,所以谈不上对之付出代价,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不能够”不可避免,“惩前毖后”的目的其实也无法实现。当然,虽然我们内心也会认为,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按照义务的要求来做,但是这时我们与其说是在责备当事人,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遗憾——要是他们果真能履行义务就好了,通过表达这种遗憾,我们实际上是在告诫他人和自己,为了保证义务能够被及时履行,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不能够”,当义务摆在面前而我们又确实能够做,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履行之。 其次,有的时候,当事人确实也会因为自己的过失甚至是故意促使自己“不能够”从而导致义务不能履行。与上述“不可抗力”导致的客观的“不能够”相比,这种“不能够”乃是当事人主观上的疏忽或者恶意而产生的。例如,张三本以为自己能够在半小时之内顺利到达学校,所以到8点半的时候才出门,但是在路上遇到堵车不能按时到达,这时张三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导致义务不能履行。有的债务人故意转移、挥霍自己的财产,导致自己不能够按时还债,这是当事人故意让自己处于“不能够”的境地从而导致义务不能履行。在上述情况下,一方面,与前一种情形类似的是,由于当事人事实上已经处于“不能够”的境地,因此根据OIC原则,在此时原本的义务由于他无法完成而已经终止,就是说他确实通过使得自己处于“不能够”的境地而成功地使得自己摆脱原来义务的约束,并且因为他没有履行该义务而确实没有获得相应的“美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指出,和前一种“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够”不同,这种“不能够”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过失或者故意造成的,也就是说这种“不能够”本来是可以避免从而原义务本是可以被履行的,因此这时当事人就必须为原义务没有被履行的后果承担责任并受到惩罚。就上述一例来说,当债务人故意挥霍财产而导致不能还债的时候,如果我们考虑他此时的“义务”是什么,那么当然无法再说他应该还债,因为此时这一义务已经不具备操作性,提出它的目的也不再能够实现。但是,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债权人经济受损、扰乱经济秩序等,却需要债务人对之负责并遭受惩罚(被指责、受到拘役、管制或徒刑等)。并且,除了遭受各类惩罚之外,根据OIC原则,他在此时有一些事情可以做,而在这些能够做的事情中会存在一个或一些行为是义务,例如赔礼道歉、通过劳动赚钱还债等,而这些行为就成为当事人此时的义务。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上述两种情形:不论是出于“不可抗力”还是行为的过失或者故意而导致的“不能够”,根据OIC原则,当事人初始具有的义务都会因为不能够履行而终止,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事人不需要为此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遭受惩罚,而后一种情况下当事人确实要承担责任、遭受惩罚。但是无论在上述何种情况下,当原本的义务因为不能履行而终止时,如果这时候人们考虑他们当前义务是什么,往往是首先考察他们目前能做一些什么,然后在这些行为中制定出新的义务来代替原本已经不能完成的义务以作出补偿。 因此,认为如果坚持OIC原则就会导致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使得自己“不能够”而摆脱义务,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考虑因为过失或者故意促使自己陷入“不能够”而导致无法履行义务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会采取上述措施,并且还随之提出,当一个旧的义务终止之后,总要有一个新的义务来替代旧的义务作为补偿。因此,如果我们认可并执行上述做法的话,那么这恰恰证明OIC原则是可接受的(11)。 [收稿日期]2013-05-15 注释: ①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②Peter B.M.Vranas:"I Ought,Therefore I Can",Philosophical Studies,2007,vol.136:170. ③徐梦秋等:《规范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47页。 ④可参见Terrance McConnell:"Ought" Implies "Can" and the Scope of Moral Requirements,Philosophia 19,1989,pp.438. ⑤可参见G.P.Henderson:"Ought" Implies "Can",Philosophy,Vol.41,No.156(Apr.,1966),pp.106. ⑥可参见Walter Sinnott-Armstrong:"ought" Conversationally Implies "ca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93,No.2,(Apr.,1984),pp.250-251. ⑦可参见Peter B.M.Vranas:I Ought,Therefore I Can,Philosophical Studies,2007,vol.136:181-182. ⑧⑨John Kekes:"Ought Implies Can" and Two kinds of Motality,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34,No.137 (Oct.,1984),pp.459-460、pp.460. ⑩James Brown:Moral Theory and The Ought--Can Principle,Mind,New Series,Vol.86,No.342(Apr.,1977),pp.217. (11)可参见Frances Howard-Snyder:"Cannot" implies "not ought",Philosophical Studies,(2006)130,pp.238.标签:不可抗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