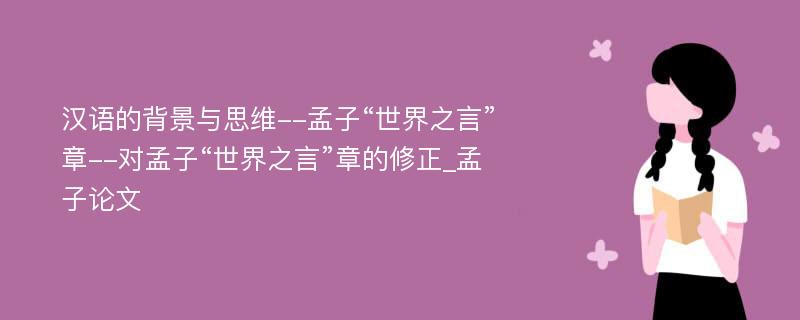
話語背景與思考坐標:孟子“天下之言性”章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之言论文,背景论文,天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國文化史中,孟子始終以其性善論著稱于世。但頗爲吊詭的是,遍翻《孟子》七篇,除了《滕文公》一篇以介紹口氣提到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之外,幾乎見不到孟子關于性善思想的正面言說;即使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孟子·告子》上)一章,也是通過對當時各種人性觀點的評論並藉助對其弟子公都子所轉述的自己思想觀點之概括加以表達的。但另一方面,孟子正面論性的文字卻又從來不提善,由于字義訓解上的問題,從而也就成爲自東漢趙岐以來始終未得到確解的一段文字。所有這些,都表明孟子似乎是在有意識地回避對性與善關係的正面言說。這種回避,不僅構成了其性善論形成上的一段秘密,而且也是以後的人們在面對性善論時不得不加以深思的問題。 由于筆者曾對孟子的“乃若其情”一章粗加訓解①,並認爲這一章實際上就代表著孟子對性善論尤其是性之所以爲善思想的正面言說,因而對于其專門討論人性的“天下之言性也”一章也就不能不加以說明。因爲如果說“乃若其情”一章是孟子對人性之所以爲善的正面言說,那麼“天下之言性也”一章雖然是其對當時各種人性觀點的一種評騭,畢竟也涉及性善論的主體——人以及如何認識人性的問题,從而也就等于從主體性的角度更加凸顯出人性的本善指向。 一、對前人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孟子對人性的論述首先是以評論時人的各種人性觀點的方式展開的: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無所事也。如智者亦行其無所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速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 從其所含攝的主題來看,這一段無疑也可以說是孟子對人性的一種正面論述,但卻完全是通過對當時各種人性觀點的評述與批評加以表達的。孟子這種方法當然可以說是以反顯正或包含著以反顯正的涵義,但由于其中的“則故而已矣”與“苟求其故”以及“以利爲本”諸說一直無確解,所以纔造成了以後的各種紛紛之論。 最早對《孟子》進行注解的是東漢的趙岐,他對這一章注釋說: 言天下萬物之情性,常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也,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于無事之處,則爲人智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載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② 趙岐的這一注解,如果僅從其對字義的理解來看,應當說是基本正確的,但卻存在著相互矛盾之處。而其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他以“天下萬物之情性,常順其故則利之也”來注解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一說,造就明顯地改變了孟子的話語背景——將孟子明確的否定性用語改變爲完全肯定的說法了,從而誤認爲造就是孟子關于人性的正面立論。至于其引用“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一說,則顯然屬于告子的觀點。所以,當他以“故常”來注釋孟子對日月之運行的“苟求其故”一說時,對字義的理解雖然正確,但卻用錯了地方,從而也就成爲一種與孟子完全相反的涵義了。這就開了一個錯解之端,因而也就開啟了以後的各種紛紛之論。 在理學中,由于朱子一直被視爲兩宋理學之集大成,而其《四書集注》又是宋元以後影響最大的著作,所以朱子的注解對于以後的各種觀點往往具有一定的定向與範導作用。讓我們先看朱子的注解: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而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也。③ 朱子這裏一方面以“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來表示“性”,復又以“已然之迹”表示“故”,這樣一來,“故”與“性”也就成爲一種表現與被表現的關係了。如果稍微熟悉朱子哲學,也就可以看出這種表達實際上正是其形而上之理與形而下之氣關係的一種直接移植,雖然這種移植在表達“性”與“故”之形上與形下關係上有其合理性,但卻未必就能緊扣孟子這裏言“性”與“故”的語境。因爲當朱子以“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來詮釋孟子對“天下之言性也”一句的評論時,實際上也就等于是把孟子帶有明顯否定涵義的反說之話變成一種正面立論了,所以就有“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這種對“性”與“故”之完全肯定的說法。這樣一來,在朱子的詮釋中,無論是“則故而已”還是“苟求其故”乃至于所謂“以利爲本”,也就完全成爲一種反話正說的表達了。 由于朱子的巨大影響,所以此後雖然清代學者的學術立場總體上有异于朱子,但在對孟子這一章的注解上卻與朱子大體一致。比如焦循就注解說:“故者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④實際上,這也就像朱子一樣,完全將孟子評論當時各種人性論觀點的否定性用語一概作爲孟子的正面立論來理解了。 郭店楚簡出土後,由于其時代被測定爲戰國中期以前(起碼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而其《性自命出》一篇中又有許多正面論性的觀點,所以梁濤先生在充分總結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又結合楚簡的說法,從而對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提出了自己的詮釋。梁濤綜述性地翻譯: 人們所談論的性,往往不過是指積習而已。積習的培養要以順從人的本性爲根本,人們之所以厭惡智,是因爲用智的人往往穿鑿附會[不從事物本身出發]。如果用智的人能像大禹治水一樣,那麽人們就不會厭惡智了。大禹治水[順從水的本性,采用疏導的辦法],不有意多事。如果用智的人也不有意多事,那麽智的作用就大了。天極高,星辰極遠,如果瞭解它們的運行規律,千年之內的日至,坐著都可以推算出來。⑤ 梁濤先生的這一詮釋,除了他將“故”詮釋爲“積習”比較對應于孟子的基本原意之外,同樣從總體上背離了孟子的基本語境。因爲既然“積習的培養要以順從人的本性爲根本”,那麽對于“積習”來說,追究竟是一種肯定呢還是否定的態度?如果是肯定的態度,則顯然與孟子背反,因爲他没有看到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一句之明確的否定意向,或者說他雖然看到了卻並不以之爲基本語境;如果說是否定的態度,那他就不應當肯定孟子所明確否定的“智”與“穿鑿”,因爲無論是“智”還是“穿鑿”,實際上也都是對“積習”的一種“培養”或刻意開發,並且也是在“培養”的基礎上生成的。至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一句,梁濤先生則完全是一種肯定的態度。顯然,造就成爲對“故”及其“積習”表現的一種全面肯定的態度了。 但對于這一章,同樣爲梁濤先生所徵引的陸象山之理解反倒更能緊扣孟子的原意。從一定程度上說,就對孟子原文的理解而言,陸象山的理解反而可能是最接近孟子原意的。他解釋說: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于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随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爲本也。夫子贊《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⑥ 僅從象山“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爲本也”一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是真正理解孟子這一論述的評價。因而也可以說,從漢代到兩宋,對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没有比這一段解釋得更準確、更清楚的了。其準確性在于,象山明確地揭示了孟子這一論斷的思潮背景與話語氛圍,是即所謂“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顯然,這一評論正是對“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一句的準確說明;而其所謂“陳迹”一說,又是對“則故而已矣”之“故”的說明。僅從這一點來看,就知道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其實就是一種明確的否定性看法。其次,象山又準確地把握了“故與智”在當時儒道兩家思想中之共通性的運用,並舉出了《莊子》和《周易》的例證,以說明“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最後,象山又在準確理解孟子用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看似與孟子完全相反的說法,因爲孟子的“苟求其故(陳迹、故常——以往的曆法),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看起來似乎是一種明確肯定的說法,實際上則是一種否定性的表達,以從反面說明“不可求其故也”。原因在于,“治曆明時,在革之象”,且“曆本测候,常須改法”——曆法本來就是在不斷變化的,如果一味“苟求其故”,那就只能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一樣,成爲一種一味求之于陳迹、求之于老黄曆而又全然以利害爲本的“推說”之論了,所以他明確申明:“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原因詳後)至此,孟子評論“天下之言性也”而對“故”與“智”之批評也就成爲其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了。 在這裏,如果說陸象山前面的理解與孟子基本一致,那麽其後面一句看起來似乎是完全與孟子相反的表達何以說是準確理解了孟子的原意呢?這是因爲,孟子這一章主要是在批評時人完全以“故”與“智”來理解人“性”的思想,而“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一句則正是從“故”(所謂老黄曆)的角度來推算“日至”的,而在“曆本測候,常須改法”——曆法不斷變化的基礎上,這種“苟求其故”能求到哪裏去呢?所以說“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這樣一來,孟子這一章也就成爲既反對以“故”與“智”論性,同樣也反對僅僅以“故”來求“日至”了。顯然,所有這些說法,既是孟子所批評的對象,當然也是孟子人性論思想出場的基本前提。 陸象山之所以能够破解這一逾千年的謎團,除了其對孟子思想與當時的思潮背景和話語氛圍有準確把握外,還因爲其擁有豐富的曆法知識;而最爲重要的一點,則在于他對當時各種時論之弊端有準確認識。比如僅就其對孟子思想的理解來說,他就明確指出:“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⑦又說:“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是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⑧顯然,這裏所謂的“求血脉”、“看意旨”等,其實都是“解字”之外的工夫。 二、孟子論性的話語背景與思潮氛圍 那麽,在兩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陸象山何以能够獨得孟子之心要呢?個中的關鍵就在于其對孟子的研究並不是以“字義”爲主要對象,也不是一味地在所謂“文義”上著工夫,而是以求其“血脉”、探其“意旨”爲根本指向的,因而他曾自述,其一生的學問也就在于“因讀孟子而自得之”。⑨而這種“求血脉”、“看意旨”式的研究,首先也就體現在他對孟子論性之話語背景與思潮氛圍的充分理解中。 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而子貢又發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的感慨以來,七十子之徒無不以“性與天道”爲窮高極微之論。而其探索的具體表現,也就集中體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土的《性自命出》一文中。比如: 凡人雖有性,心忘奠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奠。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⑩ 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凡性或動之,或逢之,或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之,或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逢性者,悅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22) 郭店楚簡的入葬時間大體被測定爲公元前300年之前,因而孟子當時是完全有可能見到上述各種人性觀點的;即使未曾見到,作爲一種時代性的思潮背景或話語氛圍也無疑是孟子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說,郭店簡中大量的人性論觀點其實也就應當是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所以形成的思潮背景,尤其是其“凡性或動之,或逢之,或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之,或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逢性者,悅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等種種說法,也就應當是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一說的針對對象。 如果人們尚不能認可這一推測性的說法,那麽《孟子》一書中告子關于各種人性觀點的概括與介紹也就完全可以看作是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的一種內證。比如當孟子與告子進行了一場人性之辯後,孟子弟子公都子就曾以轉述的口氣向孟子轉達了告子關于人性善惡的幾種較爲相近的觀點: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告子》上) 在公都子的這一轉述中,如果說孟子時代人們對于人性問題的探索有所深入,那麽這就主要表现在人們更加集中于“性”與“善惡”的關係問題上,也更加側重于對人性之善惡屬性或善惡表現的探討了,這當然也可以看作是郭店楚簡思想之先于孟子的一個證明。而這一證明同時也將成爲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所以形成的時代背景或話語氛圍。因爲孟子對于告子的上述說法完全是一種批判的態度(12),所以其“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一說也就包含著一種明確的否定意向。 如果人們仍不能接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之明確否定的句式和意向,那麽請看孟子在回答時人指責他“好辯”時的如下申明: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已,一治一亂……天下又大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 在這裏,從“天下之生久已”到“天下又大亂”乃至“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孟子的“天下”完全是指當時的實際情况而言的,也完全是作爲一種“天下無道”的負面形象出現的;至于孟子本人的儒者情懷、其繼承孔子著《春秋》的精神,也就主要表現在對“天下”的針砭與批判精神上。所以,他曾明確地自我定位:“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在這一背景下,孟子與莊子、告子的關係也就構成了一種最爲奇特的關係,也是最值得辨析的關係。一方面,告子與孟子曾展開過一場人性論之辯,並且也是孟子性善論思想的主要批評者,從其在人性論上的思想歸屬來看,雖然告子可以正面主張“性無善無不善”並列舉出“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以及“有性善,有性不善”諸說作爲佐證,但從其“生之謂性”的正面主張與“食色,性也”的舉例說明來看,告子的思想實際上更靠近于道家。(13)而當時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就曾明確地主張:“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莊子·達生》)因而他們二人也完全可以說是基本一致的自然人性論。就其關于人性論的基本主張而言,莊、告二位也可以說與孟子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但這種對立卻完全可以存在一種共同的話語氛圍,並且也只有在共同的話語氛圍中其對立纔能真正表現出來。比如就莊子而言,其自然人性論的觀點無疑是不言而喻的,但即使如此,要澄清其自然人性的觀點也必須對當時各種關于人性的流行性看法加以剥離,纔能凸顯出其自然人性的本色與真正內涵。比如莊子就在總論當時的各種人生典範時指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游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事,尊主强國之人,致功並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莊子·刻意》)在這一基礎上,莊子纔提出工作爲他之人生理想的“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同上)的自然人性觀。但即使如此,這種自然人性的觀點也仍然需要剥離各種因“故”之論纔能有所凸顯,所以莊子又說: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智)與故,循天之理……其寢不夢,其神純粹,其魄不羆,虛無恬淡,乃合天德。(《莊子·刻意》) 在莊子的這一申論中,聖人之所以能够“其寢不夢,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關鍵也就在于其能够“去知(智)與故”,所以陸象山纔認爲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一章“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意即只有在徹底剥離了“故”與“智”的基礎上纔能真正弄清孟子“天下之言性”一章的本意和底蕴。在這裏,儒道兩家所要剥離與澄清的總體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區別僅僅在于:道家是明確地以“智”作爲首先需要剥離的因素,這自然包含著其“離形去知”(《莊子·大宗師》)的關懷;而儒家則認爲“故”是必須首先加以剥離的因素,因爲“以利爲本”之“故”不僅是當時各種人性論思想的基本出發點,而且這種“故”也必然會從根本上蒙蔽人的智慧;而完全從“故”出發的“以利爲本”實際上又是其與穿鑿之“智”統一的基礎。這樣看來,雖然儒道兩家在人性論的具體觀點上是完全對立的,其對“故”與“智”的剥離次序也存在著先後之別,但卻仍然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話語氛圍,並且也有著大體一致的澄清方向。 在這裹,一個非常重要而且也極難辨析的問題就在于孟子曾明確地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僅從這一句本身來看,似乎完全可以說是一種正面肯定的用語,但陸象山卻明確地將這句話詮釋爲“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如果僅從字面意思而論,那麽象山的這一說法無疑是明顯地扭曲了孟子的原意。實際上,象山的詮釋不僅完全正確,而且也符合孟子的基本精神。這就需要孟子的“以意逆志”方法來進行具體詮釋。 “以意逆志”是孟子在解《詩》時所提出的一種詮釋方法,具體是指:“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餘。’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孟子·萬章》上)顯然,所謂“以意逆志”就是要跨越“文”和“辭”的限制以直接達到對作者之“意”與“志”的把握。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孟子的“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一句似乎完全可以進行正面與肯定的把握,但如果將其放在“天下之言性也”一章的總體背景——在剥離、否定“故”與“智”的總體背景下來看,那麼它實際上也就成爲一句完全表示否定性涵義的反話。所以,在象山引入了“治曆明時,在革之象”以說明曆法本來就在不斷變化之後,孟子所謂的“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一說也就完全成爲一種需要否定的作法了。這不僅因爲它本身就建立在“苟求其故”——與整章意思完全背反的基礎上,而且從“苟求其故”出發的“坐而致”也由于脫離新曆法,因而也就無法得到符合新曆法的“日至”了。(14)所以說,陸象山的詮釋看起來似乎與孟子的原話完全相反,實際上卻真正堅持了孟子“去故與智”的精神。這也是其“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一說對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基本宗旨再闡發的具體表現。 退一步看,如果我們先假定孟子“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確實是一種明確肯定的說法,那麽這種“肯定”卻必然會遭到來自孟子文本的反駁。比如在孟子與告子關于人性之辯中,他們曾展開了如下一段對話: (告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孟子)曰:“耆秦人之炙,無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告子》上) 在這裹,所謂“求日至”的問題自然可以說就像“耆秦人之炙,無以异于耆吾炙”一樣,完全是一個客觀的認知(感受)性問題,所以孟子承認“夫物則亦有然者也”,這自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明確肯定的態度。但人性問題是否就是一個客觀的認知性的問題呢?而對人性的認知是否也就可以像“求日至”一樣完全可以通過客觀認知的方式來解决呢?從孟子這裏“然則耆炙亦有外與”的反駁來看,他顯然是不贊成這種完全通過外向認知的方式來解决人性問題的。(15)因爲“炙”固然可以說是一個客觀的認知性的問题,而“耆炙”卻並不是一個客觀的認知性問題;至于“耆”,則主要是一個我們內在需要的問題。很明顯,即使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一種明確肯定的說法,那麽這種外向認知性的肯定也仍然無法用來說明人性、認知人性;當然,話說回來,人性問題也根本不是這種客觀、外向的認知方法可以解决的。 在這一背景下,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無論是“則故而已矣”還是“苟求其故”之類的說法,實際上也都是以否定的涵義出現的;至于“以利爲本”之說,由于當時的各種人性觀點完全是從“故”出發的,因而其所謂的舉例說明、論證等等,最後也就只能以自“利”爲歸了。這樣一來,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實際上也就等于是對儒家性善論所以確立之一種清理地基的工作了。 三、去故與智:孟子論性的思考坐標 那麽,在“去故與智”的基礎上,孟子關于人性本善的主張又將如何確立、如何表達呢?實際上,這仍然要從對“故與智”的辨析與剥離出發。 “去故與智”雖然是象山對孟子人性論主張所以形成之思路的一種概括,但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孟子確立其性善論思想的剥離與排除標準也確實是沿著“去故與智”的方向展開的,這就構成了孟子論性的基本坐標。 “故”即“故習”或“故常之說”;“去故”也就意味著對“故習”與“故常之說”的一概剥離。那麽,確立人性爲什麽一定要通過剥離或排除各種“故習”與“故常之說”來實現呢?這主要是因爲,在孟子看來,“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很明顯,之所以要剥離“故”這種“故常之說”或各種習慣性看法,一方面是因爲“故常之說”本身就建立在經驗與習慣的基礎上,從而使人無法揭示並準確把握人性之本真;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如果一味從“故習”出發,最後也就必然會陷于“以利爲本”的結局。而一當對人性的揭示完全陷于“以利爲本”時,那麽這種人性觀也就必然會失去其標準的客觀性與人倫的普遍性,從而成爲一種人人各自爲說、各自爲戰的“上下交征利”之局,是即孟子向梁惠王所開陳的:“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焉。”(《孟子·梁惠王》上)顯然,在孟子看來,考察人性之所以不能從“故習”出發,不能“以利爲本”,關鍵也就在于這種完全從“故習”出發的人性探討必然會導致人倫觀念的混亂與人倫秩序的大潰敗。所以,當梁惠王以“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于吾國”爲問時,孟子也就直接地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來應對,這就明確地排除了“以利爲本”的人性取向。 對于“故”(16)以及完全從“故習”出發所導致的“以利爲本”取向,我們還可以從孟子所極力批評的墨家思想中得到證明。《墨經》云:“故,所得而後成也。”(《墨子·經上》)這說明,在墨家看來,所謂“故”實際上也就是使某事物得以成立的條件,相當于孟子在與告子關于人性之辯中所提到的“其勢則然也”的“勢”。何以會如此呢?孟子舉例說:“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顯然,在孟子看來,如果完全以墨家的“故”爲出發點來確立人性,那麽這種人性就不可能是人的本真之性,而只能是建立在各種“勢”的基礎上對人性扭曲的相對性認識,或者說也就是人性的暫時性或相對性表現;而在各種“勢”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也就只能促使人們各自以利爲本、以利于己說爲歸了。孟子之所以認爲“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正是因爲他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故”在認知上的相對性與暫時性以及其在發展方向上的利己取向。 對于這種建立在“故”與“勢”基礎上之“以利爲本”的人性取向,我們還可以從墨子對其“兼愛”主張的論證中得到一個有力的反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异,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愈)越人,愛魯人于(愈)鄒人,愛我鄉人于(愈)魯人,愛我家人于(愈)鄉人,愛我親于(愈)我家人,爱我身于(愈)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于我。故有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 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 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我將以告人。” 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悅)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悅)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悅)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悅)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悅)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悅)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悅)子欲殺子,不說(悅)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子)之身者也。”(《墨子·耕柱》) 在巫馬子與墨子的這一對話中,墨子的邏輯顯然就是典型的從“故”出發,並且也是明確地堅持“以利爲本”的。由此來看,雖然墨家的“兼愛”主張是建立在極高的道德熱情與救世主張的基礎上,但其在這襄的論證方式卻是標準的“故”與“利”的統一,無怪乎墨家最後會以功利主義爲歸宿。孟子就生活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時代,其“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無疑就包含著對墨家的批評。而孟子的這一批評,實際上就是要剥離“故”與“勢”包括現實生活中各種在“以利爲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威脅和利誘(比如墨子的“說(悅)子欲殺子,不說(悅)子亦欲殺子”之類),從而堅持從人性自身出發來對人性作出規定。 實際上,孟子本人就是一位剥離“故習”之說的大師,比如其爲了說明人人本有的惻隱之心,就對各種“以利爲本”的“故習”之說進行了層層剥離: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 在這裏,孟子爲了說明惻隱之心之人人本有的性質,特別例舉了一個“孺子將入于井”而人皆不能不起的“怵惕惻隱之心”的心理事實,以說明面對這樣的情景,只要是人,都必然會有一種不暇思索而又不能自己的“怵惕惻隱”心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人人皆能理解且都能够接受的心理實驗。但面對這種不能不起的惻隱之心現象,孟子卻必須進行一番嚴格的“故習”剥離:“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一句話,任何後天的、感性經驗的包括各種勢位的因素都不是惻隱之心產生的真正原由,這就說明,所謂惻隱之心實際上也就是我們人人本有的內在本質。所以,孟子也就可以反過來明確地斷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孟子對惻隱之心的這一逼顯過程,實際上也就是通過對各種“故習”因素的剥離實現的。 那麽,孟子何以一定要將“智”一並排除于人性觀點的確立之外呢?難道儒家人性論的確立不需要“智”嗎?這是因爲,“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因爲如果完全從“智”的角度來確立人性,難免就會得出穿鑿附會的結論來,上引墨子對其“兼愛”觀點的論證實際上也就完全是從一種取悅于人之“智”的角度來立論的,所以說是有失其兼愛情懷與救世精神的。因爲“智”的特點往往會使人以勝于他人爲自己的追求指向,這就必然會背弃人性展現之自然而然的本質。相反,“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無所事也。如智者亦行其無所事,則智亦大矣”。顯然,孟子對“智”的這種排除與否定,其所反感者,主要在于“智”所導致的穿鑿附會之病;而其所要高揚的,則恰恰在于人性(也包括人之“智”)展現之自然而然的品格,完全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强制、威脅或利誘,也不需要各種“智”來穿鑿附會地立說。 孟子人性展現之自然而然的品格與特徵,在其與告子關于人性之辯中表現得再典型不過了。請看他們的如下對話: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之性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告子關于杞柳與桮棬關係的舉例說明,既表明他對人性的理解,同時也表現了他對仁義的理解,所以,在其“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的比喻中,表明在告子看來,人性並不必然含有仁義,而只能說是後天教化的產物,一如對杞柳的加工製作纔能使之成爲桮棬一樣。按理說,這似乎是對人性的一種較爲理智的分析與說明。但在孟子看來,“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之性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顯然,孟子認爲,從杞柳到桮棬必然要經過一個加工製作的過程,而從人性到仁義則只能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展現過程(其實這正包含著孟子“仁義內在”的思想),一如“禹之行水也,行其無所事也”,所以說“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很明顯,告子對杞柳的加工製作、對人性的“戕賊”,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明顯違背人性之固有本質及其自然展現的穿鑿之見。因而,孟子之所以批評告子,主要是因爲其在從杞柳到桮棬、從人性到仁義之間加進了加工製作(所謂戕賊)的因素,對于人的本性來說,這當然是一種穿鑿之見。 這樣看來,孟子對人性的確立也就主要是通過“去故與智”的方式實現的,“去故”自然意味著對人性以外的諸種慣習性因素之盡行剥離;而“去智”則不僅意味著恢復人性之自然與本真,而且也必須按照人性之固有本質及其自然表現來認知人性、規定人性。從當時的思潮背景來看,孟子的“去故與智”實際上也就主要是針對楊墨兩家的人性主張而言的;但如果就思想指向而論,則剥去了“故”與“利”之後的本然、排除了“智”之穿鑿附會之後的自然而然,也就代表著儒家人性論確立的基本方向。所以說,從本然的本質到自然而然的展現方向,也就代表著孟子確立人性的思考坐標。 四、“天下之言性”章思路辨正 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也就可以弄清“天下之言性也”一章的基本涵義了,當然也可以看清前人理解之困惑以及其之所以困惑。 作爲歷史上第一位注釋《孟子》的學者,趙岐雖然準確地理解了“故”之“故常”的涵義,但由于他認爲“常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也”,因而他實際上也就等于已經肯定了關于人性的故常之說。至于“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一說,雖然在孟子的語境中也不能算錯,但由于其通過“改戾其性,則失其利也”明確肯定了故常之性的出發點,因而也就只能將孟子推向告子一邊了。所以,其結論也就只能沿著故常之性的路徑前進,認爲“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載日至之日,可坐知也”。很明顯,在肯定了“故常之性”的基礎上,趙岐也就只能走向告子一路了。 朱子雖然以“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來表示“性”,復又以“已然之迹”表示“故”,從而使“故”與“性”成爲一種表現與被表現的關係。但由于他將這一切完全納入到自己的理氣關係中來理解,認爲:“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這樣一來,朱子也就不僅以其理氣關係重新詮釋了“性”與“故”的關係,而且還將孟、告、荀在其理氣關係之形上形下相區別的基礎上混一起來了。也就是說,在朱子看來,必須通過作爲“已然之迹”的“故”來認識作爲“人物所得以生之理”的“性”。在孟子的視域下,這也就等于同樣走向告子的觀點了。 至于梁濤,雖然他引用了郭店楚簡的新材料,並明確指出“人們所談論的性,往往不過是指積習而已”,這說明梁濤先生對于孟子論性的話語背景是基本瞭解的。但由于他一轉手又認爲“積習的培養要以順從人的本性爲根本”,而完全無視孟子“故者以利爲本”之明確的否定意向,因而也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孟子所明確否定的“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一說的基本立場,從而使孟子轉到告子和荀子的立場上來了。至于作爲其結論的“如果瞭解它們的運行規律,千年之內的日至,坐著都可以推算出來”,也就完全成爲荀子“苟求其故”基礎上“勸學”的口氣了。(17)對人而言,勸學當然是必須的,但梁濤先生卻没有看到,他既然認爲“此兩個‘故’字應爲同義”(18),那就應當使孟子全章的涵義基本一致,而不應當形成前邊表示明確否定的“人們所談論的性,往往不過是指積習而已”,而到後邊卻又完全成爲梁濤先生自己建立在“積習”基礎上的“勸學”結論了。因爲在孟子這一總論“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的評論中,對“故”與“智”的否定和排除實際上也就代表著其批評“天下之言性”現象兩個極爲重要的理論分支或邏輯支撑點,既然孟子對“智”的肯定是通過“智”之自我否定(“若禹之行水也”——“行其無所事也”)實現的,那麽孟子究竟從哪個角度轉向了對“故”的肯定呢?如果根本没有像“智”之自我否定一樣的過渡,那麽無論是其前面對“故”的否定還是後面對“故”的肯定,實際上也就都是一種無根的說法。 這樣,孟子的人性規定究竟是什麼呢?從告子對孟子“以人性爲仁義”的概括到孟子對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的反問來看,孟子的人性就應當是以“仁義”爲內在本質的道德善性。所以他纔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又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盡心》上)所有這些說法,既符合其評論“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的“去故”主張,同時也符合其“言性”必須“去智”之自然而然的特色;而《滕文公》篇所概括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說,起碼應當是一個孟子並不反對的結論。 但孟子卻始終没有將性與善直接聯繫起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墨家完全從“故與智”出發對其“兼愛”主張進行論證的前車之鑒;而一旦性善也成爲一種論證或理論成說,也就必然會蛻化爲一種“故”,退化爲一種“所得而後成也”的手段,這就必然會造成性、善關係的“故習”化,也顯然是違背性與善之本質性關聯的。另一方面,孟子在舉例說明“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時所展開的三層剥離,“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一句話,任何後天的、感性經驗的包括各種勢位的因素都不是惻隱之心產生的真正原由,那麽這就說明,人性之善及其相互的本質性關聯絕不是一種可以隨意選擇的理論說法,而是一種具體場景(如見孺子之入井)中當下抉擇並當下承當的絕對命令。所以,人性之善與不善、惻隱之心究竟是呈現還是不呈現,也都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辯說的問题(通過理論辯說反而只能增加人們在言說時的種種“故習”),也根本不是理論辯說所能解决的問題,更不是因爲人們在理論上承認性善就能够在生活中承當善、踐行善。而性之善與不善,既不會因爲人們的普遍贊成就增加其價值,當然也不會因爲人們理論上的否定就減損其價值。 所以,也許正是考慮到性善論的“故習”化或“成說”化,纔使孟子始終不談性與善的直接關聯,而寧願將這一問題交給人們在實踐生活中去具體抉擇、具體印證。這當然也就包含或表現爲所謂“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的不同抉擇了。但因爲人倫生活、人倫文明及其秩序都不能離開善,所以孟子纔不得不以“仁義禮智”之“四端之心”的方式來對善進行具體言說;至于人性,他寧願讓人們在“盡心”的實踐中去具體地“知性”,也不願從理論上直接對人性作出“善”的規定與說明。在筆者看來,理解了這一點,就理解了性善論的真諦,也就理解了孟子始終不正面言說性善的秘密。 註釋: ①丁爲祥:《孟子“乃若其情”章試解》,《人文雜誌》2013年第9期。 ②趙岐:《孟子注》,轉引自焦循:《孟子正義》卷八,《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第344~346頁。 ③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長沙:岳麓書院,1985年,第370~371頁。 ④《孟子正義》卷八,《諸子集成》第一册,第344頁。 ⑤梁濤:《竹簡〈性自命出〉與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4期。 ⑥陸九淵:《語錄》上,《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15頁。 ⑦陸九淵:《語錄》下,《陸九淵集》,第444頁。 ⑧同上,第432頁。 ⑨同上,第471頁。 ⑩《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頁。 (11)同上。 (12)關于孟子如何批評告子的上述概括,請參閱拙作:《孟子“乃若其情”章試解》一文,這裹不能詳述。《人文雜誌》,2013年第9期。 (13)徐復觀先生推測:“告子‘生之謂性’的觀點,也與莊子的性論非常相近。孟莊同時而未常相聞,告子或亦是莊子之徒。”——《孟子知言養氣章試釋》,《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59年,第148頁。 (14)考慮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史記·秦本紀》),是即所謂“秦以十月爲歲首”,也就完全可以理解陸象山所謂“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一說的正確性了。 (15)關于孟子與告子在確立人性之認知方式的差別,請參閱拙作:《告子的“生之謂性”及其意義》(《文史哲》2007年第6期),該文對這一問題有較爲詳細的辨析。 (16)關于“故”字的義訓,筆者基本贊成本刊同期林桂臻先生的相關考論。林先生《〈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辨正》一文從《爾雅》的“治、肆、古,故也”與《說文》的“故,使爲之也”出發,認爲“故即古,古即故,古故互訓”爲“故”的原初義;而“‘故’字古書多訓爲‘舊也’”,則可以說是其拓展義;然後纔有《說文》“使爲之也”的引申義。至于筆者下文所引《墨經》的“故,所得而後成也”,則是“使爲之”義的進一步拓展,所以今天仍有“原故”一說。而孟子此處的運用,則主要是在“古故互訓”基礎上之“舊也”一層上取義,所以筆者既贊成趙岐的“故常”之說,也贊成朱子的“已然”與象山的“陳迹”之說。 (17)當然,梁濤先生的這一誤解也有其難以避免的性質,因爲這一句獨立成句,完全可以作爲獨立的語句來理解;如果不是陸象山“治曆明時,在革之象”的提醒以及對全章涵義的反復推究,筆者也未必能够看出這一句的真正涵義。 (18)梁濤:《竹簡〈性自命出〉與孟子“天下之言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