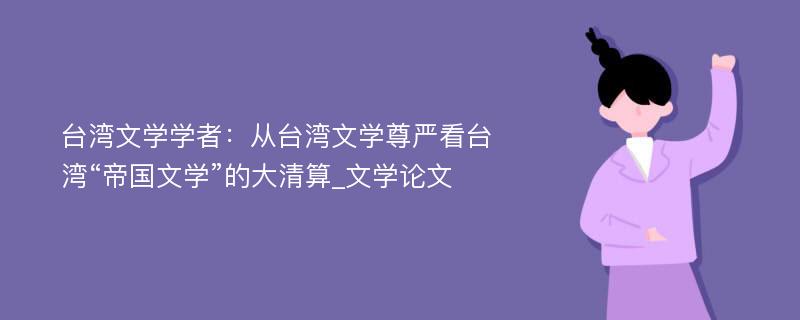
台湾学者论台湾文学——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从台湾文学的尊严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文学论文,尊严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良泽先生(以下简称为张氏)在2月10日的《联合报》副刊,5月10日的《民众日报》副刊,以及6月7日的《台湾日报》副刊上,连续以《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为名,辑译刊出了十七篇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以及三篇他对台湾皇民文学观点的文章。暂且不论其对台湾皇民文学观点的三篇文章,单以他所辑译的十七篇“台湾皇民文学作品”的内容来看,其中虽然有几篇尚可称得上“皇民文学作品”,其他则不是一般的中小学生作文,就是在战争体制下酬应时局的文章,实无从归为“文学作品”。倒是在颂扬日本的“大东亚圣战”,高倡“皇国精神”或誓言“为天皇赤子、一心报国”的主题或内容上,这十七篇“作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将之视为日本侵略战争时局下的“皇民文宣”,当更为切题。
身为第一所台湾文学系系主任的张氏,应该不会不懂得“文学作品”的基本要件,然而,他却“精心”选译了这样的内容与主题的文章,全冠之以“皇民文学作品”之名,在日报副刊上大大刊载;其著意,似乎不尽在“文学”的一面,而有“文宣”的一面;特别是在偏向的所谓“台湾意识”当道的时潮下,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文学史料的辑译了,它突出了打造“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的一面。这不是笔者个人的臆测,在他同时刊出的三篇关于“台湾皇民文学”的观点文章中,已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对于张氏的台湾皇民文学观的谬误的问题,笔者将另文批判。但无论如何,张氏处理“台湾皇民文学”的作为本身,已对台湾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淆惑与伤害,针对这一点,首先必须提出来讨论与批判。
一、对台湾文学造成了淆惑与伤害
由于日文的障碍以及对台湾的日据历史知识的不足,一般人(包括文学研究者)对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状况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更遑论对皇民文学的认识了。在这样的土壤上,张氏所辑译的十七篇所谓“皇民文学”作品在报纸大幅刊载,再加上他强调“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们,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这样的内容在大报章上的出现,对社会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它误导了一般读者,以为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的内容都与张氏辑译的皇民文宣一样,充满了歌颂日本大东亚圣战、高倡皇国精神的作品;且误认当时的台湾作家全都屈服在日本的殖民与军国体制下,积极配合日本当局的皇民文学政策,曲志节而阿权力地写了像那样的“台湾皇民文学”。结果,使一般人错以为在日据末期,台湾文学就等于皇民文学;甚至认为台湾皇民文学就是当时的台湾文学的全部。
这不但对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造成了甚大的淆惑和伤害,同时对于当时处于日本军国法西斯高压的文学环境下,凭着民族与文学的良知,以各种方式抗拒台湾文学沦为皇民文学的台湾前辈作家来说,勿宁是再度的羞辱。
二、为皇民文学的复辟铺路
另一方面,张氏的作为与谬说使当年原本以打压台湾文学而树立起来的台湾皇民文学,再度轻易地僭替了台湾文学的地位;从而掩盖了推动皇民文学的日本殖民与军国当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的文臣的罪行,最终是替当时积极地站在日本当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阵营的台湾皇民作家们涂脂抹粉,僭取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正当性。张氏的作为,与叶石涛先生最近发表在《民众日报》的一篇文章——《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注:参阅1998年4月15日的《民众日报》。)有异曲同工之妙; 叶文说:“周金波(按即皇民文学代表作之一《志愿兵》的作者)在‘日本’时代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一个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如果说张氏如此辑译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其居心,是想把所有的台湾前辈作家都贴上皇民文学作家的标签,来壮大皇民文学声势,使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正当化的话;那么叶文的“思考”,就是为台湾皇民文学作家脱罪。显然,两者都是与当年以打压台湾文学来推动皇民文学的主体者——日本军国殖民当局和在台日人御用文臣——的立场一致的;都是以当年的“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意识形态,来淆惑台湾文学,试图为台湾皇民文学在台湾文学史的复辟铺路。
本文认为,如果想要批判张氏的皇民文学观和澄清张氏此种作为所造成的对台湾文学的淆惑,揭穿其为皇民文学复辟铺路的意图,首要之处,不是在观念上打转,而是回到史实本身,揭开日据末期,日本的殖民与军国体制及其扈从者如何打压台湾文学以建立皇民文学的历史真相,以及在这压力下台湾作家所表现的抗拒与屈从的历史真貌;据此,才能辨识到到底谁才是台湾皇民文学的主体,从而认识到台湾皇民文学的性格,重新认识在这样的历史中台湾前辈作家可贵的抗拒,进而确认台湾文学的尊严。
必须在此先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台湾皇民文学”,实际上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作为日本军国当局的思想战一环的“皇民文学政策”,其次是日本在台湾的右翼文人的皇民文学思想与作品,其三是对前二者积极扈从的台湾皇民作家的思想与作品;三者也可称为“真性皇民文学”。至于如张氏所辑译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大都是在严酷的军国殖民高压下无自觉的作文或是自觉性的酬应、阳奉阴违之作,因此像那类性质的文章只可称之为“假性皇民文学”,本来就不应将之归类为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之列。该批判的应是真性皇民文学,而不是后者。
下面,将依据历史材料,来探讨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推动皇民文学的主体是谁?这主体又是如何透过打压台湾文学来建立皇民文学的支配的?而在这过程中,台湾前辈作家又是如何抗拒皇民文学的支配来维系台湾文学的气脉?同时,我们还要分析皇民文学的性格,并指出皇民文学到底是为谁的文学——是为台湾人民?还是为日本殖民军国体制的“文学”?
三、法西斯主义对思想、文艺的支配与台湾皇民文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意法西斯阵营,都把对文化、思想、教育的控制,当作推进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手段。文学与音乐、戏剧、美术、电影一样,作为文化的主要部分,曾遭受到各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的摧残;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宣扬和鼓动法西斯思想和感情的文学、艺术支配一切。譬如在德国,就有“德国文化总会”统制全德的思想、精神活动,使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德国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并且有计划地迫害、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科学家;超过五千名以上的科学、文化工作者被迫流亡,其中包括著名的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人。其他留在德国的人则拒绝写作或写作而不发表,采取内心流亡的抵抗态度(注:参照朱庭光编著《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日本,1930年前后军国主义崛起,原来在二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左翼势力全面溃灭。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原日本左翼作家被迫纷纷抛弃信仰,或转入内向的纯文学世界,或顺应军国主义的“国策”,因而形成了所谓的“转向文学”。1940年,日本成立直属内阁总理的“情报局”,并以此为中心,推动对日本文化界的全面统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1942年6月,在情报局的指导下, 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其章程规定:“本会的目的在于……,确立并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同年,又成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宣称:“不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立日本主义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注:1942年号的《文艺台湾》。)简单地说,日本军国法西斯思想的核心是:攻击西方启蒙时期以降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唯物主义等,主张发扬以“皇国精神”、“国体精神”为实质内容的日本主义,以及高倡“建设国防国家”,建设“大东亚秩序”,实现“八纮一宇”等口号的对亚洲的侵略主义。依此,日本军国法西斯对文学的要求就是:以这些法西斯思想为指导,在作品中反映这些思想,并以作品的思想性高于文学性,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指标,视文学为强化国民的军国法西斯意识的手段。这种“国策文学”构成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思想战的一环,不但施行于日本本国,而且普遍地强制施行于朝鲜、台湾殖民地以及“满州”半殖民地和所有的占领地区。它就是台湾“皇民文学”的思想根源,同时也是构成台湾皇民文学的性格的主要部分。
四、产生台湾皇民文学的时代背景和推动台湾皇民文学的主体
1940年,欧战全面爆发,日本为了从泥沼化的中国战场脱身,以及为了乘隙夺取西欧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地资源,开始采取“武力南进”政策。以“驱逐欧美势力解放东亚”的名分,用“建设大东亚秩序”的口号,发动对东南亚的侵略战争。在这种局势下,殖民地台湾的角色,由原来的日本的“米仓糖库”一变而为“日本南方的玄关子”(小林总督用语,就是指日本南进基地之意),于是,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强化在台湾的战争总动员体制;以“皇民奉公会”为皇民化运动的核心组织,彻底动员台湾的财富、人力和人命供其侵略战争的消耗。1942年1月, 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月,在台皇民文学运动的头号御用总管西川满,在他主持的《文艺台湾》扉页上,用黑体大字表明了他用文学向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交心的决意,其大要谓:
为了建设大东亚的国家的心,我们文学创作的心,只有呼应“国家的心”才能跃动。新的国家文学的理想,并非达到抽象的美的理想;而是应具体实现现实上的“国家的理想”以作为国民生活的指标。(注:昭和十八年(1943年)5月17日《兴南新闻》学艺版。)
同年,台湾总督府开始对台湾的电影、戏剧、演艺进行了统制。在这前后,西川满领导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和机关杂志《文艺台湾》以及“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共同积极地扮演了以文学协助推动日本大东亚战争的角色,并培养符合“呼应国家的心”的文学观的作家,于是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开始登上舞台。台湾人皇民作家周金波的《志愿兵》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43年,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战争开始呈露败相,从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台湾处于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内,因而进入所谓的“决战期”。同时,第一批台湾人陆军志愿兵被送往南洋战场,台湾开始成为日帝的兵源供应地。此时,台湾的文学和电影、戏剧一样,成为强化台湾人决战意识的宣传和鼓动工具。1943年4月底, 在“台湾皇民奉公会”指导下由西川满等主导,将“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为“台湾文学奉公会”。此后,“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在台日人御用文臣的杂志报刊、以及其背后的总督府保安课、情报课、州厅警察高等课、日本台湾军宪兵队等在台军国殖民主义势力,共同构成了推动台湾皇民文学的主体。
五、对台湾文学的打压,以及台湾作家的屈从与抗拒
实际上,日本军国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打压,早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就已开始。彼时,日本殖民当局逐步对全台湾社会进行战时统制;为了改造台湾人的汉民族意识,以及为了清除抗日思想,日本殖民当局展开如火如荼的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的重要一步,便是禁止报刊杂志使用汉文(中国白话文)。这对向来以中国白话文为文学表达的工具而成长起来的台湾文学界而言,不啻是致命的打击。当时,台湾文学的两大园地——《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被迫在那前后相继停刊。台湾文学的开拓者赖和、杨守愚、陈虚谷等人,为了抗拒以殖民者的语言写作,转而寄情旧汉诗文;有些失去文学园地的作家,离开故乡远赴大陆、南洋;而吴漫沙等人则继续刊行无关时局的白话文杂志《风月报》,与日本御用文人西川满主持的《文艺台湾》分庭抗礼。
如前所述,1943年,台湾进入了日帝的决战期,于此前后,在军国殖民当局和日人御用文臣加紧对台湾文学进行皇民文学化的环境下,出现了一批年纪较轻、同时在皇民化运动中正逢思想形成期的所谓“战中派”作家,他们积极创作了呼应日帝国策的作品,产生了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但是,绝大部分经历过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台湾的民族运动、社会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们,以及大多数继承了台湾文学精神的年轻作家,他们即使无力正面反抗,在生活表面上与日本军国殖民当局虚与委蛇,但是,在实际的创作上却仍然秉持文学与民族的良知,坚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继续创作,顶住来自当局与御用文臣的压力。
六、“狗屎现实主义”论争
对于台湾作家不屈从的态度,日人御用文臣们早就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的爆发,出现在“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的前后;西川满在1943年5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写了《文艺时评》,对主要以《台湾文学》为园地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批评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狗屎(日文原文为“粪”)现实主义”,是拾欧美文学的牙慧,不重视日本精神,无视台湾的“勤行报国队”、“台湾志愿兵”的热烈现实,只会写些如虐待继子或传统台湾家族纠葛的旧习俗等等。
对此,吕赫若在5月7日的日记上如此写道:
西川满的《文艺时评》所表现的低能格调,突然间引起了各方的非难。总之,西川氏是因为无法以文学的实力压倒别人,所以就用那样的手段陷人于奸计,真是一个文学的阴谋策动家。记得金关博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妨害台湾文学成长的东西就是文学家也。”
针对西川满对台湾文学的攻击,有一位以“世外民”为笔名的台湾作家,在5月10 日的《兴南新闻》上写了一篇《狗屎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予以反驳,他认为西川氏的文章,在丑陋的恶骂方面,令人惊讶。如果本岛人作家的作品是“狗屎现实主义”的话,那么,自称为浪漫主义者的西川满作品,也不可免于被指责为“假浪漫主义”。隔周,年少的叶石涛站在为西川满辩护的立场,写了一篇《给世氏的公开书》(注:刊载于昭和十九年(1944年)1月1日出刊也是它的终刊号的《文艺台湾》。);批评世外民为狗屎现实主义的信奉者辩护,不懂得日本文学的传统,是受外国文学不良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叶石涛写道,“以无限幸福、光辉和至正的建国理想建设起来的当今日本文学,正是清算明治以降来自外国的狗屎现实主义,回归古典雄浑的时代的绝好机会。”叶石涛接着写道:“对于装出一副不识时代潮流的嘴脸,得意地呐喊着什么‘台湾的反省’啦!‘深刻的家庭争议’啦!抬出让人想起十年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大题目而沾沾自喜的那伙人来说,给予当头棒喝,也不为过。”
叶石涛还举张文环的作品《夜猿》、《阉鸡》和吕赫若的作品《合家平安》、《庙庭》为例,汹汹然地质疑道:
到底在张氏或吕氏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有(类如西川满作品中的——作者)皇民意识呢?
在那样的时代空气中,被公然指为没有皇民意识,可说是被戴上不小的政治帽子,与被指为“非国民”一样严重。受到叶石涛公然质疑的吕赫若,在同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如此记道:
在《兴南新闻》的学艺栏,有叶石涛者,以张氏和我为例子,断定本岛人作家没有皇民意识。他的文章不管在论脉或头脑上都属低格调,不足为论;但在人身攻击上,实令人愤怒。
对于西川满的攻击,杨逵也以“伊东亮”的化名在7月31 日出刊的《台湾文学》秋季号上,写了一篇《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予以反击。他说:“即使浪漫主义者(实际上,不是什么浪漫主义者,而是现实逃避主义者)掩面捂鼻不想看,但现实还是现实存在的,被掩蔽隐藏的不是现实,而只是人的眼、鼻而已。……然而,到西方净土游玩、耽溺于与妈祖的恋爱故事,那到底是什么?只不过是痴人之梦罢了!(作者按:指西川氏作品)……浪漫主义决非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就只有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才会绽放出浪漫主义的花。如果是非排击现实主义就无法存在的浪漫主义,那只是空想,荒唐无稽的东西。只是不搭飞机而搭解斗云的痴人梦,只不过是类若妈祖的恋爱故事那样的东西而已。”杨逵的说理深刻,气魄懔然,今日读之,犹肃然礼敬!
七、在“决战文学会议”上,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的制压
皇民文学势力与台湾文学作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皇民文学势力挟其背后的日本军国殖民当局的威吓对台湾文学的打压,随着日本战局的颓败,而日愈紧迫。1943年11月3日,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 台湾皇民奉公会、日本文学报国会、总督府情报课协办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在会议席上,以西川满为代表的皇民文学势力,借着决战态势的压力,逼迫《台湾文学》发刊,因而爆发了双方面对面的斗争,在现在残存的决战文学会议记录中,关于这部分的记载,大要如下:
首先是西川满的发言:他对台湾作家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态度十分不满。接着,他以献出他所主导的《文艺台湾》杂志给日本决战体制为手段,要求其他文艺杂志也一齐跟着进入“战斗配置”,逼使不积极配合决战态势的文学杂志废刊(作者按:实际上是针对以台湾作家与非法西斯的日人作家所组成的《台湾文学》)。对西川的提议,在会议当场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勇敢的斗争:
接着黄得时起身反驳道:“没有必要对文学杂志管制,就像广告一样,愈多愈有人看,杂志也一样愈多愈好。”
滨田隼雄警告黄得时说:“不要把对物质的经济管制和对文化的指导统制混为一谈。”
杨逵赞成黄得时的意见,说道:“抽象的皇民文学理论与杂志的统合管制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神川清愤慨地批评杨逵的发言道:“理念与具体实践是不可分离的。”并提醒杨逵道:“假若在政策上两者分离的话,国家将会灭亡。”
(会后,神川清另外写了题名为《刎颈断肠之言》的文章,批判杨逵的发言,他认为:这是本次会议中最不幸的事(作者按:指杨逵的发言),也许是由于杨逵不努力而生的无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文学的人,居然可以在台湾安居筑巢,真是太遗憾了!
黄得时再起身说:“我并不反对西川满将《文艺台湾》献出来。如果真想把《文艺台湾》献出来的话,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杂志并没有跟着配合的义务。”
接着,西川满又提出了要求日本军国殖民当局撤消文学结社,把作家全部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进行文学管制的动议;甚至赞同在台湾文学奉公会下另设“思想参谋本部”,对作家进行思想控制。充分暴露了西川满在唯美主义的外表下,毫不保留的文学法西斯本质。
会议在总督府保安课长的讲话中结束。他说:“对决战态势无益的都不可要;文学作品也一样,只有对决战态势有助益的才可发表。”这等于宣告了皇民文学完全取代了台湾文学,也就是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完全支配了台湾文学。
会后,河野庆彦写了一篇对决战文学会议的感言——《朝向思想战的集合》,文中对于台湾作家“阳奉阴违”的态度(张恒豪先生语),如此批评道:
从会场的空气中感觉到,(台湾作家们)只是把头探出来,说些诸如皇民文学、战斗文学的漂亮话,但双脚却依然原地不动。……使人嗅到台湾文学的“体臭”,感觉到泥巴和口水到处乱喷……我们非克服这些内含的矛盾不可。……台湾文学已到了非“脱皮”不可的时刻了,不要只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样子,而是要真正成为一支受统御的思想部队。
河野以台湾人的“体臭”、“泥巴”、“口水”为言,毫不客气地表现了他对台湾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憎恶。由这些记录我们认识到,以西川满为首的在台御用文臣和皇民文学势力,如何试图以逼迫《台湾文学》废刊、撤消文学结社、利用台湾文学奉公会对作家进行统制、甚至提议设立思想参谋本部等来对台湾文学进行法西斯控制,推进皇民文学,其目标就是要消除仍散发着台湾人民主体的“体臭”、“泥巴”与“口水”的台湾文学,使台湾文学“脱皮”成受统御的法西斯思想部队——皇民文学。因此,所谓“皇民文学”,其本质是台湾文学的对立物,是扼杀台湾文学精神的。
八、台湾文学的烙痕
吕赫若在1943年12月13日的日记上如此写道:“今天当局下达《台湾文学》废刊的命令,真叫人感慨无量……。”自此,台湾文学完全被置于台湾文学奉公会的一元控制下,在军国主义的高压下虚与委蛇,等待黑暗时代的结束。
1944年,盟军攻陷塞班岛,开始对日本总反攻,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军机猛烈的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在台军国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至上指令由“决战文学”进入“敌前文学”。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6月号, 刊出了名为《台湾文学界总蹶起》的专题,其中,吕赫若写了一篇题为《宁为一个协和音》的文章,他表示在决死战争的大交响乐中,宁愿扮演一个小小的协和音——而不是主调。实际上在小说创作上,他巧妙地避开了皇民文学喧嚣狂乱的战争和大和主义的主题,致力写趋颓败的台湾封建家族以及阳奉阴违的增产文学。同专集中,杨逵在极严酷的高压下不得不也写了短短的近似自白书的《解消首阳之记》,其强忍锥心泣血之痛又不得不妥协的内容,令人忆起赖和在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被捕后,在狱中所写的《狱中日记》;在日本军国法西斯濒死的狂暴胁迫下,写下的屈辱的文字,是台湾文学的最深、最为难忘的伤痕。
九、对台湾皇民文学势力的历史总结算
从上述台湾皇民文学产生的历史过程1943年的“狗屎现实主义论战”和“决战文学会议”席上的斗争、以及1944年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的《台湾文学界总蹶起》的专题等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
1.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的镇压。
2.在“决战”局势下,台湾前辈作家仍然凭着文学的良知,抗拒台湾文学的皇民化。但是进入了“要塞化”时期,台湾作家已经不得不委屈求全虚与委蛇,不过那已经是距日帝败亡不足一年的时候了。
3.皇民文学势力,实际上包括台湾人皇民作家,日人御用文臣以及其背后的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它构成三位一体用“文攻武吓”来推进台湾文学的皇民化。
4.因此,西川满是代表这三位一体的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发出总攻击,逼迫台湾文学就范于皇民文学体制。
5.从少年叶石涛和西川氏攻击台湾文学的内容来看,它的文学思想的特征包括:排斥西方文学,反对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和自由主义,甚至反对反映台湾社会风土的本土主义;主张回归复古的日本主义和宏扬日本的建国理想,以及强调描写勤行报国队、志愿兵热等强化台湾人决战意识的文学。这不单是台湾的皇民文学势力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其本国、在伪满州国、在朝鲜、在中国沦陷区普遍推行的文艺政策,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的思想总根源就是日本的军国法西斯主义。
6.台湾皇民文学体制(包括台湾文学奉公会等),是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战争总动员体制的一环,是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树立起来的。它与当时如火如荼地在台湾推行的军需工业化、强制储蓄运动、皇民化运动、军夫、志愿兵运动是一物的两面。
十、台湾皇民文学的性格
台湾皇民文学的性格主要决定于它的产生过程和推动主体的指令。归纳起来,包括下述三方面。
(一)皇民文学的战争文宣性格
在1943年底举行的“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席上,台湾文学奉公会会长山本真平如此说道:“后方战士的责任,是在扩大生产以及昂扬决战意识:亦即与武力战结为有机一体的生产战、思想战……在思想战方面,诸位文学者正是承担着增强国民战力的任务。”
而关于所谓“皇民文学”,他说:
文学家既蒙皇国庇佑而生活,当然应当与国家的意志结成一体……。今天的文学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在反刍个人感情,而应该是呼应国家的至上命令的创作活动,当然,文学也一定要贯彻强韧有力、纯粹无杂的日本精神来创作皇民文学。以文学的力量,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
在这里,山本清楚地说明了皇民文学的性格,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力战一环的思想战,是呼应日本军事国家至上命令的创作活动;它的任务是:以文学力量激励本岛青年迈向兵士之道、激昂大东亚战争的必胜信念。由此可知,所谓台湾皇民文学,只是日本法西斯的思想队伍,是依至上命令的创作,本来就不含有什么文学要素,甚至是反文学的,充其量只可说是战争文宣而已。
(二)皇民文学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
当时,推动台湾皇民文学的主体,除了像台湾文学奉公会这样的组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批狂热的在台日人法西斯文臣;他们除了积极创作一些表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文学作品之外,还积极地发表一些具攻击性的日本法西斯文学言论,与当局的皇民文学施策共同形成了浓厚的法西斯文学环境,对台湾作家造成极大的威胁。
譬如,以台湾代表之一,参加过1942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的滨田隼雄,和自命为“皇民文学理论家”的神川清,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也与西川满同伙,是皇民文学势力的中心人物。只要概括他们几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到,所谓台湾皇民文学中的日本法西斯思想特征。
在文化思想上:
排斥启蒙哲学以降的西欧近代文化;反对文化至上主义;认为主知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敌性文化”的土壤。高举复古的日本主义,强调皇国精神与直观精神混合的盲目爱国主义,并且高倡所谓“八纮一宇”的侵略主义。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世界法西斯思想有共通的部分,也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精粹。这种思想使千万以上的亚洲人民人头落地,生灵涂炭。
在文学思想上:
它极端攻击文学的独自性,把文学当做体现上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工具。现在不妨撷取他们文章中的一些句子看看他们的观点: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于天皇之道,如果把作为文人的自觉摆在作为日本人的自觉之上的话,我认为他除了是国贼或不忠者之外,什么都不是。
文学批评的基准就在日本精神。
在皇国体的自觉中发现文学的始源,要求贯彻皇国体思想,把作品与国体结合在一起。
在终极时的精神燃烧——天皇陛下万岁,是一个文学者的描写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决战下,我们思想决战阵营的战士们,务必要扑灭“非皇民文学”,要扬弃“非决战文学”。
在文学实践上:
就如当时西川满所主持的“皇民文学垫”的同人训所揭示的头二句:“我等为皇国的文臣,文臣之道在用笔剑击倒敌人而后已。”是把文学视为实践皇国之道的武器和工具,把文学当作遂行大东亚圣战的思想部队。
(三)皇民文学的皇民化性格
前面说过,当时的台湾作家是处于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的;因此,台湾皇民文学的性格并非单只是上述日本法西斯文学思想的简单翻版;它还具有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的现实的另一面。亦即,它除了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学要求的一面外,还必须担负反映日本殖民者对殖民地台湾人民进行皇民化的文学要求的另一面,这又构成了台湾皇民文学的另一特异性格。
以处女作《道》而让西川满感动得“热泪盈眶”,被滨田隼雄赞誉为最杰出的皇民文学的陈火泉,在决战文学会议上发表了《谈皇民文学》一文,他如此说道:“现在,本岛的六百万岛民正处于皇民炼成的道路上;我认为,描写在这皇民炼成过程中的本岛人的心理乃至言行,进而促进皇民炼成的脚步,也是文学者的使命。”这句话要约地指出了《道》和周金波的《志愿兵》以及王昶雄的《奔流》等皇民文学的代表作的共通性格。这些作品的主题,大致都在表现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如何积极地自我锻炼成标准皇民的心理与言行;所谓“皇民炼成”,简单地说就是战争期间的皇民化运动,也就是在文学上表现如何抛弃台湾人的汉民族的语言、习俗、价值观,彻底地成为与“内地人”有同样神经感觉的日本人。然而,这里所指的“日本人”的内涵并非一般意义的日本人,而是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军国法西斯体制所要求的标准日本人“样板”:它有着热烈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有狂热的为皇国殉身、为大东亚圣战奉公的决心,是具有这样的成分的所谓“日本精神”的日本人。这与德国法西斯所要求的,具有德意志精神的标准日耳曼人一样,都是法西斯体制下的样板人。
既然台湾皇民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在表现台湾人皇民化的问题,因此,皇民化性格是其重要的部分。
十一、总结算
由上可知,所谓台湾皇民文学,是日本军国殖民者对台湾文学的压迫与支配的产物;首先它扼杀了文学精神,因此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对立物;它更扼杀了台湾文学的精神,是台湾文学的对立物。它也是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在台湾施行的战争总动员体制的一环,以文学的假面,宣扬日本的军国殖民法西斯理念,来动员台湾人民的决战意识,为日本侵略战争献身的东西,所以更是台湾人民的对立物,同时,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对立物。这是所谓台湾皇民文学的本质,必须先认清楚。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日本军国殖民体制高压下,虽然有些台湾人作家积极地向日本战争体制靠拢,站在皇民文学的阵地为体制效劳;但绝大部分的台湾前辈作家,有人拒绝写作,有人凭良知抵抗,有人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总之,都以各种方式表现了维系台湾文学气脉的可贵精神。对于前者的奴隶、机会主义者,和后者的以艰难的抵抗维护了人的尊严捍卫了台湾文学尊严的作家,两者之间,必须辨识清楚,不容淆惑。
以上是对所谓台湾皇民文学的总结算书;自命真正爱台湾、疼惜这块土地的人,是应该宣扬皇民文学理念呢?还是应该彰显台湾文学威武不屈的精神呢?不要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是应该把话说清楚的时候了!
面对张氏如此淆惑与伤害台湾文学尊严的作为,平日开口“台湾文学的尊严”,闭口“台湾文学的主体性”的所谓“台湾意识文学”论者,怎样都鸦雀无声了呢?是不是所谓的尊严或主体性只对中国有效而对日本军国殖民者无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