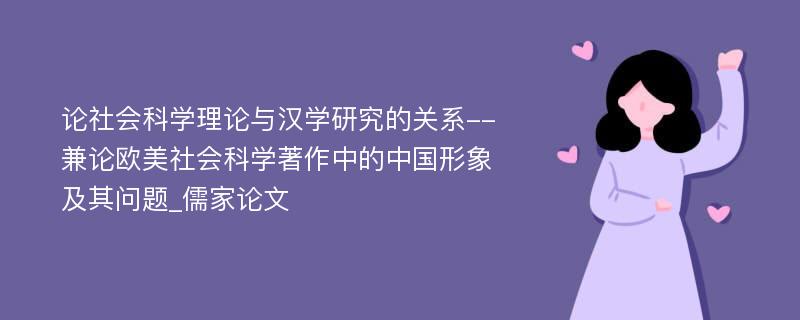
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兼论欧美社会科学论著中的中国意象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论著论文,意象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代学者钱存训曾统计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翻译西方出版物共567种,其中自然科学类占40%,社会科学类占8%。[1]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击败大清帝国,梁启超(任公,1873~1929)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甲午战争后,中国起而师法日本,[3](P.641~674)大量学生赴日留学(注:据实藤惠秀的研究,在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已在八千至一万名之间,到1906年则高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并大量翻译日本之社会科学书籍。在1896年至1937年的42年之间,中国所译日本社会科学著作数目至为可观(注:实藤惠秀统计,在1896年至1937年中国翻译日文社会科学书籍,包括教育类140种,政法类374种,经济社会类374种,地理历史类344种,其中仅关于工人问题的就有374种。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版,页167—16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多半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学术或汉学研究之间,有其矛盾之关系。哲学家熊十力(子贞,1885~1968)认为西方社会学说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他说:“今之治史者,或为无聊考据,或喜作肤浅理论,或袭取外人社会学说,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类,以叙述吾之历史,乃至援据所谓唯物史观。如此等者,皆不曾用心了解自家得失,根本缺乏独立研究与实事求是之精神”。[4](P.67~68)相反地,思想史家侯外庐宣称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伸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5]。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确实是力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亚洲版本之脚注。这些针锋相对的意见隐约间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存在有某种紧张性,不是中国屈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完全将中国经验视为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例外。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本文所谓“社会科学理论”指近数十年来欧美社会科学界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学说;所谓“汉学研究”,指关于二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研究而言。但是在进入本题之前,我们先从已故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1931~2001)的意见说起。张光直在1994年出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之前,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从古到今政治文化一直占着挂帅的地位,而孔夫子和他的信徒都是最懂得人际关系的专家。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本钱。研究的资料,则有一部二十四史,自五十年代便为玛丽·瑞德教授向一般社会科学者介绍为全世界最丰富的一座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行为的规律的宝库。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6]
张光直自己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答案是:
我们不妨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三部曲开始:第一,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第二,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在分析过后是否对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新的贡献。第三,如果有所贡献,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即不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6](P.64)
台湾的心理学家黄光国(1945~)不同意张光直的“三部曲”,他认为:“造成今天国内社会科学低度发展主要成因,在于学术经典翻译不发达,国人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潮普遍隔阂,导致学术研究对于西方的高度依赖。解除这种依赖困境的正确途径应当是加强西方学术经典的译介,彻底了解西方学术的思潮后,再回过头来,在中国社会里面找研究题材,来解决我们自己迫切的重大问题”[7]。
张光直与黄光国的说法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将汉学研究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立起来,并隐约之间认为前者具有特殊性,后者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说法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人文学者熊十力与侯外庐的意见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这种说法值得进一步商榷。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论证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间有其辩证性的有机关系,因为(1)社会科学理论如果忽视汉学研究,将成为跛脚的学术。(2)必须从汉学研究中抽离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性命题,才能使汉学研究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地域性的知识”(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所谓的“Local Knowledge”)。两者之间在研究内容上有其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论上又有其紧张性。因此,两者间存有竞争支配地位之关系。但是,两者离则两伤,合则双赢。
一、研究内容的不可分割性
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汉学研究之间,存有互补互利的关系,两者间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两者在研究内容上有其不可分割性,社会科学理论如果忽视中国历史经验,将成为不完整的学说:反之,汉学研究如果缺乏社会科学的视野,将难以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两者之间离则两伤,合则双利。
1.离则两伤
下面先以社会科学家对儒家思想的误解为例说明离则两伤。
我们要论证社会科学研究与汉学研究之不可分割性,可以先从两者断为两橛后的负面效果说起。这种负面效果首先表现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儒学的误解之上。20世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科学界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误解,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认为儒家是(1)威权主义,(2)集体主义,两者均有利于亚洲传统的专制政治。
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般都主张儒家是威权主义(Authouitarianism)的渊薮,应为传统中国的以家长制为主轴的家庭制度以及专制政治负责。这种意见在五四时代以所谓“吃人的礼教”的口号而提出,在国际知识界则形成为对中国专制政治之思想根源的共识。举例言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分析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就指出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特色在于对父亲权威的的绝对服从、反对入侵行为以及严守秩序。这三大特色不仅彼此相关,同时在家庭成员人格的塑造上也极为重要。中国是一个注重孝道的民族,中国人把孝顺父母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孝子孝女的事迹和忠臣烈士并列,二十四孝故事广为流传。出身贫贱的孩童,常常由于他们的孝行而名留青史。孝顺父母是崇拜祖先的坚实基础,而崇拜祖先又激发中国人的历史认同感,所以中国人非常服从权威,因为失掉权威的统摄,自我便失去意义。中国人对权威的认知是出于主观的态度。接受父亲无上权威是中国儿童一生中最早的权威崇拜。(注: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Mass.:The M.I.T.Press,1968),白鲁恂的论点经过他的学生索罗门加以发挥,认为中国人的集体性格有利于毛泽东的革命,参看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白鲁恂认为传统中国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早已奠基于中国人的儿童养育方式之中,这与儒家价值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白鲁恂这种意见是国际社会科学界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例如近年来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成为焦点人物的美国政治学家杭亭顿(Samuel P.Huntington),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说: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打入无数亚洲社会的儒家思想,强调威权与阶层体统,个人权利和利益次要,重视共识,避免对立,爱面子,以及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等价值。此外,亚洲人多半以世纪甚至千禧年,来思考他们社会的进化,并以最长程的利益为最高优先。这些态度和美国最重视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等理念形成对比,美国人也比较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尊重人权,忘记过去,不管未来,锁定最眼前的目标。冲突源于社会和文化最根本的差异。(注:参见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N.Y.:Simon and Schuster,1996),中译本参看:杭亭顿著,黄裕美译,《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页304。杭亭顿指出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后,“文化认同”在21世纪新秩序中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点很有见识。但他认为美国应防范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合作以对抗基督教文化,这种说法的错误则不值识者一笑。我对此书曾撰短文加以评论,另详拙作:Chun-chieh Huang,“A Confucian Critique of Samuel P.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刊于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16,no.1/2,(Spring/summer,1997),pp.147~156。)
这种意见认为儒家是传统中国(甚至亚洲)专制政治的帮凶,言外之意认为在华人社会迈向民主政治的新时代里,儒家早应与专制政体一起被丢弃到历史灰烬之中。
西方社会科学家第二种意见认为,儒家是集体主义的思想根源。早在1926年,傅斯年(孟真,1896~1950)与顾颉刚(铭坚,1893~1980)讨论“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这个问题时,傅斯年就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是中国的宗法社会的理性发展。中国始终没有脱离宗法社会。父权是宗法社会的基础,所以,儒学思想与秦汉以降专制政体制的发展颇为吻合。[8](P.155)这种看法到今天仍有其影响力。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就与傅斯年相近,但更为细致,福山说:
在儒家社会里,集团不仅在维持工作伦理上十分重要,在做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上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一个人之得到身份地位,与其说源于他个人的能力或价值,不如说是因为他属于一系列串珠式集团之一。例如日本宪法和法律体系也许跟美国一样承认个人的各类权利,但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有承认集团的倾向。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只有在他既存集团之一员又遵守其规则的前提下,才能有尊严。可是,当他一旦向集团主张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就会遭遇到社会放逐而丧失其地位,其严厉决不下于传统专制统治的公开性暴政。这会产生要求协调的莫大压力,而生活在这种文化里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这种协调性。换言之,亚细亚社会中的个人已成为托克维尔所谓“多数专制”——或者说:不论大小,与个人生活相关的一切社会集团中的多数专制——的饵食。[9](P.306~307)
福山认为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多数专制”,压抑个人意志与个体自由。
欧美社会科学家这两种对儒家的批判意见各有其立足点,也有若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论据,例如认为儒家具有威权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的说法,确能直指被大汉帝国独尊儒术以后所出现的“帝制儒学”(“Imperial Confucianism”)的核心问题;认为儒学与中国人的保守性格有关的说法,也很能扣紧儒学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之关系。
但是,再从更深一层来看,以上这两种批判性的意见却都存在有严重的思考上的盲点。这种盲点以下列两种最为深切着明:
第一,西方许多社会科学家解释儒学常常犯了“过度简单化的谬误”。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传统,从先秦时代绵延至于今日,历经两千余年之变迁而丰富其思想内容。就其时间之纵剖面而言,先秦儒学固然不同于深受政治力渗透的两汉儒者,蕴涵道家思想的魏晋时代儒学亦与唐代儒学不同;宋明儒学亦迥异于清代儒学。再就儒学的横切面观之,儒学亦有其不同之面向或层次。刘述先曾区分儒学的三种不同层次:(1)精神的儒家;(2)政治化的儒家;(3)民间的儒家。[10](P.1)这三种层次或类型的儒学,各有其互异的思想内涵,不可一概而论。李明辉(1953~)在金耀基所区分的“帝制儒学”与“社会化儒学”两个层面之外,另加一种“深层化的儒学”,认为这个层面的儒学是对现代化中国人思考方式仍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家思考模式。李明辉并指出,在这三个类型的儒学之上,尚有一个作为儒学本质的既内在而又超越的思想内涵。[11](P.6~12)不论如何,儒学具有多层面性、多元性的思想内涵,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从儒学的复杂性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社会科学家对于儒学的这两种批判,都不免犯了“化繁为简”的思考盲点,这两种意见都无意间将儒学当作是一个单元而非多元的思想传统。社会科学家所批判的基本上是汉代以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化的儒家”或“帝制儒学”,及其与权力结构挂钩后所产生的种种流弊。他们忽略了一项重大事实:“政治化的儒家”或“帝制儒学”并不能涵盖儒学的全貌。不论是作为知识菁英共同精神基础的“精神的”儒家思想,或作为民间价值系统的世俗化的儒家思想,都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第二,西方许多社会科学家讨论中国历史中的儒学时,也常陷入“化约论的谬误”。社会科学家对于儒学的批判意见,都要求儒学为帝制中国的专制政治或集体主义负责,这种批判完全忽略了抽象的思想系统与具体的社会政治建构之间,有其“不可互相化约性”(mutualirredciability),因为思想领域与社会政治领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modus operandi),思想的建构只涉及主体性建立之范畴,但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就涉及主体性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问题,状况较为复杂,而且常常不是主体所能完全掌握的。(注:我在新刊拙著《儒学与现代台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一书的《序》中,对儒学所遭受的误解有更详细的讨论。上文有部分段落取自该书《序》文。)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家要求儒学为政治的专制主义与社会的集体主义负责,并不公平,这种说法犯了“化约论的谬误”。欧美社会科学界这种思考上的盲点,固然与各个社会科学家的学力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在于社会科学界对汉学研究的忽视。
现在我们再以当代社会科学巨擘埃森西塔(S.N.Eisenstadt)对世界史上帝国的政治系统之研究作为实例[12],作进一步论证: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如果对中国经验缺乏深入的理解,终是不完整的或是以偏概全的理论。
我们首先从政治学的研究主题说起。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主题大多重视各国静态的政治制度而较少涉及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因此,传统的政治学教科书所谈的不外是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分类、国家与人民、政府组织等题目。(注:例如邹文海所著《政治学》(台北:三民书局,1957,1969)一书即为一例。)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系统的运作及其过程一变而成为政治学研究之主要课题,诸如“投入—产出”(imput-output)、“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 )之类的名词乃应运而生。首先把“系统”这个观念用来构成一个理论系统的是大卫·伊士敦(David Easton),他的《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一书于1953年问世。伊士敦的政治系统论从“持续生存”(persistence)的观念出发,为政治系统在其存在的环境中从“需求”与“支持”的投入到“决策”或“政策”的投出反馈过程建立一套理论模型。埃森西塔的政治系统论与伊士敦、阿尔蒙(G.A.Almond)、阿卜特(D.F.Apter)等人的学说关系密切。 埃森西塔的《帝国的政治系统》一书从政治系统论出发,研究人类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政治帝国的政治系统。全书共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析历史上官僚帝国政治系统发展的条件;后半部分析其持续之条件。第一部分的第一及第二章是全书理论基础之所在,全书的论述处处与这两章有密切关系。(注:我曾将此书第一章译为中文,见黄俊杰译,《历史上官僚政治组织的背景及其问题》,收录于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1981,页187~202)。)
埃森西塔研究历史上官僚政治组织中的政治系统,包括近东文明、埃及、在印加(Incas)及阿兹推克(Aztecs)之中的古代美洲文明;希腊化世界、 罗马世界及拜占庭世界;远东文明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诸如阿比塞(Abbaside )、 法蒂迷(Fatimite)及奥图曼(Ottoman)等帝国的回教世界、近代欧洲和专制政治时代。埃森西塔指出:这些帝国大部分都是在帝王统治之下,这些帝王拥有传统神圣的正统性。在帝国内,人口中占相当多数的人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消极感,而且缺乏任何普遍选举权及政治权利。这些帝国多具有相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官僚政治的行政管理及政治机关,也常见政治斗争。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在此不必细述埃森西塔的理论之细节,但他在建构他的理论时,以大量篇幅讨论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埃森西塔不能阅读中文第一手材料,他对中国史的解释都来自西文的二手资料,其书字里行间每能发现西方汉学家如韦伯(Max Weber,1864~1920)、赖德懋(O.Lattimore)、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谢和耐(Jzcques Gernet)、法兰克(Herbert Franke)、富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崔启德(Denis Twitchett)、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贺凯(Charles O.Hucker)、白乐日(Etienne Balazs)等人言论的投影。埃森西塔综合他人之研究成果,益以己见,形成他对中国史之全盘看法。正是从埃森西塔书中这一部分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社会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经验之无知而引起的理论建构上的盲点。
埃森西塔的理论主张:历史上的官僚帝国的统治者,居于政治系统的最高层,发号施令,运用社会资源,如中华帝国就建立在水利控制之上。我过去曾对埃氏解释中华帝国历史经验的盲目性有所批评,现在再稍加整理,择其要点加以申论。首先,埃森西塔分析帝国的政治系统之时,十分强调治水事业在中国史上之重要性,他说:“水道之控制是封建领主斗争之一项重要问题。运河与堤防之维持及修复乃系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它也成为一个组织完善而有效率的行政组织的象征”。[13](P.36)埃森西塔虽不满意于魏复古(Karl Wittfogel)之东方专制论。(注: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此书有中译本: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魏复古在另一篇论文中将他的学说加以精简说明:水利社会是农业社会的一种特别类型,其特征有五:(1)在文化上有农业知识。(2)在环境上是干燥或半干燥。水源的供应主要是来自河川,在缺水地区,用水于种植有利可图的农作物,尤其是谷物。在潮湿地区,种植食用的水生植物,尤其是稻米,则为此环境类型的另一变形。(3)在组织上有大规模的合作行动。(4)在政治上有水利秩序的组织性措施,这种组织如非由引导国家对内、对外重要活动如国防与治安的领袖所推动,就是快速地为其所接收。(5 )在社会上有区分水利政府人员与人民大众的阶层体系存在。专业化的组织兴起后,原始的水利社会(大部分由兼职的公务人员所领导)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水利社会(由专职的官员所领导),因而得以区分。后者也许是简单的水利社会,它也可以是种半复杂的水利社会,它内部有次要阶级,比如说工匠与商人,他们的地位建立在私有的动产上面。后者也可以是复杂的水利社会,它的次要阶级,则是同时奠立在私有的动产与不动产上面。魏复古指出:水利类型的农业社会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公元数千年前,由政府引导利用水利的农业文明,已在近东、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产生。同类结构的社会也早在印度、波斯、中亚(土耳其斯坦)、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以及爪哇、巴里,还有古代的夏威夷等地出现。参看:K.A.Wittfogel,“Chinese Society:A Historical Survey”,(刊于JAS.(16)1956~1957,pp.343~364),此文有中译本:K.A.Wittfogel著,扬儒宾译.《从历史观点论中国社会的特质》,载于《史学评论》第12期(台北,1986年9月页63~97),上文见中译本,页64~65,我引用时略有删节润色。埃森西塔曾有长篇论文评论魏复古的《东方专制论》一书,参看S.N.Eisenstadt,“The Study of Oriental Despotisms as Systems of Total Powe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7(1957~1958),pp.435~446。)但他无形中却接受维氏强调水利在中国史上之重要性这种观点,这种看法很有问题。何炳棣(1917~)就指出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土高原东南部,稍晚的新石器文化出现于黄土平原及江淮一带,地势皆较高,不受水患。中国灌溉起源甚晚,古文献中最早有关为灌溉而修沟洫之记载,仅能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中国最早文明非起源于灌溉,与古埃及文明有重大不同。(注:P.T.Ho,“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LXXV:l(Oct,1969),pp.1~36;idem,The Craddle of the East: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T.Ho,“The Chinese Civilization:A Search for the Roots of Its Longevi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XV:4(Aug,1976),pp,547~554;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水利事业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实不如埃森西塔所一再强调之重要。
第二,埃森西塔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特质均决定于儒家的思想,他说:“儒家思想把社会视为一个由士、农、工、商四个群体所组成的阶层秩序(hierarchical order)。[13](P.74)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明分士、农、工、商,并主张“四民者,勿使杂处”者系管子(《国语·齐语》),而非先秦儒家。关于儒家对社会区分之看法,虽然孔子有“君子”、“小人”的区分;孟子有“大人”、“小人”、“治人者”、“治于人者”、“食人者”、“食于人者”的区分;荀子有“君子”、“庶人”的区分,但是孔、孟、荀都在此一二分法之下,鼓吹“小人”经由进德修业之过程,力争上游而为“君子”。透过尚贤政治之实施使小人之才德秀异可以升为君子,君子之不肖无能者亦得降为小人,君子小人之社会分化已经不是森严的阶级制度,而是一种鼓吹社会流动性的主张。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之尚贤理论事实上均寓有荡平阶级、泯灭对立之宏旨,并将全社会熔铸为一不可分割之整体,埃森西塔之言不免厚诬儒家。[14](P.157~186)
从埃森西塔的具体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能充分掌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恐怕都有严重的缺陷,而伤害了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周延性。
2.合则双美
我们以“社会革命”理论及“国家”概念为例,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能与汉学研究互相交流,就可以达到互相发明的效果。就现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受西方“典范”(paradigm)支配的状况而言,则汉学研究对社会科学而言,益显其重要性。
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将中国历史经验纳入考虑,近年来愈来愈多西方社会科学家对这一点颇为重视,我们举美国的社会学家史柯普(Theda Skocpol)为例加以说明。
史柯普研究的主题是近代世界史上的“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她所谓的“社会革命”是指某一个社会中“国家”或阶级结构之快速而基本的转变。她认为,对这种“社会革命”的分析,必须采取结构的观点,并特别注意革命的国际脉络以及导致旧政权瓦解新政权建立的国内因素。她主张“比较的历史分析”是最适当的研究方法。史柯普的书就从国家结构、国际力量以及阶级关系入手,分析1787年到180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到1930年代的俄国革命,以及1911年到1960年代中国革命。[15](P.157~186)在西方社会科学界,虽然早在1853年5月,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已经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放在一起思考,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6](P.6)但到19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家才比较全面地注意中国历史经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摩尔(Barrington Moore)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17],史柯普的书在1979年问世,是近三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另一位社会学家。
史柯普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提出许多创见,对马克思与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的许多学说,既加以吸纳融会,而又提出修正。全书论述引人入胜。史柯普从中俄法三国的历史经验指出,“国家”虽然是一种行政的与强制性的组织,但是,“国家”常常具有某种潜在的“自主性”,而不受阶级的控制。她认为在分析“社会革命”时,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史柯普的书之所以能在这三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中提炼理论,主要可以说得力于她在西方历史经验之外,再将中国经验纳入考虑,从而在三个革命经验中既求其同,又见其异。从史柯普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在建构社会科学理论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接着,我们再举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国家”(state)这个概念为例加以说明。在西方社会科学论述里的“国家”是由同构型的空间切割而成的,而中国社会科学者“心目中的国家不是主权疆域,而是一种伦理导向的人际关系,国与家之间是连续的,不像欧美那样是断裂的”,[18](P.15~16)所以,中外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中国的“国家”概念时常有杆格之处。我想更进一步指出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不论是右派或左派学者对“国家”的定义,都充满了各种断裂的空间或组成部分之间“对抗的”(adversarial)氛围。例如,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认为国家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体现,驾于特殊利益之上,因此能够克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以及个人作为私人和市民之间的分裂。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995)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9](P.253)此外,西方右派社会科学者则强调“国家”(state)不是政府(government),在民主政治中“政府”屡变,而“国家”依旧。“国家”也不是“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因为“国家”包括军警机构、民意机关等,但作为“民间社会”的政党并不是“国家”之一部分。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家”的概念因为诸多空间的切割、断裂或对抗而获得突显。但是,在汉学研究中,“国家”作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意义远大于作为“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的意义,顾炎武(亭林,1613~1682)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0](P.379)
顾炎武这段话中所谓“天下”是指“文化认同”,所谓“国”是指“政治认同”,他认为前者较后者重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家”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民族共业,而不只是一套权利义务所规范的契约关系。社会科学家如果能够通过汉学研究成果而深入中国历史经验,他们思考“国家”这个社会科学重要概念时,将更为周延。
以上举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国家”这个概念为例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家能够将中国经验纳入考虑,则社会科学中的“国家”概念将获得更丰富的意涵。此类例子甚多,不再赘举。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或理论如“认同”(identity)、“人权”(human rights)(注:我曾就中西人文传统中之“人权”问题有所探讨,参看Chun~chieh Huang,“Human Rights as Heavenly Duty——A Menc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umanities East/Wes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Vol.14 (Dec.1996);黄俊杰:《儒学与人权:古典孟子学的观点》,收入刘述先编《儒学思想与现代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页33~56)。)等问题,如果能从汉学研究中汲取营养,必可开拓其深度、高度与广度。
二、研究方法的紧张性
社会科学研究与汉学研究的第二种关系在于,两者间的研究方法上具有某种紧张性。这种紧张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乃是因为,(1)社会科学宣称是一种“科学”,以建立人类行为的普遍定律为目的;(2 )汉学却以对特殊现象之描述为其主要内容。
1.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质 到底社会科学是不是一种“科学”?这是大部分社会科学教科书开宗明义就会触及的问题。例如台湾的政治学者吕亚力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绪论”中,虽然将“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的正反两面意见并列说明,但第一章以下讨论政治方法论的“概念”、“定律”、“理论”、“解释与预测”等问题时,[21](P.1~69)莫不显示作者心目中其实预设社会科学是或是接近“科学”。政治学前辈学者邹文海倾向于主张政治学是一种“弹性的科学”(dynamic science),他说:
所谓弹性的科学,既不承认有固定的法则,也不承认没有法则,而是说法则乃随环境而变更着。研究政治的人,既须注意时间的因素,又须注意空间的因素,而更须注意不同时间及不同空间中人类不同的适应,疏忽其中任何一端,则我人对仲治的认识就不很正确的。[22](P.13)
这样的说法较为通达,也很能体现社会科学寻求“弹性的”普遍理则之特质。
社会科学企图从人类行为中,归纳出若干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则,以便对人类行为进行解释,甚至对未来的发展提出预测。就其对人类社会的普遍理则的追求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近似新康德学派哲学家温德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所谓的“理则的知识”(nomothetic knowledge)。
2.汉学研究的性质 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述特质,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如文学、历史、哲学等,都具有强烈的描述特殊人物性格或事件发展的倾向。举例言之,传统中国论述政治的文献多因本于致用之目的而缺乏原理性之探讨,萧公权(1897~1981)先生说:
中国学术,本于致用。致知者以求真理为目的,无论其取术为归纳、为演绎、为分析、为综合,其立说必以不矛盾,成系统为依归。推之至极,乃能不拘牵于一时一地之实用,而建立普遍通达之原理。致用者以实行为目的,故每不措意于抽象之理论,思想之方法,议论之从违,概念之同异。意有所得,着之于言,不必有论证,不求成系统。是非得失之判决,只在理论之可否设张施行。荀子所谓“学至于行而止”,王阳明所谓“行是知之成”者,虽略近西洋实验主义之标准,而最足以表现中国传统之学术精神。故二千余年之政治文献,十之八九皆论治术。其涉及原理,作纯科学、纯哲学之探讨者,殆不过十之一二。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23](P.946)
包括大量的政治文献在内的传统中国人文研究论著,多半注重“特殊性”而较少关心“普遍性”(universality),接近于温德班所谓的“意喻的知识”(idiographic knowledge)。
因此,从方法论倾向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与汉学研究实不免有其相互紧张性存在。这种紧张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理则的知识”与“意喻的知识”之间的紧张性。
三、紧张性的克服:从互相对抗性走向互为主体性
现在,我们可以问:社会科学研究与汉学研究之间的紧张性是否能够被克服呢?我认为:(1)中国人文研究实际上常常“即特殊性以论普遍性”,并且从具体经验中提炼抽象命题,而且,(2)中国经验潜藏着大量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意识,可以补当前中文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之不足。所以,(3 )两者间紧张性之克服实建立在两者“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基础之上。我们阐释这三项看法。
1.从特殊性到普遍性 所谓中国人文研究只关心特殊性这种一般印象,实际上是一种过度渲染的说法。中国人文研究所使用的文献,虽然很强调人物或经验的特殊性,但是,却也很重视对具体而特殊的现象,进行通则性的观察,例如《孟子·告子下》归纳历史事实而指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王夫之(船山,1619~1692)的《宋论》、赵翼(云松,1727~1814)的《廿二史札记》,皆对历史事实及其发展提出许多通则性的看法。我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在儒家经典中所见的对黄金古代或典范人格的叙述,都是以朝向建立普遍的道德理则或抽象命题为其目的。因此,儒家历史学实质上是一种广义的道德学或社会科学。在这种特质之下,儒家历史叙述是一种证立普遍理则的手段。在儒家经典中,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之间有其互相渗透性。在儒家传统中,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所谓“性与天道”皆寄寓于具体的前贤往圣之行谊之中,经典正是载“道”之器。在道器不二、理事圆融的儒家传统中,普遍而抽象的理则,只有在特殊而具体的历史经验中才能觅得。在汉学研究中,“经”、“史”通贯,理事并观,求“一贯”于“多识”之中,展现一种“寓抽象性于具体性”及“即特殊性以论普遍性”之关键性特质。(注:见黄俊杰:《儒家论述中的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收入拙著:《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1,页73~104);关于中国人特重“具体性”与“特殊性”的思维习惯,参看中村元:《东洋人思维方式》(东京:株式会社春秋社,1988年第4卷)。 此书有简编之英译本,Hajinme Nakamura,edited by Philip P.Wiener,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India,China,Tibet,Japa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64),Chap.17,pp.196~203。)
2.汉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汉学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项重大意义是,可以提供深具亚洲文化特色的新的社会科学问题意识,可以丰富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内涵。
现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论述或议题大多源自西方经验与学术。诚如张光直所说:
在大半个世纪中支配全球一小半人口的史观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讲社会结构要读韦伯与列维·斯特劳思;讲语言要引福柯和强姆斯奇;每年一个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没有研究中国经济的;美术史的理论中心一直在欧洲。[6](P.64)
近数十年来海峡两岸中文学术界流行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说,莫不是源出西方社会而由欧美学人所论述,再经由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留美青壮学人的引介,而成为流行的学说。我们尚未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时间悠久而内涵丰富的中国历史经验作为基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提出重大而基本的命题、学说或理论。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家未能植根本土放眼世界,正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我举国际社会科学界很受瞩目的“人权”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当代社会科学界及国际政治界所谈论的“人权”概念,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我最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说明:(1)现代的人权观是一种权利本位的道德价值(Right-based morality),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Rights)的合法性与不可剥夺的权利。(2)“人权”这项价值是现代国家中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的天赋利器,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人权”这项价值理念,常常是在个人与国家对抗的脉络中被论述的。
相对于以上源自近代西方文明的现代“人权”理念,传统中国文化中有以下两个方面对于现代的“人权”理念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1)传统中国文化中“人权”的价值观是一种德行本位的道德价值(Virtue-based morality),中国人所强调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责任(Duty)的不可逃避性。人因其身份而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如父慈、子孝等,这种责任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而且它也有深厚的宇宙论的根据,它是“天”所赋予人的不可逃避的天职。(2 )传统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是人依其职位而相应的应尽的职分,而不是如近代西方所强调的契约。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世界中所强调的是人之反求诸己,每个人尽其职分,而不是人与国家透过契约关系的成立而让渡属于个人的部分权利以换取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以上这两种传统中国的价值观——责任重于权利、职分先于契约,都与传统中国的联系性思维方式有深刻的关系,而可以丰富社会科学中的“人权”概念的内涵。[6](P.35)
3.从西方支配到互为主体 当前海峡两岸中文社会科学界中研究有关“国家”(state)、“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性”(rationality)、“权力”(power)等议题的文化资源均来自西方经验,而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支配性地位,将原是从具体而特殊的西方经验中所建构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推广而成为普遍的学说。在这种推广过程中,西方学术“典范”(paradigm)实居于霸权之地位。
我认为,21世纪中文学术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从西方支配走向东西互为主体。我们愈深入中国历史经验与人文传统,愈能够出新解于陈编,愈能够提出新的社会科学概念与命题,而与西方的同事进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汉学研究如果愈能参考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就愈能够开拓新的视野,从而可以提出具有普世意义的新命题与新理论。社会科学与汉学研究本来就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