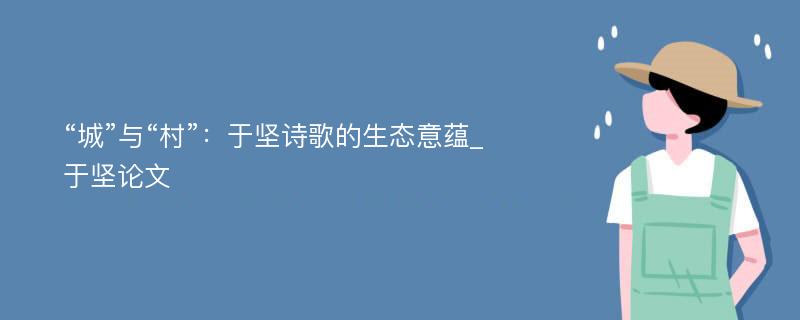
“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乡村论文,诗歌论文,生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6)06—0077—07
新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诗歌样态与诗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朦胧诗派挥手告别的“第三代诗人”,其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是诗歌创作主体刻意追求的审美特征。尽管“第三代诗人”倡导并实践着口语化的诗歌创作,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诗歌无论怎样口语化,仍然需要用“意象”传达生活与心灵的丰富性。说到底,诗歌是意象的艺术。可以说,离开了意象,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和中坚,于坚的诗歌其意象可以说是繁复的。拨开繁复的枝叶,我们发现于坚的诗歌有两大意象,或者说有两大意象系统,即“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意象,构成了两大诗歌话语体系,亦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这其中极其重要地包含着一种生态寓意。
一 “城市”和“乡村”:生态失调与生态和谐
诗歌乃至整个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反映。作为诗歌来讲,农业社会必然造就了诗歌的乡村抒情气息和浪漫色彩。古今中外的诗歌概莫例外。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从机器和烟囱中繁荣和昌盛起来,在承载物质文明的“花朵”的同时,也衍生和聚积着社会与人性的“恶”。19世纪后期出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不少篇章把“忧郁”和“绝望”献给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在中国,正如吴思敬先生指出的:“新诗从诞生以来,一直以城市为吟咏的对象之一。共和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的城市诗,是以礼赞城市建设新貌为主线的。进入新时期后,城市进入更多诗人的抒情视野,城市诗成为当代诗坛的重要景观。”[1] 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商品经济的浪潮加速了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诗歌,作为社会的神经和触角,总是会对日益变动着的生活作出敏锐而及时的反映。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城市诗人诞生了。于坚虽不能划在城市诗人之列,但是他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描写了城市生活。他的城市诗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摹写或抒情,而是有着更深的心理期待,可以看作是一部“城市生态学”的诗性记录。与此同时,他又常常抽身而出,在“乡村”的原野里走动,同样从精神的层面,完成了“乡村生态学”的考察和思考。“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意象及其意象群,构成了两种生态的存在样式。“城市”以生态失调、失衡成为了和谐、诗性的“乡村”生态的映照,二者的烘托和纠结以及诗人心灵的游走又实现和升华了诗人的理性期待。
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是要以牺牲自然天性和心灵神性为代价的。在扩张的街道、兴建的工厂、崛起的楼群和超级市场的背后,健康、单纯、诗意的自然景观和心灵图式在发生着残酷的改变和变异。栖居在“尚义街六号”的诗人于坚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切并加以了精细的描绘。诗歌《作品89号》把“城市”和“乡村”叠合在一起,既有对“工业时代”的忧心忡忡:“世界日新月异/在秋天/在这个被遗忘的后院/在垃圾/废品/烟囱和大工厂的缝隙之间/我像一个唠唠叨叨的告密者/既无法叫人相信秋天已被肢解/也无法向别人描述/我曾见过这世界/有过一个多么光辉的季节”,同时又把目光深情地投向了充满神性的乡村:“我承认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隅/属于那些金色池塘/落日中的乡村”。可见诗人在描写“城市”的时候,“乡村”成为了他的心理背景和情感依托。因此,他总是寻找和发现着城市中带有乡村气息的自然图景,在表现其曾经拥有或现在尚存的诗意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地悲叹着诗意的萎缩、流失和病态。诗歌《礼拜日的昆明翠湖公园》描写了“小桥亭子”、“茂林修竹”的公园以及流淌于其中的人性的温暖和诗意。公园,是城市中微缩的“乡村”,是人性的最后最美的一块栖息地:“一个被阳光收罗的大家庭/植物是家什/人是家长/活着的/都是亲属”。可就是这样一处绝美的风景,在城市的包围中正一点点萎缩:“离开公园/在五幢楼一单元的第七层/亮处看见这块地皮/确实只是/黑暗的一小盆/边缘/正在霓虹灯的围观下/一点点/萎缩”。当然,萎缩的不仅仅是千金难求的公园,还有与公园相依傍的人的精神领地。就连诗人所在城市的“千年的湖泊之王”——滇池也成为了“腐烂之水”、“生病的水”,“那蔚蓝色的翻滚着花朵的皮肤/那降生着元素的透明的胎盘/那万物的宫殿那神明的礼拜堂”,忽然间无影无踪,“从永恒者的队列中跌下”,诗人一方面哀悼它的不幸的死亡,一方面审视“新城”的夜晚从身边走过的“干燥的新一代”,同时还检讨了自己的心灵:“我要用我的诗歌为你建立庙宇!/我要在你的大庙中赎我的罪!”在诗人看来,包括滇池在内的“神殿”不仅构成城市的生态环境,也构成诗人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诗人“诗歌的基地”、“美学的大本营”、“信仰的大教堂”:“诗歌啊/当容器已经先于你毁灭/你的声音由谁来倾听?/你的不朽由谁来兑现?”(《哀滇池》)因此诗人的哀悼中有着更深的悲痛。
“城市”更多的在改变人的心灵。被街道、楼房和围墙所切割的生活,被程式化和繁文缛节所包围的生活,造就了人的隔膜、伪善和虚荣,带来了人性的压抑和失落。为生命画像的《事件:结婚》、为心灵写意的《事件:围墙附近的三只网球》等诗歌,在“事件”的缓慢的叙述和罗列中,由社会现象和生活现象切入到人性滞重而芜杂的层面。诗歌《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选取的观察点是“咖啡馆”,亦即以“城市”作为背景:小雨点“在滑近地面的一瞬”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于是“改变了一贯的方向/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渐渐膨胀/囤积成一个/透明的小包袱/绑在背脊上/攀附着/滑动着/收集着/它比以前肥大/也更重/它似乎正在成为异类”,最后“满了/也就断掉/就是死亡”。诗歌形象地描写了小雨点在外物的作用下发生异化直至死亡的过程,显然,这是一个象征,城市中某种人生和心灵的象征。“城市”的天空和地面在时时刻刻改变着人的观念和心态,改变着人的命运和结局。也许小雨点的异化和死亡不是它的悲哀,因为最终它“保持水分”,没有失掉本性;但就人来说,在外物或外力的影响下,欲望的“膨胀”和心灵的“重量”所导致的异化和死亡,则是令人深思的。
诗人要凸现的是“城市”以一种“物”的拥挤和膨胀对人及其精神的挤压和消解,“城市”以其强势姿态对人的精神主体性构成集体谋杀:人和人的心灵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无处逃遁。诗歌《事件:停电》,选择停电的夜晚,诗人在黑暗中于有限的空间触摸着庞杂而琐碎的“物质世界”,唯一能够感知的就是无处不在的“物”,而作为生活主体的“人”隐遁了、消逝了。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房间”里的日常生活用品,不惜以伤害诗歌的内在诗性陷入对停电“事件”的叙写,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人的物化的外部感知,虚化人的地位和精神主体性:“城市”跌落进停电的夜晚,生命在黑暗中笨拙地转动。在这方面写得最形象最动情的也许要数《事件:棕榈之死》。于坚的诗歌一般是客观的描写和叙述,带给人的是思考和联想,但这首诗歌在对棕榈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中,有着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坚硬/挺直/圆满/充盈弹性和汁液”的棕榈,是生命和激情的象征,它“蓬勃向上/高尚正直/与精神的向度一致”,则又升华着某种人格的高度,但就是这样一棵树,成为了一棵“受难的树”。因为在“欣欣向荣的商业区城市的黄金地段”不适合一棵树的生长,先是“它的根部被水泥包围”,最后“新的购物中心破土动工”,它被残暴地砍倒了。城市“最后的绿头发”在众目睽睽中消逝了。城市的生态就这样被破坏掉了。不仅如此,棕榈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城市生态的毁损还包含着一种精神性的内容。稍加比较,不难看出,同样是写树,“五四”时期沈尹默笔下明月霜风中的“树”,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舒婷笔下作为爱情独白的“树”,都是从人格、人性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的,“树”是人的情感和理想的投射物;而于坚在这里,是把“树”作为“城市”的一处生态标志和生命寓所,思考人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写作重心的转移是显而易见的。
有时候,诗人借“城市”复现一种历史的记忆和情绪,表达对“历史生态”和“政治生态”的思考。城市,刻写着更多历史的印记。诗歌《事件:暴风雨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让“城市”摇晃的暴风雨,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却叫人想到历史上的暴力和暴动:“雨水/雷和风/内容与革命完全不同/但会使经历过的人/记起那些/倒胃口的词”。现实中的暴风雨和历史上的暴风雨交织为一种错乱的感觉和记忆,让人胆战心惊。历史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失重、失衡带来人的心灵的“水土流失”,使人陷入长久的精神恍惚和虚脱。这是社会历史的“生态后遗症”,在让“城市”承担历史重荷的同时,也让个体生命付出代价。这方面的作品,还有《那时我正骑车回家》、《女同学》等。
而当诗人来到“乡村”的时候,或者说当诗人以“乡村”作为意象和空间观察点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描写内容的转换,更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审美眼光和审美心理的转换。亦即诗人希望通过对“乡村”生活的心灵感知和精神触摸,表现一种人与自然诗意相处的生态图景。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外部关系和空间关系,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生命关系和精神关系。当然,对乡村自然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生命个体的诗意表现,这是流淌于诗歌河道上的美丽的浪花。但是,当把“乡村”放在“城市”背景下来表现的时候,空间视点的拓展带来了审美心理的重组和变异,使诗歌具有了新的审美意义。
于坚笔下的“乡村”与传统诗歌中的乡村一样,装载着自由的生活和灵魂。“站在收割过的田里/听打谷场上的声音/风爱每一棵树/人也爱风”(《作品41号》),自由欢畅的风,是乡村生活的另一种形态,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造就了心灵的豁达和生命的欢愉。诗歌《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显然是以“城市”作为背景,表现人生旅途上对“乡村”的亲近和眷恋。“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假如你路过一片树林/你要去林子里躺上一阵/望望天空/假如你碰到一个生人/你要找个借口/问问路/和他聊聊”,在这里,人和环境的关系变得亲近了,人和人的关系变得亲密了,“城市”中的压抑和隔膜一变为心灵的轻松和畅快。于是便有了对鸟的歌唱的倾听,对河流的打量和对林子的神秘感知,以至最后发出生命的感慨:“你发现活着竟如此轻松”!这种生命的感慨,是“乡村”的清风和白云打开生命“城堡”之后的欢歌。
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内在精神的契合。当自我心灵放松的时候,身体和精神的每一个毛孔和感官都会打开,人就会融入大自然的神秘与诗意之中。当诗人独坐于“大高原”——这里“乡村”的意象被“大高原”置换——整个世界以“声音”的形象集中于他的耳膜:“那是树叶和远方大海的声音/那是阳光和岩石的声音/那是羊群和马群的声音/那是风和鹰的声音/那是烟的声音/那是蝴蝶和流水的声音……这伟大的生命的音乐/使我热泪盈眶”(《作品105号》)。这是一种幻美而神秘的感知,在诗人心灵世界和乡村世界的感应和沟通中,分明看到诗人精神的飞扬和生命力地跃动。诗歌《苹果的法则》,把“乡村”定位于“云南南方”:“一只苹果/出生于云南南方/在太阳/泉水/和少女们的手中间长大”,“当它被摘下/装进箩筐/少女们再次陷入怀孕的期待与绝望中”。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的遇合,带来了心灵的遐想与期待:苹果的生命历程,暗示了“少女们”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这种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循环,则构成人与自然的生生不息的梦幻和命运。
与立足“城市”表现“物”对人的心灵的挤压不同,于坚漫步“乡村”的时候,彰显的是人的精神性,“物”已美化和诗化为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命依托。因此这类诗歌有一种生命个体的精神维度。一生向着高处攀登的“男女”(《高山》),横渡怒江的“鹰”(《横渡怒江》),“使我的灵魂像阳光一样上升”的棕榈树(《阳光下的棕榈树》),像高原鼓起的血管的“河流”(《河流》),都激荡着生命的激情和热力。诗歌《独白》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望:“每当秋天/庄稼在月光下成熟”,心“渴望高贵/渴望不朽/渴望面对大海/自己从此就宽阔而深厚”。是“乡村”秋天丰收的原野激发了人的永远的追寻。生存空间的“外物”没有成为心灵的束缚,相反点燃了精神的火焰,是诗性对诗性的激发,是灵魂对灵魂的拥抱。人和自然构成一种内在的精神对话和交流。
和立足于“城市”描写底层人的生活一样,于坚笔下的“乡村”生活同样充满平民色彩。不同的是,他的“城市”诗歌主要是写普通人生活的窘迫和无奈,而且常常回溯历史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表现权力和政治对人的精神性结构的渗透和改变;而其“乡村”诗歌则表现劳动者生命的舒张和精神的惬意,关注他们“此时此刻”平凡而诗意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和“神性”的相接相通、相伴相亲。在于坚看来,诗人“是神的一支笔”,“是人群中唯一可以称为神祇的一群,他们代替被放逐的诸神继续行使着神的职责”[2],“神对于他们,不需要寻找,更不能炫耀,众神从他们诞生的时刻就住在他们家中,住在他们故乡世界的山岗树林河流以及家具之中。他们不拯救,他们只是呼吸着,在众神的空气中”[3]。作为离神最近甚至就生活在神中间的诗人,于坚在乡村世界中倾听着神的声音,感受着神的光辉。这样,在故乡的土地上的锄地者(《想象中的锄地者》)、从黎明到黄昏种土豆的人(《速度》)都是诗人乐意表现的,他们劳动的过程就是生命的过程,他们劳动时的姿势和乡村景观构成绝美的风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与大地在相亲相爱中浑为一体。诗歌《篱笆》中的篱笆:“它被牢固地安插在红色山地的中心/远离一切边缘/它并不是广场上的一尊雕塑/不过是一截篱笆”。诗歌借“篱笆”表达了对“人”的位置的思考:在乡村像篱笆一样的普通劳动者永远居于生活的“中心”,他们虽然没有城市广场上的“雕塑”高贵,但他们有自己存在的尊严和价值。这首诗歌还把农家小舍及其环绕它的诗意般的生活场景喻为“神的寓所”,一切都仿佛充满神性,那么美妙动人。于坚的“乡村”诗歌常常用“神”或“神性”设喻,不过这个“神”或“神性”不是高高在上君临万物,而是由诗意的生活所创造所包含,是内蕴的,是抒情的,而且和普通人的生活融为一体。进一步说,就是神性和自然性以及人性互含互生,构成一种“乡村生态”的诗性存在。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和“乡村”在于坚笔下构成两种生态景观。这种生态景观虽然也涉及外显的空间关系,如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等,但作为诗歌,主要是从诗性的角度而非物质的角度、从精神的层面而非空间的实体来表现的。“城市生态”的失衡,除了表现为“城市”对自然诗性的扼杀和放逐之外,还主要表现在城市的现代感和超速发展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弱化和精神的虚化之间的矛盾;而“乡村生态”的和谐不仅表现为自然万物的各得其所、共生共荣,还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人与自然的精神沟通和心灵感应。因此,从根本上说,当诗人忧患于城市生态而欣喜于乡村生态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一种贯通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内在的生态和谐,或者说是在幻想用乡村的自然神性和人生诗意来寻求城市生态的平衡。可见,诗人在为城市画像时,并不是要消解现代物质文明,以求得城市生态的协调发展;在为乡村素描时,也不是要放纵自己古典式的怀旧情绪,退回到宁静而原始的乡村社会中去。从深层来讲,诗人关注的是超越城市与乡村界限的精神生态和心灵生态。
二 从“城市”到“乡村”:寻找心灵生态的平衡
是这样一个“城市”,一个美与诗意正在流失的城市,一个充满忧郁、贫困、病痛和暴力的城市,一个人的心灵和诗歌无处安放的城市。诗歌《在牙科诊所》简直像个寓言:一边是嘴和牙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一边是诗歌与心灵世界的联系,“我像间谍那样/匆匆地记下了这些神秘的符号/他看不懂/我也无法将此事说清/诗歌/对这些病人/你叫我如何开口?”从“这些病人”身上不难看出“病”与“城市”的内在的因果关系。看来,心灵与诗歌的突围是必然的。
诗人的心灵向着“乡村”突围。只有乡村才能给诗人带来美好的回忆,满足诗人心灵的幻想和对激情的渴望。当诗人生病的日子,在一束阳光的照耀下,情不自禁地“想起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想起大地/想起树林和山冈”(《探望者》),“阳光”成为了生命的通道,使诗人从“病房”暂时进入温暖的乡村回忆,从而周身弥漫了一种生命力:“仿佛变成了一株植物/我就要长出叶子”。当诗人在城市之外发现一块空地时,幻想用来盖一幢别墅,“森林”为伍,“泉水”相伴,“豹子”为邻;而当幻想的房子建成时,“朋友和亲戚前来拜访/大家兴高采烈谈些城里的事情/那头高傲的豹子再也没有出现”(《空地》)。显然,这是诗人希望从“城市”突围出来,为心灵建造一栋房子,在那里人与自然诗意相处,亲密无间;可是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即使心灵的房子建成,也无法逃脱“城市”话语的干扰,心灵生态的和谐与宁静随即遭到破坏。诗歌《我梦想着看到一只老虎》同样是诗人的幻想,同样是心灵与想象的突围。诗人希望“远离文化中心远离图书馆”,“从一只麋鹿的位置”与一头老虎遭遇。这是对回归自然人性的渴望,对生命激情的期盼。
难怪诗人这样钟情于对“路”的描写。因为“路”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可以打开生命和心灵的城堡,引领人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诗歌《1987年12月31日》:当城市的晚间新闻报道毒品和股票市场的时候,当人们围着圆桌吃喝的时候,“我沿着雨后发亮的道路/走向一处树林”。尘埃洗尽后的“道路”通向诗意之所在,“故乡”在道路的另一端召唤着诗人的脚步。诗歌《弗洛斯特》:在离“大街”只有一墙之隔的住所,读弗洛斯特的诗歌,被带入乡村田园的诗意之中,“我决定明天离开这座城市/远足荒原/把他的小书挟在腋下/我出门察看天色/通往后院的小路/已被白雪覆盖”。诗性包裹的“小路”通向心灵的“后院”,通向美丽的“荒原”。
那些描写和表现“乡村”的诗歌,可以看作是诗人从城市突围出去之后的歌吟。阳光般的心情、生命的喜悦和激情、希望有所作为的内心冲动,在乡村的怀抱里一一流露和表达出来。这是进入生命和谐与神志畅快状态后的心灵放松,也是心灵放松后的对自然神性的更深层的领悟和感触。于是,诗人眼中的“树”不仅像是“神子”,而且也是自己生命和心灵的象征;耳中的“流水”不仅是大自然诗性的召唤,而且也是诗人获得身心自由后的激情的回旋;头顶的“鹰”不仅是世界的征服者和俯视者,而且也是自己向着高处攀登的精神标杆和心灵坐标。心灵向着世界打开,人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平衡和精神解放。
当然,生活在城市中的诗人更多的时候是无法逃离。“我是这个房间的敌人/细菌/和闷闷不乐的幽灵/但这是上帝赐予我的惟一的房间/如果我不能适应/我就无家可归”(《无法适应的房间》)。人在无法逃离“生活现场”的时候,神便赋予他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期待。于坚在目睹和感受了“城市”的灰暗和重压后,自然在“房间”里就希望打开一扇美丽而明亮的窗子——这个窗子是用那些充满神性的事物做成的,它能引领人的目光到达辽远而富有诗意的境界。风、雨、雪和海鸥等等具有自然神性的事物便以它的激荡、滋润和翩然的姿态成为“城市”的净化者和装饰者,成为诗人心中取之不尽的幻想的产物和瑰宝。诗人在《赞美海鸥》中写道:“一只海鸥就是一次舒服的想象力的远行/它可以引领我抵达/我从未抵达/但在预料之中的天堂/抵达/我不能上去/但可以猜度的高处/十只海鸥就可以造就一个抒情诗人/一万只海鸥之下/必有一个诗人之城”。“天堂”也好,“诗人之城”也好,应该说都是一个美的住所,一个万物和合、诗性交融的住所,一个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住所。这是诗人的想象力伴着海鸥的一次美丽飞行,是诗人的关于“城市”的生态童话和理想。从精神的内在性来说,这依然可以看作是诗人从“城市”向着“乡村”的行走和突围。
生态意识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生命关怀。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衡源于人类的自我中心和生命强势。那么反映到文学上,生态意识必然是对生命的注目和关怀,特别是对弱小的、弱势的生命个体或生命群体的注目和关怀。史韦兹提出了“敬畏生命”伦理,他认为,人类的同情如果“不仅仅涉及到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就是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的伦理[4]。于坚的诗歌在城市生态的构建和乡村生态的赞美中充满着一种人文关怀,灌注着一种生命的悲悯意识。在于坚的笔下,蚂蚁、蝴蝶、兔子、乌鸦等等,各有其生存的价值,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有着丰富而广大的内心世界。诗人为“蝴蝶”的受难而悲伤,为“蚂蚁”的自由而欣喜。特别是《乌鸦》一诗,充满着一种大胆的反叛精神,在对乌鸦长久以来受到的歧视和伤害表示不平的同时,不仅为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乌鸦正了名,而且对某种社会心理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诗人看来,“乌鸦的居所/比牧师/更挨近上帝”,“乌鸦是永恒黑夜饲养的天鹅”。可见,自由飞翔的乌鸦,在穿越城市和乡村上空的时候,它用它的颜色和声音证明了它的存在和价值,它同样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元素和音符,人们没有理由对它抱有偏见甚至扼杀它。于坚的诗歌超越了简单的黑与白、美与丑的定势思维,进入到内心的细腻和丰富、善良和悲悯,用生态的眼光和诗性的眼光打量着城市和乡村中一切有生命的事物。
三 作为文本:新诗链条中的诗歌生态
诗歌作为一个系统,也体现出生态特征:在诗歌的疆域或流变的过程中,从诗歌精神到诗体形式总是维持着一种互补或平衡的态势。事实证明,诗歌内涵的苍白化和沙漠化,诗歌形式的僵滞和凝固,就是对诗歌生态的损毁和破坏,必然导致诗歌元气的损伤和诗歌格局的单一。诗歌总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拯救自己,唯其如此,诗歌才能在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学生态环境中保有光鲜的面孔和饱满的精神。放在纵向的诗歌生态链中考察,于坚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具有了一种诗歌生态学的意义。
从诗歌色调以及诗歌精神来看:中国新诗完成了从“红色诗歌”到“蓝色诗歌”再到“绿色诗歌”的转变。战争年代把鲜血、红旗、号角和阵地交给诗歌,诗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呐喊和冲锋;这个时候,诗歌着重表现的是人和人、人和阶级、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从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方面思考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和平年代,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诗歌瞳孔对准的是黎明、炊烟、蔚蓝的天空和海洋;这个时候,诗歌着重表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亦即人如何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从而高扬人类的伟力和尊严。直到于坚及同时代诗人的出现,才改换了视角,淡出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收敛人类自我膨胀、自我扩张的翅膀,从人的生存环境,从人和城市、人和乡村的生息与共、心灵体验方面搭建诗歌的房子,迷人的充满盎然诗意的“绿色”成为了诗歌建筑最美丽的窗子: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类心灵深处最美好的期待。早在1986年,于坚在他的诗集中,就提出这样的见解:“天人合一,乃是与今日现时的人生、自然合一,而不是与古代或西方或幻想的人生、自然合一。”[5] 可见,对人生的关怀,对自然的关注,以及对人生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的关切,在于坚的诗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么,当年街头飘扬的“红旗”,在于坚笔下就变成了绿意尚存的“棕榈树”;当年像铁栅一样淋漓的“血字”,在于坚笔下就变成了被绿色环绕的“篱笆”;当年的“战场”和“建设工地”,在于坚笔下就变成了人性温暖的“公园”和千年的“湖泊之王”。显然,诗歌色调的改变,也是诗歌视点的改变、诗歌审美关系的改变和诗歌精神的改变。
从诗歌表现的主体来看:中国新诗经历了从自我吟唱到英雄之歌再到平民之歌的发展历程。“五四”时代的诗歌是诗人心灵的歌吟,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相当长一段时间,英雄的时代催生了诗歌激情的歌喉和崇高的旋律。虽然“五四”时代“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带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但那是在封建时代“神的文学”、“贵族文学”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且就诗歌来讲,平民化的色彩远远赶不上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样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的主体性地位特别是普通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突出和强调。于是诗歌的视线开始整体性下倾,深入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和心灵状态。于坚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于坚的城市诗歌,侧重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困顿和窘迫,以及精神与心灵遭受的挤压;而乡村诗歌,则多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凸现人的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舒放。在这里,于坚的平民之歌实则隐含着一种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的意义,他用诗歌传达了一种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诗意共存。
从诗歌语言来看:中国新诗由诗歌语言的超负荷承担到诗歌意象的集束呈现再到“诗到语言为止”的追求,显示了对诗歌语言生态的建设性态度。曾经一度诗歌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装载着思想理性和情感激流,语言以一种充血状态和紧张状态在一定的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美感。承现代主义诗歌一脉而来的朦胧派诗歌钟情于意象的营造,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意象成为语言的花朵,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审美价值。而到于坚及“第三代诗人”,诗歌内容的平民化和日常化,带来了诗歌语言的琐细化和凡俗化。和朦胧诗派比较,于坚及“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语言,不是“寄托性”的,而是“写实性”的;不是“提炼性”的,而是“还原性”的;不是“聚焦式”的,而是“散点式”的。这不是说于坚的诗歌语言就是随手拈来的,他也很注意语言的“摆弄”。正像他在《事件:挖掘》一诗中所写的:“取舍 推敲 重组 最终把它们擦亮/让词的光辉洞彻事物”。看来他追求的是词语的一种呈现方式和组合关系,并由此掘进词语和语言的内部,使语言和生活取一种同步的姿态,或者说用语言直接描写和还原生活本身。有人认为,这样的写作完全是“异类”,“诗人试图怀疑每一个词语,并执意要回到词语的原初状态,这显然是当代诗歌新的写作难度,于坚是这一难度最早的挑战者——正是这样的写作,大大激发了于坚的原创力。……于坚一直使用一些‘旧词’,并在这种使用中使许多词语重新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它们与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在别人看来最没有诗性的地方,重铸了诗性”[6]。从意象的角度来看,虽然于坚的诗歌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意象,但这些意象也是对生活的贴近,呈现出写实性的倾向和特征。上面分析的“城市”意象和“乡村”意象,就完全是生活化和现实化的,隐现的只是一个大的审美空间和轮廓,体现出一种宏阔的视野和平实的笔调。正因为这样,围绕“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基本意象就衍生出大量相关相联的意象。我们也应该看到,日常生活语言的浮现与组合以及意象的生活化乃至凡俗化,就使得于坚的不少诗歌变成了“文字积木”。所谓“于坚体”,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积木体”。有技巧和想象的空间,但是以诗意的流失作为代价的。诗歌也就完成了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变。由此从阅读效果来看,诗歌从朗读的诗歌、精神触摸的诗歌,变成了“看”的诗歌、自由拆卸的诗歌。在这里只需要生活的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而绝少需要激情和诗意的储备。
也许从诗歌文本来看,于坚的探索有他的局限性。但如果把于坚的诗歌文本放在整个新诗链条中考察,就会发现于坚以及“第三代诗人”的出现,带来了诗歌新的生态景观。于坚奔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用诗歌种植了“绿色生态植物”,描写了“平民生活场景”,提供了“生活化的诗歌语言”,这一切加入到诗歌的生态链和生态圈中去,就使诗歌的生态景观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于坚诗歌的主要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