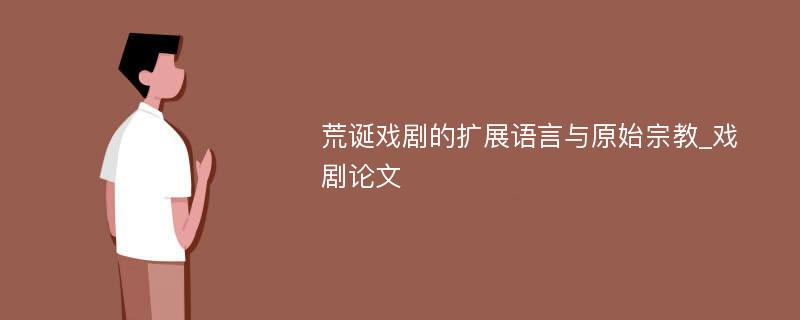
荒诞派戏剧的“伸延语言”与原始宗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派论文,戏剧论文,原始论文,宗教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荒诞派戏剧,国内的研究者多从历史的横面对它进行文化的“近点”研究,探讨它与现代非理性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本文笔者则试图追寻它更为久远的文化渊源,把它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作一次“远点”的文化透视。
众所周知,西方几千年的文明史与宗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著名文化史家道森把这种现象称为“基督教文化”,认为宗教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诸种文化实际上分别标志着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方式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类型。这就是说,宗教与文化是互融交叉的,它既影响人类文化,又是人类文化现象之一。原始宗教亦是如此。不过,由于数千年文化的深层积淀,原始宗教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已渗透到深处,成为潜藏在人类文化中的最深远而又最丰富的“矿藏”。荒诞派戏剧就是从这“矿藏”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挖掘出原始人非理性的质朴与率真,拓宽了原始人性的荒谬与怪诞,用梦幻直抒胸臆,伸延戏剧语言,演义悲剧主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此荒诞派戏剧与原始宗教产生了直接的渊源关系;思维上“返朴归谬”——使现代西方人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理性与原始人充满乐观幻想精神的非理性之间有了一种逻辑联系;心理上“返朴归真”——使现代西方人对社会绝望的孤独心理与原始人对自然敬畏的恐惧心理达到了一定的沟通。
一
所谓原始宗教,主要指原始人在自发进行巫术活动或图腾崇拜时对自身和外界世界表达出来的宗教观念和态度而言。这些活动本身虽很难说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更不是后来的宗教,但它们已包含了宗教的本质基础,而且同样是以主体感觉的方式存在。比如原始人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是由巫师借助幻想装成半神以企克服异己的自然力量。这表现了原始人的单纯主观意志——命令异己力量,控制自然神。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对待人的方式来影响灵魂”(注:弗洛依德:《图腾与禁忌》,第100页,第101页。);“万物有灵”则是魔法、图腾活动的依据。魔法同巫术一样以强迫的方式“必须使自然现象服从人的意志”(注:弗洛依德:《图腾与禁忌》,第100页,第101页。),目的仍是保护人的力量;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把动物、植物及其他物质看作所属部落的祖先的象征、氏族血统的来源,是对某种自身本质的体现加以崇拜。总之,原始人就是在这些活动中依靠幻想来理解自身及外在世界。虽然这些活动是以假幻想真,但它是原始人的“理性”表现,他们企图通过这些活动排遣自然界造成的巨大压力以寻找精神的支撑点。就此来看,荒诞派戏剧与原始人的这些准宗教活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本质的差别。一种是无奈于社会给予的巨大压力,只得以荒诞来表现内心的孤独、痛苦、焦虑、绝望,以示人与社会的分裂;另一种是企图借助神灵之威来排遣自然界施予的压力,去扩大对自然和社会的依赖。前者是以非理性表现理性,含有现代人深刻的批判和否定意识;后者是原始人对生活的肯定与追求,孕育着人类的智慧之光。但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在表现的形式上是如此相似——荒诞戏剧怪异的艺术手法和原始人荒诞的准宗教仪式都具有一种原始美感即强烈的动作性造成的动态美,扩大了视觉语言的效应。关于这种原始美感,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研究了现代残存原始部落的大量舞蹈材料之后,得出了很有见地的结论:原始舞蹈是“原始的审美感情底最直率、最完善,却又最有力的表现”,“只有比较少数的舞蹈包含宗教的仪式,而大多数的目的只在于热烈情绪的动作的审美表现和审美刺激”。(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第156页、第169页。)恩格斯曾更明确地指出,原始宗教活动中这种原始的审美特点在原始时代“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68页。)如原始人在巫术活动中,巫师带领人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以驱除某灵魂,或口中念念有词、手持利器劈剖祭物以祈神灵保佑;在魔法活动中则更强调一种感观效果。原始人用简陋材料把敌人画成模拟像,还要背诵特定的咒文,然后将这些模拟象一一焚烧。在求雨和求丰收的魔法中,为制造气氛,不仅伴有狂欢的舞蹈,模拟的形象更是极其广泛;在图腾崇拜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图腾的跳舞”。岑家梧在《图腾艺术史》里把这看作“原始戏剧表演之一形式,而为戏剧产生之渊源”。(注: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第53页,第96页)这种富于感官刺激的视觉语言构成了原始宗教的一大特色,对重视戏剧语言的荒诞派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经对当代法国戏剧产生过最强大影响之一的安东尼·阿尔托最早进行了这种舞台戏剧的革新。他经过考察和观摩一些东方舞蹈剧团的演出后,对东方戏剧突出动作这一身体语言,诱使演员进入恍惚、狂热状态的特色着了迷,提出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决心创造出一种无台词而以物质、具体的声音和形象以及音乐、舞蹈为主体的戏剧;加之他从自身的精神苦恼(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染上毒瘾)中更深切地体验到语言并不能表达真挚的情感和精神与肉体的痛苦、兴奋,必须以虚拟的手段用一种“内在现实”来表现。他首先从戏剧语言上突破,认为戏剧语言应该是无声的、形式的、灯光的、动作和姿态的语言,总之是一种视觉语言。戏剧应该努力表达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但“并不是要在戏剧中取消台词,而是要改变它的用途,尤其是要削弱它的地位。”(注:转引《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张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他宣称要“以中世纪黑死病那样的瘟疫的令人战栗的恐惧,及其毁灭性的全部冲击力,向观众猛扑过去,在它所袭击的人群中引起彻底的剧变,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剧变。”(注:转引《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张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在这种剧中没有通常意义的布景,而常以古代的人物,原始仪式中那些色彩斑斓的奇装异服、10米高的假人、与人一般大小的乐器、不知用途又奇形怪状的物体充当舞台布景。演员戴着庞大的面具像巨型雕像似地进行表演,程式化的面部表情和强烈而醒目的手势吸引观众进入魔术圈……音乐、舞蹈混在一起。这是一种诗意的、充满魔力的戏剧。它利用古代神话和原始宗教仪式的魔力将观众暴露在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最隐蔽的冲突面前,表现现实中更加真实、更加强烈的体验和孤独、恐惧、焦虑与绝望的社会心理状态。阿尔托这种理论和导演实践,已预示了荒诞派戏剧的某些基本倾向:特别强调视觉语言;主张用道具说话;使用道具要荒诞,要具有象征性,让无生命之物变成有生命之物;用环境气氛、舞台手段来表达人所无法表现的思想感情。
尤奈斯库在这种启发下,在戏剧形式上大胆创新,提出伸延戏剧语言,他说:“我试图通过物体把我的人物的局促不安加以外化,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形象……我就是这样试图伸延戏剧语言的”。(注:转引自朱虹:《荒诞派戏剧集·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于是他在《椅子》、《未来在鸡蛋里》、《阿麦迪或脱身术》、《新房客》等作品里,充分利用道具表现物的扩张与增多”,恰如“地平线包抄过来,人间变成一个令人窒息的地牢”,使观众产生了无法忍受的压抑感和虚无感,人在物的海洋中显得多么渺小、孤独。难怪有评论家指出:“没有一位当代戏剧家象尤奈斯库那样善于使家具那么雄辩地说话。”(注:转引自朱虹:《荒诞派戏剧集·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贝克特的视觉语言则以注重整体舞台效果和人物动作的单调、重复为特点。首先,他的剧本从人物的外部造型、环境布置、布景设计、灯光配备、音响效果、道具使用到人物的每一种表情、动作都有详尽具体的舞台指示,背景常常是极富感官刺激的画面:埋人的土丘、枯黄的荒原、闭塞的斗室;人物也是稀奇古怪:或置于口袋、坛子、垃圾箱里,或半截埋入土丘,或满地乱爬……以无声胜有声,烘托出强烈的悲剧气氛。其次是以静示动。贝克特认为:“只有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是纯正的艺术。”所以他的戏几乎都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情节的东西,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动作序列,前言不达后语的“对话”与絮絮不休的自言自语;戏中出场人物也很少,多数都只有一人或两三人出场。但这些几乎静止的舞台形象都构成了一幅幅奇特的滑稽可笑的场面,其中蕴藏着强烈的动感:人物空虚、潦倒、身残志弱,让人心绪不宁;人物孤独无言或绝望变态的絮絮之语、麻木不仁的行为动作让人心惊肉跳!这种“静场”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贝克特以淡化动作造成的这种视觉语言充满了原始艺术的美感,而且又是一种开拓。让·热奈对戏剧艺术的探索和大胆创新更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欺骗、假象是所有戏剧的核心,但在欺骗之后所要做的就是揭露骗局;在风格上,他刻意追求,着迷于东方戏剧的庄严、神圣、出神入化的魔力,把礼典和仪式搬上舞台。通常以礼典形式或幻觉形式表现,直接突出了原始宗教的动作美感。如《女仆》中女仆对主人的反抗就以带有向往的礼典形式出现,表述出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欲望。而这种欲在《阳台》一剧中则是通过人物五光十色的幻觉来满足。于是人物丧失自我的真实心理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
总之,荒诞派戏剧的伸延语言即视觉语言既有一种原始的审美,又有重大的戏剧技巧突破,正如尤奈斯库说的,“戏剧不仅仅是诉诸听觉的,也是诉诸视觉的。……戏剧里一切都是允许的:体现人物,也能够使焦虑、内心感受外化。因此,戏剧不仅允许,而且还要求使道具发挥作用,使物件活起来,使背景生动起来,使象征具体化。同样,戏剧台词由动作、表演、哑剧来延伸,当台词不足以表达时,这些就可以取代它,舞台的物质组成部分则可以夸大它。”
二
荒诞派戏剧的视觉语言与原始宗教强烈的动感和可视性之间除了外在形式上的联系外,还具有一些共同的思维特性即它们都是想象和幻想的产物。就一般意义看,宗教和文学的幻想和想象都要“大量地依赖于形象化语言和神话”。由于使用这同一种工具,所以“一篇宗教文章,可能被认为属于宗教,也可能被认为属于文学。同样,一部探讨不容置辩的人类事务的虚构作品,可能被认为基本上是宗教性的。”(注:N·弗莱、S·贝克等语,转引自《中西宗教与文学》马焯荣,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59页)语言文字的交叉形态使文学和宗教有了某些沟通,文学的幻想也可借助宗教的语言——视觉语言来进行幻想,以表达心灵的感觉和情感体验。荒诞派戏剧正是这样。
在原始时代,“语言有个共同的倾向:它们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态、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些语言力求把它们想要表现的东西的可画和可塑的因素结合起来。”(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0页。)比如南美巫师施巫术时为了不让人听见,用手势跟别人秘密地谈话,在这些手势里,手、胳膊肘、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行们也用手势语言回答,所以容易彼此交流,保持接触;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彼此不懂对方的有声语言,但他们能够用手势来相互交谈。人类学者马列克利专门研究了这种可视语言,说它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语法,自己的形式,为此“可以给这种手势语言编出一部厚厚的语法……即使根据下述事实也可以判断这种语言的丰富:不同部族的印第安人彼此不懂交谈对方的有声语言的任何一个词,却能够借助手指、头和脚的动作彼此交谈、闲扯和讲各种故事达半日之久。”(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3页。)原始社会当然也存在有声语言,但在当时的宗教仪式、礼典中,这种动作、手势的语言用得更多。同是幻想和想象,如果用可视语言而不是有声语言来表现,显然更易被接受,而且它所传达的信息容量更大,更具有一种神秘感。因此原始人的巫术、魔法及图腾崇拜虽然都有各自特定的方式和内容,但借助强烈的动作性表现出来的神秘感却是它们共同的特征。把这种神秘性与强烈的动作融为一体,原始人更能尽情地表现他们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更能展开丰富的幻想去模仿和塑造各自所需要的形象,以企在虚幻中找到真实感。巫术的形象模仿主要在巫师本身,他带领众人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去驱逐某一灵魂时,就伴有一定的情感体验;动物雕刻和绘画,在文化上被称为“艺术的魔法”,这是最典型的把“可画的和可塑的因素结合起来”的形象思维方式,目的是召唤魔鬼;在图腾崇拜中,幻想更具象征性,情感体验更直接,主要借助某一崇拜物表达对宗族祖先的敬畏、庄严而深厚的感情。由于可视性的张力作用,这种幻想的情感变成了真正的寄托。在这些笼罩着宗教气氛和神秘色彩的仪式中,通过视觉语言,原始人的幻想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原始宗教正是以幻想表现出极强的虚构性,而这种虚构性由于借助了可视语言,又把假当作真,使幻想中的神灵成为真实的存在。所以原始人的宗教又不是虚构,“它幻想出来的东西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各种图腾画像、魔鬼形象与存在物的联想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真正变成了同一,那些特别逼真的画像或者雕塑像就是生命实体的另一个“我”,就是原型的灵魂之所寓。不但如此,它还是原型自身。这之间极其生动的联想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魔法、图腾崇拜活动的基础,已含有一种朴素的“直觉体悟”,其中“思维的经验包含的推理只占极小的比率,然而它却包含了许多直接材料”,“它的集体表象经常具有极大的情感的性质。”(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76页。)可见视觉语言既是原始人表达宗教意识的重要媒介,又是渲泻情感表现心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历经数千年文明的沧桑,荒诞派戏剧承袭并发展了这种以主体感觉的方式创造的视觉语言。整个舞台不再围绕人物和事件转,而是综合表现作者的心理感受过程。于是现代人的非理性的梦幻揉进了原始人“理性”的幻想——现代人对社会厌恶造成的孤独心理与原始人对自然的非理性感知相沟通。由此构成了人类思维发展的逻辑联系,也由此形成了与传统文学的分水岭——由描写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向意识的主观现实转化。
在这种联系和转化中,荒诞派戏剧借助视觉语言成功地展现了他们的梦幻世界,以真为假,以假再现真,在虚幻的世界里再现心灵的真实,形成了独特的“梦幻”风格。他们把梦幻当作理性的思考。尤奈斯库说:“我很重视梦,因为梦使我有了更透彻,更深刻的看法。做梦就是思考,是以一种更深刻、更真实、更确定的方式思考,因为做梦如同自省。梦是一种沉思,一种思维。有时,梦特别富有揭示性,特别一针见血。”(注:转引《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张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他的好些作品如《空中行人》、《阿麦迪或脱身术》、《雅克或屈从》、《犀牛》等都通过梦幻或把恶梦变为现实,或探讨人生的荒诞、人类命运的虚无归宿,或揭示人被物的世界吞食的恐惧心理。难怪有人把尤奈斯库的创作(特别是他第二时期的创作)看作一种广泛的“社会参与”,认为他思考的中心离不开人和人的命运;认为他对荒诞的揭露使世人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能激励人们奋起反抗荒诞的命运。贝克特也是如此,他没有逃避残酷的现实,更以“无声胜有声”的可视语言“参与社会抗议”,使得他的思考更多了几分冷峻。热奈则善于让剧中人始终生活在别人造成的幻觉里,或与真实分离,没有真实存在(《黑人》),或用幻觉游戏让社会各阶层人物到梦幻中去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这种幻觉被认为是西方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惊人的假定之一。
他们还认为梦是真实,梦是心灵的表露。尤奈斯库说:“我们的真相在我们的梦里,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切事物每时每刻都在证实这一判断,虚构先于科学。”(注:转引《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张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因而他常在剧中用梦幻展现人的深层心理感受,而且始终强调梦往往是“现实主义的”,说戏中的梦境是现实世界的影射,是更真实的现实。阿达莫夫就把舞台当作最适合表现幻象的场所,在《塔拉纳教授》中,他通过梦发掘了自己个性中最本质最深刻的东西。正如尤奈斯库说:“对我来说,戏剧是内心世界在舞台上的投影。我是在我的梦中,我的焦虑中,我隐藏的欲望中,我内心的矛盾中吸取素材,这是我保留的权力。”(注:转引《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张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但他们在强调梦的真实的同时又极力强调现实的虚幻性,认为人生如梦,现实如梦。贝克特就用戏剧证明,真实与梦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真实是存在于我们脑际的东西,所以它与幻觉是共同性质的,人生犹如一场梦幻,到头来是虚枉的一场空,人的存在如抓一把水一样不真实。《等待戈多》就以无望的“等待”指出人类实践根本无价值,人活着实际上是死了——生活就像等待一样,是个空洞无聊的幻觉和骗局。让·热奈的戏剧更为大胆,他把现实演化为一种幻觉(《女仆》),将“人生如梦、现实如梦”直接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揭示了生存的荒诞和虚无。
总之,在荒诞派作家看来,深刻的思考受梦的启发;真实的世界、真实的情感存在于梦中;梦不是冥想而是形象;梦的形象最适合于舞台表演,就像原始人以宗教仪式表达真情一样。但荒诞派戏剧的梦幻并不完全等同于原始人的梦幻,它们是人类不同思维阶段的产物。原始宗教的幻想产生于无知和蒙昧,而现代西方荒诞派戏剧的幻想是人们彻悟后的结果。“上帝死了”,传统价值失落,人们竭力冲破宗教囚笼的桎梏去找回自我。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意识,但又借助蒙昧时代幻想的思维方式,这就使得真理与理性,虚无与非理性背逆,形成了思维的“二律背反”。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因为荒诞派是非理性的,就把荒诞仅仅看作是一种正常的蒙昧。相反在荒诞的非理性的骨子里,潜藏的是重建人类秩序的理性愿望,正如原始人在非理性的宗教活动中蕴含的是近乎理性的敬畏之心、庄严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样。不过,原始人是在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转而以宗教方式倾泻情感;现代西方荒诞派作家则是在他们的理想之柱坍塌,希望之光泯灭时,继而用虚幻方式进行自谑、自嘲。这正是人类思维高度发展阶段的现代西文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清醒认识。如此看来,用可视语言进行幻想和想象是人类思想交流的一种共同手段,它沟通了古往今来人类精神和心理发展的历程,使人类在不断的“返朴归谬”和“返朴归真”中获得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