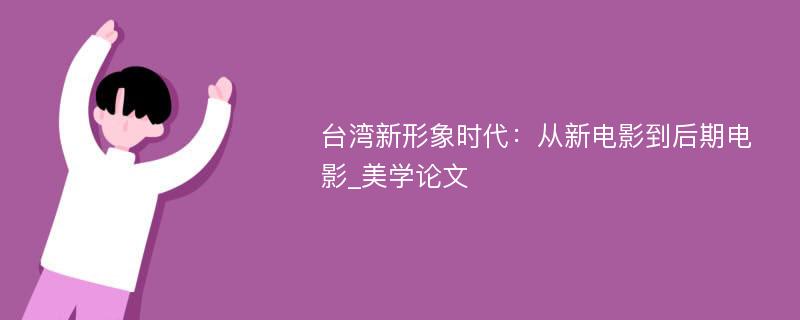
台湾的新影像时代——从新电影到后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台湾论文,影像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影像“需求”的经济相度
全球化的竞争挑起了新的经济问题,这经济问题大大地扩展了物资、物流、资本、技术、劳动、劳动力与产品的意涵;一方面,这些经济范畴过去的阶层关系与模拟性的属性关系,被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策略与市场机制所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跨越不同地理条件与交易状况的多样性及多变性网络,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在各方面——包含文化与艺术的面向——占取了决策位置的同时,也相对地使得原本分属于经济之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与市场都产生着过去所无法意料到的作用。然而,在这些作用的众多现象再现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需求”的繁生;“需求”不再只是过去对应于特殊族群与满足特殊功能的某种推断,也就是从八○年代到九○所谓的“创造市场”,而“生活样式的想象”更可以说是这一波广告化与市场化操作的滥觞。其中的“需求”所创造的意涵比较集中于族群设定的精确化、生活想象的开发与诱导、生命价值的商品化,而这三个相度都指向了“静态”主体的想象,意即完整生命的形塑与象征价值的确立。
然而,这样的需求开发在此之后的发展,却出现了一种转向式的延续,这种延续的特征就在于市场操作仍相信着市场的发生立基于需求的开发,而需求又指向想象的创新;但其中发生的转向在于消费族群不再是一种静态的恒常族群,而是某种特定时空下所能聚集的族群,并且,不再一味强调一种(生活)模式的想象,而是(生活)事件的想象,还有,发生商品化不再只是生命的超感性(象征性)价值,而是不断截入生命恒常的感性价值。如此,需求的开发指向了事件的“诱惑力”,提供的是一种跳脱生活恒常与打破整体想象的“偶发”想象,想象的构成与发生,从主体文本转向情境脉络。只是,这种事件性生命的想象——生机论的想象——并非真正地指向生命的颠覆(不论是否定式的还是流变式的),而是一种生态的加速:超验性的复苏与消费行为的加速。所以,对此特征的说明需要加注一项:虽然这种转向“浪漫”的生命追求,跟十九世纪哲学的浪漫主义一般,挑起了一种“美学”的转向,但这两次转向中的美学意涵却大异其趣,一是基于历史辩证产生对主体彻底超越(不论是黑格尔或是谢林),另一则是在一种布什亚所揭露的“安全性”意识形态之下,发展出一种以挑衅或反转主体位置或主体性的“趣味”。“趣味”建构了反叛主体的幻象,满足了“不满于此时此地”的欲望,并以此无穷的游戏保证着无止尽的“需求”,保证着市场经营的永续性。
无疑的,这个发生美学转向的市场策略已然汇合到全球化的经济运作里,趣味所衍生的需求,通过网络的复杂交错而大量地生产出“异类”趣味或“异类”需求,触及到过去市场反应所无法侦测出的个别差异,并以纷然杂沓的方式既分化着既定的文化品味,也以事件的方式集结着“即将”的族群。在“样式”的大量分化及其时间尺度上的压缩,过去由特定族群所保证的有效想象与最低利润却也因此瓦解(除了因为全球化而更坐拥垄断之便的大型跨国企业),进入到一种“微利”的操作,换言之,用样式替换的速度来累积所得:当需求与利润都是在速度中被实现时,一方面意味着需求与利润并非本质地潜存于物资、产品与消费者,而是在动态的物流、文化价值异动与消费生态下出现了事件性的独特时刻,另一方面,速度与动态使得成本与利润的额度都因为时间的压缩而出现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同调不仅可能削减着利益也可能出现骤然的利益空间。于是,我们不再从单一坐标的延伸来获取容积,而是从不同坐标的短瞬转换中,在行进中的容积差里捕捉到不同相度的容积:简言之,不再从同一性的延展计算量的累积,而是从差异性中集结不同构型的量。
“新”影像的内容:需求、本体与美学
我们便在这样的经济变动中,面对到“影像”的时代,面对到影像的“需求”问题;换言之,在这种流速越来越快的拓扑学中,对于影像的“需求”是一种“事件性”需求,是一种在发展轨迹中不断发生——足以扭转走向、甚至质性——的“新”的需求。于是,我们面对到一种本体式的生成论,一种生成的同时发生了根本——或说激进——的转化。这样的“新”意不再是过去唯心论所诉诸的天赋,也不会是唯物论所侧重的结构与形式,简言之,“新”,不再是形容词格,而是动态中的“独特点”,是行动中的“有效点”:意即“新”是一种介入。如此一来,当我们关注到新影像的问题时,就可以将问题转化为:新影像就是一种影像的介入,也就是足以构成事件的影像。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生产—消费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影像可以不作为任何存在的再现,而作为事件的创生,甚至,该事件性的生成足以“撼动”既定的再现次序。然而,这样一种影像的需求模式,不只是作为一种当代的特殊现象(历史上的),相反的,不论从“西方”或是台湾的经验来看,它早分别在五、六○年代与八○年代就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德国、南美洲和台湾地区发生;只是那时的“介入—影像”——作为事件的影像——是一种“抗争”的影像,对抗着资本主义与消费社会的“需求”,而不是作为经济现象的自然需求。它,以新电影为名的影像,并不作为一鲜明的全球化现象(地理上的),而是作为一种影像的“内在平面”:这内在平面足以描述出作为行动的影像,因为内在平面就作为“生成新关系”与“供予动力”的一种时间性平面。总而言之,事件—影像或生成—影像,一方面作为新的影像风格,另一方面往往也作为影像创作得以释放无比能量的“内在平面”。但今天,它却成为全球化时代与微利时代的“再现范式”,换言之,它不再作为内在平面的运作,而几近全然地“实在化”。在这一段概略的脉络性描述之后,如果我们回到台湾的历史现实来看,究竟在台湾发生过怎样的影像事件?而这影像事件又如何影响到影像世界的呈现?事实上,在台湾“当代性”的发展之中,新影像的创生——或说影像介入世界的事件——主要经历了新电影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重要阶段。当然,在时代的推展里,影像的创新常是一种接续性的转折系列,单以两个独特时刻加以论证,并无法完整再现或重建某种历史性的图式,但就构成事件的强度以及之后的影响力来说,我们还是得以标定出这两个特殊的发展,只是,它们并非以“某历史时刻”再现为事件,而是在整个影像动态的内在层面里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然而,何谓新影像?经由历史现象与文化政经脉络的捕捉,并不能够让我们理解到这些事件的内容;换言之,除了这些外在条件的认知以及意识到诸条件的内化状况之外,一种影像的“本体论”认知似乎是延展影像“美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这些外围条件及其内化都并非直接地作为再现内容,而是一种赋加于作品之上(或“之后”)的假设性与诠释性内容,一种开展问题与结构性介入的策略性论述。而在此所谓的“本体式”与“美学式”则是把对于作品的思考与认识引领到感知的表面及其流动变幻。“本体式”涉及到所谓的影像“本身”,这“本身”可以溯至影像存在及其作为存在之内容,但这“如此所在”(en tant que tel)的“本身”(或说“以己”(en soi)的当代意涵,首先就抛却了形而上学的建构,再则避免“再身体化”的现象学诠释,也同结构主义的问题性结构与批判性结构区分开来,当然也回避掉精神分析的建构式分析,而指向“特殊场域”的构成与论述:场域构成力的发散与动态的发生,并于其中进行数据的流通与质变。简言之,是力的发散、能量的传递与事件的发生构成“本体”,而不是某一构体化作为力、能量与事件的起源;意即物质现象的流变。而“美学式”则涉及到影像与影像事件触及到思维边界;当并非作为思维再现的影像足以启动思考时,就会出现所谓的美学事件,正是通过该类事件的发生,而足以确定某某影像的专属内容。换言之,“以非概念性、非逻辑性以及非系统性的要素或方式开启思考或分化思考”就是笔者所谓的“美学—事件”:让我们去思考非思者或说思考不可思考者;也就是回归到对于感知及感知操作的分析与思考。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本体式”或“美学式”是一种能动的表面或平面,这表面既映像自影像的平面,同时,也在启动“域外”思维时,成为独特时间出现时所形成的内在平面。
然而,基于这两个面相的新影像又会如何呈现呢?或说影像要如何才能发动这两种面相所牵系的思维动态?从电影肇始之初,伴随着现代艺术运动的加持,几乎二、三○年代的所有前卫派艺术家都谈论过“脱出自我”的“纯电影”——或说“纯影像”——只是那时候的“脱出自我”具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期待着影像足以引领人们跳脱禁锢着自身的自我,指向一种自我超越;但贝卢(Raymond Bellour)则提出了一种本体式与美学式的“纯影像”:“虚构地断绝所有滋养它的联系”。换言之,“纯”并非一种本质上的同一性,恰恰相反地,是摆脱牵系在脉络之上的同一性,“摆脱”使得影像获得了“自主性”,也自此拥有其“本体性”;同时,也在这断绝中不再通过脉络内容来加以再现,而在创作行动或呈现过程中逼近自身边界,启动“思考非思”的美学契机。于是,新影像——就本体论与美学上的特质而言——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必要撼动原有思维模式(即“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一种获得自主性的本体式生成,以及改变时空质性的美学行动。
电影的“新”与“后”
“新”不再只是由史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所说明的脉络来决定,同时也有必要考虑到感性与感知通过创作行为与思考行动——在这种脉络的影响与互动中——所挑起的反叛和逃逸。并将“新”从一种陈述的形容词格转换为动词词性,新影像也就意味着基进的创作。那么——如果接续我们所断言的新电影与当代艺术各作为创新台湾影像经验的代表——电影在这样的脉络下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而电影又跟当代艺术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在这样一种跨界的预设里,甚至,都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跨界现象的映像时,德勒兹的电影理论无疑地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看法:亦即“同(avec/with)电影的思考”过渡到“影像”的问题。换句话说,影像的需求与创新本身就是一种通过感性的“跨界”行动。为何影像具有这种几近本性使然的跨界能动呢?首先就在于影像的“可切分”、“可重组”:意即“可剪辑性”。甚至,若依循博格森与德勒兹的概念,将影像等同于感知的话,那么它本身就具有重新形塑时间的潜能,换言之,描述着时间“质性变动”的时间性就得以赋予影像一种跨越空间的“可穿透性”。最后,则是影像——如帕索里尼所言的“先于语言”的原初语言——具有无法化约的“可层叠性”:意即多重再现的叠合与质变。于是,影像就在各个不同范畴的创意(id é es)冲击中展开了它的历险。也在于影像的这种跨界特质(可剪辑性、可穿透性与可层叠性),才得以在台湾的脉络中找到新电影与当代艺术之间的联系。
如果以时代表征来看,似乎电影与“现代”艺术的渊源较它同当代艺术之间更为鲜明;因为电影从二十世纪一开始——也就是蒙太奇的出现——开启它的“艺术”历程之后,便同当时艺术圈所兴起的现代主义与前卫派密不可分:如曼·雷、杜象、雷杰等人。就如同意大利未来主义者马里内提在《费加洛》报(Figaro)所发表的一系列宣言,我们便可以见到电影跟现代主义的都会形式和现代艺术似乎就一同作为当时代的“进步象征”。电影之所以受到这些进步思潮的推举,主要就在于“电影—技术”一方面得以继“摄影蒙太奇”(photomontage)之后提供创新影像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足以支持当时“以科技理性创造新社会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在于电影的肇始就是以新技术创生新的表现形式,而并非以单纯的美学观转变或风格替换来达成,同时,其特殊的生产与展示方式开启了“大众艺术”的时代;因此,事实上,电影以其技术面与媒体面的“不纯性”和“表达艺术自身”、“以艺术评论艺术”的现代艺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而这深刻的差异,也使得电影的不纯性所指向的并非时代表征所呈现的“自然”联系,而是它同当代艺术——特别是“科技艺术”与“媒体艺术”——之间的“潜在”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艺术以科技艺术与媒体艺术为名的表现形式联系到“电影”。
事实上,目前出现的关于科技艺术与媒体艺术的论述和出版,其中不乏回溯到电影上的例子。确实,若单纯就字意上进行某种回溯而言,将科技艺术解释为科技同艺术之间的交会,那么,似乎科技艺术的源头就足以溯源到摄影或电影的肇始之初:不论依据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或是巴特(Roland Barthes)的论述,摄影与电影都因为其技术上的革新,而改变了影像的生产方式与展示形式。只是,这里的科技明显地指向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条件与生产状态,特别是“复制”的技术,一方面无法顺应科技史溯回十七世纪开始的“机械”技术(意即可运转的整体装置),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想象“科技艺术”在历史脉络中所指涉的“数字”技术(虚拟技术),跟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开始的“模拟”技术(光学技术)之间,可以用“科技”一词予以同质化。这也就是为何这些论述——除了概念上的想象与抽象化之外——都无法更进一步地厘清电影同当代艺术之间的“确切”关系,并常常忽略掉它同现代艺术之间的共时关系。因此,在科技艺术的虚构回溯中,存在着一种时序上的落差,而且这一落差就差了八十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科技艺术”也因而承担着一种超乎当代艺术所能涵括的定义与历史:无法单纯以数字技术所引发的艺术想象与事件(也就是现象的实证面向)来定义,而必须诉诸本体论的方式,通过现代科技与艺术发生互动的脉络来加以定义。可是,就实证面向来说,科技艺术跟电影之间的联系相当有限;除了所谓“后电影”(post-cin é ma)或“电影艺术”(cin é ma art)的作品中,有着较为直接可见的关系——影片作为材料或是播放形式的辩证——之外,可能就属录像艺术跟电影之间的“潜在”影响关系较为直接:这影响关系比较不是停留在媒材与形式的层面上,而是发生在“视觉”感知与“视觉”经验上的联结与呼应。若只是以实证面向来解释科技艺术或当代艺术的进展,在直观的现象上似乎显得相当明确,但大多说明这些现象的描述,却往往因为没有探究潜在联结与联结的变化,而在论述的认知与呈现上沦为事件的罗列与宣传,较难切入这些当代事件所创生出的“新感知”,也就难以捕捉这些新感知同我们之间更为细密的关系。
而这样的立论观点,表明着我们相信“新”感知的创造总是紧紧地扣连在影像(或以“视觉”为名)的历史或事件上,而不会是当下的科技事实或社会文化现象便足以充分解释这些历史转折与事件发生。所以,若电影跟科技艺术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或不可忽视的关系,那必然要论证出它们之间的“潜在”关系。在此,则企图以“后电影”定义的厘清,来作为问题的切入点。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后电影”这个可能足以给出电影与当代艺术之联系线索的指称;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定义,都仅是停留在诸如“电影之后”、“数字技术对电影进行的改造”、“用电影作为创作材料”、“与电影影像进行对话”等等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艺术现象加以特性化的“后”这一概念,除了延续以“后现代主义”为名的“不同于……”或是“在……之后”这样的相对性之外,也无法对于它同电影的确切关系进行界定。因而,似乎必要更为确切地探入“后电影”这个词项所能承载的概念内容与经验现实,从那个出现了模糊感知的边界开始,因为这个模糊感知并非乌有,只是先于当下的语言,令语言的界限呼之欲出。
让我们的思绪回到“后电影”这模糊感知的语言边界,一个属于当代的确切美学边界。“后”,在表述行动的发生来说,往往出自一种哲学意涵:一方面反对着既存的主体建构,另一方面又在时序上强调着该主体建构“之后”的转折与分化。如此来看,“后”一边强调着对于当下的一种反动(r é action),发起某种创造“当代性”的行动,可是,一边却又回到一种自然时间的描述,落入以“历史辩证”作为先决预设的“现代主义式”史观。于是,后电影的指称既来自于发生在电影之后——并不限于电影范畴内的活动、再现或展出——却又在保有或透露着电影“痕迹”的同时,不同于以往的电影经验。在暂时地厘清了“后”的可能暗示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回到电影自身系谱探究的必要;我们尝试给出几个历史性的同时也是概念性的线索,第一,事实上,电影的出现与其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895年的二十年之后)的发展:电影在经历了各种“技术”展示以及连带的“感知”惊艳、同时又以模仿简单的剧场形式作为表现形式的第一个时期之后,它在一种现代艺术与其前卫派的氛围之下,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以颠覆艺术作为艺术行动,以及艺术就是为了批判艺术等等时潮的影响之下,在德吕克(Louis Deluc)、克雷儿(Ren é Claire)、爱普斯坦(Jean Epstein)、艾森斯坦(Serge Mihailovich Eisenstein)、维托夫(Dziga Vertov)等人的论述中,也强烈地表达了对于艺术与艺术品味的反叛,并揭起返回电影与影像自身的本体论思考与美学运动,换言之,对他们来说,电影的出现就是一种“艺术之后”,同时也因为技术的革新——特别是光学显影与活动记录——揭露了本体论式的回返本身,并非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被过去直至当下所遮蔽的“未来”,一种尼采式“永恒复归”的“回返”,也作为之后结构主义时代所分化出的多种“回返”。
第二,本体论的回返自身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中,是一种令本体不可能进行主体再现或以再现作为阶层化指标的本体论运动,这在电影的发展里,紧接着就是用途的转向与新价值的建立。是一种“复制技术”、“市场经济”以及“群众政治”之后的转折,电影并非单纯地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诸如最早一批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们所期待的“大众艺术”、“真实艺术”,或是前卫派的“动态艺术”、“思维艺术”——获得新的“本体”,相反的,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现象,就是在发展新的表现形式与美学思想的同时,也变成为宣扬集体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工具”以及扩大市场占有的“消费性商品”,电影的不纯性不仅表现在其“内化”其它艺术形式的独特能力,同时也表现在艺术不再可能同政治、经济划分开来的文明特质(或说现代之后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电影创造了影像艺术,开启了影像得以进入拟像、甚至“造假”的时代,但不论在亚陶(Antonin Artaut)、皮蓝德罗(Luigi Pirandello)、本雅明、阿多诺(T.W.Adorno)、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或是巴特(Roland Barthes)那里,都充分地表达出这样的新旅程使得影像要不进入各式的“他治”(h é t é ronomie),要不就进入一种流放(exil),或是进入德勒兹所揭示的经验性先验场域——一种无法自主限定的“平滑空间”——以及贝卢所谈到的一种不断“再域化”的装置行动。
第三,电影所带有——技术造成艺术的自我批判——的历史性,以及其朝向“分化单一目的”的差异性,在数字科技的介入之后,出现了一种临时性的综合重组,使得电影在发展之初即突出的特质进入到一种“策略性的政治化场域”:即影像性、媒体性、接合性与互动性等等特质。换言之,科技的介入使得电影以着这四种特质脱离自身:若狭隘地以电影材料(胶卷与机器)以及放映方式(电影院的黑盒子)来看,电影可能就如同宋塔在电影的百年诞辰之际痛陈电影因为“爱的丧失”而已然“没落”;但若将电影视为一种影像的创生来看,那么,它以着近一百年的影像经验,进入一种极其不同的景象。因为数字摄制技术的发展,电影——并非只是影片生产的总和——所生产的影像经验,被移转到新的材料与技术上,数字化与转档改变了其创作的经济学内容;还有,场域——从电影到当代艺术——的移转,从电影院的黑盒子到使得它通过新材料获得新的媒体性的可能时,也确实地实验出了新的媒体性;这新的材料与技术的经济学与新的媒体性,使得电影能够跟他种艺术经验——如再现经验、诗学观念以及美学行动——相互接合:另一方面,也使得科技的能够进一步地改变其媒体行为,电影的影像经验不再如同过去被黏贴在银幕上,仅能透过单向投射与观众进行某种不可证的“心领神会”,而经由感应装置的操作,使得观众的想象力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影像经验,提供了互动的想象。
电影之所以衍生出后电影的转向,就在于它并没有单纯地成为数字科技的客体,没有被数字化的强大技术给完全地转译——即同质化;而且,它自身潜在的各项特质,也呼应着数字科技——这项外来的技术力量——在艺术创作、造形性与影像上的需求;再则,便是许多电影导演的跨界实践:如较早的西贝博格(Hans-J ü rgen Syberberg)、马克(Chris Marker)、高达(Jean-Luc Godard)、史诺(Micheal Snow),以及瓦达(Agn è s Varda)、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还有较近的阿巴斯(Kiarostami Abbas)与吉塔伊(Amos Gitai)等等,都以着各种影像形式或影像装置,介入到当代艺术的表现问题上,同时也作为电影影像经验的扩展与变异。这些造成美学式流变的变化又主要反映在几个面向上(当然,笔者在此无意提示任何关于这发展的任何限定,因为这项发展都仍未结束,甚至也还未被充分地厘清):一是技术的异质化,二是本体论的偏移,三是交换价值的改变,四是展示形式的多样化,五则是时间性与空间性进入另一个新的配置场域。然而,以上所提出的各种转化,都已经越来越难通过某种跨国技术或国际模式来加以界定,因为每一种变化都越细致地牵系在脉络的内容与限制上。正因为“后电影”的这些特质要能够真正实验或逼近其极端的状态,就必须回归到“在地”发生的实况;所以,后电影的另一个并非作为经验事实的重要面向,就是“土地”或“地域”的概念。“后”作为一种差异化,对于“电影”这个总括性词项进行偏移或抗拒,也就从历史诠释或纯粹理性的结构性真理辩证,移转到以“历史性”、“地域性”与“事件性”作为论证发展的主要征候,使得后电影必然朝向一种可以称之为“地理—电影”(g é o-cin é ma)。这“地理—电影”中的“地理—”至少拥有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该电影的新转折与地域性的各种脉络或造型特质息息相关;另一则是其思考模式以着空间性作为产生差异的主要依据,即使在强调着创生时间性的论调中,也必须以地域界分或打破地域界分作为描述的根据。但这种强调地域性的后电影并非国家电影,也不会是民众电影,它所创造与呈现的地域性,往往是一种尚未实存(或说是否能够实存并不作为目的)的地域性,一种尚未集聚的人民,并非停留于版图表面,也必非集体的再现,而是一种动态的乌—托邦(U-topie),一种榭贺(Ren é Sh é rer)所描绘的“空间化”:独特性的游牧散布;作品所提供的,是一种可思考与可想象的虚拟(潜在)动力。
再则,后电影的另一个转折就是“影像—电影”,也就是转向以影像作为思考课题的电影,事实上,这是对于当下电影以故事作为主要发展轴线的抗拒,但“后”电影的抗拒似乎有着一种“另寻出路”的味道:以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思考模式找到电影影像摆脱其既有发展——以故事情节和类型化影像取胜——的可能,而这可能性又不会同既有的发展进行“对质”或“取代”。影像—电影是一种电影生产体系“之外”的电影,它并不作为一种影像类型,而是一种以影像作为思考根据的电影行动。这种影像的回溯性活化(r é tro-actif)思考,重拾了前卫派对于电影中影像追求的意图,或说作为一种借口,一次次地重新厘清电影影像同他种表现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从维托夫将电影与故事对立起来,稍后爱普斯坦将这对立转化为内化的影像/故事,一直到德勒兹,以影像分类驳斥叙事的优先性。从“纯化”,经由“内化”,再进入到一种“潜在化”,都是种种影像—电影的抗争;只是,德勒兹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发展的“晶体—影像”与“造假力量”的概念,都是一种皱褶式的影像多层化,反观巴内(Matthew Barney)则是以一种撷取式的单一景象,将电影经验作为一种影像模态,利用多相位的重复性,获得电影般的“造形性”。
另外,常常同“影像—电影”的趋向有所呼应的,就是“媒材—电影”,将电影影像移置到当代艺术的创作行动与场域之中,电影影像不再直接作为作品呈现的终端,而是组成呈现的媒材,也就是电影艺术最初的界定:将电影用作为“材料”——如Doglus Golden与Kunzel。这样的挪用具有一种异常重要的当代意涵,甚至,衍生出一种潜存的,在当代艺术的讨论中还尚未被直接面对,或是过于单纯地对待:就是电影影像本身已然作为某种意指系统或现象再现,将这样自足的体系移转到一种“影像装置”的试验里,绝非只是“当作材料”如此尔尔,而是另一个影像脉络的被动介入。“媒材—电影”所界定的电影同当代艺术的关系,不似脉络性转折(地理—电影)与本体论转折(影像—电影)一般,将电影影像经验转化为一种影像思维模式来介入,比较属于“内在”(immanence)的操作。而是回归到“影像就是材料”的实际层面来处理让艺术意图“内在化”对于这些被材料化、媒材化的物材进行操作,而在作品的完成与呈现中,将电影影像的内容“脉络化”,也就是“去文本化”,同艺术创作的“设计”与“游戏”进行一种互动与互变。也因为电影影像在此并未被“模式化”或“潜在化”,而得以作为一种“实在的”影像同当代艺术所设想的影像进行对话,不同的是在一种被设计的被动态中,才容许了这样的对话——如马克与高达。
上述种种后电影的发展似乎都尝试召唤着“非电影”,也就是“摆脱电影宿命”的影像:意即电影影像的经验企图摆脱电影影像的宿命。“摆脱”意味着一个时刻的来临,但这“来临”却不同于“弥赛亚”的来临——一个永恒正义、平和与美好的来临,也就是“绝对”——而是离开现世与当下相对性平和——或说“停滞”——前往“游牧”的时刻。后电影——或许不是论述上的,而是在行动与形式上——表达了一种“非电影”的意涵,离开电影,开启电影经验的游牧,这游牧使得它面对另一个尚未被刻画的沙漠——全方位的可能性与无限的潜在性:意即当代艺术。因此,在后电影一开始以一种纯粹的意图使用“电影”时,已经造成电影与当代艺术寻获不同命运的可能,一种指向未来,让当下不再安然无恙的命运。
从新写实谈起
在将后电影的概念进行暂时的厘清之后,同时也在回到台湾当代艺术之前,先看到台湾发生于八十年代的新电影。台湾新电影的运动,事实上是继德国新电影与第三世界电影之后在全球各地掀起的影像运动,而这个全球性影像运动的源头又来自于五十年代的意大利新写实以及随之而起的法国新浪潮,若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一种“新写实”的运动。那么,在进入台湾确切的影像脉络之前,先尝试将新写实的意涵做一个整理。新写实首先就相对于战前以法国与美国为主的写实主义,这种写实主义主要转译了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与佐拉的社会写实小说精神,故事中的人物总是置身在一种社会肇因的宿命之中;社会就作为另一种使得人物产生异化的“自然”,这现代社会与工业社会造就的人造自然,令人逐渐地丧失“人性”,并在这种变化之中浮现出一种原始暴力。然而,电影在三、四十年代对于社会写实文学的改编,一方面将原本主流历史剧中王公贵族的故事移转到对于市井小民的描绘,也因为描绘的写实要求,场景与其中的对象必须回归到一种现实的“自然”,另一方面,因为单一因果关系或先决性结构关系所引致的“悲剧”,使得导演仍以棚内摄影和照明的方式,来形塑人物处境与结构性宿命。这种影片形式所蕴含的影像意义,在于影像作为“揭露”真相的接口,在当时影像感知的追求上是一种影像接口的透明度,换言之,影像必须是一种不被看到的接口,而直接地让视线穿透到“真相”上;但这影像却又因为悲剧性的营造,而使得影像在戏剧化的刻意营造下增加了厚度与不透明度,就像是一种雕塑与浮雕的光影操作。于是,大战前的现实主义便以揭露真相为名,通过感官的渲染达到一种“自动机制”的“共谋”形式:意即“入戏”与“真相”的拟像化。简单地说,写实主义用“拟像”作为揭露真相的最后呈现:通过不透明所再现的透明。
然而,同样以揭露真相作为开始的意大利新写实,却完全地朝向另一个可能的方向发展:“真实”变成为影像辩证的客体与内在动力。为何会出现新写实或说新写实的必要性呢?它的必要性出现在人们经历过大战之后,一方面在大战时,不论感官上或知觉上都有着非常不同的新经验,面对新的武器、新的政治处境、新的城市景观、新的速度、新的伤体影像、新的力量等等,另一方面,大战后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其余参战国几乎都面临着百废待举的残破家园,而在重建之际,所面对的历史记忆的矛盾、资源分配的不公、生活的艰辛以及新的政治权力的角力等等,都使得知识分子对于“现象”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和犹豫。因此,新写实首先就作为对于写实这件事情的一种辩论,就是说,现实或说现实性,成了影像的思考课题。意识到现实感来自于或说取决于影像的再现,使得现实——或说写实——就不再是一种形式风格,而是一个问题意识。现实的再现,成为电影透过影片加以辩驳的问题,而不再只是直觉性或客观性的模仿。因为,影像的存在被察觉、被思考,而挑引出真实的辩论。
所以,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它的第一项特征就是一种以“混合式”的配置,呈现出影片风格与创意的影像运动。并非像战前几个电影的先进国家,在于风格的一致性,而首先是一种影像态度,这种影像态度,也的确因为对于经验再现的追求,突显了几种特殊手法或说电影语汇的重要性与新意涵,以长镜头、固定摄影机以及断裂式跳接为着。换句话说,意大利新写实并非创出了新的形式语汇,而是使得形式语汇有了新的内涵。特别的是,这电影内涵不似战前将影像当作是一种工具——表达意念或美学的工具——而是变成窗口、变成镜子,电影语言投射着社会的环境现象,反射着观者的内在心理。语言,不再是现象的再现工具,而是现象的映射、现象得以浮现的“时空”或说“地点”。这是它作为影像运动的第二个特征,也就是影像与现象的密切关系。第三个特征,一方面因为是语汇配置的创新,另一方面因为是现象的现实性争辩,所以作者的风格与课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和差异。换言之,艺术或形式的认同不再可能,就构成了现代思想运动或是艺术运动的一个重大特色,甚至连导演自己都不再认同于运动的概略定义。这样的一种创作认同上的分裂,促生了之后对于作者的定义,也就是作者论:以个体的创作生命为指针,看待作品的价值。
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新写实的创始人——说过“事物就在那里,何必画蛇添足?”这句话奠定了新写实影像的态度,但透过《意大利之旅》,罗塞里尼发动了一次转折——像用明星,用剧情片手法等等远离新写实的手法——将新写实带得更远。事物就在那里,但在被真的看见之前,却保有更多神秘,不再沉溺于唯一真相。然而,意大利新写实的成型,除了这些意大利导演的作品之外,必须特别提到巴赞(Andr é Bazin),他的一段话“在一个已经经受过、现在仍然经受着恐怖和仇恨的世界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现实只是作为政治的象征,或者被否定,或者得到维护,在这个世界中,唯有意大利电影在它所描写的时代中,拯救着一种革命式的人道主义。”便充分地表达或建构了新写实的立场:就是将电影的美学目的投射到整个现象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则指出当时意大利电影的一个时代特质,即批判性的文化革命。
根据上述对于“新写实”的界定与说明,便可以知道为何它作为一电影潮流却得以成为影像运动,就在于它开启了影像的多重性与不确定性,并将这特质相应于“真相”与“真实”的问题,而使得电影或说影像能够以“世界的影像”与“现象的辩证”而进入到与“知识”的联系之中:影像成为“可被思考”。也就是说,影像并非给出知识的图像或说明,而是启动对于现象甚至知识的思考,作为思考的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