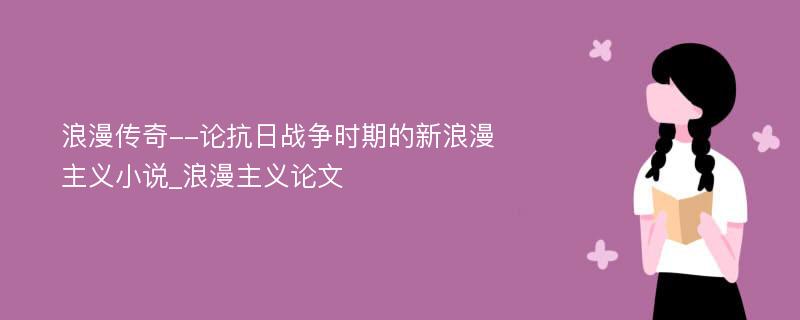
浪漫的传奇——论抗战时期的新浪漫派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浪漫派论文,传奇论文,浪漫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达到高峰后不久因队伍分化而陷入低谷,但它在低潮中继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到抗战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左翼文艺界开始重新评估浪漫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本来处于左右两大社会势力夹缝中的浪漫主义思潮拥有了较大的回旋空间;而在左翼方面率先放宽了文艺批评的标准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包含个性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又获得了反封建的意义。以此为背景,郭沫若于1936年4月接受蒲风的采访时, 重新肯定了浪漫主义,他40年代初的历史剧创作则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他自己早年诗剧的浪漫主义风格。而这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徐訏、无名氏的新浪漫派小说,这标示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又一种新的发展路向。
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的政治色彩相对地淡化。徐訏和无名氏怀着宽松的文化心态,在文艺思想上超越此前不同创作方法、不同文学思潮的界限,兼取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成分,促进了多种文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徐訏的基本文艺观点是接近创造社的,他认为“创作的一刹那,他要把他所感的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作家虽并不一定要有哲学思想,但也要靠丰富的感情与锐敏的感觉”(注:徐訏:《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文艺的自由》。转引自吴义勤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阿拉伯海的女神》中,他借人物之口说:“平常的谎语要说得像真,越像真越有人爱信,艺术的谎语要说得越假越好,越虚空才越有人爱信”,并且宣称“我愿意追求一切艺术上的空想,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不过,徐訏也受到了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意识到生活对作家的重要性,因而他又认为“伟大作家的潜能不过是‘生活’,是一组一组的生活,是直接的生活、间接的生活的混合,是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的结合”(注:徐訏:《场边文学·作家的生活与潜能》,转引自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第202页。)。他文艺思想上的这种表面矛盾, 其实质在于他所理解的“生活”,原来主要是指被人体验过、反省过、想象过的生活,因而他所“表现”的是真切的人生感受,是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化的“再现”,他“再现”的也是情感化、心灵化的东西。换言之,徐訏以他的诗人气质,强调主观的表现,在此基础上融合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因此他所遵循的主要还是浪漫主义的路线。无名氏的情形有些类似,他在《海艳》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艺术“只要超现实就行。一切离现实越远越好。现在,我只爱一点灵幻,一点轻松。这真是一种灵迹,一种北极光彩!”然而幻想也必须有一点生活的材料,所以他又在《海艳·修正版自序》中写道:“我走的不是流行的写实主义道路,但任何小说只要多少有点故事情节,就得多少参考一点写实小说艺术的手法。”(注:无名氏:《海艳》,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他的特点,就在“参考一点写实小说艺术的手法”来表达他的浪漫激情。
在浪漫主义的主调中兼容一些写实的因素,落实到创作,就把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引向了情节的传奇性。新浪漫派的“新”,即在于把浪漫主义的情感自由原则转化为讲述奇情、奇恋、奇遇,借助出奇的幻想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徐訏和无名氏虽然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但在40年代作为新浪漫派小说而备受世人瞩目的就是这种浪漫的传奇。《鬼恋》通篇鬼气森森:“我”在月夜所邂逅的黑衣女郎自称是鬼,此后一连数夜“我”与她相约在荒郊,从形而上谈到形而下。待“我”按照暗记找到她的居所时,开门的老人却说她在3年前已经染肺病死去。就这样,“我”与鬼若即若离地相恋年余,后来才得知她从前是最入世的人,做过秘密工作,暗杀敌人18次,流亡国外数年,情侣被害,现在已经看穿人世,情愿做“鬼”而不愿做人了。但若说她无情,却又有情——“我”生病数月,她暗中天天送花,到“我”病愈后才飘然离去。徐訏的许多作品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小说,都是这种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宛若眼前却又美得虚幻,恰好在似真似幻之间。不过,这类作品既超越了“五四”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把描写的重点从自我的内在世界移向了独立于“我”的现实生活,同时又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在这些作品中,“生活”基本上仅仅是作家幻想的产物。游离于现实生活的幻想,更多地是与作家的主观心愿相关的,这又使新浪漫派小说保持了与自我表现的“五四”浪漫主义的精神联系,同时也使这些作家醉心于浪漫的想象中,却与抗战时期血与火的斗争有了些隔膜——他们的作品较少正面反映抗战题材。
徐訏后来曾说:“抗战军兴,学未竞而回国,舞笔上阵,在抗敌与反奸上觉得也是国民的义务。”(注:徐訏:《徐訏全集后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不过他的“舞笔上阵”与一般作家不同,他是以浪漫传奇的风格来探索爱与人性的真谛。即使写抗战题材的《风萧萧》,其中涉及抗战内容的间谍战也仅仅作为一个背景,主要还是表现铁血之中的爱情纠缠。为了追求作品的传奇效果,他倒是在故事的言说方式上竭尽心计。在《风萧萧》中,他让“我”抱着独身主义的信仰,在白苹、海伦和梅瀛子三个光彩夺目、个性各异的女子间周旋。随着矛盾的展开,以舞女身份出现的白苹被认为是日本间谍,美方谍报人员梅瀛子要“我”去白苹那里窃取日本军部情报。“我”出于民族义愤欣然从命。经过一番曲折,双方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到头来却弄清楚白苹原来是重庆方面的间谍,于是双方联手对付日本特务。最后,白苹为获取情报而牺牲,梅瀛子为白苹报了仇,“我”则在日军的追捕之中婉拒了海伦的爱情,到大后方去从事“属于战争的、民族的”工作。洋洋40万言的小说,把言情和间谍战揉在一起,设置了一连串的鬼打墙式的迷魂阵,使读者跟着“我”如坠云里雾里,到最后才解开谜团。不过,徐訏和无名氏运用最多的还是把叙述者与主人公分开的叙述模式:“我”碰到了一个特行独立的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得知了他或她的故事,于是把这故事转叙给读者。“我”并没有在故事中扮演实际的角色,只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真正的叙述者是作品的主人公。徐訏的《幻觉》等小说就是采取这种叙述模式。这实际上便于作者利用“我”跟真正叙述者的距离产生的疑惑来大力渲染神秘的气氛,制造悬念,强化读者的阅读兴趣。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把《幻觉》的结构加以放大,也是由“我”引出奇人奇行,让真正的主人公向“我”诉说了一个令人哀绝的爱情悲剧,充满了传奇性。
徐訏、无名氏的小说,以浪漫传奇的风格荣登40年代初畅销书的榜首。这反映了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背景中,民众的阅读口味对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多人身临战乱,备尝流徙之苦,需要心灵的慰藉。新浪漫派小说适逢其时,以轻灵的幻想、缠绵的爱情故事使他们享受到了片刻的欢愉,减轻了生存的压力,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如果说,现代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呈现了反封建的狂放姿态,30年代转向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那么到40年代就分散为多种存在方式,其中新浪漫派小说的兴起代表了浪漫主义思潮从知识精英的自我表现向广大民众的阅读口味的靠拢。它适应战争的环境,淡化了自我表现的色彩,增加了通俗化的成分,获得了怡情和娱乐的功能。所谓“畅销书”,就是以传奇性为中介,兼顾了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雅俗两方面的审美要求。
新浪漫派小说,不仅缩短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而且还沟通了中西文化的联系,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探索了一条新的途径。
爱情是徐訏小说的一大主题。在他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中,女性形象总是兼有东方女子的美丽外貌和西洋女子的平等意识。如《鬼恋》中的“鬼”楚楚动人,“有一副有光的美眼,一个纯白少女的面庞”,而且知识渊博,谈吐别致。《阿拉伯海的女神》里的女巫,《吉卜赛的诱惑》里的潘蕊和罗拉,《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里的海兰和白蒂,《荒谬的英法海峡》里的培因斯,《风萧萧》中的白苹、海伦、梅瀛子,莫不是美丽温柔的仙子,同时又具有非凡的胆魄和出众的才华。男主人公则多是才子、学者、作家,常常被几个女子所包围。男女一见钟情,排除了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坠入爱河,上演了一段段奇遇故事。奇遇的背景是漂泊的旅途——“我”在阿拉伯海的轮船甲板上漫步,巧遇来无影去无踪的“女神”(《阿拉伯海的女神》);路过法国的马赛,被丘比特神箭射中(《吉布赛的诱惑》);在上海街头买一包烟,遇上冷艳逼人的“女鬼”(《鬼恋》)。一见钟情的爱情,加上人在旅途的漂泊感,构成了徐訏小说浪漫性的基础。看得出来,这种浪漫传奇中的爱情观是中西结合型的——既有中国人的希望陶醉于温柔之乡的梦想,又有西方人的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追求。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无名氏喜欢把西方爱情至上的观念和骑士式的机敏辞令嫁接到中国传统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中去,有时因刻意追求辞令的机巧,反而显得做作,失去了自然的风韵。
既然是文化的交流,就难以避免相互的冲突。当两种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时,徐訏的选择却是很独特的。《吉布赛的诱惑》写“世界第一美女中的第一美女”潘蕊从法国跟随“我”回到中国,可是语言不通,文化隔阂,就好像把热带鱼带到了北极,她日渐憔悴,“我”只得和她重回马赛。一到马赛,潘蕊当上了模特,如鱼得水,容光焕发,然而“我”却陷入了孤独和忌妒。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他们最后与吉布赛人一起,到南美的大自然去,在蓝天和白云下找到了幸福和自由。这篇小说表明,在徐訏的眼中,中西文化各有特点,重要的是找到能够超越彼此片面性、使人性得以健康发展的途径。在浪漫的爱情题材中如此开掘人性复归的主题,不仅提高了徐訏小说的文化品位,而且以他所提出的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回归自然,加强了新浪漫派小说与传统浪漫主义的精神联系。
不仅如此,新浪漫派小说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也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因素。徐訏的《荒谬的英法海峡》展现的是一幅世界大同的幻景:海盗所居住的化外之地,没有阶级,没有官僚,没有商品,没有货币,食物按需分配,劳动是尽义务,每周休息三天,生活安逸富足,当首领的也只是被众人推举出来充任差使,随时可以由别人接替。这既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乌托邦,又是中国人眼里的世外桃源和大同世界。他把这两者连同相应的具有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幻想方式,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了。
抗战时期,进步作家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文学创作向着“通俗化”、“民族化”的方向发展。新浪漫派小说顺应了这一潮流,增加了通俗化的成分,而又超越了这一潮流的保守性的一面,保持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这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鲜的作风。新浪漫派小说家这样做,首先得益于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在抗战的背景下,全国各大区域相对隔绝,解放区、国统区各主要党派又先后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立场,当局对文艺的统制因而不可能十分严密,这就扩大了作家文化选择的自由和范围,增加了整个社会对不同文学思潮的容纳能力。当然,新浪漫派小说家融合中西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最终还与其本身的条件有关。徐訏曾留学法国,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领略了西方生活的情调;无名氏也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背景。他们拥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广博的知识,因此能撇开门户之见,兼取中西之长,进行自由的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人经历和气质上存在差异,作家的创作风格必定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徐訏亲眼目睹了父母婚姻的不幸,毕生追求的是理想化的爱情。在经历了自身婚姻爱情的几多曲折后,他笔下的理想爱情大多采取了梦幻的形式,而且止于精神恋爱的阶段,又以梦醒后的幻灭而告终,给人留下几多惆怅和遐思。《鬼恋》的“女鬼”对“我”一往情深,可最终杳然离去。《荒谬的英法海峡》写青年男女可以在露露节自由宣布自己的情人,中国姑娘李羽宁突然宣布与英俊的“盗首”史密斯结婚,原来对“我”怀着爱意的培因斯却选择了她的同学彭点,个性深沉的鲁茜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我”。正当“我”晕头转向时,猛然被人推醒,原来渡轮已横过英法海峡靠了码头,有人催他出示护照,哪里有史密斯、彭点、培因斯等人的影子,不过是在轮渡上做了一场好梦罢了。理想的爱情只存在于虚幻之中,或者只留下令人伤感的回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訏对人世的失望和对爱情的浪漫想象。有趣的是作者对待这种爱情的态度,他既不讳言对异性美的欣赏,又竭力回避性的问题。他说:“在恋爱上,绝对的精神恋爱可说是一种变态,但完全是肉欲的也是一种变态,前者是神的境界,后者是兽的境界。人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所谓性美,正是灵肉一致的一种欣赏与要求。”(注:徐訏:《性美》,《徐訏全集》第10卷,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他的理想爱情显然接近神的境界——男女双方既像挚友又像恋人,只求精神上的交流和感情上的沟通,而不以结婚成家为目的。这是为了从距离上来体现精神之爱的浪漫美感,因为对爱情来说,浪漫意味着一种梦幻,一种超越了世俗事务的不实在的关系,好像水中月、镜中像,只有虚幻才能显示出美丽。但也不可否认,作者已经意识到这是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承认,男女之间的友谊不是前进到爱情,就是发展为悲剧。《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悲剧。富家小姐白蒂渴望享受完整的爱情,当她发现女仆海兰和充当精神病医生的“我”互有爱意后,重又陷入自暴自弃的病态。海兰为了成全白蒂,在献身于“我”后即自杀。这种无私伟大的精神净化了生者的心灵,使之达到了宗教般虔诚的境界。最后,白蒂皈依上帝,进了修道院;“我”到精神病院服务,把灵魂奉献给了人群。很明显,要在爱情和友谊之间作出选择时,作者倾向于止于友谊,竭力掩饰爱情,可掩饰本身似乎已经流露出他对爱情的害怕和渴望。这一矛盾正好暴露出徐訏自己以前在爱情上受过伤害而形成的心理定势,难怪他处理这类题材时总免不了价值取向上的犹豫和动摇,一般都归结到一个幻灭的结局。
无名氏写爱情传奇一开始与徐訏有点相似,但比徐訏的感伤更为沉痛。《北极风情画》中的“我”,因神经衰弱症独上华山落雁峰疗养,听一个陌生怪客讲述了一段哀伤的恋情。原来这个陌生人是韩国流亡革命者,1932年冬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城与俄罗斯少女奥蕾利亚不期而遇,坠入爱河。不久根据中俄政府协定,驻扎托木斯克城的两万官兵必须立即回国。奥蕾利亚闻讯,把一小时当一年过,以惊人的狂热享受他们分手前的4天爱情。上校回国途中得知她已经自杀, 并留下遗书要他10年后登高朝北唱一曲他们分手时唱过的《离别曲》。“我”所见到的怪客在华山落雁峰上的神秘行踪和凄厉如狼嗥的歌声,就是他10年后对这约定的履行。一朝艳遇,10年哀痛,英雄美人生死恋,一个典型的浪漫传奇(注:这种情调颇像徐訏的短篇《幻觉》。《幻觉》写一个青年画家在乡下为神秘的生命力驱动,获得一个姑娘的纯洁爱情后为她画了一幅人体写生,不几天独自离去。女孩因此发疯,被路过的尼姑收为弟子。画家无限悔恨,流浪各地寻找她的踪迹,最后发现她放火烧了庵堂,自焚而死。画家也就在那庵的对山削发为僧,每天凌晨登上峰顶等待日出,在充塞天宇的一片详和的霞光里与他幻觉中无所不在的姑娘进行心灵交流,从回忆的痛苦里体味宗教信徒皈依上帝后所享受的喜悦。但徐訏大多数浪漫传奇的结局都写得相当潇洒,显示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而写到主人公因忏悔而自己折磨自己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则只有《幻觉》一篇。)。《塔里的女人》则把这种哀痛进一步升华为一种人生哲理。罗圣提本想以自我牺牲成全黎薇的幸福,可黎薇婚后即遭遗弃。10年后,罗圣提怀着强烈的负罪感不远千里找到西康她隐埋名的小学,眼前的黎薇已经面目全非,近乎痴呆了。作品把《北极风情画》的生死界限转换成地域空间,让火热的情爱失落在遥远的边陲一角,铺排成一曲动人的浪漫悲歌。又仿佛让一个饱经忧患的衰老船夫,历经大海的变幻,风暴的袭击,困苦与挣扎,到了晚年,在最后的一刹那,睁着疲倦的老花眼,用一种猝发的奇迹式的热情,又伤感又赞叹地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于是,“我”在月夜神秘的提琴声中得到了启示:“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或许由她自己造成,或许由人所不知的力量造成!”显然,作者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归于宿命,这反映了40年代初无名氏自己独居华山一年,与高僧谈佛论道所受的影响。
徐訏和无名氏以写浪漫型的爱情而闻名,有时也对世俗型的婚姻加以嘲讽,对丑陋的人性加以拷问,对命运的无常发出感叹,在他们的浪漫传奇的风格中已经包含了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因素。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他们虽然同属于新浪漫派小说家,后来却依据各自的个性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徐訏更靠近写实主义,虽然有时也写一些带有浓郁浪漫情调的小说,如《盲恋》;或者是在写实的笔调中渗透进一点荒诞感和虚无意识。无名氏则朝着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自称代表作的《无名书》6卷,现代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虽然这些作品的现代主义色调中也仍然晃动着浪漫的光影。应当说,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受到过西方的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多种文学思潮的共时性影响,又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情况,它已经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在保持主观性、情绪化、亲近大自然等浪漫主义的基本特性的前提下,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因素。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有可能因增加故事性而向现实主义靠拢,或循着浪漫主义的注重内在表现的方向进一步深入人的潜意识而向现代主义过渡。新浪漫派小说家后来分别靠近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是作为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说明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存在,而是与其它文学思潮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