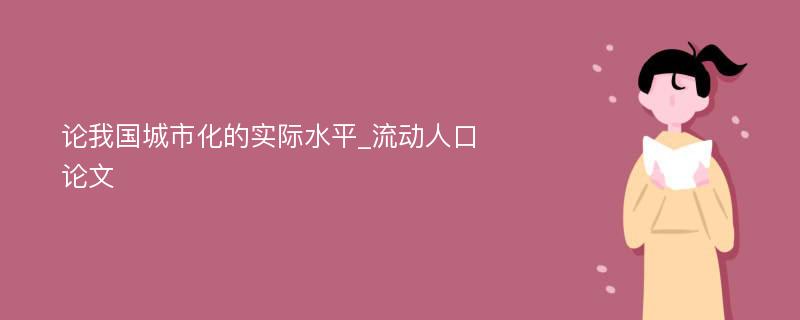
论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平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源远流长的人类史上,愈来愈闪射出璀璨的光泽。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已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追逐的目标。然而,就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以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失业、污染、犯罪为特征的“大城市病”和以侵占耕地、污染环境、成本高规模效益差为特征的“小城镇病”又扑面而来。城市化一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二难境地。继续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但是,对于是进一步加速城市化步伐,还是放慢城市化速度,人们莫衷一是。随着一些城市开始征收城市容纳费,特别是北京市以立法形式征收城市容纳费,城市的发展问题更成为争执的焦点。而要正确、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不高估、也不低估。
1、以往的认识
城市化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不同的定义。然而,无论怎样定义,人们在实际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时,基本上采用市镇人口比重这一指标。即以人口城市化水平代表城市化水平。但是,由于市镇人口的统计定义依赖于市镇行政设置,市镇行政设置又依赖于人口集中程度和非农业程度等,因此市镇和市镇人口的定义本身缺乏客观严密的基础,以至实际部门和学术界一直为市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所困扰。我国曾采用过以市镇非农业人口作为市镇人口的统计标准,也采用过以市镇地域内总人口作为市镇人口标准的方法。1984年我国实行新的市镇建制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了更好地测度城市化水平,采用了两种口径:第一口径以市镇辖区的全部人口为市镇人口,第二口径以设区的市总人口和不设区的市的街道居委会人口、镇的居委会人口作为市镇人口统计标准。人们普遍对采用非农业人口为标准的统计口径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标准低估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而1984年实行新市镇建制后,用市镇辖区的全部人口为标准的统计口径则夸大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多数人对第二口径持肯定态度,认为按这一口径计算的我国市镇人口比重26.23%,反映了我国当时人口城市化水平(乔晓春、李景武,1991;王维志,1992)。即199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26.23%。
2、实际城市化水平与流动人口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往测度城市化水平时,市镇人口的确定基本是以常住户籍为基础,而没有反映那些没有城市正式户口,却在城市居住、生活、劳动的人口,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流动人口”(事实上,真正与人口城市化有关的只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
流动人口指的是不改变常住户籍而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按流动时间分,它包括过往人口和暂住人口。过往人口指的是人户分离,在某一地临时滞留三天以内的人口。中转、出差、旅游的人中很多属过往人口。暂住人口指的是人户分离,在某地滞留三天以上的人口。外出打工、经商的人中多是暂住人口。人们通常谈论的流动人口问题,主要是针对暂住人口而言。例如,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基本是针对暂住人口,因公出差、旅游的过往人口一般不存在计划外生育问题;对人口城市化有意义的也是暂住人口。而暂住人口又包括从农村到市镇、从农村到农村、从市镇到市镇、从市镇到农村四大类。真正能够给人口城市化进程起推动作用的只是从农村到市镇的暂住人口。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有人在评估我国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时,把市镇之间的流动人口也计入其中,结果在计算人口城市化程度时重复计算了该部分人口。还有人在评估我国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时,把所有的流动人口都计算进去,以至得出的所谓“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大大高于实际。
之所以在测度城市化水平时,将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包括在内,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据估计,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约2000万,1988年大约5000万,1990年大约7000万。这种增长的势头至今仍很强劲。因此,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这一发展趋势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
第二,一些调查表明,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大多在城市从事建筑施工、行政及企事业雇工、集贸商贩、保姆、修理工等经济活动,填补了大多城市人口不愿问津的脏、苦、累、差的就业岗位,构成了城市运行、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等单位的调查表明,一些单位雇佣的外来劳动力(主要是来源于农村)占本单位职工的50%以上,少数企业离开这部分外来劳动力将无法正常运转
第三,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都需要城镇提供衣食住行。城市规划与建设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例如,上海市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上海市各级医院共有病床5万多张,其中有1/6的床位被流动人口占用(很多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由于这部分人口的存在,上海市的公共交通、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量也明显增多。因此,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时,如果不考虑这部分人的需求,必然给城市运行带来压力;而考虑这部分人的需求,则可大大减轻“大城市病”。
第四,我国74个城镇人口迁移调查和一些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都表明,流动人口中暂住时间达半年以上的占流动人口的50%左右。有的城市,如成都市1989年居留1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已达48.13%,他们实际已成为变相的常住人口。
第五,尽管对于个人来说,他们具有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但对于某个城市所有从农村来的暂住人口来说,它又具有相对稳定性。从1979年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来,除1988、1989年出现大量回流以外,大多年份,城市(尤其大城市)从农村流入的暂住人口总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正如水库的水,有进有出,但水库的水存量总保持一定容量。
总之,在衡量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时,应将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计算在内。这即有利于更好地进行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
3、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的评估
我国至今还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流动人口调查,几次规模较大的调查也仅限于市镇,特别是大城市。因此,全国流动人口数及暂住人口数、城市流动人口数及城市暂住人口数等确切数值,人们并不清楚。即使是已掌握的少量数据,也都是推测值或估计值。资料的贫乏为我们的测度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试图对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Y=r[,1]·r[,2]·r[,3]·x
其中:Y-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
x-流动人口数
r[,1]-市镇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
r[,2]-市镇流动人口中暂住人口的比重
r[,3]-市镇暂住人口中来源农村的人口比重
根据沈益民等人的测算,1990年全国大约有7000万流动人口;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迁移人口中只有20.79%是由农村或市镇迁往农村。据此,估计全国流动人口中,市镇占75%-85%;据1988年北京流动人口调查,暂住人口为90万,占流动人口69%。上海的暂住人口约67.3%。考虑到大城市虽然中转、过往人口较多,但城镇当天往返或1-3天内往返的人更多,因此,估计市镇暂住人口比大约为60%-70%之间;又据1989年上海、广州、成都、太原、郑州、吉林、哈尔滨7市流动人口调查,城市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占59.34%(假定城市与城镇这一比例相同)。据此,计算出1990年全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为1869万─2472万,实际城市化水平大约在27.89%-28.43%
以上是依据现有少量资料而提出的简便估计方法,它可以大致估算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但这种方法还存在很大局限。它把暂住人口当成了静态人口。实际上,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有部分长期居住在城市,属于静态人口;还有部分是短期居住在城市属于动态人口;对于某个城市而言,每天都有流入的动态暂住人口,也有流出的动态暂住人口,而城市每天的动态暂住人口会保持一定的存量。因此,更为精确的方法应当是在计算静态人口(如居住1年以上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基础上,再采用人口学常用的“生命表”方法计算动态暂住人口的年平均日存量。将这两部分相加,即可得到更为准确的数值,从而更好地为市政规划与建设服务。然而,由于资料所限,目前还难以采用这一方法测度,这有待于获取更为详细的流动人口调查资料后,再进行计算。
4、总结与讨论
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和市镇人口统计本身缺乏严密的客观基础,以往人们对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认识也就很不一致。大多数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因忽视了数以千万计没有城市正式户口却在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村暂住人口的存在,而低估了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少数学者虽然认识到了流动人口是城市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主张,但是却没有看到流动人口有很多类,对城市化进程有意义的只是其中的部分,以致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本文在排除了过往人口和由农村到农村、由市镇到农村、由市镇到市镇的暂住人口后,在现有资料基础上,估算了我国1990年实际城市化水平为27.89%-28.43%。然而,这只是大致的估算。暂住人口实际是“存量”概念,更好的方法应是采用生命表法。
有学者依据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余立新,1994),认为按我国1990年的人均GNP或工业化率,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达到40%。还有人建立“大国模型”(俞德鹏,1994),认为按“大国模型”我国1990年城市化水平应达到37.1%。尽管这些模型本身并不完善,例如:钱纳里模型所依据的是1950-1970年的数据,得出的是平均格局,而不是标准格局。另外,以上模型都是双变量线性或非线性模型,而城市化水平不仅仅取决于人均GNP,还取决于一国工业化程度、非农化程度等。然而,这些模型大体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事实。即使按调整后的实际水平,我国1990年的城市化水平(27.89%-28.43%)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46.1%),甚至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3%)。
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城市病”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历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城市病”。资料表明,城市化水平超过70%的国家,其“城市病”大都有明显好转。而且,造成我国“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并非城市化速度过快、农村流入城市人口过多,而是由于以往城市、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太高、城市内涵发展不够、大城市个数太少、卫星城建设缓慢、小城镇过于遍地开花等众多原因造成。所以,“城市病”并不足以过份堪忧。只要努力完善城市发展战略,通过市场发育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由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必将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