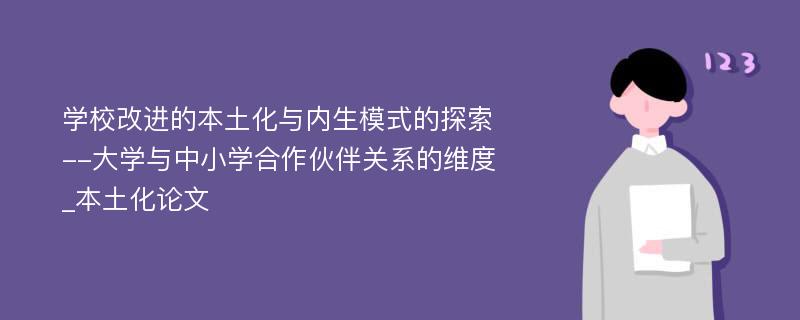
学校改进的“本土化”与内生模式探索——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伙伴关系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本土化论文,中小学论文,伙伴关系论文,内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校改进“本土化”的内涵
本文所说的学校改进的“本土化”特指大学专业人员与中小学实践者之间的一种影响与改变关系,即大学专业人员不是把从书本中或者运用头脑逻辑地得出的有关学校改进的理念、思路和具体策略“移植”到中小学实践中去,而是深入到中小学教育场域中,以“身体到场”的方式,在直面实践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时,通过与中小学实践者的对话、互动和共同思考而生成学校改进的理念、思路和具体策略,并促进中小学实践者学会反思、自主生成自己学校变革和教学改进理论的过程。
二、学校改进“本土化”的哲学立场
1.尊重学校的生命特性
尊重学校的传统、激发学校内在变革的动力是学校获得改进的前提。
2.正视学校的制度约束
学校的内外部制度环境是学校改进的基础,是学校这一生命体的生存环境。学校改进不完全是自主建构的,同时还是社会建构的。因此,大学研究者在参与中小学改进的过程中,必须学会与当地学校主管部门、社区有影响力的代表,以及学校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建立积极的战略合作关系。
3.激发“局内人”的变革动力
学校改进的主体必然是也只能是学校内部成员,任何外来的帮助只有通过“局内人”①的理解和实践才真正转变成“在原有基础上发生有意义改变”的学校改进。作为学校改进第三方②的大学研究者,不能事先就持有一种“改革至上主义”的观点,认为专家的理论或专家提出的学校改进意见一定就是好的,抵制变革一定是一件坏事。事实上,由于外部专家较少受改进后果的影响,常常倾向于推行“更为激进的变革”。[1]学校改进的“本土化”思考实际上就是从局内利益相关人的角度去思考,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学校改进计划,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发他们自己对学校改进的思考,而不是用“我们的思考”去代替“他们的思考”。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既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学会渐进地改变自己或组织的行为,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去创造有利于学校变革的新制度环境。
4.实现变革的主体完整
在学校改进实践中谁是变革的主体?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许多主体性理论都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以为只要确认了人的主体地位,他就可以自主地实现所期望的一切目标。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不完整的主体”。所谓不完整的主体,就是人不能独立地确证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需要他者,每个人的主体能力都是有限的,完整的主体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证。[2]也就是说,作为学校变革主体的实践者,自身是存在缺陷的,对理论有天然的需要。同样,作为学校变革的另一主体——大学专业人员也是不完整的,他对实践也有着内在的需求,否则任何有关学校变革的理论都不过是主观的臆想,难以获得生命力。学校改进的“本土化”就是通过两个“不完整主体”之间的互动,达成双方能力的共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改进的“本土化”就是内生化,就是学校实践者主体之实践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的过程。只有实践主体能力获得发展,学校变革才是扎根式的,才能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校改进。
三、学校改进内生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具有实践改进意向的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关系中,又存在两种基本的实践样态:一是专家理论应用式,是按专家给出的方案、指导和示范执行的实践改进;二是学校内部生长式,是在双方讨论、对话与沟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实践改进。
与专家理论应用模式相比,学校内部生长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在实践中生成理论
在专家理论应用模式中,专家的理论准备非常充分,对学校改进的影响很大,通过专家与中小学实践者的交流、互动和生成,不仅使专家的理论得以丰满完善,还使学校的自我反思能力和实践能力得以显著提升。但在学校内部生长模式中,大学研究者的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通过对学校的认真研究,从学校内部生发出符合学校历史传统和生命特征、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学校自己的理论”。
2.以学校需求为驱动力
在专家理论应用模式中,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大多数是以“专家的课题”为载体推动的,中小学是以项目实验学校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在合作的根本价值取向上,学校改进的实践运作是为了完成研究项目的需要而展开的。但在学校内部生长模式中,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大多是以“学校的需求”为载体推动的,由于各个学校对大学研究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对大学研究者的挑战是巨大的,他们经常会在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问题和领域中不断开展研究,并运用自己的思考形成对学校特色化办学理念的新认识,然后再与学校中的人员进行互动交流。由于是以学校需求为中心的,所以思想的交流会激发更大的研究和思考空间,学校人员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非常高。
3.大学专业人员的服务身份
在专家理论应用模式中,大学研究者在学校改进过程中是以“专家”的姿态出现的,专家在学校场域中的思想、看法和言论等常常会给实践者以较大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当专家的思想超越了学校的现实情境性、学校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学校受限的制度环境时,很可能就会引发学校内部的紧张。但在学校内部生长模式中,大学研究者多以“服务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更像是一个“雇员”,在为学校提出的任务而努力工作。但他们又不是“简单服从的雇员”,而是“有思想的雇员”,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而深刻的研究而赢得尊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诚实地向学校人员承认现在他们可能并不具备某些所需要的知识,但却承诺可以和学校人员一起共同努力,发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共同探索和对话的过程,不仅让学校实践者学会如何研究、如何思考,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们自主改进与发展的信心、动力和能力。
4.以学校发展规划为切入口
在专家理论应用模式中,学校改进所涉及的内容常常受课题设定边界的限制,或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或关注课堂教学或班团队会建设,或关注学校管理等,而对学校发展进行整体性规划的不多,因此学校改进多表现为部分性而非整体性,没有凸显学校作为一个生命体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整体性特征。但在学校内部生长模式中,学校改进计划常常与学校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从整体上谋划学校的改进与成长。因此,从改进的内容上看,既涉及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思路、办学特色的整体规划,还涉及学校中的德育、课堂教学、班团队活动、校本课程开发、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管理、学校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生式学校改进是全员参与的改进,是激发学校成员内在动力的改进,是让学校成员的内隐概念、心智模式和自我惯习发生渐进变化的学校改进,是“扎根式”的学校改进。
5.让每所学校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专家理论应用模式中,由于以“专家的课题”为载体推动,常常使所有参与课题研究的实验学校在总体上形成大致相同或基本相似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尽管专家及其团队成员并非不想尊重实践者的意志,但主流意识中的“专家引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实践者对专家的尊重,而不是对学校自我传统的尊重。但在学校内部生长模式中,由于以“学校的需求”为载体推动,每一所项目学校都可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办学思想和理念,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学校,而不是专家的学校,我们更像自己而不是别人”。校长及学校原有“不成熟”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会在互动中逐渐成熟进来,校长也逐步成长为专家型校长、教育家型校长,教师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教育家型教师,大学专业人员及其团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学校改进领域的“专家”。
四、大学专业人员在内生型学校改进中的作用
1.让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心智模式“亮相”
在内生型学校改进中,每个实践者都持有一套关于教育的信念和假设体系,有一套自己思考问题的心智模式,这些信念假设体系和心智模式往往是以内隐的方式存在的,很多情况下实践者并不知晓它的存在。内隐信念或心智模式常常被默默地保持着,不仅打造着实践者的教育现实,还规制着实践者的理论视野。大学专业人员与中小学实践者对话时,经常会追问“你是不是相信……”、“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吗”、“你理解你的学生吗”等等问题,通过追问实践者的思维出场,也可能使实践者的思维进入一种混乱状态,而正是这种混乱状态使实践者的重新思考成为可能,进而从自我束缚的信念和心智中解放出来,学会理论地思考、创新地工作。
2.让实践者的实践发生“第二序改变”
实践者并不是不想让自己的实践发生有意义的改变。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实践者越是积极地改变其结果就越是不变。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实践者进行的大多是第一序变革(first-order change)。所谓第一序变革是在某一系统内所发生的变革,是一种具有可逆性的变革,其结果是系统中成员发生变化而系统本身不变。如果要使实践发生真正有意义的改变,就必须进行第二序变革(second-order change),即变革系统本身而不是系统中的成员,它是一种逻辑跳跃的不可逆的变革。[3]从性质上看,第一序变革是在现有框架内的调整,不需要改变既定的哲学认知和游戏规则,因此这种变革不需要新的学习。而第二序变革则是突破常规和原有框架的改变,需要改变原有的哲学认知和游戏规则,所以这种变革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大学专业人员与实践者的对话为突破常规进行实践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3.让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发生蜕变
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合作一方面使实践者获得成长与发展、使学校达成改进与变革,另一方面大学专业人员也在合作中实现自身对学校变革理论认识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结构化的从书本到书本或者从国外到国内的文字转换和思想搬运,而是在实践的坚实基础上通过扎实的研究而获得的超越,也可以说是一种内生的和本土化的理论认识。在学校“由卵到蝶”的成长和蜕变过程中,大学专业人员也可以实现自身的“蝶变”。
注释:
①局内人中由于利益关系、价值取向等的差异经常会出现分化,学校变革需要发现一些积极的变革支持者,以“保旧立新”的方式在小范围内展开试验,一旦试验成功再大面积推广。
②实践中,有多方力量直接参与学校变革与改进。如果把学校自身看作是第一方,把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看作是第二方的话,那么大学研究者则可以看作是第三方。
